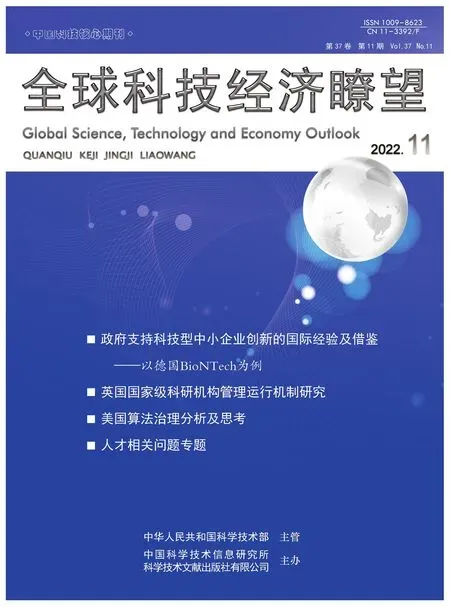中美卫生健康研究合作的机会与挑战
2022-03-13范恺
范 恺
(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北京 100190)
加强卫生健康研发,提高人民健康水平,不仅符合本国人民的利益,也符合全人类的共同利益,卫生健康日益成为国际社会交流与合作的重要基础。中美作为全球最大的两个经济体,虽国情不同,但双方卫生健康合作空间广阔,共同话题很多,对维护全球卫生安全、促进人类健康发展具有重大意义。然而在过去的几年,贸易、关税及其他经济和安全问题导致中美关系紧张,使得两国在卫生健康各领域合作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因此,有必要从历史角度和美方现实需求出发,针对双方合作开展卫生健康研究的机会和挑战进行剖析,寻找具有共同利益的重点合作主题,并为重振中美卫生健康学术交流与合作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1 中美卫生健康研究合作史
中美两国在卫生和医学方面的合作关系始于1980年初,当时美国政府成立了一个卫生领导小组访问中国,成员包括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CDC)的代表、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院长以及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HHS)助理部长等,目的是促进在公共卫生和卫生服务研究方面的合作。该小组在中国相关政府部门及中国科学院院士的支持下,迅速促成了中美之间的实质性合作,例如在学术研究方面,《美国公共卫生杂志》关于中国公共卫生的增刊发表了大量中美学者共同撰写的论文[1]。
在接下来的40年里,中美卫生研究机构之间的联系蓬勃发展。20世纪90年代,中美在叶酸预防神经管缺陷合作方面取得了里程碑式的发现,并为美国强制性叶酸强化政策提供了证据基础;2002年3月,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与新成立的中国疾控中心签署了谅解备忘录,后帮助中国建立了现场流行病学培训和结核病预防控制合作等项目,在中国应对重症急性呼吸综合征(SARS)冠状病毒、禽流感和新冠肺炎等新发传染病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和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于2010年签署了《生物与医学研究合作谅解备忘录》,双方在生物医学基础和应用研究领域的交流合作频繁。即使在双边关系恶化的情况下,双方也一直在合作鼓励生物医学研究;2016年9月,中国科学技术部副部长徐南平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与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院长柯林斯举行中美卫生科技合作双边会议,并与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常务副部长维克菲尔德签署卫生科学合作谅解备忘录,确定了两国卫生科技合作的优先领域和工作机制。
非官方机构也逐渐在中美卫生健康交流与合作中发挥重要作用。多年来,中国医学委员会、医科大学等同美国相关机构合作,培养医疗保健专业人员,发展中国在全球卫生政策和卫生系统科学方面的能力;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直接或间接通过埃默里全球健康研究院、决心拯救生命组织等机构,资助在中国的研究活动,以促进中国健康事业的发展,并利用中国的制造能力降低创新成本,增加医疗创新产品供给,造福更多有需要的人;1990年,包括中美在内的6个国家的20个科学中心合作进行人类基因组测序;耶鲁大学和哈佛大学在健康和医学方面也与中国同行保持了长期的合作关系。
2 美国卫生健康国际研究合作需求
2.1 科研院所
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是美国最高水平的生物学、医学与行为学研究机构,也是拥有最多科研预算的非国防研发部门,下设21个研究所和6个中心。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下属的部分重点研究所,如国家过敏和传染病研究所(NIAID)、国家精神卫生研究所(NIMH)、国家癌症研究所(NCI)等,资助了许多本研究所科研领域内的国际合作项目,合作对象国主要包括加拿大、欧盟、英国以及部分非洲国家。2021财年,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共资助了美国以外66个国家和地区科研机构申请的704个项目,其中南非(115项)、加拿大(100项)最多;中国有6个项目获得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资助,资助总额约288万美元,受资助单位包括中国医科大学、复旦大学、北京大学等[2]。
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下属的弗戈蒂国际中心(FIC)是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开展全球卫生和国际科技合作的核心,帮助其推动全球卫生研究合作布局,发展与国际合作伙伴的关系,并作为美国政府内部机构参与其他国家和国际组织的国际卫生研究合作计划。弗戈蒂国际中心致力于创建可对紧迫卫生需求做出迅速反应的全球研究网络;资助美国生物医学研究机构、大学和企业等与其他国家开展针对艾滋病、脑部疾病、癌症、中风和心血管等疾病的研究合作,建立长期合作关系;为全球合作伙伴提供科学研究和培训机会,加强双方研究人员的交流。通过这些合作,美国医疗技术和水平可以从全球健康研究的科学突破中受益,并使美国保持其在生物医学领域的全球竞争力,始终处于相关科学发现的前沿。
弗戈蒂国际中心近几年来的国际合作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资助全球健康前沿研究,使美国和其他国家的科研人员能够为复杂的全球健康挑战找到解决方案,以减轻疾病负担、促进健康并延长人的寿命;二是建立一个广泛的全球卫生研究人员合作网络,开展相关合作研究和培训,以应对新发传染病、日益严重的非传染性疾病和环境健康等广泛的紧急卫生需求,例如研究新冠病毒的传播模式、基因组学、干预措施的有效性以及新冠引起的严重心理健康问题,对研究人员进行流行病学、生物信息学、分子生物学、基因组学、系统建模培训以应对当前和未来的大流行病,关注野火、飓风、空气污染和其他自然灾害对健康的影响;三是对中、低收入国家进行医疗卫生援助,探索在资源匮乏环境中提高医学研究和服务水平,减少全球区域、经济、性别、文化等不同带来的健康差异,以帮助美国实现健康公平;四是建设和强化联合研究能力并在全球范围内帮助培养一批持续取得重大科学进步、推动卫生政策和临床实践发展的科学家,重点领域包括艾滋病、全球传染病、人体伤害和心理创伤以及研究伦理等,为全球卫生领域的未来发现和进步奠定基础[3]。2021财年,弗戈蒂国际中心支持中国国家艾滋病防控中心开展艾滋病研究、监督和伦理审查项目,资助经费9.9万美元。
2022年,弗戈蒂国际中心将继续充分资助全球科学家的联合研究项目和人才网络,通过跨学科和多学科方法,利用创新和新兴技术,加强关键领域的研究能力,以应对新出现的卫生威胁和全球健康挑战[4]。拟新增的国际科技合作项目包括利用数据科学促进医学发现和创新,开发最紧迫的临床和公共卫生问题解决方案;研究艾滋病和非传染性疾病之间的相互作用,支持具有不同专业知识的研究团队提出新的研究方向并开发预防和治疗的新方法,合作对象将以中、低收入国家,尤其是非洲国家为主。
2.2 企业
美国的医药健康企业,特别是大型跨国制药企业通过在全球范围内设立研发中心,有效利用当地科研劳动力,从而实现不同区域内的研发生产一体化,尤其注重开拓药物新兴市场。美国医药企业研发中心向外扩展遵循等级扩散原则,先是在发达国家设立研发中心,再向发展中国家较发达地区进行扩散,最后将这些资源进行整合并逐步网络化。比如,礼来公司作为全球十大制药企业之一,研发发展战略从一开始的自主研发模式逐渐转向合作研发模式。为了从全球范围内获得创新资源与技术,分散创新风险,降低创新成本,提高创新速度和提升企业知识识别、知识获取以及知识应用嫁接的能力,其与国际合作伙伴开展了多种形式、不同层次的合作。礼来公司依照其全球研发扩张战略,研发合作先是扩散到发达国家,例如加拿大、英国、日本、新加坡和西班牙等,然后再向中国、印度等新兴市场拓展。
从美国医药健康企业聚焦的国际合作研发领域来看,癌症相关项目一马当先,例如强生公司与其中国合作伙伴传奇生物开发了一种治疗白细胞癌的疗法。紧随其后的是神经性和感染性疾病药物合作项目,例如渤健与日本卫材制药联合研发的修正阿尔茨海默症发生过程的药物Aduhelm,可延缓疾病进展;辉瑞与德国BioNTech合作研发的新冠疫苗Comirnaty,成为全球主要接种的新冠预防疫苗产品之一。此外,基因疗法也逐渐成为合作研发热门,例如BioMarin制药公司与中国九天生物达成为期数年的全球战略合作,共同研究和开发基于腺相关病毒的新型基因疗法用于治疗遗传性心血管疾病;Code Biotherapeutics公司与日本武田联合达成合作协议,利用靶向非病毒基因药物递送平台,设计和开发用于罕见病适应症的基因疗法。
3 中美卫生健康研究合作的机会
3.1 新冠疫苗和药物
鉴于目前全球在获得新冠疫苗和药物方面存在巨大的国家和地区性差异,助长了新变种的出现和传播,从而延长大流行,因此增加新冠疫苗和药物的全球供应符合中美的利益。
中美是新冠疫苗最主要的生产国和出口国之一,美国拥有生产高效疫苗的mRNA、重组蛋白等技术,而中国有能力大规模生产更多疫苗并以高效的方式进行运输和分发。美国可以支持与中国自愿共享mRNA疫苗技术或许可中国疫苗制造商大规模生产mRNA疫苗,以满足全球对疫苗的需求,例如模仿德国BioNTech和中国复星医药集团在上海建立合资企业生产mRNA疫苗。一些处于临床后期的中国mRNA疫苗也可以在美国同行的支持下开展国际多中心临床试验,例如借助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的新冠临床试验网络(COVPN)。
中美还可以寻求在治疗药物方面进行合作,以减轻新冠症状,降低重症率和死亡率。中国的清华大学与腾盛博药研发的新冠抗体组合疗效出众,美国的小分子口服药如默沙东的莫努匹韦、辉瑞的帕西洛韦等给药更加便捷,双方可开展优势互补的研发合作。此外,中国仿制药的技术储备和能力也有助于提高新冠药物的全球供给。
3.2 公共卫生基础建设
新冠大流行突显了中美在公共卫生基础设施方面的合作潜力。中国曾在美国的帮助下,强化了医学科学和医疗基础设施的建设,对中国成功在短期内控制住新冠病毒的传播并一直保持极低感染率的帮助很大;而美国是新冠大流行前全球健康安全指数得分最高的国家之一,但它在应对新冠方面表现很差,运行不畅、结构支离破碎等因素阻碍了美国公共卫生基础设施有效缓解危机的能力[5]。
因此,中美双方可借鉴对方应对卫生危机的经验,通过合作改善基础设施,更好地促进临时医疗设施的建设,增强研究和共享生物样本和数据,以及监测传染病的传播;两国科研人员可合作验证病毒基因组序列并在疫情暴发初期更好地追踪病原体的进化;鉴于人畜共患病对人类的持续威胁,可就野生动物监测形成合作。此外,双方科学家和卫生专家可开展学术交流,分享大规模检测、密接者追踪、隔离和封锁措施、提高疫苗接种率等疫情防控经验。
3.3 生物安全
新发和再发传染病、生物恐怖、生物入侵、生物实验室事故,以及由生物技术发展产生的风险等,威胁着全球的生物安全,中美在此领域存在利益交集。例如基因编辑、合成生物学等先进生物技术一方面有助于治疗慢性疾病和开发抗旱作物,另一方面也可能导致危险的新病毒、人类基因改造,甚至生物恐怖主义。这些潜在危险的生物技术滥用几乎可以在任何地方进行,相关风险和威胁却能产生溢出效应,因此所有国家都需要制定和执行生物安全规则[6]。
中美在全球生物安全方面扮演着特别重要的角色,《中华人民共和国生物安全法》是世界上最严格的生物安全法律法规之一,美国则通过制定《国家生物防御战略》《国家卫生安全战略》《全球卫生安全战略》等,形成生物安全战略体系。基于体细胞编辑的基因治疗试验正在美国和中国大量进行,两国科研人员正在就建立相关规则和规范、管控生物技术风险进行对话与合作。此外,两国潜在的生物安全合作还包括共享与生物安全相关的样本、遗传材料和数据;研究针对生物安全事故或生物恐怖袭击的医疗对策,有关医疗、公共卫生系统如何应对新型人畜共患病或潜在生物安全事故的技术和方案;加强全球生物安全治理,制定有关双重用途研究的行为准则,防止生物技术的事故、滥用和误用。
3.4 生物医药
与其他高技术产业相比,生物医药技术的进步在更大程度上依赖知识网络和跨国合作,大量科学和技术创新研究表明,生物医药研究人员与全球多个国家的相关企业和机构合作显著提高其工作质量,其中,中美合作的贡献尤为突出。例如为辉瑞、莫德纳mRNA疫苗精确设计提供重要结构生物学基础的稳定新冠病毒刺突蛋白的技术,由清华大学博士王年爽在得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与其美国同事共同研发[7]。
即使在商业化的生物医药技术领域,中美更多的也是互补而不是竞争,例如中国的百济神州、博雅辑因,美国的安进、默沙东等本质上是全球化的生物医药技术企业,其采用跨国商业模式,充分利用中美生物医药技术生态系统截然不同的优势促进自身发展。美国生物医药企业利用中国庞大的患者群体进行时间和成本效益高的临床试验,为美国监管机构的审批提供信息支持;中国企业开发的抗癌药物以更低价格为美国患者提供新的治疗选择;中美两国的生物医药企业都定期授权彼此的技术和药物,作为其技术开发和营销战略的一部分;一些企业的首席执行官和科学顾问委员会也常常由在美国和中国的经验丰富的专家组成。
中美面临的共同卫生健康挑战,为双方生物医药合作提供了潜在的机会,包括两国人口老龄化带来的抗衰老技术和老龄化疾病治疗需求;全球环境退化、气候变化、能源危机等对健康的影响和应对;新冠肺炎、艾滋病、SARS、埃博拉病毒病、朊毒体病、中东呼吸综合征(MERS)、甲型H1N1流感、寨卡病毒病等新发、突发传染病;非传染性疾病及其风险因素,例如心脏病和中风、精神健康和药物滥用、糖尿病和饮食/营养摄入、关节炎和体育活动等。
4 中美卫生健康研究合作的挑战
中美卫生健康研究合作的挑战主要来自政治层面,尤其是美国政治阶层强推的“中美科技脱钩”,严重损害了两国正常的学术交流与合作。一是对华科技政策日渐强硬。拜登政府继承了特朗普政府对华科技政策基本思路,将科技竞争视为中美两国博弈的核心要素,遏制中国科技发展是其政策主线,试图全面切断与中国的科技合作。例如美国国会紧锣密鼓寻求通过的《美国创新与竞争法案》,包含众多围堵中国科技发展的具体法案,更以组建“科技同盟”的形式构建新科技霸权,利用法律规则的制定和解释全面制衡甚至孤立中国。二是反华政客从中作梗。每逢选举,对华不友好、大打“遏华”牌是美政客捞取政治资本的惯用伎俩,特别是随着美国中期选举临近,密集出现各类敌视中国的法案,其中不少涉及卫生健康领域。例如佛罗里达州共和党参议员马尔科·卢比奥(Marco Rubio)提出《基因组数据安全法案》,该法案将禁止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资助与中国有关联的实体[8];阿肯色州共和党参议员汤姆·科顿(Tom Cotton)和威斯康星州众议员迈克·加拉格尔(Mike Gallagher)呼吁将中国生物技术企业列入“黑名单”,抹黑这些企业出于邪恶目的收集美国公民的生物医学信息。三是实施对华先进技术管控与制裁。拜登政府认为中国已经将基因组学等“危险技术”本土化,并将利用其实力、规模和体量加速美国及其盟国的“产业消亡”,因此其广泛借助其国内和多边技术管控工具对华实施技术封锁,以确保本国在生物技术等领域的主导地位与绝对优势。例如美国商务部工业安全局将药明生物等生物医药企业列入“未经核实名单”(UVL);美国证交所将科兴生物等17家医药健康企业列入“预摘牌名单”。四是严格限制中美人才间科研学术交流。例如《美国2022年芯片和科学法》规定,禁止联邦科研人员参与以中国为首的外国政府人才招募计划,禁止中国参加相关资助项目,强制要求国家科学基金会报告对中国研究人员的财政支持情况;还有美国司法部2018年启动的以维护国家安全为由,企图切断中美两国间正常科技交流的“中国行动计划”,直接影响了中美科技人才交流和人文交流的频率和密度,引发了科技领域的“寒蝉效应”,大大降低了中美科技人才交流的积极性。该计划于2022年3月被美国司法部叫停,却是“虽停未止”,靠其新推出的“对抗民族国家威胁战略”,将原版“中国行动计划”内容纳入其中,换一种更为隐蔽的方式继续对华进行人才科研学术交流限制,使中美开展技术交流合作仍面临法律风险。
5 相关建议
综上分析,尽管中美在卫生健康领域存在广泛的利益交集,但由于美国政治层面的阻挠,仅靠中国单方面合作意愿,也难以扭转中美卫生健康研究合作的消极发展趋势。对此,提出建议如下:
(1)以应对新冠肺炎疫情为抓手,积极开展卫生健康科研交流合作。新冠肺炎疫情仍然是当前全人类必须要克服和跨越的高峰,给予中美开展科研交流合作不可多得的良机。可在公共卫生、疫苗及药物研发、康复技术、心理调适、联防联控等领域,积极倡导与美国的交流合作,推动联合研究项目合作和人才交流。此外,还应主动作为,牵头推动生物医药、环境健康等大科学计划、大工程,吸引美方参加,应对全球共同的挑战,深化国际交流合作。
(2)区分“低敏感区”和“高敏感区”科技,排除合作顾虑。例如将基因编辑、高危险性病原体等触及美国国家安全敏感神经的研究划入“高敏感区”;将癌症、糖尿病、心血管疾病、老龄化疾病等治疗划入“低敏感区”。中国可以尝试与美国在“高敏感区”边界展开技术性探讨,力争就“高敏感区”的范围达成共识,从而为“低敏感区”的研究合作提供预期的环境。
(3)充分发挥民间外交和沟通渠道,推进全方位交流。采取更为灵活的方式方法,通过民间投资机构、海外运作机构参与中美卫生健康科技合作;拓展包括中美智库、研究机构、高校、企业等在内的多方对话渠道,运用好近年来中国成功举办的、受到全球广泛关注的国际性大型经贸交流活动、会展等平台载体,如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中国国际工业博览会、中国国际高新技术成果交易会等,开展形式多样的卫生健康科技信息宣传发布、产品展示、成果交易、人才交流,引起美国的交流合作兴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