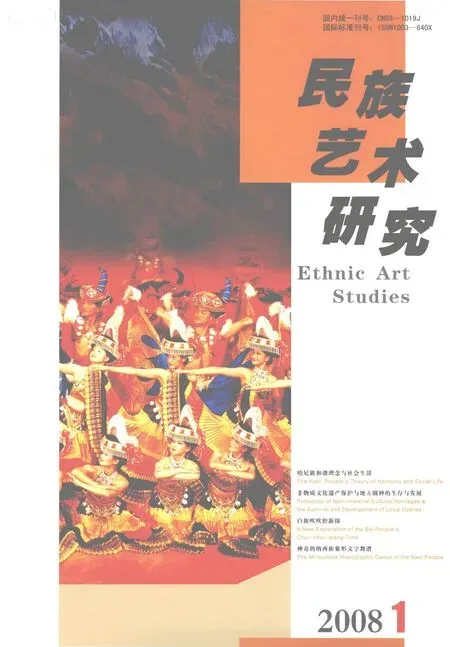汉画神仙世界的理念设定与形态构建研究
2022-03-10程万里
程万里
汉朝建立之后,由于长期的战争,导致社会经济衰败、民不聊生,急需休养生息、改善民众生活,因此汉代早期的统治阶层以“无为而治”的黄老思想作为管理的政策与理念。这一理念的推行,导致神仙思想在此时期获得极大发展,并影响了整个两汉时期。成仙、长生不老成为其时社会各个阶层的梦想,成为其终身追求的梦幻境界,并由此演化出重享乐、求长生的本土信仰。整个汉代,无数表达神仙思想的诗文歌赋,以及丹药修仙等行为记载不胜枚举,在社会中风靡一时,并延展到死后世界的幻化,造就视死如生的丧葬信仰传统,描绘着彼岸的天堂乐土,为后世留下诸多了解汉代文化的重要视觉图像。
一、归宿与彼岸
《楚辞·远游》曰:“贵真人之沐德兮,美往世之登仙。”①[宋]洪兴祖:《楚辞补注》,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64页。可见,其时, “神”与“仙”并非相同概念,也无太大关联。传统解释中,“神”是先民对待无法解释的现象与事物的敬畏与恐惧,而尊其曰“神”;“仙”是对“长生不老”的心理追求,起源于战国时期。②关于仙的起源,学者看法有分歧。一种认为产生于本土,见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许地山《中国道教史》;另一种认为是外来观念影响下产生,见陈寅恪《天师道与滨海地域之关系》、闻一多《神仙考》。东汉许慎《说文解字》云:“神是天神,是‘引出万物者也’。从示,申声。”③[汉]许慎:《说文解字》,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7页。又解释“示”云:“天垂象,见吉凶,所以示人也。从二、三垂,日月星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示神事也。”④[清]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2页。对“仙”的解释则是:“屳,人在山上皃,从人山。”⑤[清]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383页。“仙”又作“僊”,解“僊”曰:“僊,长生僊去。”①[清]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383页。[汉]董仲舒:《春秋繁露》,载[明]程荣纂辑《汉魏丛书》,吉林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45页。《释名·释长幼》解“仙”曰:“老而不死曰仙,仙,迁也,迁入山也。故制其字,人旁作山也。”②[汉]刘熙:《释名》,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第150页。对比两字,一从“示”,一从“人”,二者的分别是相当明显的,即前者属于自然,非人力可及;而后者则属于人事,是人经过追求能够达到的境界。至汉代,“神”与“仙”的界限日趋模糊。《史记·封禅书》云:“公孙卿曰:‘仙人可见,而上往常遽,以故不见。今陛下可为观为缑城,置脯枣,神人宜可致也。’”③[汉]司马迁:《史记》,[宋]裴駰集解、[唐]司马贞索隐、[唐]张守节正义。中华书局,1972年版,第1400页。可见在西汉武帝时期, “神”“仙”已混用为一。而汉武帝的求仙实践对神仙思想的传播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并因之产生了深远的社会影响。实际上,神仙境界不仅被视为是现实世界的终极境界,同样也成为亡者最为理想的归宿。
死亡是人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死亡打破了人们的正常生活秩序和持续状态,先民们无法理解生与死的分别,认为死亡不过是由此到彼的关卡。④参见李虹《死与重生:汉代墓葬信仰研究》,山东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1年,第40页。古人为了克服死的困扰就对丧葬空间进行别致而富有意味的装饰与营造,“不仅在墓室的形制和结构上模仿现实中的房屋,而且在随葬品方面也尽量做到应有尽有,凡是生人所用器具、物品无不可以纳入墓中”。⑤王仲殊:《汉代考古学概说》,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97页。它提供了一条信息,那就是死亡并不意味着人生命的终结,而是生命在另一个世界的延续,对仙界无数的描绘无不传达着墓主对超升仙界的渴求。⑥参见李发林《汉画考释和研究》,中国文联出版社,2000年版,第64—65页。
升仙之路并非唯一,无论是墓室画像或者是祠堂画像均有大量的车马出行图,旨在反映墓主(祠主)接受后人的供奉与祭祀后,踏上对升仙彼岸探寻的道路;也有吉祥瑞兽,以及张着翅膀的羽人,以及神话世界中的西王母、东王公的接引图像描绘与刻画。早在六千年前的墓室中已经出现了升天景象。⑦参见冯时《中国天文考古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407页。河南濮阳西水坡遗址发现的一组摆塑蚌图,⑧参见濮阳西水坡遗址考古队《1988年河南濮阳西水坡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89年第2期,第1059页。画面人、龙、虎等图形。龙、虎、人皆以蚌壳摆放而成,形象塑造较为粗糙,有着明显的臆造夸张及动态效果,人骑龙身之上,似有帛画《人物御龙图》《人物龙凤图》的形态,可以解释为升仙图像,但其周边蚌壳等其他形象有的遭受破坏,其组合的内涵,还需要进一步探究与解析,但其内在含义确实一目了然,其对彼岸的追求,明确而直白。
二、法天象地
古代先民们的理念中,是“天”在运行世界。孔子《论语·阳货》曰:“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⑨刘宝楠:《论语正义》,河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79页。在先秦两汉时期,“天”虽仍保持着宇宙的本性,但已成为宇宙万物和万物的抽象与具体本质的最高统治者,“天道”,一切事物衍变的源泉。葛兆光《中国思想史》云:“汉代人们普遍相信,宇宙时空由绝对中心、阴阳两极与五种基本因素构成了完美而和谐的秩序,这种秩序是一切合理性的基本依据,同时它的背后又有一种神秘力量的支持。”○10葛兆光:《七世纪前中国的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中国思想史·第一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70页。然而,武帝的“独尊儒学”将天人间的模糊关系和天命思想推向了极致,升华到了理论的高度。《春秋繁露·顺命》云:“天者,万物之祖,万物非天不生。独阴不生,独阳不生,阴阳与天地参而后生。”○1[清]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383页。[汉]董仲舒:《春秋繁露》,载[明]程荣纂辑《汉魏丛书》,吉林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45页。《春秋繁露·王道通三》云:“天覆育万物,既化而生之,有养而成之,事功无已,终而复始。”○12[汉]董仲舒:《春秋繁露》,载[明]程荣纂辑《汉魏丛书》,吉林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32页。天是世间万物的根本,也是世界的生存之道。在现实社会生活中,人类不仅可以依靠理性思维的存在,在某种程度上还需要得到上天的支持和关心。因此,人的生理结构、好恶、社会政治秩序、伦理道德,都来自“天道”,天下人都必须“法天而行”。曾侯乙墓66号漆木衣箱盖顶所绘图像,一方面,漆木手提箱顶部的画作是古人观察宇宙后所获得知识的形象记录,另一方面也可以看作是天穹的象征。这样,拱形的盖子象征着天空,长方形的身体代表着大地。不难得出结论,漆木衣箱的结构很可能被赋予了宇宙的概念。它们的出现导致人们对天空的认识从平面模拟发展到三维模拟,甚至导致了后汉穹顶墓葬的诞生与普及。
在中国的墓葬中往往会存在一种宇宙的象征物,其特点是墓葬建筑及其画像的内容和布局充分融合了汉人的生死观念和宇宙观。这里的宇宙观主要是指以汉人的“天圆地方”为基础对宇宙的不同划分隅的理解。因此,汉代墓葬的典型造型是上圆下方,而较大、较复杂的墓葬往往建成拱形穹顶。而墓葬图像中也大量可见用几何形状的“圆”和“方”或者“圆”和“方”的器物来直接对应或者比拟天与地。如山东嘉祥宋山1号小祠堂中的周公辅成王图像,①参见嘉祥县武氏祠文管所《山东嘉祥宋山发现汉画像石》,《文物》1979年第9期,第1页。成王戴着山形冠立在方形几上,左方有一人手持一个曲柄伞盖罩在成王头上。天与地成功地被圆形伞和方形几这两个器物比拟转化为一种形象化的视觉形象,同时也烘托出成王的王者尊贵。而这种对天圆地方的模拟早在礼仪建筑——明堂中便表现得十分明显和明确。何谓明堂?蔡邕《月令论》曰:“明堂者,天子太庙也。所以宗祀而配上帝,明天气统万物也。”②[唐]欧阳询:《艺文类聚》,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689页。明堂辟雍的结构同样比附了宇宙模式,在西安西郊的明堂和辟雍建筑遗址③《考古通讯》1957年第6期;《考古》1960年第7期,第38页。出土的四神瓦当,恰可与文献记载相互佐证。桓谭《新论》写道:“王者造明堂,上圆下方,以象天地。为四方堂,各从其色,以郊四方。天称明,故命曰明堂。”④[唐]欧阳询:《艺文类聚》,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688页。《三辅黄图》引《考工记》曰:“明堂五室……上圆象天,下方法地,八窗即八牖也,四闼者象四时四方也,五室象五行也。”⑤陈直:《三辅黄图校证》,陕西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12页。叶舒宪指出:“人类社会的幸福和秩序取决于太阳运行所代表的宇宙时空的秩序,为了明确宇宙的这种神圣秩序,必须由宇宙同人类社会之间的中介者在某个被认为是天下中心的地方建造一座象征宇宙秩序的神圣建筑,它的构成便是宇宙与社会之间的沟通,同时也是中介者(天子)确认统治权的明证。”⑥叶舒宪:《中国神话哲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46页。
这种对天地的比附仿效不仅成为丧葬形制的具有较大意义的形制特征与形制标准化趋同,同时也使得壁画墓、画像石墓或者祠堂所要表现的天上、神仙、人间和地下的立体层次感能够得以呈现。对于汉人而言,“死”至少和“生”同等重要,因为生命之长不过百岁,而死后如果葬在砖石墓室里,可以就此进入天上、地下、仙界或人间以及人神鬼魅共存的世界里,却是天长地久的亘古事情。因此,墓室在汉代也被称为“千万岁室”。⑦陕西省博物馆、陕西省文管会:《米脂东汉画像石墓发掘简报》,《文物》1972年第3期,第16页。扬雄《法言》中有云:“有生者必有死,有始者必有终,自然之道也。”⑧汪荣宝撰,陈仲夫点校:《法言义疏》,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521页。《列子·天瑞篇》云:“死亡与生,一往一反。故死于是者,安知不生于彼?”⑨杨伯峻:《列子集释》,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25页。根据“两元对立”的观点,人们相信死后也有一个世界,生界与死界共同构成一个完整的宇宙。但死后的世界究竟是什么样子无从得知,人们只能根据现实生活的版本加以发挥、想象和创造,故而导致彼岸世界与此岸世界在很多方面产生了高度的重合,死后生活成为人间生活的镜像。○10参见李虹《死与重生:汉代墓葬信仰研究》,山东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1年,第154页。
冯时在《中国天文考古学》中论述中国古代的天文学与丧葬制度的联系时写道:“中国古代的埋葬制度孕育着这样一种传统,死者再现生者世界的做法在墓葬中得到了特别的运用,其中最显著的就是使墓穴呈现出宇宙的模式并布列星图。”①冯时:《中国天文考古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99页。在中国天文史上,汉代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取得了许多令人瞩目的成就,尤其是在对日月星辰的观测方面。《汉书·天文志》云:“凡天文在图籍昭昭可知者,经星常宿中外官凡百一十八名,积数七百八十三星,皆有州国官宫物类之象。其伏见蚤晚,邪正存亡,虚实阔狭,及五星所行,合散犯守,陵历斗食,彗孛飞流,日月薄食,晕适背穴,抱珥虹蜺,迅雷风袄,怪云变气,此皆阴阳之精,其本在地,而上发于天者也。政失于此,则变见于彼,犹景之象形,乡之应声。是以明君睹之而寤,饬身正事,思其咎谢,则祸除而福至,自然之符也。”②[清]王先谦:《汉书补注》,书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544页。在政治制度上,汉朝的统治者尊天奉命,对天象进行细致的观察和记录,以探求“天”的奥秘和行动的轨迹。
中国传统的星象名位是以二十八宿为基础的。古人为制定历法,将天体赤道附近的星空分为二十八宿,是为了比较月亮的运动。《吕氏春秋》云:“月缠二十八宿。”③[秦]吕不韦:《吕氏春秋》;[汉]高诱注:《诸子集成·六》,中华书局,1954年版,第31页。意指月亮每天在星区停留的地方,也称为“一宿”。月亮每二十七天多一些可以在天上运行一周,为一恒星月。这样月亮每一个月要换行二十八个地方,即为二十八宿。星象图大多以日、月、星为主体,以物象为辅。如东汉陕西定边县郝滩壁画墓④参见陕西省考古研究所、榆林市文物管理委员会:《陕西定边县郝滩发现东汉壁画墓》,《考古与文物》2004年第5期。的墓室顶部,绘有月亮、二十八宿等星辰和仙人游天图及冯伯、雷公、雨师等图案。星宿图从左而右,通过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四神⑤四神,也称四维、四灵、四兽等。在中国传统的天文学体系中,将赤道附近的星空划分为二十八宿,并分别由四神(象)统辖。象是中国传统星官体系最基本的概念,作为四个赤道宫的象征,最终产生了四组灵物,分别具有四种不同颜色以及代表四个不同方向,并与二十八宿完成固定配合的严整形式,这便是东宫青(或苍)龙、西宫白虎、南宫朱雀(或鸟)、北宫玄武。参见冯时《中国天文考古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409页。在四神星象图中,多数并没有星象的出现,如河南南阳唐河针织厂汉墓北室墓顶的四神图像,以纯粹的动物形象来表示四象。还有一种是通过物象与星宿的联合方式来表现,其中以壁画中的一些四神星象图,较好地反映出四神二十八宿的结合,甚至具有一定的科学性。参见程万里《汉画四神图像研究》,东南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87—193页。来确定方位,每个星宿的星与星之间用红线连接,并且给每个星宿配了一个人物或动物。在星宿图像间还绘有云气纹和白、紫、红色星辰,用以表示星空。东汉河南南阳阮堂汉墓⑥参见中国画像石全集编辑委员会编《中国美术分类全集·中国画像石全集·河南汉画像石》,河南美术出版社、山东美术出版社,2000年版,第38页。中呈现的是东宫苍龙星象图。星象图的左上方有一月轮,其内刻画了玉兔和蟾蜍,下方是一条苍龙,从头到尾共计绘有十九颗星。该图像以物象苍龙为主,星象为辅,标示出东宫整体。这幅星象图上的龙头前后有二星为角宿。《史记·天官书》注云:“角间天门,谓月行入角与天门。”⑦[汉]司马迁:《史记》,[宋]裴駰集解、[唐]司马贞索隐、[唐]张守节正义,中华书局,1972年版,第1332页。龙腹下的四星连线成弧形,应为亢宿或者是房宿。龙躯后部有两两相连的四颗星,当是氐宿。龙尾上的八星则连线成椭圆形为尾宿。尾宿为九星,第九颗较小,而且与第八颗重叠近半。上有明月,中有蟾蜍、玉兔,说明月亮运行到苍龙星座的附近,也许行将进入角宿,表示月亮的运行将从二十八宿的第一宿角宿开始。“月缠二十八宿”的说法在这幅石刻画中被形象化了。⑧参见吴曾德《汉代画像石》,文物出版社,1984年版,第55—56页。东汉晚期河南南阳十里铺画像石墓⑨参见南阳地区文物工作队、南阳县文化馆《河南南阳县十里铺画像石墓》,《文物》1986年第4期,第51页。中的星象图,左为背负日轮之金乌,表示日在东方,时为晨。金乌左一星为太白,尾三连者为参宿。而河南南阳地区的汉画像石中还出现了日月合璧图。○10参见周到《南阳汉画象石中的几幅天象图》,《考古》1975年第1期,第59页。下组右为苍龙星座,左为毕宿,内刻玉兔。上组右刻阳乌,左为日月合璧,刻一金乌,背负内有蟾蜍之月轮。日月重叠,表示日和月来到黄道、白道的交点附近,造成日食现象。中国是世界上古代天文学资料保存最丰富的国家之一,商周甲骨文已有关于日食、月食的记录。《诗经·小雅·十月》载:“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①程俊英译注:《诗经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372页。参见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安平东汉壁画墓发掘简报》,《文物春秋》1989年第21期,第74-75页。汉代的观测记录包括了日食的方位、亏起方向、初亏、复圆时刻等。这幅日月合璧图,是研究中国古代天文科学的珍贵资料。日月交食,或称日月交璧,是祥瑞的象征。《后汉书·天文志》云:“三皇迈化,协神醇朴,谓五星如连珠,日月若合璧。”②[南朝宋]范晔、[唐]李贤等注:《后汉书》,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3214页。属于“和阴阳而二仪交泰”,③周绍良主编:《全唐文新编》,吉林文史出版社,2000年版,第5378页。充分体现了阴阳五行思想。值得注意的是,汉人绘制星象图的目的并非仅仅单纯描摹现世星空,或者为了记录当时天文学的成就,最主要的动机应是为逝者的灵魂设置具有特定象征意义的位置和空间。
《礼记·郊特牲》云:“魂气归于天,形魄归于地。”④[清]孙希旦:《礼记集解》,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714页。也就是说,世间有附身的魂魄,死后,肉体埋在地下,魂魄化气升天。天上是神仙的世界,是魂魄的理想家园。死亡只是肉体与魂魄(精神)的分离。人被造出来的时候,天给了他灵魂,地给了他身体,当他死后,这两种要素回归本源,肉体回归大地,魂魄回归天堂。在汉代的思想意识和宗教情感中,人们对“天界”的向往和追求,远远超过了他们对“地下世界”的关注和构想。人们渴望“飞升”起来,而不是“坠落”下去。埋葬是一个仪式过程,它导致一个新的居住地的产生和与冥界成员的灵魂的仪式结合。这个想法在汉代非常流行。《后汉书》云:“邓晨初娶光武姊元,后没于乱兵,光武即位,追封为新野节义长公主,及晨卒,诏遣中谒者,备公主官属礼仪,招新野主魂,与晨和葬。”⑤[南朝宋]范晔、[唐]李贤等注:《后汉书》,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582—584页。鲁唯一云:“一般地说,当魄、魂两者分离时,魂如果幸运和得到适当的帮助,将努力进入被想象成各种形式的极乐世界。”⑥[英]崔瑞德·鲁唯一:《剑桥中国秦汉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767页。因此,必须为死者精心造墓,构建一个美丽而完整的世界。
三、形态构建
由于人们相信死亡是再生的一种过渡⑦参见[英]泰勒《原始文化》,连树声译,上海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355页。形式,是可以展开生命另一种形式的存在,而墓室是他们死后进行修炼的场所,为了重新降生到新的、更优越的环境中,人们必须要死去回复到先前的景况,⑧参见[美]伊利亚德《神秘主义、巫术与文化风尚》,宋立道、鲁奇译,光明日报出版社,1990年版,第4页。因此,尽可能为死者建筑一个类似此生的空间显得尤为必要和重要。西汉时墓葬已有宅第化的特征,⑨参见俞伟超《汉代诸侯王与列侯墓葬的形制分析:兼论“周制”、“汉制”与“晋制”的几个阶段性》,载《先秦两汉考古学论集》,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第117页。墓室的空间构造能够发挥地面房屋的功能。“事实上,茔穴始终具有象征家室的意义,似乎没有人怀疑,它的产生显然模仿了人类最早出现的穴居建筑的形式。”○10冯时:《中国天文考古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296页。不仅如此,墓葬图像也在努力塑造一个完整的反映墓主生前所处宇宙与社会文化的时空范围。在较大型的汉代画像石墓中,通常分作前室、中室、后室等,主要描绘墓主人享乐生活的场景,间或穿插一些历史故事的内容。前室是男性墓主的外部活动世界,大多再现墓主人的政务、交往、出行等活动。中室(如果没有中室一般会安排在前室中的一部分)作为庄园中的庭堂部分,基本安排的是墓主人日常享乐的宴饮、百戏等内容。后室为墓主人的内寝地以及后园,表现寝卧、宴饮等家居活动。如安平东汉壁画墓,○1程俊英译注:《诗经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372页。参见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安平东汉壁画墓发掘简报》,《文物春秋》1989年第21期,第74-75页。前右侧室内主要表现了下属官吏治事和伍伯侍卫的情景。这些属吏均跽坐于帷幔下,因身份的不同,衣冠和姿势也各异。中室壁画于四壁用黄色格线由上至下分为四层,刻画了墓主人的四次出行,应是象征墓主人的四次升迁或是值得回味的事迹。再如山东临沂吴白庄汉画像石墓,①参见管恩洁等《山东临沂吴白庄汉画像石墓》,《东南文化》1999年第6期,第55页。前室和中室是画像石的主要分布区,横额计十四石十六幅画面,除了西墓室绘有一幅西王母、东王公的画像外,其余均是展示墓主生平、身份地位以及豪华生活的社会生活类的内容,如车马出行、迎宾谒拜、乐舞百戏、宴饮、庖厨、学经、狩猎等。“由于各种条件限制,这种再现的时空范围远远不能纤毫毕现,面面俱到,而只能采用高度概括抽象的形式,选择社会生活中最有代表性最为人企羡的典型场面进行反映。”②赵超:《汉代画像石墓中的画像布局及其意义》,《中原文物》1991年第3期,第24页。而且,为了在有限的空间里,更多地表现出众多的人物和宏大的场面,其图像多采用散视点结构,空白处以小物像填补,使整个画面显得非常饱满;在人物关系的处理上,则以左右和大小来区别;在纵深空间关系处理上,大多以重叠的手法表现。③参见管恩洁等《山东临沂吴白庄汉画像石墓》,《东南文化》1999年第6期,第55页。这些微缩化的场景模拟,形成一个连贯动态的生活过程,被敬献给墓主人。
在古人的眼里,墓葬建筑中的画像不单纯只是一幅或一组画像,它可以给死者的身后生活带来一种利益。④参见李虹《死与重生:汉代墓葬信仰研究》,山东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1年第90—91页。甚至他们本来就认为那些图像并非徒具形式,而是具有某种神秘力量。⑤参见崔朝阳《中国早期墓葬艺术中“神”“人”身份的图像化表》,《艺术工作》2018年第1期,第69页。类似于交感巫术中的相似律和接触律(或触染律),⑥参见[英]弗雷泽《金枝》,徐育新等译,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19页。前者属于同类相生或果必同因,后者则是物体一经互相接触,在中断实体接触后还会继续远距离互相作用。墓葬虽然位于此岸世界,但却“在想象中从属于彼岸世界的特殊时空秩序”,⑦巫鸿:《黄泉下的美术:宏观中国古代墓葬》,施杰译,三联书店,2010年版,第61页。墓主人通过建构那个想象中的彼岸世界而流露出对此生世界的深深留恋之情,正如余英时所言:“我所用‘彼世’的这一观念,并不是指对于未来生命的信仰和关心。系念的死后将是什么情况或一腔心思都想着你所希望得到的欢乐即将来临,那显然是对‘此世’恋恋不舍的一种最极端的表现方式。如果把‘彼世’想象成与‘此世’,并非截然而异类,而是大体相同,则‘彼世’不过是‘此世’存有模式的延伸而已。在这一想象中的‘彼世’,将和我们所熟知的‘此世’一样,依然是一个由变动、感性、多元与尘缘所共同构成的世界。所不同的只是尘世中的苦略去了,乐则提升了,以补偿人在生前所遭受的种种挫折罢了。如果人们所向往的‘彼世’是这样,那么它在本质上恰恰是对‘此世’依恋的一种最为极端的表现。”⑧余英时:《东汉生死观》,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8页。
可以看到,一方面,各种享乐生活题材的安排都是以墓主为核心来展开的,从许多画像石上撰写的榜题中可以看到墓主本人的在场。世俗生活被进行了分解与重构,进行理想化的塑造与夸张,将能够突出墓主成就或者将其滋润、得意的部分表现得一览无遗。即使这些内容并非全是为了再现逝者现实生活或者向宗族成员、世人或后世宣示逝者的生前拥有,⑨郑岩反对将墓葬中所有风格写实的图像全部认定为墓主生前的经历。参见郑岩《葬礼与图像——以两汉北朝材料为中心》,《美术研究》2013年第4期,第71页。那么,用来象征逝者在另一个世界的身份、地位或者某种生活状态○10参见李虹《死与重生:汉代墓葬信仰研究》,山东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1年,第90页。的做法也是建立在现实生活蓝本基础上的。另一方面,汉代人的长生不死信仰以及对生命转化的追求驱动他们倾力打造神仙世界,要在死亡和成仙之间建立起一套完整的内在联系,幻想着从“此世”来到“彼岸”。求仙是为了更长久地享受人间富贵,因此,按照逝者的意愿构筑彼岸空间,或者模拟逝者生前的享乐生活,或者塑造出一个富有众多世俗元素的“仙境”,或者将臆想中的属于仙界的某些元素引入人间生活的场景,正如像石上的仙界楼阙在模拟凡间建筑的同时还原了被凡间建筑模拟的自身,①参见邵立《东汉画像石的配置结构与意义——以宋山小祠堂和武梁祠为例》,《艺术百家》2006年第5期,第86页。从而导致了逝者生前、死后空间的区别不甚明了,人间、仙境的界线模糊不清。于是,升仙后的灵魂过着与生前无异,甚至更为美好的生活。②参见邵立《东汉画像石的配置结构与意义——以宋山小祠堂和武梁祠为例》,《艺术百家》2006年第5期,第86页。
结 语
古语:“百姓日用而不知。”哲学人类学的研究表明,人不仅是自然的存在、生物的存在,而且还是一个文化的存在、社会的存在、历史的存在和传统的存在。③[德]蓝德曼:《哲学人类学》,工人出版社,1988年版,第264—277页。当一种做法逐渐定型并形成某种传统之后,继续此传统的人并不一定都能够理解其中最原初的意义,虽然这些“常识”往往是社会生活中最重要的部分。④参见[美]诺夫乔伊《存在巨链:对一个观念的历史的研究》,张传有等译,江西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5—19页。葬礼及其图像,既是沟通地上世界与地下墓葬的桥梁,也使死者的过去与“未来”建立起意义的关联。⑤参见郑岩《葬礼与图像——以两汉北朝材料为中心》,《美术研究》2013年第4期,第72页。这种认知,不是个人的某个纯粹的主观爱好,而是遵循当时流行的意识形态的话语权的一种表现。正如哲学家斯拉沃热·齐泽克所认为的:“意识形态并非单纯的虚假意识,并非现实的幻觉性再现,而是现实本身。”⑥季广茂:《前言》,载[斯洛文尼亚]斯拉沃热·齐泽克著《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季广茂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版,第9页。与墓葬有关的宗族图像系统,既包含着人们对包括人类自身在内的空间世界的理性认识,同时又是人们对自身生命形式在上述空间世界存在方式所作的感性思考的艺术再现。一方面,其安抚着逝者,表达了生者对于此生与往生知识性的解释;另一方面,其又显示出宗族、家族、个体成员之间的关系,以及所对应的社会结构、宇宙结构、人生信仰的文化层位,并通过可感性的视觉形象再一次确证宗法共同体的身份隶属与集体情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