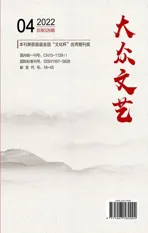岑家梧的图腾艺术研究考论
2022-03-10刘灿
刘 灿
(南京艺术学院研究院,江苏南京 210000)
一、民族艺术与图腾遗制之联系
岑家梧是中国近现代最著名的图腾研究者之一,他的《图腾艺术史》是国内第一部全面论述图腾文化的专著,著名人类学家卫惠林对该书给予高度的评价:“在三十年代对于西方学者学说研究能有此成熟的介绍和评述,确已是难能可敬,厥功甚伟”。20世纪三四十年代,我国人类学、民族学、考古学等专门的研究机构相继成立,学界开始对西南边疆各民族作专门的调查,岑家梧的研究方向也从史前艺术、图腾艺术研究转向西南边疆民族艺术研究。从图腾艺术史研究到民族艺术研究,岑家梧始终高度关注我国各民族历史文化中的图腾文化部分,认为我国西南边疆各民族艺术与图腾遗俗密切相关。
《图腾艺术史》从图腾制谈起,认为图腾制度发生于旧石器时代后期,有四大特征,一是“图腾集团以某种动植物为名称”,二是“图腾集团成员对图腾动植物加以崇敬,不敢毁害损伤或生杀”,三是图腾集团各种器具、装饰具有图腾同样化特征,四是实行绝对的外婚制。及至氏族社会期,图腾制改形换质,以图腾遗俗的形式继续留存于氏族社会中。
岑家梧在对西南边疆各民族进行社会调查后,提出部分民族仍保留着原始氏族公社制的遗迹。在《我国少数民族原始公社制研究(提纲)》一文中,岑家梧指出,我国有十多个少数民族仍处在原始公社制及其残余的不同发展阶段上,如保留原始公社制初期母权制残余的有云南宁蒗彝族自治县永宁盆地的纳西族、台湾耶美地区的高山族,处于原始父系家族公社时代的有苦聪人、独龙族、鄂温克族、鄂伦春族,处于农村公社的有云南布朗山上的布朗族、云南维西县境的怒族,从原始农村公社向阶级社会过渡的包括海南“合亩”制地区的黎族、云南佧佤山区的佤族等。
岑家梧是艺术社会学的倡导者,他认为艺术社会学正式成为一种科学体系,正是从艺术社会学开始的,艺术社会学正是“应用社会学的科学方法,以艺术为社会现象的一种,探讨其发生、发展与社会各现象间的因果关系”。岑家梧认为西南各民族生产劳动、社会活动及风俗习惯上都体现了原始氏族公社制的遗留,艺术作为人类社会生活的反映,氏族社会的某些特征当然也在西南边疆各民族艺术中体现了出来,而其中所反映的图腾遗俗最具代表性,同时,岑家梧也提到图腾艺术同时包括存活于当下各地图腾民族之中的与原始时代世界图腾民族的遗物。由此,岑家梧指出我们可从西南边疆民族艺术着手来研究图腾艺术,在研究西南边疆民族艺术时也应着重注意其图腾文化特质。
然而自20世纪上半叶至今,国内不少学者仍对西南边疆民族的图腾遗制与遗俗持怀疑态度,许多学者认为各民族所谓的图腾信仰不过为后人根据传说所附会。20世纪三四十年代,学界对槃瓠传说的质疑之声尤盛,刘锡蕃认为槃瓠实为盘古,槃瓠为狗之说是为后人所附会,徐松石认为《后汉书》中的槃瓠传说是“无羁的神话”,赞成南宋文学家罗泌的“卞明生白犬是为蛮人之祖”,认为槃瓠“乃人名而非真犬”,岑家梧认为刘锡蕃、徐松石、何联奎等学者虽对瑶畲做了专门的社会田野调查,但他们对图腾制度发生、发展、消灭的发展过程都少有正确的理解,因而才否定瑶畲风俗来源于槃瓠图腾遗制、瑶畲艺术反映了槃瓠图腾遗制。
岑家梧以槃瓠传说为例,对历史古籍与瑶畲两族民族文学、图像、歌舞、服饰及习俗进行互证,充分说明瑶畲确实保留着槃瓠图腾遗俗。《槃瓠传说与瑶畲的图腾制度》正是说明民族艺术与图腾遗制之紧密联系的经典之作。
二、民族艺术的图腾制特征
卫惠林在评价《图腾艺术史》时曾感叹,认为在这本书的正文中主要以介绍西人的著作为主,而并没有以中国图腾艺术材料作为主要内容,但也肯定“从家梧兄自己编入书后的一篇附录《中国图腾跳舞之遗制》一文,更可以证明他对中国古代图腾文化研究的造诣很深”。在后期的西南边疆民族艺术考察中,岑家梧密切关注民族艺术与图腾遗制之联系,尤其是民族艺术的图腾制特征,虽未及将民族艺术与图腾遗制的联系进行成体系地宏观阐述,却常以图腾遗俗来解读西南边疆民族艺术现象,如“海南岛的黎民文身,由传说看来,尤可知其系遵守图腾遗习”。
岑家梧对于民族艺术的图腾制特征研究,我们可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概括:
第一,部分民族艺术形式表现出“图腾同样化”。
“图腾同样化”是图腾制社会生活的重要特征,是图腾信仰的外在显现。表现在装饰上,即在身体装饰、日常服饰、住所装饰、用具样式等形式中,均对图腾动物的形象特征进行模仿与表现,如身体装饰上的敷痕、涂色、切痕、黥纹、结发、镶唇、穿鼻、毁齿等;表现在舞蹈与类似于戏剧的部族仪式活动中,即在肢体动作上进行对动物动作的模仿,一方面是祈求图腾祖先赋予新成员以神秘的狩猎机能,另一方面是希望通过象征狩猎对象被猎人所支配与征服的模仿舞蹈对现实中的动物狩猎施以效能;表现在音乐中,即为对动物叫声的模仿。
在西南边疆民族艺术中,“图腾同样化”的身体装饰方面表现最为突出,经岑家梧考察发现,在发饰上“大多西南民族的头发往昔都是椎髻的,所谓髻发,就是将头发盘成圆锥形,或结于额前,或结于背后,好像角的样子,如彝族、黎族、纳西族、苗族、瑶族等”,贵州苗族被称为“狗耳龙家”的部族便因“妇人辫发螺发上若狗耳”而得名,此外,妇女还各有不同的头上附饰物,以崇拜槃瓠为图腾的瑶族妇女便常戴象征狗的两耳的布帽。在服装上,干宝《搜神记》中述槃瓠子孙的衣服是“织绩木皮,染以草食,好五色衣服,裁制皆有尾形”,岑家梧认为所谓“好五彩衣服,衣裳斑斓”是与“时帝有畜狗,其毛五彩,名曰槃瓠”相关照的,因为槃瓠的毛五彩,所以他的子孙的衣服也是“五色”“斑斓”,而“裁制皆有尾形”,则是象征狗的尾巴,今日的瑶、畲服饰上仍有许多是模仿狗外形的,据沈有乾调查:瑶人男女身穿之衣,均有织成五彩花纹之布缝贴其上,盖传言其祖宗为一五彩毛之狗。
第二,部分民族艺术仍保留着图腾艺术的形式。
岑家梧将初民的图腾舞蹈分为两种,一种是模仿舞,另一种是体操舞,体操舞由狂热的情绪所引起,表现为多数人作一致的跃动,他认为体操舞是各图腾部族共同协力的表现,有助于各图腾部族成员舍弃各自不同的需求与欲望,而形成同一的目的与感情,以克服不规则、不固定的游离生活状态而作集团的总活动的表现。
西南边疆民族的舞蹈大多也是体操舞的形式,如广西瑶人群舞“男在外而面朝内,女在内而面朝外,成一重叠之大环形。男女各依一定规则,做种种舞蹈姿势,进退疾徐,此动彼和,均有相呼应之势”,海南黎族的夹足舞“六人坐于地上,分三人为一组,两组对面而坐。取竹竿六支,各人握杆一端。舞时此六人先高举竹竿向地上敲二次,次各将左右手的竹竿合撞一次,再拉开对撞他人手中的竹竿,以之为拍子。复使二人跳入竹竿拉开时的空隙之中。二杆合拢时,舞者迅速提足跳入另一空隙之中,双足左右跳跃,双手稍稍向上提举,如是反复动作”,更为纯熟可观的是苗族的舞蹈,从形式上便分为绕舞、对舞、跳舞、滚舞四种。
第三,部分民族艺术内容反映了图腾崇拜。
图腾制是由于狩猎生产的地域固定、狩猎范围专门化而形成的猎取一定动物的生产集团,为原始人类从事狩猎采集经济阶段上必然产生的集团制,图腾的名称便源自生产集团与动物名称的相连接。岑家梧认为氏族村落的产生使得图腾制逐渐衰落,图腾文化进入转型期,图腾制中纯粹的动植物信仰演变为图腾动物人格化,氏族酋长与动植物连接在一起,成为幻想中变化多端或半人半兽的动物。
岑家梧在《中国民族的图腾制度及其研究略史》中对中国历史上各族的起源传说进行了梳理,包括殷人的玄鸟传说、哀牢夷的龙传说、夜郎的竹传说、高车的狼传说等,指出图腾民族自称为动植物的后裔,因为信仰其来源与图腾动植物有血缘关系,且以之为部族的名号,并举例《隋书•西域传•党项》“党项羌者,三苗之后也。其种有宕昌,白狼,皆自称猕猴种”,夫余国还以兽类为官名,《后汉书•东夷传•夫余》“以弓矢刀矛为兵,以六畜为官名,有马加,牛加,狗加,其邑落皆主属诸加”。
西南边疆各民族多以相似的艺术形式反映各自不同的图腾崇拜,最主要的是祭祀时的歌舞。各地的畲民均有祭祀槃瓠的仪式,方凤《夷俗考》记载“岁首祭槃瓠,杂糅鱼肉酒饭于木横,群聚而号以尽礼”,刘锡蕃《岭表纪蛮》记载“狗王,惟恂瑶祀之:每值正溯,家人负狗环行灶三匝,然后举家男女向狗膜拜。是日就餐,必叩槽蹲地而食,以为尽礼”,岑家梧认为所谓“杂糅鱼肉酒饭于木槽”是喂狗的意思,“叩槽蹲地而食”是模仿狗的动作,由此推测祭祀槃瓠的仪式是成员盛装歌舞模仿其图腾祖先狗的动作及叫声。贵州省花苗也有祭祀槃瓠时的歌舞,如毛贵铭《黔苗竹枝词》所咏“槃瓠新年祭一遭,祖宗留饭与儿曹,棉花如雪苗娘喜,市上今年布价高”,又如“荔波县里月场,侗水瑶苗跳几回,槃瓠祭余歌舞散,肩头背得丽人来”。
第四,部分民族艺术具有图腾制时期遗留的社会功能。
图腾制社会中,集团中的成员都不敢生杀与毁伤作为图腾祖先的动植物,而是加以崇敬,当集团内的成员到了特定的年龄,便要举行图腾入社式,图腾入社式是一种特定的舞蹈仪式,即图腾集团的成员达到一定的年龄,会被引导学习图腾集团的生活规范,举行入社式后,才会被正式承认为集团中的一员。在举行入社式时,长老会申述本图腾部族的历史起源,并要求新成员对图腾的叫声与动作进行学习和模仿。
西南边疆民族中少见具有明显图腾入社式特征的盛大仪式,但部分民族艺术的存在仍体现了“入社”的社会功能。西南边疆民族中的成年式即图腾入社式的遗俗,由图腾社会中的舞蹈形式转化成了西南边疆民族地区人们成年前后身体装饰的改变。傣族有染齿的习俗,江应樑称“我初到夷区,见十数岁的少女,一口白齿,尽白粲可人。年纪较大的,便都齿黑如墨了。问之夷人,始知摆夷风俗,妇女在结婚时,须将牙齿染黑……可知摆夷妇女之染齿,实在是妇女成年式的遗俗”;瑶族妇女的狗耳帽象征着槃瓠图腾,仅限于瑶妇佩戴,“瑶妇与瑶女所戴的高帽各异。女子之帽,上面为椭圆形,妇女为两尖角形,初出嫁之年轻妇人,亦间有仍带有椭圆形帽而未戴双角之帽者,以其怕羞也。但出嫁已久,则必戴前具双角之高帽。未出嫁之女,则绝未有戴双尖帽者”,岑家梧认为“大概瑶人未出嫁的女子,尚未承认其为图腾成员,无须作象征图腾的装饰,至于出嫁妇人,已经成人,当然算作图腾的分子了”。
三、论遗俗——民族艺术与图腾艺术之区别
根据对“遗俗”的理解,岑家梧对欧美学者将非、澳、北美洲民族艺术完全等同于图腾艺术的研究方法提出质疑,并指出我国民族艺术与图腾艺术的区别,岑家梧认为我国西南边疆各民族艺术是图腾遗制的体现,也是对各民族交流史的反映,并不能将民族艺术完全等同于图腾艺术。此外,岑家梧还根据遗俗论对图腾艺术史研究与民族艺术史研究提出了科学的方法。
关于遗俗论,西方古典进化论派人类学学者认为,世界文明始终遵循着线性的、由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过程,文明人的史前祖宗便是现存的落后民族,所以若要研究文明民族的古史便要从研究现存的“蛮族”各方面着手,甚至认为研究现存“蛮族”便是研究史前时代。西方人类学功能学派持完全相反的观点,他们认为所谓遗俗几乎是虚构的概念,马林诺夫斯基认为,进化学派的方法中最重要的是便是遗俗的概念,他们从遗俗的概念出发根据现有的状况中去重构过去的阶段,并批判他们将人类学者所不能了解的一切都归结为遗俗,作为幻想和猜度的出发点。因此,功能学派认为,如果我们对文化的认识程度越深刻,那么可以被称作遗俗的也越少,由此看来遗俗几乎是虚构的概念。
岑家梧从历史进化论中得到启发,首先指出遗俗的存在是不容抹杀的,可以借现存风俗还原消失的制度。岑家梧《遗俗论》中讲道,“在文化现象中,风俗的遗留更多,且多为社会制度的陈迹……社会制度为人类自觉的行为,带有人为的强制性。制度与风俗二者的关系最为密切,制度或因袭自风俗,风俗或由制度所形成。风俗与制度,实为一事的两面,彼此相辅而行,互为因果。风俗的形成,既属自然,它借着传统的力量,深入人心,牢不可破。其改变也较为迟缓,制度是人为的强制性,人为的强制一旦消失,制度也随之瓦解,它的改变则较为急速,如此制度改变而风俗尚存,风俗与制度脱节,风俗乃成为残存的遗迹了”。
其次,岑家梧指出进化论派学者的错误,进化论学者往往采用文化遗留法来研究初民艺术。如格罗斯、哈顿等以现在非、澳洲的土人艺术说明原始艺术,但是如果像将现阶段澳洲土人的艺术用来说明欧洲驯鹿期的艺术那样的话,将两种没有任何关系的民族文化,硬套进同一阶段并且相互说明,必然会有问题。岑家梧将史前图腾文化期的产物与现存图腾文化做比较,表示“我们应该明白:目下北美、非洲、澳洲等土人社会中存在的图腾制,已非属其最初的形态”,不可根据北美、印第安人及澳洲土人的图腾集团组织,以探求图腾制度的原始形态;另外,图腾的意识形态在氏族社会中虽然并没有具体的完整的存在,但尚且保存了部分,同时演变成了特殊的信仰与独特的习俗,图腾仪式经过改质转型,也形成了文明民族的习惯与风俗,图腾遗制实贯通于氏族社会的方方面面。
岑家梧认为,研究图腾艺术、构建完整的图腾艺术史,应该留意遍及社会各阶段之图腾艺术的残留物,而并不仅限于研究原始社会图腾期者之图腾艺术为满足。同时,岑家梧还认为在图腾艺术史的研究过程中,也应注意民族艺术并不等同于图腾艺术,自古我国汉族与西南边疆民族便有交流传播的关系,文化艺术上也相互影响,甚至部分已失传的古代中原艺术在西南边疆民族中很好地保存了下来,因此,西南边疆民族艺术并不只具有图腾制特征,更是各民族史的反映。
据此,岑家梧从中国各民族历史上复杂的演进和互相影响的情况,提出可从民族交流史的角度用西南边疆民族艺术材料来研究中国民族艺术史,“边疆各族之间,或边疆与中原之间的艺术,既然有了传播的关系。我们应细为识别,做比较研究。考订其发源与传播的途径”。岑家梧指出对西南边疆民族艺术的重视既可扩大中国艺术史料的范围,又可以对中国艺术整体的美学特征做出说明,充分肯定西南边疆民族艺术研究的学术意义和地位,“边疆艺术的研究,可使今后中国艺术史料的范围扩大,不致局限于纸上的死材料了”,“如果我们将来能将边疆艺术的来源及传播,一一考订,则我们对于整个中国艺术渊源、胎息,当可明了。而中国艺术之所以富于宏厚优美的性质,也可得到说明,这在中国艺术史的研究上,实有重大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