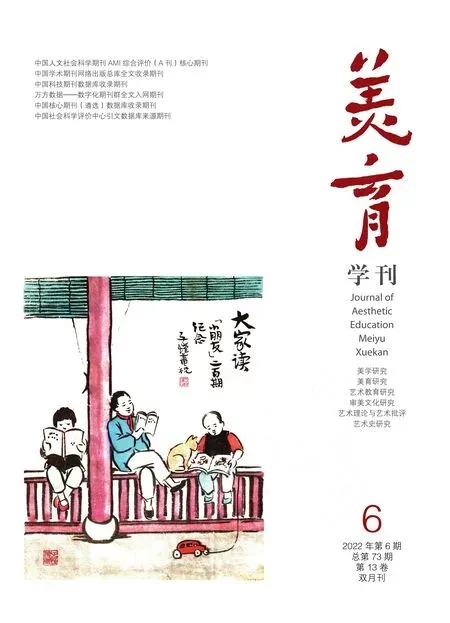莫里斯“生活艺术化”思想在民国的流变
2022-03-07张锐,张红
张 锐,张 红
(杭州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浙江 杭州 311121)
一、从“劳动快乐化”到“生活艺术化”
第一次世界大战胜利之际,蔡元培在庆祝协约国胜利大会上发表题为“劳工神圣”[1]的演讲,在这篇不足500字的演讲稿中,蔡元培虽未能充分论证“神圣”的内涵,却石破天惊地将传统中国读书人不齿的劳作升华到审美的崇高境界,引发了中国学界对劳动美学的探讨。
蔡元培随后(1920年)对劳动问题做了一些补充:“从柏拉图提出美育主义后,多少教育家都认为美术是改进社会的工具。……那些工匠,日日营机械的工作,一点没有美术的作用参在里面,就觉得枯燥的了不得;远不及初民的工作的有趣。近如Morris痛恨美术与工艺的隔离,提倡艺术化的劳动……”[2]蔡元培首先明确了艺术(1)此处美术指广义的艺术。改造社会的政治功用,阐明其美育思想的西方源头,将劳动美学与社会改造紧密联系;其次,莫里斯提倡艺术化的劳动,即艺术与普通劳作的结合,使劳动变得有趣,艺术由此改造社会。用“有趣”来阐释“艺术化”,可见蔡元培劳动美学的逻辑。威廉·莫里斯(William Morris,1834—1896),实际继承了英国经验主义的美学传统,“美感即快感,美即愉快”[3]。莫里斯的艺术美并不推崇先验的理性观念,也无关学院派的思辨哲学,他不再将艺术看成被静观的纯粹客体,而是人类主体在劳动与生活实践过程中生理上和心理上所收获的愉悦,认为这种感官愉悦即为艺术化。在他看来,“艺术的目的是增进人类劳动的愉悦”[4]593。莫里斯在《乌有乡消息》(NewsFromNowhere,1890)中将一幅幅劳动场面,如日常的打扫、季节性的收割等都描写得美妙动人,使其产生艺术化的效果。在莫里斯的乌有乡,这种愉悦与人类劳动相伴随,为劳作披上了一层愉悦的辉光。蔡元培的所谓“神圣”似乎就是这层愉悦辉光。
由蔡元培开启的劳动美学探讨,使莫里斯“劳动快乐化”思想颇受关注,在此传播过程中,“劳动快乐化”逐步泛化成“生活艺术化”。1920年,《东方杂志》刊登了数篇相关文章。昔尘(章锡琛)首先在当年第4期《边悌之社会主义》中说:“主张化劳动为艺术者,始于维廉莫理斯。”[5]随后在第7期又发表专论《莫理斯之艺术观及劳动观》,其中如此定义莫里斯的劳动观:“劳动而各从所好则其劳动自为喜悦而无苦痛,则其喜悦之表象,则为艺术。”[6]“表象”这一阐释似看透其“愉悦”的感官性与外在性,可惜未对此深挖一步,却在广度上进一步拓展“即以艺术与人生一致,凡生存之喜悦,皆在于由劳动而成之艺术品”[6]。此处将劳动泛化到整个生存状态,人生存的喜悦全在于劳动之喜悦,已向“生活艺术化”靠拢。谢六逸在第8期发表《社会改造运动与文艺》,主推维廉莫理斯等主倡的“生活艺术化”,认为“因为一般民众的生活就是‘劳动’二字的别称,现在民众勃兴的时期,‘生活的艺术化’,直而言之,就是‘劳动的艺术化’”[7]。由此,“劳动快乐化”与“生活艺术化”画上了等号,这一简单对等显然在理论上有不小的漏洞:生活中除了劳动显然还有非劳动的要素,如精神欲求;况且作为感受的“快乐”何以能与作为范畴的“艺术”简单对等?尽管谢继续追问“生活的艺术化”和“劳动的艺术化”究竟是什么,其回答依然是“就以生活化为艺术的;进一步说用生活当作一种艺术”。[7]探讨止于“艺术”“生活”等文字表面,未能深入其理论基底。1921年,杨贤江延续了这一说法:“但是确能把这生活和艺术调和的问题最彻底的最具体的考察、主张,更进而实行、体现的,却要算威廉姆·莫理斯(William Morris)为代表了。”[8]他指出:“故生活的艺术化,一方为对于近代物质文明、机械文明的反抗,一方更为对于新文化建设的暗示。”[8]杨将“生活艺术化”纳入新文化建设,以其为武器改造中国文化,有一定见地。此时,“生活艺术化”已成为新文化运动中一个较显明的口号。
而阐发莫里斯“劳动快乐化”与“生活艺术化”思想在国内传播的初始者似为本间久雄(1886—1981)。1921年初版并在民国再版10余次的《社会改造之八大思想家》影响极为深广。书中将莫里斯与马克思(Karl Marx)、克鲁泡特金(Peter Kropotkin)、罗素(Bertrand Russel)、托尔斯泰(Leo Tolstoy)、喀宝脱(Edward Carpenter)、易卜生(Henrik Ibsen)、爱伦凯(Ellen Key)并称为社会改造的八大思想家。其中,对莫里斯的总结为“从美术家至人生底(的)艺术化,竭其所能,竭力于社会”[9]。1924年,《东方杂志》刊发了从予(樊仲云)翻译的本间久雄的《生活美化论》(即《生活的艺术化》(2)本间久雄:《生活美化论》,从予(樊仲云)译,载《东方杂志》,1924年第21卷第11期。此外还有两个译本(本间久雄:《生活的艺术化》,瞿宗瑜译,载《黄埔月刊》,1930年创刊号;本间久雄:《生活的艺术化》,许达年译,载《南华文艺》,1932年第1卷第16、18期)。),此文较为详细地梳理了卡本特、莫里斯和罗素等人的“生活艺术化”思想,其中着重介绍了莫里斯的“劳动快乐化”。这篇文章后又经瞿宗瑜和许达年翻译,可见这一思想传播之广。而中国大批留日学生似乎在1921年之前已经深受影响,在李大钊、田汉、章锡琛、谢六逸、杨贤江等人的措辞和论述框架中都隐约看到本间久雄这两篇文章的影子。
莫里斯并不长于推理,其理论显然激情远胜学理,其思想在当时广受关注不仅在于其切中当时对劳动问题的关注,更在于莫里斯艺术民主的思想契合了新文化运动高扬的“德先生”。实际上,莫里斯“生活艺术化”的第一个关键词是民主。莫里斯的《民众的艺术》(“The Art of the People”)指出:“杰出的作品都是普通民众(common fellows)在普通的日常生活过程(common course of their daily life)中所创造。”[4]528莫里斯终其一生都在追求着这样一种艺术——“由民众创造也由民众享用,带给创造者和使用者同样的快乐”[4]535的艺术,并且深信:“这种艺术是唯一能够推动世界进步的真正艺术。”[4]534由此,莫里斯不断重复“民众”(the people),相对于贵族学院派的艺术,莫里斯将艺术范围与边界扩大到普通民众与日常生活当中,并认为:“快乐的真正秘诀在于真诚且饶有兴致地关注日常生活细节,并用艺术将其升华。”[4]600平庸的日常生活经由快乐可以升华为艺术;与此几乎同一进程的是,普通劳动者经由快乐劳动能够成为艺术家;艺术也不再是高不可攀的奢侈品,而是实实在在的有用之物之美化。莫里斯提到:“‘装饰艺术(Decorative Arts)’被认为是‘次等艺术(lesser arts)’,但无论多伟大的建筑、雕塑和绘画艺术,离开装饰艺术,都将失去艺术的尊严,沦为枯燥无味的矫饰和有钱人的玩物。”[4]494-495无论高等艺术或是次等的装饰工艺美术都是民众创造的,理应为民众所享受。由此,莫里斯艺术民主思想得以完整确立。莫里斯的平民艺术观,强调审美经验与日常生活的连续性,模糊高等艺术与次等艺术的边界,其本身学理是否成立姑且不论,但其确实应和了新文化运动中对民主的呼声。
莫里斯“生活艺术化”的第二个关键词是自由。在《乌有乡消息》中,莫里斯将这一时代称为“自由时代(the days of freedom)”[10]111,“整个社会变革的动机是对自由与平等的渴望”[10]66。乡民不仅有选择职业的自由,更有心灵的自由。其中第6章乌有乡民取得自由之后,竟然不知如何享受这种久违的自由。第7章专门探讨了这一精神层面的自由问题,“无威权压制,每个人都能够享有将其个人特殊能力发挥到极致的自由”[10]52,而此时,人类的劳动过程正是享受和利用这种自由的过程。不仅如此,莫里斯还强调在艺术上,“拥有想象和幻想的自由”[10]59,在爱情上,“无须法律与婚姻束缚,两性之间彼此真心相爱,可以选择自由地去留”[10]52。这种精神上、心灵上、艺术上的自由挣脱一切礼教与威权,是人类感性与天性的张扬。陈独秀在《谈政治》(1920年)中说:“人类诚然有劳动的天性,有时也自然不须强迫,美术化的劳动和创造的劳动更不是强迫所能成的。”[11]此处,陈道出了这种劳动艺术化的自由本质,这种劳动是人的一种自然欲求。陈之佛说:“再如英国马利斯(William Morris)说,自由意匠所造成的,美术的制作上,能有这样的成品(3)指哥特式建筑。……从制作方面说,工艺美术,亦能以高洁自由之快乐。”[12]哥特式建筑之所以伟岸高洁,主要因为中世纪的工匠心灵是自由的,而艺术的价值恰恰在于心灵自由之高洁的愉悦。
莫里斯“生活艺术化”的第三个关键词是社会主义。对于如何实现“生活艺术化”,莫里斯明确指出劳动艺术化之劲敌即为资本主义商业制度下的现代文明,唯有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建立社会主义才能实现生活艺术化,此为莫里斯的艺术社会主义思想,也是莫里斯自身走向社会主义的动因。[4]657-658而《乌有乡消息》中形塑的具有强烈共产主义色彩的社会图景显然令当时的文化人为之神往。较早较深入地从社会主义角度探讨莫里斯的是李大钊。李大钊1923年至1924年在北京大学的讲稿《社会主义与学艺之关系》中提到:“William Morris以为资本主义使人生活上渐趋于干燥无味之境,学艺亦日见退化,于是发生反抗,得到美学的社会主义运动。”[13]此处较之前最大之不同在于提到生活之无趣之根源在于“资本主义”,认为莫里斯的艺术社会主义充满美与快乐。吴梦非在《艺术的社会主义》(1924年)中说:“从社会的立场看出‘艺术’的重要,便叫做‘艺术的社会主义’。穆利斯的卓绝功绩,便是把艺术指导到民主的途程中去。”[14]吴的理解并无高妙之处,却几乎是国内最早使用“艺术的社会主义”这一术语的。1929年,田汉在《穆理斯之艺术的社会主义》详细地分析了莫里斯如何及为何成为社会主义者,并一再表达“真的诗人视劳动为艺术,因而就是真的社会主义者”[15]这一观点,实现了其自身思想的左转。
莫里斯的“生活艺术化”根源于普通民众的日常劳动与生活,倡导艺术民主与精神自由,并主张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实现“生活艺术化”。“生活艺术化”思想所裹挟的“自由民主”和“社会主义”的观念显然契合了整个20世纪20年代中国文化界的思想走向,所以这一思想流传甚广。
二、与生产化、军事化三位一体的“生活艺术化”
莫里斯的“生活艺术化”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传入中国以来,流传近10年,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直到1935年南京国民政府提出新生活运动第二阶段目标“生活艺术化、生产化、军事化”,至此,“生活艺术化”再次被推上风口浪尖。蒋介石如此阐释其内涵:“艺者技能、术者方法、生活艺术化者、为求生活上有合理之技能与方法也。”[16]蒋氏解读的“生活艺术化”并非感性地、艺术地生活,而是掌握衣食住行的技能与方法,使之更合理。此处“合理”二字显然追求一种理性的生活。“技能与方法”看似回归了“art”的本意“skills”,但是却使之彻底偏离了艺术美之轨道。三化口号似乎与邓文仪在新生活运动初始起草的步骤颇有抵牾:
此运动为移风易俗、教民明理知耻之始。拟以规矩、清洁二项为之首倡,如施行有效,乃进而为礼乐射御书数之六艺运动,反作到自然,去过太阳、空气、水之生活,最后不难使国民循序渐进于劳动创造武力之习练与整备。[17]
以邓文仪初稿“始”“进而”“最后”三个标识词,不难看出新生活运动应分为三个步骤。然而,迫于国内外形势,邓显然将后两步并行而为了,于是“生活艺术化”似囊括“六艺运动”,而“生产化”似指“劳动创造”,“军事化”似指涉“武力之习练与整备”,如此关涉略显机械,但已经不难看出“生活艺术化”的某种理论缘起。
此时的“生活艺术化”是新生活运动前期“礼义廉耻”的衍生,是伦理与道统的工具。而其话语也并非莫里斯吉光片羽式的点染,而是条分缕析的规则体系。“生活艺术化”分为持躬、待人、处事、接物四大纲,近200个条目。不仅有整体的公民道德规训,而且有各行各业的生活艺术化准则,如警察的生活艺术化、农民的生活艺术化,实质就是各行各业的职业道德规范,与其说艺术化,不如说伦理化。我们试图从“生活艺术化”之“衣”与“住”来分析其与“礼义廉耻”的关系:
衣服章身,礼貌所寄;莫趋时髦,朴素勿耻。式要简便,料选国货;注意经用,主妇自做。洗涤宜勤,缝补残破;拔上鞋跟,扣齐钮颗;穿戴莫歪,体勿赤裸。集会入室,冠帽即脱。被褥常晒,行李轻单。解衣赠友,应恤贫寒。[16]
以上是关于“衣”之条目共20个四字词语,6句话。以“礼”开篇,服饰是身份之彰显,礼仪之所寄托。紧接着“朴素”“简便”“经用”等词都是强调节俭“廉”;第三分句“耻”强调衣服穿戴要整齐干净,有羞耻感。以“义”结尾,用善意来体恤贫寒者。此处的“生活艺术化”与艺术无关,与装饰无关,只是礼义廉耻的伦理说教与科学卫生知识的普及和家国情怀的重申。此处的“生活艺术化”之“衣”与莫里斯对服饰的探讨完全风马牛不相及。在《乌有乡消息》中,乌有乡人的衣饰色彩、材质都与季节相称,与大自然交相辉映,风格古朴,设计精美,精工细作。不仅如此,服饰艺术化集中表现在愉悦,文中多次用在gay-clad,pleasant凸显了服饰之艺术之美与愉悦。“生活艺术化”中的“穿”无非是后续生产化,最终军事化中的第一环而已。对于“住”的艺术化,条目如下:
住居有室,创业成家,天伦乐聚,敦睦毋哗。黎明即起,漱口刷牙,剪甲理发,沐浴勤加。建筑取材,必择国产,墙壁勿污,家具从简。窗户多开,气通光满,爱惜分阴,习劳勿懒。当心火烛,谨慎门户,莫积垃圾,莫留尘土。厨房厕所,尤須净扫,捕鼠灭蝇,通沟清道。和洽邻里,同谋公益,互救灾难,种痘防疫。国有纪念,家扬国旗,敬旗敬国,升降循规。[16]
“生活艺术化”之“住”,共32个四字词语,每4个词一节。也先从“礼”着手,以天伦之序开篇,形塑一派祥和敦睦之图景,强调儒家思想中的成家立业,安居乐业,以确立正统儒家的伦理价值观。“敦睦”语出《后汉书·卷七○·孔融传》:“圣恩敦睦,感时增恩……稽度前典,以正礼制。”此处用典立意鲜明:正礼制,序天伦。但此处的“义”似有所升华,指国家大义,而其国家大义的表达方式却依然是“礼”,对国家纪念仪式中国旗升降循规之“礼”来表达。以开篇“礼”与终篇“礼义”显然无法统摄中间超长的其他条目,整个条目在文法上,铺陈却逻辑松散,缺乏环环相扣的逻辑主线,明显东拼西凑,但无疑“礼”是灵魂;在具体表述上,看似全部采用规整四字词语,实则典雅的书面语如“敦睦”“循规”与俚俗的白话口语“厕所”“垃圾”等凌乱杂陈;在语体上,极力模仿古语,力求对仗,却因内容所限,求而不得。在文法、措辞、语体上可见文言与白话、现代与复古、雅与俗的“挣扎打斗”之痕迹,总体而言,虽然在开篇结尾表达“礼义”等方面比较空洞,其他方面也确实做到了白话文运动的“八事”之首——言之有物。
相同的语言外衣难以遮蔽两次“生活艺术化”口号的根本区别。肇始于莫里斯的“生活艺术化”是艺术的、审美的、感性的,追求艺术民主和个人精神的自由;而新生活运动中的“生活艺术化”是政治的、伦理的、理性的,用儒家的礼教伦理来规训个人的身体进而禁锢人们的心灵与精神,使理性内化。实际上,如果说传统的“礼”本身与审美毫无关涉显然是有偏颇的,“礼”传达了将生活的不同实践礼仪化而从艺术上来塑造人生。[18]然而,过分强调了“军事化”而剥蚀了“礼”的仪式可能带来的愉悦价值。这里的“礼”剔除了艺术中最重要的有血肉、有性灵之活生生的个体感受。此处“生活艺术化”似是而非,名不副实已无需赘述,然而,最令人费解的恰在此处,南京国民政府为何要启用这个流传甚广,却又明显有歧义的口号?
三、“生活艺术化”:从新文化运动到新生活运动
“生活艺术化”口号如烫手的山芋,特别棘手。首先,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生活艺术化”已滥觞,而口号本身固有的对感性自由与社会民主的追求显然与蒋氏的意志南辕北辙。更有甚者,在五次围剿的大背景下,基于莫里斯的“生活艺术化”中的阶级斗争及共产主义思想都是此时南京国民政府的眼中钉。新文化运动和新生活运动的根本差异显而易见,为什么南京国民政府要使用这个明显会产生歧义的口号呢?答案有三种可能,首先是新生活运动决策层对早期“生活艺术化”内涵并不知晓。这点显然不成立。暂且不论“生活艺术化”观念本身传播之广,单就蒋氏发家之处——黄埔军校迁址南京后的最重要机关刊物——《黄埔月刊》创刊号上就刊登了瞿宗瑜译本间久雄的《生活的艺术化》长文,此文对莫里斯的“生活艺术化”做了细致梳理。早期新生活运动决策层,大多系出黄埔,不可能不知晓这个口号及其内涵。第二种可能是,“生活艺术化”是新生活运动决策层无暇旁顾的急就章。但显然不是,因为“三化”口号是在1934年新生活运动初见成效后的第二年经过审慎考量后才提出的。
那么就只有最后一种可能,新生活运动决策层有意挪用新文化运动这一旧口号,试图旧瓶装新酒抑或反其道而行之。针对新文化运动,蒋介石的这段话不容忽视:
我们试看当时所谓新文化运动,究竟是指什么?就当时一般实际情形来观察,我们实在看不出它具体的内容。是不是提倡白话文就是新文化运动?是不是祈求解放自身不顾国家社会就是新文化运动?是不是打破纪律,扩张个人自由就是新文化运动?是不是盲目崇拜外国,毫无抉择的介绍和接受外来文化,就是新文化运动?如果是这样,那我们所要的新文化,实在太幼稚、太便宜,而且太危险了![19]
蒋介石连用5个反问句和压轴感叹句,语气之激烈,厌恶之深切可见一斑。蒋氏不仅斥责了新文化运动是空洞,更直指其“个人自由解放”与“国家社会之纪律”这对核心矛盾。《国语》有云:“礼,国之纪也。”“礼”正是蒋氏孜孜以求的国家社会之纪律,用以对抗所谓的“个人自由解放”。而蒋氏对白话文的抨击更显无力,因为其抨击所使用的言辞本身就是白话文。所谓批判崇洋,他本人在中日交战白热化阶段,还提倡向日本学习,也备受诟病。蒋氏除了气势逼人之外,没有多大说服力。国民党理论权威贺衷寒似乎说得更加清晰:
自从自由主义介绍进来之后,就都把中国弄得不能统一了;自从阶级斗争的学说介绍进来之后,就把中国社会弄得不能够安宁了,这就是大家所共知的陈独秀、胡适之诸君所作的新文化运动的结果。新生活运动唯一的目的就是要把“五四”的新文化运动底(的)破坏运动,变成一个建设运动。[20]
贺衷寒去除了蒋氏的激切,在学理上指出“自由主义”与“中国统一”以及“阶级斗争”与“社会安定”、“破坏”与“建设”三对矛盾,如此一来,“统一”“安定”“建设”等老百姓渴慕已久的状态话语便归于新生活运动,那么五四新文化运动却恰恰成了这些美好状态的反面,而将这些后果统统归咎于新文化运动,这显然在理论上技高一筹,却不够中肯客观。
这两段话确实可见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国民政府对新文化运动的整体态度。而其中的“生活艺术化”却恰恰同时潜藏了“自由主义”和“阶级斗争”两大要素,应该是南京国民政府唯恐避之不及之大敌。但为何要重新启用?
其实南京国民政府不仅挪用了“生活艺术化”,连“新生活”这个词本身也有新文化运动的影子。1919年,李辛白在北大创办了《新生活》周刊,虽然杂志存续时间不长,但在当时却影响广泛。胡适在杂志创刊号上的同名文章《新生活》开篇即发问:“那样的生活叫做新生活呢?我想来想去,只有一句话。新生活就是有意思的生活。……反过来说,凡是自己说得出‘为什么这样做’的事,都可以说是有意思的生活。生活的‘为什么’,就是生活的意思。”[21]胡适的“新生活”显然是智性、充满探索的新生活。时任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的胡适在1934年3月25日,距离蒋介石是年2月在南昌行营发起新生活运动仅一个多月,就在《大公报》上发表长文《为新生活运动进一解》,这是新文化运动最重要的旗手对新生活运动做的最早、最中肯、最精辟的论述。他提到,新生活运动“只不过是学会了一个最低程度的人的样子……而救国和复兴民族……都得靠最高等的知识与最高等的技能”[22]。在1934年大灾之年提倡新生活运动,胡适的结语更是振聋发聩:“政府的第一责任是要叫人民能生活,第二责任是要提高他们的生活力,最后一步才是教他们过新生活。”[22]这是胡适对南京国民政府避重就轻、避实就虚的形式主义的温和却有力的回击。
与新文化运动一样,内里抱残守旧的南京国民政府却同样表现出对“新”字的情有独钟。值得注意的是,几乎是在新生活运动的同时,南京国民政府陆续组织成立了中国文化学会、中国文化建设协会、中央文化事业计划委员会等组织推动一系列文化运动来复兴中国文化。中国文化建设协会在其成立宣言中宣称“当此存亡绝续之交,如不急行从事于中国文化之新建设,国家民族宁复有起死回生之希望”。[23]“中国文化之新建设”似乎是对“新文化”的戏仿,新生活运动亦希望通过一场生活革命来塑造“新”人,而新生活运动之“新”本身也似从进化论意义来消解其复古的企图,从而接通与五四新文化时期求新的进步话语脉络。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裹挟“新”字的各种口号、各种命名纷至沓来,《新青年》《新潮》《新生活》,新文化运动、新女性、新人、新村、新社会,等等,一切都废旧革新,姿态鲜明,求新求进步,“新”相对于“旧”与“古”,“新”即进步。南京国民政府当然要以看似进步的话语“新”生活来掩盖其复兴古训的实质,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至少从表面上来说,这个对“新”的追逐是与新文化运动一脉相承的。在总体的进化论的进步话语体系下,西方的、现代的就是“新”的,是“进步”的。南京国民政府不但未公开与五四新文化运动决裂,甚至还借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某些词汇,如“新生活”和“生活艺术化”口号等,其口是心非的尴尬显而易见。
当然,从主观愿望上全盘否认蒋氏振兴民国的决心和举措显然有失公允,而理所当然地认定此处“生活艺术化”的儒学渊源就是彻底的文化复古则更是有失偏颇。此处的“生活艺术化”确实继承了中国固有传统礼乐教化“化民成俗”的帝王之术,然而,两者的根本区别也不容忽视。首先,复古外衣内里包藏着一颗追求现代化的雄心。正如日本学者对此做出的精辟分析:“新生活运动在抽象理念方面,是要继承中国传统思想,但在具体的礼仪问题上,却要求中国人的一举一动完全效仿近代西方(及日本)的身体美学及公共意识。”[24]36-37这一分析不仅道出了新生活运动追求现代化的时间维度,同时也引出了新生活运动的空间维度——西化,即在吃穿住行及公共礼仪上向外国人学习,以实现现代化,“新生活运动要求中国人把西方人的眼光内在化”[24]36-37。所以,新生活运动的顶层逻辑是基于古今中外的时空维度,而西化与现代显然是新生活运动整个理论构建的两根擎天柱,极力效法西方(及日本),使国民能够达及现代国家国民对公共领域的规则,成为合格的现代国家公民。西化与现代仿佛是一个同义词。因此,纯复古的“六艺”之说当然要假借更加“洋气”、更加现代的“生活艺术化”公之于众。而在这一点上,最有讽刺意味。所谓“西方”的莫里斯带来的“生活艺术化”,却恰恰在拒斥这种“现代”资本主义的商业文明,认为它是实现“生活艺术化”的最大障碍。当蒋介石对“西方”的“现代”文明顶礼膜拜之时,莫里斯却将其希冀的目光回望中世纪、远眺东方。
新生活运动对“生活艺术化”的官方阐释似乎总与文化界的理解是“鸡同鸭讲”“曲高和寡”。民间对“生活艺术化”总是张冠李戴,阳奉阴违。即使是叶楚伧主持、正中书局出版的官方新生活运动宣传品“新生活丛书”40本也难以齐备。而已出版的也是漏洞百出,如新生活运动艺术领域的4本代表作:林风眠的《艺术与新生活运动》、洪深的《电影界的新生活》、萧友梅的《音乐家的新生活》、唐槐秋的《戏剧家的新生活》都挂着“新生活”之名,却与新生活运动中的“生活艺术化”毫无关涉。
四、结语
客观来看,在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中华民族危亡之际,“生活艺术化”这种显然过于理想主义的口号理所当然地淡出了人们的视野。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人们重提“生活艺术化”之时,话语却依然如是,宋寿昌发表在《申报》1946年1月14日的《谈“生活艺术化”》:
“生活艺术化”是新生活运动的三大目标之一,所谓“生活艺术化”的意义,就是要使我们的日常生活充满美的感情,换句话说:我们的生活要感觉有趣味。艺术的本质就是美,美能使人类发生快感,所以艺术的生活,也可说是美的生活。[25]
除了第一句盖上新生活运动的大帽子,具体阐释上依然是“有趣味”“美”“快感”等词汇,显然依然是新文化运动时期莫里斯的“生活艺术化”。同样是1946年,丰子恺在《生活艺术漫谈之一》中讲:“英国工艺美术革命者莫理士(William Morris)曾以提倡‘生活的艺术化’著名于世。……他们倘看见莫理士风的单纯而坚牢的工艺品,反将指斥它们为不漂亮,不美,非艺术的呢。‘趣’之一字,实在只能冷暖自知,而难于言宣。”[26]
莫里斯的“生活艺术化”之“真趣”也许确实难以言宣,却已深入五四新文化运动那一代人的文化精神,而新生活运动中那个依靠威权强制阐释的口号却仿佛跌入历史的深渊,只能泛起了短暂微弱的涟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