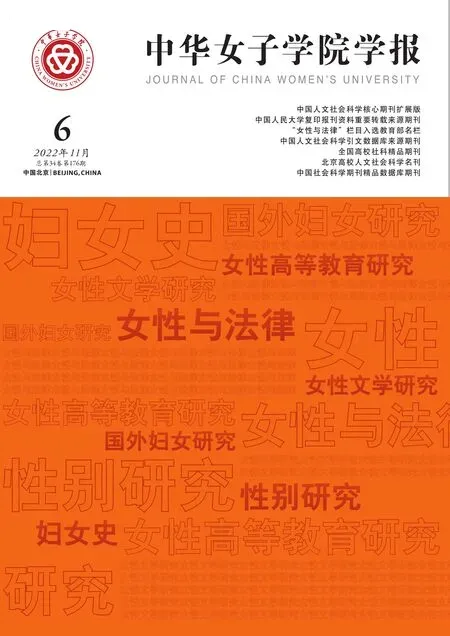在劳动中获得解放:基层传播视野下的妇女生产实践
——以解放战争时期晋冀鲁豫《人民日报》为例
2022-03-04李佳璐
李 飞 李佳璐
马克思曾高度评价妇女解放的价值与意义,恩格斯更是将妇女解放作为衡量一个社会的解放的标准,称“妇女解放的程度是衡量普遍解放的天然尺度”。[1]610马克思主义是在生产劳动视野中审视妇女解放的,原因在于无产阶级追求的所谓“劳动权”,“就是支配资本的权力,支配资本的权力就是占有生产资料”[2]6,即将包括妇女在内的所有劳动者都纳入劳动生产体系中来,参与到生产、管理、分配等全过程之中。因此,在这种意义上,“劳动权”不只是一种法律意义上的权利,更是一种争取劳动者生产自主性的实践。在这种生产劳动的视野中,妇女是与男子并无二致的劳动主体。劳动成为妇女解放、追求男女平等的“媒介”。一方面,其促使妇女与无产阶级一同追求劳动权,能够从异化的劳动关系中解脱出来,参与到生产资料的分配中,并将自身纳入共产主义运动;另一方面,劳动本身促使妇女走向社会,参与社会化大生产,培养自知自为的能力,在社会实践中践行男女平等原则。
在中国,共产党对妇女解放中追求劳动权的实践经历了一个从观念到普遍事实的过程。中国共产党继承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妇女解放成果,并形成了自身的妇女解放道路。1922年,中国共产党在第一个关于妇女运动的纲领性文件中,就强调劳动实践作为走向妇女解放的路径,“妇女解放是要伴着劳动解放进行的,只有无产阶级获得了政权,妇女们才能得到真正的解放”。[3]160由于当时党的工作重心在城市,妇女运动与妇女工作的重心也在城市。正如有研究者所指出的,其主体主要是城市中的女学生,只是随着中国革命重心从城市转向农村,其群众基础的主体才转化成为农妇。[4]这种转变也是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中思想与实践摸索的结果。1929年,毛泽东将妇女提升到“决定革命胜败的一个力量”[5]98-99的高度。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在领导妇女运动过程中积累了以劳动妇女作为自己的社会基础的经验。[6]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在1939年延安中国女子大学开学典礼上强调了妇女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作用,“全国妇女起来之日,就是中国革命胜利之时”。[7]妇女解放与劳动实践紧密结合,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妇女解放道路的重要特征。实际上,早在1937年,中组部就曾发布《妇女工作大纲》,强调“从争取抗战民主自由中争取男女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的平等,改善与提高妇女地位”[8],认为妇女解放的价值在于发挥妇女在社会生产实践中的作用。这是源于在抗日战争背景下,后方的妇女扛起了男子在前线打仗后留下的劳动生产重任,在社会生活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1941年10月,《解放日报》发表文章分析妇女解放问题,对“不从经济基础上去探究妇女被压迫的根源,而把妇女被压迫受痛苦归咎于男子;他们不向民族解放社会解放运动中争取妇女解放,而认为只要妇女觉悟起来,向男子斗争就够了”[9]为论点的妇女主义进行了批判,强调从社会物质生产中最根本的经济基础角度挖掘妇女受压迫的根源,在民族解放运动中发挥妇女的作用,同时实现特定阶段的妇女解放目标,追求更普遍的妇女解放。
一、研究缘起
解放战争时期(1946年6月底至1949年10月),追求劳动权、在劳动中获得妇女解放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实践。随着解放区土地改革政策与实践的推广及各种生产劳动宣传的展开,社会各阶层都卷入了新的社会生产关系调整之中,以实现最大限度的劳动解放,释放出更多的生产力参与劳动生产,尤其是在强调男女平等的《中国土地法大纲》公布之后。伴随着这一时期的劳动解放而出现的妇女解放,反过来因为生产领域更为平等的生产关系的出现,妇女参与到生产分配与生产管理中。在这个过程中,各根据地(后称为解放区)的党报为组织生产所进行的生产动员与生产传播作用不可忽视。1946年11月8日,邓颖超高度评价了中国解放区的妇女,认为在土改运动中劳动妇女的伟大力量明显地表现出来了,并强调“妇女是改革土地制度和人民解放战争中一个不可忽视的极重要的力量”。[10]
晋冀鲁豫《人民日报》创刊于解放战争爆发前一个月(1946年5月15日),一直到1948年6月14日,是晋冀鲁豫中央局机关报。作为延安整风后创办的晋冀鲁豫中央局机关报,其直面边区/解放区政治、经济、社会生活中的各种问题,并通过党报来指导日常工作,让人民群众参与到“国家大事”中去。这些“国家大事”包括基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实践,对组织劳动生产、调整生产关系等与劳动权紧密相关的变革,从而实现劳动解放。与劳动解放相伴随出现的妇女解放,也是晋冀鲁豫《人民日报》关注的话题。晋冀鲁豫《人民日报》作为该区党指导基层工作的组织工作中心,是当年党的妇女工作与经验传播的见证者,更是党指导、组织妇女开展生产活动,即妇女解放的见证者与历史材料。因而本文将解放战争时期的晋冀鲁豫《人民日报》作为史料,考察当时环境下党如何将妇女从受压迫的状态中解放出来,并变成后方生产的主力。
所谓基层传播,是指中国革命在革命年代形成的服务于群众宣传和社会动员的传播实践,强调对传播内容、传播主体、传播媒介和传播受众的四重改造。[11]从基层传播的视野来审视解放战争期间妇女在劳动中获得解放的历史实践,强调的是在基层社会变革过程中,传播内嵌于社会中,是整个社会变革的一部分。基层传播与基层实践紧密结合,在贯彻落实党的政策,在新生产方式、新劳动主体形成、新的更平等的男女关系形成过程中发挥着积极的作用。本文通过分析晋冀鲁豫《人民日报》基层传播的具体情况,管窥党领导的妇女解放工作是如何在基层传播层面以劳动解放促进妇女解放的。
二、基层传播:以劳动解放促进妇女解放
解放战争时期,后方生产备战成为基层生产动员中极为重要的内容。在大量男劳动力抽调到前线、劳动力短缺的情况下,妇女在生产运动中贡献了自己的力量。从1946年6月1日到1948年6月4日,晋冀鲁豫《人民日报》文章中,篇名中包含“妇女生产”的有7 篇、“妇女劳动”的2 篇、“妇女互助”的6 篇;正文中包含“妇女生产”的有49 篇,“妇女劳动”的33 篇、“妇女互助”的44 篇;均以1947 最多,而1947年是土改大力推进的一年。这种广泛的对妇女劳动的报道,让妇女劳动经验与基层生产动员变成一种日常生活实践,在基层传播了妇女劳动的新经验、新常识。
(一)基层传播内容:妇女劳动经验
拉扎斯菲尔德(Paul F.Lazarsfeld) 和默顿(Robert King Merton)认为大众传媒具有社会地位赋予功能。[12]报道本身赋予了事件重要性,尤其是晋冀鲁豫《人民日报》这样的机关报,所报道之事皆为当时的工作重点。自创办以来,该报就对劳动生产进行了广泛报道。到1947年,该报涉及生产运动的文章多达33 篇,包括军区展开节约生产运动、纪念“二七”职工大生产运动、生产节约运动、春耕大生产运动、防旱备荒生产节约运动等,还包括各地基层落实生产运动的经验介绍,绝大多数文章会提及妇女劳动。妇女劳动与各种促使生产解放的具体生产运动紧密结合在一起,成为基层社会组织劳动生产中的重要议程。在基层传播实践中,“劳动解放”的目标中内嵌了妇女劳动解放,赋予了妇女劳动重要的社会地位。
首先,生产运动在基层传播中起到了社会示范作用,让社会看见妇女的劳动贡献,提升了妇女的生产自信。山西长治二区苏店原本盛行轻视妇女的思想,但互助组很快用实践回击,并赢得了尊重:毕二云互助组的妇女割谷快,“二云嫂一天割了二亩四,秋国老婆一天割了二亩二”。后来,该地更是提出了“妇女儿童齐动手,能顶男人多半手”的口号。[13]这些在晋冀鲁豫基层中广为流传的经验,肯定了妇女解放带来的妇女劳动经验价值,鼓励妇女在后方生产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1947年的晋冀鲁豫地区,妇女儿童等辅助劳动力担负了全区农业生产中百分之三十到四十的生产任务,很好地支援了战争。很多妇女在农业生产中学会了“全把式”。[14]在这种基层农业生产中,妇女和劳动实践紧密结合,打破了此前男劳动力对劳动技能的垄断,显示了妇女的力量,培养了妇女的劳动自信。正如潞城魏花园的妇女会委员孙秀芝所言:“青壮年都去参战也碍不着种麦,有年纪的摇耧,俺妇女帮耧,还不是一样种麦吗?”[15]这样的妇女自信是妇女广泛参加社会劳动,在劳动中的贡献被社会看见、被认可所产生的生产自信。这种自信让妇女从此前的劳动畏难情绪中走出来,开始主动承担起生产中的责任。
其次,基层传播本身反过来也推动了生产实践的发展,用妇女解放的成果推动生产。大生产运动中,一个很重要的经验是对妇女劳动实践与劳动权的肯定,如树立劳动模范,表彰先进。晋察冀边区在推动生产实践过程中,奖励了各种模范妇女,包括韩凤龄(大生产运动积极分子)、张小丑(青年妇女模范)、刘金荣(纺织能手)、戎冠秀(拥军模范)等。[16]这些针对生产实践推出的妇女模范是人民英雄史观的体现,让普通的劳动妇女因为劳动生产实践成为当时劳动解放背景下的聚光对象。她们的事迹在基层传播中为广大妇女提供了行动榜样,为妇女更广泛的劳动参与起到了动员和宣传作用。
再次,生产运动与基层传播互动激发了妇女的生产积极性,在生产实践中巩固了妇女解放的成果。解放战争时期,基层诉苦会在动员妇女参加土改实现翻身后,进一步激发了她们的阶级自觉,并使其在走出家门后参加社会生产中的联合与生产互助。这种联合与生产互助显示了生产关系调整对生产力的解放作用,妇女生产互助实践丰富了农村生产管理的精细化。例如,阳城范村女劳动英雄赵美英在劳动互助中按照工作需求随时工作,纺花织布、犁地锄麦、开荒种地、送粪等样样精通,并通过精准的配工搭配,提升了工作效率,她领导的互助组十天内就能锄苗1300 亩。[17]妇女在劳动生产中还形成了相互配合、相互帮助的劳动互助关系。这种劳动互助通过发挥集体合作与资源配置的优势,克服个体单打独斗的不足,提高了生产效率,激发了生产热情。1947年太行春季百日纺织运动中发动了744634 名妇女参加纺织(占全区妇女劳动力的74%),共织布760 万斤,供给了全区军民穿衣,并帮助华北军民熬过国民党的经济封锁,实现了“生产自给”“生产救荒”。[18]妇女在劳动生产实践中帮助边区共度时艰,使得妇女工作的重要性与工作经验被广泛传播,从而进一步巩固了妇女解放成果。
(二)基层传播主体的改造:妇女走出家庭劳动
解放战争期间,晋冀鲁豫解放区在战争背景下广泛进行生产动员,让妇女走出家庭参加劳动实践。当时,在妇女没发动起来前,很多地区“对村中的事了解不多,过去妇女仍然被关在家里,很少参加村中一般的活动,客观上造成她们的落后”。[19]妇女的日常生活空间被局限在家庭,和社会生产形成了隔阂。与此同时,劳动并没有和妇女紧密相连,在特定的地区,劳动成为一种不得不为之、谋求生计的方式。1946年河北武安城在发动妇女生产前,从事劳动的主体是贫苦妇女——76 人纺织,205 人下地劳动。在当时,一些妇女养成了爱吃穿不劳动、懒惰腐化的习惯,如“抽洋烟,整天串门子打牌”“热天坐在家里还要人打扇”[20],亟须将其改造成为劳动主体。
当时,中国共产党要推进生产运动,就必须改变广大妇女与生产劳动隔离的现状,扩大劳动实践主体的范围。中国共产党通过组织动员妇女参加社会化生产劳动,重构家庭与社会关系,成为当时妇女解放的切入点。[21]早在1942年12月在陕甘宁边区高级干部会议上,毛泽东在其《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报告中便对当时的妇女组织没有找到工作方向提出了批评,认为应该研究与帮助广大妇女群众参加劳动生产。[22]在解放战争时期,党的妇女工作则是通过对基层妇女进行生产劳动动员实现的。动员基层妇女的目的是,通过将妇女从传统社会生产关系中解放出来,成为劳动的主体,以劳动解放来促进妇女解放。在当时解放区,妇女参加纺织、下地劳动等关系到根据地自给自足,同时能够让妇女在经济上获得独立,提高妇女社会地位。[23]发动妇女参加生产意味着一方面要培养妇女劳动生产实践能力,另一方面要将以往不参加劳动,甚至是边缘的人均纳入生产劳动中。在根据地民主政府和妇联会的推动下,武安城政府改造被视为寄生性群体的妇女下地劳动,挑水纺花,同时组织妇女民校,举办妇女生产学习竞赛等。在这样的动员与学习技术后,武安城过去根本不劳动的妇女763 人学会和正在积极学习纺花,73 人学织毛衣,43 人学用织袜机织袜子,470 人参加田地劳动。[24]这样,劳动主体结构由从前未曾或很少参加社会劳动的妇女变成劳动实践主体,同时被视为“寄生性群体”的妇女也被改造纳入“劳动为荣”的队伍之中。
(三)基层传播媒介:以传播催动妇女劳动意识觉醒
基层传播的制度基础是中国共产党依靠组织的力量深入基层社会,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的体现。[25]晋冀鲁豫《人民日报》作为当时晋冀鲁豫中央局机关报,对该地区全局工作进行指导,不仅组织基层工作、传播先进经验,还扮演着基层传播中枢的角色,因而既是地区全局性媒介,同时又兼具基层传播媒介的功能。与此同时,其晋冀鲁豫中央局机关报的身份,传播的内容代表着党组织的态度与意志,因而该报具有很强的组织传播性质。
晋冀鲁豫《人民日报》同时也介绍了基层组织中基层传播媒介的运作机制。其中典型代表当属后池村的生产宣传经验。该村的广播和大众黑板报成为动员妇女的最有力的武器。大众黑板报的媒介成本低,在被媒介化过程中以简明扼要的方式传播本地日常生产生活中的大事情。广播这种新媒介传播形式则和基层生产动员紧密结合——在基层组织宣传中,一旦上边放广播,下边就进行宣传解释,使群众容易接受。这样一来,在基层宣传中,模范人物的模范事迹经由广播台的广播表扬与宣传员讲解,被赋予了重要位置,受到当地的尊重,使得上广播成为妇女力争上游、高扬主体性的动力。“人家能上广播台咱就不能上?咱也好好干。”[26]正是这种对在基层广播中被传播、被认可的需求驱动,妇女们的生产积极性被调动起来,完成了此前被认为是男人的工作。由此可见,基层传播媒介的运用能够带来妇女劳动的成就感、获得感,通过让她们成为劳动实践中新模范的方式,将基层妇女动员起来,并逐步内化为自我劳动意识,实现了劳动意识的自我觉醒,以饱满的精神面貌参与到社会化大生产中来。
三、基层中的群体传播:在参与和传播中解放
在基层传播中,为有效提高妇女的阶级意识和争取男女平等的信心,解放区开展了形式多样的妇女政治动员活动,如“妇女座谈会”“诉苦大会”“婆婆会”“媳妇会”等群体传播活动,来发挥党领导妇女组织的作用。各种妇女群体通过参与表达政治诉求,在交流传播中解决矛盾,从而保障在更大范围内争取妇女劳动权。
(一)妇女座谈会:政治传播与基层工作形式
妇女座谈会是一种了解妇女群众思想、工作情况,表达相应政治诉求的途径。晋冀鲁豫边区妇女代表曾于1946年9月11日集会座谈,拥护宋庆龄、邓颖超参加国际妇女大会。到会代表二百余人,翻身的妇女与群众领袖共占到会代表的百分之六十。[27]由此,解放区的翻身妇女与群众领袖作为一种新的力量出现在政治舞台,将解放区与世界联系起来,向世界表达着解放区妇女的心声。
妇女座谈会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妇女的工作方式,在基层广泛应用。首先,妇女座谈会是了解基层情况的手段。在土改中,武乡韩壁村可以实现耕者有其田,正是建立在对34 名妇女及其他群体进行座谈的基础上的,获知了基层妇女中存在着“翻身是男人事”“怕报复”等错误思想,并制定了相应的对策推动妇女事业发展。[28]其次,妇女座谈会也是一种思想宣传的动员手段。1948年《人民日报》宣传安国七区东恍里村的土改经验,提及该村召开妇女座谈会,将之作为一个思想动员的讲台,同时妇女座谈会也是一个移风易俗、重塑价值的过程,生产积极分子带领妇女参加生产劳动,“逐步打破了妇女以劳动为耻与认为妇女不会下地劳动的错误思想,树立了劳动光荣的观念”。[29]再次,妇女座谈会是我党完善妇女工作、实现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一种形式。例如,冀南、太行、太岳各区的妇女座谈会对妇女工作进行了检讨和自我批评,认为此前抗战中的妇女工作主体存在相当大局限,“是以能说会道的妇女为工作对象”,而没有重视“不识字不会说的广大劳动妇女力量”。[30]同时由于在男女平等问题上片面强调妇女利益,导致发生了男女对立、婆媳不和等现象,结果“路线方针错了,工作没有成绩,妇女工作干部也就失掉对妇运的信心”。[30]这种对妇女工作的自我检讨与批评,强化了妇女工作的阶级基础与群众基础,为妇女工作争取了更多的支持力量,从而避免了妇女工作窄化。
(二)诉苦大会:土改运动的妇女政治传播形式
诉苦大会是在土改运动中被广泛运用的工作方式之一。尽管在进行土改动员、斗地主等基层传播活动中不乏男性,但效果相对更好的是以妇女为主体的诉苦活动。诉苦是革命理性与情感工作相结合的体现,而其中苦情戏和共克时艰的情感宣传更是主要的传播内容。因此,基层组织充分发挥女性在思想工作中的情绪感染作用,推动基层土改运动的深入开展。在晋城三区坪头村减租运动中,水和的母亲控诉被债主、地主、恶霸们压迫时,现场全体起立,高呼“你的痛苦就是我们大家的痛苦!天下农民是一家”,群众干部们也当场检讨了自己一年多没有给老太太解决问题的错误,这使得老太太心里存着的闲气也就消了。[31]在这种基层传播的诉苦活动中,情感传播比逻辑说理具有更重要的作用。当穷人进行诉说,对社会不公与悲惨命运进行控诉时,会引起在场有类似经验的人的情感共鸣。苦难作为穷人的普遍性经验,成为连接群众的纽带,阶级自觉与反抗、变革的意识也在此萌发。在这种政治状况下,基层群众干部进行检讨与启发,推动诉苦大会向推动土改、变革封建生产关系的方向发展。诉苦仪式中凸显了群众的力量,深化了“受苦人共同体”的认同,并催生了阶级自觉,即所谓“天下农民是一家”。这种认同有助于让群众认识到团结起来力量大,更容易推动土改工作。
实际上,在各地土改中,妇女成为诉苦的主体,诉苦内容包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例如,冀县“有三个妇女没有房子住,在地主和富农的宅子里时时遭受房主驱逐;一个媳妇一夏天只有一套单衣”[32],林县则深挖妇女在家庭与社会生活中是受苦最深的人的经历,“许多男人被地主逼的远逃,在家顶门应事,挨打受骂的是妇女;很多妇女给地主当使女、小老婆,都是因还不起租息所迫”[33]。在基层,正是启发贫苦妇女诉苦,从个人的日常生活经验出发,使得深受社会压迫的妇女在大庭广众下将憋在心里的苦楚以扯家常、漫谈等方式说出来,成为发动诉苦的关键。同时,通过比较发现妇女的典型案例做诉苦示范,启发更多的妇女从麻木状态或落后状态中走出来,意识到自己的处境,从而认识到阶级对立与妇女团结争取解放的必要性。动员过程的诉苦不单纯是诉苦,不仅有着自己独特的发声机制,还有着完善群众诉苦、干部检讨、启发动员、提高意识的一整套完整流程。这让妇女群众从长期的剥削痛苦中苏醒过来,建立起“阶级斗争”“封建剥削”等抽象概念与自身生命经验的关系,并在诉苦的过程中,被纳入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议程中,参加相应的政治运动,在现实政治斗争中翻身。
(三)婆婆会:传播与妇女、家庭矛盾解决机制
婆婆会着力解决的是家庭内部婆媳关系与矛盾,促进妇女群体内部的团结。黎城的经验是直面纺织生产中出现的妇女与家不和的问题,通过召开媳妇会、婆婆会,采取“二八分红”的方式,即“给外纺织家庭得二媳妇得八,给自家纺织媳妇得二家庭得八”来改善婆媳关系。[34]在这种劳动分配之中,考虑到纺织婆媳作为不同社会群体,属于不同利益主体,因而具有不同的利益诉求。这种劳动分配有利于营造向上和向善的家庭环境,兼顾了各方利益,减少了妇女内部因利益分配不均带来的妇女解放的阻力。同时,婆婆会发挥调整旧家庭关系、让家庭关系走向和谐民主的功能,使得妇女能够在新型家庭环境下获得理解与解放,从而身心愉悦地投入日常劳动生活。冀县二区堤里王村在调整婆媳关系过程中开了三个会来解决婆媳矛盾:一是青年妇女与有婆婆的中年媳妇座谈会,了解她们社会生活与参加社会活动的需求;二是闺女会议,主要是动员闺女们在家庭中发挥建设性作用,如参加家庭劳作,克服挑唆婆媳矛盾的坏习惯;三是婆婆会议,在会议上说明媳妇诉求,妇联会做婆婆思想工作并立新规矩,建设新型的家庭关系,让婆婆们安心。[35]婆婆会是将婆媳作为有着不同利益诉求的群体,发挥妇女组织的沟通与建设性作用,从而调整家庭内部的关系,使得婆媳之间、姑嫂之间的关系得到了改善,促进了家庭民主和睦。这种和睦关系避免不同家庭主体之间因为利益分配出现内讧,在翻身斗争中被地主利用做文章,从而各个击破。[36]而妇女组织的作用被认可后,会进一步发展壮大,促进了妇女解放。
四、余论:妇女在劳动中解放的历史经验
解放战争时期,晋冀鲁豫出现了丰富的以劳动解放促进妇女解放的基层传播实践。妇女在党的领导下,从家庭走向社会,从个体到互助合作,并反过来促使劳动实践带来的妇女解放向生产关系领域扩展,扩大了妇女劳动权的实践范围。[37]妇女劳动权也向分配领域延伸,妇女开始参与到处置生产劳动所得之中来,形成新的基于互助合作的分配关系。晋冀鲁豫《人民日报》中记载着互助合作中妇女在劳动中获得解放后,在管理分配制度形成过程中的贡献。例如,1946年,女劳动英雄赵美英在石振明创造的三票制度基础上,针对“所得分归妇女自己,还是归家庭”的问题进行了补充,提出了七三分红办法,即“七分归家庭,三分归妇女自己得”。[38]又如,长治二区互助组中,天河曹林水队三分队的妇女组织参加秋收时规定了家庭分红办法。[39]这恰恰是在边区政府的政治保障下,以基层传播与协商的方式让妇女参与到劳动分配管理制度建设中,从而真正保障妇女劳动权。
这正是解放战争时期,党领导的妇女运动在农村基层之中,以劳动解放促妇女解放的缩影。广大农村妇女在基层传播的动员下,走出家门参加生产劳动实践,以妇女解放促生产,并以劳动生产实践推动事业发展,进一步扩大了妇女解放成果。在当时解放区的妇女政治动员形式多样、成效巨大,有效提高了妇女的阶级意识和争取男女平等的信心。在基层传播中,实现妇女生产动员,并以妇女座谈会、诉苦大会、婆婆会、媳妇会等群体传播活动发挥妇女群体在参与表达中的政治诉求,并搭建以协商方式解决问题矛盾的机制。这样的基层传播机制将农村妇女组织到生产型的社会空间中,成为生产劳动的主体,并在生产互助合作中进一步获得分配权,参与劳动管理与分配制度的制定。在这样的中国特色的妇女解放方案中,妇女劳动权的实践是回归到当时妇女中的绝大多数——广大农村劳动妇女。她们不再只是待启蒙的、亟须被唤醒性别意识的女性个体,而是在党的领导下积极参与社会生产劳动实践、创造物质财富的主体。在劳动实践中,妇女不再是依附者,而是劳动的主体,并能够获得自身自主性。在劳动实践中以一种“嵌入式”的方式推动妇女解放,努力创造面向绝大多数穷苦人的男女平等的新秩序。在这种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嵌入式”的妇女解放道路中,妇女解放是整个新秩序中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其不仅服务于当时中国社会整体矛盾的解决,而且在劳动解放过程中与人民事业协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