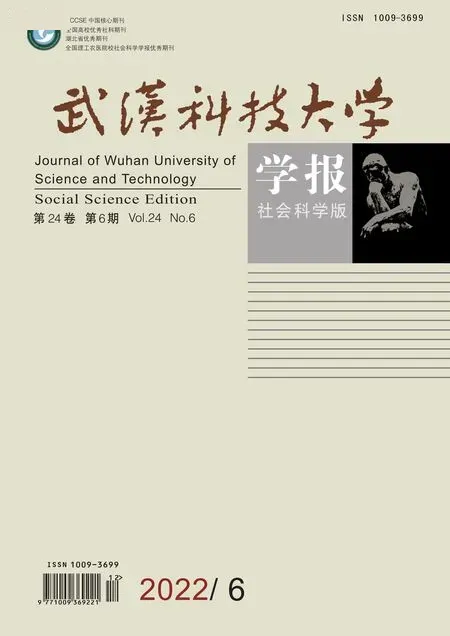论宋代社会的泛官化
2022-03-02李大秀
廖 寅 李大秀
(河北大学 宋史研究中心,河北 保定 071002)
钱穆先生说:论中国古今社会之变,最要在宋代。宋以前,大体可称为古代中国,宋以后,乃为后代中国。秦前,乃封建贵族社会。东汉以下,士族门第兴起。魏晋南北朝迄于隋唐,皆属门第社会,可称为是古代变相的贵族社会。宋以下,始是纯粹的平民社会。除却特权阶级外,其升入政治上层者,皆由白衣秀才平地拔起,更无古代封建贵族及门第传统之遗存[1]。说宋以下是“纯粹的平民社会”未免夸张,但是,宋代的确开始呈现出平民化的趋势,这种平民化表现在官与民之间的界线不再像贵族社会或变相贵族社会那样等级森严,而是变得模糊混沌。从“民”来说,官越来越向民接近,所以称“平民化”;从“官”来说,民亦越来越向官靠拢,不妨称之为“泛官化”。这两种趋向的运动是同时存在、相辅相成的。不过,“平民化”看起来更符合历史发展的潮流,所以,历来的研究多侧重于“平民化”①,而对于“泛官化”则少有人关注。但事实上,宋代社会的“泛官化”对于宋以降中国社会的影响同样非常深刻,完全有必要予以专门的剖析。
一、宋代假官的泛滥
“官不皆真官”[2]302,从国家定位来说,宋代的官员可分为真官与假官两大类。真官是国家正式的官员,其差除之法,大别有三:“自两府而下,至侍从官,悉禀圣旨,然后除授,此中书不敢专也;自卿监而下及已经进擢,或寄禄至中散大夫者,皆由堂除,此吏部不敢预也;自朝议大夫而下,受常调差遣者,皆归吏部,此中书不可侵也。”[3]8965三种差除之法大致对应官员的三个层次:圣旨除授-高层官员;中书堂除-中层官员;吏部部注-下层官员。宋代正式官员的数量非常有限,据李弘祺的统计,北宋前期,官员总数大概在15 000员左右,北宋后期,官员总数大概在30 000员左右,南宋最高峰时期官员总数为43 000余员[4]。但在真官(正式官员)之外,宋代还存在着一个庞大的假官(非正式官员)群体,“非真是作官也”[5]。
假官之中,首当其冲的是假版官。“假版,班品之卑者”“皆假官也”②。“假板官,行于衰乱之世”,尤盛于晚唐,“藩镇自辟召,谓之‘版授’,时号‘假版官’,言未授王命,假摄之耳”[6]60-61,“姑从板授,盖非真官”[7]627。相对于“真官”,假版官可直接称为“假官”。真官,又称真命、真授,“必奏真命,未尝假版”[8]334,“以假版而为真授”“异恩也”[9]506。宋承唐制,依然保留了假版官制,但除授权却从藩镇收归吏部。假版官在元丰改制前又称假试官、试衔官[10]6,如试秘书省正字、试大理评事。元丰改制,“以阶易官”,假试官改成了假阶官,如试大理评事,“元丰为假承事郎”,试秘书省正字,“元丰为假承奉郎”[10]28。
宋代假版官虽然改由吏部除授,但与吏部正式注授的官员存在一本质差异,那就是“不理选限”。“选限”,指对未出官人与未命官人候参铨选注官的期限的限制[11]。“不理选限”,表示没有资格参与铨选。所以,“自假版官而理选限”,与“自选人而改京秩”一样,“皆非常之恩也”[9]564。“自假版官而理选限”,又可表述为“以假版而为真授”[9]506,这意味着:“理选限”是 “真官”“真授”,“不理选限”则是“假官”“假授”。
是否“理选限”与官员出身有着密切的关联。宋代官员出身以科举为最正,荫补为次正,其他皆为“杂流”[12]。科举、荫补出身者虽亦有“不理选限”的假官[13]8229,但多数是“理选限”的。杂流出身则基本“不理选限”,其中尤以进纳、军功最为典型。原则上,“进纳、军功,不理选限”[14]3718。“国法,固许进纳取官,然未尝听其理选”[14]10281,军功则多“比类”[15]763进纳。需要说明的是,对于假官,平常时期的“正法”是“不理选限”的,但非常时期往往会“特与理选限”,如靖康元年(1126年)圣旨:“借士庶金银,如纳数多,当议量度于武官内安排,特与理选限,不碍正法。”[16]按照“正法”,“因军功捕盗转至升朝官,非军功捕盗人转至大夫以上,方许作官户”[17]1518-1519。升朝官最低阶为正八品通直郎,非军功系列大夫最低阶为从六品朝奉大夫[18],杂流出身者“理选限”的品级明显高于常规的假版官。
先来看进纳③。进纳,“俗谓之买官”,包括用金钱直接买以及“因纳粟赈粜及助边者”[19]。中国买卖官员的历史很悠久,但“进纳官”的提法却主要存在于宋代,元丰时期,专门制定有《进纳官法》[14]3711。进纳在宋代自始至终属于杂流,“宋兴以来”,“纳粟授官,止赎刑而已”[20]1039,“富民得试衔官者,不得与州县官属、使臣接见”[3]1820。“进纳买官,元丰系有正法”[17]1518,正因为如此,北宋中前期,进纳官基本维持在一个适度的规模,没有对社会造成重大冲击。天圣八年(1030年),朝廷籴麦京师,“数且足”,“有豪姓欲入官者以数十万石,因权幸以干掖庭”,亦未得逞[3]2538。可见当时买官是有一定难度的。
宋代进纳官的泛滥始于1100年宋徽宗即位。大观四年(1110年),臣僚言:“方今入仕之门,多流外之员,其冗滥尤在于进纳”,“朝廷以三路财用少乏,边储未丰,近年以来出颁假将仕郎等告牒,比之往岁不啻数十倍”,“一假将仕郎,其直止一千余缗,非特富商巨贾皆有入仕之门,但人有数百千轻货以转易三路,则千缗之入为有余,人人可以滥纡命服,以齿仕路”,“遂致此流遍满天下,一州一县无处无之”[13]4518。大观四年相距宋徽宗即位刚好十年,所谓“近年以来”,明显是指宋徽宗即位以来。“比之往岁不啻数十倍”“此流遍满天下,一州一县无处无之”,进纳官泛滥之势已成。
进纳官泛滥加速官价贬值,而官价贬值又进一步加速进纳官泛滥,这是典型的恶性循环。就拿文官价格最低的助教来说,元祐三年(1088年),起居舍人彭汝砺言:“今输金至三千及五千缗,入为助教、监簿。”④当时的助教价格至少为三千贯,此后一路下跌,建炎元年(1127年)跌至2000贯[13]4520,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跌至800贯[13]4522,绍熙五年(1194年)跌至500贯[13]4737。考虑到南宋物价较元祐时期上涨5倍左右⑤,元祐三年助教的实际价格当是建炎元年的7.5倍、绍兴三十一年的18.6倍、绍熙五年的30倍。北宋中前期,因为官价高,买得起的都是一、二等大户,熙宁三年(1070年),编修中书条例就说道,“进纳出身人”,“类多是兼并有力之家”[13]5166。到南宋初期,朝廷已将卖官对象瞄准了“中产之家”。建炎元年诏:“今增立诸州文学而下至进武副尉为六等,庶几中产之家易于献纳。”其标价在700贯至2500贯之间[13]4520。绍兴元年(1131年),中书舍人程俱言:“三千缗,在今日亦中人之产也。”⑥[21]增立销售的官衔的确适合“中产之家”。在众多待售官衔中,助教既便宜又相对好听,最受青睐,以致“市井、巫医、祝卜、技艺之流,孰不以助教自名”[22]。
除了向政府买官之外,富人还可向大官僚买官,这虽然不叫“进纳”,但本质是一样的。宋代中高级官员皆有荫补权,官品越高,荫补资格越多。荫补资格除了荫庇亲属之外,亦可变相出售。高宗时,有刘式者,以三千贯就宰相朱胜非“买门客恩泽,奏其子刘师心”,“又为湖南土豪姓胡人以八千缗买给使恩泽,奏承信郎”[23];“豪民徐国澄纳钱二千二百缗”,就资政殿学士杨椿买“门客恩泽”[24]3341。前述假版官中的登仕郎,即主要授予宰执门客[10]29,“富民居多以赀而入”[25]。从市场规律来说,政府与大官僚出售的官价应该差不多,像朱胜非出售的承信郎,价值八千贯,与政府售价完全一样[15]788。
再来看军功。与进纳不同,军功原非杂流,自先秦以至北宋初期,军功始终是正途[26]。大概从真宗朝开始,随着军功集团的消解和士大夫政治的确立,军功才逐渐杂流化。这种格局一直延续至清朝,即“自宋、明后,重文轻武,积以成习,士习于贵,兵习于贱”,遂有“好人不当兵,好铁不打钉”之谚[27]。
军功杂流化,除了士大夫话语霸权,军功官的泛滥是另一根本原因。与进纳官一样,军功官泛滥亦肇始于宋徽宗即位。建炎二年(1128年),臣僚言:“自数十年来保奏功赏,例多不实,或亲戚之私,或权贵之荐,或医巫卜祝之徒,或工商皂隶之贱,未尝临阵遇敌,辄冒功赏,军士怨愤久矣。”[13]8990从臣僚奏章来看,军功官泛滥最显著的特征是非军人以军功的名义获官者太多,这些非军人军功官涉及的群体非常广泛,既有权贵阶层的家属,也有“医巫卜祝”“工商皂隶”等平民百姓。
到南宋前期,军功官更是泛滥成灾。“南渡初,诸大将军中有所谓武功队,谓一队之人皆武功郎、大夫”[28]3716。宋高宗皇帝就说道:“小使臣阙只二万余,今借补者何啻三五十万。”[24]531仅小使臣就多达三五十万,全部军功官规模之大可想而知。如此多的军功官,政府根本无法进行有效管理,“第补授既多,稽考实难”,这就为各种违法交易、“顶冒脱漏”提供了广阔的空间。“顶冒脱漏者无穷”,虽然政府也有查实的情况,但“司之所发摘者不过一二”,绝大多数无法查实,所以,“补授帖牒转入他人之手,为国耗蠹,无时而已”[28]3716。违法收买、冒名顶替者自然主要是富人。绍兴三年(1133年),熊彦诗曰:“近年以来,郡邑上户系名军中,日迁月转,遂为官户。”[29]143绍兴十七年(1147年),臣僚又言:“富商大农之家,多以金帛窜名军中,侥幸补官,及假名冒户,规免科须者,比比皆是。”[13]7485“窜名”又称“寄姓名”,“寄姓名得官者甚多”[20]4597,“寄名军籍”[24]962,“身居市井,实不至军”[30]。
非军人军功官泛滥还与宋代军人的家庭结构相关。宋代“兵习于贱”,大户人家不愿从军,熊彦诗甚至建言“州县上三等人户不得从军”⑦,因此,宋代军人多来自于小户人家。“转官恩例,照条回授”[31],宋代的转官在一定条件下是允许回授给亲人的。但是,军人出身的官员家小人少,往往少有回授的对象,他们不得不倒卖多余的转官恩例。绍兴二十二年(1152年),右谏议大夫林大鼐就说道:“武臣奏荐,多出军中,军中爵秩高而少族姓,凡有奏荐,同姓皆期功,异姓皆中表,市井暴富者,咸附会以进。”[24]2663-2664
二、宋代假官泛滥一定程度上是爵官合流的结果
俗语说,“加官晋爵”,“官”与“爵”原本属于两个系列,“官以任能,爵以酬功”[20]7552,“爵以定崇卑,官以分职务”[32]。先宋时代,中国的爵制经历了一个从封闭到开放、从价重到价微的过程。西周时期,“爵以驭其贵”[33],授予对象仅限于贵族,完全是封闭化的。秦汉时期,在传统爵制(公、侯、伯、子、男)之外,开发出了新的面向社会大众的爵制(公、卿、大夫、士),典型的如二十等军功爵制。先秦秦汉的爵,不仅是社会身份的标志,而且还附有广泛的特权,如占田和减刑。正因为如此,当时整个社会弥漫着“重爵”的风气[34]。然自秦汉以降,随着“官本位”的强化,爵逐渐走向虚散化,这一过程在晚唐五代基本宣告完成[35]。虽然其早已“虚散化”,但宋代爵制始终行而未废⑧。
在“重爵”的时代,“爵”对于社会大众具有非常强的吸引力。“武爵以厉战,粟爵以劝农”,“武爵任则兵强,粟爵任则国富”[36],价重之“爵”足以诱使社会大众建功立业、“入粟拜爵”,秦汉时期即是如此。相反,在“轻爵重官”的时代,价微之“爵”对于社会大众的吸引力将会非常有限。
宋朝曾经试图复古秦汉式民爵,殊不知时已易、势已移。太宗端拱元年(988年),“赐诸道高年百二十九人爵为公士”,“秦汉以后,不复赐民爵,自籍田礼成,始复赐焉”[3]653。端拱二年(989年),再“赐诸州高年一百二十七人爵公士”[14]4079。淳化五年(994年),“诏诸州能出粟贷饥民者赐爵”[14]93。同年,“澶、密等州民年八十以上吕继美等二十九人,并赐爵公士”⑨。真宗咸平五年(1002年),“赐京城父老百十九岁祝道品爵公士”[14]118。景德年间,“福建民有擒获强盗者,当授镇将,以远俗非所乐,并赐公士,自后率为例”[14]4079。至此,宋朝所赐民爵,既有高年爵,也有粟爵和军功爵。大中祥符二年(1009年),开封府“年八十已上赐爵公士,九十已上者授摄助教”[7]819,爵与假官开始混同使用。同年,“乾封民以天书降其地,赐爵公士”[37]546。
总体而言,北宋前期的赐民爵,基本属于偶然性行为,并没有形成制度。仁宗康定元年(1040年),名士尹洙上奏《鬻爵法》,试图将赐民爵制度化。其方案如下:
朝廷创定鬻爵之法,封出空名爵牒,散下州郡,人入粟授爵。今定爵二等:
第一等爵,许畜女使,许使浑银饮飲食器。凡欲授第一等爵者,如元係州府县镇城郭等第户,即入粟一百石,如不系户等,即入五十石。
第二等爵,许以珠金为妇女服饰,如犯公罪,许赎。凡欲授第二等爵者,入粟五百石。
右入粟每百石,令入钱三十贯。……所定爵名,并更有合条约事件,乞下中书门下参酌施行。[38]
尹洙此奏,《续资治通鉴长编》亦有记载,但略有差异,“第一等爵”,《续资治通鉴长编》称为“下爵”;“第二等爵”,《续资治通鉴长编》称为“上爵”。尹洙的提案遭到了与会者的一致反对,“其议遂寢”。反对者的理由是:
古设民爵以赏武功、赐耆艾,今则鬻爵以规货财,其编户产薄者,或子孙骄靡,希一爵因至贫窘,……此礼义不立也。先王之域民也,贵贱有差,器服有别,今使下愚之民咸得僭上所为,……此法度不行也。游惰豪纵之徒,因输财得僭服以踰宪防,卒致浇漓之弊,此风俗不纯也。况卖官之令,已出权宜,……且先朝赐民爵不过公士,摄助教之名,非有阶品。若三等之上户,皆受爵号,即牙前、弓手、散从官、手力之类,悉出孤贫浮客。[3]3016-3017
简而言之,尹洙提案动机不纯(规货财),且会扰乱等级秩序和司法秩序。其实,鬻爵不可行最根本的原因是:当时已经存在“卖官之令”和假官市场,假官的功能与爵基本一样。时移势易,虚名化的爵制吸引力已经非常微弱,但宋朝却与秦汉有着相同的需求,如酬军功、劝入粟。在“重官”的时代,“假官”对于社会大众的吸引力远远超过原有的民爵,让假官与民爵合流,以假官行使民爵功能,远比直接销售民爵有效。引文所谓“卖官之令”,其实就是以“爵”的名义出台的。咸平六年(1003年),河北转运使刘综等建议效仿西汉,“使入粟以受爵(上造、五大夫、大庶长等),塞下之粟必多”。景德二年(1005年),权三司使刘师道等旧事重提,乞“依刘综等前议”施行,但却将“爵”置换成了“官”,共分十等,最便宜的是助教,须纳斛斗1000~1500石,最贵的是大理寺丞,须纳斛斗10 000~15 000石。刘师道等人的提议得到了真宗的批准,并很快付诸实施⑩。
爵制复古运动失败,仁宗以降,宋朝虽然仍在赐民爵,但很少再赐秦汉式的民爵,而是将假官视为民爵,予以颁赐。兹举例如下:
张政年,治平中,以百岁高年,得赐爵助教[39]。
陈宗礼,绍兴中,“以高年,赐爵迪功郎”[40]4990。
孙端仁,绍兴中,“以高年”,“赐爵迪功郎”[41]664。
方元恪,绍兴二十九年(1159年),“赐高年爵”,得授承务郎[42]103。
方思训,淳熙三年(1176年),以高宗七十大寿,赐爵保义郎”[41]662。
晁子与,绍熙五年(1194年),以高宗吴皇后八十大寿,“赐爵迪功郎”[8]786。
胡谘,绍熙五年(1194年),“高年者赐爵有差”,得封迪功郎[40]3102。
王永富,庆元中,“赐高年爵”,得授迪功郎[41]665。
牟格,嘉定二年(1209年),“赐高年爵”,得授承务郎[43]。
林珪,嘉定十四年(1221年),“赐高年爵”,得授迪功郎[44]。
王道昌,景定五年(1264年),“赐高年爵,蒙恩授承务郎”[45]。
赐民爵,名为“爵”,实为“假官”。同理,宋代的入粟拜爵、军功赏爵,逐渐地也以“假官”代替了“爵”,却常常以“爵”的名义行于世。戴埴曰:“今之鬻爵,泛滥极矣,多咎晁错之作俑。余谓今之弊,非鬻爵也,鬻官也。”[46]如绍兴末,“军兴,入赀佐县官者赐爵”,郭伯清因此得补迪功郎[42]115。再如隆兴元年(1163年),“朝廷募有能输财助经费者”,黄正衡因此“得以拜爵,补将仕郎”[47]。军功亦然,前述林大鼐所言“军中爵秩高而少族姓”,“爵”实当为官。刘克庄言:“军中以武功拜勇爵者,多不可算。”[28]2955“多不可算”的“爵”亦当为官。嘉定十四年,蕲州知州李诚之战死,朝廷“赐爵迪功郞者三”[14]13244,亦可算是军功的延伸。
爵与假官合流带有一定的历史必然性。假官“有名而无实,虽有官职称呼,而无位可居”[48],这与同样虚名化的爵,名异而实同。此点,唐代政治家陆贽(754~805年)已有清晰的认识,他说:“勋、散、爵号”,“假虚名佐实利者也”,“今员外、试官与勋、散、爵号同。”[49]虽然都是虚名,但在“重官”的时代,假官的市场行情还是远远高于民爵,民爵与假官合流显然是当政者的理性选择。
三、宋代社会之泛官化
所谓泛官化,指宋代社会强势力量全面向官品靠拢,努力使自己具有官僚阶层的某些特征,这些社会强势力量主要包括富人、胥吏和以医生为代表的技术人才等。
(一)富人泛官化
所谓富人泛官化,指“员外”官衔成为富人的代名词。员外之设始于唐,袁楚客规谏宰相魏元忠有云:“正员之官犹不欲其备,况正员之外更置员外乎?”[50]“正员之外,皆有版授官”[51]8247,意思是员外即假版官。富人泛官化在逻辑上经历了两个阶段:先是大多数富人通过各种手段拥有了假官(员外)头衔,然后是社会逐渐地将富人与员外划等号,“员外”逐渐成为富人的代名词,即使是没有假官头衔,亦习惯以员外称之。
宋代大多数富人拥有假官头衔肇始于宋徽宗时期,到南宋更加明显。如前所述,北宋中前期,富人求官尚有一定难度,但宋徽宗以降,富人求官逐渐变得非常容易。他们既可以向政府或大官僚买官,也可以窜名军中,向军队买官,而且,官价呈不断下降之势,买官人群逐渐从一、二等大户向“中产之家”延伸。如前所述,自宋徽宗始,假官已成泛滥之势,“比之往岁,不啻数十倍”“遍满天下,一州一县无处无之”“由是官户日繁”[17]1519,“比户称官”[14]4332。假官泛滥,一方面自然是朝廷卖官的结果,另一方面也表明富人皆有强烈的买官意愿。“至崇宁、大观间”“富室方且以希进鬻爵为荣,廉耻道丧”[52]。大概是因为首都开封假官太多且喜欢炫耀,宣和五年(1123年),朝廷不得不专门下令:“禁止市井营利之家,不得以官号揭榜门肆”[13]8330。“以官号揭榜门肆”,此前应该比较普遍,《清明上河图》有一旅店,店名即为“久住王员外家”。南宋假官泛滥更加严重,所谓“今日官户,不可胜计”[13]6087。当假官漫向“中产之家“时,高于中产的一、二等大户自然绝大多数都会拥有假官头衔。吴潜(1195~1262年)曰:“今江、浙、福建之民,盖校尉连车,而迪功平斗矣。”[53]意思是拥有假官头衔的“民”数不胜数。大致到了宋徽宗晚期,在官僚最为集中的开封地区,“员外”开始成为富人代名词,即“南渡前,开封富人皆称员外”[2]259。如宋高宗岳父吴近,“以蠙珠为业,累赀数百万”,号称“京师珠子吴员外”[54]。再如,宗室赵应之、赵茂之兄弟在京师,“与富人吴家小员外日日纵游”[55]29。南渡以后,员外泛指富人逐渐蔓延至全国。周寿昌曰:“小说凡称富翁曰员外,见洪文敏《夷坚志》,盖始自宋时”[56]。《夷坚志》的确有不少富人称员外的记载,如,“魏人王员外,以纳粟得州助教”[55]718,再如,“明州定海县人大蒋员外者,轻财重义”[55]54。明代戏曲家徐渭注释“员外”,曰:“宋富翁皆买郎外散官,如朝散、朝议、将仕之类。”[57]宋代新兴的假官群体以财富为主要特征,其假官亦多以财富直接或间接交易所得,“有财势之徒皆得假借其称”[58]61。
“富人皆称员外”,意思是富人即使没有员外官衔,社会亦以“员外”称之。当多数富人都有员外官衔时,在人们的观念中,员外与富人之间就会逐渐地划上等号。一旦人们的观念将员外与富人划上等号,即使是没有员外官衔的富人,人们也会不自觉地“顺口以员外呼之”[59],这就是富人的泛官化。
富人一般称为员外,但徽州多称为“朝奉”。对于徽州富人称“朝奉”的习俗,明清人认为始于宋代。凌濛初(1580~1644年)《二刻拍案惊奇》记载:“直隶徽州府有一个富人,姓程,他那边土俗,但是有资财的,就呼为朝奉,盖宋时有朝奉大夫,就象称呼富人为员外一般,总是尊他这个。”[60]《通俗编》记载:“徽俗称富翁为朝奉。”[58]247《癸巳存稿》亦记载:徽州人称朝奉,方回《桐江集》有《村路有呼予老朝奉者》诗,是宋时语证[61-62]。“富人”与“朝奉”的关联应与宋代的进纳法有关。如前所述,按照“正法”,进纳(非军功)出身需要转至从六品朝奉大夫“方许作官户”,因此,朝奉大夫是进纳官从假转真的关节点,必然在富人们心中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富人称“朝奉”或许缘于此。
(二)郎中/大夫成为医生的代称
宋代存在一个技术官群体,包括天文、书艺、图画、医官等“执伎以事上者”[14]3941。四类人才中,天文、书艺、图画主要在“事上”,与社会大众关联有限,独有医生在“事上”之外,与社会大众的命运亦息息相关,因此,兹主要以医生为代表来看宋代技术人才的泛官化。
郎中/大夫何时成为医生的代称,明人已有所猜测。陆容(1436~1497年)曰“医人称郎中”“此元时旧习也”[63]22。查继佐(1601~1676年)曰“元俗贱宋官”“医称郎中”[64]。陆容、查继佐皆认为“医人称郎中”是元代的习俗,但没有提供任何的佐证,完全是一种猜测,而且是错误的猜测。
清代考据学家在考证的基础上纠正了明人的错误认识,转而认为医生称郎中/大夫始于宋代。顾炎武(1613~1682年)曰“北人谓医为大夫,南人谓之郎中”“其名盖起于宋时”[65]。不过,顾炎武依据的是《老学庵笔记》“北人谓医为衙推”,证据非常苍白[66]。翟灏(?~1788年)在顾炎武的基础上增加了关键的证据,即《武林旧事》“说药”条所记“杨郎中”“徐郎中”,表明“当时即以医为郎中矣”[58,61,67]。赵翼(1727~1814年)在前人的基础上作了更加详实的考证,他说:
若医生之称郎中、大夫,顾宁人(炎武)以为起于宋时,而引《老学庵笔记》……以证之。然亦第意拟之词,而未见郎中、大夫的据。按《夷坚志》:“鄱医赵珪,……人称为赵三郞中”;又:“刘师道业医,有妇人托为魏师成之妻,求其疗夫疾。……妇忽笑曰:‘刘郞中细审此病不可医也。’……。”又:“信州吏毛遂病,为刘医误用药致死,忽复活,曰:‘是那个郞中主张?’……。”此医生称“郞中”之明证也。《夷坚志》又云:“张二大夫者,京师医家,后徙临安,官至翰林医官,人仍称为张二大夫。”则北方医生之称大夫,亦起于宋矣。
赵翼不仅补充了更多的宋代医生称郎中的材料,还新增了宋代医生称大夫的证据。晚于赵翼的梁章钜(1775~1849年),大概是没有看到赵翼的著作,也对顾炎武的假说作了补正工作,依据的材料也是《夷坚志》,结论同样是“医称大夫”“医称郞中”“自宋已然”。医生称郎中/大夫始于宋,清代考据学家的证据和结论都是可信的,兹主要补充郎中/大夫在宋代成为医生代称的时代背景。
宋代医生称郎中、大夫,首先是因为医官称郎中、大夫。政和二年(1112年)改制,医官首次具有了专属官阶。当时医官定为十四阶:和安大夫、成和大夫、成安大夫、成全大夫、保和大夫、翰林良医、和安郎、成和郎、成安郎、成全郎、保和郎、保安郎、翰林医正。绍兴改制,又增翰林医官、翰林医效、翰林医痊、翰林医愈、翰林医证、翰林医诊、翰林医候、翰林医学等八阶[14]4070-4071。大夫和郎是当时官衔的主流称呼,翰林良医等称呼明显别扭,金朝医官沿袭宋朝,即将所有下层非“郎”官称改成了“郎”官称,如医正郎、医效郎、医候郎、医痊郎、医愈郎等[68]。宋代的郎中指中央各司的正长官,如吏部郎中、户部郎中等,与医生没有任何的关联,医生称郎中很可能是“转名”的结果。和安大夫、成和大夫、成安大夫为从六品[14]4015,从六品传统上“系正郎”[14]4065,而郎中“唐以来号正郎”[69]。大夫=正郎=郎中,此种转换机制,当时称为“转名器”[70]。医生称郎中,可能还与古人的喜好有关。隋末河内有人嗜酒,“常自号郎中”[71],后唐李鏻善饮茶,尝呼“吃茶郎中”[51]10756。不过,无论是称大夫,还是称郎中,皆是当时“过称官品”风气的结果。
不管是“事上”的医官,还是“事下”的平民医生,他们的职业内涵是完全一样的。居于上层的医官会起到巨大的示范效应,居于下层的平民医生则会竞相模仿上层医官,郎中/大夫的称呼自然会慢慢地蔓延向全体医生。这种蔓延必然需要一个较长的过程,北宋后期尚不见有郎中/大夫指称医生的记载,但到南宋,郎中/大夫指称医生逐渐普遍起来,这从《夷坚志》的大量记载可见一斑。在“郎中”与“大夫”之间,宋代称“郎中”者居多,《夷坚志》即主要称“郎中”。郎中/大夫指称医生是宋室南渡后才逐渐形成的,所谓“北人谓医为大夫,南人谓之郎中”或许是金国与南宋分野的结果。
宋代技术人才泛官化,医生只是最为典型而已。事实上,其他技术人才亦存在泛官化趋向,如“镊工称待诏,磨工称博士,师巫称太保,茶酒称院使”“木工、金工、石工之属皆为司务”“盖起于宋”。
(三)胥吏泛官化
与富人、医生泛官化不同,胥吏在唐代原本属于官,只不过是流外官。唐代的胥吏,广义上包括流外官和杂任、杂职,狭义上仅指流外官[72]。到唐后期,胥吏的官衔更加地高大,“唐室衰弱”,“笞挞之吏,舆皂之役,阶叙银青,衔称检校”[73],“有积阶至司徒、司空、仆射、太保者”。这种局面一直延续到宋初,如乾德四年(966年)衡州押衙胡某的官衔即为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太子宾客。“衙校各带宪衔”,虽然看起来很高大,但只是“吏职”而已[6]38-39。
宋朝“贵官贱吏”,“胥史牙校皆奴仆庸人者”[74],虽然仍有出职为官的机会,但道路已经非常狭窄,“号为出职,未有得为品官者”[13]4376。不过,虽然国家歧视胥吏,但胥吏群体仍然自视为官,并坚守唐末五代以来的官称。政和三年,中书省言:“契勘今天下诸州军因仍五代藩镇之弊,胥徒府史有子城使、教练使、都教练使、左右押衙、左右都押衙、中军使、兵马使、都知兵马使,名称鄙俗,今董正治官,革去因袭,拟厘改作都史、副史、介史、公皂、衙皂、散皂、上隶、中隶、下隶。”[13]4375但是,到南宋初期,胥吏的官称又得以还原。绍兴元年,户部言:“吉州申,昨来衙前旧法系称都知兵马使等名目,及本州人吏系称都孔目官等名目,后准指挥,衙职改都吏,人吏改典史等,……窃恐都孔目官等并衙职等名称亦合依旧。”朝廷遂“诏诸路监司州县衙职、人吏并依旧制称呼”[13]4376。除了北宋后期一段时间外,宋代的胥吏基本上维持住了唐末五代的官称,尽管这些官称不为国家认可。
除了维持唐末五代的官称外,胥吏群体在宋代还自称为“外郎”。方回《续古今考》在谈及宋朝官制时就说:“又有小吏而妄呼为外郎者。”[2]259胥吏称外郎一直延续到明清,但明清学者却没有人知道外郎的起始时间,陆容、查继佐即认为“吏人称外郎”是“元时旧习”[63]22,[64]692,顾炎武、吴暻则说“今人以吏员为外郎”[65]542,[75]。
(四) “官人”成为强势者的泛称
古代“官人”内涵之演变,清代考据学家已经有所考证。在多数学者心中,首先着手考证的是顾炎武,他指出了“唐时有官者方得称官人”[65]546。证据有:韩愈“一女怜之,必嫁官人,不以与凡子”[76];杜甫“剑外官人冷”[77]。翟灏在顾炎武的基础上增补了宋代官人内涵,他说:“宋乃不然。若周密《武林旧事》所载金四官人以棋著,李大官人以书会著,陈三官人以演史著,乔七官人以说乐著,邓四官人以唱赚著,戴官人以捕蛇著;吴自牧《梦粱录》又有徐官人幞头铺,崔官人扇而铺,张官人文籍铺,傅官人刷牙铺。当时殆无不官人者矣。”[58]252,[67]105-114,[78]赵翼在前人的基础上亦增补了宋代官人内涵,但他没有注意到翟灏的论述。他说:
奴仆称主,及尊长呼卑幼,皆曰“某官人”,亦有所本。杜田《杜诗博议》:“官人乃隋、唐间语。”……唐以前必有官者方称官人。《昌黎集·王适墓志铭》云“一女怜之,必嫁官人,不以与凡子”是也。”
至宋则已为时俗通称。《宋史·岳云传》:“云年十二,即从张宪战,多得其力,军中呼为‘赢官人’。”《夷坚志》“易官人及第”条:有报榜者至逆旅,曰:“此店有易官人及第。”又“陆氏负约”一条:陆氏再醮后,独步厅事,有急足来称:“郑官人有书。”郑乃其前夫也。“张次山妻”一条:次山丧妻后,入京参选,偶游相国寺,与亡妾遇,惊问之。妾曰:“现服事妈妈在城西一空宅,官人可以明日饭后来相会。”此又可见官人之称在宋时已为常谈也。
《杜诗博议》已经失传,其真正的作者是潘柽章(1626~1663年),字圣木,号力田,苏州人,与顾炎武是同乡,因死于文字狱,其书在流传过程中多讳言真名[79]。赵翼家乡常州,与苏州毗邻,他对潘、顾二人应该都非常熟悉,其《陔余丛考》即“尽力模仿《日知录》”[80]。赵翼完全没有提及顾炎武,其所引杜田《杜诗博议》却与《日知录》颇有重合之处,这表明:《日知录》“官人”条很可能是沿自《杜诗博议》。赵翼的贡献在于:明确指出了“官人”到宋代已转成“时俗通称”、时代“常谈”,即强势者的泛称,并增补了《夷坚志》的证据。强势是一种相对关系,如主人之于奴仆、尊长之于卑幼、丈夫之于妻子、富人之于穷人、知识人之于文盲、官员之于胥吏、官僚子弟之于平民,强势一方皆可称为“官人”。
客观地说,潘柽章、翟灏、赵翼的证据和结论皆是可信的,本文需要补充说明的是:官人成为“时俗通称”应该是南宋的事。如果说官人在唐以前仅指“有官者”,那么,北宋时期,官人所指仅仅从“有官者”扩大到了“有官者”子弟。名士孙复居泰山,故相李迪欲以侄女妻之,孙复固辞,李迪曰:“吾女不妻先生,不过为一小官人妻。”[81]“小官人”即指官员子弟。从现有史料来看,北宋时期尚未见有官人指称官员及其子弟以外人群的例子。前述员外成为富人代称、郎中/大夫成为医生代称皆主要是在南宋时期,与此时代大趋势一致,官人成为强势者泛称亦是到南宋以后。无论是翟灏提供的《武林旧事》《梦梁录》例证,还是赵翼提供的《夷坚志》史料,都是南宋以后的事。当然,从零星的、局部的称呼到全国性的泛称,必然需要一个较长的过程,就像员外一样,不排除“官人”在北宋后期就已经开始零星地指代官员及其子弟以外的强势者,但成为“时俗通称”定是在南宋以后。反过来,因为“官人”在南宋尤其是南宋后期已成“时俗通称”,我们不能轻易地将官人等同于在官之人。咸淳七年(1271年)黄震《劝乐安县税户发粜榜》提到了很多有头衔的人,计有:詹良卿登仕、曾料院、许道州、詹季宏官人、曾正则官人、曾季同官人、詹明伯官人、康元甫官人、周叔可官人、罗袁教、罗运幹、黄景武官人暨景文、景宪、景云等官人四兄弟、黄汉举官人、陈季升官人、陈子清官人、黄晋甫官人、黄信甫官人、丘子忠官人、邓子清官人、张彝仲官人、张晋卿官人、曾季遂官人、曾季常官人、郑荣甫官人、郑宪甫官人与鄢甲头[82]。梁庚尧据此说明“官户不仅在政治上是掌握实权的分子,在经济上也自成一个阶层,是拥有多量田产的大地主,高踞农村社会的最上层”[83]。榜文共提到二十九人,除鄢甲头外,有具体官名者五人,笼统称为“官人”者二十三人,完全看不到富人。很显然,此二十三“官人”不能看成是真正的官户,他们最多是拥有假官头衔的富人。
四、余论:宋代社会泛官化的动力
宋代社会泛官化的内在动力在于垂直社会流动加速,包括官与民之间的流动、富与贫之间的流动两个层面。“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84],精致化的科举制度让官与民之间的升降通道宽广而通畅。科举制度创立于隋朝,但在隋唐时期取士规模太小,且无公平保障机制,不足以成为官与民升降的枢纽。宋朝科举取士数十倍于唐朝,且创立了“糊名誊录”制,取士“一切以程文为去留”[66]69,“最号至公”[85],科举制度遂成为官与民升降的枢纽,“惟有糊名公道在,孤寒宜向此中求”[86]。当然,科举制度加速上行流动的同时,也会加速下行流动,“盛衰之变,何其速也”[87]“生为官户,没为齐民”[13]6183。官民之间流动速度越快,卷入官僚化的人群就会越庞大,最终几乎将所有的富民卷入进了官僚化运动中,即“中上之户,稍有衣食,即读书应举,或入学校”[88],“凡今农工商贾之家,未有不舍其旧而为士者”[89]。“富儿因求宦倾赀”[90],北宋后期以降假官的泛滥,让几乎所有的富民都拥有了假官头衔,以致于黄震劝民榜中都看不到富民的存在。“贫富无定势”“富儿更替做”[91],穷人与富人更替的速度越快,卷入求官者的群体就会越庞大。当科举求仕、倾赀求宦者的人群足够庞大,“官人”成为强势者的泛称就水到渠成了。
宋代社会泛官化的外在动力在于当时官场“过呼”风气的诱导、蔓延。“过呼”又叫“过称”,指用高于某人实际官职或爵位官名称呼其人[92]。关于宋代官场的“过呼”问题,鉴于杨倩描已经作了深入研究,本文在此只强调三点:一是“过呼”现象非常普遍和严重,“妄冒称呼,不可概举”[13]8324,“中外文武官称呼之间,多或假借”,而且“称呼太过”,如殿直、承旨差出者“须邀司徒之称”[13]2382;二是“过呼”风气非常持久,虽“重行条禁”[13]2382,却屡禁不止,“其风愈炽,不容整革”[93],徽宗以后,禁令更是完全失效,虽有明文,“但未举而行之”[13]8324;三是上行下效,官场“过呼”风气会产生社会传导效应,即“世俗效之”[6]63。宋代“过呼”风气在徽宗以后更趋严重,而社会泛官化也是在徽宗以后渐趋明朗,很显然,社会泛官化一定程度上是官场“过呼”之风向社会蔓延,即官名(朝奉、郎中、员外等)“俗称”[58]247化的结果。
注释:
①参见内藤湖南:《概括的唐宋时代观》(载刘俊文:《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1卷),中华书局,1992年);高德步:《唐宋变革:齐民地主经济与齐民社会的兴起》(《学术研究》,2015年第7期);张邦炜:《宋代“平民社会”论刍议——研习钱穆论著的一个读书报告》(《历史教学》(下半月刊),2017年第8期)。
②参见方以智:《通雅》卷22《官制·仕进》(中国书店,1990年,第281页)。“假官”之“假”,既有“假借”之意,也有“非真”之意。
③关于宋代的进纳授官,王曾瑜已有详细论述,本文主要侧重于讨论进纳授官与宋代社会泛官化之间的关联,参见王曾瑜:《宋朝卖官述略》(《史学集刊》,2006年第4期)。
④彭汝砺:《(上哲宗乞详定袒免亲婚姻(条贯)》(载赵汝愚:《宋朝诸臣奏议》卷33,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327页)。原“仁宗”当为“哲宗”,据文意改。
⑤此倍数以粮价为基准,参见程民生:《宋代物价研究》(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22-124页)。
⑥南宋初期适逢战乱,“中产”的标准明显偏低,到南宋中期,“中人之家,钱以五万缗计之者多甚”(吴箕:《常谈》,中华书局,1985年),“中产”标准明显大幅提高。
⑦佚名:《国朝二百家名贤文粹》卷76《应诏上皇帝陈利害书》(载《续修四库全书》第1653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143页)。熊彦诗的建言是为了堵住富人“窜名军中”的道路。
⑧关于宋代爵位制度的研究,参见郭桂坤:《〈宋史·职官志〉“爵一十二”试解——兼析宋代〈官品令〉中的爵位序列》(《中国史研究》,2016年第3期);陈希丰:《再谈宋代爵的等级》(《文史》,2016年第3辑);龚延明:《宋代爵制的名与实——与李昌宪、郭桂坤等学者商榷宋代十二等爵制》(《中国史研究》,2019年第2期)。
⑨参见王应麟:《玉海》卷134《端拱赐爵》(载《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946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546页);程大昌、许逸民:《演繁露校证》(中华书局,2018年,第871页)。吕继美等赐爵时间,诸书皆记载为太祖开宝五年(972年),疑为“淳化五年”之误。《玉海》先记载了端拱元年赐爵,并且明言端拱元年赐爵是“秦汉以后”“始复赐焉”,但紧接着又记载开宝吕继美等人赐爵,矛盾太过明显。
⑩参见徐松辑:《宋会要辑稿》(第8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4513-4514页)。同样的官,入粟边州,区位不同,价格会有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