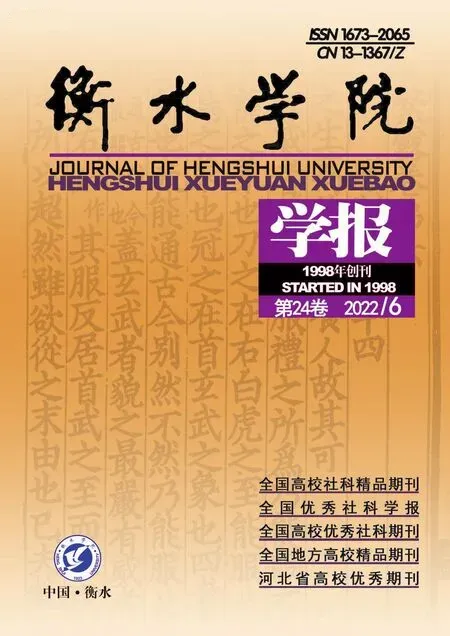人工智能生成作品的权利归属研究
2022-03-02李月
李 月
(澳门科技大学 法学院,澳门 999078)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进步,其生成内容的事例逐渐增多,内容类型涉及诗歌、新闻报道、绘画等文化艺术的各个方面。人工智能生成物对现有法律制度产生的冲击中,最基础的问题是其是否具有可版权性。在明确了生成物的可版权性后,就面临其权利应当归属于谁的问题。实践中,法院在 2018年“百家号”与菲林律所的案件里认为,应当保护生成报告的机器的研发者和投资者的权益。即肯定了对人工智能生成物保护的必要性和正当性。除此之外,也有学者基于“激励目的”或“与人类无差别的劳动成果”的出发点将人工智能生成物纳入法律保护的范围[1]。对于生成作品应当归属于谁的问题,学界观点并不统一。可以根据是否支持将生成物认定为作品的观点分为两大类:1)否定者认为人工智能生成内容不属于作品范畴,不应适用作品保护,在此项下又可以细分为两个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人工智能本质上属于一种计算机程序,故人工智能生成作品应当适用计算机衍生品的规定;第二种观点认为人工智能生成物直接进入公有领域便不需要再考虑权利归属问题。2)支持者认为人工智能生成内容属于作品范畴,在此项下又可以细分为两个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应当给人工智能以法律上的主体地位,这样便可将生成作品权利直接归属于人工智能所有;第二种观点认为人工智能不能获得法律上的主体地位,所以生成物权利应当归属于与机器或作品产生相关的自然人、法人或非法人组织①孙新强的《论作者权体系的崩溃与重建》(《清华法学》2014第 2期),陈凡、程海东的《人工智能的马克思主义审视》(《思想理论教育》2017年第11期),两篇文章均持此观点。[2-3]。
一、人工智能生成物不适用计算机衍生品的规定
人工智能是一种计算机程序,但与以往的计算机程序相比有其明显的不同点。以往的计算机程序主要有以使用者为主决定生成内容的程序和以编程者为主决定生成内容的程序两种。以使用者为主决定生成内容的程序起到工具功能,帮助使用者将创作内容具象化。以研发者设计的编码决定生成内容的程序,使用者输入的数据只是经过固定的流水线式处理,经过确定的步骤将输入的数据转化输出确定的内容。但人工智能并不是简单的工具,人工智能生成物可以看作是人机协作的产物。使用者向人工智能输入机器需要的学习数据后,人工智能抓取它所需要的数据,进行不受编程者和使用者控制的“学习”,后输出不确定的内容,即使是输入相同的数据,最终输出的内容也是不同的。
除此之外,人工智能相比较之前的计算机程序多是由自然人使用和所有,因为人工智能的研发和使用需要大量的资金和专业团队的支持,所以人工智能的使用者及所有者是法人或者组织。
二、人工智能生成物不应直接进入公有领域
认为人工智能不属于作品的学者认为,依据著作权最终是为了保障社会公众获得繁荣文化传播的目的主张将生成物直接进入公有领域。生成物直接进入公有领域表示生成物成为公共文化财产的一部分,社会成员在使用生成物时可直接使用,不需要向谁申请,不需要获得其他人的同意或向其他人支付费用。这也就没有了生成物权利归属于谁的问题。社会成员和生成物之间的接触变得容易,同时使得社会成员的创作变得容易。上述主张虽有一定的益处,但笔者认为,人工智能生成物不应进入公有领域,原因有二:一是因为人工智能生成物进入公有领域,会给人类创作带来更大的压力,进而不利于社会文化创作的良性循环。如果人工智能生成物进入公有领域,因其创作效率远高于人类的创作效率,这会给人类原创带来更大的压力。同时,机器的高效输出,使得进入共有领域的生成物太多而没有有效的办法进行标注以用于后续的区分,社会成员可能滥用生成物或将其视为自己的创作。这也给真正的人类创作者带来压力。且机器处理数据的效率是人类不能及的,大量不受控制的生成物进入公有领域致使人类创作成本更高,不利于鼓励人类智力活动的进行。这样的情势发展下去,人类创作出的新的表达方式越少,能够提供给机器作为学习的数据其新颖性表达越少,而人工智能不能自己创造出新的表达,就会使得社会文化的新颖性降低,不利于社会文化的繁荣。二是生成物的使用是免费的,这意味着人工智能相关的研发者、使用者、投资者等相关权利人员均不能从中获得收益,使得人们对于推动人工智能的兴趣大减,不利于人工智能的发展。在菲林诉百度案中,百度方正是持有人工智能生成物是由机器产生,不属于作品,直接进入公有领域,故百度可直接使用,不需经过菲林律所的同意和支付费用的观点,使用了涉案文章。如果按照这样的观点,不仅使得菲林律所在发布文章前的审核校对等各项付出得不到回报,不利于保护发布方的权利,更进一步也使得发布方不享有权利也不承担义务,造成生成内容侵权无人负责的局面。
三、暂不宜赋予人工智能法律主体地位
首先,人工智能本质上是计算机编码,是程序,是物,如果取得法律上的主体地位,则与科技、文化等相关的众多法律条文均应调整[4]。且不说社会发展总是先于法律,在面对社会发展时不能一味地变革法律而不考虑法律的稳定性,即使人工智能取得了我国法律的主体地位,在之后如果与后续的国际标准不统一,又会面对一系列的新问题。
其次,想要确定法律上的主体资格需要满足两个要求:一方面,是其能够通过自身的行为向外传达它本身的意思,称为意思条件;另一方面,是拥有从事社会活动或承担责任的财产,称为财产条件。例如,法人之所以能够拥有法律主体地位,成为法律上拟制的人,从意思条件来说,法人是由其成员组成的一个整体,其成员就是自然人,可以形成统一的意思,并对外表达。这就形成了法人的意志。从财产条件来说,法人有自己的独立财产,可以为自己的社会活动提供物质基础,也可为自己的行为承担相应的责任[5]。
但人工智能并不具备意思条件和财产条件。意思条件方面,人工智能并不会自己去解决问题,需要人类提供一个待解决问题,即人工智能生成物并不是其自身内在要解决问题的外现。如果人类没有加给人工智能一个待解决问题和学习数据,人工智能就不会开始工作并生成内容,可见人工智能生成物的开端是人类加给机器的待解决问题,并不是机器自己的内在意志的外现表达。且在生成物输出后还需经过人类的语病纠错和表达修改。生成物也是人工智能数据处理后的完整表达。从财产条件看,人工智能没有自己所有的财产,没办法独自参加社会活动或为自己可能的侵权行为承担责任等。因为人工智能仍是工具,没有权利义务观念,故无法通过著作权法保护的激励来进行更多的创作,且如果明确了人工智能的主体地位,对人工智能的意思表示、后续可能产生的侵权行为的主观过错等都不易考量[3]21。
可见,将著作权属赋予人工智能本身既不能对机器起到激励作用,即不能将获得的财产收益归于机器名下,又不能在侵权出现的时候要求机器对此负责。
并且,即使明确了人工智能的权利主体地位,机器并不能自己行使权利,需要其他主体例如设计者、使用者、投资者等来行使权利。这样直接将权利归属于设计者、使用者或投资者可以达到一样的效果,且避免了将权利归属于人工智能所带来的对法律理论的修改[6]。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赋予人工智能以法律上的主体地位进而将生成物权利直接归属于人工智能并不是适宜的选择。
四、人工智能生成物权利宜归属于其投资者
由上可知,人工智能生成物的保护路径应以作品保护为宜,并选择与人工智能相关的或与生成物有联系的自然人、法人或非法人组织。学界将此观点细分为支持权利归属于研发者、权利归属于使用者或权利归属于投资者三种[7]。笔者认为,为适应我国现阶段社会发展的保护路径宜选择将生成作品的权利归属于投资者。
支持权利归属于研发者的学者指出,人工智能的程序是由研发者设计并经研发者输入学习内容后经过调试构建的类人脑的多重神经网络。可以说机器的产生和思维取向受研发者影响最大。故人工智能编程者基于上述贡献及与作品的联系应当将生成物权利归属于研发者。
但 2016年的《关于机器人伦理的初步草案报告》中,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为现阶段的智能机器仍然是普通意义上的科技产品。那么,人工智能的流转也会像其他科技产品一样,程序在研发完成后会通过许可转让给使用者或其他所有权人[8]。之后由使用者加给人工智能一个待解决问题及相关学习资料,最终生成物的输出从这一步开始与研发者的联系被断开。所以人工智能开始的程序由研发者提供,且研发者也获得了相应的计算机程序的著作权,但后续具体生成内容与研发者之间的关系并不紧密,生成物解决问题的起点和后续的审核与修改都是由使用者完成的。
且生成物也不是研发者设计的程序的演绎结果。人工智能并不是简单的对输入数据进行流水线处理后的重复输出,是一种寻找问题最优解的算法处理。其在深度学习和信息抓取的过程中已然脱离了原有程序的预设,输出结果具有不可预见性。
故基于编程者对生成作品的贡献和联系程度不足以将生成物的权利直接归属于研发者。
那基于前文所述,使用者是否可以基于其使用行为和数据选择与生成物形成的联系而获得相关权利呢?笔者认为,虽然目前的人工智能想要生成内容,无论是在问题的提出还是学习数据的输入,抑或是对输出结果的审核修改等方面都离不开使用者的参与。且使用者选择的数据会影响到后续输出的内容质量。但笔者认为,仅凭这些辅助性的行为,就将生成物的权利归属于使用者是不恰当的。因为基于人工智能的工作原理,机器的创作过程是相对独立的,虽然输入的学习数据是由使用者筛选后提供,但是在“深度学习”的过程中,机器会有选择的抓取相关的数据,且在创作内容和生成内容的过程中,使用者并不能将自己的想法加给人工智能。对于生成物来说,其本质的创造点在于对数据处理的过程和生成物的表现上,而这些均是使用者不能参与和控制的,所以人工智能的创作有其相对独立性,在生成内容的过程中并不只是一个辅助工具,仅凭一些不与生成内容直接产生联系的行为直接随意将权利归属于使用者并不恰当。
由前文可知,因人工智能的创作过程具有相对独立性,无论是研发者还是使用者均不能在创作过程中加入自己的思想,所以凭借与生成作品的联系角度,二者不可直接取得相关的权利归属。且由研发者或使用者取得生成作品的权利归属,会对投入巨大人力、资金支持的投资者的积极性产生较大的打击,不利于人工智能的发展。并且,在明确生成物构成作品后,适宜我国人工智能生成物的保护路径应当满足既要符合著作权法的宗旨又要能够平衡各方利益。故笔者认为应由投资者取得生成物的相关权利归属。具体原因有二:
一方面,生成物权利归于投资者符合社会发展的需要。从人工智能的工作原理出发可以知道,一份生成作品的输出到具备相应的商业价值的过程中,离不开众多不同领域专业团队的合作。例如程序设计的研发团队、学习数据筛选的编辑团队、输出内容修改的审核团队、发布报道的宣传团队等,这样大规模的人力物力支持需求使得现阶段人工智能生成物多为例如腾讯等企业提供的团队完成的。由此可见,企业提供的人力支持即各专业团队及资金支持,保障和促进了人工智能的发展,也可以说,投资者与人工智能机器生成物之间关系密切,将生成作品权利归属于投资者具有正当性和必要性。
另一方面,著作权法对作品进行保护本质上是希望通过保护作品所有者的权利,保障他们获得应得的利益,进而提高他们的创作热情,最终使得社会文化繁荣发展。而将生成物的权利归属于投资者就可以达到这一目的。投资者从自己的投资中获得部分的商业利益,获得的利益作为一种激励,使得投资者愿意投入更多的人力物力在其中,从而达到人工智能投资—获利的良性循环,也进一步提高生成内容质量。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人工智能生成物不宜直接适用计算机衍生品的保护规定或直接进入公有领域,应当将其作为作品保护起来。没必要为将作品权利归属于人工智能而变革法律体系,即没必要将人工智能添加进法律主体中。可将生成作品相关权利根据与机器和作品之间的联系及对社会文化创作的激励目的归于投资者。
故笔者认为,我国现阶段保护人工智能生成作品的应然路径是构建以投资者为权利所属和为核心的基础上平衡设计者、使用者的利益。此选择避免了将权利归属于人工智能本身后无法起到激励作用和承担侵权责任的无助境地而更具有可行性[2]145。设计者、使用者和投资者之间通过合同约定的方式来保障各自的利益,做到尊重意思自治,激励各方主体,促进科技文化繁荣发展。设计者通过与投资者之间的劳动合同的方式来明确自己对生成作品享有的权利;使用者通过与投资者之间买卖或者租赁合同的方式明确自己对生成作品的权利。在三方没有约定的情况下,将权属归于人工智能的投资者。这样既能起到激励作用,保障文化的繁荣和科技的发展,又能根据权利-责任相对原则,在侵权发生时锁定承当责任的主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