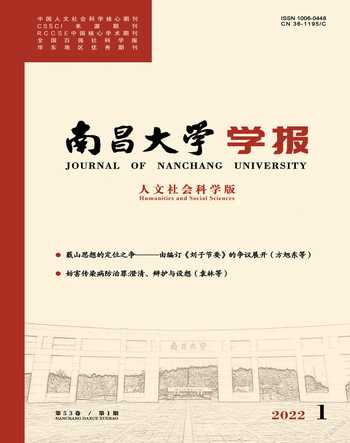妨害传染病防治罪:澄清、辩护与设想
2022-03-02袁林白星星
袁林 白星星
摘 要:基于刑法教义学和事实发生学,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罪过形式应包括故意和过失。该罪行为对象“甲类传染病”的内涵、外延应紧密观照前置法予以把握。由此作出的“甲类传染病”即“甲类以及按照甲类管理的传染病”解释为“平义解释”,非扩张甚至类推解释,并未违背罪刑法定;紧密观照前置法所作司法解释与刑法修改,体现了将“罪刑法定性”与“现实回应性”、“原则性”与“张力性”、“形式正当性”与“实质正当性”结合的刑事法治观。现行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立法还应在罪刑阶梯设置和罚金刑增设等方面予以完善。但完善前,出于贯彻罪责刑相适应和满足预防需要,特定情形的妨害传染病防治行为可论以“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而妨害传染病防治行为罪名认定所涉的“行为场所”等问题也需在转变观念中解答。
关键词: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甲类传染病;危害公共安全罪
中图分类号:D91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448(2022)01-0047-11
虽然在充分吸收司法实践经验基础上,《刑法修正案(十一)》对现行《刑法》第330条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立法予以修改,即弥补立法漏洞且完善了本罪行为方式[1](P81-83),但该罪依然存在罪过形式、行为对象理解认识和进一步的立法完善问题。既然病毒越发显示出与人类“长期共存”,则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的研究便一直在“抗疫之路”上。
一、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罪过形式问题的必要澄清
对于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罪过形式问题,理论界至今存在分歧。由于罪过性是刑事可罚性不可或缺的最后要件[2](P60),故仍有对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罪过形式予以深入讨论的必要。
(一)妨害传染病防治罪过失罪过的首先肯定
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立法颁行之初,对于该罪主观要件有如下观点:其一,该罪在主观方面是故意,即行为人明知自身行为会引起甲类传染病传播或有传播的严重危险而故意为之[3](P242);其二,该罪罪过形式可以是故意,也可以是过失[4](P448);其三,该罪主观方面是间接故意或过失[5](P419);其四,该罪主观方面是过失[6](P226)。其中,该罪罪过形式只能是过失的观点得到了学者特别强调与论证。第一,根据《刑法》第14条、15条规定,我国刑法以行为人主观上对危害结果而非行为本身的认识和态度作为区分故意和过失的标准。具体到妨害传染病防治罪,应以行为人对引起甲类传染病传播或有传播严重危险而非违法行为的认识和态度区分故意和过失。第二,虽然行为人实施违法行为可以是故意或过失,但对引起甲类传染病传播或有传播严重危险的结果只能出于过失,而如果出于故意,则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另从法定刑上来看,本罪的法定刑只重至7年有期徒刑,这反证本罪只能由过失构成,而若出于故意,则显然罪刑不相适应。第三,不排除行为人对行为本身出于故意,但只有“行为人对其行为所造成的引起甲类传染病传播或有传播严重危险的危害结果”,才是判断行为人主观态度的依据[7](P59-60)。之后,该罪罪过形式只能是过失的观点一直得到支持,如刑法理论一般认为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的罪过形式是过失[8](P1343),或如妨害传染病防治罪与“过失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均属于过失犯罪,行为发生场合的不同是區分两罪的关键[9](P3)。然而,有学者指出,将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确定为过失犯罪缺乏“法律规定”前提,故该罪属于故意犯罪[10](P1120)。
首先,排斥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的过失罪过有失偏颇,因为虽然一般人都有“传染病能够传染”常识,但行为人在“当地当时”可能会对传染病危险程度和传播危险程度难以或暂时未形成“严重认识”,从而其不利于传染病防治的行为或是疏忽大意过失,或是过于自信过失。不过,行为人应该预见自己的行为可能招致传染病传播的严重危险,但因疏忽大意而未预见,此种情形能否存在,就要看我们是否承认过失危险犯理论。这里,首先基于刑法谦抑性,以不承认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的过失危险犯为宜。其次,从刑法立法体系性来看,也不宜承认该罪的过失危险犯,正如在危害公共安全罪中过失必须造成实害后果才可构成过失犯罪。此种“造成实害后果才可构成过失犯罪”,是指危害公共安全罪的过失犯都是结果犯而非危险犯。由此,出于危害公共安全罪与危害公共卫生罪的危害性、违法性、有责性平衡,刑法立法体系性协调,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的过失危险犯不应得到承认。
另外,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罪过形式可以是过失,还可从该罪法定刑配制上论证。根据现行《刑法》第330条,妨害传染病防治罪有两个刑档,即“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和“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虽然妨害传染病防治罪属于“危害公共卫生罪”,但“危害公共卫生罪”却具有“危害公共安全”罪质[11](P142),甚至可将“危害公共卫生罪”视为“卫生类危害公共安全罪”[11](P146),从而使得妨害传染病防治罪也具有“危害公共安全”罪质,即其本应被视为具有“危害公共卫生安全”罪质。而在危害公共安全类犯罪中,情节较轻过失犯的法定刑正是“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于是,由具有“危害公共安全”罪质的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的法定刑将“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作为第一刑档,可推知该罪存在现行立法所认可的过失形态。前述理解可视为对该罪罪过形式可为过失的体系性解释。
然而,即便在过失型妨害传染病防治个案中,也通常存在两类行为动机:一是“方便生活”,由于其自利而难免有“可责性”;二是“协助防疫”等“善良动机”,如扬州等地有个别参与者或志愿者“身带新冠肺炎病毒上岗”,此类善良动机或可被“期待可能性”稀释,从而可免刑事责任。显然,除“善良动机”仍可称为“行为动机”,其他“可谴责”的“行为动机”便是“犯罪动机”。
(二)妨害传染病防治罪故意罪过的进一步肯认
学者指出,将妨害传染病防治罪认定为过失犯罪,既遵从刑法条文和解释性文件的逻辑内涵,又充分体现本罪所包含的传染病防治秩序、公共安全、个人人身权益等多重法益,并与配置法定刑幅度相适应,是自觉遵循罪刑均衡的必然[12](P78)。可见,持该罪过失罪过的观点总体仍处“上风”,但本文认为,其罪过形式为故意与过失皆可。一则,因刑法条文表述并未对该罪主观方面予以限定。二则,“妨害”即“妨碍和有害”,而故意和过失的不利于传染病防治行为都属“妨碍和有害”,故意和过失心理支配下皆可成立“妨害”。
由此,排斥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的故意罪过形式有失偏颇,因为当“传染病能够传染”既是“医学常识”,又是“生活常识”,则行为人怀揣“报复社会”等动机而实施不利于传染病防治的行为,则其行为当然带有直接故意性质;当行为人在此“医学常识”与“生活常识”中,明知自己与人接触的行为可能导致传染,但却听之任之且最终导致传染,则其行为具有间接故意的性质。如从南京“窜至”扬州的毛老太引发大面积感染,便可作为间接故意型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的适例。学者指出,明确拒绝执行防控措施的行为人对于传染病防治法规定的违反属于“明知故犯”,但对于引起传染病传播或有传染严重危险的后果完全可能持否定态度[9](P7),甚至这种态度只表现为过于自信的过失而不可能是疏忽大意的过失[13](P15)。前述论断意在否定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的故意罪过形式,但行为人对于引起传染病传播或有传染严重危险的后果“完全可能”持否定态度,也“完全可能”持肯定态度即“故意”。
回过头来,支持妨害传染病防治罪只能是出于过失的理由难以成立。第一,虽然应将行为人对危害结果的认识和态度作为区分故意犯罪和过失犯罪的标准,但并不意味着行为人对引起甲类传染病传播或有传播严重危险就不能出于直接或间接故意。第二,如果行为人出于故意时便构成“以其他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行为人出于过失时便构成“过失以其他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则第二点理由“不经意间”否定了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的立法。至于法定刑偏低,则关涉该罪罪刑阶梯完善,从而更好地体现罪责刑相适应原则问题。第三,行为人对行为本身形成故意认识与对“引起甲类传染病传播或有传播严重危险”形成故意认识,并不必然矛盾,甚至可在特定情境中“一脉相承”。如餐馆主管明知某厨师是甲类传染病的确诊者,但出于报复社会,准许其继续从事烹饪工作。因此,该罪的主观罪过形式可以是故意也可以是过失。由此,在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的罪过形式问题上,我们也要遵循刑法學命题的“形式逻辑正确性”与“生活实践适切性”[14](P3)。当教义法学的妥当性远远不是靠逻辑演绎说明,而是靠生活实践逻辑来说明[15](P58),则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罪过形式的教义学结论最终应来自该罪的生活实践。
接下来,通过“体系性解释”亦可证明妨害传染病防治罪可以是故意犯罪。学者指出,将本罪认定为过失犯罪,逻辑上不协调[16](P112-113),而我们不能为了区分关联罪名而反推本罪主观罪过为过失[16](P112)。前述论断隐含着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的罪过形式是否只限于过失事关该罪解释的体系性问题。而如果本罪是过失犯将产生“部分行为的认定真空”[17](P70),也隐含着前述体系性问题,因为“部分行为的认定真空”实即故意妨害传染病防治行为的认定真空,而为了避免这一“认定真空”就自然要采用“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这一兜底罪名,正如对“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适用的严格把握自然会使得一部分按照原有标准可以认定为危害公共安全的故意犯罪难以得到有效惩治[17](P70),亦即妨害传染病防治罪为过失犯罪,其对应的故意犯罪为“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18](P126)。可见,若将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的罪过形式只限于过失,则必将产生对该罪解释的体系性问题。
同时,妨害传染病防治行为罪过形式问题的“伪体系性思维”也要警醒。有人指出,在造成特别严重后果的情况下,妨害传染病防治罪法定最高刑为7年有期徒刑。若将本罪限为故意犯罪,最高处7年有期徒刑,法定刑偏轻,罪刑明显失衡,与我国刑法分则规定的故意犯罪最高刑一般在7年以上有期徒刑失调,故将本罪理解为过失犯罪,便可以理顺妨害传染病防治罪与其他犯罪的罪刑关系[1](P84)。学者所谓“可以理顺妨害传染病防治罪与其他犯罪的罪刑关系”,更像迫于该罪法定刑偏低的“无奈解释”,而无法否认妨害传染病防治行为“可以”是故意的“事实性”。
在肯定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罪过形式可为故意之余,我们似乎还应回应学者针对该罪所采用的“客观要素”说辞。具言之,“造成甲类传染病传播”是该罪的所谓“客观超过要素”,亦即既无须行为人明知该结果的发生,也无须行为人希望或放任其发生[10](P1120)。所谓“客观超过要素”,实为“超过主观的客观要素”,即不在行为人主观认知范围的客观要素。可见,学者所谓“超过主观的客观要素”,实即“超过故意的客观要素”。然而,只要影响刑事责任的客观要素,即使“超过故意”,也最终没有“超过过失”,从而学者所谓“客观超过要素”即“超过主观的客观要素”非“以偏概全”,而是“以全等偏”,有割裂“主客观相统一”之嫌[19](P159)。由此,割裂“主客观相统一”不仅使得结果加重犯的成立成了问题,且使结果犯的成立成了问题。回到妨害传染病防治罪,若将“引起甲类传染病传播”作为所谓“客观超过要素”即“超过故意的客观要素”,则将因违反“主客观相统一”而直接影响结果犯型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的成立。于是,这又将引起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的不成立与危险型妨害传染病防治罪都要处罚的明显不协调结论,故“引起甲类传染病传播”仍属于“主观之内要素”,其将在不同场合分别由故意或过失相对应。不仅如此,“引起甲类传染病传播的严重危险”也应纳入“主观之内要素”,以防处罚范围过宽。而为了限制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的适用范围,防止其沦为客观归责的口袋罪,就需行为人对传染病传播的实害结果和具体危险有认识[20](P13)。于是,学者所谓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的具体危险非“客观的超过要素”而是故意的认识对象[20](P4),应扩大为该罪的具体危险即“严重危险”,亦即主观方面包括故意和过失的认知对象。当然,应纳入“主观之内要素”即作为行为人主观认知对象的,首先是“引起甲类传染病传播”的实害性结果。至于“传播危险”是否纳入,则取决于采取何种立法与危险犯理论,而过失危险犯不宜被承认。可见,对妨害传染病防治罪“客观超过要素”的回应,就是对该罪罪过形式包括故意罪过的进一步交代。
(三)妨害传染病防治罪两种罪过形式并存的文本论证与比例描述
妨害传染病防治罪存在两种罪过形式,可得到相关司法文本的印证,正如“非典”时期,2003年5月“两高”联合出台《关于办理妨害预防、控制突发传染病疫情等灾害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按照该《解释》第1条,根据行为人主观方面是故意还是过失,分别认定为“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或“过失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之所以行为人在当时不构成妨害传染病防治罪,是因为当时“非典”尚未被列为甲类传染病,故妨害传染病防治罪尚难适用[1](P80)。前述《解释》印证了妨害传染病防治罪存在两种罪过形式。另外,有关《意见》也能够印证该罪存在两种罪过形式。有人指出,2020年2月6日“两高”“两部”联合制定的《关于依法惩治妨害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违法犯罪的意见》明确规定:故意传播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病原体,危害公共安全的“两种特定情况”应该“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定罪处罚,其他情况则按照“妨害传染病防治罪”定罪处罚[1](P81)。这是否意味着妨害传染病防治罪只能是过失犯罪?这需考察《意见》的具体内容及其“用意”。《意见》规定:“故意传播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病原体,具有下列情形之一,危害公共安全的,依照刑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百一十五条第一款的规定,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定罪处罚:(1)已经确诊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病人、病原携带者,拒绝隔离治疗或者隔离期未满擅自脱离隔离治疗,并进入公共场所或者公共交通工具的;(2)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疑似病人拒绝隔离治疗或者隔离期未满擅自脱离隔离治疗,并进入公共场所或者公共交通工具,造成新型冠状病毒传播的。其他拒绝执行卫生防疫机构依照传染病防治法提出的防控措施,引起新型冠状病毒传播或有传播严重危险的,依照刑法第三百三十条的规定,以妨害传染病防治罪定罪处罚。”《意见》将其所列的“两种特定情况”规定按照“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定罪处罚,意味着在其所列两种情形中行为人有犯罪故意,且至少是间接故意。既然是“传播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病原体”,且“造成新型冠状病毒传播”(对应情形二)或“有传播的严重危险”(对应情形一),则前述故意至少是间接故意,只是当《意见》所列两种情形所对应的妨害传染病防治行为形成了妨害传染病防治罪与“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竞合犯,则出于罪责刑相适应原则而最终以“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定罪处罚罢了。而之所以如此,恐与现行妨害傳染病防治罪法定刑偏低而无从体现罪责刑相适应原则有关。而《意见》在疫情防控特殊时期能更灵活地指导实践,实现特殊时期刑事政策的目的[1](P82)。至于《意见》将“其他情形”以妨害传染病防治罪定罪处罚,对照前述“两种情形”的规定,其首先有肯定该罪存在过失罪过的意味,但也并不排除该罪存在故意罪过。《意见》以“不同情形”解答妨害传染病防治行为的定罪处罚问题,也隐性地运用“体系性”思维,并最终肯定了妨害传染病防治罪两种罪过并存。前述《解释》与《意见》对妨害传染病防治行为存在故意和过失两种罪过给予事实上的肯定,正如学者指出,只有新冠病毒病原体的携带者故意不采取有效防护措施,进入医院、养老院等虚弱人群聚集场所,引起新冠病毒传播危险或者造成传播的,才能依照《刑法》第114条、第115条第1款规定,以“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定罪处罚,否则只能依照《刑法》第330条的规定,以妨害传染病防治罪定罪处罚[21](P19)。
在肯定妨害传染病防治罪既可能是故意,也可能是过失的前提下,就发案率而言,似乎应是过失型妨害传染病防治罪个案多于故意型。进一步地,在故意型妨害传染病防治罪个案中,似乎应是间接故意型个案多于直接故意型;而在过失型妨害传染病防治罪个案中,似乎是过于自信型个案多于疏忽大意型。这里有必要对过失型妨害传染病防治罪个案发生再作例证。国家卫健委先后发布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诊疗方案》明确指出,医疗机构应从流行病学史、临床表现等诸多方面综合判断“疑似病例”。可见,“疑似病人”可理解为“可能感染了传染病的人”,而其不必然但“有可能”再感染其他人。于是,当被专业结构明确告知其为“疑似病人”,行为人仍拒绝隔离治疗或者隔离期未满擅自脱离治疗,并通过进入公共场所或者乘坐公共交通工具等造成新冠病毒传播的,则认定其具有妨害传染病防治罪过于自信的过失,似乎并不为过。但若行为人已经出现明显的新冠肺炎感染症状,行为人凭借其医学常识能够知道其已经感染了新冠肺炎,但因疏忽大意而未认知,并通过进入公共场所或者乘坐公共交通工具等而造成新冠病毒传播的,则认定其具有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疏忽大意的过失,也并不为过。前述可视为对妨害传染病防治罪故意与过失两种罪过形式都可能存在的一种“发生学”补强。
二、妨害传染病防治罪行为对象解释的公允辩护
“甲类传染病”即“甲类以及(或者)依照甲类管理的传染病”是有关妨害传染病防治罪行为对象的解释,这一解释曾遭到误解,但其重要意义并不因其稍显具体的条文表述而丧失。
(一)妨害传染病防治罪行为对象解释的初步辩护
学者指出,按照《刑法》第330条的规定,成立妨害传染病防治罪需引起“甲类传染病传播或有传播严重危险”。于是,“甲类传染病”的范围便涉及刑法与前置法关系与司法解释限度。1989年《传染病防治法》第3条第2款规定,甲类传染病仅限于鼠疫和霍乱,但该条第5款授权国务院可以根据情况增减甲类传染病病种。而2004年修改以后的《传染病防治法》则取消了国务院自行增减传染病病种的权限,同时又创设了“乙类传染病甲类管理制度”。这一立法模式为我国2013年《传染病防治法》所继承。由此,按照甲类传染病管理的乙类传染病是否属于甲类传染病,便是刑法滞后于前置法产生的问题。为了激活该罪的适用,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2008年《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一)》第49条把“甲类传染病”扩大解释为“甲类以及按照甲类管理的传染病”。这一司法解释体现了规则主义与功利主义的博弈,但刑法解释并无权作如此扩大解释。但从功利主义角度,若不扩大,妨害其他传染病防治的行为,要么作无罪处理,要么以“过失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处理。但无罪化处理将导致社会失范,不利于严重传染病防控;而以“过失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处理则会导致无罪行为以重罪论处。既然《刑法》第330条规定,甲类传染病的范围依据《传染病防治法》确定,而《传染病防治法》第3条以列举式规定“甲类传染病为鼠疫、霍乱”,则刑法中甲类传染病的范围没有扩张解释的余地。上述“扩张”甲类传染病范围的司法解释,即属于“有罪论让人看不到刑法规范,规范被隐退在解释者的解释结论之后;看不到规则主义,只有打击犯罪的功利主义、实用主义在蔓延”[22](P109)。该司法解释“关注的是社会效果而非法律效果”,是反教义学化表现[22](P97)。最终,解决问题的办法是把《刑法》第330条第3款修改为“本法所称甲类传染病,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中的甲类传染病以及采取甲类传染病预防、控制措施的乙类传染病”。当然,从尊重司法解释权威来看,司法实践还是应把“按照甲类管理的传染病”当作甲类传染病[20](P13)。学者对于将“甲类传染病”扩张解释为“甲类以及按照甲类管理的传染病”的做法,给予“反教义学化”的根本否定,但是又给予尊重司法解释权威的“宽容”。不过,其还是将立法修改作为最佳方案。然而,“甲类传染病”即“甲类以及按照甲类管理的传染病”,是否真为扩张或扩大解释乃至类推解释?
首先,需考察“甲类传染病”即“甲类以及按照甲类管理的传染病”这一司法解释的实质合理性与必要性。按照《传染病防治法》,传染病可以分为甲、乙、丙三个等级。其所体现的虽非绝对清晰的“质的等级”,但至少是“量的等级”。因此,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的立法首先将最重等级的“甲类传染病”列为该罪行为对象,以体现刑法谦抑性。但同样按照《传染病防治法》,传染病甲、乙、丙三等级各自内部病种是随防治需要可增减的,故当接近“甲类传染病”的“乙类传染病”严重到需“按照甲类传染病管理”,则其就基本形成了相当于“甲类传染病”的危险性和危害性,从而将“按照甲类传染病管理的传染病”也列为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的行为对象,便又体现“刑法谦抑性”中的“必要张力性”,并转化为社会治理的“必要回应性”。有人指出,我国《刑法》未明确规定甲类传染病范围,仅笼统规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和国务院有关规定确定”[1](P80)。既有此规定,则所谓“笼统性”实则很“明确”,且体现该罪立法的“必要张力性”和预防的“务实性”,故有理由相信:“甲类传染病”的实质内涵应为“甲类或者按照甲类管理的传染病”,这一规定符合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本意[23]。
当“甲类以及按照甲类管理的传染病”完全对照《传染病防治法》及其所确立的“乙类传染病甲类管理制度”,而妨害传染病防治罪条文中的“甲类传染病”又是对应《传染病防治法》,则“甲类以及按照甲类管理的传染病”便是地道的“平义解释”,且此地道的“平义解释”后来便以稍显具体的表述而被转换为妨害传染病防治罪行为对象的最新立法规定。显然,“甲类传染病”即“甲类以及按照甲类管理的传染病”这一司法解释,是立于妨害传染病防治罪是法定犯,而法定犯的刑法解释应秉持“刑行衔接”的司法解释。而持否定态度的学者恰好指出扩张解释主要限于自然犯[20](P6)。可见,将“甲类传染病”解释为“甲类以及按照甲类管理的传染病”说成“扩张解释”或“扩大解释”,是至今无人发现的“误读”或“曲解”。至于“类推解释”[24](P6-7),更是“误读”或“曲解”。实际上,《传染病防治法》对于甲、乙、丙三类传染病病种的增减规定符合医学和流行病学规律,因为事实已证明病毒能变异和升级。
(二)妨害传染病防治罪行为对象解释的进一步辩护
现今,仍有学者质疑,《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一)》将新刑法典规定的“甲类传染病”解释为“甲类或者按照甲类管理的传染病”,明显扩大了新《刑法典》第330条的适用范围,具有放宽犯罪认定标准倾向,甚至有类推嫌疑[21](P22-24)。正如前文指出,此种解释是地道的“平义解释”,质疑并不成立。实际上,《刑法修正案(十一)》将1997年《刑法》第330条中的“甲类传染病”修改为“甲类传染病以及依法确定采取甲类传染病预防、控制措施的传染病”,与“甲类以及(或者)按照甲类管理的传染病”几乎无异,只是表述更为具体。因此,《刑法修正案(十一)》对“甲类传染病”的新规定仅是将地道的“平义解释”被人妄加的违背罪刑法定原则色彩予以抹除而已。
有人针对修改前的《刑法》第330条适用问题指出,国家卫生行政部门可依职能决定将某种乙类传染病按甲类采取防控措施,但该乙类传染病并非刑法明文规定的甲类传染病,故行为人传播行为造成的危害后果还是乙类传染病的传播或传播危险,而仍不完全符合修改前《刑法》第330条。当然,行政卫生管理考虑到此种乙类传染病的传播方式、速度、强度及危害程度接近于甲类传染病而采取相同防控措施以示重视,并无不当,但不能改变该传染病类别[25](P61)。可以认为,该论断体现的是绝对形式化的罪刑法定观,而“并无不当”又流露出“莫衷一是”。实际上,真正的罪刑法定原则将形式正当性和实质正当性紧密结合。“甲类传染病”就是“甲类以及(或者)按照甲类管理的传染病”这一解释的正当性,可从前置法得到形式和实质的说明。而《刑法修正案(十一)》将妨害传染病防治罪中的“甲类传染病”修改为“甲类传染病以及依法确定采取甲类传染病预防、控制措施的传染病”,其作为立法的正当性,可从前置法得到形式和实质的说明。因此,质疑或否定“甲类以及(或者)按照甲类管理的传染病”,就是质疑或否定“甲类传染病以及依法确定采取甲类传染病预防、控制措施的传染病”。如前所述,正如《刑法修正案(十一)》将原文规定的“甲类传染病”修改为“甲类传染病以及依法确定采取甲类传染病预防、控制措施的传染病冶”。这一修改将之前司法解释的合理内容吸收,意味着只要行为人实施了妨害传染病防控的行为,且国家卫生行政部门依法确定该传染病为按甲类传染病采取防控措施的,则修改后的《刑法》第330条便可直接适用[25](P61)。于是,我们对法定犯的立法及解释可形成如下基本观念:一是法定犯立法及解释的正当性来自前置法的正当性;二是法定犯立法及解释要体现“罪刑法定性”与“现实回应性”的紧密结合。
“甲类传染病”即“甲类以及(或者)按照甲类管理的传染病”,不仅是地道的“平义解释”,且其可取性能得到由“文义相符性”和“价值(目的)相符性”所构成的“同时符合说刑法解释论”的说明[26](P60-76)。具言之,对“甲类传染病”当然要“施以甲类传染病的管理”,而“按照甲类传染病管理”当然是“施以甲类传染病的管理”,故将“按照甲类管理的传染病”解释进“甲类传染病”便完全具备“文义相符性”即“形式相符性”。同时,从医学或流行病学规律来看,“按照甲类管理的传染病”具有相当于“甲类传染病”的危害性,从而将“按照甲类管理的传染病”作为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的行为对象具有与将“甲类传染病”作为该罪行为对象相当的规范价值,故将“按照甲类管理的传染病”解释进“甲类传染病”便又完全具备“价值相符性”即“实质相符性”。在符合前述“同时符合说刑法解释论”中,“甲类传染病”即“甲类以及(或者)按照甲类管理的传染病”只属于“平义解释”,因为该解释完全对应着刑法及其前置法的规定。由此,将“甲类传染病”即“甲类以及(或者)按照甲类管理的传染病”视为“关注的是社会效果而非法律效果”,从而“反教义学化”,正好背离了刑法解释真相。刑法解释并不或不应排斥解释结论对社会效果的謀求,因为解释刑法是为了适用,而适用又是为了更好地解决社会问题,故刑法解释谋求社会效果本是情理之中。而“同时符合说刑法解释论”的提倡就是谋求将“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结合以消除对立。
最终,“甲类传染病”即“甲类以及(或者)按照甲类管理的传染病”,这一饱受误解的司法解释贡献了极其重要的刑法立法观与解释观:无论是刑法立法还是解释适用,都要坚持将“罪刑法定性”与“现实回应性”、“原则性”与“张力性”、“形式正当性”与“实质正当性”紧密结合的刑事法治观。因此,讨论妨害传染病防治罪行为对象的解释问题并不过时,更有重要意义。
三、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现行立法再完善的设想
虽然“立法不是嘲笑的对象”,但也不能以此为借口而错失应有的立法完善。而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的现行立法确有值得再予完善之处。
(一)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的实害犯与危险犯需对应不同法定刑
对于现行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立法,首先面临着该罪结果犯与具体危险犯能否适用同一法定刑。对此,学者指出,根据《刑法》第330条规定该罪的危害结果包括“引起传染病传播”与“有传播严重危险”,两者违法程度不同,故法定刑也不同。对此,我国《刑法》存在两种立法例:一是在同一法条中规定作为基本犯的具体危险犯和作为结果加重犯的实害犯;二是在不同法条中规定同一犯罪的具体危险犯与实害犯,并且为两者设置不同法定刑。与前述相反,《刑法》第330条为实害犯与具体危险犯设置了相同的法定刑,体现了危害公共卫生罪的特殊性,即就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等危害公共卫生罪而言,传染病的传播实害与传播危险有时很难区别,也无须区别,甚至妨害传染病防治罪本质就是具体危险犯而不是实害犯[20](P10)。在本文看来,传染病的传播实害意味着传染病“已经传播”,而传播危险只意味着传染病传播的可能性。显然,二者的“违法性”和“有责性”深度有别,故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的实害犯和危险犯,应配制轻重有别的法定刑以使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在刑法立法中体现。实际上,“已经传播”和“可能传播”的专业区分并不难,而真正难的可能是“可能传播”与“不可能传播”之间的区分。
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的实害犯与危险犯需对应不同法定刑,是其罪刑阶梯之“题中之义”。
(二)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罪刑阶梯的合理调适
妨害传染病防治罪实害犯和危险犯在法定刑上不加区分,又牵涉到其罪刑阶梯的合理性设置。该问题不过是体现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和满足妨害传染病防治罪预防需要。而要讨论该罪的法定刑,进而到罪刑阶梯设置,则先要解答该罪是否具有公共安全罪罪质。于是,我们必须面对关于该罪犯罪客体的诸多观点:其一,本罪的客体是公众健康乃至生命及社会秩序安定[27](P631);其二,本罪的客体是国家医疗卫生管理秩序,特别是国家防治传染病政策和有关管理活动,以及不特定多数人的生命、健康安全[28](P759);其三,本罪的客体是国家对传染病防治的管理秩序和不特定多数人的生命、健康安全[29](P623);其四,本罪的客体是复杂客体,“主要客体”是国家传染病防治管理制度,“次要客体”是公共卫生[30](P21);其五,本罪的客体主要是国家对公共卫生与健康的管理秩序[31](P36);其六,本罪的客体是国家传染病防治管理秩序和人民健康[5](P419);其七,本罪客体是国家传染病防治管理制度[32](P1077)。可见,除了观点七,其他都直接或间接肯定了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犯罪客体中的人民健康及生命,且观点四中的“公共卫生”虽被放在“次要客体”,实则为“目的性客体”,而“传染病防治管理制度”这一“主要客体”不过是“服务性客体”。在本文看来,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犯罪客体的“公共安全性”无可置疑。
当前仍有学者指出,我国刑法学界仍对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的法益存在误解,如认为公共卫生属于公共安全,因为公共卫生也关系广大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33](P61)。但人是社会活动的中心,很多犯罪如环境、毒品犯罪等与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息息相关,但显然这些犯罪的法益都非公共安全。公共卫生学界基本上都认为公共卫生是一种“制度”或者“秩序”。2003年吴仪副总理指出:“公共卫生就是组织社会共同努力,改善环境卫生条件,预防控制传染病和其他疾病流行,培养良好卫生习惯和文明生活方式,提供医疗卫生服务,达到预防疾病,促进人民身体健康的目的。”[34](P5-11)可见,公共卫生虽涉及公众健康,但公众健康只是目的,而非公共卫生的内涵[20](P10-11)。关键是,公共卫生是通过各种努力而达到“促进人民身体健康和保护生命的目的”。若脱离人民群众的健康、生命安全,则“公共卫生”将没有目标或方向。其实,当把妨害传染病防治罪与“(过失)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定性为法条竞合[18](P127),则已经表明妨害传染病防治罪具有“危害公共安全”的罪质。进一步,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的“公共安全”罪质,可从境外立法中得到有力说明:境外将妨害传染病防治犯罪立法,或直接设置在“危害公共安全罪”中,如我国台湾地区“刑法典”在“危害公共安全罪”中设置了“散布传染病菌罪”;或将其设置在“公共危险罪”中,如我国《澳门特别行政区刑法典》在“公共危险罪”下设“传播传染性疾病罪”。当清除了“公共卫生”与“公共安全”间的观念隔阂,则以“公共卫生”为表相而以“公共卫生安全”为实质的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的法定刑完善,乃至罪刑阶梯完善便有了大致方向。具言之,我们可对照危害公共安全类犯罪的法定刑,设置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的法定刑,调适其罪刑阶梯。
(三)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立法再完善中的“一个必要”与“一个不必要”
“一个必要”针对妨害传染病防治行为的自然人犯罪的罚金刑,即在调适罪刑阶梯中,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的立法应针对自然人犯罪添列罚金刑。对于妨害传染病防治的单位犯罪,现行《刑法》第330条已通过“双罚制”规定了犯罪单位的罚金刑,但《刑法修正案(十一)》仍未就妨害传染病防治的自然人犯罪规定罚金刑。有人指出,是否需要设置罚金刑当以该罪的实际预防和惩治目标为基础。“危害公共卫生罪”共设11个罪名,其中“非法组织卖血罪”等6个罪名具有明显的经济活动属性[13](P20)。从妨害传染病防治行为的现实情况来看,有的自然人是出于任性或极端的“個人行动自由”动机,有的是出于“盈利动机”,即其具有所谓的“经济活动属性”。因此,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的立法应针对该罪的自然人犯罪设置罚金刑,且根据罪行轻重设置“单处制”或“并处制”。
“一个不必要”针对围绕着妨害传染病防治的新罪名增设。对于妨害传染病防治犯罪的完善,有人提出将“未按要求报告,或者隐瞒、谎报、缓报传染病疫情,造成传染病传播、流行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也纳入该罪[13](P22)。但有人提出增设新罪,即“隐瞒、谎报、缓报传染病疫情罪”和“不依法履行传染病疫情通报、报告或者公布职责罪”[21](P27)。首先,就增设“不依法履行传染病疫情通报、报告或者公布职责罪”而言,《刑法》第409条规定了“传染病防治失职罪”,故学者设想增设到第409条中的情形,本就可直接适用“传染病防治失职罪”。另外,渎职犯罪不宜规定单位犯罪。再就增设“隐瞒、谎报、缓报传染病疫情罪”而言,其所对应的“未按要求报告,或者隐瞒、谎报、缓报传染病疫情,造成传染病传播、流行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可直接适用修改后的《刑法》第330条第1款第5项,即“拒绝执行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疾病预防控制机构依照传染病防治法提出的预防、控制措施的”。至于现实生活中行为人采取藏身车辆后备厢等妨害传染病防治的现象,也可直接适用第5项。
(四)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立法再完善的最后归结
综上所述,我们可在现行《刑法》第330条中新增如下表述:违反传染病防治法的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列举省略),过失引起甲类传染病传播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单处罚金;后果特别严重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第1款)。行为人故意实施第1款行为造成甲类传染病传播严重危险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并处或单处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第2款),并处罚金。行为人故意实施第1款行为造成甲类传染病传播的,处5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后果特别严重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第3款),并处罚金。原有的第3、4款相应地作为第4、5款。以往关于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的修改之声仍在回响,如“适当调整刑罚量刑幅度并扩大罚金刑适用”[35](P125),或“将传播传染病主观要件仅局限在过失上不科学”[36](P71),或“为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的危险结果和实害结果设置不同法定刑”[37](P65)。本文再修法设想是对前述回响的响应。另外,本文在此要提醒:没有对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现实危害的切实体会,只会对该罪法定刑是否完善及罪刑阶梯是否调适无动于衷,而脱离对现实生活的真实感受是中国刑法理论“空发议论”的通病。
有人指出,疫情防控期间要防止情绪立法,但更要注意情绪司法,否则会造成违反罪刑法定的危险。我们要慎用“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避免使之成为口袋罪[1](P87)。“(过失)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已是“口袋罪”,但还要防止其“袋口”过度扩张。就妨害传染病防治罪而言,必要的完善非“情绪性立法”,而对相应的妨害传染病防治行为且“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论已是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立法存在“现有缺漏”下的“无奈”“情绪司法”。因此,在成文法传统下,科学的刑法立法才能从根本上抵御“情绪刑法司法”。
四、代结语: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立法再次完善前的相关适用问题
于再次立法完善前,妨害传染病防治罪仍要澄清或解答相关适用问题。
有人讨论了将妨害传染病防治行为定性为“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合理性。刑法学界一般认为,“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是指使用与放火、决水、爆炸、投放危险物质等危险性相当的其他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38](P338)。该罪与所列明的放火、爆炸、投放危险物质行为“相当”包括危害性、危险性、行为特征相当。就传播新冠肺炎的行为而言,其侵害的主要法益是不特定多數人的健康、生命且损耗大量社会财富。因此,传播新冠肺炎的行为与《刑法》第114条、第115条所列的犯罪行为在特征上基本相当,但略有差异。其一,两者均有因果关系,但紧密程度不同。具言之,放火等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的关系具有紧迫性,但新冠肺炎病毒通常有一定潜伏期。其二,行为人实施危害公共安全行为是共同特征,差异表现在放火等犯罪行为具有直观性,但病毒细小不能直观感知,且传播行为与人的正常活动的区别也难以感知。其三,两者都会引起结果或危险,差异在于放火等犯罪结果是犯罪行为直接造成,且通常不会有更大结果,而后者会在不知不觉中传染,从而产生更严重结果。其四,两者都有犯罪动机,但前者的动机一般出于报复、仇恨等,而后者的动机一般是对防控措施的反感等。上述两类行为共同或基本相当之处决定其本质的一致性、犯罪构成的共同性,而决定了适用“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合理性。但也有人认为,《刑法》第114条、115条中的“其他危险方法”,只是该两条的兜底规定而非刑法分则第二章的兜底规定[39](P43)。前述论断却主张妨害传染病防治的行为不能以“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论。在现行刑法没有调适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罪刑阶梯且提升该罪最高法定刑前,出于贯彻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和满足预防需要,至少将故意引起传染病传播,特别是“造成特别严重后果的”,论以“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是务实“权宜之计”,且具有“刑法法理”根据。此根据即妨害传染病防治罪与“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间的规范关系。既然妨害传染病防治罪具有“危害公共安全”罪质,则前述规范关系应为“法条竞合”。但在确认“法条竞合”前,妨害传染病防治行为能否实质归入《刑法》第114条、115条的“以危险方法”这一前提问题应得到合理解答。前述所引论已说明这一合理解答能够作出,但本文再作深化:《刑法》第114条、115条的“投放毒害性、放射性、传染病病原体等物质”完全可与传播传染病毒形成从形式到实质的基本对应,而之所以说“基本对应”,是因为传染病毒是“毒害性物质”,但“传播”与“投放”又不具有行为外在特征的完全“吻合性”。至于“其他危险方法”只是该两条的兜底规定而非刑法分则第2章的“兜底”,更非刑法典分则的“兜底”,这一点不足为虑,因为“法条竞合”的背后是“法益竞合”,而“法益竞合”在刑法典分则中可有较大“跨度”,这又由“法益结构”所决定。
有人在讨论妨害传染病防治罪适用问题时还提出“客观行为的环境范围问题”。即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的犯罪行为针对不特定多数人,一般发生在公共场所。新冠病毒这种以飞沫为主要传播源且传播率高、速度快的病毒可以通过多种方式传播,同样产生危害公众的后果。另外,除了人传人的传播方式,还有物传人等方式。因此,“公共场所”应作广义理解[25](P65-66)。其实,无论妨害传染病防治行为最终论以何种罪名,“客观行为的环境范围问题”都不可回避,因为其直接关涉相关罪名的客观构成要件。本文认为,应将“客观行为的环境范围”对应的“空间观念”转为“交往观念”,即由“物理观念”转为“事理观念”。如此,则诸如行为人对迎面而来的仇人“飞沫相向”以致其被新冠病毒感染,进而造成他人相继感染等类似情形,都应视为具备了妨害传染病防治罪或“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所要求的“空间条件”。
参考文献:
[1]张启飞,胡馨予.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的法教义学展开[J].法律适用,2021(7).
[2]马荣春,朱俊岑.论罪过性的要素增减与构造性[J].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19(6).
[3]陈广君.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释义[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
[4]李希慧.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新论[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1.
[5]马登民,王东.新刑法精解与适用[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97.
[6]叶峰.刑法新罪名通论[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1997.
[7]孟庆华.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的几个构成要件问题[J].法学论坛,2004(1).
[8]王作富.刑法分则实务研究[M].北京:中国方正出版社,2013.
[9]刘宪权,黄楠.论拒绝执行防疫措施行为的刑法定性[J].法治研究,2020(2).
[10]张明楷.刑法学[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6.
[11]马荣春.刑法典分则体系性的类型化强化[J].法治研究,2020(4).
[12]蔡荣.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罪过形式的确定——对传统罪过理论的复归[J].当代法学,2021(3).
[13]朱德安.妨害传染病防治罪适用正当性及其修正[J].法治社会,2020(3).
[14]马荣春.论刑法学命题的妥当性[J].东方法学,2016(1).
[15]马荣春.“三常思维”:法学方法论的统领性思维[J].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19(3).
[16]陈伟.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的主观罪过及其适用[J].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0(3).
[17]张剑.妨害传染病防治罪主观要件辨析[J].中国检察官,2020(10).
[18]赵冠男,李思尘.妨害传染病防治罪之主观罪过——“过失说”之提倡[J].湖北警官学院学报,2021(2).
[19]马荣春.“主观的超过要素”:一个不适合的域外刑法学命题[J].交大法学,2014(4)、2015(1).
[20]欧阳本祺.妨害传染病防治罪客观要件的教义学分析[J].东方法学,2020(3).
[21]冯军.危害公共卫生行为的刑法防治——《刑法修正案(十一)》的相关规定为中心[J].法学,2021(2).
[22]刘艳红.“规范隐退论”与“反教义学化”[J].法制与社会发展,2018(6).
[23]李文峰.准确适用妨害传染病防治罪 依法严惩抗拒疫情防控措施犯罪[N].检察日报,2020-02-12(3).
[24]张明楷.《刑法修正案(十一)》对司法解释的否认及其问题解决[J].法学,2021(2).
[25]范雪珂.妨害传染病防治罪适用之探讨——以刑法修正案(十一)第37条之规定为视角[J].法律适用,2021(7).
[26]马荣春.“同时符合说”:刑法解释甄别的新尝试[J].中国刑事法杂志,2019(6).
[27]欧阳涛,魏克家,刘仁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新刑法注释与适用[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1997.
[28]苏惠渔.刑法学[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
[29]周振想.刑法学教程[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7.
[30]刘远.危害公共衛生罪[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3.
[31]彭兰.妨害传染病防治罪[J].中国刑事法杂志,1998(5).
[32]曹子丹.新刑法罪名量刑与案例通览[M].吉林:吉林人民出版社,2000.
[33]陆诗忠.论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中的“危险方法”[J].法律科学,2017(3).
[34]吴仪.加强公共卫生建设,开创我国卫生工作新局面[J].中国卫生质量管理,2003(4).
[35]尹辉金.论妨害传染病防治罪[J].湘潭大学学报,2004(2).
[36]詹红星.中外妨害传染病防治罪构成要件比较研究——兼论《刑法》第330条的立法完善[J].韶关学院学报,2006(2).
[37]竹怀军.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立法的比较与借鉴[J].西南政法大学学报,2006(1).
[38]高铭暄,马克昌.刑法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
[39]张明楷.论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扩大适用的成因与限制适用的规则[J].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12(4).
The Crime of Obstructing th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Infectious Diseases:Clarification,Defense and Assumptions
YUAN Lin,BAI Xing-xing
(School of Law,Southwest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Chongqing 401120,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doctrine of criminal law and the genetics based on the facts of life,the criminal forms of the crime of obstructing th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infectious diseases should include intention and negligence.The connotation and denotation of "Category A Infectious Disease",which is the object of the crime of obstructing th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infectious diseases,should be grasped by closely contemplating the "Infectious Diseas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Law" as the pre-method.We should pay close attention to the interpretation of "Category A infectious diseases",namely "Category A and infectious diseases managed in accordance with Category A" made by the pre-method,the "Law on th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Infectious Diseases".There are problems with the principle of statutory crimes and punishments by analogy interpretation;close attention to the judicial interpretations and criminal law revisions made by the pre-law,the "Law on th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Infectious Diseases," reflects a kind of "statutory crimes and punishments" and "realistic responsiveness." So it is "principle" and "tension",and ultimately,"formal legitimacy" and "substantial legitimacy" are closely combined with the concept of criminal law.The existing legislation on the crime of obstructing th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infectious diseases should also be improved in terms of the establishment of crime and penalty steps and the addition of fines.However,before the new round of legislative improvement,in order to embody or implement the principle of adapting crimes,responsibilities and punishments and to meet the actual needs of preventing the crime of obstructing th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infectious diseases,behaviors that hinder th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infectious diseases in specific situations can be regarded as "dangerous methods to endanger the public security crime".The "behavior location" and other issues involved in the identification of the crime of obstructing th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infectious diseases also need to be answered in the changing concept.
Key words:
crime of obstructing th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infectious diseases;category A infectious diseases;crime of endangering public security
(責任编辑 刘雪斌
)
收稿日期:2021-11-06
基金项目:
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项目“多元涉诉信访智能处置技术研究”(2018YFC0831800);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理论研究重点课题“疫情防控背景下的司法政策研究”(GJ2020B01)。
作者简介:
袁林(1964-),女,四川南充人,西南政法大学特殊群体权利保护与犯罪预防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犯罪学学会副会长,从事刑法基本理论与实践、特殊群体犯罪预防与治理、刑法解释研究;
白星星(1990-),女,山西吕梁人,西南政法大学特殊群体权利保护与犯罪预防研究中心研究员,2018级刑法学专业博士研究生,从事刑法基本理论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