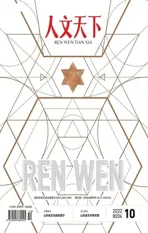神秘与人文:《论语》丧祭之礼的双重意味
2022-02-28韩小茹
■ 韩小茹
中国社会的丧祭之礼本为一种宗教性的仪式,但到了春秋时期,人文理性思潮的发展使得其宗教神秘意味骤然减少,这种理性与信仰的冲突使得学者对于礼乐文化中丧祭之礼性质的看法产生了分歧。例如,胡适认为孔子只有一种“自己催眠自己的祭祀哲学”,“往往没有一点真得宗教情感”①胡适:《说儒》,桂林:漓江出版社,2013年,第101页。;梁漱溟主张以道德代宗教,却也认为“但我们假如说中国亦有宗教的话,那就是祭祖祀天之类”②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芜湖: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89页。;冯友兰则直接否定了儒家礼教与宗教的关系,认为儒家的礼,特别是婚丧祭礼,是诗而非宗教。③参见冯友兰:《三松堂全集》第11卷,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184页。关于儒家丧祭之礼人文性与宗教性的种种分歧并非完全是因为学者本人的独特理解,而是因为导致这种分歧的矛盾与冲突在孔子时代切实存在,而且可追溯到前孔子时代。
依陈来之见,中国古代文化演进的基本方式为“包容连续性”,在分别以巫觋、祭祀和礼乐为特征的三代文化的漫长演进中,必然将前代的文化包容为自己的一部分,并且存在着道德理性逐渐压倒宗教意识的对决。④参见陈来:《古代思想文化的世界:春秋时期的宗教、伦理与社会思想》,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143页。但理性压倒宗教的过程是缓慢复杂的,到了孔子时代也是如此,故纯粹从“神本信仰”或“人本理性”的角度看待礼乐文化中的丧祭之礼是偏颇的。所以本文试从宗教、哲学双重角度来考查《论语》中的丧祭之礼,意图证明《论语》中的丧祭礼同具神秘与人文双重意味。如李景林在《儒家的丧祭理论与终极关怀》中所言“儒家言礼,以丧、祭为一体”,古代的丧礼与祭礼并不是各自分明的,在《论语》中也是如此,因此本文考察的对象为“丧祭之礼”,而非“丧礼”或“祭礼”。
一、敬:丧祭礼之呈现
《论语》中关于丧祭之礼的记述较为零散、简略,主要集中在《八佾》《乡党》篇中,可从丧祭礼仪、丧祭旁观者和丧祭对象来进行考察。
(一)丧祭礼仪
《论语》关于丧祭礼仪的记载可按照时间顺序分为前中后三部分。丧祭前,须斋戒。“子之所慎:齐、战、疾。”(《论语.述而》,下文所引《论语》一书仅注篇名)《论语注疏》中“齐”作“斋”,钱穆、杨伯峻也认为“齐”与“斋”同,《乡党》篇更有“齐必有明衣,布。齐必变食,居必迁坐”的记载。所谓“变食”,即不饮酒,不食剩菜、葱蒜、鱼肉。而在丧祭行为发生的当下和之后,《论语》强调“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为政》)、“祭思敬,丧思哀”(《子张》)、“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八佾》)的敬。这种敬一方面表现在祭祀者的心理状态是否哀戚,另一方面表现在祭祀行为是否恰当,如吊丧时不穿黑羔裘,不戴玄色冠等。
(二)丧祭旁观者
在《论语》关于丧祭的记述中还有一特殊存在,即偶遇参加丧祭活动的人。比如,穿齐衰丧服的人、轻丧去冠括发的人来见孔子,孔子必从坐席上起身;若孔子从这些人身旁走过,必改步疾行;乡里人迎神驱鬼,要穿着朝服站在东边的台阶上;孔子见到穿丧服之人,虽是平素亲近之人,必改变容色以表示哀悼;见到戴礼帽的人,要在容貌上致不安;遇到穿凶服的人,要凭轼致哀。《论语》中的这几处记载生动刻画了祭祀旁观者的言行举止,突出了丧祭中“敬”的重要性。
(三)丧祭对象
丧祭对象主要包括“泰山”“褅”“鬼”“神”“丧者”,丧祭对象正是丧祭者发出“敬”的仪式与情感的承受者。祭祀泰山,意指祭祀天地等;“褅”包括祭祀祖先、天地、社稷、五祀等;所谓“鬼”“神”,都是人死后所化,因此无论丧者是否是与自己有血缘关系之人,都可归于鬼神。综上所述,可将五种丧祭对象归纳为天、祖先、鬼神。
通过以上分析,可看出“敬”在《论语》的丧祭之礼中一以贯之的地位:或由情感表现之,或由行为表现之。然而,关于“敬”的思想并非儒家首创,在孔子之前,“敬”的观念就已经盛行。“敬”作为一种情感,最初源于先民对于神秘力量的畏惧;到了殷商时期,“敬”的对象还是超自然界,其具有的人格神特征使得对于灵魂世界的这种“敬”的情感还是宗教性的。而从《尚书》中可以看出,西周时代形成了一个以敬德为中心、上统敬天、下统敬民和敬事的“敬”论系统。此时,“敬”的对象由超自然界部分转向了人自己的行为——德,虽未完全脱离殷商时期的宗教意味,却开启了人定胜天的儒家系统。再由《尚书》发展到孔子,便逐渐使“敬”成为儒家一重要德目,包括对鬼神天命的敬畏、对他人的尊重、处事时的认真以及修己时的审慎。
“敬”观念的此种流变反映出“敬”经历了一个逐步理性化的“祛魅”过程,从对超自然物的恐惧渐渐成为一种道德观念,这一过程也是人在与超越界的对举中主体意识逐步觉醒的过程。但是,“春秋时代以礼为中心的人文精神的发展,并未将宗教完全消灭”①徐复观:《中国人性论史·先秦篇》,北京:九州出版社,2013年,第46页。,这一理性化过程在孔子时代并未完全实现,在《论语》的丧祭之礼中具体体现为外仪式与内情感的统一、敬鬼神与远鬼神的协调、主宰天与境界天的混存。
二、外仪式与内情感的统一
《论语》丧祭之礼的双重意味首先表现在守丧活动,特别是在关于“三年之丧”的讨论中。宰我认为三年之丧过于长,主张缩短守丧时间,改为一年,孔子回应“女安则为之”(《阳货》)。关于守丧,《论语》只提及了为父母守丧的期限为三年,《礼记》中有许多关于为父母守丧期间衣食住行的规定,如孝子要住在倚庐中,以草苫为床铺,以土块为枕头,不能说与丧事无关的话等。
卡西尔认为在宗教发展的过程中,存在着禁忌主义。②参见[德]恩斯特·卡西尔:《神话思维》,黄龙保、周振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第244页。禁忌主义体系注重行为而非动机,因此强加给人无数的责任与义务,如在从事任何重大事情之前必须节制自然欲望,采取禁食、减少睡眠等方法,以此来加强肉体上巫术的效验。《论语》中这种对于特定行为的回避与宗教中的禁忌主义相似,即主动让自己的躯体处于受制状态。所谓“禁忌”,除了含有禁止某些行为,也包括禁止不做某些行为,因此在《论语》中对于某些仪式礼节的恪守,如守丧的时间等,从性质上讲也与禁忌主义具有同样的宗教神秘意味。并且周公最初制礼作乐时取法于天道,参天地、阴阳、四时、日月星辰来制定,通过“神道”的方式来达到“设教”的目的。孔子虽然对其有所损益,但以三年之丧为代表的这些礼的根源仍是具有神性的天、地等事物,到了孔子这里也难说与此毫无关系。
同时,在关于“三年之丧”的讨论中,孔子将守丧与“安”建立起联系,这就使得《论语》中的守丧活动从一种充满宗教意味的行为中建立起人文理性意味。“仪式的真正合理性来源是人之为人的感情与理性”③葛兆光:《中国思想史》(第一卷),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53页。,孔子在回应宰我对于三年之丧的疑问时说“女安则为之”(《阳货》),正将整个守丧活动的合理性就建立在一个人之为人的“安”上。何为“安”?朱熹认为“夫子欲宰我反求诸心,自得其所以不忍者”④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2016年,第182页。,也就是指心安,钱穆与杨伯峻也均将其理解为心安。因此可以说,三年守丧是子女表达悲伤的一种方式,是一种心上的活动,发自内心的敬重,通过心灵的悲戚状态和不安来达到最终的安心。
心本体或情本体是儒家的基本精神,但并非完全沉溺于心或情的主宰。保持情感的哀伤以示怀思并非无节制地放纵情感,《子张》篇云,“祭思敬,丧思哀,其可已矣”,保持悲哀是丧礼的基本内容,但过于悲哀也违背了丧祭之礼。因此,儒家虽强调情感,但因为有理性的参与,便使之不同于狂热之宗教情感,这种理性参与的心理情感正是仁。这就意味着儒家丧祭之礼非是用形式或宗教将生人与逝者联系起来,而是将仪式从强制性的外在约束转化为人心自觉性的内在要求,从而使一种宗教神秘意味的仪式活动变为人伦日用之常,赋予了丧葬仪式理性气息。
因此,“三年之丧”是通过外在肉体上类似于苦行僧的居丧行为,与心理情感上的合理哀伤来使得居丧者能践行通达仁,所体现的是儒家在丧祭仪式中并非侧重于丧祭仪式中行为的敬,也非将其局限在内在情感的敬,而是关于整体身心的。孔子虽认为“丧,与其易也,宁戚”(《八佾》),但对于丧葬之礼中最为基本和关键的形式并未删减,而且还在前儒学时期带有浓重宗教意味的丧祭仪式的基础上,通过情感赋予了神秘仪式人文理性气息。
三、敬鬼神与远鬼神的协调
《论语》对鬼神的“敬”一方面承续了殷周以来崇尚鬼神的传统,是对超自然物的敬畏,具有宗教色彩;另一方面,孔子强调敬而远之。因此,这种敬已经有了人的自觉,不同于原始宗教对超自然物的虔敬。两方面在《论语》中混杂起来,便形成了《论语》中孔子鬼神观的矛盾之处。
《论语》中孔子虽不多直接谈论鬼神,但也不反对祭祀鬼神,对于鬼神总的态度是“敬鬼神而远之”(《雍也》)。所谓对鬼神的“敬”便表现在非其鬼不祭与“祭神如神在”(《八佾》),即只祭祀自己的祖先亲人,而且祭祀时心理情感要到位。这种对行为仪式的恪守和心理情感的呈现正是“敬”的体现。除此之外,《子张》篇更有“祭思敬,丧思哀”的话语,皆是强调了在祭祀中“敬”的重要性。据此,有学者认为孔子是宗教家,这种观点自然是与孔子的仁学相悖,但孔子在《论语》中主张敬事鬼神确实是带着宗教精神的。此种宗教精神来自中国历史中崇尚鬼神的传统,即意图通过祭祀的方式来讨好鬼神,从而达到祈福避祸的目的。在《论语》中对于鬼神的敬不无此种宗教心理,如“获罪于天,无所祷也”(《八佾》,“丘之祷久矣”(《述而》)。这两句的已有注解,多是从人文主义视角出发予以解读,认为孔子倾向于无神论,或是说阿附权臣不如忠于君主。但结合当时鬼神思想弥漫的时代背景,不妨解释为人虽无法干预天命,但在天命未降下之前,未必不能去祈福。
虽然对于鬼神的祭祀带有宗教心理,但发生机制却有所不同,比如祖先崇拜。《尚书》记载,效法遵循文王的德政,方能求得上天的保佑,从而实现国家的长久。据徐复观在《中国人性论史.先秦篇》中的解释,之所以如此推崇文王,主要是因为人们认识到天命不易把握,因此试图通过文王具体之德来作为行为的启示,因此“文王便成为天命的具体化”。将神秘莫测的天命具体化到人的身上,已经有了人文精神的觉醒,到了孔子,更是对禹“致孝乎鬼神”的行为表示“无间然”(《泰伯》)。将“孝”作为鬼神崇拜的部分原因,进一步赋予了敬鬼神伦理道德意味。“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学而》)“孝”构成了生者与逝者之间的联结,使得生人对鬼神的祭祀具有了道德教化的功用,以家国同构的理路推广开来,更具有稳定社会之政治作用。
此外,《论语》中孔子虽主张祭祀鬼神,但又“不语怪、力、乱、神”(《述而》),主张对鬼神“远之”。这是否能够作为孔子不信鬼神的依据,答案必然是否定的。晁福林在《春秋时期的鬼神观念及其社会影响》中指出,从严格的意义上讲,在春秋时期并没有出现也不可能出现真正的无神论者,睿智如孔夫子,也不能跳脱当时的历史环境。因此,孔子对于神秘莫测的鬼神虽不能证知,但仍然怀有敬畏之心。而之所以要与鬼神保持界限,一方面是因为当时僭越礼制的行为屡见不鲜;另一方面则是因为祭礼逐渐成为人们谄媚鬼神、趋福避祸的手段。此两种现象都属于“谄”,后果就是人们将祸福寄托于神灵,而非自己的德行。
因此,一方面,孔子非无神论者,故而仍然强调祭祀鬼神时保持敬畏;另一方面,孔子将对于鬼神的祭祀视为孝的体现,将生者与逝者的神秘联结建立在理性情感的基础上,所以又不会像之前一样对鬼神有虔诚的信仰。另外,周礼的内容主要就是祭祀天和神灵,孔子自称“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八佾》)。因此,根本取消某一项礼应该不是孔子的做法,他更可能采取的方式是对其加以修改,有所损益。因此,《论语》中孔子对鬼神的祭祀,一方面是保留了传统宗教祭祀的意味,一方面则具有了理性色彩,如果将“敬”与“远”相割裂,便会造成孔子鬼神观的矛盾,也会产生对孔子思想的误读。
四、主宰天与境界天的混存
祖先、鬼神、天三者的关系十分微妙,无论是祭祖先还是祭鬼神都可以归于祭天,即三者在意义上保持着关联。虽然祭祀的对象一般为具有人格神意味的天,但在《论语》中因为对于“天”的阐释的复杂性,且天的多重意味的界限并不十分明晰,因而不排除祭天包含着多重意味。
“天”的观念可追溯到殷商时期。晁福林认为“甲骨文的‘帝’能够表示天的大部分意蕴”①晁福林:《说商代的“天”和“帝”》,《史学集刊》2016年第3期。。虽然在殷商时,上帝不是直接祭祀的对象,但通过祈求祝福可达到敬祈上帝的目的。“帝”是殷人在思想信仰上主要敬奉的对象,凡事都要贞问“帝”,此时的宗教尚处于自然宗教阶段。因此,“帝”的观念并无道德伦理意味,完全是宗教性的,带有浓烈的人格神色彩,有支配自然的能力。而周作为“大邑商”下的一“小邦周”,继承了殷商的思想文化、宗教信仰等,包括天帝观念,故《尚书》所反映的西周时的“天”很大程度上仍是宗教意味的主宰之天。不同之处在于,到了西周时期,一方面,“因上帝之国,不在人间,而在天上”②翦伯赞:《中国史纲》(第一卷),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299页。,故上帝又称为天,因此周人更多地祭祀“天”,但也没有完全消融“帝”;另一方面,“天”具有了理性色彩,如《尚书.多士》中周公向殷民解释为何要灭掉殷时,认为是殷的嗣王“罔顾于天显民祗”,所以上天把灭亡的灾祸降临到殷商,周只是帮助上天行使命令。也就是说,此时天命的降与夺不再是盲目的,而是以人王的行为为标准。更为重要的是,也对天发出怀疑与否定,如《尚书.君奭》篇中周公即表示要“念天威”,也表示“天难谌”“天不可信”。由此可知,《尚书》所反映的周时的敬天敬帝观念承续并转化了殷商的宗教信仰,闪耀着人文理性之光。
到了《论语》中,“天”自然而然出现了多重意味,如赵法生认为孔子的“天”依然是宗周的主宰之天,③参见赵法生:《孔子的天命观与超越形态》,《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6期。路德斌细化出一种“身心与‘天命’契合无间,融而为一,无内外之分,无天人之别的‘天人合一’的境界之天”④路德斌:《孔子“天”论新探——“天”之“境界说”释义》,《孔子研究》1990年第3期。。几种不同性质的“天”在《论语》中混存,包括自然之天。主宰之天直接来源于商周时代宗教性的主宰之天,是个体命运的决定者。在《论语》中,主宰之天占绝大多数,如“死生有命,富贵在天”(《颜渊》),“获罪于天,无所祷也”(《八佾》),均表示个人命运的决定者,与此主宰之天相关的“命”“天命”也多是时命的意思,对人起了限制作用。
境界之天是儒家哲学天人合一思想的基础。孔子认识到人与天的联结,开辟出仁的路径,从而使人可以通过自我修养来通达天,实现了主宰天向境界天的转化,但此种转化并不意味着主宰之天的消失。孔子在《为政》篇云:“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学”“立”“不惑”均是达到“知天命”的修炼阶段。所谓“知”即是从自己的生命中证知了天命,而“知”之后,便可到达天人合一的境界。能够通达这种境界的途径便是“下学而上达”的道德修养,具体内容就是“仁”。将仁展开来说便是孝悌、克己复礼、恭宽信敏惠等,也包括对鬼神的敬而远之、内在情感的展开、外在行为的践行,这样便使得有限的个体有机会通过“下学而上达”的道德人格的自我修养进达“天人合一”的境界。而丧祭之礼中外仪式与内情感的统一和非鬼神与敬鬼神的协调,正包含在此途径当中。它们虽内含宗教意味,但最终的落脚点是人,具体来说便是人之道德,此正如徐复观所言:“孔子及由孔子发展下来的祭祀,则是推自身诚敬仁爱之德,以肯定祭祀的价值。”①徐复观:《中国人性论史·先秦篇》,第75页。由《论语》中“天”的此二种意义不难推断出对于天的祭祀与敬畏,既包含着由天主宰人而引起的宗教神秘意味,也包含着由人通达天的人文理性意味。
结语
《论语》中的丧祭之礼可落脚于“敬”,“敬”从前氏族时代到商周再到孔子时代的演变,包含着宗教神秘意味向人文理性意味的过渡,此种过渡是复杂且漫长的,《论语》中外仪式与内情感、敬鬼神与远鬼神、主宰天与境界天的矛盾正说明这一点。丧祭之礼是儒家伦理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论语》丧祭之礼又是儒家丧祭之礼的代表与缩影,它在保留原始宗教仪式的同时赋予其道德内核,使其从宗教仪式逐渐转化为礼。
因此,儒家丧祭之礼首先将丧祭仪式、活动的合理性落脚于人之为人的理性与情感,通过庄严肃穆的丧祭仪式给予生者心理情感之安慰勖勉,生者的这种心理情感又构成道德之本——孝,成为道德修养之基础,从而使人可以通过内在道德修养与外在行为的磨练来通达天人合一之境。
其次,对于原始宗教祭祀仪式所供奉的超自然领域的鬼神,虽然孔子时代尚不能从理性上对其进行证实或证伪,但却将祭祀鬼神的合理性部分落脚于“孝”这一德目,从人心上立论,使得神秘的宗教仪式具有了道德教化的作用,已然从鬼神的蒙蔽之下撕开了一道口子。
总而言之,《论语》一方面通过对原始祭祀仪式的甄选、对鬼神的敬畏和对天的主宰义的存留,使其丧祭礼内涵宗教神秘意味;另一方面,又通过内在道德情感世界的开辟、对超自然界的远离和境界之天的生发,体现出其人文精神,《论语》丧祭之礼的独特性与重要性正在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