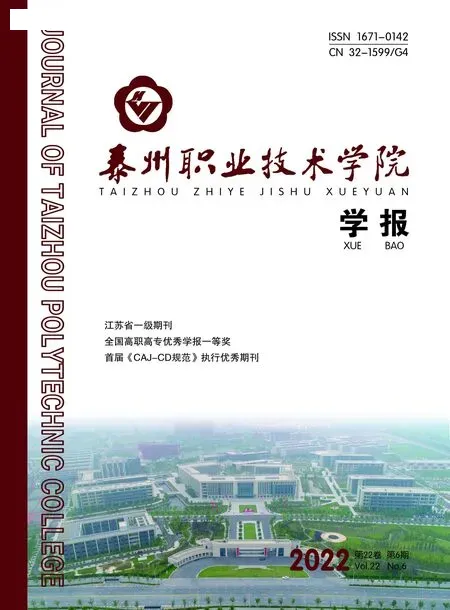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路径研究
2022-02-28沈春梅
沈春梅
(1.南京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苏 南京 210023;2.江苏海洋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苏 连云港 222005)
百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过程,同时也是一部马克思主义不断大众化的过程。从本质上看,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马克思主义获得广大人民群众的广泛认知、普遍认同,并且自觉在实践中践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质和精神内涵。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在中国的成功构建是多方合力的结果,其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意识形态内在系统包括理论体系、价值体系、话语体系和实践体系等多层内涵,其中理论体系是核心,价值体系是引领,话语体系是桥梁,实践体系是落脚点。
1 以民族文化为基础,实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
理论创新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根本动力。党的十七大报告中首次出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这一提法,此后其作为理论命题被广泛提及。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理论内涵由来已久。1938 年,毛泽东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重大命题中蕴涵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深刻理论内涵,毛泽东强调让马克思主义“群众化”,让它们走出课堂和书本,真正为“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所掌握”。[1]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最终归宿是使得马克思主义走入社会生产和生活的实践中,发挥着理论武器的重要作用。这一内涵从客观上要求马克思主义理论不能停止创新,不能仅仅停留在马克思恩格斯等经典文章和论述中,而是应该挣脱出教条主义的桎梏,站在马克思主义实践观、发展观的理论立场,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分析时代发展的实际问题,结合民族特色找到解决问题途径,同时也通过这一过程实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此外,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在深层逻辑层面有一种高度契合性,这是二者能够相结合的客观前提。正是在这种内在契合性基础上,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文化的历史性碰撞极大地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社会的广泛传播。
(1)作为中华民族“根与魂”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重要动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民族在几千年历史中创造和延续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2]五千年文明历史所积淀的“根和魂”是人类文明的精神宝库,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中丰富的新观点、新论断都是在中华文明传承的典范。具体而言,主要通过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品质和思维方式来实现马克思主义化的历史过程。其一,“万物一体”整体思维。传统文化注重事物之间、事物内部的联系,强调和天地万事万物的和谐发展。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和发展的过程中传承传统文化中的整体思维方式,坚持以经济发展为核心同时坚持全面从严治党,注重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推进社会主义文化事业发展与繁荣,注意生态保护与开发,力求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生态发展、社会治理等一体多翼、同步进行。其二,“福祸相依”的辩证思维。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朴素的辩证思维与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有着内在契合性,习近平总书记经常运用传统文化中的辩证思维来阐释在治国理政的过程中重大理论问题,多次引用“治大国如烹小鲜”“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见骥一毛,不知其状;见画一色,不知其美”等传统文化中辩证思维的典故来阐释运动发展观、整体与部分的关系等。其三,真抓实干的务实思维。中华传统文化以典型的农耕文明为基础,形成了“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的务实思维。传统文化中的务实思维深刻影响了习近平治国理政的思想,其显著特征就是注重实干。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实干精神和务实品质,“空谈误国,实干兴邦”[3]“幸福不会从天而降,好日子是干出来的”[4]。其四,“防患于未然”的底线思维。中华文明具有深沉的忧患意识,构成了中国人精神底色和思维方式。习近平总书记在传统“防患于未然”的忧患意识的基础上,发展出一套治国理政的底线思想,强调把握主动权,展现出中国共产党的洞察力,对国际、国内复杂形势的判断力,进而切实提升自身防范和化解重大危机与风险的能力。作为治国理政中的重要理论创新,底线思维建立在优秀传统文化中深沉忧患思想的基础上,展现了党和国家高超治国理政能力,也成为传统文化传承的优秀典范。
(2)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理论体系为中华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提供了理论指导和方法论基础。文化是一种时间性的存在。正如马克思所言:“每一历史时代的经济生产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的基础”[5]。文化总是存在于特定社会历史中,基于特定的经济形态和社会秩序的产物,所以正确的看待和评价中华传统文化必须在礼敬传统文化的前提下,以客观、科学的态度还原传统的时代语境和历史演进,使得传统文化成为一种富有历史性的“活”的存在,在历史性的基础上充分理解和还原其精神实质和丰富内涵。这种历史性是在唯物史观指导下,将传统文化的精神实质和价值内涵转化为精神文化资源,与当代文化接轨,与现代社会相适应,赋予其时代内涵。
中华传统文化现代转型的关键环节是正确处理文化资源与时代语境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需要历史和现实的逻辑连结而非一种机械套装,是根据现实需要,在恰切的契合点上将文化历史与现实语境进行深层的逻辑整合。在这一逻辑整合过程中,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思想成为基本方法论原则。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运用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辩证思维方法,这是一个从感性具体到思维具体的过程,也是马克思主义知识革命和知识生产的主要范式。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科学分析”、坚决拒绝的“绝对主义态度”等要求,事实上要求用辩证思维方法,即“辩证批判”和“抽象继承”,其解释性范式可以表达为“感性具体—抽象规定—思维具体”的基本形式。从本质上而言,“辩证批判”和“抽象继承”就是一种否定之否定的自我扬弃过程。作为逻辑起点的“辩证批判”是一种理性的否定,将丰富感性的传统文化作为感性具体材料进行逐级抽象,划清理论界限、思想源流、成立依据,批判内容是落后、封建、消极内容,中间环节是抽象出传统文化中带有普遍性、本质性、必然性的知识,继承的路径是抽象存在作为文化资源融入社会主义的实践,通过思维的具体再现,由此完成继承性与批判性的有机统一。
2 以传统文化内蕴的情感、信念与道德为纽带,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认同
传统文化内蕴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爱国主义情感、最坚定的经世济民的理想信念和日用不觉的道德规范体系。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目标与传统文化的上述内涵具有高度一致性,必须通过这一文化体系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价值认同。
(1)深沉的爱国主义情感。现代民族国家的爱国主义情感的建构必须建立在本民族文化的体系的基础上,才能够直击大众心灵,引发情感共鸣。爱国主义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这种爱国主义不同于西方个人与集体的二元对立思维模式,通过一系列伦理关系的整合实现个人与社会、国家甚至天下的紧密连接。这种伦理关系的主要内容是以“天下大同”为终极价值追求、以宗法血缘家庭为道德起点、以正心、诚意、格物、致知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主要路径、以自强不息和忧国忧民为精神品德。传统文化丰富的爱国主义内涵催生了深沉爱国主义情感,这种情感是从爱家为起点,扩展至家族、社会,最后落脚到民族和国家,层层递进、逐级升华。
(2)坚定的经世济民的理想信念。中华传统文化从诞生之初形成了超越个人私欲的功利观。《尚书·尧典》有云:“昔在帝尧,聪明文思,光宅天下。”此后,中国人生存之文明与政治框架就是作为一个超大规模的文明与政治共同体的天下,圣贤所思考者也是天下之优良治理[6]。圣贤所追寻、所探索的中国治理之道,从一开始就是普遍主义的天下治理之道。《尚书·尧典》中开篇即言:“百姓昭明,协和万邦。”尧开创了以亲睦、辩章、合和为纲的人间秩序。经过孔孟发展,至宋明理学后,一是“天下”突破地理和政治概念的界限,将“天下”观念的重点放在价值观念的构建上,并且将“天下”观念由政治意识向道德意识转化,通过礼乐文化的教化与道德引领来“永息战争之事”,实现王政王道;二是将个体的修养融入“公天下”的秩序体系中,实践理路沿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渐次展开。
(3)“日用而不觉”的道德规范体系。传统文化构成了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和精神家园,其重要体现在于建构了一套“日用而不觉”的道德规范体系,习近平总书记将其归纳为:“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精神特质和发展形态。作为一种伦理型文化,中华传统文化从发端起带有伦理道德的特质。先秦儒家以“仁”为核心,构建了以仁政爱民的民本思想、仁义礼智信的道德德目体系、“民胞物与”的天人道德关系、“内圣外王”的个体道德修养方法等一整套道德规范体系,为个人、社会和国家设计从上到下的道德秩序。
中华文明的深厚文化底蕴中内涵的爱国主义情感、价值体系、道德规范体系为我们提供了博大精深又灿烂丰富的文化资源,也提供了构建中华民族国家共同体的最好粘合剂。这种情感、道德、价值追求等传统文化中感性要素通过数千年血脉相连的代代相传下来,构成了中国人的精神家园,成为中国人身份确证的最有力证据。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必须建立这一环节至上,通过与这些感性因素高度融合,获得中国社会人民群众的普遍心理认同。但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传统文化的理论样态根植于前现代社会农耕经济基础、政治结构和社会秩序中,在将其融合现代社会土壤中时,必须以“双创”思想为价值遵循和方法论指导,既实现传统文化的现代化转型,又以此为纽带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认同。
3 以民族化、本土化表达为形式,实现马克思主义的话语体系创新
话语是语言符号与价值观念的整体呈现。作为政治符号的意识形态话语,马克思主义的叙事主体必须通过中国广大人民群众能够更容易认同、理解的外在形式表达出来,才能真正实现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话语体系的创新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客观要求,同时也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内在要求。马克思主义具有科学性、开放性和兼容性,其不断中国化的过程就是不断地与中国的具体实际情况相结合的过程,其中与中国文化传统的结合是马克思主义能够在中国得以生根传播的基础,也是马克思主义转化为中国文化的根本所在[7]。
(1)在表达方式上,充分关注、吸收具有民族特色、符合民族心理的话语表达方式,增加马克思主义理论话语的感染力、传播力。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构建的重要性,指出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扎扎实实做好中国事情,同时对内做好理论阐释,对外也要发出中国声音,讲好中国故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数千年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一套与中华民族思维习惯、社会心理高度契合的话语体系,可谓大道至简、意蕴深远、形象生动,兼顾阳春白雪与下里巴人的理论旨趣,善于用极为通俗易懂的语言阐释深刻悠远的道理。例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内外多个场合中均引用老子的“治大国如烹小鲜”来阐释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所秉持的辩证思维和态度。例如2015年,习近平总书记访问美国期间出席侨胞举行的欢迎招待会,正值中国传统中秋节前夕,他用“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这一俚语开场,顿时使得侨胞感受到总书记亲切问候、祖国的温暖,并以唐代著名诗人张九龄的“悠悠天宇旷,切切故乡情”[8]作为结尾,真情流露,感人至深。
(2)在表达内容上,马克思主义理论必须切实反映中国社会的现实需求,才能为中国广大人民群众广泛接受。在这一点上,中华传统文化话语表达具有无可比拟的优越性。以儒学为主干的传统文化尤其重视教化的作用,将意识形态、伦理道德与学术研究深度融合,放置于古代普通老百姓的生活世界中,通过“化民成俗”达到“风俗淳”,面向人民群众的生活和生产实践这是传统文化能够长期保存、发挥作用的关键因素。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充分吸收、借鉴传统文化话语体系的表达内容,深入浅出的解答广大人民群众的思想困惑,客观、真实的反映广大人民群众的实际需求,抓准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问题,才能真正“入耳”“入脑”“入心”“入实践”。
(3)在语境转换上,马克思主义必须运用科学的立场、方法论体系实现中华传统文化的叙事语境的转换。通过“辩证的批判”“抽象的继承”“语境再造”三个关键环节,这是一个否定之否定的扬弃过程。具体而言:首先,通过对纷繁复杂、丰富生动的传统文化进行理性的批判,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辨清源流、划清理论界限;其次,将传统文化中具有普遍意义、反映事物本质规定的内容抽象为思维具体价值追求、精神品格,对其加以继承;最后,运用马克思主义方法对其进行叙事语境再创造,将传统文化的思想精华从传统文本中提炼出来,结合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实践,植入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中。通过“语境再造”实现传统文化叙事语境的转换,使得传统文化顺利融入马克思主义理论中。习近平总书记用典集中体现了这一过程。例如习近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形成的“以人民为中心”和“人民至上”的理论就是对传统政治伦理学中“民为邦本”的民本思想的创新和转换。在庆祝澳门回归15周年庆祝大会讲话中,因为莲花是澳门特别行政区的区花,习近平总书记引用了颂莲千古名句“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8]来表达党和国家对澳门的高度关切,对澳门未来发展的“无穷碧”和“别样红”无限期许。
4 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的历史为依据,实现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认同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百年实践同时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的历史过程,并通过二者相结合的历史为依据,实现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实践认同。如何看待、评价中华传统文化始终是中国社会的重大问题,历史发展的各个阶段中国各阶层对此争论不休、莫衷一是。“理论在一个国家的实现程度,总是取决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9]。在中华民族百年复兴的伟大征程中,中国共产党根据世情、国情和党情的发展变化,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认识和评价也经历一个文化探索、文化自觉和文化创新的历史过程。
(1)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初步探索阶段。传统文化同马克思主义结合与中国社会政治变革历史、中国社会前途希望紧密相连。十九世纪六十至九十年代,地主阶级领导的洋务运动时期,中国社会广泛认同“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但甲午战争的惨败使得中国人认识到不光是器物,制度也需要改变。因此,以制度革新为目标的戊戌维新变法和辛亥革命相继爆发,但流血牺牲没有换来民族前途与光明,中国社会反而陷入了军阀混战割据的乱象中。此时,中国人又开始将变革的目标延伸至文化领域,由此掀起一场文化领域的革新——新文化运动。但中国人在学习西方民主、科学等思想的同时,出现了“西方文化优越论”“中华文化糟粕论”,甚至愈演愈烈出现了“人种优劣论”“文明等级论”等极端思想。另一方面,部分中国人为了捍卫中华传统文化,又陷入了“文化复古主义”“文化保守主义”的桎梏。对于传统文化的争论直至马克思主义传入后,在理论和实践中得到一步步澄清。中国共产党诞生后,传统文化发展进入历史新篇章。由于有了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指导、站在文明发展和国家复兴的历史高度,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张太雷等人就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提出了一分为二地看待传统文化,否定过去全盘西化或抱残守缺的理论主张,同时也注重学习欧美文化的先进之处,这与此前所有的思想主张具有本质的差别。总的来说,在国民大革命和土地革命期间,中国共产党本身处于幼年阶段,又受到共产国际的影响,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本本主义较为严重,对传统文化的态度和做法处在初步探索阶段。但这些宝贵的理论探索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积累了宝贵的历史经验。
(2)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文化自觉阶段。伴随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重大理论命题的提出,马克思主义理论真正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马克思主义开始以“民族形式”呈现,这其中内蕴着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逻辑理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发展的理论图景逐渐清晰。在不断斗争实践过程中,一方面使得中国共产党逐渐确立高度的马克思主义的文化自觉;另一方面,也使得马克思主义传播进入全新的大众化阶段,广泛在人民群众中生根发芽,扎根于普通群众中的思想。这一时期的文化自觉具体体现在毛泽东关于文化的一系列重要论断中,毛泽东认为,中国社会文化分为帝国主义侵略文化、封建文化和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文化,对待不同的传统文化要采取不同的策略和态度。毛泽东的这些重要观点和论断是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理论结晶,也是传统文化融入现代社会的指导思想和价值遵循,标志着中华民族的文化自觉。
(3)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文化创新阶段。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针对文化发展提出了“双百”方针和“二为”方向,为新中国的文化事业发展和繁荣提出了要求。经历“文化大革命”十年动荡,传统文化受到巨大冲击,与马克思相结合的进程停滞。伴随着改革开放的伟大历史转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重新走上历史舞台。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以其个人深厚的传统文化修养与底蕴、政治家的格局与智慧对中国传统文化提出创新型转化、创造性发展的“双创”方针,“双创”方针的提出,使得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不断深入,不仅推动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话语体系创新,还为其提供情感、信念和道德的价值引领,更重要的是在民族复兴的伟大实践中持续不断丰富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传播路径,包括物质载体、文明载体、精神呈现等路径全面铺展,使得社会大众在回溯、学习和重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同时,润物细无声的使得马克思主义科学立场、观点与方法论逻辑“飞入寻常百姓家”。这是从1840年以来,尤其是新文化运动以来,关于如何看待和评价中国传统文化的总的回答,是对传统文化的全新的历史定位,解决了困扰中国人一百多年来的重大理论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