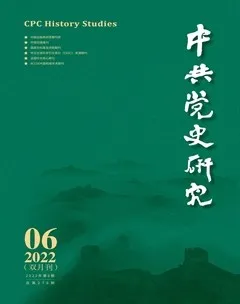新世纪以来当代中国外交史研究述评*
2022-02-27梁志
梁 志
无论从课题本身的重要性与复杂性来看,还是就史料来源的丰富性与多样性而言,当代中国外交史都是一个充满挑战却又令人着迷的研究领域。
当代中国外交大体上经历了革命外交和发展外交两个阶段,分界线基本可以划定在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在此期间,中国逐渐成为世界新秩序的参与者、维护者与建设者。受制于档案文献的解密时限,既有学术成果主要讨论了革命外交阶段的中国外交政策。这时的中国应该可以被认为是除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之外对冷战态势产生最重大影响的地区大国,“在冷战发展的一些关节点和关键问题上,中国甚至占据了中心地位”(1)陈兼:《关于中国和国际冷战史研究的若干问题》,《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第6期。。中国至少以三种方式在不同程度上塑造了两大阵营对抗与缓和的基本形态:一是调整对美、对苏外交战略,进而有意无意地改变东西方力量对比;二是参与局部战争(如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介入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纷争(如波匈事件)和第三世界危机(如老挝危机),以及参加国际会议(如日内瓦会议和万隆会议),在地区局势变动方面发挥作用;三是借助经济技术援助和文化艺术交流同美国或苏联展开“人心之争”,影响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或第三世界国家民族解放与发展道路的选择。反过来,与外部世界的交往也改变了中国自身的面貌,20世纪50年代学习苏联以及70年代从西方国家大规模引进先进工业设备与技术都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大约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随着西方主要国家和中国相关档案文献不断解密以及国际学术界新的研究方法陆续传入,中国学者有关当代中国外交史的讨论进入了以实证研究为主要特征的新阶段,冷战时期中国外交史研究逐渐发展成一门显学,并引起国际同行关注。鉴于此,本文拟从史料、理论与方法以及若干热点选题共八个方面观察21世纪以来的当代中国外交史研究(2)关于本文论述的范围,需作如下几点说明:第一,主要介绍利用中外各国档案文献进行的研究,兼及具有明显思想性、理论性或采用新颖视角的其他成果;第二,重点关注中国大陆学者在中国大陆范围内发表的学术成果,少部分涉及港澳台学者、海外华人学者的研究,以及中国大陆学者在海外发表的著作和论文;第三,为了行文方便,在“当代中国外交史”和“当代中国对外关系史”之间不作严格区分,尽管二者的学术内涵、关注范围和研究路径不尽相同;第四,文中的“外交”并非局限于传统意义上的、纯粹的国家行为(即所谓高端政治),还包括受到国家对外关系影响的下层跨国交往。,着重展现此项研究取得的进展、存在的缺憾和未来的发展前景。(3)关于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至90年代后半期当代中国外交史研究的基本状况,以及改革开放之后30年这一学术领域的进展和存在的问题,已有学者进行过总结。但总的来看,21世纪以来当代中国外交史研究呈现出来的新形态还有待观察和梳理。参见章百家:《中共对外政策和新中国外交史研究的起步与发展》,《当代中国史研究》2002年第5期;牛军:《三十年来当代中国外交研究》,《中共党史研究》2010年第7期;Xia, Yafeng (2007).“New Scholarship and Directions in the Study of the Diplomatic History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The Chinese Historical Review, 14(1), pp.114-140。
一、新史料的不断涌现
新世纪以来,中国学者之所以在当代中国外交史研究方面成绩不俗,最重要的前提是新史料不断涌现。
自2004年起,中国外交部档案馆接连公布了三批档案,档案自身形成时间分别为1945年至1955年、1956年至1960年以及1961年至1965年,总量超过8万卷。外交部解密档案内容十分丰富,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边界、人员交流、侨务等中国对外交往的主要领域。与此同时,外交部档案馆还编辑了三部档案集,主题分别为日内瓦会议、万隆会议与建交(4)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档案馆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档案选编》第1集,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档案馆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档案选编》第2集,世界知识出版社,200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档案馆、人民画报社编:《解密外交文献——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档案(1949—1955)》,中国画报出版社,2006年。。迄今为止,中国外交部档案馆馆藏档案仍旧是当代中国外交史研究者最常用的一手史料。还应该指出的是,除西藏、新疆等少数几个省区市外,大部分地方档案馆均对外开放。开放涉外档案数量和种类较多的是上海市、江苏省、福建省、河北省、陕西省、甘肃省、湖南省、湖北省、广东省档案馆以及台湾地区各档案收藏机构。这些文献也是研究当代中国外交史的宝贵资料,并已在一定程度上为研究者所利用。(5)参见姚百慧主编:《冷战史研究档案资源导论》,世界知识出版社,2019年,第323—362页。按:除了档案馆馆藏档案外,还有一些颇具研究和参考价值的内部资料,如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和外交部各自编辑了一套《毛泽东接见外宾谈话记录汇编》。
除了中国的档案文献外,西方主要国家官方资料的相继解密和公开也是当代中国外交史研究的重要前提和基础。从20世纪70年代后半期开始,美国、英国、法国和德国等西方国家陆续开始大体按照时间顺序公布有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原始档案,文件形成时间的下限已到80年代。这些国家对华关系档案文献解密和公开的程序较为规范,呈现形式多样(包括档案馆未刊档案、纸质档案文献集、电子数据库、缩微文献等),获取也相对容易。(6)参见姚百慧主编:《冷战史研究档案资源导论》,第1—150、206—303页。另一个令人振奋的变化是,苏东剧变后,苏东国家的官方档案大批量对社会开放,其中相当一部分涉及对华关系。虽说从苏东国家档案馆收集文献要付出较为高昂的费用,但毕竟还是为冷战时期中国外交史研究打开了一扇新的大门。而且,近年来上述国家出版了数量可观的涉及本国与中国关系的档案文献集,这些资料相对更容易获取(7)俄罗斯出版的中苏关系档案集主要包括:Мясников В.С.(под ред.) Китайская народная республика в 1950-е годы, Сборник документов, т.1, Взгляд советских и китайских ученых, Москва: Памятники исторической мысли, 2009; Мясников В.С.(под ред.) Китайская народная республика в 1950-е годы, Сборник документов, т.2, Друг с союзник нового Китая, Москва: Памятники исторической мысли, 2010; Ледовский А.М., Мировицкая Р.А., Мясников В.С.(сост.) 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в XX веке, 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 Том V, Совет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1946-февраль 1950, Книга 1: 1946-1948гг., Москва: Памятники исторической мысли, 2005; Ледовский А.М., Мировицкая Р.А., Мясников В.С.(сост.) 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в XX веке, 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 Том V, Совет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1946-февраль 1950, Книга 2: 1949-февраль 1950гг., Москва: Памятники исторической мысли, 2005; Ледовский А.М., Мировицкая Р.А.(сост.) 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в XX веке, 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 Том IV, Совет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1937-1945гг., Книга 2: 1945г., Москва: Памятники исторической мысли, 2000。俄罗斯、东欧档案解密情况,以及关于东欧国家与中国关系的档案文献集情况,参见姚百慧主编:《冷战史研究档案资源导论》,第151—205页;沈志华总主编:《东欧各国社会制度转型档案文献编目》,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总序”、第9卷“副篇三”。。总的来看,从事当代中国外交史研究的学者已经较为普遍地使用西方国家档案文献,但对苏联档案的利用仍不充分,对东欧国家档案的关注更是刚刚开始。
中国周边国家的档案文献同样是当代中国外交史研究不可或缺的史料。近些年,日本、韩国、蒙古、印度,以及缅甸、越南、老挝、柬埔寨、泰国、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国家均陆续解密和公布了大量档案文献,其中一部分涉及对华关系,档案形成时间的下限至少到20世纪60年代,有的下延到80年代甚至90年代上半期。上述国家中,日本和韩国的档案文献公布数量最多,管理最为规范,获取也最为便捷。(8)参见姚百慧主编:《冷战史研究档案资源导论》,第304—322、386—466页。但总的来看,对这些档案文献的利用基本上均处于初步阶段。
学者们在涉华外国档案的整理和研究方面作出了大量努力。相关文献集的面世为一些尚未掌握外国语言或暂时无法获取外国档案的研究者带来了便利,至少为他们进一步收集史料提供了线索(9)近20年,沈志华、陶文钊、牛军、张曙光、杨奎松、周建明和姚百慧等学者组织翻译并出版了一系列涉及冷战时期中国对外关系的外国档案文献集。参见沈志华执行总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34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沈志华主编:《朝鲜战争:俄国档案馆的解密文件》上、中、下册,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2003年;陶文钊主编:《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1—3卷,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2005年;张曙光、周建明编译:《中美“解冻”与台湾问题:尼克松外交文献选编》,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8年;沈志华、杨奎松主编:《美国对华情报解密档案(1948—1976)》(1—8),东方出版中心,2009年;沈志华编译:《俄国解密档案:新疆问题》,新疆人民出版社,2013年;沈志华主编:《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第1—12卷,东方出版中心,2015年;《中国与苏联关系文献汇编(1949年10月—1951年12月)》,世界知识出版社,2009年;《中国与苏联关系文献汇编(1952年—1955年)》,世界知识出版社,2015年;姚百慧编:《中法建交多国档案选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
2013年,华东师范大学周边国家研究院启动“冷战时期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和边疆问题”研究项目,并于2015年获得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特别委托项目资助。此项目的核心目标是广泛收集、整理和翻译周边国家对华关系档案,在双边甚至多边档案互证研究的基础上重新讨论冷战时期的中国外交政策。项目组多次赴美国、英国、俄罗斯、澳大利亚、日本、韩国、蒙古、缅甸、越南、老挝、柬埔寨、泰国、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国家的档案收藏机构调研和收集文献,已经编辑了100多卷的档案文献集。(10)该项目组成员在《中共党史研究》和《冷战国际史研究》上发表了一系列文章,介绍相关档案文献情况。
为了配合项目研究工作,2014年,华东师范大学—东方历史研究基金会当代文献史料中心成立,主要致力于冷战时期各国(包括中国)有关中国内政与外交的档案,特别是周边国家对华关系档案的整理、编目和数据库建设。东方历史研究基金会还联合几家国内高校举办了一系列以青年学者为主的研习营活动,加强其文献解读能力(11)2015年,东方历史研究基金会主办、华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承办了第一届“当代史:文献与方法”研习营,近30位研究生学员参加,10余位教授参与授课。第二届至第六届研习营由华东师范大学(2016年、2019年和2021年)、大连外国语大学(2017年)和广西民族大学(2018年)承办。。此外,出于逐步突破语言瓶颈的考虑,2017年至2018年,华东师范大学周边国家研究院开设俄语、越南语、缅甸语和泰国语集训班,数十位师生接受了培训。
二、新理论与新方法的陆续引入
严格意义上讲,对历史研究者来说,史料永远是不充分的。因此,如何驾驭和解读相对有限的文献资料并在可能的情况下进一步扩充史料来源,便成为历史学方法论的努力方向之一。作为历史学分支的当代中国外交史研究亦是如此。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那样,从事当代中国外交史研究不能仅仅依赖外交档案,不能在研究方法上因循守旧,而应当及时了解国际学术思潮,注重同其他学科之间的交流,采用跨学科研究方法(12)参见牛军:《当代中国外交史研究的几个问题》,《近现代国际关系史研究》第11辑,世界知识出版社,2017年,第2—24页。。事实确实如此,近些年相关领域的国际学术潮流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了当代中国外交史研究者开掘新史料、更新观察视角的出发点与依据(13)当然,多年前也有学者提出当代中国外交史研究的“本土化”问题,批评对西方流行的方法论和研究方法的盲目崇拜和教条主义运用。在笔者看来,这与重视国际学术思潮的主张并不矛盾,应该适当借鉴而非照搬照抄国际学术界提出的新理论和采用的新方法。参见肖佳灵:《当代中国外交研究“中国化”:问题与思考》,《国际观察》2008年第2期。。
作为当代中国外交史研究的重要参照物,美国外交史研究很早便开始自省。自20世纪60年代起,传统的美国外交史研究先后受到新社会史和新文化史等新兴学术思潮冲击。最终,“国际化”和“文化转向”成为其革新和再造的两个主要努力方向。长期以来,美国外交史研究单方面利用美国档案文献,有意无意地沿袭“美国中心论”视角,忽视他国对美国外交决策的制约和影响。与之相对应,“国际化”的主张则强调将美国外交决策置于全球环境中加以审视,采用多边视角,运用多国档案,着重揭示美国与其他国家交往的历史过程,而非片面地观察美国对外部世界的重塑和改造。部分地受到该主张影响,笔者近年来连续撰文呼吁当代中国外交史研究者采用“多国多边档案互证”研究方法(14)参见梁志:《当代中国外交史研究应当注重多国档案文献互证》,《中共党史研究》2019年第4期;梁志:《当代中国外交史研究如何利用多国档案文献》,《中共党史研究》2020年第4期。。所谓“文化转向”是指越来越多的美国外交史学者倾向于从文化的视角阐释美国对外关系,他们在很大程度上将国家间关系视为一种文化关系。具体的研究范畴和路径包括:信仰、情感、价值观、成见等因素如何塑造美国领导人的决策行为;美国如何在外部世界开展文化、宗教、教育等相关活动,其产品、思想和生活方式如何在海外传播;如何从普通大众的视角探寻美国外交政策背后的文化力量;如何阐释外交文献的语言和修辞、对外交决策进行话语分析;等等。(15)参见王立新:《试析全球化背景下美国外交史研究的国际化与文化转向》,《美国研究》2008年第1期;夏亚峰、栗广:《美国外交史研究现状》,《史学集刊》2015年第2期。与此相类似,已有中国学者指出,当代中国外交史研究应该重视对意识形态和思想观念的考察(16)参见牛军:《关于当代中国对外关系史研究的几点看法》,《中共党史研究》2019年第4期。。
前已述及,中国是东西方冷战时期国际格局的一个重要支点。从这个角度讲,完全可以将当代中国外交史研究划归冷战史研究领域。就研究方法而言,冷战结束以前,所谓冷战史研究“几乎完全以美国与西方国家的资料为依据,实际上往往只是美国外交史研究以及与之相关的美苏两大国关系研究的一部分,至多也只能说是美国对外关系史研究的一种延伸”。相应地,在观察视角、方法论和研究对象选择上,明显体现出“美国中心论”倾向,过分强调纯粹物质意义上的权力,且集中讨论高层政治。20世纪90年代上半期,美国著名冷战史专家约翰·加迪斯(John Gaddis)大力倡导开展“冷战史新研究”(The New Cold War History)或曰“冷战国际史研究”(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Studies),即在冷战结束赋予研究者的全新时空框架内,利用多国多边档案,挣脱“美国中心论”的羁绊,重点关注第二世界和第三世界,重新认识意识形态在冷战中的影响力。事实上,“冷战史新研究”之所以能够形成学术潮流,与中国学者特别是旅美中国学者所起到的推动作用是分不开的。(17)参见陈兼、余伟民:《“冷战史新研究”:源起、学术特征及其批判》,《历史研究》2003年第3期;戴超武:《“新冷战史”与当代美国外交史学思潮》,《美国研究》1999年第1期;曲升:《约翰·L.加迪斯冷战史研究的方法论转向》,《史学理论研究》2018年第2期。新世纪以来尤其是近十年来,国内从事冷战史研究的众多中青年学者进入当代中国外交史研究领域,并将“冷战史新研究”所提倡的视角与方法应用到了新的研究当中。
自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起,国际史学界开始在研究方法上强调“去国家化”,跨国史研究由此兴起。从事跨国史研究的学者主张超越民族国家的传统疆域界限,将其历史置于全球特别是跨国语境中加以理解和考察,重点关注非国家行为体、跨国人口流动、新兴交通和通讯工具、国际人权史、国际体育史,以及现代性观念跨国传播史等。跨国史研究试图“在别人身上看到我们自己”,即于国家疆界之外“发现”影响本国发展进程和人类命运的历史。极而言之,跨国史研究方法的出现和推广已经或将会改变许多国家“国史”研究的基本面貌,当代中国外交史亦在其列。(18)参见王立新:《在国家之外发现历史:美国史研究的国际化与跨国史的兴起》,《历史研究》2014年第1期;王立新:《跨国史的兴起与20世纪世界史的重新书写》,《世界历史》2016年第2期。或许正是在这一新的学术思潮促使下,已有中国学者倡导采用“跨国史”视角研究当代中国外交史(19)参见徐国琦:《从“跨国史”和“共有的历史”角度推进当代中国外交史研究》,《中共党史研究》2019年第4期。。
长期以来,当代中国外交史研究的学科归属问题始终困扰着国内学界。主流看法似乎认为它理应属于中国史研究,但以下现象也在引起越来越多的人注意:新世纪以来,很多原本从事国际关系史尤其是冷战史研究的中青年学者转而关注当代中国外交。过去他们致力于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利用的史料大多为外国档案,因此习惯性地将当代中国外交置于更为广阔的国际环境下加以考察,注重挖掘对象国的档案文献,在此基础上从双边乃至多边互动的视角诠释中国外交政策制定、执行、调整的背景、动因和影响,进而令当代中国外交史研究带上了某种“世界史”色彩。由此可见,将当代中国外交史研究划为中国史与世界史研究的交叉学科,或许更为妥当和符合实际。抑或说,应更为均衡和全面地看待影响当代中国外交走向的内外部因素。或许正因如此,新世纪以来,一批中国学者不失时机地引进、有意无意地借鉴了“复兴”和“再造”后的美国外交史研究、“冷战史新研究”、跨国史研究所倡导的史学理念,利用中外各国新近出现的档案文献,围绕中国在冷战中的地位、意识形态在冷战时期中国外交政策中扮演的角色、冷战政治对中国普通民众产生的影响,以及中外民众的跨国交往等问题展开了研究。
三、建交问题研究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不同时段、针对不同国家采取的建交方针存在明显差异。例如,有的经过了建交谈判,有的则没有;总体上坚持将与台湾断交作为与对方建交的前提,个别情况下也会变通处理。近年来,学者们选择典型案例,利用中国和建交对象国的档案文献对建交问题展开研究,不仅展现了大量被遮蔽的历史面相,更从多个侧面描绘了新中国的建交政策乃至其在不同时期的国际处境与对外战略。
缅甸是第一个承认新中国的非社会主义国家。范宏伟最早讨论了中缅建交问题,认为缅甸国内左派政治团体要求与新中国建交的呼声是吴努政府很快承认新中国的主要动因(20)参见范宏伟:《从外交部解密档案看建交初期(1949—1953)的中缅关系》,《云南社会科学》2008年第2期。。笔者则试图在补充利用缅甸、美国和印度等相关国家档案的基础上,挖掘缅甸承认新中国的内外部双重动力。该研究认为,缅甸承认新中国是对中共政权疑惧心理和英联邦国家态度影响共同作用的结果。前者决定了缅甸几乎从一开始便确定要承认新中国,后者则决定了直到新中国成立后两个半月,缅甸才真正付诸行动。在这两个半月里,吴努政府与有关国家沟通,最终确认英国、印度决心承认新中国,缅甸承认新中国不会使自己在国际社会陷入孤立,于是抢在印度前面成为第一个承认新中国的非社会主义国家,以博得这个“北方强邻”的好感。(21)参见梁志:《一九四九年至一九五三年的中缅关系再探讨》,《中共党史研究》2016年第5期。
印度尼西亚是第一个未经谈判而直接与新中国建交的非社会主义国家。张小欣较早关注中印尼建交问题,将其置于中—印尼—荷三方关系框架下加以阐释,认为新中国之所以同意不经谈判而与印尼建交,主要是因为与印尼总工会代表团进行了前期接触,且荷兰宣布与台湾断交(22)参见张小欣:《论中国与印度尼西亚建交》,《当代中国史研究》2011年第1期。。高艳杰秉持“国际史”研究方法,综合利用中国大陆、台湾地区和美国档案,得出如下新认识:在中国国民党撤守台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在中共和国民党之间选择哪一方,印尼政府有一个观望的过程;斯大林决定承认印尼是促使新中国不经谈判直接与印尼建交的重要原因之一;两国建交后的几年间,由于对新中国心存疑虑、对美国过度依赖,印尼刻意与新中国保持距离,双方关系处于一种“建而不交”的状态(23)参见高艳杰:《“建而不交”:冷战前期的中国与印尼关系(1949—1954)》,《世界历史》2018年第3期。。此项研究在东西方冷战和非殖民化运动等多重视角下,借助史料日渐丰富的有利条件,较为清晰地展现了中印尼双方在相互承认和建交问题上的多重考虑和复杂心态。
印度是第一个同新中国进行建交谈判的国家,也是资本主义国家中首个同新中国建交的国家。潘敬国的研究表明,协商建交事宜之初,中印双方领导人内心均存有疑虑。1950年1月下旬印度共和国成立和中苏条约谈判取得突破性进展推动了中印建交谈判进程。中印建交具有明显的象征性意义,新中国第一次实践先谈判后建交模式,并进一步明确了同台湾断交和支持新中国恢复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等基本谈判内容。(24)参见潘敬国:《中印建交与新中国外交抉择》,《当代中国史研究》2008年第1期。高国卫、高广景则着重展现了新中国成立初期印度政府内部在是否承认新中国与何时承认新中国问题上的明显分歧。他们认为,促使印度决定尽快承认新中国的主要推动力,是印美关系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和英联邦国家就早日承认新中国达成一致意见。反过来,在英国和印度之间,新中国选择优先处理与印度的建交问题。(25)参见高国卫、高广景:《中印建交的历史考察》,《党史研究与教学》2011年第3期。按:还有学者对中国与韩国建交的过程进行了探讨。篇幅所限,兹不详述。参见董洁:《中韩建交中的中国外交决策再探讨》,《中共党史研究》2019年第8期。
除周边国家外,与西方国家的建交问题也受到了学者们的关注。英国是第一个承认新中国的西方国家。也许正因如此,早在20世纪90年代就有学者利用英国档案考察了英国承认新中国的决策过程,包括其与西方国家和英联邦国家的磋商,以及内部讨论过程中反映出来的政治、经济和国际法等层面的考虑(26)参见金光耀:《1949—1950年英国对新中国的承认》,《历史研究》1994年第5期。。与此相对应,潘敬国展示了新中国对待英国承认问题的态度:将中苏新约谈判放在首位,不急于与英国建交;拒绝在与台湾完全断绝关系、新中国联合国代表权和国民党香港财产问题上作出实质性让步。这表明在建交顺序上,新中国采取了先苏联及东欧各国,再周边国家,最后考虑西方国家的方针。(27)参见潘敬国:《新中国成立之初中英建交谈判中的中方决策因素》,《中共党史研究》2006年第3期。徐友珍同时从中英双方切入,并把考察的时间下限延伸到1954年,将从1950年1月两国相互表达建交意愿到1954年6月宣布建立代办级外交关系的谈判作为一个整体加以观察。在她看来,中英能够在1954年建立代办级关系,主要基于以下原因:其一,国际局势缓和与新中国推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使毛泽东等领导人转而在中英建交谈判问题上采取灵活立场;其二,双方政府对此次谈判高度重视,英国外交大臣艾登与中国外长周恩来亲自指导谈判进程;其三,两国官方和民间多层次的接触对谈判取得进展起到了推动作用。从谈判的整个过程来看,新中国的态度经历了由恪守原则到灵活务实的变化,并始终主导着谈判的节奏和走向。(28)参见徐友珍:《走向半外交关系:1950—1954年的中英建交谈判》,《史学集刊》2013年第5期。
1964年,中法建交,此事被媒体喻为“外交核爆炸”,不仅提升了双方的国际地位,更对世界格局产生了深远影响。翟强阐述了中国领导人决定同法国建交的动机和考虑。他分析道,根据毛泽东提出的“两个中间地带”理论,为了利用美法矛盾,中国在与法国建交问题上采取灵活务实的态度,没有将法国和台湾断交作为与法国建交的前提。中国领导人并未将中法建交模式视为日后处理类似问题的样板,而是把相关经验仅仅当成一个特别案例。(29)参见翟强:《从隔阂到建交:一九四九年至一九六四年的中法关系》,《中共党史研究》2012年第8期。姚百慧针对中法建交问题进行了系列研究:首先,他将1963年法国前总理富尔访华作为观察中法建交动力的切入点,强调此次访华是中国在“第二中间地带”理论指导下对欧战略、对法政策调整的结果,认为中法双方在追求独立自主外交、冲击美苏两极格局方面的一致诉求对两国最终建交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30)参见姚百慧:《中国对法政策调整与富尔一九六三年中国之行》,《中共党史研究》2014年第5期。。其次,他更为细致地考察了作为中法建交方案的《周恩来总理谈话要点》(主要内容为两国关于台湾问题的“三项默契”)的形成过程,认为该文件是双方平等协商的结果,直接推动中法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但在台湾地位和法台可能保持“领事”关系两个问题上,两国并未达成一致。(31)参见姚百慧:《中法建交谈判中关于台湾问题的“三项默契”——〈周恩来总理谈话要点〉形成考释》,《当代中国史研究》2012年第2期。再次,他利用台湾地区档案并辅之以法国、美国和中国等多边档案,在“国际史”的视野下,将讨论主题扩大到中法建交前后的台法交涉,展现了台湾当局对台法关系走向的误判及其影响(32)参见姚百慧:《中法建交与台法交涉——基于台湾档案的考察》,《中共党史研究》2016年第1期。。
1979年中美建交是中国调整中美苏三边关系、改善外部环境的重大外交举措。虽然有关中美建交的中方档案尚未解密,但美方的一手文献已经大量公开,学者们根据这些新史料展开了研究。中美建交的动力来自苏联的战略威胁和双方的经济需求,学界对此大致持相同看法。但在1977年美国国务卿万斯访华的成效问题上,学者们之间看法各异。董振瑞认为此次访问“很不成功”,因为双方在台湾问题上没有达成任何协议(33)参见董振瑞:《邓小平与卡特时期的中美外交博弈》,《党的文献》2012年第3期。。韩长青和吴文成则判断说,万斯访华虽然并未取得立竿见影的效果,但作为一次战略试探,可以说卓有成效:初步了解了对方的利益关切(如对苏联安全威胁的共同认知)和利益冲突(主要表现在台湾问题上);建立起两国新领导人之间的高层联系渠道;彼此表达了推动中美两国最终实现关系正常化的愿景(34)参见韩长青、吴文成:《外交承诺与战略试探:万斯访华与中美关系正常化》,《外交评论》2014年第6期。按:还有学者讨论了中国与瑞士建交问题。参见姚百慧:《从公使到大使:中瑞外交关系的建立与发展》,《当代中国史研究》2016年第5期。。此外,有学者还原了1978年12月邓小平与美国驻华联络处主任伍德科克四次建交会谈的历史过程,澄清了中美建交公报中加入“反霸”条款、中方同意美方“终止”而非“废除”“美台共同防御条约”,以及双方暂时搁置美国对台军售争议等问题的谈判经过(35)参见薛鹏程:《邓小平与中美建交最后阶段的谈判》,《上海党史与党建》2019年第9期。。
总体上看,虽然由于受到各种条件限制,大多数研究者还未能使用三国或三国以上档案对中国与其他国家建交问题进行讨论,但他们普遍采用了“国际史”的观察视角,力求将建交这一双边关系问题放置在多边关系的网状结构中加以认识。在此基础上,研究者们揭示了影响中国处理与周边国家、西方国家之间建交问题的各种内外部因素,展现了中国在不同时段、对待不同国家的政策差异。
四、陆地边界问题研究
中国是世界上陆地边界线最长的国家(长达2.2万余公里),也是陆地邻国最多的国家(新中国成立初期,与之接壤的国家有12个)。20世纪50年代后半期开始,中国逐步放弃“暂维现状”的方针,以缅甸为突破点,启动与周边国家的谈判,陆续同多个接壤国划定了陆地边界。新世纪以来,随着中国外交部档案的解密和各地方特别是边疆地区档案馆相关文献的开放,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处理陆地边界冲突和划界问题逐步进入学者们的考察范围。
沈志华从总体上讨论了中国解决陆地边界纠纷的方针。他认为,在两大阵营对抗的冷战背景下,中国解决陆地边界问题的出发点是突破帝国主义的封锁和包围、缓和与周边邻国的紧张关系。这不仅促使中国在谈判中作出让步,而且影响了对解决边界问题的方针原则的贯彻。(36)参见沈志华:《冷战年代中国处理陆地边界纠纷的方针》,《二十一世纪》2014年6月号。此项研究为后来诸多个案研究提供了较为坚实的基础。
中缅边界是新中国成立后划定的第一条陆地边界,因此成为学者们关注的焦点。从还原史实的角度来看,冯越依据中国外交部档案和中国领导人公开文献所进行的历史叙述最为详尽(37)参见冯越:《中缅边界问题解决的历史过程(1954—1961)》,《南洋问题研究》2014年第3期。。对于中国解决中缅边界问题的评价,研究者们看法不一。齐鹏飞、张明霞等学者认为,中缅边界的划定确立了一个“率先垂范”的成功样板,开创了中缅睦邻友好关系的新历史,树立了中国负责任的地区大国形象,使和平共处五项原则逐渐成为国际关系准则,并留下了很多宝贵历史经验(38)参见齐鹏飞、张明霞:《中缅边界谈判的历程及其基本经验》,《中共党史研究》2012年第1期;冯越、齐鹏飞:《中缅边界谈判述略》,《湖南科技大学学报》2006年第6期。。范宏伟分析道,中缅边界问题的解决推动了双方互信关系的发展,促成了两国对逃缅国民党军的联合作战行动。但他同时指出,划定边界对中缅关系而言不具有转折性意义,更不能认为该问题的解决改善了中国外交格局或者促使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成为处理国际关系的指导原则。(39)参见范宏伟:《中缅边界问题的解决:过程与影响》,《南洋问题研究》2010年第3期。还有学者考察了印度对中缅边界谈判施加的影响。戴超武的研究表明,为了确认中印边界东段“麦克马洪线”的“合法性”,进而将缅甸牢牢纳入印度的势力范围,印度总理尼赫鲁对中缅边界问题采取了积极干预的政策,为缅甸提供相关文献资料,支持缅甸的边界主张,并向其通报同中国领导人商谈边界问题的情报(40)参见戴超武:《中缅边界问题与尼赫鲁的干预及其战略意图(1956—1960)》,《中共党史研究》2016年第11期。。关培凤则从另外一个角度判断说,1959年先后在中印边境发生的朗久事件和空喀山口事件促使中国加快解决中缅边界问题的步伐。相反,缅甸希望利用中印边界冲突向中国施压,并尽可能照顾印方感受,转而在中缅划界一事上表现出消极态度。(41)参见关培凤:《1959年中印边界冲突对中缅边界谈判的影响》,《当代中国史研究》2014年第1期。
无论是从1959年中印边界冲突和1962年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还是从中印边界至今仍未划定的现实考虑,学者们都有充足的理由将中印边界问题作为重点研究对象。在相关成果中,戴超武依据中印双边档案进行的研究最具代表性,其中几项关键结论特别值得关注:其一,19世纪80年代至20世纪50年代,中国地图中印边界画法的演变凸显了中国中央政府对边疆地区认识和管辖能力的加强,显示出中国的边界主张具有基于传统习惯的历史权利的突出特点。印度地图画法的变化则是英国和英印政府在测绘、考察基础上在印度周边地区推行“前进政策”、实施“战略边界”政策的结果。(42)参见戴超武:《中国和印度有关地图边界画法的交涉及其意义(1950—1962)》,《中共党史研究》2017年第5期。其二,1953年10月,中共中央驻藏代表张经武在发给外交部的题为《关于中印在西藏关系之诸问题》的电报中,建议中央在中印有关西藏问题的谈判中首先解决同印度的边界问题,但中央并未接受这一建议。这体现了中国“暂维现状”的政策。相应地,中国对印度占领“麦克马洪线”以南地区采取了忍让克制的态度。(43)参见戴超武:《中央驻藏代表张经武1953年10月21日电报探析——兼论中国处理边界问题的“暂维现状”政策及其影响》,《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15年第5期;戴超武:《中国对印度占领“麦克马洪线”以南地区的反应及其意义(1951—1954)》,《中共党史研究》2014年第12期;戴超武:《中国对印度占领“麦克马洪线”以南地区的反应及其意义(1951—1954)(续)》,《中共党史研究》2015年第1期。其三,中国在处理1962年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印度战俘事宜时,进行了较为精心的准备和安排,保证了印俘的基本需求,并最大限度满足了印度在接运战俘时提出的要求。在教育印度战俘、处理同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特别是印度红十字会的关系等问题上,中国的政策尚存在一些值得探讨的地方。(44)参见戴超武:《中国对印度战俘的处理与中印交涉(1962—1963)——基于中国外交部档案的考察》,《冷战国际史研究》第15辑,世界知识出版社,2013年,第43—91页。
另一个受到关注的议题是中苏边界问题,它的特点是边界线长、领土“旧账”多且曾引发军事冲突。早在20世纪90年代,学者们就已开始讨论1969年中苏边界冲突。李丹慧的研究表明,珍宝岛冲突绝非孤立事件,而是中苏边界长期冲突的继续、中国对苏联不断挑衅的反击,并促使毛泽东决定打破对美关系僵局(45)参见李丹慧:《1969年中苏边界冲突:缘起和结果》,《当代中国史研究》1996年第3期。。牛军进一步指出,中国决策层对中苏边界冲突的判断经历了一个从认为是偶发事件,到断定苏联有可能发动大规模侵华战争进而全面备战的变化过程,但并没有证据显示中国领导人有意识地利用此次事件为调整中美关系服务(46)参见牛军:《1969年中苏边界冲突与中国外交战略的调整》,《当代中国史研究》1999年第1期。。
新世纪以来,李丹慧转而对中苏边界问题进行全景式的观察和思考。她认为,20世纪50年代,在“同志加兄弟”的两党和两国关系影响下,中苏边界成为双方共同的边界,苏联承担着保卫中国边界的责任。60年代,随着两党两国关系日渐恶化,中苏之间的界务纠纷逐渐政治化。在此过程中,中国主动出击,从意识形态斗争需要出发,公开提出中苏之间存在不平等条约问题,苏联被迫作出回应。相反,面对1969年边界冲突,苏方步步紧逼,中方则只能被动应付。这一切都从侧面显示,60年代中国对外政策整体上在向“左”转。(47)参见李丹慧:《同志加兄弟:1950年代中苏边界关系——对中苏边界问题的历史考察(之一)》,《国际冷战史研究》第1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71—102页;李丹慧:《政治斗士与敌手:1960年代中苏边界关系——对中苏边界问题的历史考察之二》,《社会科学》2007年第2期。按:还有学者讨论了中国与朝鲜之间的陆地边界问题。参见沈志华:《最后的“天朝”:毛泽东、金日成与中朝关系》,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521—550页。
严格来说,上述研究都是个人努力;与之相对应的是,已有学者在陆地边界问题上展开了集体探索。2017年,华东师范大学承担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特别委托项目“中国周边国家对华关系档案收集及历史研究”第二期中,就包含了一个涉及中国处理陆地边界问题的子项目。这应该是学界第一次针对该问题进行全面的实证研究。
综上所述,在陆地边界问题上,学者们既进行了总体上的探讨,又进行了多项个案研究,既有个人努力,也有集体协作。在研究视角的择取方面,大多没有就边界谈边界,而是将陆地边界冲突和划界问题置于双方关系乃至多边关系的场景下加以体认。就史料来源来看,多数研究者能够尽可能地利用中国外交部档案和中国领导人公开文献,并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采用双边乃至多边档案互证的研究方法,参考中国外交对象国和第三方的一手史料。
五、经济援助、贸易往来与技术合作问题研究
新中国成立伊始,国内百废待兴,国外又面对美国等西方国家的贸易管制和禁运,但中国依旧积极进行易货贸易,向社会主义国家和新兴民族独立国家提供经济援助,并在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寻求技术合作。20世纪70年代以后,随着中美关系逐步解冻和改革开放渐次展开,中国的对外经济技术联系更加频繁,范围也更加广泛。新世纪以来,学者们在对外经济援助、贸易往来和技术合作等方面进行了大量个案研究。
针对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援助,学者们主要讨论了朝鲜和越南两个案例,从不同角度展现了中国对外援助政策服从于总体对外战略这一显著特点。沈志华和董洁考察了朝鲜战争结束后中国对朝鲜的经济援助。他们认为,中国是推动朝鲜战后重建的重要外部力量,援助金额一度超过了苏联和东欧国家的总和。(48)参见沈志华、董洁:《朝鲜战后重建与中国的经济援助(1954—1960)》,《中共党史研究》2011年第3期。董洁还在中苏朝三边关系变动的视角下,分析了20世纪60年代上半期中国对朝鲜的经济援助问题。在她看来,面对中苏分裂局面,为了争取朝鲜的支持,中国对朝鲜的经济援助政策呈现出两大特征:一是尽己所能,甚至超出合理负担范围;二是“只算政治账,不算经济账”。但从援助效果来看,中国大量的经济援助并未改变朝鲜的经济结构,在政治影响力方面的效果也很有限。(49)参见董洁:《中苏分裂后中国对朝鲜的经济援助(1961—1965)》,《外交评论》2014年第4期。
张勉励讨论了20世纪50年代中国对越南的援助政策。她的研究表明,这一时期中国对越援助历经了由军事援助为主向经济技术援助为主、由党际援助为主向政府间合作为主的转型。(50)参见张勉励:《中国对越南经济技术援助的历史起步》,《外交评论》2010年第5期。邵笑将中国对外战略由“反美反苏”转变为“联美反苏”作为大背景,论述了越南战争期间中国对越南的援助政策。他的讨论显示,中国对越南的经济援助数量呈现增长—缩减—再增长—再缩减的态势,其间出现了1965年、1967年、1972年与1974年四个高峰。总的来看,在推动双边关系层面上,中国经济援助的效果并不理想,双方互有不满。(51)参见邵笑:《越南战争期间中国对越援助与援越政策研究(1964—1975)》,《冷战国际史研究》第25辑,世界知识出版社,2018年,第53—86页。范丽萍另辟蹊径,利用广西地方档案探讨了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中越铁路联运这个以往极少受到关注的问题。她得出的结论是:中越铁路国际联运不仅与“胡志明小道”一起构成了越南获得战争最后胜利的后勤保障体系,而且为广西的经济增长乃至经济重心转移注入了动力。(52)参见范丽萍:《冷战与地方社会:1955—1978年五国铁路国际联运中的广西》,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此项研究致力于挖掘地方文献,从“地方视角”观察中国对外经济援助政策,颇具新意。
亚非地区非社会主义国家也是中国对外经济援助的对象。其中,柬埔寨是新中国提供经济技术援助的第一个民族独立国家。张勉励指出,中国对柬埔寨的援助从1956年到1970年持续14年之久,总体上看取得了积极成果,包括推动两国建交并促进双方友好关系发展,加速了柬埔寨民族工业的成长,有助于中国在印度支那地区战略目标的实现(53)参见张勉励:《中国对柬埔寨经济技术援助的历史探析(1956—1970)》,《中国浦东干部学院学报》2014年第1期。。李一平、曾雨棱分析道,1958年至1965年,中国对印尼的援助情况同两国友好关系的发展进程并不完全同步,主要原因是中国在援助印尼的外交决策中将“革命”作为首要评判标准。印尼政府是否革命或者说是否有利于革命力量的发展,对中国援助印尼的态度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54)参见李一平、曾雨棱:《1958—1965年中国对印尼的援助》,《南洋问题研究》2012年第3期。周振在中国—尼泊尔—印度三边关系的图景下探讨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对尼泊尔的经济援助政策。此项研究表明,印度始终是影响中国对尼泊尔援助数量和力度的重要因素,中国对尼泊尔的援助是助推两国友好关系平稳发展的动力之一。(55)参见周振:《20世纪50—60年代新中国对尼泊尔援助问题探究》,《当代中国史研究》2017年第5期。
在中国对非洲经济援助的问题上,蒋华杰的研究最为引人注目。他从中国援建坦赞铁路、顶替台湾在非“农耕队”、培训非洲实习生和留学生等多个个案入手,详细考察了1960年至1983年中国对非洲国家的援助政策。此项研究不仅体现了其他研究者着重揭示的中国对外援助政策的意识形态特征,还展示了社会制度移植和跨文化碰撞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他认为,中国对非援助行为与通常所定义的发展援助有很大区别。对非援助行为不仅是中国组建国际反帝反修统一战线的政策工具,还体现出输出自身经济社会发展道路这一典型的意识形态特征。中国的经验之所以并未被非洲国家接受,背后的原因是复杂的,既有政治、国际关系因素造成的阻碍,也有社会制度、种族、文化差异带来的挑战。随着走向改革开放,中国对非援助政策逐渐由“援助换政治”向“援助推发展”转型,其重心由实现革命外交转变为同时追求现代化发展与国家安全战略两大目标。(56)参见蒋华杰:《冷战时期中国对非洲国家的援助研究(1960—1978)》,博士学位论文,华东师范大学,2014年;蒋华杰:《现代化、国家安全与对外援助——中国援非政策演变再思考(1970—1983)》,《外交评论》2019年第6期。
在与社会主义国家的贸易关系方面,学者们进行了初步探讨。与过去学界着力突出苏联援助中国不同,姚昱关于中苏橡胶贸易的研究另辟蹊径(57)这里所说的橡胶贸易有两层含义:一是中国帮助苏联从东南亚地区大量代购橡胶;二是中国在华南地区帮助苏联种植橡胶。,凸显了中方对苏方的“反向援助”。他的研究证明,虽然中国的对外经济政策具有主动性和灵活性,但其相对有限的经济资源与苏联庞大的刚性需求之间存在着难以解决的矛盾,这导致中苏橡胶贸易合作时间早、规模大、内容广,但又结束得非常迅速。(58)参见姚昱:《橡胶合作:中苏经济关系的个案研究》,沈志华、李滨(Douglas A.Stiffler)主编:《脆弱的联盟:冷战与中苏关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第168—205页;姚昱:《20世纪50年代初的中苏橡胶贸易》,《史学月刊》2010年第10期;姚昱:《新中国华南橡胶垦殖中的科技争论》,《中国科技史杂志》2011年第1期。葛君的研究展现出20世纪50年代上半期中国与民主德国贸易关系的特殊性,即民主德国在中国与联邦德国的贸易关系中扮演着代表中国的代理人角色。他认为,隐藏在这一现象背后的是民主德国谋求德国唯一代表身份和主导德国统一进程的深层政治考量。相应地,中国也从支持民主德国统一社会党政权稳定的角度出发,在双边贸易中给予对方特殊待遇。(59)参见葛君:《试论新中国与民主德国的早期贸易关系(1950—1955)》,《中共党史研究》2016年第11期。金泉对中蒙贸易关系的研究揭示了社会主义国家间关系“政经分离”的一面。他认为,由于边境线漫长、彼此经济需求明显、经济结构互补性强等原因,中蒙贸易在双方政治关系敌对时期仍呈现出“藕断丝连”的状态,为之后的“触底反弹”预留了足够的回旋空间。(60)参见金泉:《“政经分离”:冷战时期中蒙贸易关系历史考察》,《冷战国际史研究》第21辑,世界知识出版社,2016年,第233—252页。白林的研究更为细致,专注于考察1949年至1955年中蒙贸易关系的确立与初步发展,落脚点是内外部影响因素孰轻孰重。在他看来,这一时期中蒙贸易关系的变化主要受到朝鲜战争和中苏对外政策调整等外部因素影响。(61)参见白林:《中蒙贸易关系的建立和初步发展(1949—1955)》,《中共党史研究》2020年第3期。
在与西方国家的贸易关系方面,研究成果相对比较丰富。以往学界对于中国冲破美国等西方国家对华贸易管制的手段很少关注,而张夏婷的研究恰恰是这样一个选题。她利用广东地方档案讨论了新中国成立之初与资本主义国家进行的易货贸易问题。在她看来,此举有助于打破西方的经济封锁,获得了大量国家建设所需生产物资,但也暴露出处理危机时缺乏计划性、各地方之间缺乏联系,以及干部思想和业务水平有待提高等问题。(62)参见张夏婷:《中国对资本主义国家的易货贸易研究(1950—1952)——以华南区为例》,《中共党史研究》2015年第5期。高嘉懿考察了20世纪50年代后半期中法之间就互派商务代表而进行的外交磋商。她比较了中国在设立商务代表处问题上对待埃及的积极态度和面对法国时相对消极的态度,认为此时在中国的对外战略中,法国处于“中间地带”和“敌对阵营”之间的“灰色地带”。(63)参见高嘉懿:《一九五五年至一九五七年中法围绕商务代表问题的外交互动探析》,《中共党史研究》2017年第8期。葛君和王若茜分别探讨了20世纪60年代联邦德国和意大利寻求加强与中国商贸往来的问题。虽然就结局而言,一个失败一个成功,但两个案例从不同侧面说明,毛泽东提出“第二中间地带”理论并非意在改善与西欧国家的关系,而是要利用它们与美国的矛盾达到反帝的目标。(64)参见葛君:《“第二中间地带”策略与1964年伯尔尼接触》,《中国社会科学内部文稿》2013年第4期;王若茜:《中国外交在“第二中间地带”的成功实践——对1964年中意互设商务代表处的历史考察》,《党的文献》2012年第5期。20世纪70年代前期的中美贸易关系对实行改革开放产生了巨大影响。戴超武认为,美国“贸易自由化”政策开启了中国从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大量引进先进技术设备的历史进程,这为改革开放奠定了政策、技术和物质基础(65)参见戴超武:《美国“贸易自由化”政策与中国“改革开放”(1969—1975)》,《史学月刊》2010年第2期。。邓峥云则更多地从相互认知差异的角度来看待这一时期的中美贸易关系,着重阐释中国对尼克松政府“中国许可证清单”出台的冷淡反应以及双方关于中国对美纺织品出口配额问题的交涉(66)参见邓峥云:《尼克松政府“中国许可证清单”的出台与中国的反应》,《世界历史》2016年第4期;邓峥云:《多面互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美关于纺织品问题的交涉》,《中共党史研究》2017年第3期。按:学者们还讨论了20世纪60年代初中国与加拿大的粮食贸易问题。参见李瑞居:《迪芬贝克时期加拿大与中国小麦贸易探析(1957—1963)——基于对加拿大政府解密档案的解读》,《冷战国际史研究》第24辑,世界知识出版社,2017年,第155—177页;瞿商、许天成:《1960年秋至1961年5月中国自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的粮食进口》,《当代中国史研究》2017年第4期。。
研究者们还就对外技术合作相关问题展开了讨论。董志凯这样概括中国科技发展的特点:在自力更生的方针下引进吸收,在消化吸收的基础上有所创新,形成工业经济的完整体系(或产业链)(67)参见董志凯:《自力更生与引进、消化相辅相成——1949—1978年中国科技发展回顾与启示》,《当代中国史研究》2019年第5期。。具体到从苏联引进技术,张柏春等人认为,1949年至1966年苏联向中国转移技术的行为主体是政府,形式包括技术输出、技术贸易、技术援助和技术合作,技术本身是混合式的,大多数属于中间技术,但也包含先进技术、尖端技术以及较为落后的技术。这是中国历史上首次比较系统、完整且效果较好的一次技术转移,推动了现代技术在中国的体制化以及技术科学在中国的发展,但在一定程度上也使得中国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长期吃苏联技术的老本。(68)参见张柏春等:《苏联技术向中国的转移(1949—1966)》,山东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401—415页。
在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技术合作时,中国基本上扮演的是技术输出的角色。王勇忠以中国科学院为研究对象,考察了中国与古巴、朝鲜、越南的技术合作,并得出如下结论:中古两国科学院的农业技术合作虽然受到两国关系波动影响,却从未中断;中国科学院和朝鲜科学院的技术合作则受两国关系影响较大,双方运行体制的不同也明显阻碍了合作的深入进行;受制于越南战争和越南国内科学水平,中国科学院与越方的科技合作以人员往来为主,在科研项目和科研仪器方面的支援很少(69)参见王勇忠:《1963—1969年中古两国科学院的科技合作》,《当代中国史研究》2015年第1期;王勇忠:《中朝两国科学院的科技合作(1953—1976)》,《冷战国际史研究》第25辑,第109—126页;王勇忠:《中国与越南的科学技术合作(1964—1976年)——以中国科学院开展与越南科学技术合作为中心的研究》,《东南亚纵横》2018年第6期。。董洁也讨论了中朝技术合作问题,切入点是朝鲜技术考察团。同样是个案研究,相较而言,此项研究更具理论张力。董洁认为,中国开展对朝科技合作的原动力在于政治,这是一种争取政治盟友的重要方式,中朝科技合作与中朝政治关系因此呈现正相关关系。正因为在两国技术合作过程中,政治属性被过度强化、技术本位相对缺失,合作的效果大打折扣。(70)参见董洁:《解读中朝科技合作——以朝鲜技术考察团为中心》,《冷战国际史研究》第28辑,世界知识出版社,2019年,第79—92页。
20世纪60年代初,由于中苏关系恶化,苏联停止了对中国成套技术设备的供应,中国转而致力于与西方国家展开合作。牛建立指出,从西方国家引进成套技术设备推动了中国的科技进步,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国民经济发展中的关键问题,为20世纪70年代初扩大对外引进规模和以后的对外开放创造了条件,并在某种意义上为中国与西方国家建交奠定了基础(71)参见牛建立:《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前期中国从西方国家引进成套技术设备研究》,《中共党史研究》2016年第7期。。周磊选择的切入点更为微观,考察了20世纪70年代初“四三方案”期间中国大规模进口法国工业技术和成套设备的情况。他断言,这次技术引进是冷战时期中法经济关系中的里程碑事件,不仅促进了中国工业薄弱部门的发展,而且重振了低迷的中法贸易,对此后的中法经济关系和中国改革开放亦产生了积极影响。(72)参见周磊:《冷战时期中法经济关系发展的里程碑——“四三方案”期间中国大规模进口法国工业技术和成套设备情况》,《中共党史研究》2017年第1期。与20世纪六七十年代相比,80年代中国的技术引进更具开放性。陈弢选择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至90年代初期的桑塔纳轿车国产化问题作为研究对象,揭示出大众集团、中国中央政府、上海地方政府三者之间的复杂互动和各自考量,展现了中国经济如何通过此次具有代表性的技术引进工程,进一步加入全球生产和交换网络之中(73)参见陈弢:《中德有关桑塔纳轿车国产化问题的协商及其影响(1985—1991)》,《中共党史研究》2022年第2期。。
简言之,新世纪以来,学界关于中国对外经济技术联系的研究已遍布各相关领域,且普遍利用了中国外交部档案,必要时还参考了各省市地方档案和美国、英国、法国、德国等对象国档案。这些研究成果在很大程度上展现了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中国对外援助、经贸往来和技术合作的宏观走向。在一些具体的案例研究中,学者们还对有关对外经济技术联系的成效作出了研判,总结了经验教训。不过,相对于建交和边界问题,这一研究领域还未呈现出学术争鸣的态势。
六、文化交流问题研究
当代中国外交史研究并非仅仅依据一手文献讨论“高政治议题”或进行纯粹意义上的官方对外政策考察。新世纪以来,一些学者开始转换视角,探索新的学术路径,尝试超越外交史的学科传统,从跨文化交流层面阐释中国与外部世界的互动。当然,此种“文化转向”只是初露端倪,从成果呈现和领域分布上看还显得较为零散、不成系统,主要体现在电影、美术、体育、建筑、国际博览会等几个方面,种族、性别等更具理论挑战的课题则很少涉及。
学者们已经注意到了新中国成立之初对待美国文化和苏联文化态度的巨大反差。杨奎松从宗教、教育、广播和电影四个方面展现了中国利用美国实施封锁这一契机清除其在华文化影响力,进而消除民众“亲美”“崇美”“恐美”思想的历史过程。与一般意义上的认知和判断不同,他认为,新政权本想利用五至十年的时间进行社会改造和文化统合,但朝鲜战争爆发与美国加强对华遏制政策迫使中国领导人不得不采取肃清美国文化影响的举措。(74)参见杨奎松:《新中国成立初期清除美国文化影响的经过》,《中共党史研究》2010年第10期。储著武对1949年至1956年中国学习苏联文化的历程进行了解读,将其划分为初步学习、全面学习和反思学习三个阶段,揭示了其中的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倾向(75)参见储著武:《文化范例:新中国学习苏联文化及文化建设经验的发展历程(1949—1956)》,《河北师范大学学报》2018年第1期。。
电影是中外文化交流的主要形式之一。王宇平的研究展示了20世纪50年代后半期中国对外电影交流背后存在的商业利益考量。她指出,1956年至1957年,在“双百”方针指导下,中国一改之前几乎只参与社会主义电影或进步电影内部活动的局面,积极参加包括戛纳电影节在内的各类国际电影节。这背后固然隐藏着意识形态和政治宣传的考虑,但更多的是希望借助电影节构筑的市场平台促进影片对外输出。(76)参见王宇平:《20世纪50年代新中国电影与国际电影节》,《文艺研究》2016年第5期。王玉良则专注于讨论1945年至1950年美国电影在中国的际遇。他认为,在此期间,中国对好莱坞电影的批评历经了“个体式”“集体式”“全国性”三种模式,始终受到政治意识形态深刻影响。1950年以后,中国大力宣传苏联、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的影片,逐渐使之成为一种风尚,并在创作上为接下来的“十七年电影”指出了不同于西方电影的另一种方向(77)“十七年电影”,指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前中国大陆的电影。。但另一方面,美国电影在中国并没有销声匿迹,而是偶尔仍会作为学习或批判的样本,在一定范围内放映。(78)参见王玉良:《“清算”好莱坞:论战后中国对美国电影的批评模式(1945—1950)》,《文化艺术研究》2016年第2期。与这一判断相呼应,柳迪善指出,长达30年的美国电影禁令从未完全擦除中国普通观众对好莱坞的记忆,这构成了民间力量的一次“胁迫性挽留”。1979年之后,中国开始采购美国影片。不过,在经济落后和意识形态制约的共同作用下,能够进入中国的美国影片依然有限,且多为二流作品。(79)参见柳迪善:《美国电影在民间中国(1949—1980)》,《北京电影学院学报》2019年第2期。这两项研究反映了美国电影在中国长时间的“隐性”存在。王瑞芳将视线转向苏联电影,梳理了20世纪50年代中国政府甄选、放映苏联电影,以及中国观众观看苏联电影的历史脉络。她的研究表明,苏联电影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思想教育与文化娱乐的双重功能。(80)参见王瑞芳:《寓教于乐:20世纪50年代苏联电影对中国民众生活的影响》,《当代中国史研究》2020年第3期。与之相反,张建华选择20世纪70年代意在宣誓俄国和苏联对乌苏里江流域主权的电影《德尔苏·乌扎拉》作为观察对象,描述了中国对这部苏联电影的严厉批判,展现了中苏交恶时期艺术背后的国家间政治(81)参见张建华:《〈德尔苏·乌扎拉〉:冲突年代苏联电影中的“中国形象”与中苏关系》,《俄罗斯研究》2015年第2期。。
美术交流展是中国对外文化交往的另一种形式。胡清清按照交往国家类型详细讨论了1949年至1966年中国的对外美术交流展,阐释了中国学习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美术体系,以及通过美术交流增进同新兴民族独立国家的友谊、加强对日本和少数几个欧洲国家民间外交的大体经过。此项研究从一个侧面诠释了中国“文化先行、外交殿后”的理念。(82)参见胡清清:《新中国的对外美术交流展研究(1949—1966)》,博士学位论文,南京艺术学院,2016年。赖荣幸的研究更为细微,聚焦1950年在苏联和东欧国家举办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艺术展览会。该案例的特殊性在于它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文化“走出去”的第一次重大活动和新中国美术对外交流的重要开端。参展的现代美术作品是新中国第一批革命现实主义画作,中方有意通过这种形式接受苏联的检阅,向苏联学习。(83)参见赖荣幸:《新中国第一次中国艺术海外展的模式与意义——1950年苏联“中国艺术展”》,《美术研究》2014年第2期。
体育交往是当代国家间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有时甚至成为外交的一部分,对中国来说也不例外。1963年印度尼西亚举办的第一届新兴力量运动会,是二战后第三世界国家主导的首次重大国际体育赛事。张小欣的研究显示,中国将全力支持新兴力量运动会作为推动召开第二次亚非会议和实施反帝反殖革命目标的重要手段,中国和印尼两国在此事上的合作有助于打破西方对国际体坛的垄断(84)参见张小欣:《新兴力量运动会的缘起与中国和印尼的关系》,《当代中国史研究》2014年第2期。。“乒乓外交”是中美关系缓和期间的一段佳话。李洪山从中美文化关系而非纯粹意义上的外交关系角度展开讨论,认为此次活动开启了两国文化交流的“乒乓模式”,即政府主导、民间实施、短期交流。20世纪70年代,中美之间数以千计的科学、技术、教育、医药、体育、艺术等各界人士以个人或团体方式进行的横跨太平洋交往,基本上都遵循了这一模式。(85)参见李洪山:《中美文化冷战结束之开端——“乒乓外交”新探》,《社会科学论坛》2012年第6期。徐国琦也研究了中美之间的“乒乓外交”,但他的视野并不局限于美国乒乓球代表团访华,而是同时论及中国乒乓球代表团回访美国,认为“乒乓外交”是两国一段“共有的历史”,不但加速了中国的国际化,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中美关系,重新塑造了世界政治格局(86)参见徐国琦:《体育与中美关系的历史发展——纪念“乒乓外交”50周年》,《美国研究》2021年第3期。。赵青峰则选择建交前的中韩体育交流作为研究对象,这是一个以往几乎没有受到中国学者关注的课题。他断言,20世纪80年代中韩之间的体育往来完全由政府主导,与两国关系的发展轨迹相吻合,具有浓重的政治色彩。体育交流是双方累积信任并最终走向建交的助推器。(87)参见赵青峰:《水到渠成:建交前体育交流与中韩关系发展》,《冷战国际史研究》第25辑,第127—150页。沙青青更是独辟蹊径,将目光投向棒球运动在新中国的趋热、遇冷与缓慢复苏,从军事体育、统战体育和外交体育三个层面展开论述。此项研究表明,意识形态的复杂性和政治局势的多变性必然导致棒球运动在新中国只能短暂繁荣。(88)参见沙青青:《在新中国打棒球:一项体育运动的境遇变迁及其多重角色》,《中共党史研究》2014年第2期。
苏联对新中国的影响极其广泛,建筑艺术也在其列。李扬指出,1954年建成的北京苏联展览馆(今北京展览馆)是一道苏联式文化景观,它不仅是新北京的城市地标,更充分体现了北京都市文化中的苏联印记。该展览馆及其附属建筑莫斯科餐厅(俗称“老莫”)、电影院、露天剧场等在当时刮起了一股“苏联风”,引领着中国首都的娱乐文化与消费时尚。(89)参见李扬:《“苏联式”建筑与“新北京”的城市形塑——以1950年代的苏联展览馆为例》,《首都师范大学学报》2017年第2期。张建华专注于探究作为公共空间的莫斯科餐厅在“文化大革命”前后从“政治符号”到“文化符号”的转变(90)参见张建华:《北京“老莫餐厅”:公共空间的苏联形象与中苏关系变迁的映像》,《俄罗斯学刊》2018年第4期。。洪长泰则反其道而行之,着力阐释苏联专家在天安门广场扩建问题上影响的有限性。此项研究认为,苏联专家将红场作为原型来协助扩建天安门广场,但中国领导人不愿把天安门广场改建为“红场第二”,而是秉持“洋为中用”的精神,希望作为政治符号的天安门广场能够体现出中国的独立自主。两国专家在天安门广场大小和形状等方面均不同程度地存在分歧,天安门广场的规模和布局最终由毛泽东亲自确定。(91)参见洪长泰:《空间与政治:扩建天安门广场》,《冷战国际史研究》第4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7年,第138—173页。
参加国际博览会是展示国家形象、增进其他国家对中国了解的途径之一。1951年至1957年,中国共参加了20多场国际博览会。夏松涛指出,这让中国向世界展现了自己的工业建设成就和传统文化,国家形象得到较大提升。(92)参见夏松涛:《1951—1957年新中国参加国际展览活动的形象探析》,《当代中国史研究》2020年第3期。其他学者的研究较多聚焦莱比锡国际博览会。陈弢认为,由于经验不足和情况不明等原因,中国参加1951年春季莱比锡国际博览会时,在布展方面出现了诸多问题。尽管如此,此次参展仍在很大程度上起到了宣传新中国建设成就、纠正部分欧洲人对中国的认识,以及促进中国与民主德国乃至整个欧洲经济交往的作用。此后几年,中国加大投入,不仅继续参展,还提升了规模和级别。在民主德国和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大力支持下,中国借助莱比锡国际博览会对欧洲展开的公共外交取得明显进展。尤为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参加莱比锡国际博览会,并不完全意在体现“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还希望凸显“中国特征”。(93)参见陈弢:《新中国对欧公共外交的开端——以莱比锡博览会为中心的考察》,《中共党史研究》2018年第2期。关于没有参加1962年春季莱比锡国际博览会的缘由,中方的解释是外汇不足,民主德国则认为是中苏分歧。童欣的研究表明,双方的说法都不全面,真正原因在于中国与民主德国之间积累了越来越多的矛盾,以及中国国内出现经济困难。(94)参见童欣:《中国未参加一九六二年莱比锡春季展览会原因探析》,《中共党史研究》2019年第6期。
宏观来看,上述新近问世的研究成果呈现出如下特点:其一,大多数研究采用了文化与政治互动的视角;其二,苏联和美国依旧是多数学者在探讨中外文化交流时优先选择的观察对象;其三,虽然讨论的是“低政治议题”,可以摆脱高度依赖官方档案的常规模式,但并非不需要利用一手文献,一些研究者在史实还原的过程中还是借助了中国外交部和各省市档案以及对象国的官方史料;其四,部分研究成果展现了中国对外文化交流的独立性、官方与民间态度的反差,以及商业利益方面的考量等,带有明显区别于既有研究的个性化特征。
七、外交史中的“普通人”问题研究
外交决策基本上处于政治精英的掌控之中,一般公众只能置身其外,但一部真正意义上的外交史却绝不能少了普通人的身影。20世纪五六十年代,随着新中国缓慢融入国际社会,跨国人员流动逐渐增加,他们是那个时代中国与外部世界关系的见证人与亲历者。新世纪以来,部分学者将视线转向这些普通人(主要是专家、实习生、留学生和工人),通过考察他们跨国交流的经历来展现中国和其他国家之间的互动。就研究场域的转换而言,这样的尝试给当代中国外交史研究注入了一股“革命性”气息。
20世纪50年代苏联对华经济援助的一个重要侧面,是向中国派遣了约2万名专家。沈志华的研究显示,中国一开始就从心理上把苏联派出专家和提供其他援助视作国际主义原则下理所应当的政府行为,而赫鲁晓夫则把派遣专家作为迫使中国在理论和政策分歧上就范的外交筹码(95)参见沈志华:《苏联专家在中国(1948—1960)》,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
为了“增进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和繁荣,发展我国同民族主义国家的友好关系,和打击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阵营的侵略和扩张活动”(96)《中央批转陈毅同志和李富春同志〈关于加强对外经济、技术援助工作领导的请示报告〉》(1958年10月29日),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B134-1-11。,新中国成立伊始就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义无反顾地开始了对外经济技术援助,培训外国实习生便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蒋华杰从总体上讨论了冷战时期中国培训外国实习生的政策。他认为,这并非单纯的技术转移问题,而是意识形态宣传和社会主义联盟的政治问题。随着20世纪50年代末社会主义阵营逐渐走向分裂,中国的实习生培训工作超越社会主义阵营的旧有范畴,转而成为支持第三世界国家革命的手段,意识形态输出逐步升级为首要政策目标。(97)参见蒋华杰:《解读冷战时期中国对外经济技术援助:以外国实习生培训项目为个案》,《近现代国际关系史研究》第9辑,世界知识出版社,2016年,第130—165页。董洁和笔者分别以北京和上海为例展示了朝鲜实习生的在华经历。董洁将来华特别是在京朝鲜实习生作为中朝关系的一个缩影,认为意识形态是决定双方所有交往的唯一标准。(98)参见董洁:《对在京朝鲜实习生的历史考察:基本状况及政策变化》,《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11年第6期。笔者则从政府与民间、党际关系与国家间关系的双重视角考察了在沪朝鲜实习生问题。该研究认为,20世纪50年代,政府塑造和民间自发共同勾画了这段中朝民间友好的历史轨迹。60年代中期前后,随着中朝两党两国关系由亲密转向冷淡,两国工人的关系也由和谐融洽转为矛盾丛生。在沪朝鲜实习生这一案例表明,由于党际关系左右着国家间关系,技术培训更多时候只是从一个侧面扮演着中朝两党关系晴雨表的角色,并未真正成为两国关系的重要推动力。(99)参见梁志:《作为政治任务的技术培训——以在沪朝鲜实习生为例(1953—1959)》,《党史研究与教学》2016年第3期;梁志:《作为政治任务的技术培训——朝鲜实习生在上海(1953—1967)》,《近现代国际关系史研究》第10辑,世界知识出版社,2016年,第127—163页。游览有关中国培训越南实习生的案例研究表明,与传授专业技术相比,中方更重视思想政治教育。但这种意识形态输出并未取得理想效果,越南实习生之所以对华亲近,主要源于与培训人员特别是师傅的个人友谊,而非受到中方思想政治教育感召。(100)参见游览:《技术援助中的意识形态输出——冷战时期中国对在华越南实习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外交评论》2012年第6期。蒋华杰从公共外交行为的角度对中国培训阿尔巴尼亚实习生作了解读。他指出,中方将培训目的定为塑造老师傅和实习生的个人友谊、缔造两党两国友谊。然而,由于对“社会主义劳动者”这一概念认知迥异、双方的民族性格和文化差异十分明显,以及中国调整对外战略,20世纪70年代,中阿友谊彻底破裂。(101)参见蒋华杰:《公共外交的意识形态化:冷战时期中国培训阿尔巴尼亚实习生计划解读》,《外交评论》2012年第4期。
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向苏联派出大量留学生,同时也接受了许多社会主义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的留学生。白冰研究了20世纪50年代初至60年代中期的留苏潮,展现了中方对留苏学生的政治审查过程,以及两党两国关系变化对中苏师生交往的影响。他认为,虽然一度受到中苏关系恶化或国内“左”倾错误影响,但当时间来到90年代,曾经的留苏学生开始不同程度地在科技、艺术乃至政治等领域发挥重要作用。(102)参见白冰:《中国学生赴苏学习问题的历史考察(1951—1965)》,《中共党史研究》2017年第12期。游览的研究表明,20世纪60年代中苏关系恶化使中国留苏学生陷入尴尬境地:既要继续完成学业,又必须顶住苏联政府的压力,根据国内指示战斗在反修斗争最前线。从本质上讲,他们的身份依然是学生,并不适合从事政治斗争,结果反修活动屡遭挫折,非但没能“以斗争促团结”,反而将本已剑拔弩张的中苏关系进一步推向敌对的边缘。(103)参见游览:《中苏关系走向破裂的见证者——20世纪60年代中国留苏学生的历史考察》,《中共党史研究》2014年第10期。蒋华杰则将视线聚焦于20世纪60年代在华非洲留学生的退学现象,展现了深受西方文化观念乃至政治价值观影响的非洲学生,在面对中国教育部门革命教育改造时的“水土不服”(104)参见蒋华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在华非洲学生“退学现象”分析》,《党史研究与教学》2016年第2期。。
冷战前期,中国还通过派遣工人的方式援助苏联和蒙古的社会主义建设。谷继坤指出,在就中国工人“赴苏援建”问题进行交涉的过程中,中苏双方均夹带着民族感情,抱有猜测与试探对方的心态以及“碍于情面”的心理。这是因为在社会主义国家之间,意识形态的同一性替代了各自国家利益的实际需要。从民间交往的角度来看,中国工人为苏联建设作出了贡献,得到了当地企业的认可,同当地居民之间也结下了深厚的个人友谊。但值得注意的是,选择定居在苏联的中国工人从未放弃自己的中国国籍,这体现出他们在国家和民族身份认同上不同于一般“劳工”的一面。(105)参见谷继坤:《中国工人“赴苏援建”问题的历史考察(1954—1963)》,《中共党史研究》2013年第10期;谷继坤:《对河北省清苑县工人“赴苏援建”问题的历史考察(之二)》,《冷战国际史研究》第26辑,世界知识出版社,2018年,第107—133页。按:还有学者考察了山东工人赴苏援建的历史。参见郭本意:《1956年至1964年山东省对苏劳务援助初探》,《安徽史学》2018年第5期。谷继坤还从历史记忆、地缘政治和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关系等多个角度研究了中国工人“赴蒙援建”问题,描述了中国工人与蒙方发生的矛盾和纠纷,揭示出蒙古迫切需要中国工人但又对他们怀有戒心的复杂心态,以及中国坚决拒绝从内蒙古地区大量派遣蒙古族工人背后的考虑,并以此阐释中蒙之间党际关系掩盖甚至替代国家间关系的现象(106)参见谷继坤:《中国工人“赴蒙援建”问题的历史考察(1949—1973)》,《中共党史研究》2015年第4期。。白林大量补充利用蒙古国档案,更为细致地还原了1949年至1964年中国工人“赴蒙援建”的历史过程,呈现了中国工人在蒙经历与两国外交决策之间的互动(107)参见白林:《中国赴蒙援建工人研究(1949—1964)》,博士学位论文,华东师范大学,2019年。。
仔细观察可以发现,上述研究主要考察的是中国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跨国人员流动。研究者们不但关注普通人的经历,更有意识地将他们的命运与宏观时代背景联系在一起,借助不同案例、从不同角度对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党际关系与国家间关系的张力进行理论思考,呼应和印证了中苏关系研究中的“结构失衡论”观点(108)沈志华和李丹慧曾就中苏同盟关系破裂的原因提出独到见解——“结构失衡论”:其一,社会主义阵营领导结构发生变化以后,中苏两党平起平坐,争夺话语权成为二者解决路线和政策分歧的基本手段,而目标则在于国际共运的主导权。其二,党际关系掩盖甚至替代了国家间关系。从本质上讲,在这种结构中没有主权意识,没有平等观念。这一结构性缺陷是中苏同盟必然走向破裂的深层原因。参见沈志华、李丹慧:《结构失衡:中苏同盟破裂的深层原因》,《探索与争鸣》2012年第10期。。同时,以上讨论还揭示出历史记忆、价值观和文化差异等过去往往被忽视的因素对中国与其他国家跨国人员交往的深刻影响。
八、回顾与展望
新世纪以来,从纵向上看,中国学者有关当代中国外交史的研究至少在如下三方面实现了令人瞩目的推进:其一,努力发掘中国、俄罗斯、美国、法国、德国、日本、韩国,乃至缅甸、蒙古、马来西亚、印度等国家新公布的档案,采用“国际史”的文献研究方法,在中国与各国建交、解决陆地边界问题、对外经济技术联系,甚至“夫人外交”“动物外交”等诸多子领域推陈出新(109)受篇幅和主题所限,对于“夫人外交”“动物外交”等选题,本文不作详细介绍。参见蒋华杰:《革命外交的张力:关于新中国夫人外交的历史考察(1950—1965)》,《中共党史研究》2016年第5期;刘晓晨:《兄弟之盟:新中国同社会主义国家间的动物外交》,《史林》2015年第2期。,开发了许多新课题,揭示了大量被尘封的历史事实,在一定程度上为未来重新搭建当代中国外交史的解释框架打下了一定的基础;其二,将电影、美术、体育、建筑、博览会等文化要素纳入考察范围,追求当代中国外交史研究的“文化转向”,从文化与政治互动的角度呈现当代中国与外部世界的跨文化交流;其三,不断扩大观察视野,秉持“跨国史”视角,从重点关注高层交往到适当兼顾底层往来(如援华专家、外国实习生、留学生、援外工人等),将普通人的命运置于大的时代背景下加以观察,并从多个角度探讨了意识形态在中国外交决策中扮演的角色。
从国家类型上看,新世纪以来中国学者的研究主要针对中国与社会主义国家、第三世界国家的关系,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关注相对较少。具体到国别和地区,在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关系方面,主要的研究对象是苏联、民主德国、朝鲜和越南,对其他东欧国家、蒙古和古巴等涉猎较少。在与第三世界国家的关系方面,重点国别是缅甸、印度和印度尼西亚,重点地区是亚洲和非洲,与拉丁美洲地区的关系几乎还没有进入学者们的视野(110)在关于中国与拉丁美洲地区关系的研究中,较有见地者不多。参见张琨:《比森特·罗维塔与原生书店——试论冷战时期毛泽东思想在拉丁美洲的传播》,《冷战国际史研究》第25辑,第151—172页;孙洪波:《中墨关系(1950—1960):基于中国外交档案的分析》,《拉丁美洲研究》2013年第4期。。至于与资本主义阵营的关系,美国自然最受关注,中国与英国、法国等西欧大国的关系也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考察,其他西欧小国和北欧诸国则很少引起学者们的兴趣。
值得注意的是,在当代中国外交史研究领域,国内已形成了华东师范大学周边国家研究院(前身为冷战国际史研究中心)和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南北两大学术研究和资料收藏中心。前者主要从事中国与社会主义国家、周边国家关系研究,收藏有大量相关国家对华关系档案文献以及中国外交部档案、各省市县地方档案;后者重点关注中国与资本主义国家关系以及各国冷战史档案资源的开放和利用状况,收藏有数量十分可观的西方国家对华关系档案文献。
整体而言,当代中国外交史研究尚且存在如下几方面明显缺陷:其一,相当一部分学者致力于从事“阐释性”研究,即片面地依靠《人民日报》等官方报刊资料,至多点缀性地使用少量档案文献,对中国外交决策或对外关系作出完全正面的阐释,而未从正反两方面辩证评价成败得失、客观总结经验教训;其二,部分中青年研究者机械地套用而非批判性地借鉴“软权力”概念、外交决策分析模式、层次分析法、需求层次理论等国际关系理论学界研究成果,用以分析中国外交决策或对外关系,以论代史或选择性使用史料,偏离了外交史研究与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相互促进的初衷;其三,或许是为了获得学位、晋升职称等功利性目标,一定范围内存在着既无新史料又无新观点的“炒冷饭”式重复研究,这突出表现在中苏关系、中美关系以及毛泽东、邓小平等中国领导人的美国观、苏联观等研究领域;其四,既有研究大多着力于史实还原,对于文化传统、民族主义情绪、反帝反殖思想、主权国家观念、“大国身份”意识如何塑造当代中国外交决策等更具理论性的议题关注得很少;其五,由于受到史料多寡等因素影响,既有研究对国家间关系讨论得比较多,对党际关系的讨论则明显偏少。
若要更为准确地概括当代中国外交史研究的成就和不足,还需将其置于国际学术发展进程中加以观察。近年来,随着各国档案文献的不断公布以及中国国家实力的逐步增强和国际地位的不断提高,当代中国外交史成为国际学术界高度关注的研究对象(111)例如,国际知名智库和研究机构伍德罗·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Woodrow Wilson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Scholars)近年来一直致力于收集、翻译世界各国有关冷战时期中国外交政策的档案文献,并开发了“中国外交政策数据库”(The Chinese Foreign Policy Database)。。中国学者关于中苏、中朝、中印和中缅关系的研究已然居于世界前列,前述陆地边界、外国实习生、援外工人等课题,国际学术界更是未曾触及。中国学者的一些研究成果在国际上受到普遍认可。例如,沈志华有关冷战时期中朝关系的日文专著不仅由日本顶级出版社岩波书店出版(112)参见沈志華著、朱建栄訳『最後の「天朝」——毛沢東·金日成時代の中国と北朝鮮』(上·下)岩波書店、2016年。,而且陆续推出了繁体中文、英文以及韩文等版本。又如,沈志华、李丹慧和夏亚峰有关冷战时期中苏关系的最新英文著作,被哈佛大学冷战研究系列丛书收录(113)参见Shen, Zhihua and Xia, Yafeng (2015).Mao and the Sino-Soviet Partnership, 1945-1959: A New History.Lanham: Lexington Books; Li, Danhui and Xia, Yafeng (2018).Mao and the Sino-Soviet Split, 1959-1973: A New History.Lanham: Lexington Books。。再如,2017年4月,美国外交史学家学会(Society for Historians of American Foreign Relations,SHAFR)会刊、国际学术界公认的外交史和国际关系史领域最顶尖的学术期刊《外交史》(Diplomatic History)第41卷第2期集中刊发了一组题为“来自中国的冷战史新观点”的专栏文章,包括夏亚峰和笔者的一篇20世纪中国对美国政策研究综述以及王栋和詹欣的两篇中美关系史专题论文。2018年秋和2019年夏,韩国庆南大学主办的东亚问题研究知名学术杂志《亚洲视角》(Asian Perspective)第42卷第4期、第43卷第3期以“中国与邻国关系:当下问题的历史视角”为主题,接连刊发了两组以中国中青年学者为主的有关当代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的专题论文。2019年8月,香港中文大学创办的著名中国问题杂志《中国评论》(The China Review)第19卷第3期则以“冷战时期中国与社会主义国家间的人员交流”为主题,通过专刊的形式发表了一组中国中青年学者的专题论文。由此可见,从事当代中国外交史研究的中青年学者已经逐渐成长起来,其研究成果特别是研究方法和视角已经得到国际主流学术界认可。
应该指出的是,在利用中国外交对象国的档案文献方面,国际学术界总体上仍走在前面。例如,哈佛大学助理教授杰里米·弗里德曼(Jeremy Friedman)利用中国、苏联、南非、莫桑比克、智利等十个国家的官方档案,细致勾勒了中国与苏联两个社会主义大国在亚非拉地区展开竞争的历史过程。此项研究最大的学术价值在于摆脱中美苏“大三角”关系的传统视角,从争夺第三世界的层面描绘了中苏关系的又一重面相——独立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制度“人心之争”以外的“另一种冷战”(Shadow Cold War),或者说革命意识形态之争。(114)参见Friedman, J.(2015).Shadow Cold War: The Sino-Soviet Competition for the Third World.Chapel Hill: 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又如,2017年6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史评论》(The PRC History Review)杂志集中刊发了八篇各国学者撰写的利用珍稀史料研究冷战时期中国对外关系的短文,相关档案来源地包括坦桑尼亚、赞比亚、阿尔及利亚、摩洛哥、墨西哥、俄罗斯和德国等国家。相较而言,相当一部分中国学者还只是利用中方档案文献进行当代中国外交史研究。此外,外国学者的一些选题视角比较独特,值得中国学者借鉴,比如中国政府利用杂技表演推动中美和解、可口可乐与中国改革开放初期的中美关系、西方经济学家怎样通过与中国改革者的互动影响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进程等(115)参见Zhang, Tracy Ying (2016).“Bending the Body for China: The Uses of Acrobatics in Sino-US Diplomacy during the Cold War”.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ultural Policy, 22(2), pp.123-146;Kraus, C.(2019).“More than Just a Soft Drink: Coca-Cola and China’s Early Reform and Opening”.Diplomatic History, 43(1), pp.107-129; Gewirtz, J.(2017).Chinese Reformers, Western Economists, and the Making of Global China.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在中国学者暂未涉猎或涉猎不深的一些研究课题上,外国学者迈出了探索的步伐,例如冷战时期中美两国在第三世界的竞争、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如何促进中美经贸和外交关系发展、20世纪60年代末至80年代初西欧与中国的关系、20世纪70年代的中英科技关系、20世纪70年代中美石油外交、1949年至1972年中国的对日民间外交、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与华约的关系,等等(116)参见Brazinsky, G.(2017).Winning the Third World: Sino-American Rivalry during the Cold War.Chapel Hill: 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Talley, C.(2018).Forgotten Vanguard: Informal Diplomacy and the Rise of United States-China Trade, 1972-1980.Notre Dame: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 Albers, M.(2016).Britain, France, West Germany and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1969-1982: The European Dimension of China’s Great Transition.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Agar, J.(2013).“‘It’s Spring Time for Science’: Renewing China-UK Scientific Relations in the 1970s”.Notes and Records of the Royal Society of London, 67(1), pp.7-24; Minami, Kazushi (2017).“Oil for the Lamps of America? Sino-American Oil Diplomacy, 1973-1979”.Diplomatic History, 41(5), pp.959-984; Wits, C.(2015).“The Japan Hands: China’s People’s Diplomacy towards Japan, 1949-1972”.Ph.D.dissertation, Doshisha University; Lüthi, L.(2007).“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nd the Warsaw Pact Organization, 1955-63”.Cold War History, 7(4), pp.479-494; Ciorciari, J.(2014).“China and the Pol Pot Regime”.Cold War History, 14(2), pp.215-235。。
未来若干年,在当代中国外交史研究领域,中国学者或许可以尝试从以下几方面作出努力,争取实现突破性进展:其一,在中国外交部档案馆和各省市县档案馆文献开放程度不理想的情况下,通过提高外语能力,大力发掘国外档案,在中国之外“发现中国”,针对一些选题空白点进行开拓性研究,比如中国与拉丁美洲、非洲、东欧、北欧国家的关系等(117)已有学者尝试聚焦小语种、关注度相对较低的国家,例如湖北大学巴西研究中心程晶正在利用巴西档案,辅之以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档案,对冷战时期中国与巴西的关系进行研究。。其二,在继续进行外交决策过程研究的同时,将部分注意力转移至中国对外决策机制、外交理论、领导人思想和意识形态等过去较少得到学术化研究的议题(118)参见李潜虞:《试论新中国对外国驻华使馆的管理(1949—1965)》,《外交评论》2013年第5期。。其三,将视线下沉到“低端政治”,在跨国文化和人员交流方面加大探索力度。这方面可以讨论的话题还很多,比如苏联文学作品在新中国的阅读史、中国与周边国家之间的跨境民族流动、归国留美和留苏学人群体等。其四,在专注于某一时间段的中国对外战略、双边关系、重大历史事件或重要人物等个案研究的同时,进行带有“通史”性质的宏观和长时段考察。其五,针对合适的选题,适当汲取国际关系学、心理学等其他学科养分,主要是其概念和视角,以此丰富当代中国外交史研究的理论资源。
笔者认为,坚守“中国中心”、秉持世界眼光是当代中国外交史研究未来的方向(119)坚守“中国中心”、秉持世界眼光,指研究者要兼具中国史和世界史两个一级学科的知识结构,同时利用中国和外交对象国乃至第三方的档案文献,从中国国内形势与国际处境两个方面理解中国外交。,相信随着新史料不断问世并得到开掘、年青一代学者快速成长,以及国内外学术交流持续加强,在不久的将来,当代中国外交史研究这块远未完全开垦的土地上必会结出更为丰硕的果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