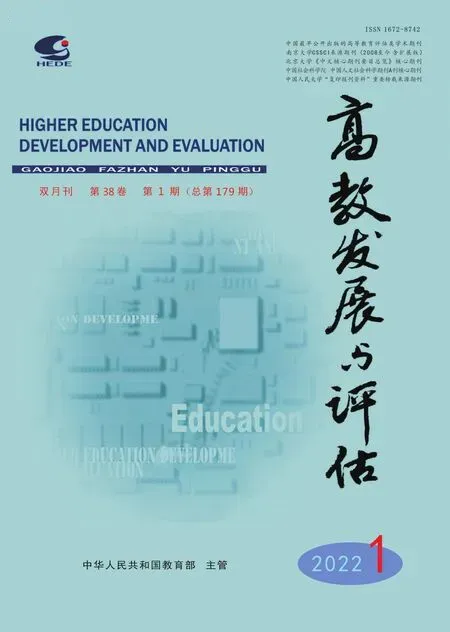研究生导师的教育爱及其实现
2022-02-26国建文傅淳华
国建文,傅淳华,肖 李
(1.北京师范大学 教师教育研究中心,北京100875;2.中央民族大学 教育学院,北京100081;3.云南艺术学院 课程中心,云南 昆明650500)
以研究生导师落实“立德树人”职责为研究对象的师德研究受到了诸多学者的关注,主要有三类:一是研究生导师立德树人的本体论分析,如研究生导师在立德树人过程中如何当好学术传导人、学术训导人、学术引导人的学术逻辑;二是研究生导师立德树人的模式建构,如从理想信念、学风道德、身心健康和社会实践等四维一体去建构研究生导师立德树人的长效机制;三是研究生导师立德树人过程中合理导学关系的建构,如有研究界定出剥削紧张型、梳理松散型、雇佣关系型、传统师徒型、良师益友型五种导学关系,进而对合理导学关系的建立提出具体建议。[1-4]
研究生导师落实立德树人的职责在本质上而言是一种爱的活动和爱的显现。道德不限于爱,但人的诸多道德规范都是以爱为基础的,没有爱这一根基,人的道德就会变得僵硬。[5]49从根本上而言,研究生导师教育爱的生成和实现是其履行立德树人职责的前提和基础。但是相关研究似乎对研究生导师的教育爱进行了隐遁和消解,因而缺少了深层次的阐释与反思。
一、研究生导师教育爱的本质探寻
揭示研究生导师教育爱的本质,是研究生导师理解和践行教育爱的关键。正如亚里士多德论及友爱时曾提及的:“人们在因所爱的人自身之故而希望他好时,这种善意不是基于感情而是基于一种品质。爱着朋友的人就是在爱着自身的善。”[6]238从根本上说,研究生导师的教育爱发轫于研究生导师的人性之善,因为,唯有爱着自身的善,才能爱他人。当然,研究生导师的善并非是说研究生导师已是至善之人(德性完满的人),而是说研究生导师是走在求善、向善路上的“爱智”之人。按照苏格拉底的说法,人性之善就是人的美德,美德就是人所追求的最高的知识,而最高的知识,正是“获得幸福,避免祸患”的知识[7]88-94。柏拉图也表明,这种知识就是德性和幸福[8]。换言之,研究生导师的教育爱,首先表明的是,研究生导师自身是一个好人,一个好人首要的标准就是要守住人性的善端,而人性的善端就是最大的德性和最好的幸福,这种幸福、这种德性就是苏格拉底所说的最高的知识,即爱智慧的知识。这就要求,研究生导师要首先具备“爱智”的道德品性,追问什么是可能的、好的生活,如此,研究生导师才能保持自身“求善”的本心,进而具备教育爱的能力。这也正如孔子所言,“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论语·述而》)。所以,研究生导师的教育爱根源于研究生导师作为一个好人对智慧的追求。当然,这种追求本身要求研究生导师能够过一种沉思式的自我省察的生活。因为“沉思生活代表着最为卓越的内在生活的范本。这种生活几乎是独立的,因为它对外在的要求实在太少……并不以外在事物为目的”[9]。这意味着,研究生导师教育爱的本质是一种自足自爱的幸福,一种值得欲求的好的生活,这种生活本身能够为研究生导师带来属己的快乐。
二、研究生导师教育爱的发生逻辑
研究生导师教育爱的本源在于个体人性的善端,始于个体对智慧的欲求,但研究生导师的教育爱并不能也并不会仅止于个体初始的爱欲,而会发生转向和上升。缺少了爱欲的扩展与提升,则个体发展始终局限在日常生活视域之中,无法转向更高的美善事物。[7]156研究生导师教育爱转向和上升主要向两个向度敞开:一是研究生导师追求智慧的同时关心和尊重学生,实现研究生导师与学生的彼此驯服,这里的驯服指称的是一种相互关爱的关系;二是研究生导师教育爱的上升主要指向研究生和研究生导师在教育爱的氛围中共同去亲近更高的、更美善的事物,即真理。在此意义上,研究生导师的教育爱依托以下方式而渐次生成。
(一)研究生导师教育爱的发生以“自愿”为自然基石
在亚里士多德看来,一项行为,如果其始因是外在的,行为者就如人被飓风裹挟或受他人胁迫那样对这初因完全无助,就是被迫的行为。[6]58认清自愿性,可以从不自愿开始。在亚里士多德看来,一个人之所以会做出不自愿的行为主要基于两种因素:受到外部的压迫或是出于自身的无知。被压迫是指由于外在的、外力的胁迫与裹挟而使自身不能自主地决定所发生的行为;无知是对行动时刻的具体环境无感,但又对行为所产生的后果产生了痛苦或者悔恨的感受。自愿性行为是自我理智自身的情感和性格,并愿意为自己行为的后果负责。这意味着,“我的责任仅局限于那些我自己所承担的”这一观念,是一个具有解放意味的观念。它假设……那唯一约束我们的道德责任的来源,并不是习俗、传统或继承状态,而是每一个个体的自由选择。[10]由此,个体才会对所付出的感情和实践负责到底。正如黑格尔所说:“只能以我所知道的事况归责于我,仅仅以摆在我面前的存在为我所认知者为限。”[11]因此,研究生导师教育爱的发生以研究生导师的“自愿性”为根基,这种感情实践的自愿性就像“一块抛向空中的石头会自由向下落”一样自然。
(二)研究生导师教育爱的发生以“驯服”为天然情境
“爱不是对象,爱是关系,是你在对象身上付出的时间和心血。”(《要塞·序》)研究生和研究生导师所建立起的师生关系不仅是一种学术指导关系,也是一种情感关系、人格关系。[12]这种情感关系、人格关系归根结底植根于研究生导师与研究生之间所建立起的教育爱的关系。因为教育爱是联结教育领域中其它一切关系的纽带与基础。教育爱不仅仅是教师对学生的爱,更是对教育关系的道德承诺,即无论学生如何,教育者都对这种教育关系负有道德义务和道德责任,无论付出什么代价,都不能放弃这一关系。换言之,研究生导师的教育爱是研究生与研究生导师建立起的“爱”的关联,即彼此驯服。在驯服情境中,研究生和研究生导师两个人原本可能是不认识的,经过双方努力,慢慢变得熟络,培养出深厚的感情,最后彼此紧密相联。[5]55
(三)研究生导师教育爱的发生以“尽责”为实然动力
研究生导师的道德责任是内在于研究生导师与研究生建立起来的“教育爱”的关系之中的。如果研究生导师能够全身心地投入这种教育爱的关系,他就会充分认识到因教育爱而伴随的“传道、授业、解惑”的责任,并努力善尽自己的责任,从而产生自我约束力。反之,如果研究生导师轻易放弃自己作为导师的责任,就说明他从未投入与研究生建立起的教育爱的关系。研究生导师教育爱的生成所伴生的责任问题不是要研究生导师考虑应不应该负有相关的责任,而是怎样才能更好地尽到自己的责任,怎样在这种教育爱的关系中驯服他们(彼此)在乎的人。[13]
研究生导师为了更好地履责以推动教育爱的生成,需要重视以下两个方面的问题。其一,关注当下和未来的职责。诺丁斯说:“关心者,无论男性女性,都不会在抽象的原则或者事物中寻求心安理得。她追求对被关心者此地此时的责任,对当下情形以及对她和被关心者所规划的可以预见的未来的责任。”[14]在教育爱中,研究生导师不仅要履行教育爱所生发的当下的责任,还应有批判性思维来预见今后的责任。例如,研究生导师对“下一代”科研学术人才培养的责任;研究生导师对研究生未来人格的健全与文化的传承的责任等。其二,践行唤醒与给予之爱。这种唤醒与给予的爱是为了导师权力与权威的隐退而非控制做准备。“给予之爱肩负着重任,它必须朝着自己的引退努力。我们的目标必须是使自己成为多余。当我们能够说‘他们不再需要我了’,那一刻便是对我们的奖赏。”[15]而研究生导师应警惕最极端的倾向,即控制变成了人对人行为的约束而使教育爱落空。[16]6
三、研究生导师教育爱的具体实践
一方面,研究生导师的教育爱是为使研究生能够从师获益、能进行自我教育,并与人格平等的求知识获智慧的人(包括导师)进行富于爱心的交流所构筑的理想,希冀以此照亮现实[16]1-2;另一方面,唯有依据现实状态,才能展开研究生导师教育爱的理想追寻。我们应关照与回应现实,探索研究生导师教育爱的理想的实现方式。研究生导师必须重返自身,审察自我内在的心灵世界与外裹自身的教育制度。
(一)研究生导师心灵的丰盈和引领
若将研究生导师与研究生个体置于冷冰冰的学科体系、导学关系和社会要求之下,并把培养“科研人”“社会人”作为预设目的。其教育内容基于现代技术文明,过度宣扬价值中立的实证科学,忽视乃至践踏了研究生导师教育爱的价值使命。研究生导师关注的只是为学术机构服务和提升自己的学术职务,失去了眼中的“学生”。正是这一缘故,研究生往往只是追求学位的声望而不追求其他价值。[17]
研究生导师若要实践教育爱,就不能一味地向研究生传授科学知识,而应该自愿地与研究生创设彼此驯服的情境,进而在这种驯服的情境中善尽自己的职责,释放教育爱,促使研究生走上一条充满爱的道路。为此,“人应该上路,爱之路,这路是一道美的阶梯,是身体的,更是灵魂的,努力攀爬者已经在分享着美,已经在美的光辉里了”[18]。研究生导师要践行教育爱,首先要学习自知自爱。不爱自己、不懂得自己的人,没有好的方式去理解和爱他者,但是,认识自己与爱自己并不容易,因为“眼睛看不到眼睛”(维特根斯坦语)。这就要求研究生导师要敬重和细读经典文本,与伟大人物展开心灵的对话,与历代思想家一起思索如何去做一个自爱的教师。“如果没有那些伟大的启示、史诗和哲理构成我们自然观的一部分,我们从外部世界就看不到任何东西,最终内心也会空空如也。”[19]与伟大的作品(心灵)展开的对话能够帮助研究生导师重拾自爱的道德感觉,并逐渐认清自己,将自爱自知丰盈心间。
研究生导师需要理解和在乎研究生,自愿引领研究生走“上升的爱之路”。因为,“理解的心灵是一个教师的一切,是怎么高估也不为过的。课程只是必要的原材料,但对学生的热情是育人育树的根本”[20]。导师要做到真正理解和在乎研究生,必须建立起彼此驯服的共同体关系。这种关系的建立不能一蹴而就,需要时间与空间,以及仪式,以此构筑一个话语的共同世界。例如,时下倡导的研究生团队导师制,导师与青年教师、导师与学生的沟通交流频繁,导师需要时刻吸收新知识,碰撞新思维,进行创新思维体系升级。[21]在团队导师间的沟通交流和相互理解将构建一个彼此驯服的共同体组织。同时,研究生导师与研究生要放弃商品逻辑,愿意付出时间去相互了解,努力驯服彼此,从而形成真正的爱的共同体,共同走向有爱的生活世界。这也意味着:研究生导师已经做好了自愿承负由教育爱的付出而来的可能的伤害;同时,研究生不能是等待着被爱的实体,更应主动去学习如何接受教育爱。
(二)研究生导师对外在制度的反思和突破
研究生导师的教育爱从本质上而言是自身道德品质的显现,从其外在表现形式而言,是研究生导师与研究生建立起来的道德关系。但是,无论是道德品质的形成亦或是道德关系的维系,都离不开制度的有效支持。“任何一种德育,都要根据一定的德育思想建立起一套实践体系,其核心就是德育制度。没有制度体系保障的德育思想,是不会成为实际的教育行动的。”[22]虽然现行研究生德育以制度化为其基本形式,以公正、人本为基本价值指向,但是功利化价值与商品化思维的流弊依然渗透在研究生德育领域,与教育爱对立的恶与懦弱的行为层出不穷。若德育制度倘失却了对高尚的教育爱的关照和融合,研究生导师就变成依据制度而存在的、不分善恶的、没有崇高理想的“中性人”;相应地,无法根除的恶将成为研究生教育时刻面对的基本事实。在此境遇中,研究生导师一方面安于现状,只做“制度的囚徒”;另一方面,邪恶不仅来自人的自由意志,也出于人天生的道德欠缺和软弱。[23]而试图规避人之天性弱点的德育制度又走向了庸常化和功利化。如此,制度与设计制度的人(所有人)正可以“狼狈为奸”。为了摆脱德育制度对研究生导师教育爱的遮蔽与驱逐,重拾德育制度对研究生导师教育爱的关切和引领,需要研究生导师在个体层面重拾起哲人的身份,做趋引德育制度向善向好的守卫者和护卫者。
研究生导师对德育制度的反思和突破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展开。
一是研究生导师以反思的方式和想象化的对话省察德育制度的理念。德育理念是德育制度得以建立和运行的先决条件,研究生导师必须以一种哲学家沉思式的生活方式与德育制度保持一定的距离,并能够对其进行审视。当然,研究生导师并不是哲学家,但须以一种反思德育制度和与其展开想象化对话的方式来省察德育制度建设的理念。唯有如此,研究生导师才能够鉴别与发现:德育制度建设的理念是否将研究生导师的教育爱予以考量?德育制度何以必要关注研究生导师教育爱的实现?德育制度也是由人所制定的,并非具备自然的正当性与合理性,需要我们对其不正当、需完善的内容做出适时反思。
二是研究生导师对德育制度的突破。德育制度所规约的教育方式由教师来践行,教师可以在真实的教育活动中去追询德育制度是否彰显着教育爱,从而发现制度中的自我(导师)是否真正在释放教育爱。在此基础上,研究生导师才能不断刺破与揭穿德育制度所可能隐蔽的灰暗阴冷的一面,而将教育爱注入到德育制度之中,使其发挥护佑研究生导师教育爱落实的功能。当然,将教育爱的理念与实践注入德育制度之中是一个漫长的转变与等待的过程,研究生导师不能看低这微小的可能发生的变化对德育制度的完善产生的影响,你怎样实践德育制度,德育制度就会成为怎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