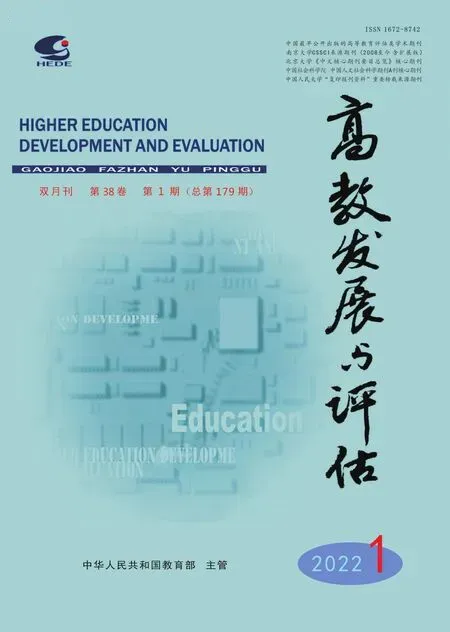论教育史研究者的五维素养
2022-02-26刘秀霞严孟帅
刘秀霞,严孟帅
(1.四川师范大学 四川文化教育高等研究院,四川 成都610066;2.四川师范大学 教育科学学院,四川 成都610066)
教育史研究者素养问题是教育史学科建设领域中的重要议题之一。张斌贤将“教育史研究工作者所应具备的基本学术素养”作为教育史学科的基础理论问题之一,提出当代教育史研究工作者应掌握科学的历史思想方法、广泛的知识和足够的语言能力[1];杜成宪认为“中国教育史学工作者的修养等理论问题”是中国教育史“形式研究”属下的若干范畴之一[2];周洪宇视学者素养要素论为教育史学若干问题之一,并提出“一个合格的教育史学研究者应具有‘史德’、‘史识’、‘史学’、‘史才’四种学术素养”[3]。国外学者同样十分关注教育史研究者的素养问题。布里克曼(William W.Brickman)主张,教育史研究者除具备称职的历史学家应具备的素养外,还应“精通教育一般和特殊方面的知识”以及教育实践类知识[4]248;教育史研究者应具备八类素养,包括普通教养、世界历史知识、教育历史类基础广博知识、教育历史类专项精深知识、研究方法、编史的知识、阅读史著中使用语言的能力、对话所需的知识和能力等[5]。
已有研究论述了教育史研究者素养问题的学科意义和学术价值,并探讨了素养内涵和构成等问题。但存在如下不足:其一,国内学者的论述多为概论,对教育史研究者的素养内涵及结构缺乏细致入微的探讨,教育实践意识较为淡薄;其二,西方学者的论述多基于近代分科体系逻辑,缺少中国传统史学内涵。本研究在理论层面上探讨教育史研究者素养,以期为当下建立素养结构合理的教育史学人才队伍提供学理支持和实践路径。本研究中,教育史研究者的素养主要是指从事教育史研究工作的相关人员应具备和能适应教育史专业发展的需求,并独立进行教育史研究的知识、品格和能力。本文以中国传统史学中良史、史才的评判标准为根基,尝试从才、学、识、德、道五个维度对教育史研究者的素养结构进行探究。
一、非“才”无以善教育史之文
教育史研究者之“才”,主要指研究者的才干,即进行教育史研究的兴趣与天赋,包括进行教育史研究的兴趣、记忆以及撰写文章的表达力等。刘知几认为,“夫有学无才,犹愚贾操金,不能殖货。”[6]4522章学诚指出,“所凭者文也”,“非才无以善其文”[7]257。此“才”是指人的天赋才能,教育史学家不是训练出来的,而是天生的,“因为每个人都具备此种天赋”[8],如进行教育史研究的兴趣、记忆、语言文字的表达能力等。对教育史相关问题的兴趣是持续进行教育史研究的动力,对教育史实的记忆是进行教育史研究的必经路径,教育史料的组织应注意剪裁、排列,文字表述应真实、质朴、简洁、含蓄、音韵[9]296-297。
兴趣与记忆是指研究者主动探索教育史问题,并积极记忆相关的教育制度、人物思想、史料来源等以形成体系的能力。兴趣是研究者进行学术研究的精神力量,它推动个体关注教育现象,探究教育历史。准确的记忆力是进行教育史研究的重要才能之一,也是进行教育史研究的基础。记忆是进行教育史料收集和储备的重要方式;准确的识记有助于梳理不同教育史实及思想,迅速建立彼此间联系,发现其异同;高效的记忆力,能促使研究者提纲挈领地把握教育史实,实现融会贯通。
表达力即对教育史实、思想、发现等通过文字、图片、表格等方式予以呈现的能力。文字、图片、视频、实物等是教育史研究者进行思想表达和传播的重要媒介。编年体、纪传体、纪事本末体等编纂体裁均可为教育史研究者选用,借由文字呈现研究成果。无论选用何种表达媒介或编排方式,客观、系统的史实呈现都是教育史研究者的应有之义,“以正确无误而又简明扼要的词汇反映周围千变万化的现实生活”[10]121。更高级别的教育史研究成果与著述表达融思想、情感、诗意于一体,即教育史文本应富有感召力。唯有此,教育史研究方可引人入胜,激发读者想象力。为了达成这一目标,研究者需要“进入历史,去经历历史而感知历史”[11]37,学习教育史编排与文辞技巧,“表述方式上,遵循客观性与艺术性的统一,在尊重客观史实的基础上展现生动活泼的教育世界,使之实现‘心灵的’或‘精神的’学科功能”[12]。
“才”,因兴趣提出教育史研究问题,经记忆完成对相关教育史料的融会贯通,由表达力呈现研究成果并陶冶读者情操。
二、非“学”无以练教育史之事
教育史研究者之“学”是指教育史研究者通过后天塑造的学习品格、积累的知识和培养的技能等。已有学者提出“有才无学,犹巧匠无楩柟斧斤,弗能成室”[6]4522。“记诵以为学也”,然而“非学无以练其事”[7]257。教育史研究者需要通过学习获得普通常识及专门学问,通过练习达到勤学而熟,熟能生巧。研究者学习和练习的内容以教育史知识、理论与方法为重。
学会学习,即研究者树立终身学习的意识,掌握有效的学习方法,形成学习品格,进而积累教育史专业知识和技能。其中系统化、结构化的教育史理论知识体系应涵盖但不限于:中、外教育史,教育史学,教育史研究方法,教育学原理,史学理论,历史文献学,中、外哲学等学科性理论体系和知识内容。学养深厚是优秀教育史研究者的必备品质,“研究历史之事,不限于读书;读书不限于读中国书;读中国书亦不限于旧日之史籍……治学故贵专精,规模宜需恢弘”[13]。教育史研究者还应了解多学科领域的知识,体会钱穆所提出的“成家而化”的状态,即由一人、一派进入了解,后扩展至广博,再由博反约至“致曲”,最终须能化[14],为其专业研究提供广博的知识背景。专业技能即教育史研究者通过一定训练而获得的阅读、选题、史料收集与解读、论著撰写等专业能力。教育史料的辑佚是教育史研究领域中的一项重要工作,要求研究者学习史料收集和整理方法,包括学会查找图书馆纸质资料、网络数据库资源,收集原始和辅助资料[4]8-147,并运用史料分类法、计量统计法等加以整理。对教育史料的掌握要求研究者具备相应的语言素养,即古代教育史研究者需掌握读古书的综合能力,习得训诂学、音韵学、目录学、校雠学、版本学等传统史学应具备的方法。同时,随着全球教育史的发展,外语能力是每位教育史研究者的必备技能,通过阅读外文原著,准确地把握史料并形成全球视野,借由外语将研究成果分享至世界。此外,研究者还应掌握教育史分析、解释与撰写的方法,培养阐释与撰写教育史的专业素养。
勤于习练,即教育史研究者应勤于寻求各类教育史材料、事实与证据,勤于练习各种教育史专业技能,包括教育史资料搜集整理方法、教育史问题的研究方法、教育史文章的写作技能等。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教育史料的存储路径发生了众多变化,研究者经常搜集整理相关史料,方能熟知不同类型史料的存储位置与获取方法,求得相应的事实与证据;常用某类研究方法探究教育史问题,方能熟练使用该方法,熟知方法背后的理念,甚至有所创新;勤于撰写教育史文章,方能提升语言表达水平,完成富有内涵与启发价值的文字篇章。
“学”,学习做教育史学问的理论与方法,在研究中学习、在教育实践中练习,好学、会学、勤练,从而塑造学养深厚的品质。
三、非“识”无以见人所不见
教育史研究者之“识”,指研究者鉴别教育史料的见识和进行褒贬评判的胆识,即独立见解、彰善贬恶的立场和态度。章学诚视史识为“欲于记诵之间,知所抉择,以成文理耳”[7]257。梁启超首先强调史家的观察力,求关联的事实,实亦包括思考力[15]115。钱穆认为卓越的史识“能见其全,能见其大,能见其远,能见其深,能见人所不见处”[16]。何兆武重视“历史理性”,即对史实的“理性思维和体验能力”[17]43。教育史之“识”需要研究者培养其理性思维、想象力和创新性思维等。
理性思维指围绕教育史研究问题,对搜集而得的教育史料进行鉴别、批判、重构的思维品质。教育史研究者应积极关注并参与教育实践,从教育史学科的视角出发,发现并提出有价值的研究问题。鉴别能力即对搜集到的教育史料进行考察与辨析真伪的能力。教育史料“以求真为尚。真之反面有二:一曰误,二曰伪。正误辨伪,是谓鉴别”[15]57。之所以需要正误辨伪在于:教育史研究的对象“有自己的时间和地点”[18]231,即有客观性、科学性却不可再现,且部分教育史料有意记录了“精心粉饰的形象”[10]8。考据、版本、校勘等方法可辅助鉴别。仅考据出教育史料的真假只不过是完成了一半的任务,教育史研究者还必须深入揭示人们作伪的动机及其背后的难言之隐。故而,需要在准确把握相关史实的基础上对已有“资料”进行辩证性批判。评判教育史人物须遵循教育实践、社会发展、历史贡献和人民利益的标准,评论教育史著须遵循相应的社会和学术标准。[9]118但评判不是目的,重构才是旨归。在重构的过程中,还原教育史实的发生、发展过程,洞察教育发展规律。此外,还应关注教育史观如唯物/唯心主义教育史观、马克思主义教育史观、现代化教育史观等对这一理性思维过程的指导作用。
想象力即在心灵中进行教育史实重演的思维品质。教育史研究中,想象力的作用“并不是装饰性的而是结构性的”[18]238,不可或缺。进行教育史研究,“没有想象力和体验力是不行的”[19]366,且“必要的体验能力和想象能力,常常是研究是否能够有所突破的很重要的因素”[11]41。合理的想象在还原教育实践本来面貌、认识教育家思想、推动研究进程中均扮演重要角色。但想象并非幻想和瞎想,要求研究者进行有边界的体验感知与想象,即“证据、证据,必要的证据和大量可靠的证据,这是我们确定历史想象合理性的基础”[19]366。故而,需培养研究者在充足证据基础上进行合理想象的素养。
创新性思维即发现新的教育史料,或对已发生的教育事件或思想提出新见解的思维品质。教育史研究“最重要的就是要根据史籍或其他资料证明史实,认识史实,对该史实有新的见解,或新的看法”[20]。杰出的教育史研究者通常具有可靠的直觉判断力。新视角或理论如社会分层论、教育生态学、性别哲学等,能帮助研究者重新看待已有的教育史料,透过不同的理论镜片,“同一史实可能呈现不同的面貌”[21]。从多层次、多角度还原史实,阐释其意义。教育史研究发展本身要求教育史研究者有理论创新意识。“从史料(历史事实)中取得认识,回头再用此认识去观察史料(历史事实),认识水平就会逐步提高。辗转推进,由简单认识提升为理论,再运用理论去认识历史,这就是方法。”[22]唯有不断进行创新,才能深化教育史研究并促进学科发展。
“识”,赋予研究者以慧眼:经由理性思维,在教育实践中洞见有价值的研究问题,并实现对教育史料的正误辨伪与重构;通过想象力,推动研究进程,还原教育史实全貌;基于创新思维,获得新面貌,形成新观点、新理论。
四、非“德”无以求教育史之公
教育史研究者之“德”,“德者何?谓著书者之心术也”。就是要求研究者“必学养淳粹,不恣情,不使气”[7]257;教育史研究者在著述时应尽其天职,端正心术,直书、实录,使主观符合客观,反映历史真实面貌。“所谓史德,乃是对于过去毫无偏私,善恶褒贬,务求公正。”[15]111“德”的素养指研究者的行为规范与内心修养,包括在日常生活中,持有人性向善的信念,培养个体端正的品行;工作领域里,持有对教育事业的热忱,并通过规范直书的学术研究态度与行为方式,塑造其职业素养;在学科发展中,积极参与教育实践,并通过对有民族特色的教育问题的阐述,形成责任担当的品格。
人格修养,即秉持人性向善的信念,在日常生活中遵守社会契约,操履良直,并培育仁、义、礼、智、信等优良品格。信史总是基于对撰史者品行的信赖,秽史与谤书因撰写者德行有失而不为人所信。故古人选择史官时强调尤须好是正直。“修撰国史,义在典实,自非操履贞白,业量该通,谠正有闻,方堪此任。”[23]治学与做人密切相关,教育史研究者应将操行清白置于才华之前,尤需注重其人格修养,养成谦虚、谨慎的品质。
职业素养,即研究者怀揣对人类教育事业发展的热忱,通过遵守学术规范、教育史行业准则,维护研究伦理等行为,逐渐形成的一种修养。教育史研究者应关注并参与教育实践,牢固树立遵守学术规范的意识,禁止史料造假与学术剽窃,尊重前人研究成果,规范学术引用。在收集教育史料和展开教育史研究的过程中,研究者应充分尊重研究对象的意愿和选择,避免因学术研究产生伤害。同时,处理教育史料要忠实公正,“史家第一件道德,莫过于忠实”,即“对于所叙述的史迹,纯采客观的态度,不丝毫参以自己意见”[15]111。讲求“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24],不恣情,不使气,实现秉笔直书,以还原教育历史真相。
责任担当,即教育史研究者通过学术研究、参与或指导教育实践等方式承担发挥教育史学科的实践价值,促进教育发展的责任品质。年鉴派学者认为,“提出问题是所有史学研究的开端和终结,没有问题便没有史学”[10]10。研究教育史问题需从服务教育的视角出发,注重其价值性,以引起对现实教育问题的关注,通过对古今同异的描绘,探究当前教育问题的根源所在。教育改革要求注重教育史学的现实性、应用性,重在发挥对当代教育实践的借鉴与指导作用。教育史研究者应以历史的视角看待当今的教育问题,并与全部教育生活之源泉——现实保持不断接触,以洞察问题根源。近年来,随着全球史及思想史的兴起,研究者应关注“观念在各民族中和跨民族间的传播与碰撞”[25]。为此,教育史研究者应竭力发掘本民族特色,如,以学为本的教育特点、因材施教的教育方法、语言表达的间接性、思维模式的缄默性等,在解释、理解和研究教育历史时,主动传承此种特色,形成相应的概念、理论与框架,进而生长出能够独立于国际教育史之林的、有中国特色的教育史体系。
“德”囊括三维:人格修养,为教育史撰写做好铺垫;职业素养,为生涯发展保驾护航;责任素养,为民族教育发展提供借鉴。
五、非“道”无以适天下育人之用
教育史研究者之“道”,指研究者将探究教育发展领域的总趋势与根本规律视为其价值追寻的品质。“古之所谓良史者,其明必足以周万事之理,其道必足以适天下之用,其智必足以通难知之意,其文必足以发难显之情,然后其任可得而称也。”[26]良史标准由“三长”引申为四点:明、道、智、文。其中明、智、文相当于识、学、才,而“道”则要求“以适天下之用”。所谓常道即“通人物,达四海,塞天地,亘古今,无有乎弗具,无有乎弗同,无有乎或变者”[27]。“道”的素养内涵包括:理解力,把握人类教育意识;觉悟力,体察以教育史明育人之道的境界。
“理解”是教育史研究的指路明灯。理解力即对教育史中的个人情感与命运、人类生活与意识、教育发展与历史普遍过程的关系的同理能力。教育史学科是一门人文学科,蕴含思想精神和情感态度等人文价值,这些需要通过研究者的理解力获得,而唯有对这些内容加以理解,才能真正描绘教育史实写真图,探究个人与教育的关系,实现对人类教育意识的理解,从而培养一种对过去(教育)现象的全面理解能力。[28]教育史研究的目的之一是探究人类的教育意识,通过展现教育对个体发展的作用,启发教育实践,从而帮助个体实现其全面发展。为此,教育史研究者应培养其同理能力,实现对人类教育意识的全面理解。
觉悟即教育史研究者对具体教育历史、思想等进行抽象思维,从中觉悟教育发展规律,理解教育与天、人之间的关系,以达成通过教育史明育人之道的价值追寻。这种反思与觉悟所形成的研究发现赋予教育史研究者持久动力,提醒研究者不能“只满足于研究形而下的器,而不肯去思考自己事先所假定的形而上的道”[17]36。“盖欲为良史者,当慎辨于天人之际,尽其天而不益以人也。”[7]261“‘天’是一个形而上学的哲学概念,它意指超越历史事实之上的历史演进的趋势和法则——天道。”对天道的求索,“应该自觉以形下之器—史—对形上之道—天—进行提炼和升华”[29],从而形成教育史学家以教育史明教育之道的体悟力和觉解力。唯有基于对数千年来教育历史发展的回顾和对形而上的教育之道的思索,教育史学家才能最终实现对教育对象——人的向善性及其全面发展之道的探究、觉察和体悟,从而影响教育实践。
“道”孕育于双翼之中:通过理解力,觉解人与教育间的关系;基于反思与觉悟,达成以教育史之实明育人之道的目的。
六、教育史研究者五维素养的结构关系
皮尔·卡斯巴(Pierre Caspard)认为,“什么是好的教育史研究,其标准是:符合被国内或国际史学家所认同的标准;有创新,无赘言;能回答重要的和持久的社会问题”[30]。那么,什么样的研究者能称之为卓越的教育史研究者呢?笔者认为应具备上述五维素养:才、学、识、德、道。五维素养之间的关系如何呢?冯福京指出:“擅三者之长”:学以通古今之世变;识以明事理之精微;才以措褒贬之笔削。[31]还应增加两点:德以立学术之丛林,道以适天下育人之用。五维素养间顺序又如何?“各人主张不同:子元以才为先,学次之,识又次之;实斋又添德于才、学、识之后。”梁启超则提出“先史德,次史学,又次史识,最后才说到史才”[15]110。本研究认为,教育史研究者素养的顺序为:才、学、识、德、道,五者相辅相成,是教育史研究者素养的有机组成部分。
若将教育史研究者的素养喻作中国传统建筑,那么“才”是木,中国古建筑多为木制建筑,木是其主要原料,无木则无传统中国建筑。“学”为建筑之柱——顶梁柱,唯有通过持之以恒的学习、习练和思考才能支撑起宽敞明亮的室内空间。“识”为传统建筑的图样,图样之意涵可用《易经》之理喻之。也就是说,传统建筑中蕴含的文化哲理、人文气息及其天人合一的外貌特征直接来源于图样,而图样的精髓则源自古代工匠心中的《易经》之精义。同样,识之素养也是教育史研究者的精髓所在。“德”为基,初阶之德提供牢固平台,高阶之德稳固建筑重心,使教育史研究者有稳固的根基。“道”为灯光,灯光使得优美的建筑轮廓在夜晚展现其风采,照亮传统建筑当中行人的路,教育史研究所探究的蕴含于复杂多样的教育史实当中的教育之道,同样可以照亮部分处于黑夜中的教育实践者,导引教育实践者的前行方向。
“才”为木。主要为天赋成分,教育史研究者之才具有先天性、基础性和易获取性,为培养其他四类素养提供前提和条件。“学”为柱。该素养后天形成,在五维素养间起承前启后作用,是教育史研究者走上专业工作的必经之路。“识”为图。该素养具有较大的个体差异性,体现研究者的思维品质和心智模式,含理性思维、想象力和创新性思维,是在教育史研究者之才与学累积基础上的点睛,容理性与感性于一体,可见微知著。是更高级别的思维方式,也是教育史研究者高下之别的关键所在,彰显着研究者之德与道的智慧。“德”为基。该素养有初阶(行为规范)和高阶(内心修养)两个层次,含人格修养、职业素养与责任担当,务在求真、求善、求正,是进行教育史研究的出发点和保障。教育史研究者之德的素养为其才、学、识等素养价值的发挥提供保障与动力。“道”为灯。该素养孕育教育史研究者的最终价值追寻,即普遍的人类教育发展之道,含理解力和觉悟力。对育人之道的觉悟,使得蕴含于复杂教育历史中的教育发展规律得以明晰,形成可适天下育人之用的规律与法则。
概言之,具备上述五维素养的教育史研究者似一座典雅的中国传统建筑,透过建筑物的窗口,人们可以欣赏波澜起伏的教育发展史;通过建筑里的镜子,人们得以总结前人教育探索的智慧与教训,从而坚持现今教育实践中的优点,反思并完善当下教育实践中的不足。
(致谢:感谢华东师范大学杜成宪教授对本文提供的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