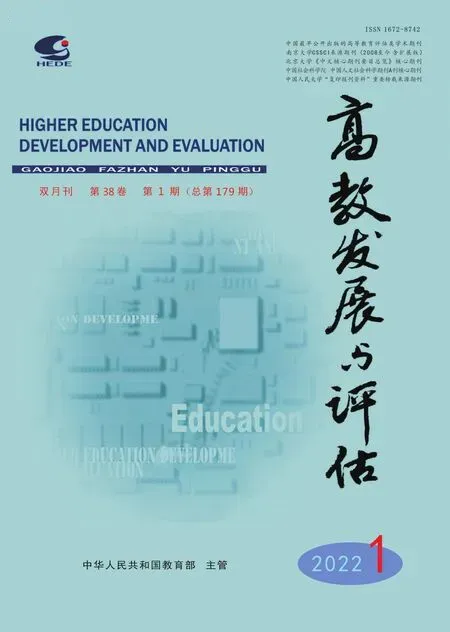师道传承与教育人文的守望
——读董云川教授《复杂时代的简单活法》有感
2022-02-26叶文梓
叶文梓
(深圳大学 教师发展学院,广东 深圳518060)
一
生命,是一代代延续的;社会和历史,也是一代代延续的。年长的人,经历了一些世事,有了些生活经验,甚至学了些文化,就难免生出人生这样或那样的感慨,也就禁不住地要对年轻人说道说道。经过几千年的演化,时至今日,年长者的说和年轻人的听,似乎早已成了生命的本性,也似乎早已成了我们文化的传统。
然而,在我看来,不管是年长人的说,还是年轻人的听,都是非常复杂而且为难的。就年长者的说而言,说什么?怎么说?是否说出了微言大义?是否适合年轻人的口味?是否有益于年轻人?等等。就年轻人的听而言,听谁说?听什么?怎么听?听了以后怎么办?等等。诸如此类问题,无疑既不简单,也不轻松。
然而,不简单也罢,不轻松也罢,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代人与一代人之间,总是要有人说的,也总是要有人听的。否则,生命怎么延续呢?文化怎么传承呢?因而,这说和听,确实不只是两个人的事,不只是两代人的事,还真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大事件。
二
云川兄告诉我,本书“作者简介”前无古人:不见名头,不见光环,卸下盔甲,回归本源,唯独余下一个质朴的老师封号和一个自我调侃的教书匠形象。长者对年轻人的言说,有不同的立场、角色和站位。比如,父母对孩子的言说,领导对年轻下属的言说,或者一个成功者、或者一个过来人对年轻人的言说,等等。然而,我是理解云川兄的,他是简单且坚定地站在教师立场对弟子言说,并且把这种言说看作是自己作为教师的责任和本份的。
教师对弟子的言说,以及弟子对老师的倾听,在历史不同时期有不同的样态。更远古的且不去说,单从孟子那时开始。孟子曾言:“人之患,在好为人师。”动不动就想当别人的老师,其实是讨人嫌的,对自己也未必是好事。于是魏晋之后,人们就不太愿意拜人为师了。然而,假如人们都不想做老师,也都不愿意向老师学,其后果是很严重的。韩愈曾对此大发感慨:“嗟乎!师道之不传也久矣!欲人之无惑也难矣!古之圣人,其出人也远矣,犹且从师而问焉;今之众人,其下圣人也亦远矣,而耻学于师。是故圣益圣,愚益愚。圣人之所以为圣人,愚人之所以为愚,其皆出于此乎。”[1]20然而,韩愈“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者也”和“道之所存,师之所存”的为师理念,以及他那一腔好学向善、崇文弘道的宏愿,并没有为世人所理解。其后来的处境也艰难,其结局也可叹。柳宗元发现,韩愈作《师说》,不顾流俗,收召后学,抗颜而为师,结果却是“世果群怪聚骂,指目牵引,而增与为言词。愈以是得狂名,居长安,炊不暇熟,又挈挈而东,如是者数矣。”[1]261也许因此缘故吧,柳宗元对韦中立要拜他为师坚辞不受。不过,柳宗元虽不受为师之名,却也行了为师之实。就作文与为人而言,他对韦中立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这种风范,可从他《答韦中立论师道书》中真切地感受到。与受人嘲弄而仍力倡师道,以及不为师名而为师实相伴随的,是“朝闻道,夕可死”的尊师重道的传统。杨时和游酢程门立雪的典故就生动地诠释了弟子对先生的恭敬。宋濂在《送东阳马生序》中也讲述了自己求学的恭敬之情:“先达德隆望尊,门人弟子填其室,未尝稍降辞色。余立侍左右,援疑质理,俯身倾耳以请;或遇其叱咄,色愈恭,礼愈至,不敢出一言以复;俟其欣悦,则又请焉。”我有时想,也许正是因了那力倡师道、诚心向学、君子人格的传统,中华民族的文化血脉才能够传续几千年而不断。甚至扩大一点说,也正是因了这样的传统,才形成了中华民族所特有的道统与学统。
近现代以来,中华民族陷入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困境,处身于生死存亡之际,也历经欧风美雨的变幻与无常。这一时期,围绕救亡图存这一艰难的时代主题,中国社会似乎成了一个大的试验场,各种各样的思潮与各式各样的教师不断地涌现出来,此起彼伏,激荡不已。然而,就教师的言说而言,他们却有着一样的目标、一样的情怀、一样的气质,在人类文化与教育发展过程中成为一道独特而亮丽的风景线。1917年,蔡元培先生留欧归来长于北大,在其就职演说中即告诫北大学生: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并以三事为诸君告:一曰抱定宗旨,即入大学者本为研究高深学问,而非为做官与致富;二曰砥砺德行,即学生要束身自爱,以身作则,不同乎流俗,不合乎污世;三曰敬爱师友,以诚相待,敬礼有加。蔡先生所言说的,是大学的精神,是大学生的责任与使命。1927年,陶行知先生在晓庄师范开学典礼上与他的学生这样说:“今天是我们乡村师范开学的日子,我们没有教室,没有礼堂。但我们的学校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我们要以宇宙为学校,奉万物作宗师。蓝色的天是我们的屋顶,灿烂的大地是我们的屋基。我们在这伟大的学校,可以得着丰富的教育……”。[2]陶先生所言说的,是希望晓庄师范的同学们为做一大事而来,到乡村去做乡村教育,以现代化的教育来促进国家和民族的现代化。1940年,西南联大吴宓教授为其毕业学生送别的留言是马修·阿诺德论述“甜蜜与光明”部分中的三行原文,其意为:“对完美的追求就是对甜蜜和光明的追求。”“文化所能望见的要比机械深远得多,文化憎恶仇恨;文化具有一种伟大的热情,这就是甜蜜和光明的热情。它甚至还有更伟大的热情!——使甜蜜和光明在世上盛行。”“我们必须为甜蜜和光明而工作。”[3]305吴先生所言说的,就是坚定苦难中的学生对未来的信心和对光明的希望。更值得我们关注的是,这一时期的教师们,不只是以文字言说,更以自己的行为向学生言说。1915年,苏步青先生以优异成绩考入设立在温州的浙江省第十中学。他数学成绩非常好。当时既为校长也兼教平面几何的洪颜远先生,对他非常赞赏。然而,不久之后,洪先生就调到教育部工作了。临走时,他告诉苏步青:“我要调离学校,到教育部去工作。你毕业后可到日本学习,我一定帮助你。”苏步青中学毕业后,想起洪校长的话,便写信向洪校长求助。令他没想到的是,不久后他便收到了洪校长寄给他的200块银元。由此他才得以于1917年秋到日本留学。而就在苏步青从上海赴日本留学之际,洪校长给他寄来了临别赠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要为中华富强而奋发读书。”[3]145-146匡互生先生是“五四”运动中火烧赵家楼的勇士,在当年春晖中学任舍务主任。有一次,几个学生在学校中聚赌,后经学校商量,并由学生协治会决定罚犯错误的学生写大字和打扫学生宿舍卫生一个月。身为舍务主任的匡先生,则认为学生犯错与自己监管不力有关,因而自罚一个月的薪俸,并每天与学生一起做劳务。那时的教师,不管他信仰的是什么,但自有一种思想的信仰;自有一种学贯中西的文化气象与格局;自有一种重视人格养成和信仰爱的教育的责任与使命;自有一种在苦难之中的乐观与通达。不管在学问、理想、人格等大的方面,还是在日常起居饮食等小的具体的方面,这些教师都是捧着一颗心来,真心地待学生,真切地关怀学生,也是严格、务实地要求与指导学生。我常想,这一时期教师们的言说,其实是一个苦难民族的思想启蒙与自我觉醒的呼号;其实是为求生存求未来而上下求索的相互激励;也是在无数的绝望中对无限希望的无尽的讴歌。我似乎至今还能听得见这一时期教师们言说的声音,也似乎还能看得见他们慈祥而微笑的样子。
时至今日,我们的民族,我们的国家和社会早已融入人类现代化的时代洪流之中,并取得了伟大成就。中华民族正以昂扬的步伐走在伟大复兴的征途上。我们的教育,也正在从教育大国迈向教育强国。然而,就教师的言说而言,现代科技的迅猛发展,市场化的全面确立,全球化的反反复复,我国独生子女政策的实施,等等,无不带来了深刻的挑战。事实上,处今日之际,作为教师如何对学生言说,似乎成了一个越来越大的问题。越来越多的教师不想说,越来越多的学生不愿听,师生之间彼此冷漠。也有相当一部分教师,不想付出思想,不想付出情感,其实也没有多少思想和情感,于是只在你好我好大家好中敷衍了事。也有一部分教师确实为难:说轻了,学生听不懂;说重了,学生受不了。也有一部分教师,虽然在言说,但不是作为教师在言说,而是作为官员在言说,作为老板在言说。这是很普遍的。云川兄几十年来,一直作为一个质朴的教师在言说。一个质朴的教师的言说,需具备三个“真”标准:一要有真性情。言说不是应付,不是表演,而是以自我的真性情对人对己,以自我的真性情对学问、对工作、对生活。这样的言说,发乎心、顺乎情、至于理、成于事与人。二要有真本事。质朴教师的言说,不吹牛,不虚妄,实实在在,就像当年夏丏尊先生形容李叔同先生一样:“李先生教图画、音乐,学生对图画、音乐,看得比国文、数学等更重。这是有人格作背景的缘故。因为他教图画、音乐,而他懂得的不仅是图画、音乐;他的诗文比国文先生的更好,他的书法比习字先生的更好,他的英文比英文先生的更好……这好比一尊佛像,有后光,故能令人敬仰。”[3]276云川兄论教育,常常将教育摆在社会的大背景中思考,将儒道释融合在一起,谈社会中的教育、文化中的教育、世界中的教育,实质归于人生教育。三要有真实效。质朴教师的言说,直抵学生的心底。学生听了这样的言说,无论在知识上、在学问上、在性情上、在行为上、在人格上都会有所收获、有所变化、有所进步,都能向着未来更光明的地方前行。云川兄作为一个质朴教师的言说,绝非作为经师在言说,而是作为人师在言说。因此,云川兄写给弟子的新年寄语,实乃人生之寄语。他是以自我的真性情激发弟子的真性情,以自我的人生智慧启迪弟子的人生智慧,以自我的文化自觉培育弟子的文化自觉。他不只是希望弟子成为更好的自己,更希望弟子能够传承中华民族的文化血脉,担负起我们生活于其中的时代的责任,让自己活好,更让别人活好,生生不息,携手共创更幸福的生活和更美好的未来。这样的言说,应该是我们时代师道的传承和教育人文的守望。
三
云川兄的言说,不是平常时光的言说,而是新年辞旧迎新之际的言说;不是日常的一般言说,而是寄语性的言说。新年,是时光流淌中的重要节点。因而,新年的寄语也自然是庄重而正式的。新年寄语,是对过去时光的回味,是对未来时光的期待,是对一切亲爱的人和事的真切祝福,更是关乎前途与命运的反思和行动。云川兄的新年寄语,不是给别人的,而是给自己弟子的。云川兄很少称“学生”,喜欢称“弟子”,或者称“徒儿们”。弟子是不同于学生的,弟子一定是学生,但学生不一定是弟子。至于弟子与徒儿,在云川兄语境中应该是等同的。而他每每说到弟子或徒儿的时候,眼睛总会闪出不一样的光芒,嘴角也会情不自禁的露出会心的微笑。这光芒与微笑,似是自豪,似是骄傲,更是意味深长的狡狤。由此,他给弟子写新年寄语,是极其认真、极其用心的,也是极其幽默而风趣的。他将这近十年来每年元旦致研究生的新年寄语以及研究生的对话回应汇集成书,取名为《复杂时代的简单活法》。我想,这不只是他对新年寄语的简单纪念,更不是他对自我作为董老的陶醉,而是在这个暄嚣尘上的世界里让自我再一次清静,让自我与众徒儿们再一次的省察、反思与再出发。这省察与反思,关于大学、关于生活、关于人生、关于时代、关于世界、关于未来……
《复杂时代的简单活法》内容包括:2012,末世新年的寄语;2013,不得不说的啰嗦话;2014,现象与真相;2015,千万别失联;2016,做一个有格调的人;2017,我真的不想说教,你完全可以不听;2018,千万别成为时间的笑话;2019,活法;2020,在平庸里打趣;2021,渊深鱼自乐。从这些题目来看,没有高大上,更没有假大空,就像一盘盘的家常菜,就像一天天的平常日子,有的是生活的情趣和日子的味道。云川兄对本书的定位:师父对弟子的棒喝、学者致教育的真言、朋友与至交的神聊、凡人在世间的梦呓。这是极为精准的。《中庸》有言:道不远人,人之为道而远人,不可以为道。道就在人伦日用之间。越是身边具体的,越是简单的,越是质朴的,就越是包含着天地人间的至理。
“复杂时代的简单活法”,这个书名精准地突出了新年寄语的内容与主题。每个人只有一个人生,这个人生是用来干什么的,当下的人们似乎越来越困惑了。近些年来,我周围一些朋友及其孩子,患忧郁症的越来越多,年龄也越来越小。我们的时代怎么啦?其实,我们身处的时代,是一个以追求美好生活为主题的新时代。云川兄慧心独存,早在2013年的新年寄语中就坚定地告诫徒儿们:“一息尚存,从吾所好!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才是天大的事!奉劝大家,新纪元纵然又是千万年,但摊到个人还是只有二万多天,于是,请抓紧时间,用智慧的心灵去感知你所喜欢的生活方式,用加倍的努力去为你选择的生活方式赢得更大的自主权,把最多的时间消耗在你认为值得的事务之中——每个人都不同,各有各的精彩!”人生是为做一大事而来的。这大事,不是别的,就是生活,你的生活、我的生活、中国人的生活、天下人的生活。凡是与生活无关的,都不是大事,而与生活相关的,则没有小事。我因此主张,我们时代的教育应当从成功教育转向幸福教育,尤其要重构教育与生活的关系,要坚守“生活成就教育,教育创新生活”的基本理念,要让我们的弟子们和学生们,要让这个时代的年轻一代,因为接受了教育而创造出更加美好更加幸福的生活。在这种意义上,云川兄是新时代生活教育的倡导者、实践者与创新者。
这个书名把我们时代的迷误刻画出来了。生活其实需要的不多,而世间人想要的却是太多太多。我们有了小房子就想着要大房子;有了普通车子却想着要更豪华的车子;有了一定数目的存款却想要更大数目的存款……于是,滚滚红尘,执念无限,欲望无边,本是简简单单的生活硬是搞得非常的复杂。于是乎,就教育而言,当今教授越来越多,而学者越来越少;研究生越来越多,而研究者越来越少!也许正因为这样的众生相,余世维才说:人生最重要的修炼就是“像那个样子!”然而,我们周边的很多人也确是很在乎“像那个样子”的,但遗憾的是,“像那个样子”是装出来的,而不是基于本性修炼出来的。为了装出“像那个样子”,把本已复杂的搞得更加复杂了。云川兄是解构的高手,他善于把那虚的、假的、作伪的,一层层地解构出来,在不经意的嘻嘻哈哈中还原其真相,最终让那一切的假象显露无遗而无可逃遁。
这个书名把生活的切实路径给我们指示出来了。生活的切实路径无它,就是简单生活。所谓简单生活,是生活不断展开的过程,是人生的无上智慧,是一种朴素的生活方式。生活源于心,每个人都生活在自己的状态里。心的样子决定了生活的样子。爱默生曾指出:人的心灵就是未来的万能君主,也是神秘而又无可侵犯的思想源泉。他坚信:听从内心的声音,世界会围着你转。然而,何为心?人们普遍地执着于人心与道心、天理与人欲。阳明先生指出,人心若能守正即为道心,道心不能守正即为人心。道心与人心,并非两颗心,而是一颗心的两种形态。心即理,循理而动,即为本心或是真心。[4]因此,简单生活并不是压抑的生活,并不是固定静止的生活,并不是重复的生活。就人生而言,人之初生,不会说话,不会走路,更不会复杂的思维和行为。人,只是带着许多可能性来到人世间的。当然,人与人的这些可能性、这些天赋,都是各不相同的。在人生展开的过程中,简单生活就是遵循本性的真实生活。简单生活,意味着每一个阶段做每一阶段要做的事,像不同的季节就开不同的花一样。人生的每一个阶段都是精彩的,关键是要能够展示出不同阶段的精彩,并能够欣赏不同阶段的精彩。简单生活,还有重要的意蕴,就是要把每个生命所固有的各种各样的可能性激发出来,实现出来。一切的压抑与限制,都是扭曲,都是变形,都不是真实的。不真实的就是复杂的,真实的就是简单的。顺其本性的真实生活,就是简单生活。对人生而言,惟有简单生活,才能保存自己、发展自己、超越自己、成就自己。那么,如何通向简单生活呢?简单生活的基本方式就是知行合一。“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无知之行是冥行妄作,无行之知只是伪知。知不离行,行不离知,知行合一。对大学的学者而言,知行合一,意味着不要在项目、职称、基地、中心等各种称谓中迷失了自己,意味着守护大学之正道,回归自我之本性。云川兄是知行合一的倡导者与力行者,他所走出的为学之路、为师之路,乃至于他的生活之路,不一定是我们所要模仿的,也绝不可能是我们所能模仿的,但一定是我们所不能不重视而给予我们无限启示的。因为,云川兄上下求索的是一条回归自我本性之路,是一条回归大学本性之路,是一条回归生活本性之路,也是一条知行合一的简单生活之路。我看见,云川兄一直走在这样的路上。
四
我相信,一本书与一个人其实是一样的,自有其天赋与气质,自有其命运与前途。现在,云川兄新书终于付梓了,还邀了很多朋友开了一个低调而奢华的发布会。这也算是为这一新书举办了一场庆生会。当然,这也意味着,作为一本书的命运也从此开始了。
在我们这样的时代,有很多书,很快地走红,也很快地消失。甚至消失得比它走红还来得快。当然,也有另外一种情形,那就是在作者生前沉默无声,而在其身后却大红大紫。叔本华、尼采的很多著作就是这样的命运。
对于云川兄的这本书,我是既有疑惑,又充满信心的。我疑惑的是,复杂时代的简单活法,现在能在多大程度上可行呢?现在的人们,不管年长的还是年轻的,正如鲁迅所言,人心很古,也人心不古,但多数还是人心很古的。要是人心很古,在这复杂的时代能够简单生活吗?我是禁不住疑惑的。而我充满信心的是,这本书一定不会寂寞。因为,这是一位可敬的老师,带着一群可爱的弟子,对大学精神的守护,以及对为学、为师、为人之道的真心探索。这本书,记录着他们守护的坚定,闪烁着他们探索的智慧,也宣告着他们的主张。正如新书发布会上大家所言,不管你是成长期的青年学子,还是困顿期的成年人,或是成熟期的过来人,这是一本三代人都可以看的好书,无论什么人皆可以在其中发现自己的身影——青年人发现路径,看见曙光,回答:世界看起来如此,知道什么是假象;中年人实现转型,寻找出最合适的活法,回答:世界看起来如此,分清什么是实情;过来人会心一笑,得到慰藉,回答:世界原来如此,明了什么才是真相!
我读云川兄的这十年寄语,也给自己写一句寄语:知行合一,简单生活,无悔教育与今生。与君共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