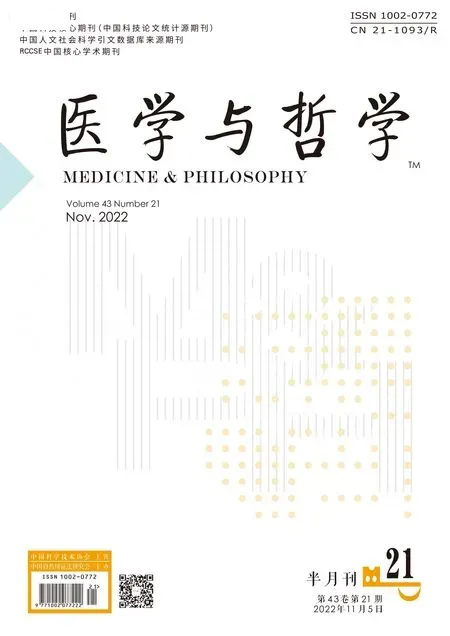新冠疫情相关压力对青少年心理健康损害的研究进展*
2022-02-26吕小康张涵玉
王 丛 吕小康 张涵玉
由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以下简称“新冠”)引发的全球健康危机的破坏力和持续性超出了多数人的预期。日常生活的剧变、社会互动的缺失、被隔离的歧视感知、对感染和患病的恐惧等多重因素交互耦合,勾勒出疫情期间个体或群体所面临的压力相关的心理健康风险图景。已有研究确认了新冠疫情相关压力的存在,甚至可引发“新冠疫情压力综合征”[1]。近期大量涌现的研究报道了新冠疫情相关压力(以下简称“疫情相关压力”)对心理健康的影响,包括睡眠问题、焦虑、抑郁、创伤后应激障碍(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PTSD)、自杀意念的增加[2-6]以及新冠病毒恐惧症的出现[7]。疫情相关压力的影响不仅会波及到一般人群,更会影响特定脆弱群体的心理健康,而青少年更是诸多脆弱群体中的“重灾区”。一些人能够快速地从压力环境中“回弹”,但青少年这一脆弱性群体却有可能遭受重创。因此,梳理疫情相关压力对青少年心理健康损害的国内外研究进展,鉴别青少年面临的疫情相关压力源,可为完善有针对性的心理干预措施、制定行之有效的公共卫生政策提供新的见解和思路。
1 疫情相关压力对青少年心理健康的损害
1.1 青少年心理健康损害的具体表现
疫情相关压力使得全球范围内青少年焦虑、抑郁、PTSD 和药物滥用的患病率以及严重程度都在增加[8]。国外研究多以横断评估、在线调查和自我报告的形式呈现疫情暴发初期(2020 年3 月~2020 年5 月)青少年焦虑、抑郁的患病率及严重程度。例如,在西班牙大学生中,分别有21%、34%和28%的被调查者报告了压力的增加以及由压力导致的中度至极重度的焦虑、抑郁[9]。美国71%的被调查大学生报告压力和焦虑的增加[10]。孟加拉国超过80%的被调查大学生表现出不同形式的轻度至重度的抑郁和焦虑症状[11]。
也有研究试图探寻与疫情相关压力有关的自杀意念的变化,但所得结论不尽相同。如法国被调查大学生的自杀意念达到11%[12]。然而日本的一项研究却发现,2020 年3 月~2020 年5 月,20 岁以下人群的月自杀率在学校停课期间略有下降并且与前两年没有显著差异[13]。加拿大被调查青少年的自杀意念低于6%。原因在于疫情期间有更多时间与家人在一起,参加体育锻炼或投身于业余爱好,这些变化反而对部分青少年产生了积极影响[14]。
少数国外学者对疫情相关压力的水平及其引发的认知与情绪问题开展了纵向调查。例如,苏黎世的一项社会发展项目对疫情前和疫情期间的大学生压力水平进行了跟踪评估,发现大学生在疫情期间的压力水平明显增加[15]。美国的一项纵向研究表明,对比2020 年春季学期,被调查大学生在疫情期间(2020 年春季学期结束时)的注意力问题呈现出恶化趋势[16]。荷兰的一项研究对疫情防控前和防控期间的大学生进行了生态学跟踪调查,发现大学生在防控期间的情绪稳定状态显著降低,并且之前患有精神疾病的大学生在情绪稳态方面表现得更差,这与能够改善情绪的活动参与度减少有关[17]。对澳大利亚青少年的纵向研究表明,疫情期间的青少年抑郁和焦虑症状显著增加以及生活满意度下降[5]。目前,此类针对疫情相关压力引发的青少年心理健康状况变化的纵向比较性研究还较为稀缺。
国内研究大多拘泥于自我报告式的横断研究,90%的被调查青少年报告他们的焦虑和抑郁症状在疫情期间是常见的[18],25%的被调查大学生报告有轻度至中度的焦虑[3]。除聚焦于焦虑、抑郁的患病率,也有国内研究关注大学生躯体症状,发现大学生关注的躯体症状问题中35%与疫情相关压力有关[19]。
一些国内研究者尝试验证疫情相关压力对心理健康负面结果的传导路径。研究发现,在控制了性别、地区后,疫情期间学生的心理应激反应正向预测攻击性行为,而消极应对方式在心理应激反应与攻击性行为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且这种间接效应受到情绪管理能力的调节[20]。此类研究揭示了应对疫情相关压力的保护因素和个体特征因素,如研究发现心理灵活性在大学生疫情压力感知与抑郁之间起中介作用,且内控型大学生的心理灵活性更容易受到疫情压力感知的影响[21];疫情相关压力体验对急性应激障碍的影响受到大学生的内部因素(心理韧性和适应性应对策略)和人际因素(社会支持)的调节[22],为此,这些研究为制定有针对性的干预措施提供了有价值的实证依据。
1.2 青少年心理反应的阶段性变化
对青少年心理治疗个案的临床观察发现,在疫情的不同阶段,青少年对疫情相关压力的心理反应呈现以下阶段性变化[23]:(1)集体心理韧性生成阶段。疫情初期,为了响应居家隔离政策,一种“我们能做到”的集体心理韧性逐渐生成,青少年在居家上网课的过程中,重拾旧的或发展新的业余爱好来应对压力。(2)“坚定决心”阶段。青少年开始树立“我们必须渡过难关”的决心。在这一阶段,青少年和大学生群体不得不直面网课适应困难、居家办公实习模式的适应困难、家庭收入波动以及为避感染而导致的社交距离和人际关系疏离等现实问题的冲击。(3)“更大的焦虑和疑虑”阶段。这一阶段的典型心态是“我们开始对这种生活状态感到厌倦了”。疫情相关压力对生活的多重影响逐步凸显,而青少年经常被这些影响产生的不耐烦和沮丧情绪所困扰,他们的心路历程阶段性变化映射出疫情相关压力背后的心理动力学机制。
同时,临床观察揭示的青少年心路历程在一项对压力感知水平的追踪研究中也得到了印证。总体来说,随着疫情的持续,个体的焦虑水平呈显著上升趋势,心理健康状况呈显著下降趋势[24]。与此类似,我国大学生在疫情期间的心理波动也经历了由稳定到恐慌、由信任到疑惧、由平和到焦虑、由充实到空虚的嬗变历程[25]。这种动态变化与疫情的持续时间、个体持续应对疫情相关压力以及持续压力调节导致的非稳态负荷有关。当然,并非所有青少年个体对疫情相关压力的心理反应都会遵循同质性的轨迹,由于易感性和心理韧性的差异,不同个体精神苦痛的波动轨迹在疫情的不同阶段呈现出极大的多样性。值得注意的是,一种压力源的影响辐射到了疫情的所有阶段,即对感染与患病的恐惧。
2 青少年疫情相关压力源与易感性因素
2.1 对感染和患病的恐惧
作为新冠疫情压力综合征的核心特征,对感染和患病的恐惧增加了意大利被调查大学生的PTSD 症状[26]。我国约23%的被调查青少年在近30 天的防疫封控后出现抑郁和焦虑症状,这与他们对疫情的不乐观预期和害怕被感染有关[27]。无论真正地暴露于新冠病毒的客观风险或是对新冠病毒的主观恐惧都预示着个体PTSD 和焦虑水平的升高[28]。一种情况是个体真正暴露于病毒感染的威胁,如所在社区有人感染、自身有疑似症状等,这一群体的心理症状均值均显著高于对照群体[29]。而更多的情况是个体对病毒“想象中”的主观恐惧,这种恐惧常源自于媒体表征的“助燃剂”效应,如媒体对累计确诊人数的报道、网络谣言、对疫情不准确的甚至是煽动性的报道等。个体或群体通过媒体对新冠病毒的表征间接感知到感染的风险,甚至仅阅读或听到新冠肺炎严重性和传染性的相关信息便可成为最常见的压力源之一[30]。
2.2 日常生活方式的剧变
疫情对日常生活方式的冲击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1)体育活动的减少与电子产品使用频率的增加。对我国青少年的横断研究报告了体育活动的减少和电子产品使用时间的增加[31]。缺乏体育锻炼增加了抑郁和焦虑的风险[32],而疫情期间智能手机和网络成瘾与青少年抑郁症呈显著正相关[18]。(2)睡眠问题,主要表现为睡眠中断[10]和睡眠时间的增加[31]。不仅如此,体验到较高水平压力的人更容易做关于监禁、失败、无助、焦虑、战争、分离、疾病、死亡、新冠病毒等特定主题的噩梦[4]。(3)网课学习的适应困难与对学业、成绩的担忧。对美国大学生的研究发现,对学业、成绩的担忧是疫情相关的压力源之一[10]。超过80%的孟加拉国被调查大学生表现出不同形式的轻度至重度的抑郁和焦虑症状,这些症状与对学术活动的担忧有关[11]。疫情期间我国青少年的学习焦虑水平显著上升[33],担心疫情对学业的延误也是导致我国大学生焦虑的主要因素[34]。网课学习的适应困难以及由此引发的与父母冲突的增加预示着青少年心理健康状况可能会变得更差[5]。
2.3 防控隔离与社会孤立
根据压力应对理论,由于歧视感知、社交距离和社会孤立等,防控隔离这一外部事件可视为一种启动应对反应的压力源[35]。与未隔离的大学生相比,被隔离的大学生的抑郁症状、自伤行为、自杀意念和情绪困扰的患病率不断上升。这部分大学生的心理问题很大程度上源于被隔离的歧视感知。并且隔离的时间越长,感知到的压力便越强[36],而且这种心理影响可能在数月或数年后延迟出现。更严峻的是,保持社交距离更容易让青少年体验到社会孤立,而疫情期间的社会孤立直接加剧了青少年的PTSD,限制了青少年创伤后成长的实现[37]。当然,保持社交距离的动机类型与心理问题的症状有关。由于害怕自身染病或避免被他人评判而产生的社交距离与较高水平的焦虑有关。然而,本身喜欢宅在家里而产生的社交距离却与较少的焦虑和抑郁症状有关[38]。
2.4 社会支持系统遭到破坏
疫情期间青少年典型的社会支持系统遭到破坏,而社会支持(包括实际获得的社会支持与感知到的社会支持)的减少是疫情期间个体情绪困扰的重要预测因素。例如,感知到的社会支持水平较低的我国青少年报告了较高水平的焦虑和抑郁症状[39]。此外,作为社会支持系统的微观层面,社会关系,尤其是与四位亲密他人(母亲、父亲、兄弟姐妹和最好的朋友)的积极关系或消极关系会与其他疫情相关压力源产生交互作用,从而对青少年的适应起到有利或有害的影响[8]。如对北京市某大学的调查发现,疫情期间没有知心好友的大学生在人际关系敏感、抑郁和恐怖方面的得分均显著高于有知心好友的学生[40]。而在所有的亲密关系中,父母支持的下降对青少年总体心理健康问题的负面影响最大[41]。
2.5 个体易感性与社会脆弱性因素
除人格特质、不良童年经历、应对方式等个体易感性因素,疫情相关压力对心理健康的损害程度还会受到年龄、性别、身心健康状况、社会经济地位等社会脆弱性因素的影响。例如,一项元分析归纳了疫情期间焦虑和抑郁的高风险因素:年龄小于35 岁、女性、生活在农村地区、社会经济地位较低、感染风险较高、社交媒体使用时间较长,曾患有身体或心理疾病[42]。事实上,这方面已有不少与疫情相关压力有关的、以健康不平等为主题的心理学研究或大型社会调查。有研究认为,年龄在10 岁~24 岁或是学生群体中的一员是遭受疫情相关苦痛的风险因素[43]。高中生和女性受到的危害程度更大。对比中小学生,我国高中生有着更高的精神病理症状水平以及更低的生活满意度水平[44]。对比我国的企业员工,学生尤其是高中生的应激、焦虑反应更严重。且女学生有明显应激反应的比例要高于男学生[45]。此外,对2020 年武汉疫情暴发期间的居民生活状况的调查也发现,女性,尤其是30 岁以下年轻女性的抑郁程度显著高于男性[46]。
从素质-应激理论视角分析,疫情相关压力有可能激活某一种素质或易感性,并将潜在的易感性转化为现实存在的精神病理症状。但某一精神病理症状的出现取决于个体对该疾病的易感性是否超过了阈值。能否超过这一阈值则取决于压力源的严重程度、素质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及素质和压力间的综合作用。因此,作为一种极端环境压力,疫情相关压力将会与个体易感性因素和社会脆弱性因素交互作用,协同影响青少年的心理健康状况。
3 针对青少年群体疫情相关压力的干预与研究建议
3.1 针对疫情相关压力源开展干预尝试
新冠疫情给青少年群体留下的心理足迹比医学足迹更为鲜明,未来的研究与心理服务工作实务应侧重对青少年焦虑、抑郁等情绪症状的干预。由于精神病理学症状的早期变化可能是慢性精神疾病发病的先决条件,因此,应实时监测青少年的情绪症状程度,在必要时引导他们进行早期干预和治疗,对丧亲或有自杀意念的个体及时介入哀伤干预和自杀危机干预。同时,可“锚定”疫情相关压力源开展以下相应的干预策略。(1)相关部门应做好舆情监控,提供及时准确的疫情信息,消除媒体表征的替代性影响引发的恐惧。实际上,相对于对感染和患病的恐惧,防控隔离等防疫措施对社会活动和学校教育施加的限制所引发的适应困难对心理健康的影响更大。因此,有必要帮助青少年适应和应对社会环境和日常生活方式的剧变,全民科普并提升对防控隔离益处的认知以减少被隔离者的歧视感知,增加网课学习的技术支持与课后辅导,减少与网课学习适应困难有关的抑郁症状,提高情绪管理能力以减少学生的攻击性行为等[20]。(2)给予青少年足够的社会支持和家庭支持以缓解情绪恶化、抵御焦虑。尤其是在疫情严峻时期个体采取自我隔离措施时,感知到的社会支持能够缓冲对感染与患病的恐惧对心理健康的负面影响[47]。(3)鉴于疫情相关压力的破坏力存在个体差异,有必要建立心理卫生大数据检测系统,识别高风险群体,尤其需要关注高中生、年轻女性和低社会经济地位等社会脆弱性群体的身心症状评估、心理疏导与生活帮扶。
3.2 开拓多元化的研究方法
尽管国内外文献中充斥着大量的研究数据,但大多数针对青少年群体疫情相关压力的影响与干预研究是在疫情初期进行的,通常随访时间有限,且研究方法严重依赖于观察性的横断评估和自我报告形式的调查,样本量往往不大,一些基于非代表性样本观测的研究结论就不可避免地存在偏差,对理解个体易感性与社会脆弱性所必需的社会背景因素和个体特征因素的评估也相当有限。因此,未来研究可增加家长和教师的评估环节并辅以心理实验、纵向追踪、比较性研究等多元化的研究方法,突破横断评估和自我报告研究范式的局限。
实际上,一些国内研究者已经开始运用试验法开展多种干预尝试,例如,李世峰等[48]通过试验法考察了社会心理干预手段“自我肯定”对疫情引发的焦虑和抑郁情绪反应的缓冲作用;柳碧婷等[49]将问题管理家应用于疫情期间的应激反应干预,试验结果发现这一技术能够有效缓解个体的焦虑、抑郁、躯体症状和压力感。此类研究多采取在线干预和电话访谈的形式,减少面对面接触的防疫需要,非常值得在实践中推广。例如,陈瑜等[50]证实了借助网络视频会议的减压网络团体辅导对于疫情中的大学生具有一定的有效性和适用性;刘竹等[51]尝试对被试进行7天的在线摄影干预和随后3 周的追踪研究,证实了基于网络的摄影干预在疫情突发应激中提升控制感、缓解抑郁的作用。然而,考虑到青少年对疫情相关压力的心理反应随疫情进程呈现阶段性的变化,未来可针对疫情前后以及疫情不同阶段的青少年心理反应开展长期的动态追踪研究,探查诸多压力源的累积叠加效应,以便为疫情心理影响时程路线图的绘制[52]以及疫后长期心理服务计划的制定提供更为科学的依据。此外,可利用脆弱性-压力-应对模型和已有的测量工具,如Campione-Barr 等[53]针对青少年群体编制的新冠疫情相关压力量表 ,甄别易感性个体或社会脆弱性群体并开展与普通青少年群体之间的比较性研究。如收集普通青少年和有心理问题或精神疾病的青少年在防控隔离期间如何处理自我护理、网课学习以及恢复性睡眠的比较性观察数据,这些数据对于公共政策的制定至关重要,因为有心理问题或精神疾病的青少年,特别是受焦虑和抑郁影响的青少年往往呈现出更弱的抗压能力。
值得注意的是,除运用以问题修补为中心的病理学取向干预策略外,还应重视以增强心理韧性为目标的积极心理学取向干预策略,辅导青少年采取积极的应对策略,如保持社会联系、接纳负面情绪等,借助品味和感恩训练、正念冥想等方式塑造积极情绪、提升积极品质[54],从而提高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能力。当然,个体面对疫情相关压力的威胁是脆弱的还是高韧性的,取决于神经生物因素、心理因素和环境因素的协同作用。因此,应大力鼓励治疗新冠患者的医生、精神科医生、心理学家、社会学家和神经生物学家开展跨学科合作。同时将预防、干预措施纳入未来的国家应急管理法律法规中,构建完善的以身心健康为目标的公共卫生应对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