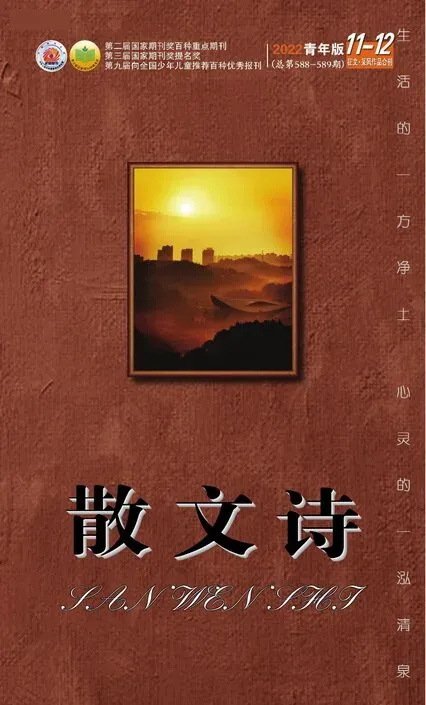脚手架上的蚂蚁
2022-02-25陈兴
陈 兴
脚手架上的蚂蚁
从农村到城市
你有了一个新的名字
叫农民工
城市的楼房再高,也是你们
一手一脚垒成
高高脚手架上
你如一粒蚂蚁
在烈日下大声吆喝
而在低矮狭窄的工棚里
你带着汗味酣然入梦
一次次梦回家乡
你说,城里的房子都太高了
要是矮一些,再矮一些
你翻山越岭的目光,就能
望见梦中的家乡
望见家门口日渐老迈的爹娘
望见沉睡中,蜷缩着的孩子
城市的绿化地,都种下了
花草和树木
却没有一棵你熟悉的庄稼
春天,你总是与一些
鲜艳的花朵擦肩而过
你甚至来不及与一棵树话别
就要像一粒细小的蚂蚁,爬上
高高的脚手架
你认得那些叶子
每一片都暗藏着熟悉的乡音
一座城市还无法安放
你睡梦中的花朵
而你依然感激每一个日子
感激来自家乡的风
吹动你的衣衫
他们在树底下睡着了
一个外省汉子在树底下睡着了
他赤裸着晒得黧黑的上身
只穿一件短裤衩
双脚沾满了泥巴
仿佛是刚从泥土里拔出来的
两条老树根
更多的他们,也在
这棵树下睡过
像暮色中,一群疲倦的麻雀
回到了巢穴
不要去叫醒他们
每一声粗重的鼾声里
都深藏着一个遥远的故乡
更多的时候,他们像一群
争抢谷物的鸭子
伸长着脖子,把雇主团团围住
讨要一份粗重的苦力
一年年过去了,仿佛只有那些
累人的活儿
才能叫醒他们命中的绿叶花朵
挑沙子的外省汉子
湿漉漉的沙子其实异常沉重
从一楼上到五楼,每走一步
他都十分吃力,肌肉
一块一块地鼓凸起来
仿佛就要从古铜色的身上
分离出去
但他却一刻也不愿停歇下来
仿佛肩上挑着的
是一家老小生活的全部
这些和一担担沉重的沙子一样
构成了他生命中
所有的痛苦和欢乐
结账时,他慷慨地少收了尾数
这使我感到,其实一粒看似
粗糙的沙子,也有着它的光芒
结实,沉重,而金黄
她,或者他们
每天,她和我一样准时上班
有时是走路。高跟鞋
在水泥路上,笃笃笃地
敲出清脆的响声
有时也开着那辆奶白色小座驾
在晨光中发动,在晨光中出发
每次,她都走得那样匆忙
有时还带走了
几声蘸着露水的鸟鸣
其实他们的装修公司并不算远
走路过去,也不过十多分钟
她坐上那辆奶白色的小座驾
似乎是要一次次给自己提速
再提速
黄昏,当她和他们回到
出租屋楼下,除了车尾箱里的铁铲、灰刀和卷尺
那些浓重的外省口音,也被
她和他们一道
大大咧咧地搬上了楼
20年
这座南方小城,我认识一个
外省来的民工,至少20 年了
但我一直不知道他的名字
20 年前,他和他的几位老乡
为我翻砸过旧楼板
挑一袋袋废料下楼
我认得他,不仅仅是
他的身板壮实得像一头黑水牛
还因他似乎成了我庸常日子里的一份牵挂
每次路过桥头
我都要看一看
他是否还在那里
20 年了,他的父母
可都还在世上?
他的孩子,是否
学业已成,或已成家立业?
20 年来,他沾满泥巴的脚
在故乡和他乡之间奔走
走过了多少条漫长的路!
一群民工在清晨喊口号
“为了老婆,为了孩子……”
每天开工前,他们
都要站成一小列
由领头的带着喊口号
那声音并不很整齐
似乎还夹杂着
一些沙哑的成分,因而听起来
似乎有点滑稽
我看了一眼夹杂在中间的那个
看样子年纪还轻。每次喊到
“老婆孩子” 这一句时
就微微红了脸
他的工帽前沿,比别人的
压得更低一些,似乎是要
压住一些青春期的秘密
每天清晨,他们都这样
鼓足力气地喊着
仿佛所有的幸福和寄望
都在喊声里回荡
仿佛故乡亲人也全都在喊声里
仿佛他们一喊
故乡的山水就会响起回声
再一喊,老屋上的瓦楞草
就会在风中招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