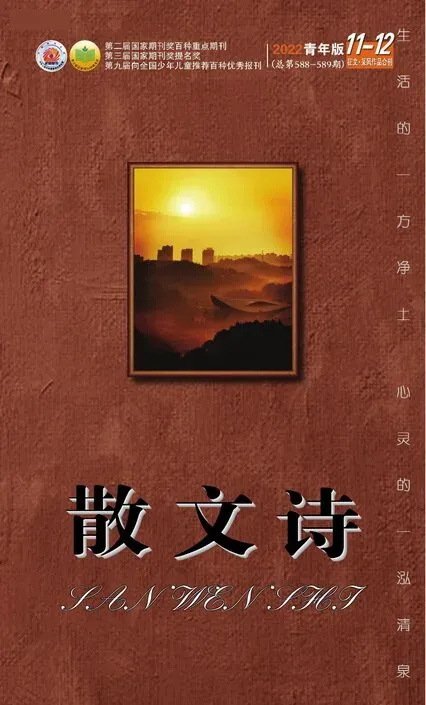看门的人(外二章)
2022-02-25粟辉龙
粟辉龙
纹丝不动的稻草人,优雅地站立在田地里。
驱赶鸟雀,帮我们守着故乡的门。
潦草、破败、苍老,身上穿戴的旧衣服,收藏了太多风雨,已经遮不住暴露的伪装。
从初夏守至今日,故土遍地雨雪蒙蒙。
被伸直的双臂,想抱住过往的寒风,握住一朵飘飞的雪花,却只有徒劳地瑟瑟发抖。
早已颓败,北风搜去了所有的籽粒。
觅食的鸟雀,飞起又落下,落下又飞起,始终不敢靠近。
远远看去,执拗站着的稻草人,就像大地迟迟不肯收回的一根手指。
稻草人,没有灵魂。
而看门的人有血有肉,有精气神。
守着小区大门的,是一扇生锈的铁栅栏,还有年过半百的鲁建国。
身体羸弱的他,始终珍藏着业主、小区和一个人的责任。进出皆是宿命,如围城难以选择的课题,我们心里都有一个远方。
鲁建国拨亮黑夜的灯盏,在岁月的一隅里守候钟声,或是泛着草色的黎明。像故乡的稻草人,让我们热泪盈眶。
隐于市的他,耐得住清贫,守得住心灵的高贵,保持着一座城市的庄严。
在电视上看到单霁翔,自称故宫博物馆看门人后,鲁建国挺了挺身子,仿佛五尺之躯,又高了两尺。
砍树的人
电锯的轰鸣声,打破了清晨的宁静。
园林工人胡树生,又在小区修枝剪叶。技术娴熟,他走过的地方,绿篱、灌木球像天使一样脱颖而出。野心满满的植被,也变成了低矮的灌木。
小区的常绿乔木天竺桂,长势良好,没过几年,就已长到碗口大。开枝散叶的速度,阻碍了采光和通风,还隐藏了坐立不安。
瘦黑的胡树生,把一棵枝繁叶茂的天竺桂拦腰锯断。
悲伤瞬间涂满了旁边的红叶李,如果走近一些,还可闻到风中的血腥味。
树上的鸟鸣没了飞向蓝天的家。
被砍去头颅的天竺桂,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静静地站着。
几个月过去了,在时间横截面的周围,已经悄悄地长出几支新的叶芽,牙关紧咬,铁骨铮铮。
每年3 月12 日,胡树生都会交出修剪工具,加入志愿植树的队伍。
以节日之名,在高高低低的山冈,把砍去的树再种回来,还原绿色的底片。
清风徐来,像一棵棵朗诵的树,加入了森林的合唱。
错落有致的音符,不绝于耳,在祈求得到春天和生活的宽恕。
送信的人
我刚把一张单薄的信笺铺好,还未动笔,就被春天的一缕风,比一页纸还轻的风,掀动信笺的一角。
给父母写一封春天的家书,让天空一样蓝的蓝墨水,在纸上缓缓洇出。
盖上邮戳准备寄出时,才发现父母就在身边。
写信时突然发现,我们的语言少了。
送信的人还在坚守,邮局还在那里。
但有的地址已经不见了。
昔有高原邮差王顺友,跋山涉水传承父亲的教诲;今有雪域信使其美多吉,雪域邮路上飞雪带春风。
他们唱出了高原最深沉的歌。
在我生活的小镇上,每天会准时看见穿着绿衣服,骑着绿车子的邮递员。
不用说我也知道,那车里装着生活的嘱托。
为了保持住车里的温暖,一只绿蚂蚁,牵着自己的身体,在小镇上来回穿梭、奔跑。
比一棵草矮。
比一座山高。
一只绿蚂蚁又上路了,脸上阳光般的微笑,抵消了他身后跟着的疾风、雷声和滂沱大雨。
一封家书抵万金。
如今写信的人少了,但我每次看见送信的人,仍就像看到久未谋面的亲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