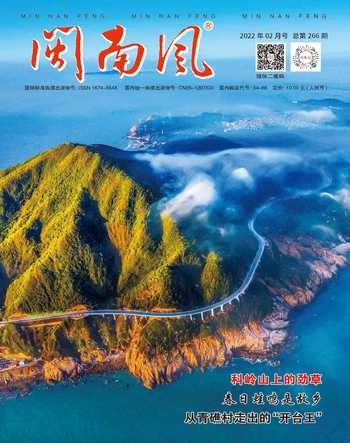一扇重新观览文学史的窗口
2022-02-24尚永亮
尚永亮
上海古籍出版社近日推出煌煌八册近400万字的《林继中文集》,既是造福学林的善举,也为我们打开了一扇重新观览文学史的窗口,可喜可贺!
《文集》由《杜诗学论薮》《杜诗选评》《杜诗菁华》《文化建构文学史纲》《文学史新视野》《唐诗:日丽中天》《唐诗与庄园文化》《我园论丛》《栖息在诗意中:王维小传》《中晚唐小品文选》《我园杂著》《杨少衡新现实主义小说点评》等多种论著构成,其中与唐代文学相关者占三分之二强;而在唐代文学中,与杜甫相关者即达二分之一,由此见出林先生研究重点之所在。
杜诗是林先生学术生涯的起点,并贯穿于他的整个研究过程中。他20世纪80年代中期撰成的博士论文,即以宋赵次公及其杜诗注为研究对象,通过惨淡经营,为杜甫研究“提供了一个至今为止最为完善的赵注本”,由此得到导师萧涤非先生的高度肯定。1994、2012年,这本名为《杜诗赵次公先后解辑校》的大著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初版、再版,在学界引起了不小的反响,林先生也成为公认的杜诗专家。虽然这次出版的《文集》未收此书,只录了书中的前言部分,但由此也足可窥斑知豹了。与这篇前言一起收入《文集》第一册中《杜诗学论薮》的,还有29篇杜甫专论,其中既有宏观览照,又有微观考论,或发前人所未发,或在前人基础上深入推进,由此构成了林氏杜甫研究的完整体系。莫砺锋教授在序中评价说:“林著中这些论文并未有意标新立异,但它们以实事求是的态度研究杜诗,得出的新颖见解具备充足的文献基础和学理依据,在我心目中,这就是古代文学研究领域中最有价值的论文。”这一评价,我以为切中肯綮。除《杜诗学论薮》外,《文集》还收录了《杜诗选评》《杜诗菁华》两部关于杜诗的选评本。前者收诗约200篇,后者收诗近500篇,二者相加,已达全部杜诗的半数,这个体量,恐怕是历代杜诗选本中最大者之一了。围绕这些精选的篇目,作者或以时序编排,予以精当扼要的注释和点评,或在注评之外,加以当代语译。含英咀华,要言不烦,极便读者。谓之为杜诗功臣,也未为不可。
由杜诗研究出发,作者还将相当大的精力投入盛唐作家群和田园诗的考察上。《文集》第六册所收《我园论丛》是一部涵纳了61篇论文的研究专集,其中涉及六朝者5篇,宋代者6篇,涉及文化诗学、文论者约10篇,而关乎唐代文学者即占21篇,其中又大多集中于对盛唐气象、盛唐田园诗以及李白、王维等精典作家的研讨。诸如《盛唐气象的审美特征》《李白诗歌的悲剧精神》《布衣感新论》《王维情感结构论析》《盛唐田园诗的心理依据》《漫说唐人田园山水诗的画意与禅趣》等,从题目即可看出论述的重心和要点,而一读之下,更觉新见迭出,常有“会心处不在远”之感。尤可注意的,是在这些散篇论文之外,《文集》第五、第七册又收录了与之紧相关联的几部专著,如《唐诗与庄园文化》《栖息在诗意中:王维小传》《唐诗:日丽中天》《中晚唐小品文选》,由此构成围绕几个专题点面结合的系统框架。在这些论著中,作者以“了解之同情”,设身处地,贴近对象,通过对文化背景、作者身世的深入把握和作品的精当解读,去探查、了解作者的真实心态,尽力接近历史现场,带领读者重回大唐。在《栖息在诗意中》,作者分析了王维《桃源行》后指出:“与其说是王维将桃源幻化为仙境,毋宁说是王维以现实中的地主庄园取代了全封闭的近乎原始的乡村,从而使桃源更现实化了。事实上花、竹、松、月是唐代田园诗中最为常见的意象。这一转换虽出自少年王维之手,却经历了六朝至隋唐那么漫长的历史变迁,问题涉及的是士大夫文化心理结构的演进。”而通过这些演进历程,再验之以王维的人生及其富于弹性的心理结构,则王维诗是一面”开向生命的窗子”这一概括便很能令人信服了。在《唐诗与庄园文化》中,作者通过对均田制瓦解、庄园经济普遍化并成为盛唐文人重要文化生活场所的考察,一步步逼近“诗意的居住”这一主题,最后得出结论:“历史环境的变迁使士大夫文人虽仍沉湎于庄园生活之情趣,但具体经验已更多地虚化为精神上的向往而留在士大夫生活态度之中”,并由此“凝成了诗歌理论与创作上对‘韵外之致’的追求,它从田园诗创作实践中萌发,却超越其界限,成为中国古典诗歌的一个重要品格。”这里由小见大,源流并举,文学与文化、生活与心理相交相融,在看似平淡的話语中拈出核心理念,极富学理性和启发性。

如果说,以上研究虽不乏宏观视角和史的勾勒,但整体上还多为关于作者、作品和某些文化现象的点状考察,那么,收在《文集》第四册的《文学史新视野》《文化建构文学史纲(魏晋——北宋)》,便是两部放开眼界纵览文学发展大势的宏观大著了。前者重在考察文学史生态、发展模式及其与文化建构的关系,并将整个文学史的生成概括为“蔓状结构”,由此呈现出一种新的文学发展史的阐释模式。后者则是在作者同名旧著“中唐—北宋”段基础上增补改订而成,论述自魏晋经隋唐至北宋的文化、文学进程,学术视野颇为开阔。作者以文化史与文学史之双向同构为核心理念,着重揭示了9至11世纪间由雅入俗又化俗为雅的文学演进路径,并从政教一体化的要求推导出士大夫人格机制与文学倾向的转变,从文学经典化的角度,勾勒出杜甫被选择为诗歌典范及其由“诗史”到“诗圣”、最终蜕化为内观照之“山谷模式”的过程。陈伯海先生在该书序中称道其“写得丝丝入扣,令人拍案叫绝”。当然,该书另一位序者赵昌平先生在予以肯定的同时,也指出所存在的一些问题,认为其以“士族文学”与“世俗地主文学”为两阶段文学特质的标志,并以士庶之判与雅俗之分作大体对应、以黑格尔正—反—合思辨模式与“通变”相联系等做法值得商榷。但这些问题,似并不影响该书对中唐至北宋时段文学演进的整体判断,而作者所作的颇具深度的一些思考,无疑会启迪读者对唐宋文学史之走向形成新的认知。比如,在作者看来,浅近易晓的诗风左右着近半个世纪的宋初诗坛,它表明中唐——北宋的文化是一板块的整体结构,旧王朝的崩溃、新王朝的建立,并不能使自中唐开始的“由雅入俗”的文学运动为之终止。这一论断,似可为我们重新认识近些年再度兴盛于学界的“唐宋变革论”提供一种反思;而从另一角度看,在宋人眼中,“唐人工于为诗而陋于闻道”(苏辙语),正道出盛唐人与北宋人价值选取标准的差异。由此导致由一度在盛唐闪现过的个体自由的追求,转为中唐以后日渐自觉,至北宋终成个体规范化自觉追求的历史之潮。这股思潮,某种意义上也可谓之“人与文学的再自觉”。这一论断,则在“自由”“自觉”两个看似相近的概念中透露出某种文化人格的大的变异,其见解不可谓不敏锐。
从以上简述,已可约略见出林继中先生数十年学术研究的基本概况和路数,如果做一总结,我想可概括为三点:
一是专精与广博的结合。专精,指其扎实的文献学根底,这在《杜诗赵次公先后解辑校》中历历可见;广博,指其以文献为基础,放开眼光,纵览全唐乃至整个文学史,从中发现规律,指明整个中国文学发展的形态和路向。
二是学术与思想的结合。学术,重在学理性的发明,思想,重在从此发明中揭示更为深层且蕴含启示性的普遍意义。早在上世纪九十年代,王元化先生即曾呼吁“追求有思想的学术”,陈伯海先生总结20世纪唐代文学研究时说:“唐诗学由古典向现代学术形态的转变,关键倒不在史料的发现,而在于观念的更新。”因为学术只有与思想、观念结合,才能唤醒其深层活力,才能强化、提升其穿透力和引领力,有时甚至会带来某些革命性的变化。而继中先生的学术研究,正具有思想与学术紧密结合的鲜明特点。他一再申言:“探索本身自有其不为目的所囿的价值与乐趣。”(《文化建构文学史纲·跋》)“不过,有一点还想请读者诸君垂顾:我的观点、结论或许经不起推敲,但提出问题或思路,万望諸君驻足三思焉。”(《我园论丛·自序》)说的便是这种情况。
三是文化与诗学的结合,由此构成其“文化诗学”的研究路径和目标。所谓文化诗学,重在一种人文关怀和诗性精神,它将文学艺术等方面的问题纳入文化范围,借助文学文本和文学现象的解析,达到对深广宏博的人文世界的透彻解悟和深层认知。这其中有融合各学科知识的跨界考察,有对庸俗浅薄世风的深刻批判,更有一种对理想的执著追求和对现实的自觉关注。用作者的话说:“我赞成鲁迅的研究魏晋乱世与明清专制,从中找出‘国民性’的病灶来;我也欣赏马斯洛的研究人类‘不断发展的那一部分’的主张,我于是想在唐文化的研究中描画出我民族肌体曾经有过的健美,但我反对以任何影射的方式去处理历史上发生过的任何事情和现象……可我却又喜欢用现代人的眼光来观照古人古事,企盼能在今古之间发现一条时间的隧道……力图让孤立的现象在文化各因子错综复杂的大构架中找到合适的位置。”这样一种目标设定和自我期许,在前述多种论著中均有程度不同的展露,而在《文集》第八册《我园杂著》和《杨少衡新现实主义小说点评》中,有着更直接的体现。前者收录了作者多年来的一些随笔、杂文,或谈历史,议文学,或记人物,论现实,均有感而发,深切著明,小问题隐含大旨趣,有时寥寥数语即砭人肌骨,发人猛醒。诸如《心的记忆》《阅世虽深有血性》《梁启超的识见》《中国人的生命力》《对死亡的美学思考——夜读李贺诗》等,均具此特点。后者则花费大力,系统评点作家杨少衡的一部中篇小说《蓝名单》。在他看来,“当下以反腐为题材的小说并不少见,而能从一塌糊涂泥洼中看到星光倒映,从病体中找到抗体,从是是非非中发掘出人性的诗意,于无情处见情,于有情处见理、见法,从现状中反省历史、忧患未来,能如此者为罕见矣。杨少衡的小说当属此珍品。”一个古代文学研究者,突然热衷起当代小说来,并予以细密点评,若非怀有一个更远大的关注目标,便很难令人理解。事实上,结合林继中先生的学术经历、研究对象和他对文化诗学的倡导,很可以见出其一以贯之的中心线索。
在《文集》总序(原为林氏《文本内外——文化诗学的实验报告》一书序言)中,孟泽如此热情洋溢地说道:林继中之所以倡导通过“文化诗学”的路径研读历史,检阅现实,“根本的动力也许在于,他试图拥有一种充分理解传统文学与文化的精神高度,一种具有普遍意义和价值的思想逻辑,并由此融贯中西,汇通古今。”我同意这种说法,因为在林继中的心性中,既有着来自诗国高潮之盛唐气象的久远滋润,又有着对中国民族忧患历史的深切洞察,更有着上世纪八十年代那场已很难重复的学术文化高潮期的精神贯注,所以他能以远较一般学人阔大的胸襟和高自树立的人格境界,去呼唤盛唐,去反思历史,去直面现实,去嫉恶扬善,他在努力地用自己的笔,为人们打开一扇重新观览文学史的窗口。尽管在其内心深处,更接近的似乎还是唐代田园诗人那种无拘无束、淡泊优雅、自由散朗的生活方式和文化品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