片面的深刻:论新时期小说苦难形象特质
2022-02-22严运桂殷满堂
严运桂 殷满堂
(长江大学 人文与新媒体学院,湖北 荆州 434023)
“苦难”与“形象”是本文的核心范畴,本文所阐述的逻辑与它们的内涵密切关联。苦难,通常指痛苦与灾难。它既可是物质性质的,诸如生活物质的极度匮乏导致的饥饿冻羸、工作环境恶劣造成的人身伤害、制度失衡带来的非和谐现象、人性局限酿成的难咽苦果、天灾人祸降临的毁灭性灾难等;也可是精神性质的,诸如人生迷茫时的孤寂荒凉、目标难达时的沮丧无奈、壮志难酬时的痛心疾首、遭受践踏时的被辱隐忍、失亲失爱后的肝肠寸断、欲壑难填时的疯狂焦躁等。简言之,苦难既可以是挑战人生存的极端威胁,也可以是伴随人生活的磨刀石。对人而言,它可以是摧毁性的,可以是腐蚀性的,可以是锻铸性的,可以是砥砺性的。或使人畸形变异、尽失人性,或让人束手就擒、举手投降,或令人毛骨悚然、逃之夭夭,或催人崇高无畏、涅槃重生……凡此种种,它们既可是物质状态,也可是主观感受,既可是短暂的人生之坎,也可是恒常的人生之路,这些与本文的“苦难”相关。形象,指文学形象,“凡是能够将审美意识通过语言外化为使他人在接受过程中产生审美想象和联想的感性对象,都可称之为文学形象”[1]28。除此之外,学界还有其他表述:“文学形象就是通过语言形式化了的生活”[2];“从感性的方面看,文学形象也就是一定的生活的感性表现形态”[3];文学形象“不仅仅有视觉表象,同时还存在着其他对应的听觉表象、嗅觉表象、味觉表象、肤觉表象等各种感觉上的记忆表象”[4];等等。综合上述观点,我们可分解出文学形象的义项:一是文学形象体量可大可小,可以是一个感性片段(如一声叹息、一缕荷香);可以是一个具体场景(如阴沉沉的天空);可以是由若干文学形象有机组合成的情节故事(如窨井盖没了,一个看手机的行人走着走着就突然消逝了)。二是文学形象的感觉是所有感觉器官都能感觉到的信息,并非只是视觉信息,通过看、听、嗅、触等获得的对象都有可能成为文学形象。三是文学形象的类型多样化,其对象不只限于我们习惯所指的人物形象,还包括了声光电、景物事、氛围等可感对象。四是文学形象可实可虚,审美主体由感知某种现实的信息进而产生审美想象和联想的感性对象,均属于文学形象。由此观之,对文学而言,形象是核心要素,它蕴藏着审美主体的人生体验、情感思想,它激发着审美主体自由驰骋、情思飞扬,它引领着审美主体顿悟真谛、直达澄明之境。它的更高形式是与意融合一体而成意象,我们也称之为文学形象。“苦难”与“形象”,两者组合成一个偏正词组,其形象的色调不言而喻。
新时期小说,尽管流派演变,异彩纷呈,但它们大多与苦难形象结缘,书写苦难几乎成为这一时期小说创作的风尚。或重现历史、反思“文革”、再现当下,或摹写市井、描写乡村、揭示黑矿,或刻画内心、建构家庭、剖析社会等,苦难形象之于新时期小说,犹如空气之于人一样。虽然此前的小说(比如“十七年”的小说)也有苦难形象的叙写,但它们都是创作者体现主旨的陪衬、烘托因素,且颇有节制,在秉持现实主义创作原则的作家笔下,它们主要是为塑造典型人物、树立英雄形象服务的;而新时期小说中的苦难形象是全息性的,能感知的小说时空,几乎都被苦难形象充斥着。从时间方面看,苦难绵延,如余华《活着》中的主人公福贵,早年被人设局输光了家产、气死了父亲、做了壮丁、从死人堆中捡了条命、母亲病逝、儿子被抽血而死、女儿难产大出血而死、妻子得软骨病而死、女婿被水泥板压死、外孙吃豆子活活撑死。一个个苦难形象叠加累积,让人毛骨悚然。从空间方面看,苦难弥漫,如陈应松的“神龙架系列”小说,穷山恶水、乌烟瘴气、生态失衡、恶俗遍布、刁民成群等。走的是会摔死人的山路,看见的是滥砍滥伐的林地、升腾的瘴气、杀人的场面,嗅到的是腥臊腐臭,用的是带有鸡屎味的碗筷,吃的是长了几年绿霉的猪肉,交往的是流氓等。脏、乱、差、假、恶、丑、穷、冷、残等,应有尽有,无边无际。综合考察新时期小说的文学形象,大多是类似的片面的苦难形象呈现,具体体现出伪自然性、反讽成习、与死结缘等特征。
一、伪自然形象——现实主义的异化物
新时期之前,我国当代小说形象追求“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的典型化创作原则,文学形象多是加工改造后的“高于生活”的形象,使得众多形象具有了功能性。为了凸显主要形象的光亮,其他形象可分两种状态,一种是有些许光亮的,尽量散发出自己的光亮,向主要形象聚拢,使其光亮更加耀眼;二是没有光亮的,索性在他者的光亮下尽显自己的阴暗冷酷,这样明暗对比,目的是让主要人物的光亮在比较中更加鲜明和热烈。被典型化了的形象虽然有些现实依据,但超离了生活,好的美到没有瑕疵,坏的浑身都是恶毒,他们都在生活的基础上有了大尺度的变异,“塑造”痕迹明显。而新时期小说中的各种形象,则呈现出反 “典型化”的特点:平凡庸常,貌似与现实生活高度贴近,我们称其为“原生活形象”。无论是描绘形象,还是叙述情节,虽然都有“写实”因素,但与现实主义文学形象有较大的差异。
第一,人物形象多为非英雄、非典型。现实主义主张营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新时期小说则反其道而行之,去英雄化,去典型化,这种人物形象在新时期一些有影响的作家文本里俯拾皆是,诸如韩少功、阿城、苏童、叶兆言、莫言、余华、格非、马原、孙甘露、迟子建、池莉、刘震云、刘恒、贾平凹、刘庆邦、陈应松、葛水平等,他们小说文本的人物形象,或胸无大志,算计于柴米油盐家人邻里;或自甘沉沦,周旋于领导同事和各色女人之间;或有勇无谋,出入于匪群青楼;或游手好闲,伺机坑蒙拐骗;或据权力与金钱的优势,作恶多端仗势凌人;或本性善良,但缺乏能力与智慧,终结于变异和悲剧;等等。
第二,各种形象更多显示的是人性中的丑恶欲望。人的欲望有美好与丑恶、人性与兽性之分,现实主义文学主张提炼生活,而新时期的一些小说是“照搬”生活。没经过过滤的现实生活是比较丑陋的,新时期小说特别关注且聚合体现人性的丑恶猥琐的形象,有的从篇名就能看出来,如《黑脉》《黑洞》等。《黑脉》写的是黑心煤窑题材,小说里出现的所有形象,包括跟煤利益链相关的上下人物(他们为了侵吞国家财产狼狈为奸)、被煤窑主许中子草菅人命的打工者(愚昧冷漠)、煤窑内外的危险环境形象(煤窑塌陷、农田塌陷),小说中的狗也是个势利眼(它对人或“贴着手亲热”,或“叫得怒气冲天”),煤窑所在地“捉马村”一片破败光景等,这些文学形象无不暴露了人性的虚伪、自私、贪婪。《黑洞》向我们展示了陆建桥一家在拆迁后寄居姐姐篱下的窘境。作者通过一系列形象呈现了两家六口人粗鄙低俗的生活,同时也揭示了亲情在自私脆弱人性面前的不堪一击。除此之外,新时期小说中的苦难形象还与性结缘,许多性象描写,没有了情爱的社会内容,主要是为满足生理需求,甚至于是兽性的发泄,这种描写同时也呈现了人物内心孤独苦闷、精神空虚无聊、理想信念迷失等。作家对此的描写表现出既不敬也不雅。
第三,形象本身情感价值蕴含匮乏。现实主义文学作品注重理性或理念的关照,因此有价值评判和情感渗透,从而对人有导向和潜移默化的作用。而新时期小说作家(比如新写实小说)追求“零度状态”,他们在描述形象时往往是一个冷眼旁观者,几乎不用议论与抒情的表达方式,呈现所谓生活的“原生状态”。这方面最具典型性的是池莉的系列作品,诸如《冷也好热也好活着就好》《烦恼人生》《太阳出世》《来来往往》等,作者对以猫子、印家厚、赵胜天、康伟业等武汉市民的生存状态进行了客观平实的描述,作者隐匿了喜欢、同情、指责、暗示等情感态度,也没有生活意义的追问与阐发,形象的蕴含,全靠审美主体感悟与体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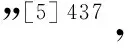
这些“原生性”的形象,学界认为是作家们秉承自然主义的创作观念与方法的结果,“只有到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语境中,在‘新写实主义’勃兴的浪潮中,外国的‘自然主义’才真正在中国文学土壤中开花结果”[6],但细究起来,新时期小说这种写实性与自然主义的写实有较大出入。所谓自然主义,是文学艺术创作中的一种倾向,它一方面排斥浪漫主义的想象、夸张、抒情等主观因素,另一方面轻视现实主义对现实生活的典型概括,而追求绝对的客观性,崇尚单纯地描摹自然,着重对现实生活的表面现象作记录式的写照,并企图以自然规律特别是生物学规律解释人和人类社会[7]。反观新时期小说的写实性,可以说是伪自然性的:首先,主要是采用庸俗的、阴暗的、丑陋的、残酷的形象,即便民间崇尚的侠肝义胆和忠勇之气,在诸多小说文本中也成了无魂的草莽之举,平日人际间本该有的温情和美好几乎被抽空,这不是绝对客观的“描摹”“记录”。其次,作家们虽然极力回避流露情感以达到所谓的“零度情感”,但创作主体的情感还是能透过纸背,这主要体现在他们对形象处理的技艺之中,只不过是否作家对社会现象的不满和批判之情更加冷峻而已。再次,小说文本中有关人性的文学形象,比如自私残酷、男欢女爱等,千百年来都是不可细述的“丑”事,虽然它是“真”,但这种“真”是不宜暴露在众目睽睽之下的,可是新时期的小说作家们添油加醋,大书特写,不仅使文学本该有的道德意蕴尽失,还有诲淫之嫌疑。故而,新时期的小说文本如果说是写实,只能说是变异的写实,一切都在创作主体的主观情感控制之中,“作家追求的是内在心理真实,认为只有精神的和心理的才是生活的真实”[8],这种文学现象,是对自然主义的误解还是歪曲?准确地说,他们是“把自然主义的消极因素发展到了顶峰”[9],使文坛涌动着一股戾气。
二、反讽的形象——揭露矛盾的马前卒
反讽可以简单理解为说反话,是说此指彼、正话反说的一种技法。就小说创作而言,是指一种单纯从字面上不能了解其真正要表达的事物,一般要结合语境才能理解其原本的意义,而这意义正好与字面意义相反。新时期小说文本因为运用了反讽使得诸多苦难形象具有了更为深刻与犀利的含义。也就是说,反讽不仅在小说文本言在此而意在彼的修辞学意义上得以体现,更在形象乃至形而上的意蕴反讽层面得到表达(其他时期小说虽然也有运用,但运用人数之众、频次之多远不及新时期小说)。新时期小说反讽手法可分为语象反讽、情景反讽、意境反讽等。
第一,语象反讽。语象是语词或词组给人的感性形象(如金发碧眼、蓝天白云等)。语象反讽主要体现在小说语言的语词方面,新时期小说较为典型的语象反讽是小说文本的取名上。《高兴》(贾平凹)、《福翩翩》(迟子建)等,如果单从小说名所显示或所激发想象的形象看,它们的字面意思都与苦难无缘:“高兴”一词有多条义项,诸如愉快而兴奋、高雅的兴致、喜欢等;“福翩翩”是个词组,指幸福的、美好的事情接二连三地呈现。而这些小说实际描述的是什么呢?《高兴》写的是因生活所迫卖了一个肾的刘高兴到城里拾破烂的悲苦生活,孤单一人,何谈高兴; 《福翩翩》写的是社会转型时期,城乡接合部的两邻居家的生活的艰辛与无奈,幸福生活离他们很遥远。这么一对比,小说命名的反讽效果不言而喻了,作者的期许和现实的巨大反差残酷地张开着,给人一种吞噬之感。
第二,情景反讽。情景,顾名思义指的是具体的情况、情形、场景等,新时期小说的情景反讽,主要体现在将罪恶景观化。莫言《檀香刑》中有名刽子手叫赵甲,他是清朝刑部大堂里的首席刽子手 ,受过慈禧太后和皇帝的嘉奖。他杀人技术高超,手段残酷,性情冷漠。作者为了凸显他的形象特点,着重写了他执刑的两个场面:一是凌迟革命党人钱雄飞,一是行刑造反英雄孙丙。小说细述了他如何用上等材料做刑具,尤其是他和儿子赵小甲在戏场上众多看客面前行刑的场景。赵甲以他杀人的技术为傲,引来了众多的围观者,还得到了统治者袁世凯等人的赞赏。这种反讽效果极其深刻,把一个杀人不眨眼的魔王嘴脸和万恶的清朝社会刻画和描写得淋漓尽致,更深刻的是把人性深处极其丑陋不堪的恶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第三,意境反讽。意境,是指文艺作品中描绘的生活形象及其蕴含的思想情感共同作用而产生的所指。新时期小说形象的荒诞方面就达到了意境反讽的效果。吴玄《像我一样没用》中的丁小可,大学毕业生,32岁,家有妻女。由于广播电台被迅速发展的电视与网络挤占了发展空间,作为电视台工作人员的丁小可也变得清闲,他的生活除了下围棋还是下围棋,不建设家庭,更不关心社会,生活无目标无热情,活脱脱成了一个“废物”。当他妻子与曾连厚好上了,他不相信也不在意,当妻子提出离婚,他也无所谓地答应了;当曾连厚被他人杀害,而他被当成了凶手,在没在刑讯逼供的情况下,他主动承认他是杀人凶手并捏造杀人理由与细节,当案件终于真相大白证明他是清白的,他却在公安局又哭又骂,因为他的目标是等死,公安局破案将他的希望击破了。丁小可的荒诞令人心酸,稍有认知力的读者决不会认为他只是一个“懒人”,会进一步思考小说文本深处的所指。
反讽手法体现在新时期小说的字里行间、整个形象体系及其意蕴之中。作家们往往居高临下,俯瞰世态,利用反讽的矛盾性,对形象的隐喻义给予了深刻的否定,否定现实的不完善因素,否定不同时期的非合理现象,否定人性深层的卑污等,作家们“高明”得让人震撼。他们“不满于任何固定形式的”,“敢于在创造中否定创造”[10]。他们或给普通的形象披上一层神秘的外衣,让有限的东西发出无限的光芒;或通过形象隐含理念,甚至于毁灭形象影射理念。德国浪漫主义奠基人施莱格尔曾这样界说反讽:“反讽出自生活的艺术感和科学的精神的结合,出自完善的自然哲学与完善的艺术哲学的汇合。它包含并激励着一种有限与无限无法解决的冲突、一个完整的传达既必要又不可实现的感觉。它是所有通行证中最自由的一张,因为借助反讽,人们便自己超越自己。”[11]57
三、向死的形象——刺向时弊的利剑
如何理解“死”这一概念呢?我们通常理解的就是生物体生命的突然终止,文学死亡现象还不只是指人的生命的逝去,它还有更加宽泛的内容,诸如精神的荒芜、理想的消失,失去本性,沦落为“非人”。此外,死亡还涉及各种非人物形象的灰暗沉寂或被毁灭等。无论何种死,都是灾难性的,都是苦难的极限!它们因何而死?死又何如?诸如此种追问才是文学死者留给读者的反响。
第一,人物形象的非正常死亡是新时期小说文本的底色。生命对人来说只有一次,珍贵无价,突然死亡无论对家庭还是对个体都是灭顶之灾。综观新时期小说文本,其人物的死因千奇百怪。一是自杀死。自杀死亡者,大多是身心太过痛苦,生不如死,最后只得一死了之。其采取的方式有喝毒药、上吊、投水等,如迟子建、鬼子等小说中的人物的死亡。二是受刑死。接受刑律死亡者,大多并非罪大恶极之人,只是人们的行为可能是危害了统治者的利益,从不同角度看,他们可能还是值得众人尊敬的人,然而他们却不得“好死”,如莫言、须一瓜等小说文本中人物的死亡。三是意外死。遭受意外死亡者,看起来纯属偶然,实则是有其必然性的,工伤事故死亡、车祸死亡、难产死亡、自然灾害死亡等,这些死亡结果后面必有原因,如余华、苏童小说文本人物的死亡。四是争斗死。争斗死亡者,一般分个人与群体两种情况。个人争斗,要么是谋财搏命,要么是争强斗狠,要么是报仇雪恨等。集体争斗,要么是围绕权益与政府警察对峙,要么是与利益相关联的争夺方发生械斗等,这种争斗往往非常血腥,如韩少功、铁凝小说中的人物死亡。五是疾病死。疾病死亡者,最让人无奈,让人哀叹。一般是分两种情况:一种是生活水平低下、饥寒交迫,积劳成疾,可是无钱医治; 一种是因自然环境毒害成疾,灾役流行,人们愚昧不知,还信宿命等死——此类死亡者本有机会重获健康的身体,但因种种主客观的因素,眼睁睁地任由生命失去,如陈忠实、阎连科的小说文本中人物的死亡。六是神秘死。诡异的死者,一般是指其死法有明显的象征符号意味,较为神秘和荒诞,按常规思维都不知其死因和意义,如王小波、王十月小说中人物的死亡。等等,林林总总。小说人物形象惨死一片,会强烈刺激社会,唤醒人心。
第二,人物形象的精神崩溃或毁灭伴随难挨的人生。“哀莫大于心死”,虽然心死与不可逆的身死相比,还有重生的机会,但心死之时,其生存状态如死寂的荒漠,令人可怕。这种精神向死的形象因致死原因不同而有别:一是身外的打击。如李兰(余华《兄弟》)因丈夫做了见不得人的事死去,她羞辱难当,一心指望儿子,儿子小小年纪也步了父亲的后路,在厕所里偷窥女人而被人逮了现行。父子做出这等丑事,让她情何以堪!她处处躲着人,抑郁落寞,如若不是中学教师宋凡平主动走进她的生活,她很难再次品尝到做人的尊严。二是人性深处的欲望发展。如《妻妾成群》中颂莲始而贪图享受,继而设法争宠,进而欲望难抑,加之来自封建家庭的各种恐惧,疯疯癫癫成了她必然的结果。精神的向死总是伴随着苦难的人生,它不一定促成人的生物性死亡,但它却比生物性死亡更具悲剧性。
第三,趋向死亡的非人物形象充斥人的生存空间。非人物形象,指与人相关的云霓山川、动物植物、水分空气、声色形状等,它们是人的实践活动的环境、条件、对象、结果等,是小说不可或缺的文学形象。新时期小说所呈现的非人物形象,格调让人格外压抑。诸如山秃水浊、道险路泞、人际冷漠、工地混乱、疾病缠身、新坟烟袅、鹰鸦翔集、箫声呜咽等。非人物形象与人物形象的关系,跟传统现实主义小说文本比较,有一些区别:传统现实主义小说的环境形象是为人物形象尤其是主要人物形象服务的,它们处从属地位;新时期小说中的环境形象却相对独立,我们不排除它对人物形象有衬托功能,但方向不同,前者是反衬,效果是“乱世出英雄”,而后者是铺垫和预告,它与人物形象一道作为作者苦难意识和死亡意识的形象载体呈现在文本中。
新时期小说的死亡形象的精神指向,与社会关系和社会心理相关。从社会关系而言,变革时期的价值观多元甚至混乱,个体之间、个体与群体、个体与国家、集体与国家、群体与群体等关系,常常因利益问题导致非和谐,甚至形成尖锐矛盾;从社会心理而言,由于社会制度和社会关系中的一些负面因素的影响,在社会大众生活中产生了焦躁情绪、蛮横态度、过激言论、不良风气,等等。这些都影响到作家的创作心理,于是,直面文学形象走向死亡,就成了文学家们揭露丑恶、刺激人心、呼唤良知的重要手段。
无论新时期小说苦难形象呈现何种特征,其实质是辩证的否定。其辩证之处表现在,一方面,“苦难形象潮”作为一定社会存在的反映,是文学发展的阶段性体现,作家通过苦难形象的塑造,否定非合理的现象,否定人性深处的卑污,否定陈旧的观念等;另一方面,它对未来文学发展也会有推动作用。“在后现代小说中,人性的异化已经渗透到日常生活的各个角落,叙述者不仅毫无能力再把握整体的世界,而且自身也受到了本体论式的质疑。为了追求最本真的现实,叙述者必须通过否定前一阶段的模式,才能向后一个阶段发展。作家们采取这种方式的目的不仅是要呈现变化了的世界,更是要激发人们的自我意识。”[12]我国新时期小说,具有西方后现代小说的某些特点。辩证的否定是通过“审丑”来实现的,即以审美的态度去审视、选择、提炼、表现“丑”,从而使人们厌恶丑、追求美与善。有学者曾说:“市场化时代的丰富性、复杂性,它对社会生活和欲望释放的强烈刺激造成的加速度运动,在政治、经济、文化诸领域,都以各自的方式和样态,为人性的考察提供了千载难逢的聚光镜和放大镜。这就是中国文学面对的繁复的现实。”[13]“作家的职责就是将这些看似微小的影响所具有的爆炸性能量揭示出来,将其夸张放大,给世人以警醒。”[14]审丑的过程就是辩证的否定。新时期小说以多种苦难形象为审美对象,体现出了一种片面的深刻。这种深刻性,除了有反思批判、揭露抨击、发展创新等显性功效外,还在于苦难形象的隐性功效:首先,苦难形象具有多维、多元的思想价值,它可将触角伸进人们向往的美的盲区和灰色区域,完整真实、立体多层地展示世界。其次,苦难形象具有激活价值,“往往具有突破思想牢笼和思维禁区的价值”[15]231。新时期小说的苦难形象有别于传统小说,其苦难形象深藏破坏性及其在破坏中重建的渴望。同时,需指出的是,苦难形象因为片面而把握失当之处,则又显现出了审美文化的负面效应、负面结果和负面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