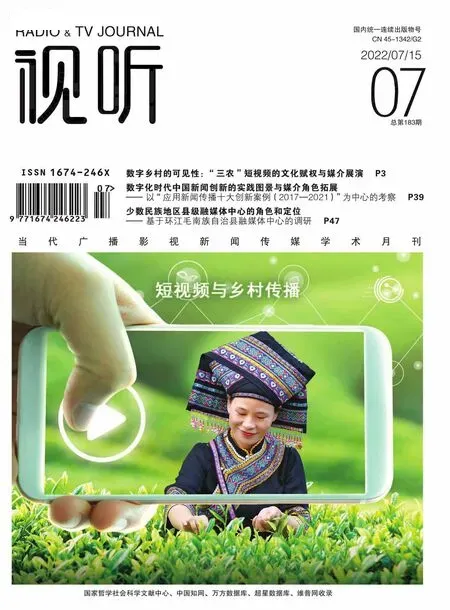数字乡村的可见性:“三农”短视频的文化赋权与媒介展演
2022-02-18周孟杰谭舒婷
周孟杰 谭舒婷
一、文献梳理与问题提出
学者丹尼尔·戴扬针对虚拟网络等新媒体出现后当下公共空间领域的转型,提出了“可见性”的概念。可见性是指能否被他人看见,或者能否获得大众的注意力。如果获得的注意力达到了一定的程度,并产生了相应的权力关系,那么就产生了可见性。在深度媒介化的语境下,新媒介技术决定着人们生存空间的可见性程度。随着网络新媒体的出现,传播环境、媒介技术与受众用户关系都发生了一定程度的改变。传播方式的革新,赋予了权力以新形式的可见性,从而使权力处于一种持久的公共注视之下,可见性也逐渐与现实场景中的对话交流相融合,成为媒介公共性的核心元素之一①。
有学者认为,短视频社交平台的职业可见性使得个体都可以主动走上前台,站到聚光灯下,从情感维度和知识技能维度积极展演自身的职业可见性②。在获得可见性的过程中,媒介通过为公众提供展演平台来赋予公众可见性,同时,公众也通过媒介提供的平台实现自己对可见性的追求。与传统媒介只是提供信息假定的赋予方式不同,当下的网络新媒介承担着赋予某些事物可见性的功用③。而可见性的获得要求公众主动参与到媒介展现中来。
传统媒体时代,由于地缘或社会资源的限制,乡村青年很难获得相应的文化话语权。然而,互联网媒介的诞生给予了人们获得话语权的机会,也使得原本不能被看见的信息中下层群体可以通过技术的力量走到前台,从而获得可见性或增权赋能。原本位于信息中下层的乡村青年在新媒体平台崭露头角,其媒介展演与实践的过程是媒介社会学中经久不衰的话题。新媒体技术已经赋予了大众自我展演的机会和可能性,那么乡村青年群体如何通过新媒体实现自身的可见性?这一问题引起了众多学者的关注。本研究以美食视频博主“滇西小哥”为例,探寻乡村青年实现自身可见性的内在逻辑,并分析在乡村振兴背景下乡村青年可见性的获得对乡村文化的整体性影响。
二、生命历程:再嵌入的视频化生存
为了更好地深描乡村青年群体的可见性过程,笔者引入生命历程的视角来加以考量,这也暗合了生命历程社会学的观点:研究者需超越个体和家庭的层次,将生命变化与宏观的社会结构、长期的历史背景结合起来,且不能忽视宏观的社会结构性因素的影响④。对“滇西小哥”媒介实践生命历程的溯源是探究其可见性不可回避的问题,由此可更好地理解新媒体赋权的过程。总体来说,“滇西小哥”经历了从脱嵌到再嵌的三个社会化阶段。
(一)返乡入场:个体化回嵌
“滇西小哥”,本名董梅华,她出生于云南保山的一个小山村。从小在农村长大的她经历过贫苦生活,立志要认真读书,出人头地。2012年,她凭借优异的成绩在四川警察学院毕业。毕业之后,她成功进入一家互联网公司,拿着不错的薪水。她本想在城市干出一番大事业,让自己的家人摆脱贫困,过上好日子,但2016年,父亲因病住院,她只能被迫离开工作岗位,回到小山村,照顾生病的父亲。为了补贴家用,她通过销售家乡土特产获得收入。刚从城市回到农村,对家乡的经济发展情况不甚了解的“滇西小哥”在销售土特产上屡屡碰壁,而且在远离家乡后回到家乡的陌生感也让她倍感无奈,难以融入。学者朱妍和李煜提出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处于“传统脱嵌”的状态。传统脱嵌指的是公众脱离家乡传统的社会结构,并且不再认同家乡传统的生活方式⑤。“滇西小哥”在返乡后也面临着传统脱嵌问题,这迫使她必须寻找一种方式,回嵌到农村社会结构中。
(二)数字进场:叙事化再现
伴随新媒介技术对于乡村社会的深入影响,短视频应用开始潜移默化地介入村民生活中。作为一种媒介技术,短视频甚至成为乡村发展的内生力量之一。短视频凭借其记录性的特点,使得视频创作者可以从自己的视角记录自己的生活。2016年,被迫返乡的“滇西小哥”抓住短视频行业的浪潮,开始了她的乡村短视频实践之路。“再嵌”是一种自我认知和协调的过程,个体在“再嵌”的过程中会不断地调整自己的状态,从而适应眼前的生存环境,并做出一定的行为反应。在短视频创作初期,“滇西小哥”的“再嵌”策略是模仿,她跟随互联网中兴起的土味文化,制作了“油炸竹虫”等猎奇视频,吸引观众的眼球,实现了数字进场。但是通过分析用户粉丝的反馈,她发现这种做法不能长久地留住受众。于是,她结合周遭环境,重新思考视频内容与叙事风格。经过一段时间的摸索,她开始在视频中记录自己的田园生活,叙述云南美食从食材准备到成品展现的全部过程,并且在视频中融入云南的田园风光,以及她与家人其乐融融的日常生活等元素。2019年9月,“滇西小哥”将视频时长由原来的5分钟左右延长至10~15分钟,以“美食创作生活”为主题的视频内容从此定型,她也由此初步完成了重返乡村的“再嵌”过程。
(三)资本在场:平台社会数据化勾连
乡村短视频迅猛发展,一定程度上也使得乡村卷入平台控制与算法数据的宰制之中。资本平台与数据流量的在场,约束着乡村短视频的文化实践。所谓“在场”,指的是由特定的大众传播制度及相应实践所建构的媒介时空中的一种“结构化”存在及象征意义⑥。资本在场指的是资本在短视频平台这一行动的场域中对视频创作者的种种限制与制约。2017年,“滇西小哥”加入MCN机构Papitube。该机构是由短视频创作者papi酱与泰洋川禾创始人杨铭于2016年4月成立的,帮助签约作者进行有效推广、垂直化经营以及商业变现。“滇西小哥”加入Papitube后,以自己优质的视频内容和公司的支持,成功获取流量并火爆全网,实现了自身可见性的资本嵌入。截至2022年2月20日,“滇西小哥”在全网粉丝量已突破千万,成为YouTube十大中文博主之一,微博视频累计播放量达到13.54亿。在平台社会,算法技术已嵌入赋权与可见性的过程中,并重塑乡村社会权力秩序⑦。“滇西小哥”的视频化生存不仅基于现有的平台资本的在场,而且与数据化的媒介环境密不可分。
三、实现路径:场景、文化与关系的三重勾连
(一)场景连接:数据算法权力的延伸与控制
媒介化时代,数据算法与信息技术使人类生存方式、思维方式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变革。新媒体场景在为大众提供自我展演空间的同时,也为大众提供了数字化生存的渠道。技术变革与新型基础设施的发展为“滇西小哥”的视频创作之路打下了坚实的基础。2016年被视为短视频元年,短视频的出现为信息中下层群体提供了追求可见性的机会,视频创作者通过短视频技术实现自己的生活场景与视频场景的连接,将现实的场景有选择性地录制在视频中。然而,“滇西小哥”在通过短视频呈现自己生活的同时,也被短视频媒介卷入线上的数据化平台中。
在普通人拥有了视频记录权、创作权,获得了更多的可见性之后,他们逐渐形成了一种新的视频化生存方式。这种生存方式既是一种日常生活的媒介化,也是媒介化后的日常生活⑧。“滇西小哥”返乡后,便进入了一种家庭主妇的生活状态中。一日三餐,柴米油盐。她每天很早就起来,叫上自己的家人去乡间寻找做饭的食材,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她与亲人的日常交流以及与宠物的开心逗乐都用视频记录了下来。她将自己朴实的生活,借助短视频媒介发布到互联网空间,视频映射了她的日常生活,也使她逐渐适应了视频化生存状态。
然而,短视频背后强大的算法体系,使得短视频创作者必须摸索出自己的视频内容定位,精准的定位会为流量的获得提供保障。“滇西小哥”在生活中会不自觉地审视她周围的一切,以获得与自己视频内容定位相匹配的素材来源。同时,她也会时刻关注视频的播放量和点赞量,并通过受众的反馈进行一定的调整,强化粉丝黏性。正如喻国明教授所言,“构成智能时代‘基础设施’的算法是一种更高意义上的媒介,它通过一系列判断架构连接、匹配与调适价值关系,形塑认知、建构关系、整合社会。”⑨因此,可见性不仅依赖于媒介技术的物质性与可供性,而且突出算法权力的控制性与反身性。
(二)文化传递:劳动化叙事与全球传播
智能媒体的出现使得传播环境、媒介和受众关系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也带来了异域文化之间的互动共联。抖音、B站等平台的出现为国人向外界展示中国文化提供了一种话语空间场域。笔者在对“滇西小哥”的视频考察中发现,其视频中通过对云南美食的劳动化叙事、云南方言的情感化传播以及云南文化的全球传播,实现了中国民俗文化的国际化传播。
其一,云南美食的劳动化叙事。“滇西小哥”的每一条视频都有自己和家人以及周围邻居们辛勤劳作的身影,她将自己家乡美食的制作手艺与自己的劳作相结合,展现出独有的劳动美、生活美、自然美。可以发现,这种劳动化叙事作为一种媒介展演策略,促进了乡村品牌的重塑与传播。“滇西小哥”将自己的劳动过程融入视频叙事之中,看似只是一种对自我日常生活的记录,但其实也包含了对于乡村品牌形象的一种塑造。“滇西小哥”通过劳动化叙事,展现出乡村独有的慢节奏、劳动美的生活方式。不仅激发了城市人对乡村的向往之情,而且她以云南保山市文化和旅游宣传大使的身份,带动了乡村旅游的发展。也就是说,通过短视频的劳动化叙事,不仅实现了乡村文化的再现,还促进了乡村的产业振兴。
其二,云南方言的情感化传播。乡村方言作为一种地域性的口语文化,彰显着本土文化及社会情感结构。在“滇西小哥”的视频中,人们用于日常交流的并不是普通话,而是他们的方言,浓浓乡音是对云南滇西文化的展演与再现。在媒介化背景下,“滇西小哥”的家乡方言通过视频的方式被激活,但此时的方言并不是一种获得点赞量的营销策略,而是一种乡村文化的传播。这种熟悉的乡音以及朴实安稳的生活,勾起了无数离散不在场的滇西青年的乡愁,通过新媒介对乡音的广泛传播,实现人们对本土文化的共情与共享。
其三,云南文化的出圈与全球传播。网络的分布式传播特点为中国文化走向世界提供了坚实的技术基础。“滇西小哥”借助短视频平台,推动云南文化走向世界。在她的视频里,家乡是清晨将新鲜的食物从田间摘下,在暖和的柴火里,变成热气腾腾的美味佳肴;家乡也是全家围坐在一起,促膝享用家里的美食,阿公阿婆脸上洋溢着的微笑。用视频不断记录云南美食与文化风俗,将中国乡村宁静而闲适的生活场景通过短视频平台推广至世界。“滇西小哥”短视频的成功出圈,使云南本土文化乃至中国乡土文化实现了全球化呈现。
(三)关系互联:从商品化到情感化的转向
网络传播的发展从Web1.0的“内容为王”转向Web2.0的“关系为王”。在Web2.0时代,人与人、人与技术之间的关系是信息中下层群体实现可见性的关键因素。笔者在考察“滇西小哥”发布的视频作品后发现,她与粉丝之间的关系并不是简单的互动,而是存在着商品化的亲密关系,与资本流量之间的关系也并非顺应或服从,而是博弈与共存的动态关系。粉丝是网红经济不可或缺的一股力量。无论哪个短视频平台,“滇西小哥”都在评论区积极与粉丝互动,每条微博回复评论约十条,回复的主要是用户对其产品的反馈、视频中菜品的制作手法以及乡愁方面的内容,这也充分拉近了她与粉丝之间的关系。出于商业目的,“滇西小哥”与粉丝亲密互动的过程也一定程度上被商品化和利益优先化,即通过一种情感营销来进行商品销售。
“滇西小哥”的短视频中还存在一个动物主角,即宠物“大王”。它是一条阿拉斯加犬,体型庞大,深受网友喜欢。而“滇西小哥”也借助动物萌宠化的视觉形象来获取粉丝受众心理上的接近,将宠物形象融入商品海报中,提升宣传效果。此时,除去粉丝对“滇西小哥”所宣传的美食的喜爱外,宠物的戏剧化张力也为粉丝购买产品起到了心理暗示的作用,粉丝在不知不觉中被商品化了。“在媒介技术演进的语境中,媒介技术与情感的互动关系表现为媒介技术与情感的共在性、媒介技术与情感的具身性。”⑩在短视频中,不论是与粉丝的亲密互动,还是通过萌宠动物的视觉展演,都延伸了传播符号形态的情感表达,表现出日常生活中的情感元素。这种数字媒介实践唤起情感的过程,不仅传递了乡村文化,而且促进了乡村青年群体可见性的获得。
四、乡村振兴背景下可见性的文化创生
(一)助力中国数字乡村振兴与转型
数字化是乡村经济发展的新阶段与新方向,可加快乡村经济信息化转型,开启城乡经济融合新局面,催生新的乡村产业形态⑪。直播带货作为互联网技术的衍生品,通过其完善的产业链,也有助于实现农村农业转型升级。“滇西小哥”通过短视频技术将云南美食传递至网络场域,实现裂变式传播,同时经营电商平台,与消费者进行线上产品交易,并通过各个社交媒体评论区以及店铺评价接受反馈。依据用户反馈,不断提升农产品质量,最终形成一条自产自销式完整可行的产业链。“滇西小哥”不仅通过社交电商产业链获取利润,改善自身经济情况,而且带动了乡村经济产业发展,助力数字乡村转型。
充分利用数字媒介技术带来的巨大红利,能从根本上促进乡村文化的生产、传播和消费,数字技术为乡村“文化+产业”的全面融合提供了可能。目前,线上直播带货已经成为中国农村经济良性互动的重要一环。自淘宝在2019年开启“村播计划”后,以快手、抖音为代表的短视频平台也将目光投向农村地区,让“三农”领域创作人成为自己家乡的代言人,实现中国数字乡村发展与转型。乡村短视频与直播带货,将乡村推向媒介前台,并卷入全球化、商业化与媒介化的浪潮之中。
国家数字乡村战略的提出为乡村数字化经济的发展提供了空前绝后的机遇。数字乡村依托线上经济的拓展,以数字化信息网络为重要推动力,以智能化信息技术为重要载体。数字技术具有传统媒介技术不可复制的优势。数字媒体具有便捷性强、信息量大、互动性强、个性化程度高等特点,不仅能吸引乡村青年,促进乡村数字化建设,还能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乡村文化与农业生产之间的壁垒,丰富乡村优质文化的内涵与外延,甚至能打破乡村文化资源的壁垒,加快城市文化资源与乡村文化资源的借鉴融合,促进乡村优秀传统文化资源的开发,实现乡村文化跨越式发展,助力乡村振兴。
(二)铸就乡村共同体意识与身份认同
在新媒体技术出现之前,以电视、广播和报纸为主的传统媒体挤占着乡村社会的公共空间。原来由口语主导的“强连接”被削弱,乡村内部的交流呈现“弱连接”模式。但是微信、短视频等新媒介的出现,让原本疏离的村民变得熟络了起来。生活在农村的居民开始通过微信交流日常以及乡村发展事务,并且能通过视频通话等方式实现离散在外的村民“共同在场”,促使村庄内部关系重新变为“强连接”。与此同时,受城市化与全球化进程的影响,远离家乡在外打拼的乡村青年从乡村在场青年拍摄的视频中获得归属感,唤起了此前近乎被消解的乡村共同体意识。
媒介在乡村文化生活中主要发挥呈现与连接两方面的作用。一方面,媒介凸显了农民的主体性;另一方面,媒介具有连接整合的作用,强化村庄内部的共同体意识⑫。短视频的出现无疑给那些离散在外的乡村青年提供了重新认识自己家乡的契机。他们主动利用短视频记录生活和表达想法,主动讨论家乡发展问题,为自己的家乡建言献策,并不断对乡村文化进行融合创新,强化了文化自信,也实现了身份认同。
短视频等新媒体的出现使得乡村实现精神上的连接和认同,乡村逐渐糅合成一个庞大的线上群体⑬。生活在城市的离散青年与乡村在场的家人们通过微信等新媒体“再连接”,由于他们有着相同的文化环境与风俗习惯,在处理自己乡镇事务中保持一致,并且都致力于为自己的家乡做贡献。如果说广播的出现使中央的政策可自上而下在农村普遍传播,将村民信仰与国家精神联系在一起,那么短视频等新媒介的力量则使乡村文化在赛博空间中实现裂变式传播,增强乡村青年对乡土风俗的认同,并且对自己家乡的发展保持高度的自信,从而增强自己的文化归属感,铸就乡村团结。
(三)促进国家形象的对外传播
国家形象是一个国家民族精神、国家意志的集中体现。短视频以其时长短、传播速度快、互动性强等特点,深受现今互联网用户的喜爱,成为建构国家形象的重要力量。以快手、抖音为代表的短视频平台,以较低的准入门槛,吸引了大量的农村用户,致使我国形成了一种全民短视频的热潮,而这种趋势也为彰显我国的国家形象提供了良好的契机。以“滇西小哥”为例,2016年,她作为返乡青年,在短视频中用自己的视角记录下家乡的生活和文化风俗以及祖国的大好河山,在营造“传播共情性”的同时传递美好的中国形象,并且通过自己、家人和家乡的村民等符号弱化宣教意味,增强传播感染力。这种淳朴的民风民俗,不仅感染了国内网友,而且通过Tik Tok、YouTube等平台实现国际传播,实现与海外网友的共情。
短视频传播范围广、精准性高,成为我国宣传国家形象的重要媒介载体。抖音海外版Tik Tok等短视频平台正是通过大数据等手段,实现有趣味、有内涵的中国短视频的议程设置,将中国传统文化以简单朴实的方式进行展现,让外国各年龄层的受众接纳中国文化,建构了一个“离散”的文化圈层。东西方文化再次交融,中国文化在新媒体平台屡屡破圈,诸多短视频博主实现海外圈粉,彰显出了中国文化的国际形象。
基于社交媒体的国家形象的传播是一种去中心化的传播,营造了一种“自下而上”的传播趋势。这种传播趋势对内弥补了原有“自上而下”传播模式的不足,对外消解了西方话语对中国文化建构的影响。鉴于全民传播风潮,中国乡村文化通过赛博空间的裂变式传播,让各国受众都能更加多元地了解中国,有利于国外受众丰富对中国乡村的形象认知,消除对中国的刻板印象,从而使中国在形象塑造上获得更多的话语权。“自下而上”的传播趋势通过描述平民生活,关注中国普通人的生活状态,实现国内外受众的共情。诸如“滇西小哥”等自媒体人,将中国山水、乡村文化、人情风俗杂糅在一起,构建视频内容,立体展现中国乡村的形象风貌,丰富全球话语体系下的中国形象,打破了西方对中国形象的刻板成见。
五、结论与反思
在新媒介赋权背景下,可见性的研究范围已经逐渐被扩展至政治、文化等领域。网络新媒介的发展与变革极大地拓展了公共空间的内涵,使乡村青年群体获得可见性成为可能。他们借助短视频平台,通过自我的主动展演以及资本平台的介入,拓宽了自身获得话语权的渠道与机遇。网络数字经济催生了新兴的数字劳动实践,其灵活多变、个性化的用工形式最大化地激发劳动者的自主性,一定程度上改善了乡村群体在传统劳动场域中较为被动的境遇⑭。在媒介化语境下,乡村青年群体能够借助技术的可供性将日常生活通过视频化的方式传输至网络空间,并且通过网络媒介的分布式传递,实现自我身份认同,从而获得可观的经济收入,改善生存条件。
乡村青年从传统乡村社会结构中“脱嵌”,又在返乡后通过视频化生存方式实现“再嵌”,从信息中下层发展为建设乡村的中坚力量。在此过程中,他们不断调整自身的实践方式,逐渐实现了个体乃至群体的可见性。新媒体技术不断激发公众的主体性,在提高用户身份地位的同时,也面临着政策风险和平台制度的规制,易出现“唯流量”等问题。首先,要从风险防控的角度出发,警惕算法数据对商业化、媒介化与个性化带来的公共性流失与主体性消解的风险,注意其可能带来的信息茧房、算法偏见以及主流价值观引导缺失等方面的技术陷阱。其次,要提升公众对数字媒介平台殖民风险的认知,重塑乡村青年群体的文化价值观,促进乡村文化的健康发展。最后,加强对“三农”短视频创作者的扶持,提高参与主体的积极性,鼓励乡村青年投身于数字乡村建设中,做乡村文化的代言人和推广者,以自身的媒介实践推动乡村发展,助力乡村振兴。
注释:
①姜红,开薪悦.“可见性”赋权——舆论是如何“可见”的?[J].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03):146-153.
②陆晔,赖楚谣.短视频平台上的职业可见性:以抖音为个案[J].国际新闻界,2020(06):23-39.
③孙玮,李梦颖.可见性:社会化媒体与公共领域——以占海特“异地高考”事件为例[J].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02):37-44.
④石义彬,邱立.弱者的力量:生命历程视域下留守妇女的社交媒体赋权[J].新闻与传播评论,2021(05):13-27.
⑤朱妍,李煜.“双重脱嵌”:农民工代际分化的政治经济学分析[J].社会科学,2013(11):66-75.
⑥郭建斌.在场:流动电影与当代中国社会建构[M].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9:2.
⑦周孟杰,卢金婷,刘子瑨.返乡创业短视频的传播语境与赋权机制研究[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2(05):147-155.
⑧彭兰.视频化生存:移动时代日常生活的媒介化[J].中国编辑,2020(04):34-40+53.
⑨喻国明.技术革命主导下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学科重构与未来方向[J].新闻与写作,2022(07):15-21.
⑩孙强.媒介技术演进中的具身性情感研究[J].新闻与传播评论,2021(04):72-85.
⑪李翔,宗祖盼.数字文化产业:一种乡村经济振兴的产业模式与路径[J].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0(02):74-81.
⑫沙垚,张思宇.公共性视角下的媒介与乡村文化生活[J].新闻与写作,2019(09):21-25.
⑬刘娜.重塑与角力:网络短视频中的乡村文化研究——以快手APP为例[J].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06):161-168.
⑭张文娟.“底层”数字化生存的可能及其意义——基于“60后”下岗工人个体生命历程的考察[J].新闻记者,2020(11):3-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