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情书
2022-02-18刘烨BerlinZhang西西
刘烨 Berlin Zhang 西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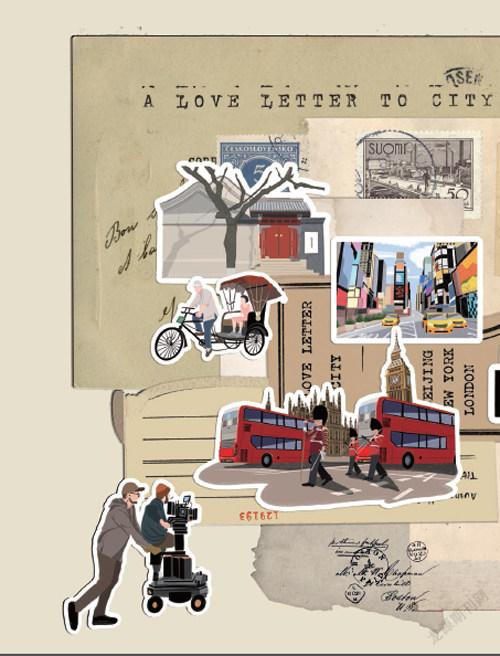
早上好。我刚刚完成今日冥想,屋外很安静。
这么一算,你回法国也有小半年了。和小凤聊起来这些时,我总开玩笑:“艺术家朋友都相继离开了,剩我孤身一人在家画画。”好在北京永远不缺有趣的人,我认识了不少新朋友,组成了一个小团体,活动特别丰富,大家都乐意分享自己的技能。以前我不是特别爱运动,现在特别愿意参加瑜伽、冥想这样的活动,也会不定期开一些小型绘画工作坊,以画画的形式和大家分享我的生活见闻。好奇怪呀,突然给自己的生活增添了这么丰富的活动,日子反而变得愈加简单了,日常变得十分规律,好像全部进入了一种“减少”的状态,大概这就是找到了理想的生活节奏吧。
前阵子在家附近闲逛,我总觉得走到哪儿都有施工建筑,散步都变得不怎么顺溜儿了。但前几天出门的时候,我发现北新桥和雍和宫附近那一段不再施工了,视野也变得开阔起来,于是我舒舒服服走了一圈儿 ,心情大好。
最近我遛弯有些新发现,东四北大街开了一间临街的咖啡馆,透过大大的落地窗几乎能看见店里的一切。天冷的时候挨着窗边坐会儿,在太阳出来的日子就去户外,无论怎么都是舒服的状态。我去了好几次,老板是一个女孩,总是一个人打理店铺的一切,井井有条。这里有点儿闹中取静的感觉,你一定也会喜欢的。我还和朋友在鼓楼东大街发现一间适合小聚的 Live House,喝杯酒,看会儿演出,挺放松的。虽然不方便出去旅行,但我在北京的日子也有滋有味。以前我从来没想到自己能在北京生活这么多年。如果一定要说这里有什么吸引我的,可能还是这里的人。这座城市特别包容,你无论在哪儿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生活步调。好多人看了我画的《慢游记》后,说我是“胡同艺术家”。我就得澄清一下了,北京可真不是只有胡同。你肯定明白我的意思,对我来说,胡同很重要,它总是给我一种住在北京但又不是北京的感觉。这是一片很生活化的区域,安安静静地散发一种粗粝的质感,我特别珍惜在这里的生活。
10月的时候,我开展了一个“蓄谋不久”的计划。哈哈,我就是这么随意,像一个游戏一样,每天做一件新的事情,可以是突破性的尝试,也可以是精神上的探索,或者干脆是去“打卡”一个新地方,无论怎样都行,重点在于“新”。比如,突发奇想五点起床,赶在景山公园六点开门前到达,这一天的目标是去景山看日出,但是还没进门,我就发现了不一般的东西。首先,我肯定不是最早的,前排的大爷大妈们个个都精神头十足,他们互相认识。有一位奶奶是专门来喂猫的,规律到连附近的两只猫都知道她要来了;有一位大爷是来练嗓子的,六点准时入园,吆喝声就没停过。后来我们一路往里走,到了山顶,相互打招呼,拍几张照片,各自散去。这趟日出看得多有意思呀,虽然早起有一点儿痛苦,回程路上却特有精神。
2021年11月,我接到了一个特殊的任务 —— 为20位残障姑娘绘制肖像。那是我第一次这么近距离集中接触残障人士,我有很多感触。大概也是2021年重新拥有了大把的时间画画之后,我发现自己很愿意从最简单、纯粹的情绪出发,画一些实实在在存在的人或者场景,这可能是非常私人化的情绪表达吧。就和你经常喜欢拉上我们去鼓楼逛一圈差不多,顶伞、画画、踢毽子,我越来越喜欢这种感觉了。
新年计划我都想好了,希望可以再去巴黎生活一阵子。我想把北京和巴黎两地的生活见闻都画出来。如果真的可以实现,我们再一起去巴黎的大街小巷找乐子吧,那也是我一直想念的地方呀。
期待我们早点儿相见吧!
刘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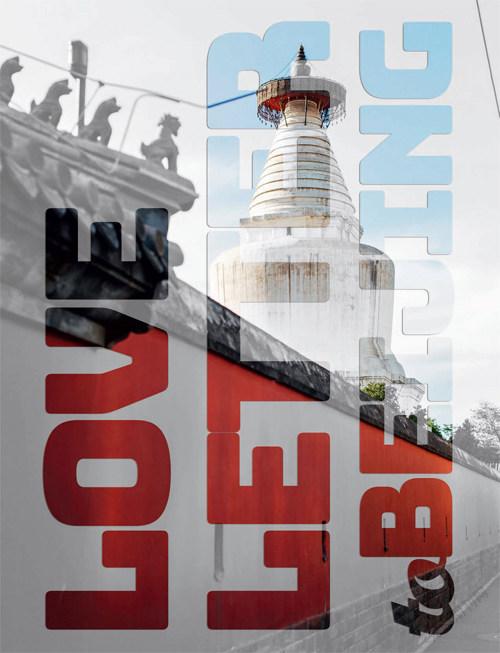
聪聪,好久不见。提笔回信,讓我的思绪再次回到在北京生活的那些日子。
好几个月了,我开始学着适应一件事 —— 家附近步行可及的广场不再是鼓楼 —— 那是我最想念的地方。也是在这样的时刻,我突然想起一位朋友以前对我说的话:无论你身在何处,心中的牵绊总是那些曾经与你相遇的人。我想,我之所以如此热爱北京,是因为这座城市那么鲜活,你们那么可爱,在北京街头遇见的陌生人也那么可爱。
北京实在太大了。对于像我这样的外国人来说,即使在北京生活了几年,也很难看遍它的全貌。也许,只有东城区才是我真正熟悉的北京,那儿是我生活的地方,有我最喜欢的胡同。穿梭其中,我时常迷路,却乐此不疲。那种感觉很独特,不知为什么,我总觉得只有在胡同里才真正来到了北京。日子绵长而舒缓,给了我潜心创作的时间,生活就是最好的素材。
我们时常去鼓楼附近的胡同和公园散步,也是在那一片,我遇到了许多有趣的人,用老北京话说,大概叫“顽主”?好像是这样用的。他们的日常生活中充斥着各种各样的户外活动,有放风筝、打弹弓、遛鸟、武术等,太丰富了。我喜欢观察这群人,在我心中,他们就是这座城市中的歌剧演员,任何一个角落都是他们的舞台,这样的相遇总是带给我许多欢乐。
几天前,我在蓬皮杜中心看了一场精彩的演出,编舞师 Jerôme Bel 和中国舞蹈家小柯的合作让我印象深刻。之后,通过一个视频,小柯讲述了她作为一名舞者这些年来的经历,其中提到了中国的广场舞。她认为这是中国最具当代特征的一种舞蹈形式。我是非常认同的,第一次在北京看到一群人在极其响亮的电子音乐引导下同步跳舞时,我感到无比震撼,但这恰恰是一种最真实的日常生活。如今,相比于走进当代艺术作品云集的展厅,我似乎更容易理解这样一种充满生活智慧的文化现象。
当然,北京也有许多鼓舞人心的艺术场所。自从2017年第一次访问国家博物馆,我对那里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后来我又陆陆续续去了几次,时空转换,也产生许多与艺术有关的思考。后来你也经常带我去798,看过各种各样的艺术展览之后,我感觉逛艺术区和逛胡同也有相似之处,漫步其中,绕迷宫一般,也有不少收获。
我常想,在这偌大的城市里,有你这样一位好朋友、好邻居是一件多么幸运的事。你画的画很简单,却很温暖,我喜欢这样的作品。你还记得吗?我北新桥家里的书桌上一直摆着你的一幅画,你画了在胡同里遇见的一位外卖骑手。我一直记得他的样子,也想起了许多北京的马路。大概这就是回到巴黎之后我会一直怀念的东西。
在鼓楼的广场前,我将一把巨大的油纸伞绑在身上,试试看自己的平衡能力怎么样,周围有许多人看着我,以这样的方式和周围的人打个招呼,我很开心。
那些年,我们在什刹海滑冰时遇见的陌生人、在公园里遇到的蘸着清水在地上写书法的老大爷,还有日复一日跳着广场舞的阿姨,就是我最怀念的北京生活啊。
聪聪,你还记不记得我的邻居,就是那位退休的电工?我们从交换食物开始,慢慢熟悉起来,他邀请我走上露台,欣赏他种植的花卉。那一刻,我觉得他太了不起了。大概这就是北京吧,你身边的每一个人都可能是一位默默无闻的“艺术家”,高手在民间,你说是不是?
我一直都特别喜欢你在《慢游记》里展出的那些作品。如果你有什么新想法,一定记得随时告诉我。说不定哪一天,我又会回到北京,咱们接着一起逛胡同去。

见信好。
我离开巴黎已有六年,未曾想到一提起来最怀念的地方竟是楼下的面包店。下楼就能买到的刚出炉的面包远胜过排行榜上的第一名。
我记得卡尔维诺在《看不见的城市》里面这样说过:“你喜欢一个城市的理由,不在于它有7种或70种奇景,而在于它对你的问题提示了答案。”
我是西安人,我的故乡被称作“古都”,但是我天天看到古迹,仿佛看到的只是历史本身,看不到时间的层次,看不到我的城市如何过渡到今天的样子。后来我来到巴黎学习建筑。当我在玛黑区闲逛的时候,走出一条小街突然就看到了蓬皮杜,那栋有着裸露排气管的先锋建筑竟然隐藏在古旧的小街小巷里面,就这样突兀地出现在我面前。年轻的艺术家、流浪汉、游客和市民聚在广场前聊天、吃面包、喂鸽子,学生们排着队进入图书馆,那时候我受到的冲击非常大。后来我才知道,那种感受上的“冲突”正是我喜欢巴黎的原因。
刚到巴黎时,我是“睁开眼睛”的。巴黎有很多建于不同时期的建筑,从古典主义到现代主义,我不偏好某一个时代的建筑,也不追逐某一种具体的风格,因为所有保留下来的、我们今天有幸看得到的建筑都是它们那个时代的集大成者。我更喜欢看不同时期的建筑混在一起的状态,时间与时间在空间里碰撞,迸溅出无数碎片,我觉得那些碎片就是建筑物的价值所在。我“睁大了眼睛”去收集这些碎片。
做了几年建筑师后,我反而“闭上眼睛”了,我想探索人与建筑到底是什么关系。建筑不应该是孤立存在的盒子,它必须是很好“进入”的,就像那年我走出一条街道就撞见了蓬皮杜。从此以后,蓬皮杜就从一个有仪式感的地方变成了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我有时特地约朋友去那里见面、吃饭,有时偶尔路过,又正好有时间,就顺便进去看看。当人与建筑产生了某种连接时,他就能看到建筑最令人惊喜的部分,但那是建筑师“设计”不出来的部分。
写到这里,我暂时闭上了眼睛。脑海中的幻灯片播放了在某一个整点,埃菲尔铁塔闪光的样子。我感到很平静,又很幸福。铁塔已经不仅是一座建筑,更是象征着幸福的暖流。我喜欢能给人带来幸福感的建筑。我也很确信,我眼睛的“一睁一闭”成为我与巴黎同在的方式。
在巴黎生活的后几年,我搬到了最喜欢的玛黑区,买了一辆自行车,骑车上下班。从前我以地铁站为坐标系,点对点地在家与公司之间通勤。改成骑车之后,我才深入了巴黎的肌理。不急匆匆地回家了,而是悠闲地找一家小酒馆喝一杯,去别的工作室串门,或是漫无目的地瞎逛。从圣殿老妇街的当代画廊晃悠到毕加索美术馆,在一间没有见过的新开小店门前驻足,或是被门头吸引,或是喜欢橱窗里的某样摆件,于是我停好自行车信步走入。巴黎真是一个适合骑车去发现的城市,虽然卢浮宫这样的“动脉”很壮观,但是稀松平常的买手店、画廊、古董店、餐厅和咖啡馆就像“血管”一般遍布城市的街巷。我喜欢“偶然的相遇”,家里那些心仪的小玩意儿就是这样淘来的,至今仍在使用。
2020年的疫情促使人们更多地去思考居住的环境。建筑是庇护人身的地方,建筑里的绿色空间是抚慰人心的地方。但是随着住在城市里的人越来越多,土地越来越有限,人能与自然产生的互动越来越少。多少年来,建筑师都在城市化进程中寻找与土地、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方法。我还能回憶起第一次看到你为盖布朗利博物馆做的垂直花园时那种豁然开朗的心情 —— 棕红色的博物馆外墙上布满了不同颜色和形态的植物,如一块地毯般高低起伏,那是一种前所未有的植物观赏体验,它在不占用土地面积的同时,扩大了绿化的可视范围,让人们在很远的地方都能欣赏到。会呼吸、会成长、能循环的建筑,也如闪光的铁塔一样,是能带给人幸福感的建筑。
说来遗憾,我只在2016年回过巴黎,之后便忙于工作,疏于休息。给你写信的时候,我突然在想,如果有机会重返巴黎,我一定要沿着塞纳河散步,再选一个可以看见巴黎圣母院的地方野餐,吃饱喝足后,闲逛去蓬皮杜看看有什么新展,末了去爱乐厅听一场音乐会。那该是多么完美的一天,我在心里盼望着这一天早日到来。就写到这里吧,祝你生活愉快,身体健康,工作顺遂。
你的朋友,姜元

你好,很高兴收到你的来信,我们因为一个项目而认识,一晃都过去五年了。你在让· 努维尔工作室时参与设计的爱乐音乐厅已经开放,静候你来听音乐会。
我很高兴你发现了打开巴黎的最好方式,就是从地下走到地上来,而你描述在玛黑区闲逛的情景竟让我追忆起我的童年和青少年时期。
我记得小时候每逢周四 —— 因为那是学校放假的日子 —— 我的母亲都会带我去看纪念碑,去参观博物馆或是去看动植物展览。那时候我的母亲热衷于自己做衣服,我们常常步行去香榭丽舍大街上的漂亮面料店 Max和 Bouchara,之后步行到老佛爷百货或是春天百货,我的父亲会在那里接我们回家。
20世纪70年代,我在巴黎六大念书。课间有一两个小时的空档时间,我便步行去拉丁区或圣日耳曼区的咖啡馆喝一杯咖啡,我最喜欢的是花神咖啡馆。晚上去剧院看完演出后,我就跟朋友去圆顶餐厅(La Coupole)共进晚餐。我一直很喜欢美国酒吧 Rosebud。当我还是学生的时候,我每周三晚上都在莎玛丽丹百货公司(Samaritaine)的水族馆卖热带鱼,用赚来的钱去塞纳河另一边的 Alcazar 餐厅看表演,特别是看香颂演出。说起来,除对热带植物的热情之外,我还喜欢看香颂演出。我记得很清楚,1962年10月,当时我只有9岁,我被父母带去看了伊迪丝· 琵雅芙 (Edith Piaf) 最后一次演唱会,我大概是全场年纪最小的观众。虽然我至今不会唱歌,但我和帕斯卡住在一起,他是一位声音非常优美的歌手。
我已经习惯人们因为我的绿色头发而固执地看向我,以至于我也会毫不犹豫地看不同的人,看他们的长相、衣服和举止,就像我观察和分析热带雨林中的植物多样性一样,步行是我观察生活多样性的方式。
你在信中提到了“令人感到幸福的建筑”,由于我是植物学家,而不是建筑师,所以我看待建筑的角度是很个人化的,也是很具体的。如果说有什么让我感到幸福的建筑,那一定是我的家 —— 因为它是我全凭自己的喜好建造的地方。
现在我住在巴黎南部,就在意大利门后面不远。我在那里找到了一座很大的 Loft 式房子,一看到它,我就隐隐约约地有预感,我梦想中的家即将变为现实了。这要归功于它的尺寸 —— 无论面积还是高度 —— 给了我充足的发挥空间:我把我的工作室建在了一个巨大的水族箱之上,低下头就能看见鱼和乌龟在我脚底下游泳;书桌背后是一个大的植物墙,上面有鸟窝,有蜥蜴和青蛙。我终于在家里重建了一座热带雨林。
但无论房子的位置如何、大小几何,我认为每个人都可以建造让自己感到幸福的建筑。我从儿时改造我的小卧室开始,到传统的奥斯曼式公寓,再到郊外的小屋,最后才是现在的 Loft。说到底,“令人感到幸福的建筑”永远跟个体感受有关。当然,人们越了解自己,他们就越能真正实现心中畅想的那个画面。
你说巴黎解开了你关于 “ 建筑的时间性”的疑惑,你“睁开眼睛”看到冲突, “闭上眼睛”思考感受,而我此刻也试着闭上眼睛 —— 我看到了我15岁时创建的第一面植物墙。尽管我从小就对异国情调的鸟类和鱼类感兴趣,但是到大学我才系统学习生物学,并在19岁前往马来西亚和泰国,看到了真实的热带雨林。后来我被任命为 CNRS的研究员,我经常去世界上其他的热带雨林研究植物的习性。植物最让我着迷的是它们适应环境的能力,同一种植物可以通过不同的方式生长,这取决于它长在地面、岩石、树干上还是斜坡上,与动物和人类相比,植物能够更有效、更和谐地自我改造。
在我看来,人类不是因为疫情才去思考居住的环境和身处的空间,我们记得住在被植物覆盖的洞穴中的舒适感 —— 这是存在于我们基因里的。我建造的植物墙不过是唤醒了人类作为穴居人的久远记忆。如果说疫情之前我一直在“出去”,那么疫情之后我不得不“回来”。疫情让我被迫中断考察,待在家里,但幸运的是,我真的好好利用了家里的小型生态系统来亲近自然,获得喘息,我的家庭成员 —— 我指的是我们的植物、鸟类、鱼类 —— 构成了一个不断变化的世界。疫情根本没有影响我,我无须到外面购物,可以在家里锻炼,甚至每天在露台上淋浴,而且帕斯卡正好热爱下厨,我们享受在家里就餐。
再次感谢你的来信,让我回忆起一些往事,这对我来说意义重大。我也诚挚地期盼你能重回巴黎,再看看这座城市的变与不变。
祝好。
你的朋友,Patrick Blanc

节日的氛围越来越浓了,上海的街道更热闹了,东京一定也色彩繽纷吧?不知你是否别来无恙。
2020年年初我回国时,新冠肺炎疫情刚发生,我在东京停留的时间也比计划延长了许多。转眼又快两年了,我不禁感叹时光流逝如此匆匆。
记得有一次,受你邀请前往位于浅草的舵轮俱乐部,在这个小而温馨的场所里演奏,度过了愉快的一晚。
东京的爵士乐酒吧比上海的规模小很多,但数量的确惊人。我偶尔会怀念那些为演出忙碌的时光,常常一边品味便当的余味,一边着手后面的工作,那种感觉真好。但我最想念的还是父母,日常生活中的每一件小事一幕幕出现在眼前。父亲年轻时的梦想是成为歌手,他非常热爱唱歌,于是每一次回到东京,我一定抽出一天时间和父母去唱卡拉OK。和父母一起唱歌也变得如此珍贵,我不确定,也许这就是我惦念的东京生活。
对我来说,回到东京一定要去的地方是银座。没错,我们东京人也是喜欢银座的呢,来到银座,我才能找回东京的味道。光是去山野乐器银座总店和雅马哈银座店买乐谱、音乐专业书籍和 CD就足够让我逛上一天。如果时机合适的话,我还可以参加有趣的活动和讲座。
我总觉得东京这几年几乎不曾变过什么,这里从来都不缺少有才华的爵士音乐家。在爵士乐酒吧和居酒屋,每家店的演奏者日日更替,不仅有以音乐为业的专业演奏者,也有一边从事其他工作一边进行演奏活动的爵士乐爱好者。可以说,在东京,只要愿意,你随时都可以接触爵士乐。
也许是巧合,从1967年开始经营的六本木爵士酒吧 Izumi是一家由上海人经营的小店。它是我最喜欢的地方之一,上一次回国我也回到那里演出。另外,高田马场的 Intro、吉祥寺的 Sometime、阿佐谷的 Manhattan等都是让人兴奋的地方。我离开东京多年,每一趟重逢都来去匆匆,是否有新的地方出现呢?
回想起来,一起在东京完成的每一场演出都是属于我们无可取代的美好回忆。但偶尔听朋友说起,好几家老店都相继关门了,真是有些伤感呢。
我已经在上海生活超过十年,十分开心,却很难只用“开心”描述这样的日子。这里的生活太丰富了,光是料理的种类就让人眼花缭乱。当东京的朋友来上海玩时,我总是会犹豫,该带他们去吃湖南菜、涮羊肉还是烤鸭呢?
对了,最近,我有点儿想念日本海滨烧烤店的味道了。虽然我在上海也能吃到美味的海鲜,但日本的浜烧才是最可口的,只需滴上酱油就能还原食物本身的味道。
但上海总是给我带来惊喜。原本以为疫情的存在会打消人们到现场观看演出的热情,但开票3天竟然就售罄了,我和搭档坂本健志都很意外。他从北京赶来,我们一起策划并完成了一场在 Bluenote上海的演出。以爵士乐的形式演奏日本的流行歌曲和动漫歌曲是一次大胆尝试,没想到这些伴我成长的歌曲在中国也有很高的人气。
因为动漫歌曲的改编受到欢迎,我们也萌生了一个新想法,不如把它做成一个系列。对了,我连名字都想好了,就叫“JA*PANE*ZZ”。
给你写这封信的时候,没几天就是圣诞节和新年了,要是这会儿在东京,也许我们就能一起演出了。我们可以在喜欢的爵士乐俱乐部里举办圣诞音乐会,和客人一起享受音乐和美酒,又或者成为“神秘嘉宾”,突然出现在老友的演出中,结交新的朋友。在没有演出的日子,我们就和父母享受特别的家庭日吧,去一家温馨的寿司店、去超市采购、一起去沙滩烧烤,享受料理的快乐。如果有机会,我真想回到东京,和你们一边喝着葡萄酒,一边好好聊一会儿,就这样悠闲地迎接新年。
我常常在刚回到东京的时候感叹,街巷里几乎没什么新鲜劲儿,也许,我们自己才是那个打破时空的元素。与之相比,上海的变化总是迅速。我思索一番,可能正是因为东京和上海之间不远不近的距离,我的思绪中保持着一些复杂的情感,或许,我们的这种距离反而让彼此亲密了不少。
我总是和你聊起這些无足轻重的小事,但就是这样温馨啊。新年了,阳光依旧温暖,让人不由得祈愿“2022年一定是美好的一年”。
满怀感恩之心,保重。
岸祐子

每到圣诞节将近,差不多也到了一年工作终结的时候。当我写这封信的时候,2021年只剩下十几日了。岸祐子小姐一切都好吧?
这两年来,东京甚至整个日本都充斥着“害怕外出”的气氛,就连最低限度的外出也会因为介意周遭社会的眼光而暂缓。人们滞留在家的时间大幅增加了,由运动不足导致的肥胖和精神压力在所难免,我也不得不思考出各种应对办法,比如在室内做运动、使用网络与朋友联络。迄今为止,好像也没什么新意,我们不得不面对无法回到从前的日子。
不管怎么说,东京的城市景观还是有少许变化的。新落成的国立竞技场和奥运村都为城市增添了不少奥运元素,与之相配套的还有道路的改造和修缮,比如完成迁移的丰洲市场和改头换面的涉谷车站。说来真是奇怪,就连一直住在东京的我也开始在涉谷迷路了,出现如此情况,变化该称为“巨大”吧。就拿山手线举例,从车站出来走一段,自涉谷到品川的整个南半部分都快变得让我认不出了,好在上野、御徒町的一些地方还保留着一些古旧而美好的东京痕迹。你若回来,去那里的街道逛逛是不错的。
东京的爵士俱乐部也面临不小的危机。Live House不得不全部休业,音乐家也相继取消了演出。即便如此,我们都相信终有一天会解封,即使处于“休业中”,经营店铺的老板仍会开放预订。大家都是抱着这样的想法:“如果下月能解封,我们一定会演出”。但临近演出时,我们又不得不发出通知:“很遗憾这次也因为不能开店而取消演出”。周而复始,这总是让人烦恼。不过,限制自11月左右开始有些松动,比如出现了一些有时间限定、条件限定的短暂开放。在这两年间,我看到许多店铺不得不停止经营,但也有许多 Live House还在坚持。一些例行举办的爵士乐活动也在慢慢恢复,我们正慢慢适应线上演奏的模式。虽然观看直播和Live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感受,但能重新回到演出的状态,已经是我们久久期待的,每个人都希望以充满活力的姿态告诉观众,日本的爵士乐不会就此沉沦。
住在东京的音乐家正在渐渐习惯这种生活,也尽量避免出现在人流密集的地方,这样一来,自然景观丰富的郊外便成了一个不错的选择。除了有名的高尾山,我在青梅、桧原村都见到了与东京中心部完全不同的风景,那里美得像一幅幅画,完全称得上“治愈人心灵的壮丽画卷”。回到东京之后,我整个人仿佛又多了一些生活的勇气和力量。这样看来,想要好好创作的时候,时不时也需要到这样的地方吸收一些灵感。
不过,对于日常活跃在东京近郊的音乐家来说,东京无疑是充满创造性和活力的。新宿依旧是爵士乐最前卫的演奏据点之一,这一点从未改变,但爵士乐在东京的扩散速度也是十分惊人的,在银座、六本木、赤坂,人们更乐意听到以主唱为中心演绎的乐曲;而在新宿和池袋的 LiveHouse,人们能观赏到更多的现代爵士乐(Modern Jazz)、自由爵士乐(Free Jazz)、甚至是爵士舞(New Jazz)的表演。可以说,在东京,古典的、前卫的、更多元的爵士音乐应有尽有,也正在影响更多人。
说到这,我们也时常感叹,日本人真的很热爱爵士乐。按理说,这种诞生在美国的音乐中,大部分经典歌曲的歌词、术语都由英语组成,对于土生土长的日本歌手来说,英语的发音绝对是一座需要翻越的高墙。但我不得不佩服岸祐子小姐对于爵士乐的理解和发音技能。美国的流行音乐,尤其是爵士乐的歌词,要踩住节奏中的“音韵”,如果发音不好的话,“音韵”不能与节奏契合,听上去就索然无味了,但岸祐子小姐的演唱水平真是毫不逊色于美国本土的爵士乐歌手。上次你暂时归国,我们一起登台,听过后我感叹你的发音实在美妙,真是完美再现了爵士乐的内核。
因为岸祐子小姐常年居住在上海,同台演出变得十分难得。上次演出之后,我也无比期待能够与你再次合作。如果有机会,我也想尝试为岸祐子小姐制作一首不拘泥于传统爵士乐的、全新风格的作品。如果能在保留日本爵士乐特色的基础上加入中国元素,那一定会是非常棒的作品。
不过,一切的前提都是疫情能够被消除,毕竟,回归正常生活节奏才是最让人安心的。AIM乐队是我目前的工作重心,我们这个以钢琴演奏为主基调的三人小乐队正在努力创作一些新作品,也希望和更多优秀的音乐人合作,这当然包括像岸祐子小姐这样的主唱,还有萨克斯演奏家、小号演奏家等。
今年平安度过了,愿新年也是美好的一年。
川畑良之介

从2013年到2015年,我陆陆续续在纽约生活了一年半多的时间。从加拿大研究生毕业的那天,我就搭上了去纽约的大巴,奔赴一个陌生的城市,去和一个念念不忘的爱人团聚。我们在中国城 Eldridge Street租了一间小屋,过起了日子。那时候我们穷得底儿掉,谈恋爱是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颗糖,每天我们都大步地走很多路,又怯懦又痴狂。
今年我格外想念纽约的冬天。前些天我看了《我是监护人》,电影又把我带回在Eldridge Street生活的日子,同一条街道,同样的店铺招牌,连光影打在窗户上的样子都一模一样。离开之后,我似乎想不出如何用一句话来描述纽约,因为纽约本身更像一个形容词,或者是某种混合而成的香料包。
纽约的冬天看起来总是煙雾缭绕的,哪怕是暴雪天气,也会给人一种热气满溢的感觉。很奇怪,我明明是不爱过节的人,但偏偏钟情于纽约的圣诞季,每年11月底到来年2月,整个城市到处洋溢着圣诞节的氛围,这种凄冷中的浪漫才是让人欲罢不能的浪漫。
记得每年冬天路过 Bryant Park, 一听到溜冰场在放的 Mariah Carey的歌,我就觉得整个人被点亮了,不管冷漠的还是压根就不会溜冰的人,都会很想加入溜冰大军。大暴雪的时候,你能看到大街上到处是精神抖擞对抗恶劣天气的人,他们光着腿,披着貂,花枝招展,甭管多大年纪,都不遗余力地在自我表达。这种“生命力” 让我觉得无比受用。谁说“超脱”就一定是平静或者是素色的呢?我也总是会隔一段时间就畅想一下自己65岁时候的样子,也许我会染上蓝色的头发,希望那个时候,我还拥有不老的表达。
对于一个电影人,真实的纽约生活是每天都在上演和电影里一样的故事。闲暇时候,我们都会钻进纽约遍地的独立电影院里。每天在纽约上映的影片都超过100部,Film Forum和 Angelika Film Center是我们常常混迹的地方,只要想看独立艺术电影或者考究的纪录片,我们不用做功课就可以在这之前过去看一场。希望不久的将来,以一个新的身份,带着一部属于自己的作品回到纽约电影节。那个故事应该会从纽约出发,关于我自己,也关于那些我所见到的,同样在纽约热烈地活着的可爱的人。
很多时候,我感觉构成人生的计量单位不是年,而是瞬间。拥有的那些瞬间决定了我们幸福不幸福、快乐不快乐。我在纽约住的时候最好玩的一点就是大家都愿意分享故事,而且你永远不知道今天出门会撞见谁。我在家门口的路上,碰见过穿着居家服买菜的 David Bowie,还有等饺子外卖的坂本龙一和独自溜达的 Patti Smith。我从没想过,我和那些被奉为殿堂级的人物的邂逅不是在闪耀的电影节,而是在我们都蓬头垢面的时刻当面撞上,那种相逢真的是太妙了。
在纽约的日子,很多让我记了很久的时间,都是陌生人带给我的。当我们与陌生人交谈时,有时其实更愿意展示自己天真而脆弱的一面,不是吗?有一次我路过 UnionSquare,不知怎么,就跟一个吹萨克斯的黑人老大爷聊起来了。他觉得我一个中国小姑娘很有意思,就收了摊儿邀请我去家里吃饭。我在他布鲁克林的家里,见到了他80多岁的妈妈还有一大家子人,我们一直唱歌跳舞到晚上。后来我们没再刻意地联系,但我还会经常想起那一天,是偶遇的陌生人让我再一次拥有纯粹快乐的能力。
回到北京之后,我也变得爱和陌生人讲话了,是那种发自内心的接触,而不是礼貌客套的寒暄。我想,这也是在纽约的那些不期而遇带给我的习惯。
我常常想起走在纽约街头被人潮淹没的感觉,连同我自以为的痛苦和烦心也都在这座大都会被稀释了。当一个小我融入一个更广大的群体时,不管你是富翁还是流浪汉,十八岁或者八十岁,远近皆知还是默默无闻,你都只是一个普通人,拥有每个普通人的平凡和伟大。
韩夏

我总是会回想起这么一个画面:有一次我们去纽约的河边看日落,有一个男人跑过来请我帮他录视频。我接过他的手机,突然间,他一把抓住身旁的女孩,一个单膝下跪,完成了一系列的求婚动作,然后两个人抱在一起哭得稀里哗啦。出于摄影师的职业素养,我掩盖了吃惊,稳稳地记录下整个过程。当时你指着我告诉对方:“你可真的找对人了,他可是一个正儿八经的电影摄像师。”
这就是我所怀念的纽约日常,不知道我们闯入了谁的镜头里,也不知道下一秒在眼前上演的 Modern Love 会有多么感人又动人。这座城市很难一言以概之,《圣徒指南》里的皇后区老街、《布鲁克林》里曼哈顿对岸的平凡生活、Begin Again 地下铁里凌乱的伴着音乐的步伐,都是构成它五光十色的因子,也是无数小故事的发生地。
我怀念的纽约绝大多数时候还是跟味道有关。自从和你搬到中国城生活后,那里的一切就变成了靠味道激发的回忆。
我们家楼下有一家闪着汤碗形状霓虹灯的兰州拉面馆,面馆里汇集了南来北往、操着各地口音的中国人、外国人,蒸腾着冒着热气儿,让人感觉特别踏实。直到今天,我们在半夜肚子饿的时候,下意识最想吃到的还是那碗兰州拉面。
兰州拉面的隔壁是一家朴实无华的 Bar169,美其名曰是一个新奥尔良风格的 Bar,但让我怀念的,还是5美元一大杯的啤酒和蘸辣酱的饺子。Bar 169很小,一进门有一种 Disco古着店的气氛。酒吧1916年就开始营业了,看得出来店里的瓶瓶罐罐、桌椅板凳,甚至台球桌都是20世纪70年代从二手市场淘来的。和兰州拉面一样,我对这里念念不忘也是因为永远不缺各路古怪又有趣的人。
无论生活在这里的的居民,还是过路的游客,他们都因此享受到移民聚居带来的多元文化福利。我们对于麦当劳有着不可言传的迷恋。
和你第一次约会就是在中央公园旁的麦当劳。后来无论在哪座城市,麦当劳就是一个秘密据点,只要推开任何城市任意一家麦当劳的门,相同的配色、相同的菜单都让我回到我们刚在一起的那一顿餐,无比美妙。
尤其是纽约的麦当劳,大家挨在一起啃汉堡。进到店里,你所能感受到的就像是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小孩子第一次吃到麦当劳时候的幸福感,特别单纯。
纽约就像是放大了的麦当劳。对于一个以移民为主的城市来说,有一个地方能够给你“此心安处是吾乡”的感觉真的是极大的幸运。
我有时候在想,为什么我们常年异地(当然这一次最夸张,足足分别了一年半多),但也没什么焦虑的感觉?可能是因为我们快乐的密码出奇一致吧。
作为两个同行又同频的人,我们在纽约有无数找乐的方式。我们一起去参加纽约电影节;一起去一家不知名的酒店邂逅 DanaMichele的舞蹈表演;一起去城市的犄角旮旯寻觅美食,像寻宝探险一样,每次都有意外之喜……
在偶尔得闲且想要逃离城市的周末,我们会坐着地铁直达F号线的终点站,去Coney Island疯玩一天。没错,它就是伍迪· 艾伦《摩天轮》里的那个小岛,像半个世纪前的“小逃亡者” 一样,逃到 ConeyIsland尽情当小孩。
我们就像两个孩子,喝棉花糖味的啤酒;玩儿岛上的过山车;在和 La La Land里 Gaosling低吟浅唱 City of Star 时如出一辙的紫色海滩撒欢儿;偷偷在夜海里游泳时被罚了50美元……
等回到纽约,我要去我们曾经生活的街区,看望还住在那里的老邻居;要看每一天的河边日落;去曾经的电影院随便看一部新片或老片……不去找刻意的新鲜事,在这座城市,每一天都无比寻常,也无比新鲜。
Matt
老兄,你怎么樣?
看样子伦敦现在很冷吧?你需要来点儿烈酒了。但你知道我有多想念伦敦吗?真的,我太久没有回家了。
成年之后,我几乎远离了英格兰,远离了我的家乡伦敦。这些年,你一定听我说过不少次“我有多想念伦敦”这样的话吧?而你要知道,我的确回去过许多次。过去的20年间,我带着中国的调酒师无数次地回到伦敦,无论参加比赛还是参加全球性的大型鸡尾酒活动,我都希望世界尽可能多地了解伦敦这座鸡尾酒文化高度繁荣的城市。伦敦是我的家乡,也是现代酒吧文化的起点,也许,这是我表达对家乡热爱的一种极致方式。
来到上海,我惊喜地发现这座城市也有着深厚的鸡尾酒文化底蕴。“上海制造”的鸡尾酒早在约一个世纪前就出现了。因为当时著名的绅士俱乐部上海总会(The Shanghai Club)是英国在沪侨民的俱乐部,也是上海的一个重要的社交场所,如今,这里是外滩华尔道夫酒店(Waldorf Astoria)的所在地,这里的酒吧晚上很热闹,离它不远的和平饭店(Fairmont Hotel)内也有一个不错的爵士乐主题酒吧。
伦敦作为“酒吧之都”,和大西洋彼岸的纽约一样,都是鸡尾酒文化发展和延续的重要目的地。上海的许多经典鸡尾酒吧也从伦敦和纽约的酒吧文化中汲取了灵感,并将其与20世纪流行于东京的、更精致的酒吧文化相结合。时至今日,上海和中国其他地区的许多酒吧已经成功地获得认可和尊重,怎么说也有我的一份功劳吧,在“弘扬家乡文化”这件事上,我做得不错。
过去20年来,鸡尾酒文化无时无刻不为伦敦的繁华与魅力增添新的色彩。在“世界50佳酒吧”奖项(World's 50 Best Bar Awards)和许多其他顶级荣誉中,无论独立酒吧还是奢华酒店的酒吧,伦敦都是不可或缺的重要元素。我从心底感到骄傲,不断向我的中国朋友介绍伦敦。虽然伦敦的冬天冷得让人难以忍受,但也是在这样的日子里,伦敦的酒吧更热闹了,在节日气氛烘托下的伦敦是一座温暖的城市,这是一年中游览伦敦的最佳时节。
对了,你一定记得我喜欢的那家中餐厅唐茶苑(Yauatcha Soho)吧?那里的点心真不错,丘德威(AlanYao)真厉害,创办了这么美味的餐厅,我发自内心地对他说声感谢,让我在伦敦也能品尝到这么有特色的中国茶点。然而你一定想不到,在上海外滩,他也开了一家人气爆棚的粤菜馆 Hakkasan,外滩景观的位置总是早早被预订,菜品也没得挑。唐茶苑和 Hakkasan的选址一样棒,周围的区域适合散步,也适合我们规划夜晚的美妙生活。The American Bar就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下次回伦敦,我们一定得再安排一趟。
对于 The American Bar所在的萨沃伊酒店(The Savoy),你肯定不陌生吧。这里是伦敦调酒师最活跃的场所,“世界50佳酒吧”的名头响当当的。我总是和朋友开玩笑,说“那里的调酒师见过不少世面,你最好穿得体面一些。”
如果离开伦敦西区,圣约翰酒吧餐厅(St. John Bar and Restaurant)就是首选。传统英式风格的简餐可口美味,葡萄酒的品种也很丰富,无论怎么搭配都不容易出错。另外,还有金莺酒吧(Oriole),鸡尾酒和爵士音乐的完美配合让人放松又自在。接着就该往肖尔迪奇区(Shoreditch)移动,开启另一种夜场之旅的体验了。
我总是对身边的人说,伦敦的好酒吧太多了,只要去对了区域,大体都是不错的,但一定会提醒一句,千万别忘了去 HappinessForgets,这是我在伦敦最喜欢的酒吧之一。当然了,也许因为我来这里从来都不用排队。这里一直很火爆。
怎么样,这些提议还不错吧?你一定也期待我再次回到伦敦,记得好好招待我。
Theo Watt
Cheers !圣诞快乐!
我还好,人们也在大规模接种疫苗,会越来越好的。
你还是老样子,挂念的都是我们常去的老地方,我的酒吧也受到一些影响,毕竟人们出行变得谨慎了许多。疫情让我们失去了一些很棒的场所,但我们也明白,这是一次机会 —— 成为更强大的人,经营更棒的酒吧,创作更有意思的鸡尾酒空间。的确,我们的办公状态变得更灵活了,很多人都开始居家办公,一周五天,至少有一两天时间,人们都选择在家里生活和工作,自然也减少了夜间生活。周末是大家难得放松的时间,我们必须做得更好。和同行交流一番,我们都觉得伦敦的鸡尾酒吧需要更多创新,比如食品和饮料的融汇、各种食材的糅合都是打破常规的选择。伦敦总是不乏创意的,你现在甚至能在 Tayer and Elementary(注:一家伦敦的“世界50佳酒吧 ”)喝到 西瓜内格罗尼(Watermelon Negroni)。这些经典的鸡尾酒作品还在流行,但它们也被奇妙地赋予了更新鲜的元素。
在疫情之下,人们的生活方式变得更直接、简单,酒吧的经营模式也在调整,但大趋势仍是回归经典,并在经典中融入一些巧思。像 Tayerand Elementary、Hacha、Little Mercies、Cross Roads等酒吧,以及我們 Happiness Forgets都推出了保留经典作品同时融入创新元素的酒单。比较有趣的是 Three Sheets,应该说,是它率先倡导了这样的理念。调酒师习惯预先将杜松子酒而不是香槟和酸葡萄、天然葡萄酒在室内进行碳酸化处理,味觉上的先体验也让“French 75”这款老派的鸡尾酒重新收获人气。
当然,伦敦最近也出现了一些引人注目的新酒吧,比如游牧酒店(The NoMad Hotel)的 Side Hustle,还有马克西姆· 舒尔特(Maxim Shulte)经营的人气餐厅KOL,那里的 梅斯卡尔(Mezcaleria)十分受欢迎。
如果你有机会回到伦敦,我倒是想带你去一些开业许久却略显冷清的老店,也许你以前没有注意到,但它们真的不错。Sager+Wilde推出了许多按杯出售的酒单,达尔斯顿的 P.franco和 The Laughing Heart在酒单设计上也都各有特点。另外,还有我之前提到的 Little Mercies和Cross Roads,我是常客。我很喜欢 Little Mercies的鸡尾酒,那里的厨房可真让人羡慕。如果你想同时喝到最棒的鸡尾酒、葡萄酒,顺便填饱肚子,那就得去 Everafter。每次去,你都能喝到不一样的新东西。
不知道你什么时候能再回来,你看,我攒了好多东西,等着你一起来分享。
Alastair Burgess
对了,圣诞快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