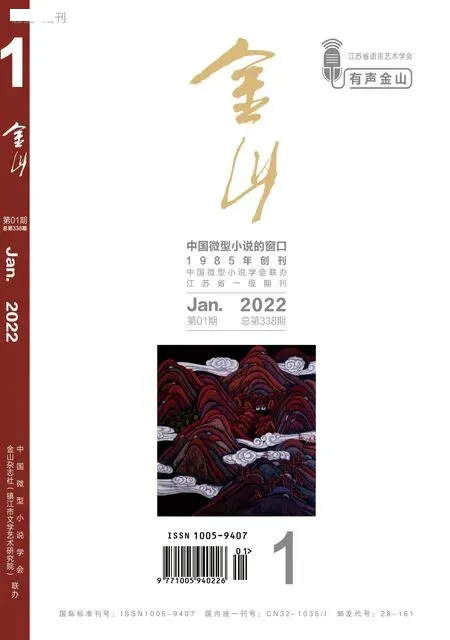漫谈西元《曰心曰生》:关于人与死的终极命题
2022-02-13张雨寒
张雨寒
年逾四十却一事无成的中文系副教授,事业有成却染上恶症的女人,城市边缘苟延残喘的村庄与人群……这是《曰心曰生》呈现给我们的“另一个世界”,这个世界在别处发生,存活在文学与哲学所使用的话语之外,却如此鲜活、灵动、富有张力。
历史本身就是人与死之间的故事,也是人之死的故事。西元在《曰心曰生》这篇小说中试图传达的,是一个个将死去的、已死去的、未死去的人和死亡的对话。以及他们面向自我的思索,关于意义的追问。世界是否有其他可能?人是否能够摆脱肉体存在?文本中不断寻找答案的这些疑问正是文本的魅力所在:这些近在咫尺的可能性构成了更多哲学思索的进路,也生成了更宏大的、关于人类与死亡的终极命题。
疯 子
小说的开篇是一个天气清朗的初冬早晨,最先进入叙事的是声音:狂风吹过杨树林,那是地球的呼号;然后是更加真实的、人发出的号叫。在故事的起点,一个正在挨打的疯子神谕一般地出现了。这是西元埋下的隐喻:住在大泽旁的疯人呼告着人类的幻灭,人类以为石头扔向了疯子,其实砸到的是先知。
“疯”是《曰心曰生》的一个叙事前提。小说中,西元三次提到“疯人”,折射的是“我”内心的异变。除了开篇挨打的疯子,小说中首次写到学者的“疯”,是在听到哲学教师讲授康德后展开的联想。如果人的意识、人的意志并不是世界的原创,站在科技不断飞升的时代路口,人类到底应该怎么理解自己、认识自己?过往的所有人类知识,和对自我的理解是否只是一场空虚的自我游戏?哲学、文学、社会学、心理学是否随时都可能分崩离析?无法被回答的这些问题,是疯癫的源头,也是这篇小说的引线。
之后,“我”又想到了20世纪60年代一个理论物理学家的疯狂。他用函数证明了世界可能是无数的、重叠的、相互交错的,他不被他人认可,甚至不被自己认可,最终走向疯癫。两个学者,一个是假想的疯,一个是真实的疯;一个是哲学的疯,一个是物理学的疯。二者的关联与区别在哪?或者说,西元是否从一开始就没有打算区别疯与未疯?这两个学者,恰是“我”的两个对半分身,一半在游离,一半在疯癫;“我”站在疯癫与清醒的交汇线上反复权衡,永续循环,却无法做出抉择。
如果说疯癫史的讲述在20世纪已达到了某种高峰,那么小说呈现出的疯癫却是极具当下性的,带有更多信息时代的审美趣味。《曰心曰生》真正站在21世纪猛烈飞跃的科技视角下,通过疯子的嘴、“我”的笔,去叙述在巨大的科技洪流中,人类如何自处的难题。小说中,“我”在思考中写就的诗,似乎正是“我”的疯狂自白:完整与碎裂的、诞生与永生的、重叠与交融的,这些形容词是关于“我”的,是关于所有人类的,甚至是关于整个世界的。
不同于大紧闭时代的瘋人景观,西元暗示着,当下的疯癫正与人类对自己本质的认识发生更密切的互动。“我”不止一次地思索人类的命运、世界的未来,正是因为那些横亘心头的疑问时时作祟。“游戏里的那个虚拟的世界就一定是假的,而外面的那个丑陋的世界就一定是真的?”这些疑问不仅是“我”在问自己,更是西元对读者发出的追问。
醉 汉
如果说疯子是理解小说的进路,那么醉汉似乎更像是进入故事的钥匙。“醉汉”的出现引起了我的注意,又引领着“我”再次回到了曾经住过的“××村”。在这个“××村”,我故地重游,在酒精的指引下,自己也变成了一个醉汉。这种接力棒一般的身份传递是迷人的。存在主义曾不止一次指出酒神精神之于美学与哲学的意义,小说中,“我”变成醉汉的过程也是“我”逃离“疯人”的过程。在酒精的作用下,“我”开始在寒冬中恢复意识,重新变得有血有肉、重新感受到身体对“我”的爱意与依恋。醉意让“我”颠三倒四,也让“我”一直被压抑的欲望喷薄而出。在与暗妓的性爱后,“我”“复生了”,不再思考灵魂的幻灭、不再专注死亡的诱惑——“这下死不了了”。
第一场“醉”只是故地重游的一个楔子,第二次与多年前“我”曾暗暗爱慕的女人的相逢把酒为我们引出了小说更加宏大的脉络。醉酒让两个失散多年的人重新相逢,对彼此袒露心肠,说起二十年前的荒唐与迷惘,也引出了二人的当下。
小说对于“人”的设置在此处变得更富深意了。醉汉代表的不仅是污秽、肮脏,更承载了一种真实。疯子的崩溃在意识,而醉汉的崩溃则是肉体的。买醉是“我”寻找自我的方式,也是小说对人类存在提出的另一重命题。醉让“我”不再向死,少了对“生”的恐惧。小说的最后,“我”在“××村”经历了数次生离死别,德子的病、女人的死,“我”最终在醉酒的状态下去看了“××村”举办的晚会:朦胧的醉意中,生与死的界限变得分明了。斯人已去,活着的人如何活着?
在醉酒中,“我”对人类命运的思索终于有了一个尚不清晰的念头:真正的活着、真正的“人”不在肉体里,甚至不在意识中,而在那些“骨头缝里的东西”。我愿意相信,西元意图向我们展示的正是一种极具当代性的英雄主义,一种对无穷尽的人类的能量的信心——换言之,人类的无可替代性。这种信心或许就藏在醉汉的哲学中,悬浮在微醺的空间里。
病 人
尼采曾做出断言:不尊重死亡的人,不懂得敬畏生命。小说中形形色色的病人形象,是西元死亡观的侧影。正是通过书写死亡,书写关于面对死亡、迎接死亡、接受死亡的故事,小说关于人的命题才扣上了最后一环,构成了完整的图景。
《曰心曰生》的叙事是意识流的。在无限流动的“我”的思绪中,当下在“我”的身边与“我”发生着关系。小说中数次描写病人:罹患艾滋病的女人,确诊癌症的德子,临终关怀中心里疼痛到尖叫的孩子……他们面容模糊,只有那些展现着病痛的眼睛歇斯底里地沉默自白。
“女人”与“我”的久别重逢构成了小说主要的叙事。从“女人”坦言自己得了病,到“我”与“女人”一同去捐款、去学校,到“女人”住进医院、离开人世,“女人”的病贯穿了小说。也正因此,关于“死”的命题与讨论也在小说的各个角落出现。“女人”说,死亡是一条巨蟒,被死亡缠上,人就能越发明白,“你不过是一摊烂肉”。这是小说对死的第一重叙述。相比之下,年轻的相声演员德子的死来得似乎更豁达。在得知自己的绝症后,德子不再接受治疗,而是选择用最后的时间回到他长久停留的“××村”,用尽最后一份时间戏谑人生,他说死亡不是孤独,“虽然前面是一片黑暗,可只要稍稍回过头,我就能看见我的兄弟姐妹,他们从未消失过”。这是第二重,也是更本质的一重叙述。
死亡到底意味着什么?小说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西元是一个自顾自的说话者,这些故事与念头紧紧缠绕,他不吐不快。小说中的“我”的经历,正是对“死亡”这种宏大命题的无数次重新认识。在小说最后,“我”再一次和那位软件学院的青年教师相遇了,也又一次说起开篇关于精神与意识是否可以被替代的话题。“我”的回答和最初面对小男孩时的悲观主义已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我说:“人也许还有机会。”
人还有什么机会?因为人可以生、可以死。人并非不灭,这反而成了人的“机会”。能够切肤地感受死亡、感受生的挣扎和消散,才能够真切地理解“人”、真正地成为“人”。也正是这样,在对病人的书写中,西元织就了小说关于人与死亡的命题。
《曰心曰生》的标题讲的是“心”与“生”,文本关注的实际是“人”与“死”,二者形成了一层微妙的互文与对话。在“我”与“女人”的对话中,“我”说我想做一个光一样的人,轻盈、自由、来去如风,在疫情仍在的世界里,这或许是一句意蕴深厚的谶语。正是有“心”,“生”才不是伪命题;也正因为“死”,“人”才是真正的“人”。
西元向我们展示的是一个完全虚构的故事吗?我想并不尽然。小说中的“××村”、被切断水电的“外来人”、城市边缘的摇滚青年与文学论坛,都是一个个讳莫如深的注脚。《曰心曰生》似乎讲的只是围绕着“我”的事件与思索,实际上却灌注真情地记述了“××村”的一个个人、一个个冬夜,与那些冬夜里,城市边缘处不曾熄灭的火光。
作为读者,我们该敬畏这些火光,敬畏这些“骨头缝里的”、永不消散的力量。
注:本文正文均引自西元《曰生曰心》(《花城》2021年第1期 P31-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