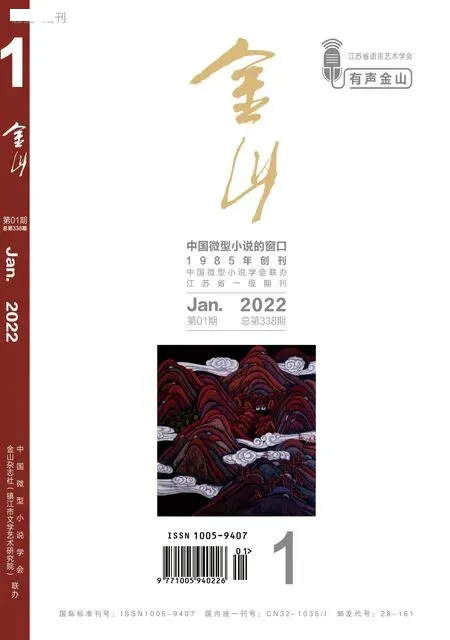雪山窝
2022-02-13马璐瑶
马璐瑶
深入雪山腹地的第十天,我看到了一间藏匿在白雪之下的房子,准确地说,那更像一个窝。它在白雪之中鼓出一块小山包一样的尖尖角,与周围高高低低的雪堆没什么两样,除了中间那扇摇摇欲坠的木头门。
我搓着灼热的双手,敲开了那扇门。
有人应答着,“桀桀”,随之一股热流从洞开的门里涌出,我忍不住眯紧了眼睛,狭小的视线里,一个几乎与我肩膀等高的白色长形生物哼哧哼哧地冲了出来,我睁不开眼,只能挥舞着双手避让,靴子深陷在雪里,我竭力晃动几下,最终还是后仰着坐在了地上。
屋里又传来了几句人声,不知道是哪里的语言,轻缓好听,我遮挡着脸,看清了那停在眼前的白色生物。
猫的长相,长长的白毛,圆嘴巴尖耳朵,粉红的长满倒刺的短舌头,它细瘦得如同一只最普通的猫咪,却不同寻常地伸展长长的身躯两脚行走。它停在我身前,上半身直挺挺地倾倒,十分轻盈地扑在地上,四脚着地在我身上乱嗅。屋子里终于慢腾腾地走出了一个人类,他吹了一声口哨,那白毛生物从鼻子里哼出一串热气,不情不愿地离开了我。白毛生物踱步回去蜷在了那个人类脚下,虽说仍旧体型硕大,至少神态终于像一只真正的猫咪那样了。
“桀桀桀桀桀桀桀桀桀桀桀桀。”人类说。
我疑惑地望着他,用蹩脚的国际通用语言说:“对不起,我听不懂您的语言。”
他恍然大悟一样,嘴角咧开了大大的笑容,用同样蹩脚的国际通用语言说:“对不起,太久没人光临寒舍,一时间忘记了语言的障碍。”
他热情地伸出手将我拉起来,单手搂着我的后腰邀请我进屋坐坐——那温暖的,燃烧着火种的屋子。
这位在雪山窝中居住的人类看起来很苍老,身材魁梧,皮肤红红的,从脸到脖子到他裸露的手臂,身上的毛发则是白茸茸的一层,眉毛尾部长长地耷拉下来。幸好他并不算是毛发旺盛的那类人,否则难免会被误认成某种巨兽。
他在房子正中间的火堆旁盘腿坐下,白毛生物也懒洋洋地窝在了他身边,他双手一拍:“快坐下啊,远道而来的客人,快坐下。您不知道我多么开心你来到这里,大概有多少年了……让我想想,我这老糊涂,我想不起多久,总之很久啦,我成日都见不到人类,当然每天也不说话。刚开始我根本没意识到我的语言能力正在悄悄溜走,直到有一天我突然发现我无法思考问题了,我的大脑仍旧在转动,但是思想却无法转译成某种具体的东西了,后来我恍然大悟,那某种具体的东西就是语言啊,人类思考也需要语言啊。于是我开始听广播,我以为这种语言练习可以挽救我的语言能力,我几乎每天都会听几个小时广播,广播里的内容也很奇怪,例如今天提到防治地球污染,明天却又统计化工产业排名;今天提到我们爱我们的家园,明天却又谈起有哪个临近星球或许可以供人类居住……对了,听广播说人类准备迁居火星,真有这事儿吗?你知道,我对外面的事情是一无所知的,也从来没有人类来到过这里。”
我相信很久没有人类到过这里了,没人与他对话,他大概真的憋坏了,根本不给我开口的机会。
我想要说点什么,可是国际通用语言并不是我擅长的语种,正磕磕绊绊组织语言时,他又说话了,他顺着那只白色生物的毛摸了一把,喉咙里又发出了一连串“桀桀”的怪声。他看了我一眼,解释道:“没办法嘛,没有人类可以与我对话,多年来,唯一陪我的就只有我的老伙計,所以我只能开始学习他们的语言,现在好了,至少我每天可以与它对话。”
那位白毛老伙计舒服得发出桀桀桀桀的声音,老人低头在那只白毛生物耳边说了些什么,那只白毛生物也睁开眼低声叫唤,看起来他们真的可以对话,这场你来我往的对话持续了一会儿,那只白毛生物落了败似的,扑打了一下尾巴,慢慢地站起来,四脚着地走出了门。出门前,它扭头瞪了我一眼,就像是……太奇怪了,那种眼神,就好像我抢走了它的爱人。
那老人浅浅地笑着,在橘黄色的火苗那端,幸福而又温和:“我吩咐它出去猎点食物回来,待客之道,我们可不能让我们的客人饿着肚子……”他看了一眼紧闭的门外,“它在这里时许多事情我说不出口,虽然我知道它听不懂人类的通用语言,但我还是会羞涩。有些东西说出来,就太肉麻了,但不说出来,又实在不吐不快啊。有了它,我才发觉语言是多么匮乏,我该怎么称呼它呢?爱人这种词好像太狭窄了,这个时候就不得不提到人类语言的狭窄,你想啊,语言如此狭窄,那么相应的,要依靠语言来具象化的思想,能广阔到哪里去呢?用人类的语言,我只能称它为‘我的爱’,但总觉得语焉不详,相比而言,它们的语言就好多了……‘桀桀’,用它们的语言,我可以这样称呼它。还没跟你介绍它们的族群吧,其实翻译成人类通用语,大概是雪猫的意思,用雪猫语描述就是‘桀,桀’。雪猫语是伟大的语言啊,如果我的‘桀桀’不是这世界上仅存的一只雪猫,那么以它们族群的智慧足以建立起一个强大的文明,只是雪猫的繁殖能力很弱,我的‘桀桀’曾告诉我,或许这就是头脑强大的交换条件,所以你看,愚蠢的生物总是在不停歇地大量繁殖,世界就愈被愚蠢占据。”
他当然可以大力称赞他的爱人……他的爱……我是说,他的桀桀,但不该与此同时贬低了人类,我也顾不上什么礼貌不礼貌、口音蹩脚不蹩脚了,很快地开口:“至于您说到繁殖,这绝非是人类愚蠢的证据,任何智慧的物种,他们总在精神与物质中追求兼得,人类建立的文明不伟大吗?不辉煌吗?不灿烂吗?我们的艺术,我们的哲学,我们各族语言之间的互通,我们的科学,我们的技术,我们的交通,我们庞大的制造与创造……包括你的广播,这还不足以证明人类智慧吗?人类思考历史、存在与宇宙,却并非不务实,也最看重生存,我相信任何族群都是这样的,希望这个族群延续下去,延续,就需要生命。我想繁殖正是生物的自救。”
“这不正是愚蠢之处吗?”他将摆放在高处的广播拿在手里,上下掂了几下,似乎为了证明什么,快速将它投进了火堆里,塑料金属在火焰中噼噼啪啪地碎裂,“有些东西,那些为了舒适便利而存在的东西我就暂且不提了,生存是什么呢?你引以自豪的庞大的制造与创造,是席梦思吗?但是你好不容易得到了席梦思,就想要水床,有了水床,就想要更大的,有了更大的床,岂不要更大的房子来装?真的需要吗?稀有金属的流通,还有金刚石、装饰物,那些永不腐坏的塑料,这难道还不够愚蠢吗?”
我摇了摇头。
他也摇摇头。这时我又想到,难道人类奇迹般相通的肢体语言还不够证明智慧吗?他说:“你以为我真的只是从广播里了解人类吗?我太了解人类了,因此我才来到了这里。人类太无趣。最初来到这里的时候,那时候我的语言能力还很旺盛,于是放心地挥霍,花大量的时间,有时候甚至连续好几天,只是躺在那里看着天空,看天空的运动,看它变了颜色,看太阳换成月亮,看飞鸟换成星星,看白云变黑,看雪瓣掉进我的眼眶里,看看都有什么路过我,看看都有什么路过它。从来不去思考生存。在这里,我想得最多的就是自由。我曾经以为,只要往前,一往无前,就可以最终找到自由,但是在我们这个星球,谁都知道,向前是无法逃离的,最终绕一圈还是回到原来的地方。向上倒是可以,只是逃离了这个星球,难道就是自由吗?”
我问:“那你有没有想过,地球真的是个球吗?我相信地球是平的,为了证明‘地圆’这个认知是错的,我出发了。我决定在某地做标记,一路直行,如果最终我无法回到起点,那么地球怎么圆呢?不过我们都知道,走直线是很难的,一开始,我想用指南針,但想到指南针的原理本身就是基于球体的极点才成立的,只能作罢。后来我选择了相信光,但就在行走到半路时,我突然想到,如果我不相信地球是圆的,那么我凭什么相信光沿直线传播呢?我只能重新做标记,重新出发,这次我选择相信自己的直觉。”
“你因此来到了这里?”他问。
我说:“对,你知道,走直线是不能畏惧的,无论面前是什么,都要直直地走过去。”
来到这里之前,我正在穿越一个沙漠,途中也碰见过很多人,有一个向导告诉我,不要再往前了,从来没有人能穿越这片沙漠,这条线,就是脚下这条线,是人类能走到的最远,再往前,没人能活着返回。这个时候,一位探险者挑衅一样的向那条线外迈出了一步。两步,三步,四步,他笑嘻嘻地说:“这样,我就打破了世界纪录吗?”“那这样呢?”他得意洋洋地继续向前迈步,五步,六步,七步。我眼睁睁看着他越走越远,那个向导摩挲着界线前竖的石碑:“知道为什么无人可以突破这条线吗?只要向前跨出一步,就总想着多一步,再多一步,等终于意识到该返程了,他也永远回不来了。”
向导劝我返回,我问他:“你知道什么是直线吗?”
我辞别向导,继续向前走了几天,在路上看到了那探险者的尸体,他正在回程的路上,胳膊长长地向前伸着。
“我正在穿越一个沙漠,不知道走了几天,最终来到了你家门口。”我告诉雪窝里的老人。
说完,木门吱了长长的一声,冷风穿过被推开的门扑满了我的后背,一些雪沫也乘着风挤了进来,我扭头看去,雪猫甩着脑袋抖落了毛上的雪,它四脚爬进屋,嘴里叼着一只扑腾着翅膀的公鸡。冰天雪地,哪儿来的鸡?这鸡毛色鲜亮,嗓音昂扬,怎么也不像是在这茫茫雪山中应该存在的东西,不过转念一想,难不成按照常理这个小屋就应该存在?按照常理难不成我就该在这里?我只好认可这只鸡的存在。
老人高兴地站起来,双手一拍,他的“桀桀”就钻到了他的脚下,眯着眼睛在他的脚边来回蹭了几圈。他弯腰拎起鸡,咧起嘴朝我笑:“远道而来的客人,你一定饿了,看,我的桀桀为我们带回了食物。”
雪猫也大咧着嘴巴笑。
我的确饿了,我心里翻腾着,胃也跟着翻腾,肠子一拱一拱的。面前那只鸡还没有变成油润的一锅汤或者劲道的一盘肉,它仍是个生物,我却因为他积蓄了满嘴的口水,这口水令我无法说话,这口水令我难以判断我是否还是一个高级动物——思考文明、存在、生存、制造、创造的高级动物。是本能,让我原形毕露。
我盯着那只活鸡的眼睛,它那双小小的眼睛同样也在凝视着我,似乎是在诘问。我看着它,却是在垂涎。肉,鸡肉,我要吃肉。
老人高高举起一把刀,另一只拎着鸡脖子的手也跟着举起来,像是什么古怪的仪式,那雪猫“桀”一声,老人也“桀”一声,我也只能跟随他们,高声喊道:“桀!”喊声落下,那老人手起刀落,利索地砍断了鸡脑袋。
血与鸡都没有反应过来,脖子里滴下了几大滴粘稠的血,鸡头疼得一抽,还没有落地就疯狂地在半空中扭动着冲了出去,血才后知后觉地喷溅了出来,鸡翅膀扑腾着接住了一小半血,那细瘦的爪子徒劳无功地蹬啊蹬啊蹬,鸡头终于掉落在了地上。雪猫舔着自己的毛向后退了一步。接着,老人又一刀,鸡脖子被砍了下来。我想不到一只鸡能有这么多血,这次是大股大股地向外涌,那断开的裂口处有不整齐的碎皮半掩着,早被染成了红色,随着血液的涌出一开一合,像是张口呕吐的丑陋怪物。那热腾腾的血让我的眼睛也跟着温暖了起来,我兴奋地攥紧了拳头,看着老人一刀砍在鸡的屁股上,一刀砍到鸡的前胸,一刀砍向它的左腿,一刀砍向它的右腿,直到最后只剩下一个圆滚滚的大肚子,老人抬头给了我一个眼神。
从他的眼睛里我看到了一个红彤彤的我。
雪猫退得更远了。
我的心、胃、肠子也更加靠近,他们前所未有地亲近,蜷缩在一起,抖动着,狂欢一样地抖动。
老人的刀轻轻的,这一刻,不断撞击着木门的狂风也停了下来,肃穆宁静的一刻,他轻轻划开了鸡的肚皮,干瘦的手温柔地伸进去,拿出了一颗沾着粘液的亮晶晶的鸡蛋。他将鸡蛋握在手心里,摊开在我的眼前展示这来之不易的战利品:“看,朋友,我们的食物。”
我看着那颗鸡蛋,老人看着那颗鸡蛋,雪猫也在看着那颗鸡蛋。
老人将手里的鸡尸撇出了门外,在厚厚的积雪上砸出了一个深坑。此时,那早该死去的鸡头突然疯狂地弹了起来,直直地向着被丢弃在门外的尸体冲了过去。它飞过我的眼前,合不上的眼睛仍旧深深地凝视着我。
我决定离开这里。
老人极力挽留,我还是坚持离开了。他站在门口向我挥手告别,我将脚踩进雪里,那被鸡尸砸出的深坑早已被新的落雪填平了,连一点点零星的血迹都没能留下。老人的身后,那只雪猫正在啃食着鸡蛋。
决定返回小屋时,我已经在风雪里行走了三天。那时我正在看着前方夜空中一颗怪异的星星,那星星极其亮,几乎让它身边的月亮湮没在了夜空中,这样显眼的星星,以前我怎么从没见过呢?为什么?就在这时,我突然明白了为什么,因为以前这颗星星并不在我前方。
自从拐进那个小屋,我就再也不是在走从前那条直线了。于是我决定掉头回去,但是在无际的沙漠中,我怎么也找不到那间茫茫雪山里的小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