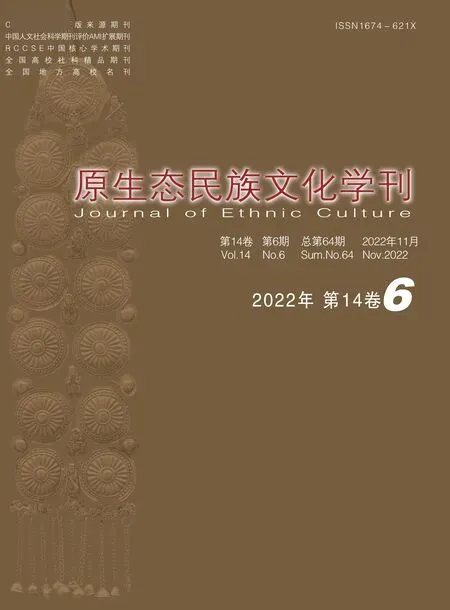线性音乐文化空间研究
2022-02-11赵书峰
赵书峰
一、“线性音乐文化空间”的概念
“线性音乐文化空间”概念的提出主要受到人类学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界定的影响。人类学界“线性文化空间”领域的研究主要受“流域”“走廊”“通道”等有关的诸多民族志个案研究的影响,尤其是杨志强[1]、赵旭东[2]、周大鸣[3]、田阡[4]、吴才茂[5]等学者的研究成果给民族音乐学的“线性音乐文化空间研究”提供了诸多方法论思考。民族音乐学关于“线性音乐文化空间”的研究主要以张应华[6]、杨志强[7]、赵书峰[8]、杨红[9]等学者为代表,主要针对“走廊”“流域”“通道”音乐展开的流动性、关系性的多点民族志研究。
“线性音乐文化空间”是由“流域”“通道”“走廊”“丝路”等具有“带状”特性的自然与人文地理文化空间内诸多流动性的传统乐舞文化景观构成。杨志强教授认为:所谓“线性文化空间”,是指人类社会在一些特定的重要交通线或地理走廊上,因长期不间断活动形成的具有整体性关联的文化地理空间。在这些区域内,不同族群或地域社会间,因频繁交流互动而产生某种共同的特质、关联性和延续性,从而文化在空间上会呈现出某些明显的因果关联。[7]55比如,南岭民族走廊不但连接长江流域与珠江流域,而且是以“潇贺古道”实现汉族与南方少数民族音乐文化的互动交融交流之地。该区域内的平地瑶音乐文化景观的构建就是明代以来中原文化与过山瑶传统音乐文化互动交融(涵化)之产物。再如古苗疆走廊留存的古庙宇、戏台、以及诸多汉族与少数民族互动交融下再生的传统乐舞的新品种,都是空间与其区域内流播的传统乐舞之间互动交融的产物。
“文化线路”是“线性音乐文化空间”构建的基础,既是地理廊道,又是文化廊道。主要包括自然线路、商道线路、战争线路、移民线路、宗教线路等[10]。“对它的认识不仅是停留在沿途的书院、会馆、寺庙、茶馆、牌坊等古建筑及古道、关隘、驿站、渡口、码头、桥梁、摩崖石刻上,更注重线路的文化和社会意义,强调因线路而带来的不同区域的文化交流和对话”[11]。《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文化线路宪章》将“文化线路”定义为“必须来自并反映人类的互动,和跨越较长历史时期的民族、国家或地区或大陆间的多维、持续互惠的货物、思想、知识和价值观的交流”“必须在时空上涉及的所有文化间的交流互惠,并反映在其物质和非物质遗产中”“必须将相关联的历史关系与文化遗产有机融入一个动态系统中”[10]88“‘线路文化’作为一种‘线路遗产’(heritage route),主要表现为以某一种‘线路’为媒介,形成了历史上的文化交流带”[12]。随着传统乐舞文化的线性流动过程,致使不同族群传统音乐文化之间相互接触、冲突、吸收、采借、发明、创造,形成了“线性文化空间”内多点之间的传统乐舞的关系性、流动性、相似性特征,以及主流传统乐舞在异地传播中的本土化或者涵化现象。如,“贵州花灯”音乐的形成与江苏民歌、东北民歌沿着元代开辟的“苗疆走廊”作为文化传播的文化传统通道,形成的跨区域、跨族群间文化传播与涵化现象[13]。综观中国传统音乐品种的形成多与“流域”“走廊”“通道”等形成的“路文化”有关,即“路”给传统乐舞文化在跨地域、跨族群、跨文化的异地传播带来便利。比如豫剧“沙河调”(豫南调)的形成就是“流域”背景下的文化产物,它是“以‘沙河调’为主体的‘淮北梆子’,受到清末流传在沙河一带的‘沙秦班’给予‘高梆子’的巨大影响”[14]。比如“川盐古道”中诸多传统民歌、戏曲、歌舞音乐的形成,多与“盐业”的开采、运输、交易等等因素有关。“文化线路”沿途中的祠堂、庙宇等仪式信仰文化空间,为传统乐舞的构建与表演营造了浓厚的生成空间。如江西会馆的万寿宫、广东会馆的南华宫、福建会馆的天后宫,等等。还如,流播于湘鄂渝黔交界处的传统戏曲——阳戏音乐唱腔因其传播路线与地域不同又分为四个流派,曲调风格各异。这种具有祭祀仪式的民间戏曲的不同流派与表演风格的差异,是以流域文化传播不同路线,与经过地的语言,地方民间小调,劳动号子,民间祭祀仪式相互融合后产生的一种新的表演流派。阳戏在湘鄂渝黔交界区域内的传播后形成的不同流派,也是与该区域发达的流域文化有关,尤其沅水流域、酉水流域等形成的“线性文化空间”的文化传播便利,形成了阳戏在汉族、土家族、苗族、侗族等跨族群、跨区域之间的文化传播。如张家界阳戏、贵州阳戏、重庆酉阳土家族苗族阳戏,等等。
“线性音乐文化空间”是一个流动性、开放性与动态的文化空间,是多族群传统音乐文化的立体构建,是以“文化线路”作为音乐传播的主要载体,依靠人员与商业、军事征服、社会交往等因素形成特定的音乐文化传播之道。比如,“大运河”音乐文化空间,是以汉族传统乐舞文化为主体性构建。流域周边的汉族民歌、秧歌戏,等等,多是以流域文化空间为载体的跨区域、跨文化间的多维建构,尤其以人与物质交流其构建受到“自然环境”“文化环境”“历史环境”“现代环境”等诸多因素制约,是过往与当下历史、社会时空交错的产物。诸多传统乐舞文化品种的生成,是由文化的多个源头形成的,这个“源”就是“文化”的线性传播过程。传统乐舞文化的“一体多源”,就是主流文化或者源发地传统乐舞在沿着“文化线路”传播过程中形成的“多源”之间的互动、交融背景下造成的新的传统乐舞品种不断生成,以及文化涵化现象。俗话说:“商路即戏路。”如沅水流域中的土家族三棒鼓、地花鼓等等,以及汉族戏曲辰河高腔在贵州、重庆的跨区域传播,多是沅水流域人员与物质交流往来造成的众多传统乐舞文化的交流、融合与文化涵化的产物。
二、“线性音乐文化空间”学术史梳理
1.“线性音乐文化空间”的历史音乐学研究
2013年中国政府大力倡导“一带一路”发展战略,提倡中国与周边国家文化互鉴与互动研究,在此背景下,音乐学界积极响应,学者们结合历史音乐学与历史民族音乐学、后现代地理学、历史与文化地理学等研究理念,开始针对“丝绸之路”上的传统乐舞展开跨区域、跨国界的系统比较研究。“线性音乐文化空间”的考察聚焦于丝路乐舞文化研究,发展成为历史音乐学与历史民族音乐学共存的研究理念。早期的丝路音乐研究更多地从历史音乐学角度展开研究,尤其结合历史文献学与史料学、历史图像学等理论展开的源流考证研究。比如席臻贯[15]、阴法鲁[16]、李雄飞[17]、王其书[18]、周菁葆[19]等学者,针对丝路中外乐舞的文化传播研究、丝路乐舞文化的重建研究、域外视角观照中国丝路音乐研究,等三个维度展开的研究。再如上海音乐学院赵维平主持的2019年国家社科艺术学重点项目《丝绸之路上的音乐史研究》也是有关丝路音乐的历史音乐学研究。截至当下,以《音乐研究》刊物为代表分别在2016 年至2022 年期间,专门开设“丝绸之路与当代音乐学术”“‘一带一路’音乐文化研究”专栏,登载了共计26 篇文章,这些文章主要结合历史文献学与历史音乐学、历史民族音乐学理论关注丝绸之路上的传统乐舞,族群传统乐舞的历史流变与跨文化传播,文化交融交流等问题研究,其学术话题集中、问题意识聚焦、学术影响力大。
2.“线性音乐文化空间”的音乐形态学研究
“线性音乐文化空间”研究主要关注于传统乐舞跨区域间的文化传播与历史渊源关系的考证研究,在其艺术形态研究成果方面较为缺乏。当下其研究主要聚焦于多点之间的音乐本体的比较分析考察,强调音乐本体关联与人员流动迁徙之间的互动关系考察。代表性的研究论文有:周青青《北京通州运河号子中的山东音乐渊源》[20],以口碑资料为思考线索,通过分析通州运河号子的旋律特点,采用音乐形态分析、历史文献考证的方法,并借鉴语音学研究成果,得出通州运河号子中有山东音乐渊源的结论。张应华《贵州民间音乐“涵化”现象的本体形态研究——以苗疆走廊作为参照》[21],结合音乐形态学理论,针对“苗疆走廊”(贵州段)的民间音乐本体形态的涵化现象进行了深入的分析研究。同时看出,聚焦于音乐形态学的个案分析成果较少,学界主要以历史音乐学与民族音乐学研究的成果居多。
3.“线性音乐文化空间”的民族音乐学研究
截至目前,学界关于“线性音乐文化空间”研究积累了众多学术成果,从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到期刊论文发表,以及举办的各种高端学术论坛等等内容都是围绕上述问题展开的。如上海音乐学院亚欧音乐研究中心举办的两届“ICTM 国际专题:“从乐弓到齐特:丝绸之路上的乐器系列研究”①主要包括:“丝绸之路上的抱弹类鲁特”“丝绸之路上的复合簧管乐器”“丝绸之路上的鼓与鼓乐”。,主要针对丝路音乐文化展开的历史民族音乐学研究。李祖胜主持2019 年国家社科艺术学一般项目“长江中上游大筒类胡琴音乐文化研究”。赵塔里木主持的2021 年国家社科艺术学重大项目“黄河流域音乐文化多元一体格局研究”。魏琳琳主持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大运河文化带’视域下的节庆仪式音乐与国家认同研究”,等等社科项目选题,多是围绕“流域”音乐文化空间展开的宏观与微观研究。这些课题不但有宏观的理论思考,而且还有多点的田野个案考察研究。既聚焦于历史音乐学的文献史料考证,又专注于历史民族音乐学的研究,也强调流动性、开放性与动态性、关系性的具有时空压缩性质的后现代地理学(文化空间理论)思考,同时也导致了民族音乐学研究范式的转型。即学界受到“流域人类学”理论思维的影响,开始从传统村落与社区中的音乐的个案研究走向以“路”文化空间中音乐的动态的、移动的“线索民族志”书写的范式转换。重点关注特定的自然与人文地理空间中的“路”对于传统乐舞结构与象征意义的生成,及其音乐的区域与跨区域、跨族群文化的互动与交融等问题的思考[8]94-95。如“苗疆走廊”内的民歌《赶马调》[6]64-68,就是某一传统音乐文化事项在以“苗疆走廊”为传播载体,实现的跨族群,跨区域,跨文化之间的文化交融与交流形成的产物。如“丝绸之路”琉特琴乐器的跨区域、跨族群与跨文化传播,以及乐器演奏、形制变迁构成了以“丝路”为传播载体的多维度、多点之间构建的同质化、关系性特征。
全球化背景下自媒体时代给传统乐舞的文化传播带来革命性变革,这种时空压缩性质的传播通道构建了虚拟的“线性网络音乐文化空间”。尤其在新冠疫情时期,现场表演活动被动取消后,使传统乐舞文化更多依靠强大的自媒体直播网络平台来传播。“非遗”展演活动或者重要的节庆活动也只能依靠直播平台(如“哔哩哔哩”“抖音”等)进行文化推广。传统的以“流域”“通道”“走廊”构建的音乐文化传播、交流交融之道,被现代化的航空交通体系、高速铁路与公路取代,使音乐传播方式走向虚拟性、开放性的线性网络文化空间方向发展。
进入21世纪以来,“丝路乐舞文化”研究强调历史文献与音乐活态“接通”性质的历史民族音乐学,即不但关注传统乐舞的历史文献挖掘、分析,而且聚焦于“文化线路”内诸多传统乐舞形成与其特定时期王朝国家的历史、社会、政治、权力等等之间的互动关系问题考察。正如有学者谈到丝路音乐文化研究的意义认为:“在传统研究方法和观念基础上,丝路乐舞文化研究加强了‘通道’意识,对音乐事象的考察不再局限于溯源,注重从发生学的意义观照音乐文化类型的生成问题,注重从一件乐器或者音乐事象看丝路交流与整体生态、文化系统之间的关系。”[22]如赵塔里木[23]、杨民康[24]两位学者通过历史文本(历史图像)与田野的互动研究来探析南北方“丝绸之路”上中国传统音乐文化的传播与活态传承问题。主要强调历史学、图像学、考古学等等具有历史学性质的考察研究,既聚焦于乐舞的历史图像学、音乐考古学、音乐传播学研究,又比较关注具有历史民族音乐学性质“乐舞文化重建研究”。
三、“线性音乐文化空间”彰显的学术问题意识
第一,从“线性文化空间”中音乐的研究走向“线性音乐文化空间”研究。上述问题多是以族群、乐种等为单位的微观个案研究,较少涉及传统乐舞的艺术结构与文化表征的形成,跨族群传统乐舞之间的文化交融与其所处的历时与共时性建构之间的互动关系问题考察。“只是将线路视为一种人文地理的表现方式,而长期缺乏对于线路本身的关注,造成对线路中物质与文化要素独特性研究的缺失”[25]。以往的研究只是静态地关注其音乐本体特征,较少关注地理文化空间的历史与空间形态特征如何影响了传统乐舞文化的形成以及随人的迁移、物的交换等等所携带的传统乐舞文化如何形成音乐的“在地化”过程。或者说,我们只关注到线路文化中音乐形态与风格的研究,忽略了音乐与空间塑造过程中的权力因素如何影响与制约音乐结构、风格与文化象征的生成互动关系研究。即从“线性文化空间”中音乐的研究走向“线性文化空间”与音乐生成的互动关系研究。
第二,“线性音乐文化空间”的塑造既是历史的产物,又是权力关系的空间构建过程。传统音乐品种与风格形成在某种程度上受到诸多权力因素制约。权力关系的立体构建与其所处的社会、政治、历史、民俗、宗教等综合因素有关。音乐在跨区域、跨族群、跨文化间的流动建构了风格的趋同性,因为处于同一条“文化线路”中的民俗、宗教、语言等的互动交融造成了音乐结构、风格的诸多文化关联性。“文化线路是线性遗产的特殊形式,是由特定交通线路为基础串联起来的一条呈线性分布的文化遗产的集合体,主要服务于一个特定的文化交流或产品贸易目的,具有较长的历时性并形成了一种传统,同时跨越较远的地域空间成为跨文化甚至跨文明的联系纽带”[26]。比如花灯戏(地花灯)是长江流域湘、鄂、渝、黔等地的跨区域、跨族群传播以及文化涵化的产物。湖南丝弦小调(“武冈丝弦”“常德丝弦”“长沙丝弦”“浏阳丝弦”“衡阳丝弦”)的分布以及称谓,音乐唱腔的差异多是与湖南境内发达的水上交通有直接关系。
第三,“线性音乐文化空间”是由不同地域、不同风格、不同族群,且具有多元一体特性的传统乐舞音乐文化景观构成的。其与音乐文化景观的概念有细微不同,是由其“文化线路”内众多的音乐景观构成的,是某一传统乐种在随人员的迁徙流动过程中与传播地之间音乐涵化之产物。“文化线路与文化景观是两个不同的科学观念。文化线路以动态性表征,包括无形的、空间动力特征。那是文化景观所不具的;文化景观尽管也具有穿越时代的许多特征,但在本质上更具静态性和规定性。通常,文化线路包含许多不同的文化景观。一处文化景观在地理语境中不是动态的,也不及文化线路潜在涵盖的内容广泛。文化线路可能已经生成并继续生成许多文化景观,反之则不可能发生”[27]。
第四,强调基于“线性文化空间”内的传统乐舞文化事项之间展开移动的、多点的、关系性的互证互释研究,即民族音乐学研究中的关系民族志研究。强调这个带状空间内的传统乐舞的区域与整体之间的关系,多个“线性音声景观”之间互动关系,即音乐生成与发展变迁的过程,特定带状区域内的传统音乐的文化属性的建构如何表征了特定的区域社会、族群、国家、政治之间的关系。其不但隐喻了特定线路与区域内的传统乐舞本体形态的结构生成特征,而且通过这些不同区域、不同族群、不同文化间的传统音声景观的建构过程,折射出王朝国家与地方民众之间的社会、历史、政治、军事、经济之间的互动关系。比如南岭民族走廊内的汉族与少数民族音乐之间的互融、互动、交流过程表达了历史上国家与地方、汉族与少数民族音乐之间的互动关系。其不但是历时与共时性地考察了传统乐舞文化之间的跨区域、跨族群、跨文化的传播,而且也促使民族音乐学的田野工作从静态的、定点的、居住式的,走向移动的、多点的、关系性的线性音乐文化空间内的传统音乐事象之间的互动关系思考。“从点到线,流域研究为区域研究提供了一条线索。因为河流是线性的,不同的文化区域就如同五颜六色的珠子,被河流贯穿在一起,形成一条‘项链’。在不同的文化区域流淌着的河流,发挥着勾连、贯通的作用,成为民族迁徙、文化交融的通道”[28]。
四、结语
“线性音乐文化空间”是由众多传统乐舞文化沿着某一“文化线路”展开的跨区域、跨族群、跨文化的传播,是一种流动的、开放的、动态的、关系性的多维度的音声景观立体构建。我们的研究不能只关注线性文化空间区域中的音乐研究,要聚焦于线性文化空间区域内的多点之间的传统音乐生成的立体性、社会性、关系性研究,即空间如何赋予传统音乐的象征意义,以及空间的历史性、社会性构建如何影响了空间内的传统音乐风格与象征意义的形成。其学科意义不但是研究范式的转换(田野民族志书写从定点→多点),而且从一个新的视角考察传统乐舞结构与风格的形成与其所处的线性地理文化空间的历史与社会构建的互动关系思考。从早期的重视历史音乐学的音乐文献考证,到基于历史文献与田野“接通”性质的历史民族音乐学研究,再到聚焦于后现代地理学、历史地理学、人文地理学思维下的音乐与“路”文化空间互动关系研究,这种研究理念与研究方法与视角的转矩,也是学界受到跨学科交叉互动影响下不断深化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