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刻机之王登峰之路
2022-02-10陈启
陈启
提起荷兰,大多数人的第一反应是郁金香的国度。
但除了郁金香,还有一家曾默默无闻的半导体设备公司—光刻机设备制造商ASML(阿斯麦)。
这家公司的成长经历颇为传奇,成立初期便遇上半导体低谷期,一台设备都卖不出去,亏损近10年,一度徘徊在生死边缘,在老东家飞利浦眼里食之无味,弃之可惜。但顽强的ASML最终挺了过来,逆袭成為当下光刻机领域的绝对王者,目前在高端光刻机市场占据90%以上份额,成为现在EUV光刻机唯一的供应商。
本文将结合光刻机发展历程,呈现如今38岁的ASML是如何一步步登峰的。
芯片产业是信息时代的基石产业。有了更先进的光刻机,人类得以不断挑战芯片制造工艺极限,摩尔定律不断延续,计算机、手机等电子产品性能才能越来越强、功能越来越丰富。
从集成电路工艺的角度而言,芯片制造就是在硅片上指甲盖大小的面积里放下几亿个甚至几十亿个晶体管,并且一次性生产几千片,甚至几万片这样的硅晶圆。同样面积内的晶体管数量要翻倍,就意味着每个晶体管就必须不断缩小。
要做更小的晶体管,需要更小的曝光技术,光刻机就成了最关键的设备。因此,光刻机的水平决定了一家芯片制造公司的工艺水平。
1904年,美国科学家约翰·安部罗斯·弗莱明,为自己发明的电子管弗莱明阀申请了专利,这标志着人类历史上第一只电子管诞生,世界开始迈向电子时代。
1942年,在宾夕法尼亚大学莫尔电机工程学院的莫希利教授,以及计算机之父约翰·冯·诺伊曼的努力下,第一台电子管计算机“ENIAC”被制造出来,计算速度提升了上千倍,但体积大、功耗大、易发热,且极易损坏。
1945年夏天,贝尔实验室制定了一个庞大的研究计划:以固体物理为主要研究方向,希望用半导体技术替代真空电子管。
1947年12月,人类第一个点接触晶体管在威廉·肖克利、沃尔特·布拉顿、约翰·巴丁3人手中诞生,这是一个跨时代的伟大发明。1956年,3人共获诺贝尔物理学奖。
1959年,在晶体管发明10年后,德仪工程师基尔比和英特尔的诺伊斯几乎在同一时期发明了集成电路,人类进入集成电路的新世界。
1965年,英特尔创始人戈登·摩尔预言了未来集成电路的发展规律:每18个月,同样面积下的晶体管数量翻倍,但价格不变(摩尔定律)。这意味着晶体管尺寸将不断缩小,晶体管的制程工艺不断微缩。从制造简单的分立器件到复杂集成电路,光刻机作为关键核心设备登上舞台。
早在1930年代时,哈佛大学杰斐逊物理实验室的天文学家David Mann就制作了一个带有导程螺丝杆和微米线的测量引擎,使其能够高精度地测量和定性光谱。在同事鼓励下,David Mann以自己的名字创立了一家机械测量仪器公司。当时,David Mann的“微米轮”可达1/1 000毫米的精度,是个难以置信的成就。
1959年,传奇公司GCA(Geophsical Corporation of America)收购了这家小公司,David Mann成了GCA公司的一个事业部。
1960年,David Mann的工程师利用博士伦光学显微镜的物镜部分,制造了第一台完全手动的分布重复照相机,即分步重复曝光光刻机。
次年,David Mann向市场推出了第一台光刻机—971型,尽管这台机器有瑕疵,但足以满足当时晶体管的制造水平,包括太平洋半导体、IBM、肖克利半导体、德仪及飞利浦的电子制造部门Elcoma都采购了这台光刻机。
David Mann公司的成功,促使好几家公司开始效仿,踏入了这个新兴的市场。不过当时光刻机市场规模还太小。
除了David Mann,其他美国厂商也向显微镜制造商博士伦订购光学元件,但随着退货次数增加,供应商名单换成了日本尼康。尼康开始进入半导体光学领域,为其日后推出自家的光刻机打下了坚实基础。
1960-1974年,当时光刻机所使用的掩膜板是1 :1的,没有复杂的光学投影系统。彼时市面有两种光刻机,接触式光刻机和渐进式光刻机。
接触式光刻机,即把光掩膜板盖在涂有光刻胶的硅片上,然后打开光源,“咔嚓”一下,完成曝光。这个方法使得光刻胶很容易造成污染,且随着曝光次数增加掩模容易损坏,因此失败率很高,芯片良率奇低,成本非常昂贵。
渐进式光刻机,光掩膜板不与硅片直接接触,光刻机里加入了量测工具,让两者尽可能接近。但新的问题随之而来,光有衍射效应,投影时边缘会变模糊,造成光刻机精度下降,出现较大的投影误差。
因良率太低,一片4英寸硅片压根生产不了几颗芯片,所以当年的芯片极其昂贵。
1967年,美国军方联系老牌光学设备厂商Perkin Elmer(珀金埃尔默,哈勃太空望远镜的镜片制造商),希望能做出一种精度高,又不用把掩膜板压在光刻胶上的光刻机。
经过数年开发,Perkins Elmer在1974年推出了划时代的光刻机:Micralign 100。自此,光刻技术进入投影式时代。
Micralign的诞生大大提高了光刻工艺的良率,良率从接触式光刻的约10%提高到了70%。技术的更新,芯片制造厂的良率大幅提高,芯片价格立竿见影大幅下跌。
1974年,摩托罗拉的6800微处理器要卖295美元/颗。1年后,摩托罗拉的工程师查尔斯·恰克·佩德尔带着一群小伙伴加入了MOS科技。在MOS科技,他们使用Micralign 100光刻机生产出了MOS 6502处理器,只卖25美元。
MOS 6502引起了一位年轻商人的兴趣,他就是苹果的创始人斯蒂芬·乔布斯,随后苹果电脑上用上了这颗芯片。
MOS 6502大卖,仅25美元的价格让一切变得可能,市场上基于MOS 6502的微型电脑如雨后春笋般出现,从数千美元一台的商用微型计算机,到只有几百美元的家用计算机都能看到它的身影。大名鼎鼎的任天堂红白机,以及国内曾红极一时的文曲星也使用了这款芯片。
英特尔、德仪等公司的订单如雪花一样飞来,Perkins Elmer因Micralign 100光刻机的大卖赚了一把。尽管售价是渐进式光刻机的3倍,但良率提高最终能得到的芯片更多,反而让所有采购Micralign 100的客户赚得盆满钵满。
进入半导体设备领域不到3年,Perkins Elmer变成了当时最大的半导体设备公司。
但好景不长,随着摩尔定律继续发展,芯片制程继续缩小,Perkins Elmer基于1 :1纯反射式光刻机的缺点越来越明显。Perkins Elmer开始追不上更精密的芯片制程,步进式光刻机(stepper)开始崭露头角,光刻技术进入缩放投影时代。
1978年,GCA公司率先推出首款步进式光刻机DSW 4800并迅速占领市场,实现了高达70%的市占率。紧接着日本双雄—尼康和佳能也开始发力。而Perkins Elmer继续沉迷在过去的成功中,既没有投入资源研发下一代光刻机,也没有认真听取客户意见故步自封。
丢失市场后的Perkins Elmer醒悟时已为时已晚,最后孤注一掷研发EUV,结果也以失败告终。之后,Perkins Elmer的半导体光刻机事业部卖给了SVG,2001年SVG又被ASML以16亿美元收购。
尽管Perkins Elmer在后续竞争中失败,但不可否认Perkins Elmer的Micralign 100光刻机的贡献。Micralign 100光刻机大幅提高了芯片制造的良率,芯片价格降了下来,由此让更多电子产品走进了寻常百姓家。
至此第一次光刻机大战结束,美国几个厂家你追我赶,最终GCA笑到了最后。但意想不到的是,接下来GCA也因傲慢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GCA公司因研发出倍缩光掩模的步进式光刻机—DSW 4800,夺回了失去的市场和客户。70年代初,GCA把镜头供应商从博士伦换成了尼康,但为了获得所需的远心式镜头,GCA抛弃尼康,转头和德国蔡司合作。
而这家被GCA抛弃的日本公司,最终成了GCA的掘墓人。
正当GCA与Perkins Elmer两家美国厂商打得火熱时,1982年在IBM和德仪的工厂里,出现了一台来自日本的光刻机,不管是光学系统,还是硅片工件台,看上去都和GCA的步进式光刻机相差无几,这就是尼康当年推出的NSR-1010G。
这家在镜头配件只配做GCA小弟的日本厂商,如何能在短短几年内打破GCA的技术垄断,研发出自己的步进式光刻机?故事要从1976年说起。
1976年,日本通信产业省开启了超大规模集成电路计划,简称VLSI项目—“超LSI技术研究组合”。
这是一个举日本全国之力推动电子产业升级的4年规划,政府每年投入180亿日元,组织日本国内最大的5家半导体厂家东芝、日立、富士通、三菱电机、日本电气在内的技术联盟,彼此合作,集中力量办大事。
在4年规划中,日本选择了几个重点突破技术路线,光刻技术和设备就是其中之一。
作为老牌光学厂商的尼康和佳能,虽明面上没有加入该项目,但也在通产省组织的合作框架下,开始了各自的光刻机研发任务。
佳能此前主要做相机镜头,在精密测量部分尚有欠缺,因此仿制的是门槛较低的Micralign对准仪。而尼康前身是成立于1917年的日本光学株式会社,在镜片制造和精密测量技术方面有深厚的技术功底,既能做高分辨率的相机镜头,又能做天文望远镜,甚至军工级的光学测距仪。此外,在GCA踢除安捷伦时,用过一段时间的尼康镜片,让尼康得以了解半导体光学的最新技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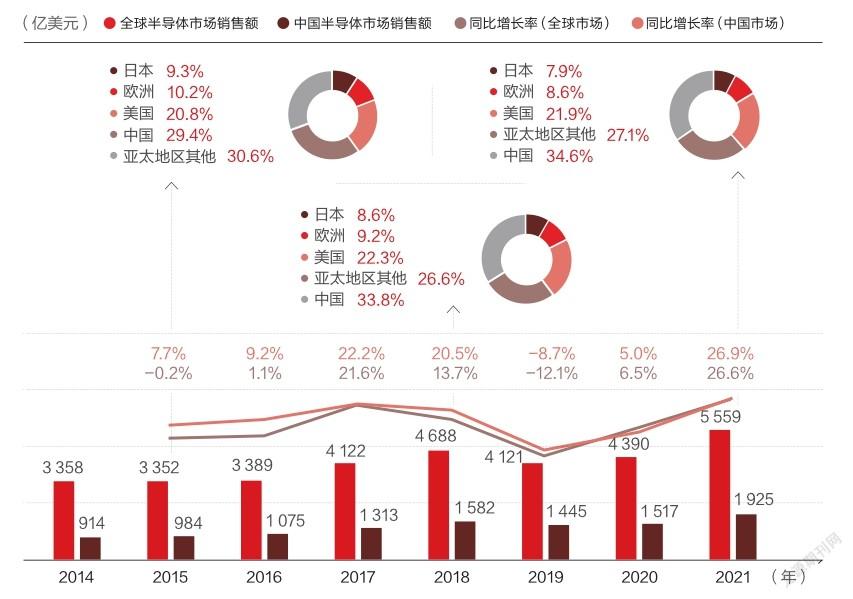
精密光学镜片加工能力和精密测量技术,这两者都是解锁步进式光刻机的前置技能,因此尼康被寄予厚望。
尽管自身技术积累不俗,但尼康要想实现从无到有,也非易事。日本电气把买到的GCA光刻机交给尼康拆解分析研究。不久后的1980年,尼康推出了首台步进式光刻机。
初代尼康光刻机有不少问题,但在日本电气和东芝支持下,多方技术人员通力合作,及时反馈实际工作过程中的问题,帮助尼康更新迭代技术,尼康光刻机水平迅速提高。
1982年,尼康成功把机器卖到了IBM和德仪。美国人惊讶地发现,尼康的“山寨”光刻机有不输GCA的性能,而镜头稳定性和自动化程度在GCA之上,更重要的是其服务态度,非傲慢的美系厂商可比。
当时,美国厂商设备卖出去就不管了,而日本厂家还赠送5名工程师组成的服务团队,随时提供技术支持,保证光刻机稳定运行。
当尼康一路高歌猛进时,GCA的产能问题迟迟没有改善,其镜头供应商蔡司当时正值低谷期,镜头频频出现质量问题,延迟交货,无法满足GCA扩大产能的需求。此消彼长之后,其他厂商逐渐失去了对GCA的耐心。
1984年,尼康出货量基本与GCA持平,甚至还先于GCA推出升级光源后的i线光刻机NSR-1010i3型,广受客户好评。此时,另一家日本光刻机厂商佳能,也推出了自己的首款步进式光刻机FPA-1500FA。
同年4月1日,在欧洲荷兰的一个小城市,还诞生了一家脱胎于飞利浦Natlab的小公司,即日后的光刻机霸主—ASML(阿斯麦),但当时ASML还完全没法与尼康及GCA竞争。
1985年,尼康正式超过GCA,成为业界第一大光刻机供应商。这一年GCA大亏1.45亿美元,次年放弃低端机型断臂求生,把全部身价压在了高端机上,但因资金链断裂无力支撑后续研发,而蔡司退出合作给了GCA致命一击。
1988年,走投无路的GCA被出售给了General Signal,几年后GCA因找不到买主被迫关闭,当年的美系光刻机龙头就这样消亡了。
80年代初还占据大半壁江山的美系三雄,到80年代末已摇摇欲坠,而日本光刻机双雄尼康和佳能强势崛起,超越美系厂商占据了超70%的市场份额。
十年不到,风光一时的美系厂商被日系厂商反超,日系光刻机厂商如何能迅速崛起打破美系厂商垄断?可以总结出以下这些经验。
首先,内因方面:
一是日本两家公司在光学设备及精密机械上拥有深厚功底。这是研发光刻机的前置技能。
二是日本集中力量办大事,给予了优厚的政策和丰厚资金。VLSI项目出钱,成立联合实验室,实现上下游厂商通力协作。而美国芯片厂不愿和GCA分享信息怕泄露技术细节,导致GCA不知道客户的真实情况。
三是日本厂商垂直整合度更高。尼康和佳能不管是镜头、平台,还是自动化技术全部自研,从源头解决需求,研发沟通更迅速,技术迭代更精准,生产成本更低廉。而GCA完全依赖蔡司镜头,一旦蔡司品控和沟通出现问题,会造成灾难性后果。这个问题在ASML和蔡司的早期合作中也出现了,ASML对蔡司进行了彻底改造,才消除了这个短板。
四是美国厂商的守旧与傲慢。Perkins Elmer故步自封,死守Micralign系列,看不到缩影式的发展,丢失市场后着急转型EUV,但已为时已晚;GCA则目空一切,当客户反馈尼康和佳能的设备性能更好时,管理层甩锅给销售团队,而不是反思自己的设备为什么不如竞品。
五是日本厂商的经营理念和服务支持。GCA在亚洲的服务团队,都是外派的美国人,无法融入当地客户;而尼康非常重视客户需求,在1982年第一台设备交付美国客户时,就开始雇佣当地工程师建立硅谷服务中心。
其次,外因方面:
一是70年代末半导体产业发展前期,各种光刻技术路线层出不穷,光刻机还处于草莽时代,日本可以用高效和低成本打法反超美系竞争对手。放到现在则很难,在光刻技術路线基本成熟、尖端研发陷入停滞的当下,中国厂商很难复制当年尼康的成功路线。
二是在当时的经济大背景下,美国处于石油危机所引发的经济衰退中,GDP下降、失业率上升,美联储不得不实行货币紧缩政策,而日本经济则处于景气周期,尤其是半导体产业。
因此,80年代的日系厂商,不仅在光刻机领域把美系厂商按在地上摩擦,在内存等其他芯片市场也攻城略地,打得美国芯片公司节节败退。那些年无论是德仪、仙童,还是AMD都自身难保,英特尔甚至因为退出内存市场而被迫裁员。
但好景不长,在产业层面日系公司把美系公司打得毫无招架之力,回头美国就把日本放到案板上狠狠宰了下去,这一刀让日本大失血,好多年都回不过神来。
这一刀就是著名的美日《广场协议》。
1985年,著名的《广场协议》诞生,在协议生效后3个月内,日元兑美元快速升值20%,不到3年升值接近100%,削弱了日本出口商品的竞争力。1986年9月出台的《美日半导体协议》,对日本芯片强制征收100%的惩罚性关税。
尽管日系公司依靠之前的技术积累继续保持市场份额,但这两刀砍得实在太狠,自此日本芯片产业盛极而衰,在政策大刀下被迫退守。行业景气周期还能吃肉,一旦出现经济下滑遇到行业冷周期,日系厂商便死伤无数。
在台积电以及韩国三星们的进攻下,日系企业在内存及先进数字芯片制造方面节节败退,而三星和台积电发展壮大至今,成为半导体行业两大巨头。
2012年,日系内存最后的独苗尔必达公司被美光以25亿美元的“白菜价”收购;2017年,东芝存储也因东芝集团自身深陷财务问题,最终被美系的贝恩资本以180亿美元收购,后改名铠侠,曾辉煌一时的日系存储基本消失殆尽。
日系光刻机厂商全面打败美系厂商赢得了光刻机战争,但对日本而言,两个不平等协议一签,输掉了半导体的一个时代。
正当美系和日系厂家竞争白热化时,没人注意到欧洲的飞利浦也在自主研发光刻机。
平房里诞生的巨头
1950年代,作为欧洲老牌工业巨头的飞利浦集团也开始进入微电子领域。
1952年4月,飞利浦的物理实验室Natlab派代表团从荷兰到达美国AT&T的贝尔实验室,参观学习半导体技术。贝尔实验室向参会者分享了所有晶体管技术,专利授权费仅2.5万美元。
1952年底,Natlab尝试生产了数百个结式晶体管。到1958年,飞利浦的技术已经非常成熟,推出了各种元件,在商业上大获成功。
1963年,当David Mann的新一代1080型光刻机设备出现在飞利浦的半导体和材料事业部Elcoma时,年轻工程师克洛斯特曼(后来的光刻机构架师)仔细学习之后,觉得它还有很大的改进空间,于是决定自己做一台。
1966年秋,克洛斯特曼四处学习积累了丰富的光刻经验。1年后,成功制造出了6个镜头的重复曝光光刻机的原型机。这台设备在当时已经是最先进的技术了,但毕竟是原型机,设备还不够成熟,且当时光刻机市场不大,飞利浦还没想好到底要不要将其商业化,因此一拖再拖。
到1980年代初,财务状况不佳的飞利浦决定关停光刻机项目,去美国找了Perkins Elmer、GCA、Cobilt、IBM等公司,都没人愿意合作。
1983年,ASM International(ASM国际)创始人普拉多(Athur Del Prado)听说后,主动找到了飞利浦。1年后,飞利浦同意与其设立持股50 :50的合资公司。飞利浦和ASMi各自出资210万美元,而飞利浦把16台还没做好的库存PAS 2000光刻机折价180万美元算作出资款。
就这样,1984年4月1日,新生的ASML呱呱坠地,尽管顶着脱胎于飞利浦的光环,但之后10年间,ASML都不曾盈利,飞利浦和ASM一度失去信心,甚至ASM吃不消无止境的烧钱,把股份卖了,亏了3 500万美元。谁也不曾料到,从生死边缘站起来的ASML,成了当今世界最炙手可热的科技公司。
2022年4月25日,其他欧洲知名公司如飞利浦、空客、宝马,市值分别为234亿欧元、819亿欧元、489亿欧元,加一起1 542亿欧元,而ASML为2 414亿美元(约2 245亿欧元),市值仅次于LV集团。
自信的CEO
新公司建立之初,虽顶着飞利浦Natlab的光环,但当时ASML的光刻机无人问津。
彼时的光刻机巨头是美国的GCA和新崛起的日本尼康。装机量是所有人关心的关键指标,GCA和尼康已达数百台,而ASML还是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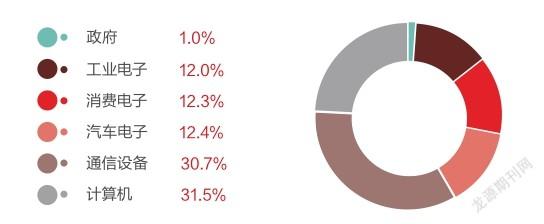
尽管其他人都认为ASML不可能突出重围,但ASML首任CEO斯密特(Gjalt Smit)断言,从大规模集成电路(LSI)到超大规模集成电路(VLSI)的一步显然就在眼前,芯片的晶体管尺寸将缩短至1/1 000毫米以下,光刻机也不再处理4英寸晶圆,而是转向6英寸。
这种变化下,产业需要新一代光刻机,它必须可以将0.7微米的细节成像到晶圆上,并实现更紧密的微电子集成,但目前没人做成这一套光刻解决方案。
美国和日本的步进式光刻机达不到生产VLSI的水准,包括佳能、GCA、尼康和Perkins Elmer公司制造的光刻机,还在用导程螺丝杆来移动晶圆台,这意味着它们的图像细节达不到1微米的定位精度,而精度恰恰是ASML的技术优势所在。
斯密特认为,大家都低估了ASML的技术潜力。尽管当时ASML排在光刻机设备供应商的末尾,但他坚信可以成功,特别是ASML精确的对准技术当时是无与伦比的。
要么开业就关门,要么交付一台可靠的VLSI光刻机,让ASML的光刻设备征服客户和市场。斯密特坚信新世界的大门会对勇敢的创新者打开。
带着这样的精神,ASML推开了光刻机世界的大门。
初露锋芒的PAS 2500
斯密特发现,PAS 2000之所以不符合客户需求,是因为油压设备对晶圆厂干净的洁净间而言是个巨大的灾难。于是,他决定开发新一代采用电动晶圆台的光刻机,型号PAS 2500。但留给ASML的时间只有2年,2年内如果不能把PAS 2500制造出来并顺利交到客户手上,市场就会被虎视眈眈的巨头们瓜分,ASML就真的要关门了。

为了最短时间把PAS 2500造出来,斯密特做了巨大的改变和尝试。
斯密特觉得,如果ASML打算一年制造数百台设备,有太多部件加工工作需要自己完成,对于初生的ASML来讲,成本完全不能接受。
于是,ASML成立之初就定位为:一家只进行研发和组装的公司。别人都觉得ASML完全疯了,但正是ASML这种开放的理念,反而让ASML变得更加高效。日后也为与尼康在世纪大战中的逆转埋下伏笔,后者因为过于封闭和保守的体系而陷入泥潭。
对ASML而言,必须要快。斯密特打破传统,把光刻机拆分成各个模块,专业团队并行开发每个模块,每个模块都有自动通信接口,最终模块组装成整个光刻机。这种模块化研发安排,大大提高了效率。
当时的步进式光刻机有数千个零部件,ASML花费数百万美元采购了美国施乐的XBMS系统,这在当时是最快的物料管理系统。同时,ASML和供应商建立了深度合作关系,告诉供应商需要什么、什么时候要,打通整个产业链,确保新技术能快速有效转化为可靠的产品。ASML的理念就是开放创新,同时管理好供应商物料,高效低成本解决所有问题。
接着,ASML又花了不少钱建无尘车间,确保机器组装不受外界因素干扰。
在研发中,ASML比同行更进一步的是,拒绝闭门造车,邀请客户共同开发测试。
现在,芯片制造公司与供应商通力合作已经成为行业文化,于是有了“一代设备,一代工艺,一代器件”的说法,新工艺都是大家配合搞出来的。英特尔、台积电、三星等制造大厂和设备大厂AMAT、LAM、TEL等都是这样过来的,通力协作,共同进步。
1986年,ASML和德国蔡司深入合作下,终于推出了第二代产品PAS 2500,并第一次将其卖给了美国当时的创业公司、今天的NOR Flash(非易失闪存技术)巨头赛普拉斯(Cypress,2022年被英飞凌以101亿美元收购)。
救急的大单
80年代,为了不被势头强劲的美日甩开距离,欧洲共同体在高科技领域推出了政府资助主导的“尤里卡计划”。
在该计划框架内,有关集成电路的子计划叫作JESSI,其中最重要的一个项目叫MEGA,即做Megabit(1Mb)的内存。内存是电子业的石油,几乎所有的电子产品都需要用到。目前内存已经成为集成电路领域最大的一块细分市场,每年有近1 000亿美元的市场规模。
而MEGA项目的核心主导者就是飞利浦和西门子,考虑到内存业巨大的技术和投资风险,两公司的分工是:飞利浦负责SRAM(静态随机存取存储器),西门子负责DRAM(动态随机存取存储器)。
1984年,MEGA项目正式启动。然而,SRAM的市场需求并不大,且英特尔还把它集成到CPU里变成了Cache(缓存)。最终飞利浦的MEGA项目失败了。
有意思的是,飞利浦MEGA的失败却酝酿着一个巨大的成功:台积电。
台积电1987年诞生时,是中国台湾工研院和飞利浦的合资公司。在台积电里,飞利浦占了27.5%股份,是最大的外部股东。飞利浦毫无保留地把MEGA生产线开放给台积电学习,还把整条生产线搬到了台积电。
意外的是,1988年底新生产线快装好时发生了一场火灾,台积电把被烟熏了的光刻机退回ASML,并下了一个17台新机的订单。
这笔订单帮了大忙。
当时ASML刚好缺钱,这些订单在关键时刻救了急。结果为火灾买单的保险公司成了1989年ASML最大的客户,ASML勉強盈利了1年。
时势造英雄。ASML和台积电两个当时默默无闻的小公司,因缘巧合互相扶持,成了今天半导体行业的绝代双骄。
网红爆款光刻机的诞生——PAS 5500
尽管台积电17台订单替ASML救了急,但彼时的光刻机市场依然是日本双雄尼康和佳能的天下。
尼康一年出货400台设备,显然ASML还无力挑战尼康。
最终1991年,ASML渐进式创新,稳扎稳打,催生了真正的翻身之作—PAS 5500。而在PAS 5500的开发过程中,ASML还征服了一个重量级客户—蓝色巨人IBM。
1988年,IBM宣布将成为第一家在更大晶圆(8英寸)上制造芯片的公司,为此孤注一掷砸了10亿美元,开发了业界第一条8英寸产线及配套工艺。
如果ASML能把光刻机卖给IBM,那么同行都会来找ASML,这就是头部标杆客户的示范效应。但想要争取到IBM的青睐并不是一件易事,ASML将希望寄托在了PAS 5500上。
当时,世界上没有一台光刻机可以像模型积木一样拆装。就传统光刻机而言,当光刻机出问题要更换零部件时,芯片制造商通常需要停产数周花费大量资金,而ASML模块化的设计在设备出问题时,只需及时更换问题部件,就能在最短时间内让光刻机重新投入生产。时间就是金钱,ASML坚信这套技术足以打动IBM。
1991年,PAS项目经理波拉克用摄像头记录下光刻机组装的全过程,然后带着录像带直冲美国东海岸。在IBM会议室,看到视频播放后,IBM的人大吃一惊,他们从未见过如此先进的设备。
这台ASML眼中的“梦想机器”PAS 5500,看到了胜利的曙光。
PAS 5500模块化的设计使客户可以根据不同工艺随意选配不同部件包,因此子型号层出不穷,甚至多到连ASML员工都搞不清楚到底有多少个型号。ASML利用PAS 5500的技术平台做到了百花齐放。
电话那端的奇怪口音
90年代初,三星在美国的技术帮助下,发起了对日本同行一轮轮的进攻。彼时微软的Windows操作系统走进千家万户,这是PC历史上的黄金时期,催生了对内存的巨大需求。
到1993年,三星成了全球最大的内存制造商,这一年三星内存增长72%,营收超20亿美元,反超日立、日本电气、东芝等日系传统内存巨头。
同年秋天,ASML的销售总监道格·马什接到了一通电话,电话那头是韩国三星的一名采购经理,他问马什是否有兴趣来首尔谈论未来的合作机会。
尽管三星画的饼非常诱人,但提出了各种新技术要求。
当时,不同产线对光刻工艺要求不同,ASML规模较小,无法为每个客户提供半定制化服务,更没精力为单个客户进行新设备的大规模研发,所以ASML只能做一些标准设备。
但如果抓住三星,那么未来几年可以交付100台光刻机,其价值超过5亿美元,这是一个可观的数字。最终ASML答应为三星的内存光刻工艺做一些改进。
1995年2月,第一台PAS 5500到达三星工厂。三星用它开发了一项0.25微米工艺用于生产 16Mb内存颗粒。不久后,韩国另一家内存厂商海力士也开始使用PAS 5500。次年10月,海力士装机了第一台PAS 5500,到1998年,这个内存巨头一跃成为ASML的最大客户。
尽管PAS 5500通过了IBM验证,但并没有下大订单给ASML。因为尼康的NSR-S204同样优秀,美系厂商对尼康的依赖程度很高,客户惯性依然强大。结果是三星、海力士这些存储大厂成了ASML的大客户。
但面对这么多订单,ASML又犯难了。
改变这个老古董
ASML在韩国市场大获成功,但要如何满足源源不断的订单需求?蔡司何时能及时交付镜头?
ASML在踢掉法国CERCO后,蔡司成了其核心部件镜头组的供应商。但蔡司和ASML两家公司文化差异极大,ASML是一家年轻且雄心勃勃的公司,蔡司是一家历史可追溯到19世纪中叶的家族企业,一个不折不扣的老古董。
1990年时,蔡司6名顶级技工1年只能磨出10套i线光刻镜头。ASML必须说服蔡司增加产能,准时交付高质量的镜头。
ASML意识到,越来越先进的光学镜头已经让蔡司引以为豪的工匠们的“金手指”越来越吃力。工匠们打磨镜头完全靠手感,显然旧方法已经不能满足PAS 5500所需。如果蔡司不改变,ASML可能因为蔡司的低效,让好不容易争取来的订单飞走。

于是,对这个老古董的改造开始了。从观念灌输到新技术新设备,蔡司百年以来的老生产线被改造成符合ASML要求的柔性生产线。最终,交付的镜头品质和效率大幅提高。
之后,ASML和蔡司还签署了一份契约,ASML在蔡司半导体光学部门(SMT)拥有24.9%股权,两者牢牢绑在了一起。
此后,蔡司不断提高技术成为全球最强光学公司,没有之一。
成功上市
无论是韩国客户的大订单,还是下一代DUV研发,都需要投入重金,钱从哪来?此时的飞利浦已经失去了往日的辉煌,再靠老东家输血不太现实。

于是,ASML监事会成员亨克·博特想了一个办法:让投资者掏钱,让ASML上市。
1994年春天,飞利浦和ASML的高管们紧锣密鼓为在纳斯达克的路演做好了准备。经济和行业仍处于上升期,博特希望在新危机再次出现之前,完成上市。
在举步维艰的一年里,ASML收到了来自三星的大订单。蔡司CEO利希滕贝格听到巨额订单消息后,选择赌一把,砍掉部分业务部门,把剩余部门整合到一起,按照ASML的要求改造生产线。
利希滕贝格赌对了,蔡司解决了镜头生产对人手的依赖。随着PAS 5500签下一个又一个订单,蔡司也搭上ASML的东风,一扫阴霾。
1995年3月14日,ASML在美国纳斯达克上市,获得发展急需资金。其PAS 5500i线步进式光刻机成为了芯片厂的主要设备。
1996年初,ASML又推出了DUV 248nm版本,这些设备单价售价高达600万美元。
而彼时,尼康依然是横在ASML面前的强大竞争对手。
兵败157nm
凭借PAS 5500,当时除日本和美国市场外,ASML势如破竹。但由于客户惯性,英特尔、IBM们依然选择了尼康的光刻机。
1990年代末,集成电路工艺开始从130nm进入90nm,晶圆尺寸也从8英寸升级到12英寸。与此同时,光刻机的波长也从248nm进入到193nm。
干式193nm光刻机的极限工艺是65nm,再往下就很难实现了。如何跨入40nm工艺,成为阻挡在所有半导体厂商门口的拦路虎。
2000年,ASML收购SVG,拥有了157nm技术,砸了数亿美元进行研发。此外也尝试开发EUV光刻机。没想到的是,“双保险”一时半会没用上,一个更巧妙的技术解决方案出现了。
2002年7月,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的157nm微影技术研讨会上,臺积电的林本坚在介绍“浸润原理”的专题演讲时,宣布找到了 134nm波长的光波。林本坚回到中国台湾后,在张忠谋及蒋尚义的支持下,台积电开始了“浸润原理”的商业化研究。
“浸润原理”,即在晶圆光刻胶上方加一层水,水的介质折射率是1.44,193nm/1.44≈134nm。因此,在不改变光刻机波长的情况下,193nm波长能等效出134nm的波长,属于小工程改动但得到最大效果。
2004年12月,ASML正式推出浸没式光刻机的原型机,并证明了浸没式光刻机方案具备可行性。
2006年,ASML的XT 1400i进入英特尔并顺利通过40nm工艺验证。1年后英特尔向ASML下了大订单,其余厂商纷纷效仿。而尼康花费心血搞出来的157nm光刻机无人问津。
尼康在2000年还是光刻机领域的老大,但到2009年被ASML反超,只剩下3成市场份额,ASML占了近7成。尼康的干式157nm败给了ASML的193nm+浸没式方案,这一仗输得一败涂地。
193nm浸没式光刻成功翻越157nm大关,把工艺带到了40nm以下。随着技术的改进,193nm浸没式光刻机一直做到了今天的7nm工艺。
TWINSCAN系统
2020年,ASML出货了史上第一套能够每小时处理超过300片晶圆的光刻系统,这得益于该系统上最新的TWINSCAN平台技术。
TWINSCAN,即双扫描工件台,这项技术是ASML保持竞争力的秘诀之一。
对于垄断CPU市场的英特尔而言,市场蛋糕足够大,完全可以躺赚,因此未要求高产能,一度英特尔的产能利用率只有60%。但台积电们不一样,产能就是生命线。对台积电这类晶圆代工企业而言,必须在成本、效率、产能上有优势,才能在竞争中站稳脚跟。ASML准备用更高产能的光刻机抓住台积电们的心。
如同许多突破性技术一样,回顾起来解决方案其实很简单。图案在被曝光到晶圆前,必须对晶圆进行精准量测。量测和曝光都需要时间,为提升效率,为什么不在曝光一个晶圆的同时,对后一个晶圆进行量测和对准工作呢?就这样,TWINSCAN系统诞生了。
TWINSCAN是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具有双晶圆工作平台的光刻系统,量测对准和曝光同时进行,极大提高了光刻机单位小时内的产能,帮助台积电们提高了生产效率。
TWINCAN系统与浸没式系统双剑合璧,让尼康彻底败下阵来。
时至今日,受制于专利和技术,尼康依然在追寻能对标ASML的TWINSCAN的方案。
外星科技般的EUV
如果世界没有EUV,也许就永远卡在7nm工艺上了。
如今,ASML的NXE系列EUV光刻机一台卖到1亿多美元,高NA版本的EXE 5000系列每台要卖3亿~4亿美元,客户仍排队下单。有人说,ASML躺着就把钱赚了。
实际上为研发EUV系统,ASML近20年时间投入了上百亿美元研发费用。若从成本角度考虑,一台EXE 5000卖3亿多美元算不上躺赚,毕竟就算是EUV光刻机也就50%出头的毛利率,成本之贵可想而知。
1997年,英特尔看到了跨越193nm的巨大难度,决心集结精英一起愚公移山,以公司形式发起了EUV LLC的合作组织。
该组织由英特尔和美国能源部牵头,集合了当时如日中天的摩托罗拉、AMD,以及享有盛誉的美国三大国家实验室:劳伦斯利弗莫尔实验室、劳伦斯伯克利实验室和桑迪亚国家实验室,投资2亿美元,集合百位科学家,从理论上验证EUV可能存在的技术问题。
英特尔还力邀ASML和尼康加入,因为当时美国光刻设备公司基本已经凋零。最终尼康被排除在外,更为开放的ASML做了一堆许诺后被允许加入。
2006年,在ASML实验室里有了EUV的原型机。4年后,在ASML手中诞生了人类第一台EUV工程样机:NXE 3100。
珍贵的门票
2000年,ASML以16亿美元收购了市值仅10亿美元的SVG。当时SVG年营业额2.7亿美元,光刻制程水平远不如ASML,市场并不看好这次收购,消息一出,当天ASML股价大跌7.5%。
但这次收购ASML得到了最宝贵的两样东西—技术专利和门票。
SVG曾通过收购Perkins Elmer有了EUV及反射镜技术专利,而现在被ASML收入囊中,ASML有了EUV相关专利技术。
最重要的是,收购SVG还收获了另外一样东西—英特尔的供应商资格,这是一张弥足珍贵的门票。ASML曾数次敲响英特尔的大门而不开,这次终于叩开了,得到业内大客户的认可才算真正成功。
探索永无止境
第一台验证机NXE 3100只能做到每小时曝光30片晶圆,无法满足客户要求,最大的问题卡在光源强度上,想要增加产能,就必须增大光源功率。
当时负责光源的Cymer是一家美国公司。目前,全球仅2家有能力生产光刻机光源的公司,除Cymer外还有日本的Gigaphoton(小松),但EUV光源主要是Cymer负责。
2012年,ASML花费26亿美元收购了Cymer,随后投入人力物力,把光源功率从30W提升到了250W,产能提高到每小时125片,勉强达到商用标准。2018年,正式商用版的EUV光刻机NXE 3300开始出货。
ASML在EUV上的成功彻底断了尼康的念想。目前而言,尼康不可能在短期内研发出比ASML更強的设备。
如今在光刻机领域,ASML占据了90%以上份额。
从90年代末到现在的20多年时间里,ASML依靠“TWINSCAN系统”“浸没式系统”“EUV系统”三大战役,彻底把昔日的光刻巨头尼康踩在了脚下,ASML也从当年那个平房里不起眼的小公司,成长为半导设备领域的绝对霸主。
如果你觉得ASML成功研发出EUV光刻机,把工艺带到7nm就大功告成准备躺赚就错了。在5nm以内,以及英特尔路线图上的18A工艺需要更先进的光刻机。
新技术探索的道路是永无止境的。
有人赞叹诞生于飞利浦的ASML是天之骄子,但纵观ASML的38年发展史,很难说过程是一帆风顺的。
创业前10年,亏损有9年,前期一台设备都卖不出去,但ASML并没有放弃,而是紧紧抓住机会,一步步走到了舞台中央。ASML不断寻找对手设备缺陷并加以改正,不断自我突破。合作、开放、创新、进取,是ASML能成为现在光刻设备霸主的内在精神。
很多人一直在思考:为什么ASML能做出这样先进的光刻机?
从产业实际角度出发,光刻机是人类科技之集大成,是全球顶尖公司、顶尖科学家和众多工程师们共同努力的结果。
研发光刻机需要众多前期技术做铺垫,是一个厚积薄发的漫长过程。核心技术当然要掌握,但开放创新融入全球产业链,提出更好的技术和做出更好的产品才是正确出路。
在众多半导体设备商中,ASML除了EUV,其他光刻机都能买到。
全球环境风云突变,有挑战也有机会。我们不仅需要加大底层技术研发力度,更要吸取各方长处,不仅是技术,还包括管理、文化、市场运营、团体配合、产业链搭建等,只有这样我们前进的动力才更足更稳。
ASML之所以能成为现在的样子,是在成立之初就计划好的。
(本文来源于公众号启哥有何妙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