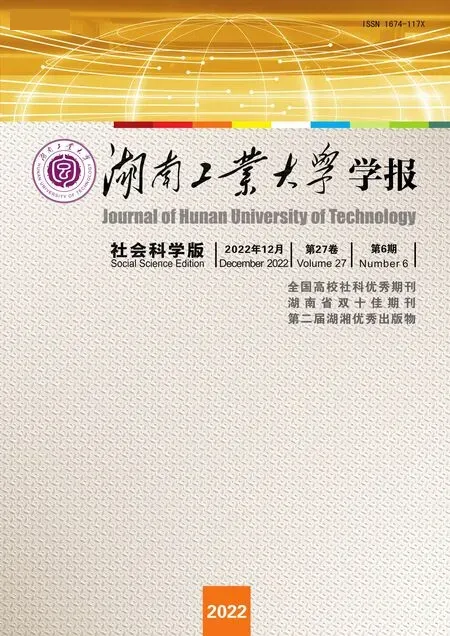《送我上青云》:都市独立女性影像书写的新境界
2022-02-10傅异星
傅异星
(湖南师范大学 文学院,湖南 长沙 410081)
2019年滕丛丛导演的处女作《送我上青云》(以下简称《送》)以对女性欲望的大胆表达引发了社会较为热烈的关注。3年过去,关于电影的讨论依然持续不断。作为一部表现当代都市女性生存状况和精神世界的电影,《送》对当代女性独立之路有着深入而独特的思考。不过,从已发表文章来看,学界对《送》的研究多集中在女性意识的觉醒和当代社会依然存在的男权统治等方面,而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从当代都市女性已经独立这一状态出发来评价它之于当代女性的现实意义以及它在中国女性电影创作方面的探索性价值。
一、独立:被批评所忽略的当代都市女性生存状态
截至2022年4月,中国知网共发表以 “《送我上青云》” 为主题词的评论文章40篇;其中以 “女性意识” ” 性别意识” 为关键词的文章10篇左右,以 “困境” 为关键词的文章12篇左右。这些文章主要从意义、价值和艺术缺憾两个方面对电影进行了多样的讨论。肯定的方面主要集中在:(1)电影在中国电影史上第一次提出了女性性愉悦的权力问题;(2)电影揭示了当代社会中女性欲望、女性诉求的表达困境,以及社会刻板女性印象形成的女性发展困境;(3)电影突破了二元对立的性别思维,从女性角度观照了物质高速发展下当代社会男女两性的精神和生存困境,显示了更为阔达宽容的女性视角。对电影的批评则主要集中在其情节结构和人物塑造上。电影上映半个多月后,滕丛丛的老师谢飞导演就指出,《送》在情节结构陷入了 “多人多事” 中心不突出的境地[1]。可以说,谢飞导演的言论几乎左右了之后评论界从艺术表现方面对该电影评价的走向。其后,《艺术评论》发表《人物塑造的逻辑偏移影响电影表现的深度——〈送我上青云〉的缺憾剖析》一文。该文认为,电影主题含混不清,众多思想交杂,浅尝辄止;人物性格内涵单向度,缺乏现实生活逻辑。文章认为,影片艺术缺憾的形成原因主要是 “影片观念太强、试图触及的东西太多而四处铺展导致重心缺失……到处都是思想和重点,就使得面面俱到、过于直露的弊端展露无遗”[2]。以上两种批评,虽然也指出了这部电影存在的一些不足,但依然肯定其在女性主题以及艺术表达上的开拓性探索。
不过,2020年《当代电影》上发表的《〈送我上青云〉:女性主义是一种表达,还是一个标签?》一文却否定了该电影在女性主题上所作的探索意义。该文认为, “整部影片却凸显出人物脸谱化,场景架空化,故事失真化的问题,导演既没有清晰地阐释盛男所面对的真正问题是什么,也没有诚实地描写女性在日常生活中的真实困境,这都让影片成为一种空洞而又漂浮不定的能指。” 文章认为,电影有价值的地方倒是 “反映了金钱导向的价值系统下主体的失落” , “并不是男性压迫了女性,而是一种整体性的奔溃” ,电影具有在揭示金钱社会中男女两性普遍精神困境方面的价值[3]。这些评价不一的文章,是否全面地揭示了《送》的意义和问题呢?从性别角度看,一些年轻女性评论者往往从女性主义批评理论出发,分析电影中当代社会的男权统治以及女性在男权社会中生存发展的困境,其大都囿于20世纪早期女性主义批评两性对立的理论视野;而一些男性评论者则无法感同身受地体会现代都市独立女性的心灵世界,难以与电影产生更深刻的共鸣。
应当承认,《送》的主要价值,的确不是其对当代社会男权压迫的揭示。20世纪中国女性的解放是同民族解放、阶级解放结合在一起的,女性解放构成中国革命事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中国革命事业大大促进了中国女性的解放。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在法律、制度、组织、舆论等多方面为推动男女平等和女性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女性依法获得参与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建设的权利,社会地位和作用发生历史性转变。因此,在经历了100多年女性解放发展历程的当代中国,两性平等的观念已然深入人心;特别是长达30多年的独生子女政策使得 “重男轻女” 传统观念得到了重大改造。当然,有着2000多年历史的 “男尊女卑” 观念不可能在短时间内烟消云散,中国社会在文化观念方面必然还存在一些隐性的女性歧视,但不可否认的是,中国女性在平等受教育、平等工作、平等待遇等方面的权利得到了基本保障,越来越多接受教育的女性走上了独立自主的道路。《2015女性生活蓝皮书》一书刊登的《第10次中国城市女性生活质量调查报告(2014年度)》显示,在一二线7个城市1000多名女性调查对象中,本科及以上学历的女性占68.2%,高中及以下学历的女性占7.9%;在女性的职业分布中,公司上班的女性占比44.2%,公务员和事业单位上班的女性占比43.4%。2014年美国贝恩公司关于中国职场两性平等的调查结果显示,女性占中国大学毕业生的47%和占全部工作人群的46%,中国女性就业率达到73%,中国是全世界女性就业率最高的国家之一[4]。因此,对于当代中国都市女性来说,她们的困境并不是普遍的男权压迫,她们也不再是鲁迅《伤逝》中的子君,光喊出了 “我是我自己的” 心声却缺乏自我独立的能力。事实上,她们已经走在了一条独立自主的人生道路上,这也是我们评价《送》时应该考虑的时代背景。
电影《送》没有停留于女性觉醒与女性是否能独立等女性发展的初始问题,而是以当下都市独立女性为对象,将女性独立问题的讨论往前推进了一大步。影片主人公盛男是一位出生1980年代初、几近30岁、高学历、未婚的都市独立女性。盛男的都市单身女性的身份正是新世纪以来都市单身女性人数快速增长现象的一个影射。有关中国单身青年现象研究数据显示:2000至2010 年,20~44岁各个年龄段的单身青年女性比例都呈增加趋势,而且女性单身现象以都市为主;随着教育程度的提高,女性单身的比例在逐渐增多,其中25~29 岁研究生学历的女青年单身比例增加更快。都市青年女性不婚的一个主要原因是更高的受教育程度、更有保障的工作和更高的收入降低了她们对于结婚的迫切性[5]。另据2018年民政部的统计数据显示,中国男女单身人数达2.4亿,其中女性单身人数超过1亿。由此可以看出,都市单身女性是中国女性中一个数量庞大的存在,这是电影中盛男形象的现实社会基础。影片不以历史中的女性生存状况为表现对象,而是将生死病痛摆到都市单身女性面前,试炼她们面对生活问题的能力,考察她们的独立性程度,思考摆脱困境的可能性。这是一个具有鲜明现实意义、未来指向的主题,它将女性电影从对历史状况的控诉推向了对当代出路的讨论,这种现实关怀也是这部电影能在当代都市女性观众中引起广泛共鸣的主要原因。
二、盛男:当代都市独立女性的典型意义
100多年前,易卜生笔下的娜拉曾经是父亲、丈夫的玩偶。当意识到 “我必须首先是一个人,与你同样的人” 的时候,娜拉明白,只有离家出走成为一个依靠自己的独立的人,才能最终与丈夫海尔茂站在平等的位置上。女性的独立既是女性解放的目标,也是女性实现个体诉求的手段方式,而女性的独立程度更能反映出女性意识觉醒的程度。盛男这一形象有利于我们认识和理解中国当代女性的独立性问题。
影片一开始呈现为开阔高远的山野环境,盛男独自一人攀爬到大山之上调查山火发生的原因。记者身份、硬朗利索的着装,对山区环境精确的数字化分析,对火灾原因的周密推理,显示出她是一位专业、理性、勇于开拓的职业女性。这样的场景首先将女性从被 “观看” 的位置解放出来——女性不再是逢迎男性目光、展现身体奇观的客体,她获得了独立的主体性位置。有学者认为, “女性获得社会认同的代价是对生理性别的遮蔽,盛男在外貌、行为、语言、性别上呈现出的中性化倾向便是女性进行社会抗争所付出的成本。”[6]287该观点是一种将女性特征本质化的观点,它将女性气质等同于女性生理性别特征。后现代女权主义者激烈批评性别气质问题上的本质主义,否定把两性气质特征作截然两分的做法,推翻了男女对立的二元结构,其认为男女性别气质是非自然化和非稳定化的,两性性别气质是包含一列间色的色谱体系[7]。这就是说,现实中并不存在严格的男女性别气质区分,女性个体以何样的性别气质出现都是其个性的自由体现,不应理解为一种社会异化。盛男所表现出的中性化精神气质,见出她在女性独立的道路上走得更远,摆脱了社会关于女性应阴柔、感性、优雅的性别气质要求,活在了社会性别规训的目光之外。
与同事四毛相比,盛男是独立于社会意识形态的思想清醒者。四毛渴望成功以获得世人的尊重,在晨练的时候也喊着 “成功!成功!” 口号。他对成功的理解是拥有足够多的金钱。曾经的四毛拿过新闻记者的奖项,但为了钱,他出卖了自己的职业操守,被单位炒了鱿鱼。在火灾调查事件中,他篡改盛男调查得出的人为放火这一真相的结论,将纵火者、有钱的大佬李平塑造成救火的英雄。其目的是巴结上这一有钱人,为自己成为有钱人铺路。四毛以获得世人的尊重为人生目标,却是以放弃个人尊严开始的,而四毛渴望成功的心理正是认可了社会关于成功男性的意识形态——它将成功男性定义为有钱。四毛成为了这种意识形态的屈从者和被压迫者。盛男清醒地看到这一点,她说四毛 “比起色盲,渴望成功才是绝症” 。在社会流行观点面前,她比四毛这样的男性更具有思辨性和独立性。她大龄未婚,听到路人嘲讽 “剩女” ,却淡然从容;她不惧报复,公开阻止小偷偷盗。有评论者指出,盛男在得知自己得了卵巢癌之后,把得病原因与不洁性行为联系起来的想法,是盛男在思想上无法摆脱社会观念污名化某些疾病的影响的表现[8]。从医学角度讲,生殖器官的某些癌变的确跟混乱的性行为密切。对此,笔者认为,我们与其把它理解为盛男在思想认识上依然受到社会观念的约束,不如把它理解为职业压力下盛男对自己身体的忽视和回避。
相比刘光明这样耽于幻想的怯弱者,盛男是敢于行动的勇敢者。刘光明初中时就能背诵圆周率小数点后百位数,被誉为神童,但连考3年才考上一个大专。是命运不济,还是资质平平?刘光明终究不满足于这样的人生结果。当通过读书改变命运的希望落空之后,他娶了有钱人的女儿来改变自己的境遇。他对柳絮词的理解 “柳絮因为轻,可以借力使力,活出新人生” ,正是对他这一行动动机的最好解释。他的婚姻包含着他的世俗、取巧和妥协。从这点说,刘光明就不是一个生活的强者,他不能以自身的力量去与狰狞的生活相搏。他高谈 “眼睛所看到的超乎人的想象” “时间的物质性、灵魂的永恒性” ,而无法将追求付诸行动,只能靠空谈来安慰未死的心灵。因此,面对盛男直白的求爱,他只有落荒而逃。内心的怯弱使他担不起盛男的爱,也离不开他拥有的家。盛男则是一位勇敢的行动者,相信 “走得远才能看清世界” 。当发现小镇青年刘光明身上闪烁着理想的光芒时,她敢于向他大胆求爱;当财大气粗的李平想用钱买她的服从、要做她的衣食父母时,她敢于拿希特勒性功能的缺陷作话头回击李平,并撕毁合同;当她发现刘光明是一个委曲求全、贪生怕死的怯弱者时,她以一个强吻告诉刘光明,人不可如此低微、隐忍。盛男没有青年女性通常的那种羞怯,她坦诚人性最基本需求,也不留情地揭露人性的缺陷。她挑战世俗、反抗威压,是当代女性中少见的敢于行动者。这种行动能力是她主体性、主动性的充分体现。
盛男超越了那些为社会定见所束缚男性的人生境界,很大程度实现了自我的解放,活得自我又自由。盛男这样的女性形象是否是导演滕丛丛表达个人主观化意念的一个特例呢?典型的创造过程,本身就是 “杂取种种人,合成一个” ,我们不能因为盛男这一形象在社会上没有普遍性,就否认该形象的现实性。其实,与《送》同时期的女性电影在女性塑造上都体现出相似的精神特征。《柔情史》(2019年杨明明导演)中那个踩着滑板来去自由的写作者小雾,在美好婚姻和自我追求间,选择一个人去开拓自己的世界。《春潮》(2020年杨荔钠导演)中承受原生家庭创伤的新闻记者郭建波虽未婚生女,但却坚持自我,坚持理想,不妥协于生活。这些女性自编自导甚至自演的小众电影,很明显都不是为市场而创作的。她们殊途同归,表达的正是当代女性独特的精神世界和生活体验。电影《送》深入地阐释了当代女性不役于物、不役于世俗、有理想、有追求的独立内涵。盛男形象超越了以往女性电影中以爱情、婚姻、家庭为价值皈依的女性形象,是一个富有探索意义的当代独立女性形象。
三、孤独:现代都市独立女性的生活与心灵困境
盛男的确缺少救治癌症的医疗费用,但这不是因为盛男独立性不够。对于每一个靠勤奋和智慧获取生活保障的普通人来说,超越其经济收入的医疗费用都能令其不堪重负。在大多数情况下,人们都是通过亲友救助和社会救助来摆脱困境,但当盛男面对这样的状况时,她发现居然没有人能帮助她。一方面这种困境是原生家庭造成的。盛男父亲多年前出轨盛男的同学,原生家庭破碎。母亲看到女儿受伤,只问了一句就转而津津乐道她的丰唇针。父亲看见女儿受伤,只在乎女儿是否打赢对手。母亲幼稚,父亲冷淡,盛男得不到来自家庭的温暖。父亲公司经营不善,没有工作的母亲更是依靠父亲的施舍生活,盛男也不能从家庭中获得经济支援。另一方面,在家庭之外,盛男几乎没有朋友,特别是没有女性朋友。这是盛男中性性格使然吗?究其原因,恐怕更多是与多年前父亲出轨同学的事件密切相关。正是在女性朋友的身上,盛男体会了背叛,受到了伤害,致使她宁愿选择与四毛这样世俗的男性做朋友。盛男的孤独是她的现实生活处境所致。
在遭受挫折的环境中,盛男没有成为被生活压弯的小草,自强不息的秉性养成了她在道德上的优越感和桀骜不驯、尖锐刻薄的个性。因为不满自己父亲出轨,她不仅倒掉了送给父亲的酒,还一把火烧了父亲送给情人的礼物。她不待见一辈子依赖男人生活的母亲,对她的电话总是爱接不接,并拒绝给她拍照。四毛拒绝她求爱的要求,她买一套粉色的西服作弄色盲的四毛。相比盛男,这些人的确各有各的人格缺陷。父母毕竟有养育之恩,而四毛也有多年同事的情谊,但盛男毫不留情地怼了他们。她的尖锐刻薄加深了她与亲友之间的隔阂和自己的孤独。当她向四毛借钱时,四毛以她活不长还不完欠款为理由拒绝借钱。是四毛重利轻义吗?盛男是否真心将四毛作为自己的朋友呢?一句 “你比我更擅长与傻逼打交道” 的话语,透露了盛男对四毛态度。盛男与四毛在工作上相互需要,四毛利用盛男的创作才能,盛男利用四毛的钻营技巧,但更重要的是四毛为了追求成功而做人隐忍妥协,尖锐刻薄的盛男才能有这个多年的同事。当盛男嘲笑自己的母亲 “够蠢” 时,四毛一句 “你就孤独终老吧” ,揭示出强势刻薄、缺乏原宥之心的盛男必定孤独的原因。
盛男的独立自强与尖锐刻薄就如同硬币的两面,是相生并存的。它形成的原因既有成长时遭遇的创伤,也有作为一个独立自强女性的自大,这正如影片中梁母所说 “你的自我那么大,那么自大” 。自大源于盛男们的自强与自信,在成长的过程钟,她们依靠自己的努力克服了诸多的困难,相信凭借自身的力量可以活得顶天立地。因此,她们一幅高高在上的样子,看不起怯弱者,看不起与自己价值观相悖的人。如盛男一样,电影《找到你》中的律师李婕也是一个自大的人。李婕在一次官司中将孩子的抚养权判给了出轨的父亲。她觉得,停职在家的全职母亲没有能力养活自己,也就没有权利得到孩子的抚养权。李婕将这位女性当事人的不利处境归于她的不自觉、不奋斗。应该说,这种强者的自大自傲,才是盛男们孤立无援的真正原因,它造成了独立女性与周遭世界的对立。这一点上,电影是深刻的,它刻画出了当代独立女性的精神全貌。
强势、主动、刻薄,也是盛男云山之行不能获得爱情与爱欲满足的主要原因。在两心相悦的爱情中,刘光明没有盛男这样自强不息、毫不妥协的灵魂,他不可能与盛男共赴一场心灵之约。四毛只追求金钱与成功,他的欲望的满足通过与酒店女招待鬼混得以实现,盛男这样个性卓越的女性已经完全不符合他心目中温柔、娇美的女性形象。从这个角度讲,女性的现代内涵与社会的传统女性观之间的差异与矛盾,是盛男孤独处境的深层社会文化原因。这种传统女性观,一方面认为美丽、温柔、内敛、贤淑是女性的理想气质,另一方面认为女性的价值主要体现在家庭这个私人领域,好妻子、好母亲是女性价值之所在。即使女性走入社会,与男性一样挣钱养家,承担家务劳动、养育孩子依然被认为是女性天经地义的事情。这种传统女性观不仅在男性身上广泛存在,在传统女性身上也存在。如电影中梁母认为,盛男这种什么事情都自己做的强势女性在现实中很难找到男朋友。盛男的不婚虽有父母婚姻在心中留下阴影的原因,但更可能是这种女性观下无奈的选择。当在个性保持、自我发展与爱情、婚姻间找不到平衡点时,独立自强的她不愿意因为爱情、婚姻而放弃个人追求与自我实现。因此,她的 “剩女” 特征以及被压抑的爱欲需求都可以看成是受当代社会依然牢固的传统女性观作用的结果;这种刻板的女性观使得当代独立自强、中性化的女性成为被社会有意无意排斥的群体。
在孤立无援的人生处境中,面对死亡威胁的盛男必然会产生了一个自我追问:如何面对未来的生活,是否有足够的勇气独自面对生死?是否要妥协地接受婚姻?在撕毁与李平的合作合同后,盛男曾站在悬崖边上,试图体会寻死之时遭受的的恐惧感。这是盛男对死亡的试探,试探自己能否直面死亡。随后盛男在图书馆与刘光明约会,坦诚她的人生迷茫:对未知的恐惧,对死亡的恐惧,不知道怎么活。盛男的问题起始于病痛和死亡,这不是女性所独有的问题,但是这样的问题对在当代都市选择独立生活的女性尤其具有迫切性。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密切关系着现代女性的 “独立” 内涵和独立道路。那种认为 “导演既没有清晰的阐释盛男所面对的真正问题是什么,也没有诚实地描写女性在日常生活中真实困境” 的观点,恰恰例证了男性对女性问题的隔膜。
四、自我实现:当代都市女性独立之路的探索
云山之行是电影叙事的主线,它以旅途相遇的方式将诸多人事统一到这条主线中,使得电影内涵丰富,但形式不散。有学者指出,云山之行使得《送》具有了公路电影的类型特征,其通过人与人的相遇、人与环境的相遇, “让女性在流动的文化地形中寻找自我” ;同时,远离都市的山林和小城镇等自然空间对于都市女性有身心的治愈意义: “这里没有职场的竞争和生活的压力,女性寻求精神交流、性欲满足、焦虑释放的自由,这样的生命经验借助空间的置换而获得。”[6]289-281该观点阐释了电影空间叙事的意义,将盛男的疾病和困境看成是都市对人压迫的结果,从都市空间与自然空间的对立去阐释云山之行对于盛男的治愈意义。笔者认为,云山之行对盛男来说,并不是一场寻找自我之旅,因为她迷茫的不是失去自我;也不是一场自然治愈身心之旅,因为真正对盛男产生影响的是人事。云山之行其实是一场盛男与周遭世界的和解之旅、一场女性的自我成全之旅。
影片中李平的父亲、书法家李老是引导盛男走出心灵困境的关键人物。李老奋斗一生,功成名就。他人到老年时渴望长寿,就在云山上辟谷以抵抗死亡。当遇到梁美枝,被她的美丽所打动时,他重新投入世俗生活。在生命的最后时光,他开心于梁美枝的陪伴,同时也从容接受了死亡。对于儿子李平,虽一生都在嫌弃其蠢和傻,但他最终还是接受了儿子的平庸粗鄙。为了儿子在他死后能快乐生活,他留下个人传记为儿子装门面。李老的通透,在于他领悟了 “爱欲乃人的生死之门” 意义。人的渴望与欲求是人的动力,也是人的局限,没有人是完人,没有人生可以圆满。李老接纳了儿子的平庸粗鄙,让儿子活在自己的爱欲里;他也接受了死亡,因为人有爱就有生,有欲就有死。
聆听李老对原谅儿子蠢傻的解释是盛男观念转变的开始。她第一次主动为母亲拍照,影片也特写了盛男对母亲久久的注视的场景。云山同行,她看到了母亲的脆弱,也看到了她的挣扎和不易。之后,在刘光明背圆周率的场景中,盛男不忍目睹刘光明的卑微,敲碎了警报器。离别刘光明,一向坚强、不露声色的盛男痛哭起来。这痛哭中有她对刘光明心比天高却身在尘埃的困境的哀痛。对四毛也一样,在拒绝四毛强迫求爱的过程中,盛男最终被四毛渴望成功、渴望他人尊重的强烈心愿所感动。她眼角湿润,不再反抗四毛求爱的举动。盛男在他们身上看到了人的局限,也看到了他们对美好人生的渴求以及在困境中的人性挣扎。盛男体谅了他人的世俗与不完美,也获得了审视自高自大的自我的机会。影片结尾时刻,盛男将四毛扔掉的新闻奖杯重新送还给他,同时在父母注视下进入手术室。虽然造成盛男孤独的社会原因一时无法改变,但盛男完成了对自我问题的思考,从而消除了与身边人的对立立场,达成了与周遭世界和解。
李老扮演了一个启发者的角色,那是否说李老这个拥有社会地位、名为 “李正权” 的男性充当了盛男的拯救者呢?应当说,盛男的困境是物质的,更是精神的。盛男与李老之间是传记作者与传主的关系,是一者付出劳动一者付出金钱的契约关系,李老不曾在物质上帮助她。而要求找到心灵的归宿,即使有导师,最终还是要靠自我的体悟与智慧。李老的劝导可以看成是自表心迹,他一直为自己设计一个如何死的情节,以使自己的人生看起来更有意味。他们之间相互仰仗、相互成全,说不上李老是盛男的拯救者。那么,是否要将李老这种带有中国文化、哲学特征的思考看成是男性文化呢?肯定这样观点的,无疑是从男女两性对立的角度来看问题的。中国传统哲学认为,宇宙万事是相互关联的,多样性生物之间的和谐才是宇宙万物发展根本[9]。李老对儿子的态度、对待死亡的态度恰恰是与中国传统哲学观念相一致的。盛男与李老的相遇,更适合看成是现代都市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相遇。盛男的病痛是现代都市文化对她单向度影响的结果。对文化思想的发展来说,一元意味着封闭,其最终会导致文化思想没有新鲜血液而至于干瘪。正是由于这种相遇,盛男获得了传统文化的智慧,领悟了自己身处困境的原因。从这个角度讲,《送》摒弃了两性对抗的思维模式,采取兼容并收的思想策略,展示了女性思考随女性现代处境的发展而发展的向度。
云山之行也是盛男的一场寻求性满足之旅,不过寻找的结果却出乎意外,她最终以自慰的方式让自己获得性满足。影片以中景的方式表现盛男满足之后的坦然与平静。自我满足场面不仅突破了中国女性电影表现的界限,坦陈了女性欲望的权利,打破了女性欲望表达的禁忌,更有意义的是它表达了女性的困境要依靠自我来解决的观点。四毛,或者说男性在这场性爱中意义的消解,意味着男性之于女性的人生意义被消解了,女性撑起了自己的天。盛男让疯子说 “我爱你” 的片段也可做如是解读。一方面,对于盛男这样独身的人来说,哪怕是一个疯子的话,在她耳边出现也是难能可贵,有聊胜于无;另一方面,疯子的话徒具空洞的形式,而没有情感意义,而盛男恰恰并不介意这句话中是否具有实际意义,因为爱情对她来说并不是人生的唯一意义。影片的最后,盛男登上山顶,敞开胸怀,目见峰峦之上虽然云聚云散,但太阳终究还是透过云层照在了沉静挺拔的苍山之上。如此境界,即是盛男释然心境的写照。所谓释然,是她看清楚了自己的人生遭遇;所谓坚定,是她将继续独自前行。她再也不是那个渴望 “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 的人,她将是一个独立面对人生困境的攀登者,她相信自己的坚持终将守得人生的月朗风清之境。
影片内容的确有些驳杂,情绪表达也有些峻急,但电影成功塑造了一个顽强、果敢的当代独立女性形象,并在经济独立的层面上,建设性地阐释了现代女性思想独立、情感独立的多重独立内涵。它深入到当代独立女性心灵的痛感层面,揭示社会依然顽固的传统女性观对女性生存的影响,并为身陷困境的当代女性展示了一条自我实现、自我救赎的道路。对于中国广大在经济上基本独立并在积极寻求自我价值实现的女性来说,这是一部充满启示性和鼓舞性的女性电影;同时,它也是一部显示了新时代女导演开阔视野和宽广胸襟的电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