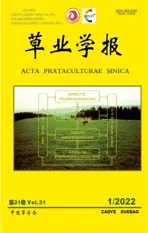氮添加对内蒙古不同草原生物量及土壤碳氮变化特征的影响
2022-02-10韩小雨郭宁李冬冬谢明阳焦峰
韩小雨,郭宁,李冬冬,谢明阳,焦峰,*
(1.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水土保持研究所,陕西 咸阳 712100;2.中国科学院水利部水土保持研究所,陕西 咸阳 712100;3.中国电建集团河南省电力勘测设计院有限公司,河南 郑州 450007)
草地生态系统作为陆地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重要的生态服务价值[1],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过程中扮演着关键的角色,近年来,全球气候变化以及日益频繁的人类活动诱导大量氮沉降增加,使各类草地发生了不同程度的退化,对生态系统结构和稳定性产生了深刻影响,我国已成为世界三大氮沉降集中区之一[2],因此亟待通过科学的草地管理手段来恢复和改进退化的草地。草地施肥通过改善土壤肥力进而增加草地生态系统生产力,已成为恢复和保护草地资源、提高群落生产力的重要管理措施。氮肥是植物生长与发育所必需的营养元素,也是草地生产力的主要限制因素之一,因此,研究草地生态系统对氮添加的响应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植物生物量是衡量草地生态系统生产力的重要指标,众多研究表明氮素的增加能够刺激植物生长,提高生态系统生产力[3—6],但以往的研究多集中于对地上植被的影响,对于地下生物量来说,由于研究方法的差异以及植被地下部分的复杂性和不可见性,目前对其研究较少,Majdi等[7]研究发现,氮添加会使植物地下生物量增加;Nadelhoffer[8]却认为养分添加使地下生物量降低;也有研究发现地下生物量对氮添加没有响应[9—10],研究结果存在较大差异,尚没有得出普遍规律,氮添加量以及生态系统特性的不同都可能是造成其对氮添加响应出现差异的原因。同时,刘永万等[11]研究得出施氮处理促进了植物对土壤养分的吸收,从而导致返青期土壤有机碳、全氮和有效氮含量明显下降,这意味着植物地上地下生物量又受到土壤养分含量的影响[12],土壤C、N是植物体生命活动主要的养分来源[13],植物吸收并以凋落物的形式将其归还土壤,形成生态系统的能量流动和养分循环过程,极大地影响着生态系统的过程和性质,研究植物生物量与土壤碳氮含量对氮添加的响应,有助于深入理解全球氮沉降背景下生态系统碳氮循环过程,为维护生态系统养分平衡提供科学依据。
全球氮添加的实验表明施氮可对植物的生长、物种结构及土壤肥力等产生一系列影响,且不同的草地生态系统对施氮的生态学响应存在明显的差异[14—18]。草甸草原、典型草原、荒漠草原是内蒙古草原的主要类型,在调节气候、涵养水源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是研究全球气候变化背景下土壤碳氮特征的天然实验草地。本研究通过对内蒙古3种草原试验区域草地植物群落进行施氮控制试验,拟解决以下3个科学问题:1)不同草原类型生物量及土壤碳氮含量对氮添加有何响应?2)氮添加如何影响3种类型草地群落生物量、根冠比以及碳氮含量?是否因草地气候条件不同而异?3)氮添加对草地生态系统生物量及碳氮含量影响机制,可为我国草原可持续管理提供重要的基础资料。
1 材料与方法
1.1 研究区概况
研究区位于我国北方温带草原内蒙古自治区境内(37°24′24″—53°20′02″N,97°10′18″—126°03′56″E),地势相对较高,地域辽阔,沿东北向西南方向年均温呈现递增趋势,水热梯度和土壤类型差异使内蒙古草原类型依次形成草甸草原、典型草原和荒漠草原(图1)。本试验沿东北—西南方向分别设置3个研究站点,其中草甸草原选择鄂温克自治旗,试验区内主要优势种为羊草(Leymus chinensis)、茵陈蒿(Artemisia capillaris)、冰草(Agropyron cristatum);典型草原选择锡林浩特,试验区内主要优势种为克氏针茅(Stipa krylovii)、灰绿藜(Chenopodium glaucum)、刺藜(Chenopodium aristatum);荒漠草原选择杭锦旗,试验区内主要优势种为短花针茅(Stip breviflora)、猪毛菜(Salsola collina)、狗尾草(Setaria viridis)(表1)。

表1 研究区基本概况Table 1 Basic over view of the study area

图1 研究区概况Fig.1 Study area
1.2 实验设计
本试验于2017年5月进行实地考察布设,在3个地区选取质地匀质且平坦的自然草地作为试验样地,进行人工围封以排除人为和牲畜对样地的干扰。综合前人的研究成果[19—20],并采用完全随机区组设计原则,设置7种氮添加梯度,分别为CK(0 g N·m—2·a—1)、N1(5 g N·m—2·a—1)、N2(10 g N·m—2·a—1)、N3(15 g N·m—2·a—1)、N4(20 g N·m—2·a—1)、N5(25 g N·m—2·a—1)、N6(30 g N·m—2·a—1),且每个施肥处理设置3个重复,因此1个研究站点布设21个小样方,共计63个样方,每个小样方的面积是2 m×2 m。试验所用肥料为纯度46%的尿素(CH4N2O),用电子天平称量不同处理下的氮肥用量并装入自封袋,于每年5月中旬前后进行氮肥处理,施肥时将肥料和水放入25 L的喷壶中充分搅拌,然后均匀地喷洒在相应的样方内。于2018年7月中旬植物生长高峰期沿着样带方向依次进行所需样品采集。
1.3 生物量测定
地上生物量采集使用传统收获法,首先设置(0.75 m×0.75 m)小样方调查框,将框内所有植物从基部用剪刀剪下,带回实验室经105℃杀青处理后(大约30 min),置于65℃烘箱中加热烘干至恒重称重即得到最佳的烘干质量。地下生物量采集通过内径7 cm的根钻随机采取2个点获取根系样品,将样品用清水充分浸泡后过1 mm筛网反复冲洗并晾干,同样经105℃杀青处理后于65℃烘箱中烘干至恒重称重。

1.4 土壤养分指标测定
在每个小样方里选取两个样点按0~10 cm与10~30 cm分层钻取土样,经四分法取舍混合后装入自封袋带回实验室,清除土壤样品中杂物后在阴凉处自然风干并进行研磨过1 mm筛处理,土壤全氮含量使用流动分析仪分析测定,土壤中有机碳采用重铬酸钾容量外加热法测定,测定方法可参照《土壤农化分析》[21]。
1.5 气象数据采集
从中国气象数据网(http://data.cma.cn/)获取内蒙古3种不同草原类型区各个站点1998—2018年的气象资料,根据研究站点的经纬度采用Kriging插值法提取各样地1998—2018年的降水与气温数据并计算均值。
1.6 数据分析
采用Excel 2010进行数据整理,并对整理后的数据进行正态分布检验(S-W检验),结果符合正态分布后,使用单因素方差分析(One-way ANOVA)对不同氮添加水平、不同草原类型植物生物量及土壤C、N含量分析比较,各指标均在LSD=0.05的水平下检测差异显著性。最后采用Pearson相关系数计算土壤碳氮组分及其比值、水热因子与生物量之间的相关性。所用软件为SPSS 17.0和Origin 9.0。
2 结果与分析
2.1 氮添加对不同草原类型区生物量的影响
与对照相比,各种施肥处理对草甸草原和荒漠草原的地上生物量都有促进作用,对照处理的地上生物量分别为246.73、232.41 g·m—2,表现为在N1、N2处理下无显著增加(P>0.05),其余各处理(N3、N4、N5、N6)均有显著增加(P<0.05),其中草甸草原分别增加了144.72、177.53、248.93和195.28 g·m—2,荒漠草原分别增加了163.31、167.66、160.53、142.39 g·m—2,但这4个处理之间没有显著差异(P>0.05)。而在典型草原实验区,各个施肥处理对群落地上生物量均没有显著影响(P>0.05)。但总体而言,氮添加对内蒙古温带草原的地上生物量有一定的促进作用,平均增加了35.92%(图2)。相较于地上生物量的显著影响,地下生物量对氮添加的响应则较小,平均增加了29.41%,3种草原类型区对氮添加的响应均不显著(P>0.05),但也存在差异,典型草原和荒漠草原地下生物量在氮添加下都有一定增加,而在草甸草原试验区,各个处理均使之下降。由表2可知,不同氮添加下研究区内3个不同草原类型区的平均地上生物量分别为388.14,122.93,361.91 g·m—2,平均地下生物量分别为2994.13,2545.79,1529.95 g·m—2,地下生物量均大于地上生物量,且草地群落总生物量和地下生物量的大小顺序均为草甸草原>典型草原>荒漠草原,而地上生物量则表现为草甸草原>荒漠草原>典型草原。

图2 3种草原类型区不同氮处理的植物地上、地下生物量及总生物量Fig.2 Plant aboveground and belowground biomass and total biomass with different nitrogen treatments in thr ee gr assland types(Mean±SE)

表2 不同草原类型区氮添加下地上生物量、地下生物量、根冠比和总生物量的方差分析结果Table 2 ANOVA results of nitrogen addition aboveground biomass,under ground biomass,root-shoot r atio and total biomass in different gr assland types
由图3可以看出,氮添加对3种草原类型的生物量分配也产生了一定影响,6种氮处理下草甸草原试验区根冠比均显著低于对照(P<0.05);在典型草原试验区,各个处理下根冠比都有增加,且在N3处理下显著增加(P<0.05),达到最大值33.68,与对照相比增加了168%,整体呈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而在荒漠草原试验区,除N2,N5处理有所减少外,其余则有轻微增加,但均未达到显著水平(P>0.05)。3种草原类型试验区根冠比大小顺序为:典型草原>草甸草原>荒漠草原。

图3 3种草原类型区不同氮处理的植物根冠比Fig.3 Root-shoot ratio of different nitrogen treatments in three grassland types(Mean±SE)
2.2 氮添加对不同草原类型区土壤C、N含量及C/N的影响
图4结果表明,施氮对荒漠草原和草甸草原0~10 cm土壤C含量影响均不显著(P>0.05),对10~30 cm土壤C含量部分影响显著(P<0.05)。但与对照相比,N4处理显著提高了典型草原的土壤C含量(P<0.05),而其他氮添加处理与对照相比均无显著变化(P>0.05)。在草甸草原试验区,0~10 cm和10~30 cm土层的土壤N含量在氮添加下没有显著变化(P>0.05),而典型草原与对照相比分别平均减少了12.63%、5.70%,且表层(0~10 cm)土壤N含量在N2处理下显著低于对照(P<0.05),荒漠草原在一定程度上有所增加,两个土层分别平均增加了12.60%、3.99%,其中在N3处理下均显著高于对照(P<0.05),分别增加了18.52%、12.73%。对于土壤C/N而言,草甸草原在各个施氮处理下都没有达到显著水平(P>0.05),而在典型草原实验区均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变化趋势,与对照相比两个土层分别平均增加了31.06%、18.30%,荒漠草原土壤C/N均小于对照。总体上,氮添加下3种类型草原试验区之间土壤C、N含量均有显著差异(P<0.05)(表3),表现为荒漠草原低于草甸草原和典型草原,且0~10 cm土层土壤C、N含量均大于10~30 cm。

表3 不同草原类型区氮添加处理下土壤C、N以及C/N的方差分析Table 3 Variance analysis of nitrogen-added soil C,N and C/N in different grassland types

图4 3种草原类型区不同氮处理的土壤C、N含量及C/NFig.4 Soil C,N content and C/N of different nitr ogen treatments in three grassland types(Mean±SE)
2.3 不同氮处理下植物生物量与土壤碳氮含量及水热因子的相关性分析
地上生物量与年均降水量、土壤C/N呈显著正相关关系(P<0.01)。地下生物量和总生物量相关性一致,且土壤C、N含量、年均降水量以及根冠比对二者均产生显著正效应(P<0.01),而土壤C/N与年均温则对二者呈显著负效应(P<0.01)。另外,根冠比与0~10 cm、10~30 cm土层土壤N含量、土壤C/N、年均降水均显著相关(P<0.01)。土壤C、N含量均与年均降水量呈正相关,与年均温呈显著负相关(P<0.01),且表层(0~10 cm)土壤C、N含量与之相关性均大于深层(10~30 cm)。草原类型的不同也会使土壤C、N含量及地下生物量存在显著差异(P<0.01)(表4~5)。

表4 氮添加下不同土层土壤C、N化学计量特征与生物量及水热因子的相关性分析Table 4 Correlation analysis of soil C,N stoichiometric characteristics with biomass and hydrothermal factors under nitrogen addition
3 讨论
3.1 氮添加下不同草原类型区地上、地下生物量、总生物量的特征分析
本研究中,不同浓度氮添加对内蒙古总生物量有一定的促进作用,尽管存在空间差异,但总生物量平均增加了29.66%,说明内蒙古草地生态系统受N限制,并且一定程度上施氮肥能够提高其生产力,这与以往的很多研究结果相同[22—23]。对于草地生态系统,水热因子是影响其生产力的主要因素[24],其中水分是影响草地生物量的关键因素[25—26]。Lee等[27]认为,草地生态系统对N添加的响应与降水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即水分越充足,响应越大,地上生物量增加越多,本研究与其结果一致。本研究发现草甸草原和荒漠草原试验区地上生物量对N添加的响应显著大于典型草原(P<0.05),这可能与降水量有关,本试验典型草原研究区域锡林浩特的多年平均降水量低于草甸草原和荒漠草原试验区,较少的降水量不易使肥效发挥出来,对N添加的响应较小,且表现出草甸草原最大,典型草原最小的分布特征。另外,除典型草原外,氮肥增加使草甸草原和荒漠草原的地上生物量呈“先上升后下降”的单峰型变化趋势,这意味着氮添加下草地生态系统对N的需求有一定的阈值,超过这一阈值,会使生物量降低,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可能在于随着氮素浓度的增加土壤逐渐酸化,影响养分平衡,进而对植被生长有一定的抑制作用[5],马玉寿等[28]通过对青藏高原小嵩草(Kobresia pygmaea)草甸氮肥添加试验表明,施肥量在30 g N·m—2·a—1较为合理,Bai等[19]在内蒙古锡林郭勒典型草原进行4年长期氮添加试验得出其氮饱和阈值为10.5 g N·m—2·a—1,本研究结果与此存在差异。本研究显示草甸草原、荒漠草原试验区N3、N4、N5、N6处理与对照相比地上生物量均有显著增加,但其相互之间无显著差异,因此可初步判断内蒙古草甸草原、荒漠草原草地植物生长在N3即15 g N·m—2·a—1处理下可能已经接近饱和状态,典型草原地上生物量对氮添加没有响应,这可能与其近年来干旱灾害频发[29]导致的年均降水量较少有很大关系。

表5 氮添加下生物量与水热因子的相关性分析结果Table 5 Results of correlation analysis of nitrogen added biomass and hydrothermal factor
祁瑜等[30]和Bai等[31]研究得出氮添加对地下生物量没有显著影响,本研究也得出3种草原类型区地下生物量均对施氮没有显著效应(P>0.05),但也存在一定差异,造成差异的原因可能是:N可能是影响草地植被生长的最主要因子,而根系生物量对氮添加的响应取决于N限制减缓或消失后是否受其他生态因子的影响,例如,温度、水分等环境因子[32],气候条件较好的草甸草原氮添加下植物地上部分发育迅速,地下部分需供应大量的能量以满足其生长需求,故地下生物量有所减少,而典型草原和荒漠草原年均降水量较少,对植物地上植被的生长有所限制,根系部分储存较多能量,形成了地下生物量相对增加的分配格局。此外,相较地上生物量,地下生物量表现出的变化趋势更具规律性,呈由西南向东北递增的线性关系,这很大程度上与年均温相关[33]。
根冠比的动态变化与地上、地下生物量密切相关,可反映植物对资源的分布和转移情况。很多研究发现,施氮会显著降低植物根冠比[34—36],原因可能是养分添加减缓了植物生长的N限制,增加了土壤中有效氮的含量,植物竞争格局发生变化,由地下部分的养分竞争转化为地上部分的光竞争,并将更多的能量分配给地上组织,来增加群落生产力。本研究得出氮添加显著降低了草甸草原植物根冠比(P<0.05),对荒漠草原没有显著影响,而典型草原根冠比表现出与之不同的规律,在N3处理下显著增加(P<0.05),且先上升后下降,可能原因有:1)北方天然草地的根冠比与年均降水量呈负相关关系[37],故年均降水量可能是引起3种草原类型对氮添加响应规律出现差异的原因。2)随着氮添加浓度增加根系吸收能力也相应提高,进而对地下生物量产生正效应,故根冠比增加明显,而在N3添加达到最大值可能也与其接近“N饱和”点有关。3)施氮处理对根冠比变化规律存在差异的原因是复杂的,很大程度上受植物生长的微环境以及不同物种氮利用效率的影响[38]。
3.2 氮添加对不同草原类型区土壤C、N及C/N的影响
生态系统碳循环与氮素存在耦合关系,二者密切相关[39],碳氮耦合在土壤养分循环以及植物生长、分配过程中具有重要的作用。土壤有机碳含量主要取决于植物凋落物对土壤的碳输入及分解矿化作用的动态平衡,氮添加下土壤有机碳含量存在极大的不确定性[40],本研究结果显示氮添加下典型草原0~10 cm与10~30 cm土层土壤有机碳含量在N4处理下显著增加(P<0.05),而土壤表层(0~10 cm)全氮含量在N2处理下显著减少(P<0.05),总体上表现为土壤C/N增加,与郑海霞等[41]在内蒙古锡林郭勒盟典型草原连续5年施用氮肥对土壤C、N含量无显著影响的结论不一致,施肥时间的长短可能是造成结果存在偏差的原因,也可能是由于添加的氮素被土壤微生物矿化对土壤C增加产生了影响。在荒漠草原试验区,施氮对土壤有机碳含量影响很小,但是0~10 cm和10~30 cm土层土壤全氮含量与对照相比分别平均增加了12.60%和3.99%,且在N3处理下增加最显著(P<0.05),首先可能是由于随着氮肥含量的增加,植物因生理过程对水分需求增大,而荒漠草原年均温明显大于典型草原和草甸草原,土壤水分蒸发快,减缓了枯落物分解速率,进而减弱了养分循环速率,氮素聚集多,且淋溶损失小,造成了土壤中各种形态氮含量的增加[18],其次本研究与很多研究均发现土壤C、N含量与年均温显著负相关(P<0.01),与年均降水量存在正相关性[42—43](P<0.01),故这可能与荒漠化草原自身特有的生境条件有很大关系,其三是本研究3.1中初步判定N3处理下荒漠草原可能接近N饱和状态,进一步的N输入可能会对土壤微生物构成毒害作用,进而增加N素流失的风险[44]。氮添加对草甸草原土壤C、N含量以及土壤C/N均没有显著影响(P>0.05),原因可能在于水热条件较好的草甸草原碳氮循环也较为活跃,氮添加增加了土壤中碳氮含量,但也同时刺激了微生物活性,促进植物生长,导致土壤有机碳和无机氮以及其固有氮素输出的增加,二者可能相互抵消,再加上草甸草原土壤有效氮含量本身较高故其对氮素增加响应不明显。土壤C/N是衡量碳氮元素平衡的重要指标,对碳氮循环有一定的影响。本研究显示氮添加下3种草原类型的土壤C/N范围为8.36~16.13,平均值为11.77,基本处于中国土壤C/N均值(10~12)范围内[45],这意味着尽管氮添加对土壤有机碳、全氮含量产生一定影响,但其作为结构性成分存在相对稳定的比值。
3.3 施氮处理下植物生物量与土壤碳氮化学计量特征及水热因子之间的相关性分析
氮沉降增加背景下植被和土壤作为草地生态系统重要组成部分极大地影响着生态系统的过程和性质[46],土壤养分是植物生长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二者相互反馈,相互影响,且随空间尺度的不同而存在差异。刘永万等[11]研究得出不同氮添加下土壤有效氮含量与植物地上、地下及总生物量之间呈现出显著的相关关系,显著改变了植物生产力。戴诚等[47]和杨秀静等[48]研究也发现地下生物量与土壤全氮和有机碳含量显著正相关,本研究结果与其类似,此外,本研究中施氮条件下随着土层深度的增加地下生物量与土壤C、N含量以及土壤C/N的相关性呈现逐渐下降趋势,由此可见土壤表层具有较强的养分供应能力,原因可能在于氮添加提高了草地植物生产力,进而使凋落物增加,而凋落物是土壤C、N的重要来源,故表层土壤C、N含量相对大于深层土壤,其次植物根系在氮添加下浅层化,加之水热条件在土壤表层较下层适宜,因而形成了养分表层积聚现象。不同草原类型区在氮添加条件下由于水热因子的差异造成植物生物量及土壤碳氮含量存在差异,养分添加与水分、温度等环境因子结合参与各种新陈代谢过程,影响植物的生长发育,成为了生物体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一方面,温度以及氮肥供应可以通过改变酶活性影响植物对水分和矿质的吸收,进一步影响植物体细胞功能的发挥从而对其代谢活动产生影响。另一方面,由于氮素进入土壤后只有溶于土壤水溶液并转化为离子态才能被植物吸收利用,随着氮素添加的增多土壤含水率相应减少,适当的水分补给可以通过提高酶活性对植物生长产生一系列正效应[18]。这表明氮添加下水热因子以及土壤养分对植物生长具有重要作用,但由于土壤碳氮含量在动态转化过程的复杂性,以及植被生物量还受凋落物质量、土壤酶活性、微生物活性以及其他土壤理化性质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因此有关施氮对内蒙古温带草原土壤养分以及生物量的影响机制还需要进一步研究。
4 结论
短期氮添加对内蒙古温带草地生态系统土壤碳氮特征和植物生物量及其分配格局产生了一定影响。施氮对草甸草原和荒漠草原植物地上部分生长有显著促进作用,且初步断定在N3(15 g N·m—2·a—1)添加时接近饱和阈值,对3种草原类型的地下生物量的影响均不显著,而对根冠比表现为草甸草原显著下降、典型草原增加的趋势,这种异质性主要受水热、土壤养分等因子影响。另外,不同浓度氮添加对相对湿润的草甸草原土壤C、N含量没有显著影响,而对较为干旱的典型草原和荒漠草原存在显著影响,这说明氮添加对更缺N的生态系统表现更明显。综上所述,施氮对不同草地生态系统生物量及土壤碳氮含量存在积极作用,但由于土壤碳氮循环的复杂性以及植物生物量还受多方因素的干扰,还需结合植物生理学以及生态学等多方面的研究进一步分析,以准确揭示其影响机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