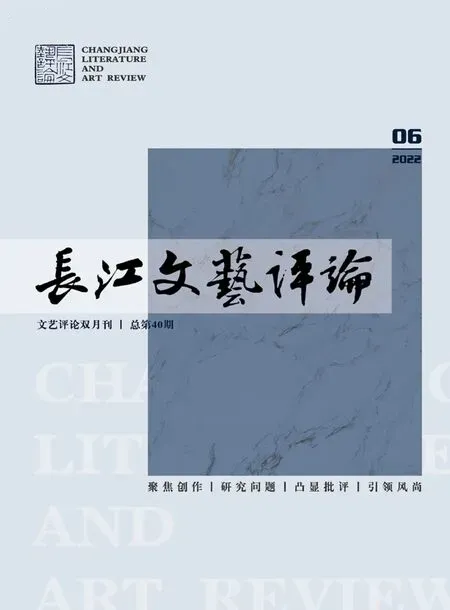记忆图绘与经验悬浮
——《北流》的几个侧面
2022-02-09康志刚
◆康志刚
一、记忆/经验与反叙事
林白的《北流》问世后,评论界对她这部历时9年创作的小说给予了高度的评价。李敬泽评之:“《北流》几乎可以看作是林白所有著作。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是经历了沧海桑田。这个沧海桑田不仅仅是作为故事,也不仅仅是作为叙事,而是作为一个人类的经验。……在回忆中保证生命的饱满”。[1]在众多阅读中,对记忆/经验的解读,成为该小说重要的阅读进入方式,也是对这部小说的总体性把握的关键。正因为如此,《北流》中“那种突然间生活随时要折断的一种时刻”(陈晓明语)完全打破了传统的封闭式线性结构的叙事方式,以一种回忆/经验的碎片化呈现,展开了一个纯粹的经验世界,一个处处“此路不通,请随意观赏”的记忆图景。这个游弋于上世纪70年代——80年代——当下的碎片化讲述,构成一个记忆弥散的时空。在这样的时空之中,人本身的经验变得踟蹰难行、举棋不定。正如小说中罗世饶认为其十五年的坎坷经历可以写成一本书——在李跃豆这里被认为是一种外行的想法——纷繁的记忆恰恰是闭环式叙事的最大难题。
齐泽克对拉康“我们为什么要讲故事”这句质问给出的解答是:叙述之所以会出现,其目的就是在时间顺序中重新安排冲突的条件,从而消除根本矛盾冲突,因此,叙述的形式也正证实了一些被压制的矛盾冲突,以叙述解决问题,人们付出的代价,则是时间环上的预期理由——叙述悄悄地把它意在再生产出的东西预设为业已存在之物。[2]也就是说,“讲故事”本身的目的在于构建先在预设的意义,要做到这一点,必须一定程度上有意遮蔽内在的实质性真相和冲突。因此,《北流》选择用注、疏、笺、异辞的结构方式,以纷繁的记忆图像和语言力图来呈现其原始的面目,就是一个“反叙事、反遮蔽”的写作策略。
以艺术原始素材的个人经验生活,来定位主体的空间/时间位置,是隐蔽在林白写作中的意图,借用杰姆逊“认知图绘”的美学思维,我们可以把林白所有的作品看作是一个寻求相对于社会空间、时间、家族进行定位的超文本。无论是早期的《一个人的战争》《致命的飞翔》中的“个人的感性与智性、记忆与想象、心灵与身体的飞翔与跳跃”[3],还是后来的《妇女闲聊录》《北去来辞》里女性身体与灵魂在宏大的社会空间漂泊的感知,以及《北流》里纯粹、广袤的记忆图景中的经验弥散,都暗合着杰姆逊对个体经验的描述,即“那些封闭的主观世界与它们(社会的巨大空间和逾半个世纪的时间跨度——笔者注)之间的相互作用,两者同时存在,但是不相关联,就像船只在夜间驶过,仿佛形成了航线和水面永不相交的离心运动”。[4]
《北流》无疑是一个庞杂的“图绘”世界,从生活在时间意象丛林的南方植物,到各个城市空间转换,再到各个人物的历史/当下叙说,这些“互不相干的素材”“既保持原貌,又能舒服地进入一本书”。[5]这样的“图绘”世界,是一次林白私人经验对历史的敞开,也是一次在历史时空里重新定位的努力。
二、时间流动中的经验图绘
林白在《北流》中,时刻提示着时间的在场与缺席。《序篇》里植物的生长,仿佛都是在时间的意象中爆发生命的狂热。“无尽的植物从时间中涌来/你自灰烬睁开双眼”“无穷无尽的植物/在时间中喃喃有声”“龙眼出现在我两岁/它在手心满满一握”“凤凰木,我逐年失去了你们”……在这一部纵跨60年的时间描述的小说里,时间有时候被刻意忘却,有时候又变得无比尖锐;有时候成为提示人物命运的承载物,有时候又被切割成众多的不可言说的片段。每一个个体都以不同的方式经验着与时间的关系。在李跃豆这里,80年代送给别人诗集,却已经完全忘记了那人是谁;关于弟弟米豆,也只是部分片段可记取,根本无法连续成成长的记忆;往时的衣柜,也已“近三十年没注意它了,看而不见”。这样的时间,都隐匿在李跃豆青春勃发的生命时段,在这个时段,她厌倦自己的故乡,身体里蓬勃着逃离的冲动,那种“看而不见”的不是生活的林林总总,恰恰是对时间的本能背叛。然而,作为生命与记忆的策源地,更早期的北流生活,反而让跃豆的记忆异常活跃。六七十年代童年和青春期的政治生活牢牢占据着记忆空间,六感大队的下放生活“六感日记早就销毁了,但我记得它们的样子”,为大队写通讯稿,具有时代特色的各种红歌、戏剧、口号,还有诸多人物命运,都鲜活地扑面而来。记忆的断裂隐喻着对时间的个体感知,也隐喻着对时代的或者疏离或者笃定的态度。
相比较而言,作为上一代人的梁远照却“总能审时度势,追着时代的脚步”,“翱翔在这些人之上”。从50年代读医学培训班“终至主治医师职称,官至副院长……”,年轻时丈夫去世再嫁萧伟杰,苦苦支撑原生家庭七口人,甚至以65岁的年龄只身闯荡广东,带着电饭煲拼杀天下,直至八十多岁的高龄,依然保持着和时代同样的步调。梁远照的个体时间感知,永远都是当下性的,充满着对新事物的好奇并一往直前。她对年轻时的回忆,也仅仅是浮光掠影似的事件性追溯:“我年轻时径几活跃的,我还演过话剧呢,工会组织的……”即便是与其同时代的“三个老阿姨”,在讲述生活的过往,也是事件性回溯,仿佛那是与己并不贴身的时间流,哪怕时间在她们生命里铭刻了重大的创伤。对时间的笃定带着这一代人的气定神闲,淡然面对一切命运的安排,一如“曾经光芒四射的女人”姚琼,那个从时代光辉的舞台走下来,被时间淘洗成半身不遂的疯妇。
表兄罗世饶一生中的时间仿佛都压缩在十五年的流亡生活中。这段遍布大半个中国的流亡生活时间,事实上也正压缩着中国人最惊心动魄的历史时刻。小说中提到的安东尼奥尼220分钟的长纪录片,仿佛将1972年的中国凝固成为一个扁平化的镜头,刻意地共时化了一段历史,也表征着他者对中国时间的观看方式。这一段时间重大的政治事件频频发生。然而,这样的时间观照并不属于罗世饶,罗世饶的时间是纯粹历时性的,是网格状地遍布于大半个中国,他以“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的感知方式,在各种召唤和心灵的冲杀里和十五年的时间搏斗,直到最后听到一个特殊时代结束的消息,“欢呼中想起了久违的他的线性数学”,新的时代的生活,又让他“多年闻鸡起舞自学的高等数学也就此拉倒了”。在他的时间感知中,大江大河、与赖胜雄的时空交错、二十一个生命中擦碰而过的女人等等,将其记忆不断刷新,从而频繁变换着生活的主题,从爱情转而到家族再转而“三十多年的厄运,永不停歇的奋斗”,最终定焦在“两性经验”这一永恒的主题上。他和李跃豆一样,记忆的高光始终停留在某一段时间上,其余的都变得无足轻重,“一日,管人事的找到他……终究还是一惊,居然就六十岁了,再无念头,一生落定”。罗世饶的流亡生活将其时间的感知也相应地悬浮于属于他个人的历史时空里,与李跃豆始终无法确定自己的经验身份不同,他最终把时间经验锚定在“两性关系”的记忆上,以此给自己滑动的生命主题一个交代,当然,这依然是一个此生意难平的欠然。
此外,陈地理的远古与当下身体互嵌式时空幻想、“时间支流”的臆念,及他人对其失踪的“平行空间”的推测;庞天新那神秘的,代表无限的“∞”;那“往时入口”,如同时光机的米缸,以及当下“对年轻人而言,80年代是古时候,很古”的时间感知,泽红、泽鲜、赖最锋的生活经历等等,都以或对时间的抗争,或对时间的笃定、怀疑经历着个人的存在体验。然而,无论小说中的哪一个人物的时间感知,在《北流》所展示的繁杂惊人的“时间图绘”中,都混融为一个属于林白的时间经验,一团无法楔入历经六十年变迁的世界图景的漂浮物。
三、繁华都市/边城的经验错位
《北流》正文的开篇,即是在香港这个“异地”的城市风光中展开。这座拥有全球化气质的国际都市,在各种后现代视觉冲击下,与各种仿古、戏拟的城市标志构成与整部小说恍若隔世的气象。整个“香港”叙事里,流淌着一种艰涩的、难以捏揉在一起的繁华都市/边城记忆的反差观照,那些与北流相比似是而非的南方植物,当代大学图书馆里作家画像与童年记忆中的时代标志性画像,各种都市意象与童年所经历的文化事件等等,形成为小说中所说的“重叠。参照性。一种连绵。”正是因为身处一个陌生的后现代化城市,所以叙事者总是有意无意把视觉拉回到自己的记忆和想象之中,仿佛要在一个偌大的陌生空间里找到自己的想象的位置。就如同阿兰·德波顿在其《旅行的艺术》中用梵高画中的柏树对眼前所看到的柏树进行编码重构,生成的多种意象和感觉碎片。[6]
杰姆逊在其《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中写道:“林奇告诉我们,异化的城市首先是一个人们无法(在他们头脑中)图绘的空间,他们既无法描述他们自己的位置,也无法描绘他们身处的城市总体。……而传统城市的‘去异化’需要重新夺回方位感,以及构建或者重建一个能被记忆保留的连续整体,个人主体能够沿着移动的、可选择的轨迹进行图绘与再图绘。”[7]城市空间的异化导致人的经验无枝可依,不管是香港这样的国际城市,还是南宁这样的自治区首府,甚至北流这样的七线小城,在《北流》的描述中,除了80年代及之前的记忆/经验有着清晰而生动的面孔外,一切都已经物是人非。“为何街名没有绵延居住的气息,大而无当且与其他城市多有重复……全市最大的书店和最活跃的地摊夜市混在一起,形同水火……”“县城自90年代起就面目全非,分不清东南西北远近。”这样的城市地理构造,已经无法用个人的经验图式来进行统合。作家返乡的“六日半”,更近乎寻找业已不存在的城镇和乡村过往,而这一番寻找,几乎串接了中国几大城市空间的想象。“金洲路,前所未闻的路名,它到底是在80年代的哪一片?”那一件承载着武汉城市记忆,又曾穿越南宁街道的风衣,早已成为一个历史的标记,只能在记忆中存活。“时代前行,样样颠倒。颠倒着风驰电掣。”此外,在叙事者的经验图绘中,不止一次地通过描述机场航空站这种串接各个城市的枢纽,来放大自己的文学性地理版图想象:“阑尾,这是我献给你的昵称/正如广西的七线小城/你是祖国版图的盲肠”。
赖胜雄、罗世饶在革命串联中所迸发出来的火热激情表征着对各个城市空间经验嵌入的欲望。与之相比,李跃豆的记忆追踪所传达出来的城市经验,使空间成为一种无法读解的混乱景象,连带着空间串接的路径也变得支离破碎:“有关路,眼下的、‘作家返乡的’、21世纪的路面让我意外,再也没有比这更不适合踩车的路了。……而1975年的玉梧公路,……整个路面都是我们,从右边横到左边……”这样的历史经验变迁,当然也切合列斐伏尔历史—社会—空间的三元辩证法。
通过既定的记忆/经验来审视“颠倒着的风驰电掣”,注定要付出经验错位的代价,也注定是失败的。这种失败导致的结果,是叙事者经验的本能逃离和躲藏:“火车一直向前,轻微地摇晃……在外游荡几十年,她从未找到自己的避难所,故乡不是异乡也不是,……若要找一只避难所,火车应该是首选……她喜欢火车上的陌生人……只要下了车,一切都删除了。”“她奇怪地不愿意坐飞机,中途的车站是无比熟悉的长沙株洲衡阳冷水滩,她无数次路过的。她简直觉得回到了家,熟悉的地名使她安稳。”
《北流》中反复出现的,对当下都市冗长而沉闷的描写与边城过去鲜活的记忆反差,以及城市异化空间设计对旧时记忆的入侵,都流露出林白对城市空间去历史化、去理想化的叙事焦虑。
四、词语流变中的经验图绘
《北流》当然是一部语词的小说。全书不仅精心地运用着原生态的地方方言,也保持着一种高度的语词敏感。张莉认为林白是“一个锻造词语的人”,[8]梁鸿鹰说“从来没有人像林白这么大规模地实验,方言化是一个方面,方言、辞典、注、疏、书信、自序、独白,她把多种元素大规模地集成引进到小说的文本当中,这个确实令我们叹为观止”。[9]这样的评价并不为过。《北流》从结构上以注、疏、散章、后章、异辞、时笺等布局,到方言化的叙事,再到各种语言冲突的描写,再一次彰显林白写作的先锋气质,当然,这样的实验贯注着理性和深沉的人文思想。
《北流》首先是一次大规模通过语词的运用来唤回记忆的文本。那些虚构的《李跃豆词典》,南方植物的符号化的诗志,以及特殊年代的红色语汇、80年代的文化标志等等,不仅以散片化方式时刻发出对各个时代的记忆召唤,“你的源泉来自梭罗,万重山送你一路前行”,“这里鸡蛋花树、凤凰木……它们发出了声调有别的、来自时间深处的方言”,甚至延伸到更远的历史空间,比如中学图书馆里的图书所标志的知识和文学记忆、西南联大的知识分子等等。具体的意象和声音,也总会让记忆穿越时空,回到被时间遮蔽的生活片段之中。“有关米豆……她带过他几日,标志性事件有两件——教会了他认识‘的’字……”,“瓦窑中‘缸’这个音节忽然铛铛响起来,……他知道这米缸的底部通向何处。”在小说中各个人物的记忆叙事中,总有语词的光亮熠熠生辉。罗世饶的多数生命时刻,似乎是由他刷写的标语给串接起来的。即便是小城里“重叠呼叫法”也会唤起对过去革命题材影片《南征北战》《英雄儿女》的回忆——“长江长江,我是黄河……”小说中虚构的《李跃豆词典》及不断提及的《突厥语大辞典》等等,更像是在词语——所谓的存在之寓所中试图定义古老的生存体验。小说中“你”“我”“她”的叙事人称无序交替,叙事视角突如其来的变化,也体现出作者对观看、体验与沉浸的经验互换,传达着叙事上对语词视角的处理用心。
面对时代中语词的流变,我们可以清晰地辨识出叙事者的语词敏感和语言忧患。在“香港叙事”中,叙事者时常表达出语言陌生境况下的话语挫败感:“一个不懂英语的人来香港需要强大的内心,需要自我勉励,自我喜剧化”,在普通话不断推广的语境中,“她还是频频想着‘驯养’这个词,就是说,她前十九年养熟的是老家的土话,……至少有十到二十年,普通话这种第二语言使他没有自信,光彩顿失”。所以,突然以故土方言袭入来收束“香港叙事”,很容易让人理解为一次本能的话语对抗和语词返乡。同样的,在“作家返乡”的讲述中,当地各种所谓的话语“原创”,在叙事者看来,无非是一种语言上的沦落:“早已认定普通话代表至高水平,圭宁话上不了台面。时代车轮滚滚,方言迟早都会被普通话的大轮碾压掉的。”所以,叙事者认为“新名词都是破坏人生的,固然使人兴奋,同时也使人慌乱”。这也是叙事者对“春晚体”拒斥的原因。
在叙事者这里,语言流变中的统一化、规范化、网络戏谑化,一方面形成了语言流通的“硬通货”,但同时也遮蔽了方言的原初意义和丰富的存在感知,有着一定程度的暴力因素。正如黑格尔意识到的,在对事物进行符号化之中存在着某种暴力的东西。“语言简化了被指涉之物,将它简化为单一特征。它肢解事物,摧毁它的有机统一,将它的局部和属性视为具有自主性。”[10]这正是《北流》作为一个语词小说最深重的人文关切。小说中虚构的《李跃豆词典》以及时不时出现的《突厥语词典》《亚洲干燥史》、当代的“倾偈”等等,其意义就在于提示语言学的基本逻辑——一切记忆皆在语词之中,语词的丧失,也就意味着记忆的湮灭,也就意味着个体存在感的历史性消亡,至少是其生动性和原初性的消亡。这是作家潜藏在心灵深处的最深重的忧患。
记忆图绘中的经验悬浮,一贯是林白写作的前结构。正如杰姆逊所认为的那样,图绘的功能,在于自身定位的经验与“身处何方”的存在性政治/哲学感知,然而,作者自身所属的“北流”经验,在记忆与时间的变动及各种记忆承载物消亡的前提下,将始终作为无法书写的创伤性情感停留在作者的“真实界”之中,以一种悬浮态,成为一种写作的永恒姿态。将林白作品中反复出现的“私奔”“出走”的幻想式书写,解读为一种对时间与空间甚至是语词的逃离,并不牵强。在未来的一切记忆无从铭刻的时代(或停留在网页搜索的记忆功能,或地图导航的遗迹之中),如何铭刻记忆,如何在记忆的图绘中定位自身的生存体验,林白以一部《北流》,隐秘传达了其内在的写作意图。这也可能是未来文学记忆书写的一大困境。因为在那时候,我们可能已经完全丧失了大写的记忆功能,成为尼采意义上无法承载历史和未来的“末人”。《语膜》一章中关于病毒攻击大脑语言区,人类丧失语言能力,借用语膜作为语言工具,是一个值得玩味的寓言。
注释:
[1][8][9]澎湃新闻:林白《北流》:一种颠覆和对抗线性结构的小说写作,2021年11月2日。
[2]【斯洛文尼亚】斯拉沃热·齐泽克:《幻想的瘟疫》,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2页。
[3]《林白作品自选集·林白论》,漓江出版社1999年3月,第392—393页。
[4][7]转引自阿尔伯特·托斯卡诺,杰夫·金科:《绝对的制图学》,长江文艺出版社2021年版,第19页,21页。
[5]《就这样置身其中》,http://www.chinawriter.com.cn/n1/2021/1019/c404032-32257739.html。
[6]【英】阿兰·德波顿:《旅行的艺术》,南治国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年版,第188—189页。
[10]【斯洛文尼亚】斯拉沃热·齐泽克:《暴力》,中国法制出版社2012年版,第5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