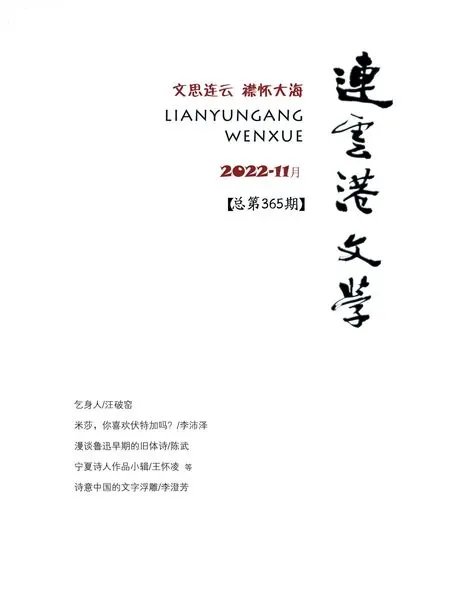雪中奔跑的孩子
2022-02-09朱未
朱未
一
或早或晚,我们谁也没能逃离那个诅咒。
这一生,我们注定要和某个朋友分开,注定要从一段亲密的关系中抽离,直到彻底失去他的音讯。“向阳”这个名字,听上去就自带昂扬的朝气,就像一株迎着太阳生长的向日葵。向阳长脸,浓眉,小小年纪就带着一股刚劲。
小学二年级,学校将两个班合并成一个庞大的班级——印象中有56 人。许多年过去,光阴在风雨中漫漶褪色,如今还能留存于记忆的名字屈指可数。那些或亲或疏的名字,代表了闪闪发光的童年。毕竟成年后所有的幸福或不幸,都源于童年的完整或缺失。
小学从北至南呈三级阶梯,一溜平房坐北朝南,于最高处俯瞰全校;下一缓坡,第二阶梯处设有体育设施,单杠、双杠和零星的树木;最低处是教师办公室、圆形的花坛和没有跑道的操场。厕所位于校园最东侧,传统的旱厕。夏天,厕所的气息“老远就放着哨”,只有经过哨兵严格的盘查,才有资格如厕。这样的基础设施是90 年代北方乡村小学的正常配置。
校园围墙边长着一溜神奇的树,有人说是胶树:叶子捣碎后仍筋脉相连,簇成一团。这种有黏性的叶子成为学生的玩具——就像打雪仗,把碎叶子扔向对方,叶子会粘附在衣服上。我们乐此不疲,胶树听到下课的铃声,忍不住瑟瑟发抖。就像有一双透明的手送来四季的风,每隔一段时间,就有新的游戏在学校传播,至于是谁引进了游戏,无从知晓。攻城、打方包、抓石子、丢沙包,这些游戏就像衣服的款式,隔一段时间又重新流行。攻城游戏需要多人配合,在地面上画出双方的城池。上课铃声响起,我们看到班主任背着手从第三级阶梯走上来,攻守双方均放弃了堡垒,呼拉拉跑进教室。那个作鸟兽散的画面重复了很多次,成为童年心境的一种象征。
我和向阳就这样一起学习、游戏、奔跑,一路跑进了初中。求学时代,唯有成绩才是衡量学生优秀与否的标准。向阳成绩普通,在校园里不是耀眼的存在。进入初中的他,总是默默的,低着头,不怎么说话。有一天我感冒了,路上遇到他,他陪我穿过操场去卫生室。我很开心——欣慰我们的友谊一直都在。
从中学回家的路不只一条,乘车二十分钟,步行则要翻过两座山花上几个钟头。沂蒙山地区的山,不是标准意义上的崇山峻岭,只是低矮的丘陵。然而,在少年的视域中,那是很高的山,很长的路。回家的路途充满期待。家是与幸福有关的一切的终点。三年里,记不清有多少次和朋友们步行回家。累的时候,把书包穿在木棍上,像抬着一串硕大的糖葫芦。登顶后,我们坐在山巅大口大口喘着气。待气息均匀,拿出专门为此刻预留的食物。此刻,风从四野散漫地吹来,汗水从年轻的两颊滴落。我吃着东西,听着同伴嬉笑的声音,看着比平日更近的天空,想着母亲备好饭菜在家中等着我,感觉来到人间是如此的美好。
下山后的路会经过向阳家。那是春末的一个周六,我汗水涔涔地从山上下来,向阳正在家门口嗑瓜子。他看到我,不由分说,抓了一把瓜子放到我衣兜里,然后将我拉进了家中。
向阳的妈妈个子不高,留着齐耳根的短发,那天穿了一件黄白色棋盘格褂子。她很快炒出了两个小菜,热忱地招待年少的客人。她身上有着和所有农村妇女一样的朴实,我和向阳吃饭的时候,她在别处忙碌着。我打量着向阳家的布置,他家的条件属于中上。向阳的爸爸在大队里任职,他家属于干部家庭。这顿午饭,不仅感动了我,也感动了母亲。向阳的妈妈去世以后,母亲惋惜地对我说,她还给你做过饭呢。
向阳的爸爸是村里的名人,大队外墙、沿街商户墙壁上的标语都出自他的手笔。小时候,我常常看到那个穿中山装的男人一手提着颜料桶,一手刷标语。那种创造是从无到有、成竹于胸的过程,对于孩子们来说,充满了神秘的色彩和无限的想象。
很遗憾,向阳没有遗传其父的艺术才华。班主任看着向阳的字,忍不住叹惜,更多是不解,爸爸的字是村庄的代表,为何儿子的字不忍卒读。每每如此,向阳低着头不说话,仿佛给自己的爸爸造成了多大的屈辱。
或许靠近艺术的人,本质上都是浪漫的。城市对男欢女爱的包容度要大于乡村地区。作为熟人社会的乡村,一点点情爱的纠葛容易衍生成招致灾难的重大事件。我读高中时,向阳的母亲喝农药自杀了,据说是因为向阳的爸爸有了外遇。那位曾经为我做过一顿饭的女性,是怀着何样的勇气,才决定撇下未成年的儿女离开人世。她一定是对人性失望透了吧。
向阳在十几岁的年纪失去至亲,他是如何艰难地成年,如何独自面对残酷的现实,他哭了多久,痛苦了多久,他是如何接受下失去母亲的生活?这些我都不得而知。那时我的母亲还活着,我不敢想象失去母亲后,一个人该如何活下去。
后来我读书、远行、考研,南下的火车是从故乡出发的河流,那弯弯曲曲的河道正如我走过的路。向阳初中毕业就早早步入社会,我没有见过成年后的向阳。如今,向阳的孩子正在和某个同学经历童年,就像很多年前我和向阳一起经历的那样。他们一起学习、游戏、长大,或许也会在某个命运分岔的路口分别。人生代代,花开花落,没有尽时。
二
张欣的妈妈,是村庄里独特的存在。她年轻、高挑、美丽,与众不同。她和村庄里面容粗糙的妇女们不一样,或许,她不该属于村庄,她应该生活在摩登而现代的地方。很多年里,故乡的女人中,只有她给过我那样的感觉。
学会骑自行车后,我的活动半径得到延伸。我们骑车去张欣家,他的妈妈热情地招待我们,他的家也是时尚的。一个富裕的和谐的家,是我羡慕的家的样子。张欣的爸爸做生意,他家境优渥,似乎只有那样富裕的家庭,才会有张欣妈妈那样的存在。
张欣有零花钱,很多。赶集的日子,他请我吃东西,夏天吃雪糕,冬天吃年糕。我常常为他的馈赠感到羞愧。总想做点什么报答他。父亲从县城新华书店买给我的三本连环画,他是第一批读者。唯有这样的待遇,才能回报他的友谊。我们是童年里无话不说的朋友,他告诉我,他的母亲在怀他之前还有过一个孩子,只是那个孩子并未来到人世。后来我想,如果张欣有个哥哥或姐姐,至少在他母亲去世的时候,会有人真心地与他分担悲伤。
县城有四所高中,我在二中,张欣在四中,见面的机会少了。初秋的一个周日,我、倩倩和张欣一起乘车进城,他俩邀我到四中转转。我们像小时候一样在校园里走着,走累了,躺在草坪上聊天。那天的画面带着青春电影的滤镜,儿时的同伴在奔跑中长大了,男孩长成了俊朗的青年,女孩长成了漂亮的姑娘。他们在那个午后,怀揣着莫名的心事,对未来充满憧憬。春风迟迟,连柳树都染上了情绪,带着青春的喟叹。
帅气的人大都容易恋爱,普通人对他们的恋爱故事表现出理解和包容。中学时代,帅气的张欣呈现给世界一副多情公子的形象。他拥有幸福的家庭、优渥的家境和帅气的外表,他是令人羡慕的,他的多情是顺理成章的。
二中位于县城的中心,沿着学校门前的大路一路向北,不远处的东方超市是县城最大的购物中心。某天,我在东方超市遇到了张欣和他的爸妈。我和他们聊了一会,他的妈妈依然光彩照人,分别的时候,她笑着对我说,放假的时候去家里找张欣玩,语气中仿佛我和张欣还是小孩子。我知道她生病了,但那天她充满活力的状态一度让我以为关于生病的消息其实为误传。那是我最后一次见到她。
高考前,张欣年轻的妈妈去世了。张欣没有选择复读,他去青岛投奔堂哥,做学徒、开店,倔强的他与这个世界短兵相接。听说张欣的母亲给他留下十万块钱,那是一位母亲远行前为儿子留下的干粮。基于女人对男人的了解,她预感到没有妈妈庇护的张欣,未来的路会走得很孤独。几年后,张欣的爸爸再婚,而且有了新的孩子。
张欣和其父的关系一度僵硬。他爸想续弦,他不同意,甚至被棍子抽过。亚楠成为张欣全部情感的寄托。亚楠在新疆读书,天山万里,鸿雁难至。亚楠后来对我说,在张欣最痛苦最难耐的时候,我们都不在他身边。作为朋友,我感到抱歉。张欣希望亚楠给一个答复,可是亚楠不敢,她要在遥远的边疆呆三年,她怕辜负了张欣的等待。
长大后的张欣向这个世界证明,他不再是那个多情的公子,他有耐心,并且痴情。张欣和亚楠结婚了,生了两个女儿。我结婚的时候他们带着孩子来了,孩子们在席间嬉闹,就像我们小时候那样。
三
南京入梅的那个早上,空气中有凉风流动。开车去单位的路上,打开怀旧歌单,听到了《摇太阳》这首歌,一瞬间,我回到了二十多年前的那个清晨。我、妹妹和母亲在吃早饭,山东台在播放早间文艺。一位身材高挑、长发如水的女子边唱边跳:“我们一起摇呀摇太阳,不要错过那好时光。”我看得出神,手中的筷子停了下来。母亲少有地开玩笑说:“长大了,是不是想娶个这样的老婆。”我羞愧地赶紧低头吃饭,脸自然是红了——那是童年里珍贵的戏谑而温情的时刻。
我一直觉得,母亲有一种神力,一种预测未来的神力。初中时,我要去镇上上学,母亲说,带上伞吧,下周下雨。我没有带,下周果然下雨。母亲说,天要冷了,多带一件衣服吧。我没有带,下周天气骤凉。母亲就像一个先知,似乎可以预料一切。
牙疼困扰了母亲好多年,从外婆过世起,断断续续了十年。看牙要花钱,这是她一直拖着不去治疗的原因。饭桌上,常常是刚吃了几口,母亲就牙疼得放下筷子。我催她去把坏牙拔掉,换上新的,她一拖再拖。人活着,还有什么事比吃饭更寻常、更频繁、更现实的呢。牙疼剥夺了母亲吃饭的快乐,降低了生而为人的质量。终于,在我读研期间,她换上了烤瓷牙。她高兴地对我说,现在吃什么都可以了。医生问她:要不要换至少保质10 年的牙。她笑着对医生说:能不能活10年还不一定呢,就换个普通的吧。她又笑着把她说给医生的话转述给我。她果然没有等到那颗假牙的有效期。她和那颗假牙仅仅相处了两年,就猝然离世了。
母亲离开前的最后一个春节,我们一家人去女友家拜访。那是双方家长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会面。母亲见到了未来的儿媳,身材高挑、长发如水。中午,两家人在饭店吃饭,母亲担心父亲喝多了酒出丑,不停地给他暗示,就像她小心翼翼的一生。母亲对女友非常满意,她的神力又一次起效了,她或许预感到什么,在离开前要了了最大的心愿。当她看到儿子可以独立生活后,就安心地离开了。
母亲走后,一部分的我也随之死去。从此,所有关于收获的喜悦都打了折扣。
高考结束后的那个暑假,我被调剂到中外合作办学专业,学费高得离谱,远超家庭所能承受的程度。我决定回去复读,我不想为了读书而把家庭拖向一个更深的深渊。那个夏天无比漫长、无比燠热,又无比绝望。时间像是在这个夏天停止了运转。时值盛夏,我却觉得很冷,像高烧不退者忍不住地战栗。我感到一股强大的无力感把我往深渊里拽。我不想吃、不想爱,对身边的任何人任何事提不起兴趣,我只想摆脱这无尽的不幸和纠缠。
那时的我沉浸在自己的痛苦中,却忽略了:母亲一定比我更难过。她自己的命运多舛,她的儿子求学乖蹇,她的父亲卧病在床,那时最难熬的是母亲,不是我。
复读的生活就像舔着一枚五角的铜币,冰凉而单调。希望是没有的,只有绝望。我在等待,等待那审判的日子早点到来。朋友们写信给我,那些信就像是从异地飞来的热气球,让我短暂地脱离日复一日的枯燥。亚楠从新疆写信给我,鼓励我:请相信我,也相信自己,你的苦难将会被几倍的幸福弥补。人到中年,当我重新翻阅那些信时,我依然落下了与初次阅读时同样的泪水。
四
那个庞大班级中的人,向阳、张欣以及后来的我,像是陷入了某种不能逃离的诅咒,或早或晚,我们在年轻的时候就失去了至亲。在年轻时失去至亲的人,就成了无家可归的孩子。他们在大雪中狂奔,迷了路,回不了家,不知要去向哪里。他们一生的爱恨都在漫天飞雪中迷失了。
母亲离开后,我在不同的梦境中与她重逢。其中一个梦中,我是一条鱼,在一汪水里,隔着一片苍茫的玉米地,我不停地喊着,妈,妈,声音很大。可是不管我怎么呼喊,都没有人应答。我终于走出了玉米地,还在喊着,母亲还是没有回应我。我喊累了,后来二姨走了出来,问我怎么了。
还有一个梦,我回到老家,可是没有地方睡觉,母亲不在,没有人为我铺床。我只好辗转找地方住宿,我去了三伯家,被赶了出来。路上遇到一个老人,她对我说,你妈妈是个好人,我说去你家玩,你妈妈就一直等着我,本来你妈妈打算洗头的,为了等我也没洗。醒来后,我想起来,那个老人就在我的童年里,她常常坐在门前的石阶上,我和母亲曾经陪着她聊天,度过了许多个冗长的下午。
随着年岁渐长,我们对时间的感知力也在不断变化。小时候,一天两天就像一生一世,长大后,十年八年就像弹指一挥间。我们永远无法理解当下经历的一切有什么意义。只有时过境迁,从未来回看当下时,就像回放的慢镜头,才能发现闪光的细节。
更可怕的是遗忘。当母亲突然从我的生命中抽离,母亲在院子里扫雪的形象,站在电风扇前包饺子的形象,目送我乘坐公共汽车去上学的形象,那些形象纷至沓来又重合起来,每每想起心脏就像被人用力地捏住。几年后,我竟然慢慢地适应了没有母亲的生活,并非是我把母亲遗忘了。我和遗忘做着胶着的较量,因为我知道,遗忘是对一个人不可原谅的背叛。
后来当我读到《朗读者》:“可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对她魂牵梦绕的回忆不再伴随我。回忆留了下来,犹如当火车继续前行,一座城市留了下来一样。”于向阳、张欣和我而言,不同的是我们留下的不是城市,而是乡村,我们最珍贵的、像金子一样的回忆都在共同的乡村。我们的母亲一直都在,就在少年时期的村庄。她们就在那里,无声无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