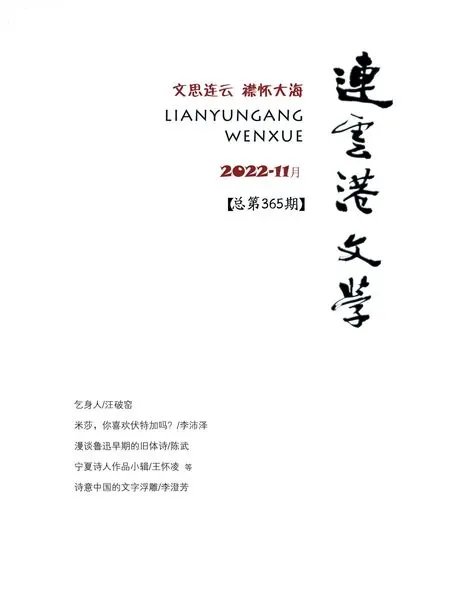米莎,你喜欢伏特加吗?
2022-02-09李沛泽
李沛泽
淡淡的花香伴着秋天的雨。轮胎碾过长满鲜花的泥泞之地。在这异乡的土地上,坐在车里,我听着秋雨打在钢铁上的声音。很快,难闻的机油味又充盈了我的鼻腔……
“该死,这玩意不动了。”
我听到身旁机械师的咒骂。他和司机已经一夜没能合眼。而现在,他还得顶着冰冷的雨水,拖着疲惫的身体,趴到外面去检查车辆。
有好奇的小伙子爬出装甲车,看着机械师翻开一个个面板,讥笑机械师被密密麻麻的排线绕得团团转。
同行的车子停下来,我探出头,去看我们的朋友。那边也有小伙子过来凑热闹。放眼望去,我却找不到我想看到的人。
几个小时前,我们还在高加索小城的酒馆里消遣着短暂而宝贵的假期。
他叫米莎·阿列克谢·伊万诺夫。
在高加索的这几年,我没学会太多东西,唯独和一些老兵一样爱上了喝酒。他们总是成群结队地溜到附近的镇上,跑到小酒馆里搞点廉价的伏特加,喝得烂醉如泥,然后再被不敢喝多的新兵拖回去。五大三粗的他们往往把新兵累得够呛。
那一年圣诞节,格外寒冷。小镇的街道被大雪覆盖,超市停业,交通停摆。庆幸的是,酒馆还开着,还有酒喝。在那个寂寞的圣诞夜,我遇到了米莎。
他个子不高,瘦长的脸上长着一双忧郁的棕色眼睛,我不知他的眼睛是不是从前就这样悲伤。但吸引我的不是他的样子,而是他手中的酒。
他没有和其他兵士一样畅饮着伏特加,而是一杯又一杯地细品黄色的白兰地。我有些好奇,去问他为何不喝点更加俄国的酒,比如伏特加。
“你好,我不喜欢白色的酒。”
他的回答令我惊讶。
“可伏特加是透明的。”我追问道。
他又饮下一杯酒,没有回答。
“小子,你没听说过在咱这,年轻的人不能回避长者的问题吗?”
他没有回答我。屋里的空气变得和外面一样冷冰冰的,即使有炉火闪着光,发着热。这便是我与他的第一次相识,滑稽而尴尬。
我喝完我的伏特加,走出酒馆。小镇的圣诞远无家乡那般富有生机。想起故乡的村子,从秋收到冬藏,同圣诞一起庆祝丰收,一路上张灯结彩,街道上开满了欢乐的面孔。至少在我儿时是如此。眼前这座风雪小城里,每个人都闭户不出,晚上也少有灯火。大雪势头减缓,我漫步在街道的一旁,嘴里叼着兜里的最后一根香烟。
当我又走回酒馆的门前,发现一个消瘦的身影正吃力地拖着某物。好奇心驱使我快步上前。于是我看到了那双忧郁的眸子。
是米莎,他正拖着一个喝醉的士官,他的脸看上去已经冻僵了。
我急忙跑到他身边,把那名士官架起来。当我扶起那名士官的同时,米莎也瘫倒在地上。
“小子,你这么做,结束的可不只是你自己的军旅生涯。快起来,帮我搭把手。”
他吃力地起身,我们两个人架着快要变成人棍的小士官走在街头。还好,此时的雪并不是很大。
两个人默默无言,只是低头看着脚下,用力支起昏睡的酒鬼士官。可我这样的话痨哪忍得住寂寞,再次开口向他搭讪:
“嘿,小子,你还是没有回答我的问题。”
“您说什么?”他喘着粗气,但说话的语气比刚才礼貌了很多。
“你为什么不喜欢喝伏特加呢?”
他沉默了一会儿,最后还是缓缓地开口:
“我父亲喜欢喝这个酒,喝完就抄起棍子追着我打。”
“不过,不是所有喝伏特加的人都会那样。”
“是的……比如说您。”
“没错,我喝完酒从来没打过人,哈哈……”
我尴尬地笑了笑,而他也没有力气再多说一句话了,好在最后平安地回到了营地。倒霉的士官遭到了处分,不过好在没有在外面冻成人棍。
在那次相识之后,我们便经常一同去那家小酒馆。每次他都会点一杯不一样的酒。不变的是他忧郁的眼神和永远不沾的伏特加。
说老实话,他长得并不算丑,应该说还算标致,再加上忧郁的眼神,女人缘本应不差。但这么久了,我还没见过有女人跟他搭讪过。或许在这座寒冷的小镇,在今天这个冰冷时代,这儿已不再缺少忧郁的眼睛,让他只能是寒冬里一棵不起眼的枯草。
他告诉我,他来自解体前的阿塞拜疆,那里也曾盛开着鲜花。
我没有去过那里,在我的印象里,那里盛产石油。那里的人们很富裕,最起码……比我要富有得多。我上不了大学,也找不到什么工作;军队对我来说,是个可以安生的地方。我想我这样的思想很不健康,但说实在的,在这个时代,有几个人不想找个可以安生的好工作呢?后来,我大概知道了米莎参军的原因。
那一年的四月,冰雪渐融,路边慢慢地长起了野花野草,可仍很少见到美好的阳光,大家还是喜欢夜里溜出去喝闷酒。这天晚上,他喝得格外多,格外多。
“今天是我母亲的生日。”
他微红着眼睛,晕乎乎地小声告诉我。
“你有给你的母亲写信吗?”
“没有。”他说着,伴随着一杯刚刚下肚的酒。
“你不想她吗?我记得我们已经很久没有回过家了。”我拍了拍他的肩膀。可换来的是一阵叹息。
“我很小的时候,她便不在了。”
听到这样的回答,我表现得有些惊讶,但心里并没有多少意外。当然,接下来也没有问他具体的细节。
“在我很小的时候,她就因为白内障再也看不见了。她的眼睛从蓝色变成白色,再到我也不知道那是什么颜色了。”
“是透明的吗,就像伏特加。”我小声说道。
“也许吧……”他擦了擦眼睛,然后接着说,“失明以后,她总是做错事,总是犯糊涂,那时我的父亲还很爱她,每天与她形影不离,无微不至地照顾她;跑遍了全俄最好的医院,花光了本就微薄的积蓄。”
“后来呢?”我给他倒了一杯酒,他一口吞下。
“再后来……奔波的途中,她染上了其他的病,可我父亲再也没有钱带她治病了……你知道,那时候钱可是过了几天就贬值得厉害。”
我沉默着。
“很快,她便走了,一天晚上,走在我父亲的怀里。她年纪并不老呀,但相比她的同龄人,显得那么虚弱而消瘦,仿佛一具骷髅……我听别人这样形容她。她生了重病后,我就再也没见到她。她走了之后,父亲完全变了。他没了工作,整日酗酒,喝醉了便砸家打人。喝光了积蓄,就把房子卖掉,到出租屋里继续喝。那时我已经十岁了,我不能像其他孩子一样上学。因为我没有上学的钱,一分钱也没有。”
“那你去了哪里?”
“我父亲没钱喝酒了,把我卖给了酒馆的老板当伙计。之后,我再也没见过他。”
说到这里,他哽咽了一下。我给他递了一杯酒,让他先别说了。这天是我第一次听他说这么多话,平时他可是这家小酒馆里最安静的人。
他不再说话,只是一个劲地喝酒。他从来没喝过这么多的酒,很快他便醉倒了,睡着在吧台上。我背着他走回了营地,一路上都是他的碎碎念,嘴里说着我从没听过的奇怪方言,眼角滑下的几滴泪珠,冷冷地滴在我的后颈上。
这可真是个可怜的人,我已经可以想象到他被卖掉后又发生了什么。我不知道他是如何辗转来到了这里。我不想再让他揭开自己的伤疤,希望他明天就能忘掉这一切,变回那个寡言而忧郁的米莎。
可我没想到的是,他虽然醉了,可什么也没有忘掉,酒精是他伤感的助燃剂。记忆不像火,燃烧之后不会随着风消散,而是更深地刻在他心灵深处。令我奇怪的是,米莎并不介意与我分享他悲惨的过去。
第二天,他再次邀请我一块去小镇上的那家酒馆,继续带我回忆他那不堪回首的往事。
“在酒馆的那几年,我并没有感觉到和以往的日子有什么区别,不过酗酒的人从我父亲换成了素不相识的路人。我不同于其他的酒保,我是最没有地位,最下层,最卑微的,是人人都可以欺负的,人人都可以踩在脚下。很多时候,就算我做得再好,没有一点失误,也会被酒鬼们拉过来摁在桌上殴打。”他喝下一杯酒,然后拉下自己海魂衫的一角。他告诉我,那是他第一道永久的伤疤。
“有天晚上,我不小心把客人的一瓶酒弄倒了,酒瓶渣子落得到处都是。那人捡起一块碎片,直接扑过来在我的锁骨下划了一道口子。”
我看他抚摸着那道伤疤。他低着头,眼神不再像之前那样忧郁,像看自己孩子一样看着那伤疤。
我感到很奇怪,为他加了一杯酒:“怎么,这疤痕还有别的故事?”
“是的,你可真聪明。”他抿了一口酒,像是在回忆一件美好的事情,嘴角露出了我从未见过的微笑。
“我的血止不住,从胸前流到脚底……此时此刻,唯一能容纳我的地方只有那狭小又阴暗的储物室,我想都没想就跑到了那里。每当我遭遇折磨,痛苦的时候,我就到那里去。储物室最里面的墙上,有一面破碎的镜子。”
酒馆的储物室,阴暗而潮湿,散发着老鼠窝一般污臭的味道——这应该是令人崩溃的地方啊。我心里这样想。
“我脱下我的上衣,看着已经被鲜血染红的胸膛,不敢说话,心中满是恐惧。虽然我内心早已不再畏惧死亡,可真到了这个时候,还是感到害怕啊!但我身上已经一无所有了,我连用来擦身体的毛巾都没有,我只能绝望地看着镜子,直到……”
他小呡一口威士忌。
“米莎……一个人在用温柔的声音呼唤我。镜子里看到的,是一个女孩的身影……”
“哇哦……”
没有注意到,在我认真听他说话的时候,身旁出现了一个姑娘。她留着一头金色的齐肩短发,水灵的大眼里闪烁着好奇的光,她也在专心致志地听着米莎的故事。
“接下来,会是很浪漫的故事吗?”女孩满眼期待地望着米莎。
“我想,算是吧,可能也不是……”米莎把下巴搭在自己的手上,一脸温柔地对着女孩说。我可从来没有见过他这样的神情。
接着,他又把头转向一边,露出他忧郁的眼神。
“她为我抱来一条温暖的毯子,用酒精和棉球擦拭我受伤的身体;她还轻柔地抚摸我身上那些往日的伤疤……在我耳边轻声说,孩子,你一定受了很多苦吧……”
我看到他眼角露出了泪光,加上他忧郁的眸子,看得让人心碎。他向我们描述了那个女人对他温柔的抚摸,用丰腴的身体把他搂入怀抱,擦去她的眼泪。就像是……
“就像是……我的母亲吧。”他停顿一下,喝了一杯酒。
“之后发生了什么?”女孩贴近了他,轻声地问道。
“在那之后,我再也没能见到她,就像我再也见不到我的母亲一样。”米莎捂着半边脸,做了一个深呼吸。他深情地望着眼前的女孩,似乎很久没有遇到这样愿意听他倾诉的人了。
“你的母亲,她怎么了?”
“你愿意听吗?”
“当然,伤心的孩子呐,我愿意听你给我讲到深夜。”
“我很久没有遇到愿意和我说话的女孩了,请问,我可以知道你的名字吗?”米莎挪动自己的胳膊,他与那个姑娘的距离更近了。
“娜杰日达(俄语意:希望)。”那女孩撩了撩自己的短发,“娜杰日达·伊万诺夫娜·捷列什科娃。”
“真是个好名字。”就在米莎感叹的同时,娜杰日达把她纤细洁白的手搭在了他的手上。
我觉得我不能继续待在这里了,可不能坏了这可怜孩子难得的好事。喝完杯中的伏特加,我走出了酒馆。这里的空气如高加索山上的鲜花,绽开着春意。
“你真的是我的娜杰日达。”这是我走到门口时,听到屋内的最后一句话。
很快,米莎这小子便更加频繁地溜出军营,而与我一同去酒馆的次数变少了很多。我总是一个人喝着闷酒。直到某天我坐在酒馆的窗边,看到不远处的路灯下,在清澈的河水边,那古老的石桥下,看到那对年轻人在热吻,我禁不住流下了热泪。此刻的我不只是年长者羡慕他的年轻,更多的是为他找到爱和希望而欣慰吧,虽然我并不曾有过。
我在新生的米莎眼里,看到了不同于以往的眼神。他更富有精神,像是初生的小草。
我希望他们的爱情也可以像小草一样,满是韧劲。不过我大概还是高估了他们一见钟情持续的时间。
“记得,常给我写信,好吗?”
这是娜杰日达上车前,说的最后一句话。她很幸运,可以离开这偏僻的小城,去更远的地方,更繁华的街市。但米莎只能同我一起,继续留在高加索的边疆。
“我保证,亲爱的,可我还是最后恳求你不要离开。”
米莎紧紧地抱住她,在站台上,背对着簇动的人群,消失在列车的呼啸之中。
此后,我很少看到米莎出门,除了训练便是埋头在自己的房间里,不断练习着自己的西里尔字母,精心地准备每一个信封,写好每一封信,然后满怀期待地坐在邮政室的一角。
可是,几个月后,娜杰日达很少再给米莎回信了,而他的热情却没有消散。一次次等待后的失落,等不到信的绝望就像被泼了冷水,给他梦中的恋爱降温。很快,他的眼睛再一次蒙上了忧郁,越来越深。
那年秋天,他已经很久没能收到娜杰日达的来信,他又爱上了喝酒,虽然他仍不愿意喝伏特加。
而在昨天晚上,他第一次向我表示,他愿意尝试一下这杯透明的烈酒,把自己埋葬在充满麦芽味的醉乡。
“你知道吗,我会好多次在梦中醒来,看到堆满信与花香的小山,然后再在梦中睡去,从梦中醒来,再看到堆满的回信,再睡去,再醒来,直到看到她站在开满雏菊的山岗上……”
我真希望他永远停留在梦里,忘掉爱情给他的伤痛,还有战争给他的疲惫。
我想,此时的他可能过于疲倦,还在那辆装甲车里做着美好的梦。
外面雨水渐停,天空明朗,万里无云,再无风声的喧嚣。
“那是什么声音?”
一个我感觉陌生的声音。
是他,米莎!对着天空大声叫喊着:
“是引擎!该死的,是引擎的声音!不是我们的飞机!”
很快,天边出现了一窜白烟,飞快地扑向这里。
“快跑!有袭击!”一个士兵疯狂地喊着。
“就地解散!重复,就地解散!”
士兵们跑出装甲车,四散奔逃。很快,随着一声巨响,一辆装甲车变成了燃烧的废铁。很快,这片土地又恢复了平静。
一个看上去年轻的士官在统计损失,除了那辆装甲车外,还有一具除了心脏以外,完好无损的尸体。
一道弹片正中他的心房。
“长官,你可知道他的名字?”那个年轻士官面向我问道。
我用颤抖的双手拂去身上的灰尘,跪在地上,用手盖住那双已经失去光芒、忧郁的眼睛。
“米莎。米莎·阿列克谢·伊万诺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