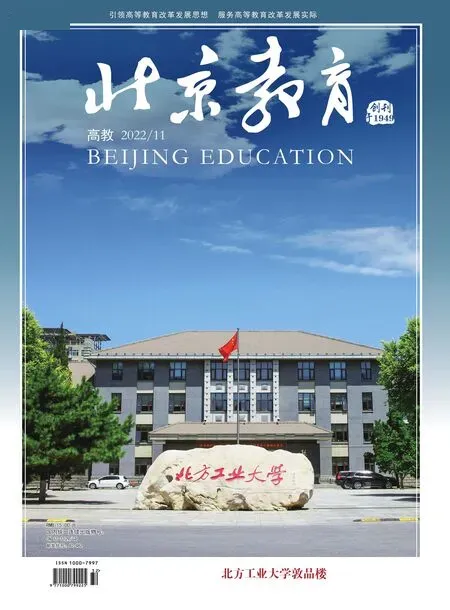学科融合视角下科研团队组织模式变迁及权变分析
——以北京大学和东京大学为例
2022-02-09李芳敏
□ 文/姬 懿 李芳敏
交叉学科团队建设是交叉学科发展的重要根基。随着知识的创新、发展与进步,单一科研人员已经很难紧跟多门学科知识的更新与进步[1]。而现实社会对科技发展与进步的需求又刻不容缓,这使得科研的发展不得不从个体的、自发的科研向集体的、团队的科研工作转换[2]。那么,高校交叉学科研究团队组织模式究竟经历了何种变迁?受哪些因素的影响?本文拟通过比较北京大学和东京大学的交叉学科团队组织模式,拟重点采用权变理论①进行诠释和解答。
北京大学和东京大学交叉学科团队组织模式的比较
1.北京大学交叉学科团队组织模式变迁与现状
北京大学交叉学科经历了一个从自发到有组织、从虚到实、从散到合的发展过程:20世纪90年代,北京大学的交叉学科研究开始出现了以人才培养为核心的跨学科组织模式,如课程、研讨班、讲座等,交叉学科团队建设仍无固定的、特殊的形式,以自发的组织为主。21世纪初,北京大学出现了一批以跨学科为目的的研究机构。例如:2000年10月,北京大学成立了生物医学跨学科研究中心(Biomed—X Center of Peking University),虽然学校并未给该中心配备额外资源,参与者的人事关系和管理体制均保留在原院系不变,在跨学科中心参与的事项仅可作为社会服务考核中的内容体现,但这已经成为跨学科研究团队具体依托的机构雏形。
从21世纪初至今,北京大学已经发展成立了多个跨学科中心,初期以理工科领域为主,如分子医学研究所、定量生物学中心等,后期还出现了西方古典学中心、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等人文社科领域的跨学科研究中心。2006年,北京大学成立了前沿交叉学科研究院,将生物医学跨学科研究中心等11家研究机构的学生管理、招聘引进、学术交流等多项事务纳入统一管理。至此,北京大学的跨学科团队组织模式开始逐渐地正规化、规范化,团队组织模式逐渐形成三种发展模式:一是自发组织的“民间”团体,基于个人兴趣汇集在一起;二是依托于虚体研究机构,这类机构对团队的管理多起到聚合作用,学校并不投入实际的资源,更多的是争取外部支持;三是依托于实体研究机构的团队组织形式。实体机构又分为挂靠类实体研究机构,这类机构的管理更多依靠于院系,院系原有的研究团队和机构的研究团队结合得更为紧密,希冀其相互碰撞获得学术创新。而另一类则是独立实体研究机构,他们的团队组织则更加自主,从人才引进、人才评估考核到后期的各项人事业务均由其自行管理。实体研究机构已成为学科交叉的重要力量,截至目前,北京大学共成立了49个学术实体研究机构,其中跨学科类33个。实体研究机构的蓬勃发展为跨学科团队的发展提供了土壤。
2.东京大学交叉学科团队组织模式变迁与现状
20世纪70年代,东京大学开始实行“大讲座制”,是较为初期的交叉学科团队组织模式。“大讲座制”中的每个讲座由1个或多个研究方向构成,每个研究方向由1位教授、1位~2位准教授或讲师和若干位助教组成,并会相应配有1间研究室。
2005年—2008年,东京大学牵头组建了多个跨学科研究机构,这些机构成为全校知识创新平台。例如:系统疾病生命科学先进医疗技术开发据点(Translational Systems Biology and Medicine Initiative,以下简称为TSBMI)[3],该组织形成了与多个研究机构之间的联合状态,研究人员具有极强的流动性。这种开放性为具有不同学科背景的人员之间的学术目标、学术兴趣甚至合作方式的契合提供了良好的机制。
目前,东京大学交叉学科组织已经发展出多种形态,有的交叉学科组织是实体型的,具有正式的组织建制、专职的研究人员、独立的场地和实验设施;有的交叉学科组织是虚实结合型的,即在容纳多学科的综合性学院中设立的各种交叉学科实验室、研究中心、研究所,这些机构虽然有组织构架并经常举办各种前沿讲座和会议,但其研究人员和学生的身份都归属在各个院系。
团队组织模式变化的权变因素分析
1.外部环境:高等教育的变革
1999年,中央和教育部先后提出,要进一步转变高校治理模式,加强了高校办学自主权。高校办学自主权的增大,使学校在人事管理方面的权利相对独立,编制、岗位严控的局面已更多转变为总量控制。学校能够更自主地调配其内部资源,这为一部分交叉学科机构诞生提供了制度土壤。
日本也基本于同期开展了法人化改革。2003年7月,《国立大学法人法法案》和另外五个与国立大学法人化相关法案的颁布,标志着国立大学独立行政法人化改革正式开始。改革后,日本的国立大学都相应获得了独立的财政权,可自由支配取得经费。约在一年后,东京大学便大力发展了多个跨学科中心,积极布局交叉学科,这些跨学科中心慢慢拥有了独立的科研团队和经费。
2.战略:学校目标的转变
2007年,《北京大学章程》制定工作启动,该项工作于2014年完成。章程的发布明确了学校的使命、愿景和责任。例如:章程“第二章职能”的第一条,即学校动员和组织资源,优化资源配置,主要发展自然科学、人文学科、社会科学、医药科学、工程与技术科学,开展人才培养、科学研究、文化传承创新、社会服务,开展深入、广泛的国际交流与合作。可见,学科建设是大学的首要职能之一,且学科被分为了不同类别,为了让学科做大做强,大学必须发展出与之相匹配的组织模式予以支撑。
2005年,《东京大学2005-2008行动纲领》对大学的发展重点进行了阐述,它提到大学战略实施的两个重点是“自律分散协调系统”和“知识的构造化”[4]。知识的构造化实际上就是要构建起有利于现代知识创新实践的学科发展的组织网络体系。这些变革也导致了东京大学交叉学科科研团队组织模式的变化。随着学校战略目标的转化,东京大学的跨学科建设已经逐渐上升到了战略高度,跨学科团队的组织也越来越规范,由原先的游散于各个院系到后期的专职再到最后的大学院制集合性组织。
3.规模:教师数量激增
从20世纪末至今,东京大学和北京大学的规模和人才引进方式都发生了较大变化。1997年,日本颁布了《关于大学教师等的任期制的法律案》后,日本公立、私立大学广泛采用聘任制,东京大学也不例外。北京大学改革稍晚,2014年,全面推行“预聘制—长聘制”(Tenure Track-Tenured)。这些变革都让人才引进、评估、晋升成为学校的常规业务固化下来。目前,在北京大学已形成每季度召开人才引进、晋升会议的工作惯例,这些都直接导致跨学科团队的管理方式必须依托于某一院系或独立实体机构的学术委员会。
4.内部环境:成员素质
无论是北京大学还是东京大学,教师的素质和结构也都发生了较大的变化,随着海归群体的增多,教师对跨学科研究的重要性和关键性都有了更深的认识。从跨学科团队的构建看,北京大学和东京大学后期跨学科机构引进的人员层次都比较高,有些是在世界范围内有较高声誉的学者。这些学者大多带来了自己的支撑团队,并将这种跨学科交流的文化和氛围进一步根植高校。
结论与展望
北京大学和东京大学交叉学科团队组织模式都经历了一个从自发性组织到实体性组织的过程,并根据外部环境和团队科研项目特点建立符合团队本身的发展模式,最终建立适应环境发展需求、契合团队内部发展规律的发展路径。不同之处在于,东京大学跨学科研究团队的组织对实体研究机构的依赖相对较小,方式更加多样,对学校资源的需求也相对更低。基于权变理论的分析框架,本文认为,交叉学科团队组织模式是基于其根植的外部环境调整形成的,为了更好地促进交叉学科团队建设,我国高校在交叉学科团队的环境建设方面应予以加强。
第一,要建立真正促进学科交叉的制度环境。现有高校人事管理必须有实体依托,如北京大学的人才引进、评估必须由院系或独立实体中心组织同行评审、学术委员会审议等,还需要出具院系评估、推荐意见和师德师风审核,因此由院系(所、中心)统筹的管理方式必然会长期存在。但在此基础上,我国高校可多推广交叉学科项目、多搭平台、多配资源,以项目制吸引和联合教师。例如:东京大学在交叉学科发展中特别注重利用校外资源,如与相关企业集团、科研院所、医疗机构都建立了合作伙伴关系,开展交叉学科交流活动,这种做法大大降低了交叉学科对实体中心的需求与依赖。
第二,要特别注意对部分团队的精准支持,充分挖掘、激活现有团队活力。目前,很多高校在长期发展过程中培育了一些团队,其中不乏成熟群体,如北京大学人工智能团队已与校内工学、计算机科学、医学、艺术等团队均建立交叉与联系。发展交叉学科并不一定非要做增量,高校可在现有成熟团队基础上,适时地引入整合其他学科资源,并加以重点培养和扶持,特别是要注重对团队首席科学家的重点扶持和资源倾斜,使现有团队以最小的资源消耗迅速成长起来。
第三,要建立促进交叉学科发展的人事评价体系。例如:北京大学的人才评估小组特别注重理科、工科交叉,人文和社科交叉,注重人员构成中的学科平衡。同时,北京大学建立了相对完善的联合聘用制度,在考核评价时充分考虑教学科研人员在交叉学科平台方面的工作量,使在交叉学科平台供职的教学科研人员有了制度和政策的保障。
注释:
①权变理论,是系统设计思路的一个重要分支,其核心思想是强调设计决策取决于环境条件,是对环境权衡的结果,即将组织看作一个开放的动态系统,侧重点在于组织结构必须根据所处环境的变化而不断地进行调整。权变观点的最终目的在于提出适宜具体情况的组织设计和管理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