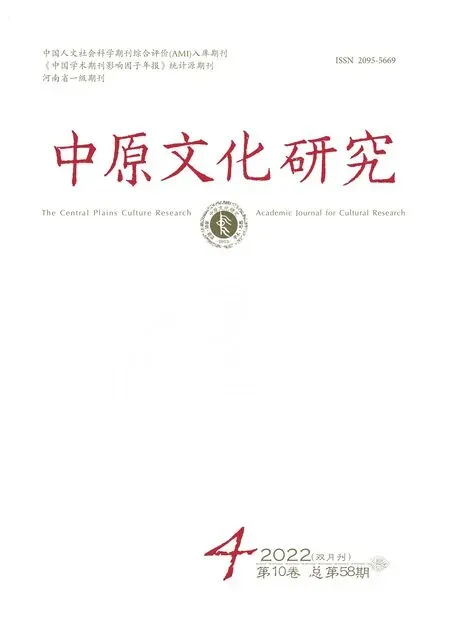宋代《中庸》经筵进讲与帝王修己治人*
2022-02-08刘美芳
王 琦 刘美芳
在宋代儒学发展与社会秩序重建过程中,《中庸》从《礼记》中独立出来,无疑是四书学发展史上的标志性事件。自唐代李翱《复性书》以《中庸》为依据,建构儒家心性之学以来,为应对佛道冲击,复兴儒学,挽救世道人心,《中庸》的价值意义与思想资源在宋代被重新挖掘。范仲淹、胡瑗、李觏、张方平、陈襄、周敦颐、司马光、程颢、程颐、苏轼、范祖禹、吕大临、晁说之、游酢、杨时、侯仲良、朱熹、真德秀、袁甫等均有诠释《中庸》之作,一时蔚为壮观。尤其是朱熹将《中庸章句》《大学章句》《论语集注》《孟子集注》合编为《四书章句集注》,在理宗朝受到官方的推崇后,便奠定了《中庸》在“四书”中的重要地位。
《中庸》在宋代的发展与兴盛,不仅与智圆等佛教徒们的提倡、士大夫的撰述与阐释密切相关①,而且还与其适应了时代与社会发展的多种需求有关②。然而一种学术思想与价值观念要成为全社会共同认可的主流意识形态,固然离不开一批批士人通过著书立说、授徒讲学等方式向社会传播,同时还必须得到最高层的认可与推崇,方可形成引领学术发展与社会思潮的合力。目前学界对《中庸》的研究更多集中在其作者、文本、思想等方面的探讨,对于《中庸》如何为帝王所熟知与认可,则少有学者涉及。本文以经筵进讲为视角③,全面梳理《中庸》向帝王传播的情况,揭示其经义诠释与帝王修己治人之间的内在联系,探寻《中庸》兴盛与发展的另类根源。
一、《中庸》在经筵的传播
宋代帝王“无不典学”的制度安排,促进了经筵制度的完善,为士大夫向帝王进讲儒家典籍,传播儒家学术思想与价值理念,获得认可与支持提供了有效平台④。《中庸》从《礼记》中独立出来,成为“四书”之一,与其在经筵的进讲与传播密切相关。
现存最早的《中庸》经筵进讲的记录,是宋真宗景德四年(1007年),“帝宴饯侍讲学士邢昺于龙图阁,上挂《礼记·中庸篇》图,昺指‘为天下国家有九经’之语,因讲述大义,序修身尊贤之理,皆有伦贯。坐者耸听,帝甚嘉纳之”[1]82。邢昺以《中庸》“为天下国家有九经”的思想,劝谏宋真宗修身尊贤以治天下。其实,宋真宗早在为太子之时便已接触、学习过《中庸》。据王应麟《玉海》记载:“真宗自居藩邸,升储官,命侍讲邢昺说《尚书》凡八席,《诗》《礼》《论语》《孝经》皆数四焉。”[2]516又说:“邢昺在东宫及内庭侍上讲说《孝经》《礼记》者二,《论语》十,《书》十三,《易》三,《诗》《左传》各一。”[2]516可见,邢昺在东宫多次进讲《礼记》,则《中庸》必在讲读之列,只是此时《中庸》还没有从《礼记》中以单篇形式独立出来。
宋仁宗时,迎来了《中庸》发展的重要时期。天圣五年(1027年),宋仁宗“赐新及第人闻喜燕于琼林苑,遣中使赐御诗及《中庸篇》各一轴”[1]91,并“令张知白进读,至修身治人之道,必使反复陈之”[1]91-92。这是宋代帝王最早以《中庸》赐新及第进士的记载,并由当时的宰相张知白当场讲解经义,足见其对《中庸》修己治人之道的重视。同时也说明了至少在宋仁宗时《中庸》已开始从《礼记》中独立出来。天圣八年(1030年),宋仁宗“赐新及第进士《大学》一篇。自后与《中庸》间赐,著为例”[3]5268。可知,从宋仁宗天圣八年(1030年)开始,以《大学》与《中庸》“间赐”新及第进士已经成为惯例,这对于《大学》《中庸》地位的提升与影响力的扩大无疑是起到巨大作用的。宋仁宗为什么会如此重视《中庸》等经典呢?这与经筵官们多次为宋仁宗讲读《礼记》密切相关。早在天圣三年(1025年)三月,宋仁宗就“召辅臣于崇政殿西庑,观孙奭讲《曲礼》”[3]2132。从《曲礼》进讲开始至天圣五年(1027年)十月,“以讲《礼记》彻,燕近臣于崇政殿”[4]2452,共计用时两年多,而《中庸》必在讲读之列,否则就很难理解宋仁宗单独从《礼记》中择取《中庸》以赐新及第进士,并以之为常例的行为。这一切应源自儒臣讲读及宋仁宗对《中庸》思想价值及修己治人之道的高度认同。
治平二年(1065年),侍讲司马光以《中庸》学、问、思、辨之语,劝诫宋英宗在经筵学习时要多加询访、诘问,以裨圣德。熙宁元年(1068年),宋神宗召王珪、范镇等讲《礼记》。宋哲宗元祐四年(1089年),文彦博请哲宗依例科场给赐“臣僚《儒行》《中庸》篇”[4]10448,以警策士行。元祐八年(1093年),经筵《礼记》讲毕。可见,终宋哲宗一朝《中庸》也是其经筵学习的重要内容。宋孝宗乾道年间,“因讲《礼记》,首尾两年”,中书舍人梁克家请“如元祐中范祖禹申请故事,或许择诸篇最要切者,如《王制》《学记》《中庸》《大学》之类,先次进讲,庶几有补圣德万分之一”[3]2891,被获准。隆兴元年(1163年),“起居郎胡铨兼侍讲,讲《礼记》”[3]3196。淳熙四年(1177年),宋孝宗幸太学,曰:“《礼记·中庸篇》言‘凡为天下国家有九经’,最关治道。”[5]3877命经筵官进讲。淳熙九年(1182年),朱熹“将《大学章句》《中庸章句》《论语集注》《孟子集注》集为一编,刊刻于婺州,是为《四书集注》,经学史上‘四书’之名始于此”[6]731。至此,《中庸》成为“四书”之一,而其地位的最终确立及“四书”得到官方推崇,则在宋理宗时才得以完成。
宝庆元年(1225年),“太学正徐介进对,论《中庸》谨独之旨”[5]4446,宋理宗深有体会曰:“此是以敬存心,不愧屋漏之意。”[5]4446宝庆三年(1227年),宋理宗下诏称赞朱熹所“集注《大学》《论语》《孟子》《中庸》,发挥圣贤蕴奥,有补治道”[7]879-880。并对其子朱在曰:“先卿《中庸序》言之甚详,朕读之不释手,恨不与之同时也。”[7]880可见宋理宗对朱熹学识的赞许及对《中庸》等“四书”经典的认同。端平元年(1234年),真德秀为引导宋理宗穷理正心以成治道,进呈了自己倾十年心力而作的“帝王之学”的典范著作《大学衍义》。该书“因《大学》之条目,附之‘六经’《论》《孟》《中庸》等经史,纂集为书”,成为宋理宗“朝夕观览”之作。此外,该书选取《中庸》首章、中庸、中和、自明诚、自诚明、五达德、三达道、道不可须臾离等章节经文,汇聚周敦颐、程颢、程颐、朱熹、吕大临等先儒论述,列入《大学衍义》各纲目之下,多次在经筵被进讲⑤。据真德秀《讲筵进读大学章句手记》记载,其进读《大学》忿懥章时,曾引《中庸》“中”“和”之言诠释中节、性情、体用等问题。后又向理宗进读《大学衍义》“九经章”,又读《中庸》至圣章等。《中庸》等“四书”经典在经筵的进呈与讲读,必然对宋理宗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不仅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得到表彰,而且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朱熹等大儒均得以从祀孔庙⑥,从而奠定了“四书学”的官学地位,程朱理学成为了宋代的“正学”。
可见,从邢昺为宋真宗讲《中庸》,到宋仁宗朝以之赐新及第进士,再到宋理宗朝“四书学”地位的确立,《中庸》终宋一朝,均在经筵不断地被进讲,成为帝王汲取修身立德智慧,提升治国理政能力的重要思想源泉。
二、《中庸》诠释主旨与帝王修己治人
由于年代久远、典籍散佚的原因,《中庸》经筵讲义现存寥寥无几,但我们从真德秀《大学衍义》与《经筵讲义》中有关《中庸》经义的阐发,以及《宋朝诸臣奏议》之“君道”与“帝学”中汇集的士大夫们运用《中庸》思想,劝诫人君修己治人等奏札⑦,依然可以管窥宋代士大夫与帝王对《中庸》思想资源的挖掘与运用。
(一)“凡为天下国家有九经”成为士大夫与帝王最为关切的主题
通过对《中庸》进讲情况的梳理,可以发现“凡为天下国家有九经”成为了士大夫与帝王最为关切的主题。其间,既有士大夫主动向帝王进讲“九经章”的,如邢昺、真德秀等,也有帝王要求士大夫进读的,如宋仁宗、宋孝宗等。由于《中庸》“九经章”勾勒了从修身到尊贤、亲亲,再到体恤、亲爱臣民乃至于柔远人、怀诸侯等平治天下的路径与纲目,为士大夫以儒家价值理想引导、教化帝王提供了诠释空间,同时又为君德成就与治道的实现奠定了理论基础与操作方法。
如真德秀在《大学衍义》中不仅将《中庸》“九经章”列入“帝王为治之序”,而且将其思想渊源上溯至上古时代,指出《尚书·皋陶谟》所言“慎厥身修,思永。惇叙九族,庶明励翼。迩可远,在兹”[8]11,乃是“九经之序”之“所祖”,从而提升了《中庸》在经学史与儒学史上的地位。此外,真德秀还汇聚了《中庸章句》《中庸或问》中关于“九经之序”的阐发与议论,指出“修身”乃是“九经之本”。只有修身立道,为民表率,方可推之家国天下。他指出“凡此九经,其事不同,然总其实不出乎修身、尊贤、亲亲而已”。所谓的“敬大臣,体群臣”,是“自尊贤之等而推之也”[8]18;“子庶民,来百工,柔远人,怀诸侯”,则是“自亲亲之杀而推之也”[8]18;而尊贤亲亲则是“修身之至”,从而凸显了“修身”在“九经之序”中的首要地位,勾勒了由“内圣”而至“外王”的儒家王道理想实现的路径与次第,所以真德秀赞曰:“九经之说,朱熹尽之矣。”[8]20并将“九经章”要旨归之于“一”,而以“诚”“敬”贯穿始终,则《大学》之“意诚、心正在其中矣”[8]20,从而贯通了《中庸》与《大学》的要义。可见,《中庸》“九经章”勾勒了帝王成君德立圣治,由内圣而外王的修己治人的方向与理路,是士大夫与帝王共同关注的思想资源与治国理念。
(二)“道德性命之说”成为帝王修身立德的思想源泉
为应对佛道思想的冲击,重振五代十国败坏的人心世道与社会秩序,儒学复兴的当务之急就是建构一套精密的心性道德理论,为世人安身立命提供思想与理论支撑,《中庸》的道德性命之说适应了时代的这种需求。
北宋陈襄明确提出“《中庸》者,治性之书”[9]第50 册,217,较系统地阐发命、道、性、情、形、气、中、庸、和、诚、善、恶等问题,开启了宋代理学体系建构的核心话题⑧。同时他还充分运用《中庸》的思想引导帝王修身立德。如其《上宋神宗论诚明之学》曰:“帝王之德,莫大于务学,学莫大于根诚明之性而蹈乎中庸之德。”[10]45希望宋神宗能够以诚立善,以明致道,守中庸之常德,成就君德帝业,并认为如此“三者立,天下之能事毕矣”[10]45。又其《上神宗论人君在知道得贤务修法度》指出,人君治天下首务在于明晰性情、邪正、天道、人伪之分,“养心治性,择乎中庸”,“进诚明之学”以“知至道”之要,要求君主与贤者“日与讲求性命之理、道德之源,养而充之”,然后任贤使能,修明法度,如此君臣“相与共济”“立民之极”,则可成“尧舜之举”[10]17。刘述在《上神宗五事》中指出:“帝王接物也,以至诚为先,权术不足任也。”[10]9相对于帝王之术而言,刘述认为帝王修至诚之德才是更为根本的。李常在《上神宗论修身配天始于至诚无息》中说:“昔者子思论为天下国家有九经,所以行之者,修身而已……其修身之叙,亦必始于至诚无息,而极乎高明,上配天德。”[10]18-19劝勉人君欲成就尧舜之德业事功,当以“至诚”修身为先。孙觉上《上神宗论人主有高世之资求治之意在成之以学》奏札,认为人主之学,当“深造于道德性命之际,极高明而道中庸”,方可实现“度越汉、唐而比隆于三代矣”[10]44的治世理想。可见,《中庸》道德性命之说是帝王学为尧舜、修身立德的重要思想资源。
真德秀《大学衍义》是为成就君德治道,建构其理想的“帝王之学”而作。为引导帝王格物致知以正心修身,真德秀选取《中庸》首章“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的经文,引朱熹之言,阐发了人人皆有的天赋仁义礼智信之性“无一不本之天而备于我”[8]73,引导宋理宗明“天理人心之善”,并以之为“人君致知之首”,进而指出只有“知己性之善”“知人性之善”,方可知“我”与“人”皆可以为尧舜,从而治己治人,使君为尧舜之君,民为尧舜之民,达到尧舜之治。同时,他还择取《中庸》“三年之丧”的思想,阐明父母之丧是人人均应遵守的人伦之本,引导人君恪守“天理人伦之正”,爱敬事亲,身为表率,“躬行于上”而“德教自形于下”[8]93,收至孝治天下之效。此外,为了启沃宋神宗成就修德爱民之实心实事,真德秀选取了《中庸》诚者与诚之者、自诚明与自明诚、至诚与致曲、五达道与三达德等章节,指出“诚”乃真实无妄的“天理之本然”,“致诚”之本在“尽己之性而已”,圣人“可学而至”[8]194。劝诫宋理宗“为君必尽君道”[8]196,行君臣、父子等五伦之道,成仁、智、勇之德,则可修齐治平,进而参天地赞化育。可见,《中庸》为士大夫贯通天人、性命、道德以引导帝王修身爱民、学为圣人提供了理论依据与价值源泉。
(三)“执中以致和”的中道思想成为帝王为治立政的根本原则
真德秀认为“人君以一身履至尊之位”,必“有天下之绝德”,立“至极之标准于天下”,而后“卓然有以立乎天下之至中”,所以作“亿兆之父母,而为天下之王”[8]174。那么,人君修身立政以致极的标准与大本是什么呢?那就是“尧舜禹汤数圣相传”的“惟一中道”[8]169。真德秀继承与发扬了程颐、朱熹的中道思想,认为人君为治天下当“执中”以“致和”,育万民而参天地。所谓“中”即“不偏不倚、无过不及”的“天理之当然”与“天下之大本”,是“天命之性”,为“道之体”。“无所偏倚”描绘的是喜怒哀乐未发之时的“在中”状态,“无过不及”指的是“发而皆得其当”、得其“和”的效用,为“著情之正”的“道之用”[8]184。“中”与“和”的关系是“此为彼体,彼为此用”的体用关系,执“中”以致“和”,得“和”以显“中”,人君当“深体力行之”,以收“正心”以正朝廷、百官、万民之效。
同时“中”又不是固定不变的,朱熹曰:“盖中无定体,随时而在是,乃平常之理也。”[8]186程颐举例曰:“一厅则厅之中为中,一家则厅非中而堂为中,一国则堂非中而国之中为中。”[8]186又如“初寒时则薄裘为中,如盛寒而用初寒之裘则非中也”[8]186等。“中”随着空间、时间或事情的变化而变化,执“中”以致“和”需要因时因地而采取不同的策略,所以说“欲知中庸无如权。权须是时而为中”[8]186,“知中则知权,不知权则是不知中也”[8]187。人君应“知中”而又“知权”,把握好“中”与“权”的关系,应对万物、治国理政。所谓“权以中行,中因权立”,将原则性与灵活性高度统一,“随时以取中,因时而执中”,进而致“中”、致“和”。这既是人君尧舜等圣圣相传“制治”之“准的”,人君“执中”之大本,又是“吾道源流”之正学,“范民”立政之轨范,“其体则极天理之正”,“其用则酌时措之宜”[8]170。“中道”思想蕴含了先哲们治国理政的智慧,成为历代帝王们为治立政的根本原则与重要尺度。
三、《中庸》诠释的特点
由于“天子之学,与凡庶不同。夫分文析字,考治章句,此世之儒者以希禄利取科级耳,非人主所当学也。人主之所当学者,观古圣人之所用心,论历代帝王所以兴亡治乱之迹,求立政立事之要,讲爱民利物之术,自然日就月将,德及天下”[10]24。经筵讲学的对象是贵为天下至尊的天子,需要围绕着国家立政立事之要,挖掘历史兴衰治乱存亡之迹,讲明古代圣人爱民利物的道理与方法,切不可像普通学子与儒者那样分章析句以求取功名利禄。因而在诠释经义时,经筵官往往联系帝王为学为德为治的切要处,选取经文,发挥义理,力求主旨明确,说理透彻,有的放矢,指陈时事,劝谏人君。
(一)经文选取,主旨明确,修己治人
无论是陈襄、刘述、李常、孙觉、程颢、吕公著等运用《中庸》思想所上奏札,还是真德秀经筵进讲《中庸》,他们均是紧密围绕着人君修己治人的主旨,择取经文,诠释经义,所以《中庸》“九经章”成为了士大夫为帝王讲解修己治人之道最重要、也是进讲次数最多的篇章。又如《中庸》首章,既是全篇的纲领,又是性命道德之说的源泉。真德秀为建构其“帝王之学”的理论架构,并没有按照《中庸》首章经文的原有结构与次序依次阐发,而是将其经文根据诠释主旨的需要,分拆列入《大学衍义》“格物致知之要”与“诚意正心之要”不同纲目下的细目。如将“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8]72的经文列入“明道术”目下的“天理人心之善”;“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故君子慎其独也”[8]472列入“崇敬畏”目下的“操存省察之功”;“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8]183列入“明道术”之“吾道源流之正”。从各个不同的侧面与角度,阐述帝王正心修身的经义要旨。诸如此类,不一而足。可见,在经筵讲学中,经筵官选取哪部经典的哪段经文予以讲解与阐发,均是为君德成就与国家治理服务的,有其鲜明的针对性与目的性。
(二)经义阐发,反复开陈,说理透彻
关于经筵讲经的特点与方式,朱熹说得很透彻:“大抵解经固要简约。若告人主,须有反复开导推说处,使人主自警省。盖人主不比学者,可以令他去思量。”[11]2576对于日理万机的君主而言,经筵官应逻辑清晰地将经文中所蕴含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要旨,反复铺陈阐发,务必透彻、清晰、明白,警醒君主切身力行。如陈襄讲人君至道之要“在乎养心治性,择乎中庸而已”,通过对命、性、中、情、欲、正、邪等关系的梳理,指出人皆有天之所命的仁义礼智信之“五善”,然其一旦“感物而动”则为情,情“有邪有正”,因此必须择善固执,通过博学、尽心、明善、持志、养气、充体等方式进“诚明之学”,从而使“五善”“七情”皆得其正,君王如能养心治性“莫不与天下共之”,“必求天下之贤者而任之”,则可君臣“相与共济”以“定民之志而立民之极”[10]16,天下自然不言而化以出治道。通过一步一步剖析阐发,陈襄清晰透彻地讲明了人君养心治性的可能性与必要性,及修己治人的方法,以此勉励人君成君德出治道。又如真德秀在进讲《中庸》“九经章”时,不仅阐释了修身为九经之本,而且指出朱熹“内外交养,而动静不违”的要语“至为精切”,将其要义归结为一个“敬”字,言简意赅地阐明了人君修身为治的切入点。而真德秀对《中庸》“诚”的经文选取及阐释,不仅揭示了“诚”的内涵是“真实无妄”的“天理之本然”,圣人“得诚之名”,常人因其私欲须择善固执以诚之,而且指明“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此诚之目”,明示为学修身的途径与方法,最后之落脚处则在于劝诫人君将修德爱民之“实心”,落到治国理政的实际处,以实德成实政。
(三)有的放矢,指陈时政,劝谏君王
经筵不仅是帝王们接受儒家文化教育之地,而且为士大夫们“得君行道”,建言朝廷时政,参政议政提供了重要渠道。因而在儒家经典解读与经义阐释的背后,往往寄寓了士大夫们匡正时政、致君尧舜的政治理想[12]60。据《玉海》载,邢昺在为宋真宗讲经时,经常“据传疏敷引之外,多引时事为喻,深被嘉奖”[2]516。真德秀在进讲《中庸》“九经章”时,特重“续绝世,举废国,为怀诸侯之首”经义的阐发,意在劝诫宋神宗“重骨肉之恩”,为功臣立后。为增强劝说的信服力,真德秀首先引用孔子《尧曰》篇之言,将《中庸》“续绝世,举废国”之意上溯至《尚书》,将
其定位为“自昔帝王相传之法也”,认为“《中庸》之言,盖祖乎此”[9]第313 册,290,从而增强其言说的权威性。接着历数春秋时齐桓公存三亡国的典故;汉成帝感杜业之言,“复绍萧何之世”并“增曹参、周勃之后”的“美事”;唐德宗念李怀光之“前功”为之立后的仁德;宋朝“每大赦令,辄取昭宪太后子孙,或及赵普之徒”等生动可感的故事,增强论说的感染力与说服力,进而针对南宋外有强敌虎视眈眈,内则吏治腐败、民不聊生的现实,提出“当此兵事方兴之时,谓宜访问,加以存录,至于骨肉之恩,析而不殊,尤仁圣所宜哀恻也。故因《九经》之义推而及之,以赞陛下矜恤之仁云”[9]第313 册,291的建议。希望宋理宗能够于国家存亡治乱之际,普施仁义恩德,抚恤功臣之后,凝聚人心,可谓借经义以阐时事,积极为人君出谋划策,具有强烈的现实关怀。进读完毕后,真德秀进而奏云:“大抵续人之祀者乃盛德事,天之所予也;绝人之祀者非盛德事,天之所恶也。”[9]第313 册,291将“续绝世”之意,上升到“天”之好恶的高度,从而收到了经筵进讲之效,“上意亦觉悚动,退而李正言甚称开陈之善,谓其言切而不露也”[9]第313 册,291。宋理宗后来对朱熹、程颢、程颐等道学人物的表彰与对其后人的嘉奖,与真德秀为代表的士大夫不断地劝谏、上奏不无关系。
结 语
《中庸》从《礼记》中独立出来单独成“篇”到成为“四书”之一,经历了一个在经筵不断被进讲及向最高层传播的过程,尤其是宋仁宗时以《中庸》赐新及第进士,与宋理宗对“四书”的表彰,对《中庸》地位的提升起到了重要作用。为实现秩序重建与儒学复兴的重任,经筵官们充分挖掘与运用《中庸》“凡为天下国家有九经”“道德性命之说”“执中以致和”的中道思想,采取切近人君实际选取经文,围绕着人君修己治人的主旨,阐发经义,反复开陈,有的放矢,指陈时政,劝诫君王,从而引导帝王按照儒家的价值理想与思想观念,修身立德,治国理政,学为尧舜,进而加深帝王对《中庸》的认同与理解,使之获得了官方的认可与推崇。同时在君主制国家,“人君一身实天下国家之本”[8]11,其言行举止皆影响着天下之风向。《中庸》成为帝王经筵学习与经筵官进讲的重要篇章,无疑提升了《中庸》在士大夫及百姓心目中的分量,有利于推动《中庸》官学化、社会化与普及化,进而奠定了其在宋代学术思想、人心世道与国家治理中的影响力。《中庸》经筵进讲及帝王对其思想价值的认同与理解,既是宋代《中庸》地位提升的关键性推动力量,又是研究宋代《中庸》学兴盛发展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呈现了学术、思想、政治与社会之间的互动。
注释
①陈寅恪在《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报告》中指出:“北宋之智圆提倡《中庸》,甚至以僧徒而号‘中庸子’,并自为传以述其义。其年代犹在司马君实作《中庸广义》之前,似亦于宋代新儒家为先觉。”参见陈寅恪:《陈寅恪集·金明馆丛稿二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284 页。②对宋代《中庸》学进行系统研究的主要有:王晓薇:《宋代〈中庸〉学研究》,河北大学2005年博士学位论文;郑熊:《宋儒对〈中庸〉的研究》,西北大学2007年博士学位论文;王晓朴:《南宋理学视阈下的〈中庸〉思想研究》,河北大学2015年博士学位论文等。③经筵进讲是儒家士大夫向帝王讲解经史、传播儒学思想、提升帝王道德修养与治国理政能力的讲学与教育活动,是北宋经筵制度完善的产物。翰林侍讲学士、翰林侍读学士、侍讲、侍读、崇政殿说书、天章阁侍讲等统称为经筵官。④参见王琦:《学术与政治的互动——以真德秀与徐元杰经筵讲读为例》,《湖南大学学报》2021年第1 期。⑤据真德秀《大学衍义》中《中书门下省时政记房申状》记载:“于今月十四日轮当进读《大学章句》。既毕,忽蒙圣训:‘向所进《衍义》之书,便合就今日进读。’”可知,真德秀在经筵进读朱熹《大学章句》的时候,曾经应宋理宗的要求进读《大学衍义》,宋理宗亲口承认“卿所进《大学衍义》之书,有补治道,朕朝夕观览”,经常翻阅、学习真德秀进呈的《大学衍义》。参见真德秀:《大学衍义》,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7 页。⑥据陈邦瞻《宋史纪事本末》卷八〇记载,淳祐元年(1241年),宋理宗下诏曰:“朕惟孔子之道,自孟轲后不得其传,至我朝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真见实践,深探圣域,千载绝学,始有指归。中兴以来,又得朱熹,精思明辨,折衷融会,使《大学》《论》《孟》《中庸》之旨本末洞彻,孔子之道益以大明于世。朕每观五臣论著,启沃良多。今视学有日,其令学官列诸从祀,以副朕崇奖儒先之意。”参见陈邦瞻:《宋史纪事本末》,中华书局2015年版,第880 页。⑦赵汝愚所编《宋朝诸臣奏议》中收录了陈襄的《上神宗论人君在知道得贤务修法度》《上神宗论诚明之学》、程颢的《上神宗论君道之大在稽古正学》、吕公著的《上神宗论人君在至诚至仁》、刘述的《上神宗五事》、李常的《上神宗论修身配天始于至诚无息》等篇目,均是对《中庸》思想的发挥与运用。⑧参见陈重:《简论陈襄〈中庸讲义〉的思想内涵》,《浙江学刊》,2013年第2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