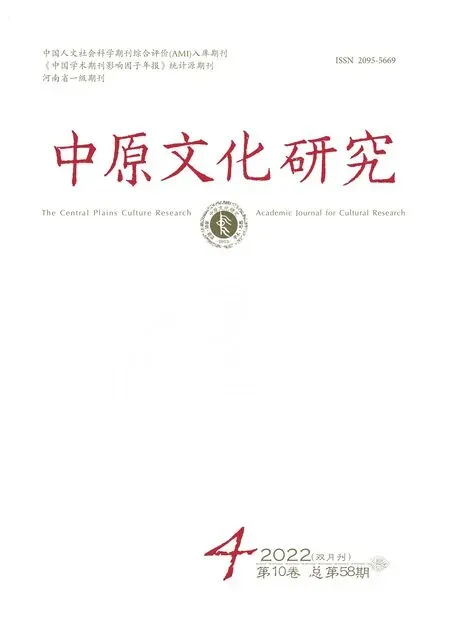秦汉时代大禹传说与中国认同的巩固及拓展
2022-02-08崔建华
崔建华
顾颉刚曾说:“战国、秦、汉之间,造成了两个大偶像:种族的偶像是黄帝,疆域的偶像是禹。这是使中国之所以为中国的;这是使中国人之所以为中国人的。二千余年来,中国的种族和疆域所以没有多大的变化,就因这两个大偶像已规定了一个型式。”[1]141如此说来,黄帝与大禹便是战国秦汉时期中国认同①得以实现的重要政治符号。但是作为“疆域的偶像”的大禹,其形象究竟以怎样的具体路径而使中国认同得以实现,仍是一个有待深入讨论的问题②。本文拟以大禹传说为重点,考察这一文化资源对秦汉时代中国认同的影响,力图展示大禹传说促进中国认同的线索,不当之处,敬祈方家指正。
一、《禹贡》与秦汉王朝对中国的区域控制
战国时代列强争雄,直观地看,是对兼并战争主导权的争夺,而实质上也是为了回答一个重大的时代之问,即谁能代表中国。在此背景下,遂有《禹贡》。作为一篇托名于禹的文献,《禹贡》所载其人其事多属想象,但造作此种想象的主体,以及引发此种想象的历史背景,则是读史者应当关注的。史念海指出,该书“应该是战国时期魏国人著作的”,“是在魏国霸业基础上设想出来大一统事业的宏图”,其根本目的“当然不是为了称颂夏禹的功德,而是为了扶持梁惠王的霸业”[2]392,407,413。从徐州相王的事实来看,文化的武器最终未能使梁惠王成为霸主,他不得不与齐王平分秋色。不过,《禹贡》的影响并没有因为此次致用的挫折而告终结,该书对社会的一大影响便是九州观念的进一步普及。
然而,值得关注的是,秦统一之后,在隆重的政治仪式中却不使用“九州”的概念。秦始皇二十八年(公元前219年)泰山刻石曰“初并天下”“既平天下”,琅邪刻石曰“普天之下”“日月所照,舟舆所载”“临察四方”“存定四极”“六合之内”“人迹所至”。秦始皇二十九年(公元前218年)之罘刻石曰“周定四极”“经纬天下”“宇县之中”“振动四极”“阐并天下”“经理宇内”。秦始皇三十二年(公元前215年)碣石刻石曰“天下咸抚”。秦始皇三十七年(公元前210年)会稽刻石曰“平一宇内”“亲巡天下”“六合之中”“天下承风”[3]243-262。可见,在秦王朝的政治话语中,“天下”一词使用频率最高,而用来指代天下的还有“四极”“六合”“宇内”“四方”等多种概念,唯独不见“九州”一词,这意味着《禹贡》对秦王朝政治生活的影响有限。
对于秦王朝而言,影响其重大政治决策的因素在现实与历史两端。比如在讨论区域管控模式时,主张分封的一派说:“诸侯初破,燕、齐、荆地远,不为置王,毋以填之。请立诸子。”这便是从现实需要出发,主张施行周朝旧制。而反对分封的廷尉李斯则说:“周文武所封子弟同姓甚众,然后属疏远,相攻击如仇雠,诸侯更相诛伐,周天子弗能禁止。今海内赖陛下神灵一统,皆为郡县,诸子功臣以公赋税重赏赐之,甚足易制。天下无异意,则安宁之术也。置诸侯不便。”言语中既反思周代历史,又正面考虑了秦国长期以来政治实践的既有效果。秦始皇作为终极决策人,面对分封制与郡县制的争执,他说:“天下共苦战斗不休,以有侯王。赖宗庙,天下初定,又复立国,是树兵也,而求其宁息,岂不难哉!廷尉议是。”[3]238-239他的决策也是建立在历史反思之基础上的。这样的决策思路,与秦国法后王、重实效的法家意识形态无疑是相一致的,而大禹作为上古圣王,事迹虽盛而难验,自然难以成为秦朝政治效法的对象。明了这一点,《禹贡》九州的天下模式未能进入秦代政治话语体系当中,也就不难理解了。
相比于秦朝施政对历史经验与现实情境的关注,汉王朝在制定政策时,则积极发掘想象类历史的价值。相关研究表明,汉初很可能已遵循《禹贡》所提供的九州地理架构,施行州制以控驭天下。《通典》卷三二《职官十四》载:“秦置监察御史。汉兴省之。至惠帝三年,又遣御史监三辅郡,察词讼,所察之事凡九条,监者二岁更之。……文帝十三年,以御史不奉法,下失其职,乃遣丞相史出刺并督监察御史。”[4]884关于“丞相史出刺”,东汉卫宏《汉旧仪》曰:“丞相初置,吏员十五人,皆六百石,分为东、西曹。东曹九人,出督州为刺史。”[5]36辛德勇据这两则史料指出:“丞相史出刺诸州,虽然文帝十三年始见诸记载,但汉代存在‘州’的区划,却应当在此之前,如若不然,朝廷委派的丞相史则无由按州派遣。”在推断州制于汉文帝十三年(公元前167年)之前即已存在的基础上,其还指出:“出刺诸州的丞相史,因设有九名,分头外出,所以,其各自分担的‘州’,很可能是《禹贡》的九州。”[6]101若此,《禹贡》就是汉帝国确定统治地方策略时的灵感来源。
《禹贡》的政治影响不仅局限于传统意义的华夏控制区,汉王朝还利用《禹贡》来配合疆域的进一步拓展。西汉前期,《禹贡》所见“弱水”“昆仑”“流沙”“三危”等地名,原本缺乏确切的地理指向,人们只是大体感觉到,这些地方位于中国的边缘。但汉武帝时代设置河西四郡后,这些地名的定位日益明确。《汉书·地理志》可见金城郡临羌县有“弱水、昆仑山祠”,敦煌郡广至县有“昆仑障”。张掖郡居延县条载:“居延泽在东北,古文以为流沙。”[7]1611-1614《禹贡山水泽地所在》载:“三危山在炖煌县南。”[8]954此外,随着对河湟地区羌人的征服,《禹贡》所见“积石”“析支”“西倾”等地名也有了比较明确的方位。对于汉帝国将《禹贡》地名安插于新辟疆域的做法,有学者作出如是分析:“对于汉帝国来说,以《禹贡》地名命名新拓边疆,三危、弱水这些新山川便分享了经学知识体系的合法性,即当人们谈论起它们时,它们不会被视作新开辟领土,而是被视作自三代以来就属于华夏政权的上古山川。”[9]也就是说,只要搬出《禹贡》来,汉武帝以来开疆拓土的性质便可以由以力为雄的军事征服,转变为对固有领土权益的坚守或兑现。
汉王朝援引《禹贡》以加强区域控制,这个方针思路并非突发奇想,其离不开禹画九州观念在社会层面的广泛影响。既然机械地法后王、重实效的施政路径并未使秦朝长治久安,继起的汉王朝在反思秦政后,重视发掘群体想象之历史对国家施政的积极效用,便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当然,对于政治而言,《禹贡》只是一个辅助施政的文化工具。不同的历史阶段出于特定的现实需要,区域管控并不会严格遵循《禹贡》。比如王莽复古,重《周礼》《诗经》等经典,于是便有据国风分部的做法,庸部牧之类即此[10],此时的《禹贡》显然相对边缘化了。不过,到东汉末年,《禹贡》再次成为区划更革的依据。建安十八年(213年),“诏书并十四州,复为九州”,紧接着,曹操受封魏公,以冀州十郡为国。值得注意的是,河东、河内二郡在传统上由司隶校尉监察,这次亦被划入冀州,成为魏公封地。可见,重行九州之制,颇有推动汉魏禅代的意图。在这个事件中,表面上看,《禹贡》作为一种经典,是消解汉王朝政治权威的元素,助长了政治裂变。然而,亦应看到事情的另一面,《禹贡》州制提升了曹氏的政治威望,其不仅帮助曹操扩大了封地,更为重要的是,其使“九州”的天下模式在这个时期得以凸显。曹操受封魏公及魏王时,汉献帝策文中皆无“九州”概念[11]37-39,但是当曹丕受禅时,汉献帝在诏书中谈及董卓之乱,特意说此乱“遂使九州幅裂,强敌虎争,华夏鼎沸,蝮蛇塞路”,而曹操则“清定区夏,保乂皇家”[11]67,平定九州的功业成为了曹魏代汉的合法性所在。从这个角度来说,《禹贡》有时候是推动改朝换代的文化工具,据有九州即有资格替代汉王朝代表中国。
二、从禹系方术看秦汉时代中国区域文化的融合
春秋战国时代,原本依靠宗法制度维系的华夏共同体,分裂为多个地缘性政治实体。长期的割据状态,致使各个政治体内形成了较为顽固的国别认同。因此,区域文化的融合是战国秦汉时代的重大历史课题。
秦人作为兼并战争的主导者,在较早的时期已于国内开展整齐风俗的事业。《商君书·农战》:“善为国者,其教民也,皆作壹而得官爵。”“作壹,则民不偷营。民不偷营则多力,多力则国强。”[12]20所谓“作壹”,即是对秦国内部的文化整合。然而,当秦国将风俗整合的目标转向新占领区时,却遭遇了挫折。睡虎地秦简可见秦始皇二十年(公元前227年)南郡守腾向属县发布的《语书》,其中说道:“古者,民各有乡俗,其所利及好恶不同,或不便于民,害于邦。是以圣王作为法度,以矫端民心,去其邪避,除其恶俗。”[13]15郡守三令五申的情形表明,楚俗对秦俗的抗拒力量较大。秦统一之后,秦始皇刻石宣称在全天下范围内“专隆教诲”“匡饬异俗”,最终达到了“黔首改化,远迩同度”以及“大治濯俗,天下承风”的治理效果[3]243-262。事实上,这只是一种夸饰的政治宣传。此外,秦王朝全面施行的以吏为师、以法为教的政策,亦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整齐风俗的意味。但由于该政策所体现的“排斥父道、师道而独尊君道、吏道的政治精神”,毕竟只是“片面的深刻”[14]255,最终导致了秦朝的覆亡,并使秦王朝长期蒙受残暴、专制之讥。整体说来,尽管秦人对区域文化的整合并不成功,但不可否认的是,秦统一的进程毕竟使不同区域文化当中的同质因素增加了,托名大禹的方术由秦楚民众共享,就是一个表征。
有学者指出:“巫觋活动,数术之学,在秦代以及前后临近的历史时期曾经有十分广泛的社会影响。当时,生老病死,衣食住行,处处都可以看到这种文化形式的作用。”而日书作为当时“选择时日吉凶的数术书”[15]2,在民间影响很广泛。日书当中不乏假托大禹的名目,比如“禹之离日”。据湖北云梦睡虎地秦简《日书》甲种《艮山》,在离日“不可以家女、取妇及入人民畜生,唯利以分异”,离日亦“不可以行,行不反”[15]145。还有所谓“禹须臾”。睡虎地秦简《日书》甲种有两篇《禹须臾》,其一曰:“戊己丙丁庚辛旦行,有二喜。甲乙壬癸丙丁日中行,有五喜。庚辛戊己壬癸时行,有七喜。壬癸庚辛甲乙夕行,有九喜。”刘乐贤认为:“这种以大禹名字命名的须臾术似乎可以理解为一种让人能够快速判断行事吉凶的方法。”[16]165另一篇《禹须臾》涉及出行时间的有“莫市以行”“日中以行”“莫食以行”“旦以行”。有学者认为这些描述“都是指短时限内出行。‘须臾’的意义可能与此有关”[15]466。
仅仅通过睡虎地秦简《日书》“禹须臾”的篇题,读者并不知道该篇是对生活中哪一方面的指导,甘肃天水放马滩秦简《日书》甲种则有篇题为“禹须臾行日”者,直接点明是指导人们出行的,但具体的表述方式有所不同。睡虎地秦简《日书》以十个天干名日,而放马滩秦简则以“入月一日”“入月二日”直至“入月卅日”的序数名日[17]85-86。尽管存在这样的差异,但秦楚两地皆流行以“禹须臾”为名的出行择日术,这个事实本身即是区域共性的表现,这个共性至少可以为区域间的文化交融提供一个良好的平台。
实际上,收录《禹须臾》的睡虎地秦简《日书》本身即是不同区域文化融合的产物。林剑鸣认为,睡虎地秦简《日书》“有较多的礼制影响和较浓的神秘色彩,反映了楚文化的特点”,而放马滩秦简则相反,“显得质朴而具体,因此少有礼制、道德以及鬼神的影响,反映了秦文化‘重功利、轻仁义’的特点”[18]70。考虑到两批简牍均写成于秦统一前后,两者存在较大的国别文化差异,其实并不奇怪,毕竟文化融合往往滞后于政治统一。但从积极的方面来看,睡虎地秦简《日书》已表现出非常明显的文化融合的迹象。李学勤指出,睡虎地秦简《日书》甲乙两种“都包括两套建除,一套显然是秦人的建除,一套应属楚人”[19]135-136。李零进一步指出,睡虎地秦简《日书》的建除分楚除、秦除,“楚除包括甲种《除》篇的前一种和乙种首篇复合日名中的第一套名称,同于九店楚简,这是主体;秦除包括甲种《秦除》和乙种《徐(除)》篇,则是附录”[20]320-321。也就是说,睡虎地秦简《日书》以楚文化为主,吸收了一些秦文化的成分。
虽然秦朝短祚,但秦文化的影响并没有就此中断。这一点,在出土的汉代日书材料中有所体现。湖北随州孔家坡汉简被确定为汉景帝时代的文化遗存,其中的《日书》也有一篇《建除》,整理者指出:“内容与睡虎地秦简《日书》甲种的‘秦除’、放马滩秦简《日书》甲种的‘建除’基本相同,可见本篇属于秦的建除。”与秦系建除的沿用相伴的是,孔家坡汉简《日书》未见楚系建除,这与睡虎地秦简《日书》秦、楚建除并行抄录的情形已然不同。由秦代并抄到汉代偏收,这个转变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视为秦文化的延伸。而孔家坡汉简《日书》中的《禹须臾》亦可体现这一点。有一篇文字被整理者命名为《禹须臾行日》,采取了与放马滩秦简相同的序数名日法,整理者指出其内容“与放马滩秦简《日书》甲种的‘禹须臾行日’篇大体相符”[21]149-151。另有一篇为《禹须臾所以见人日》,整理者仍曰:“内容与放马滩秦简《日书》甲种的《禹须臾所以见人日》篇大体相符。”[21]130由此不难感知,孔家坡汉简《日书》是取法于秦文化的择日传统的。有学者说:“汉代《日书》是以秦地的《日书》为基础,并在统一和整合全国文化的过程中形成的。”[22]112虽然此论基于对秦人故地关中地区《日书》的研究而来,不过,从孔家坡汉简的内容来看,这个认识也是可以成立的。
“禹之离日”“禹须臾”等名目在民俗文献当中的存在表明,华夏共同体内部在秦汉时代的融合进程中,大禹是一个高频出现的政治文化符号。日者们之所以在数术论著中“借用‘禹’的名字”,“喜欢把自己的东西同禹挂上钩”,“应当有取其宣传效用的动机”[23]47。因为“传说中的治水英雄大禹是整个社会各个阶层的人都熟知并崇拜的大人物。即使在下层民众中,大禹同样为大家熟知和崇拜”,日者们为了使自己的说辞“为广大的下层群众接受和相信”,“选取大禹来抬高自己的一些东西是很自然的事”[16]465-466。学者所谓“广大的下层群众”,绝不仅局限于某一国,列国术士纷纷以禹名技既体现了诸夏在信仰上的共同点,同时也为区域文化的融合打开了一条路。
三、禹至会稽与秦汉时代东南地区的中国化
大禹传说不仅促成了战国以来以七国版图为限的文化整合,在华夏共同体向周边拓展的过程中,也发挥了显著影响。先秦时期,大禹传说与会稽地区的关联度已很高。一说禹至会稽,如《国语》引孔子曰:“丘闻之:昔禹致群神于会稽之山,防风氏后至,禹杀而戮之,其骨节专车,此为大矣。”[24]202一说禹葬会稽,如《墨子·节葬》:“禹东教乎九夷,道死,葬会稽之山。”[25]184此类说法应当与春秋晚期吴越争霸的历史密切相关。作为活跃于华夏边缘的政治体,为了更好地参与中原列国之间的政治斗争,吴越便借力于大禹这一符号。而通过将禹的事迹附着于会稽,吴越民众强调了“本地人的华夏性”,“借华夏自重”,最终达到了“洗刷蛮夷之名”的效果[26]70。逐鹿中原也便有了更足的底气。
大禹传说在向吴越地区传播的过程中,具有极强的活力。《史记·封禅书》引管仲曰:“禹封泰山,禅会稽。”而对尧、舜诸帝的封禅,管仲或言“禅云云”,或言“禅亭亭”“禅社首”。云云山,《集解》引李奇曰:“在梁父东。”《索隐》引晋灼曰:“山在蒙阴县故城东北,下有云云亭也。”《正义》引《括地志》:“在兖州博城县西南三十里也。”亭亭山,《集解》引徐广曰:“在钜平。”《索隐》引应劭云:“在钜平北十余里。”《括地志》云:“在兖州博城县西南三十里也。”社首,《集解》引应劭曰:“山名,在博县。”又引晋灼曰:“在钜平南三十里。”[3]1361-1362要之,云云、亭亭、社首皆在泰山周边。唯有大禹,封禅地乃在会稽。《史记》明言此说源于管仲,若由此推断管仲的时代已有此说,应当不合逻辑。然而,司马迁应有所本,战国时代托名于管仲的书应是其资料来源。因此,战国时代必已产生了大禹会稽封禅之说。而大禹封禅独与尧舜等圣王不同,其背后的逻辑或许如此:先秦时期的大禹传说与会稽的关联度极高,而这个情形亦为吴越以外的人们所接受,他们在造作大禹封禅故事时,不得不顾及这一点。
对吴越地区盛行的大禹故事,统一之初的秦王朝并没有特别在意。在议立“皇帝”号时,大臣们盛称秦始皇的功业“自上古以来未尝有,五帝所不及”。秦始皇二十八年琅邪刻石又给予其“功盖五帝,泽及牛马”的评价。还说“古之五帝三王”“实不称名”,而始皇帝“昭明宗庙,体道行德,尊号大成”。大量证据表明,在秦统一之初的政治舆论中,五帝三王逊色于始皇帝,并且秦始皇认为他之所以能够“以眇眇之身”而横扫六合,乃是“赖宗庙之灵”[3]236,与五帝三王无干。在这种情况下,舜、禹应当不会成为秦始皇的祭祀对象。但随着秦帝国整齐乡俗事业的深入,睡虎地秦简《语书》所谓“去其邪避,除其恶俗”的做法,绝不会仅限于故楚腹地的南郡。吴越地区作为曾经的楚国边缘,当其转换为秦帝国的边缘,秦王朝的文化统一势必触及此地。对于秦王朝而言,吴越一带的大禹信仰并非“恶俗”,不仅不必去除,反倒可资利用。因为在秦人的群体记忆中,他们的祖先大费曾经“赞禹功”[3]173,祭祀大禹乃是发扬祖先的荣光。更重要的是,凭借对大禹的祭祀,秦始皇至少可以在形式上找到一把沟通秦人与吴越民众情感的钥匙。《史记·秦始皇本纪》载秦始皇最后一次出巡,“上会稽,祭大禹,望于南海,而立石刻颂秦德”[3]260,无疑具有文化统一的历史意义。
虽然秦始皇“祭大禹”之后不久即去世,但大禹传说对于增进华夏共同体的凝聚力,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一方面,汉代人取名常用“禹”字,如汉武帝时有酷吏赵禹,汉武帝托孤重臣霍光之子名霍禹,汉成帝时有丞相张禹。这样的取名风尚意味着,在华夏共同体的核心区内,大禹虽然仍是圣人形象,但已更为亲民,具有进一步民俗化的趋向。另一方面,华夏边缘的吴越地区继续流传着大禹故事。《汉书·地理志》会稽郡山阴县条:“会稽山在南,上有禹冢、禹井。”[7]1591司马彪作东汉《郡国志》对此县仍曰:“上有禹冢。”[27]3488可见,两汉吴越民众延续了对大禹的信仰。不仅普通民众口耳相传,东汉吴越的精英阶层也在以文字的力量,使这种信仰得到确认与强化。《吴越春秋》《越绝书》的写作可为明证,两书堪称大禹故事的集大成者③。这类写作,给传说贴上“春秋”的标签,表现了吴越士人在与帝国核心区展开“历史”类文化资源的竞争时,具有一种不认输不服输的韧劲儿,这种参与竞争的精神状态,无疑折射出了吴越民众融入华夏共同体的积极性与主动性。
个别的时候,由于融入的心态过于急躁,甚至会发生令人颇为诧异的现象。比如,东汉末年,王朗担任会稽太守,“会稽旧祀秦始皇,刻木为像,与夏禹同庙。朗到官,以为无德之君,不应见祀,于是除之”[11]407。众所周知,秦始皇在汉代长期受到激烈批评,但会稽民众对此似乎无感,他们看中了秦始皇哪一点呢?如果注意到会稽的秦始皇祭祀场景以与“夏禹同庙”为特征,那么,可以推断,对秦始皇的祭祀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这个皇帝曾经“上会稽,祭大禹”。也就是说,会稽地区的秦始皇祭祀,实属大禹信仰的衍生品,当地民众很可能认为,祭秦始皇与祭大禹具有相似的效果,皆可增强他们在政治上、文化上的华夏属性。
四、大禹的苗羌行迹与秦汉时代西、南两方的中国化
大禹传说在吴越地区传播的过程中,已渐有自吴越而西之势,这个趋势突出表现于禹征三苗之说。《墨子·非攻下》:“禹亲把天之瑞令,以征有苗。四电诱祗,有神人面鸟身,若瑾以侍,扼矢有苗之祥,苗师大乱,后乃遂几。禹既已克有三苗,焉磨为山川,别物上下,卿制大极,而神民不违,天下乃静,则此禹之所以征有苗也。”[25]147-148墨子持有神论,他笔下的大禹凭借神人护佑,最终攻克三苗。《韩非子·五蠹》则记载了大禹的一种负面形象:“当舜之时,有苗不服,禹将伐之,舜曰:‘不可。上德不厚而行武,非道也。’乃修教三年,执干戚舞,有苗乃服。”[28]445《吕氏春秋·上德》亦曰:“三苗不服,禹请攻之,舜曰:‘以德可也。’行德三年而三苗服。”[29]认为大禹颇有穷兵黩武之嫌,非秉德之人。
至于三苗的活动区域,《史记·孙子吴起列传》载吴起曰:“昔三苗氏左洞庭,右彭蠡,德义不修,禹灭之。”[3]2166相同的文字,还见于《说苑·贵德》[30]97。虽然此说见于汉代典籍,但《史记》《说苑》既将其冠于吴起名下,由两书编纂的特点来看,应有先秦传闻、传记材料作为依据。因此,三苗活动于洞庭、彭蠡之间,先秦社会对三苗的认知已然如此,不待汉兴方有此说。而大禹征三苗之说的流行意味着,战国秦汉的人们普遍相信,大禹的足迹也到达了长江中游一带。
值得注意的是,在西汉晚期编纂的《说苑》当中,大禹故事呈现出集成趋向。除了《贵德》篇载吴起说禹征三苗,《君道》篇曰:“当舜之时,有苗氏不服。其所以不服者,大山在其南,殿山在其北,左洞庭之波,右彭蠡之川,因此险也,所以不服。禹欲伐之,舜不许,曰:‘谕教犹未竭也。’究谕教焉,而有苗氏请服。天下闻之,皆非禹之义,而归舜之德。”[30]5-6大禹尚武,这是沿袭了《韩非子》《吕氏春秋》的说法。《说苑》对禹征三苗故事的集成,自然离不开这一历史背景,即战国秦汉时期长江中游一带中国化的程度越来越深。关于这一点,大禹“苍梧罪己”故事的出现,可以视为重要表征。
《说苑·君道》:“禹出见罪人,下车问而泣之。左右曰:‘夫罪人不顺道,故使然焉,君王何为痛之至于此也?’禹曰:‘尧、舜之人皆以尧、舜之心为心,今寡人为君也,百姓各自以其心为心,是以痛之也。’《书》曰:‘百姓有罪,在予一人。’”[30]8这个故事的创生当然不始于《说苑》,但从始见于《说苑》的情形来看,似乎比禹征三苗故事要晚一些。需要留意的是,《说苑》当中并没有标明大禹罪己的具体地点,然而在后来的传播过程中,这个故事有了具体的发生地。东汉前期,赵晔著《吴越春秋》即谓此事发生于大禹“南到计于苍梧”之时[31]163。而东汉后期的名士陈蕃在劝谏皇帝时,也引此故事曰:“昔禹巡狩苍梧,见市杀人,下车而哭之曰:‘万方有罪,在予一人!’故其兴也勃焉。”[27]2166可见,东汉时代的大禹罪己故事,已经习惯性地与苍梧地区联系在一起。
彭蠡、苍梧相关事迹的生成已透露出这样的趋势,即大禹故事一直在溯江向西,将秦汉帝国的南部、西南部逐步纳入大禹传说的体系。而在帝国的西部,大禹传说正在由西方向西南扩展,似乎对大禹传说的溯江向西形成接应。
《后汉书·西羌传》的开篇部分述戎而不及羌,真正谈到的第一位羌人曰“羌无弋爰剑”。所谓“无弋”,“羌人谓奴为无弋,以爰剑尝为奴隶,故因名之”。而此人的为奴经历据说与秦国有关,“秦厉公时为秦所拘执,以为奴隶”,“后得亡归,而秦人追之急,藏于岩穴中得免。羌人云爰剑初藏穴中,秦人焚之,有景象如虎,为其蔽火,得以不死”[27]2785。有学者认为这段记载“极有可能只是华夏单方面的建构”[32]155,但此说也反映了一个极其重要的历史事实,即羌人的发展与秦国历史紧密关联。秦与戎长期共生的历史,羌与戎在族源上的关系,秦与戎、羌活动区域的毗连关系,都决定着秦国历史对羌人发展的深刻影响。秦人既然学会了借助大禹形象来提高自身的政治地位,与之交往密切的羌人也就可能接触到大禹故事。
目前所见最早言及禹与中国西部地区关系的是《荀子·大略》,该书曰“禹学于西王国”,所谓“西王国”,后世有注家坦承:“未详所说。或曰:大禹生于西羌,西王国,西羌之贤人也。”[33]489西王国是否指西羌?不易确定,注家之说也只是一种联想而已。但有一点似乎可以感觉到,荀子既曰“西王国”,而不曰“秦国”,这个概念与先秦传言的西王母之邦极类,说明荀子脑海中的大禹足迹远至秦国以西,而在这个区域活动的正是羌戎。当时人们既有此一说,那么,由此推论,在秦国的影响下,至迟在战国晚期,大禹传说的西部边界已及于羌戎,应无太大问题。否则的话,汉代社会对大禹与西羌之间特殊关系的传言将成为一种无源的突变。《新语·术事》曰:“文王生于东夷,大禹出于西羌。”[34]43司马迁也说:“夫作事者必于东南,收功实者常于西北。故禹兴于西羌,汤起于亳。”[3]686可见,西汉初期以来即盛传大禹“出于西羌”“兴于西羌”,从文化渐变的角度衡量,这种说法应是“禹学于西王国”之说的具体化。
西汉晚期,来自蜀地的扬雄在作《蜀王本纪》时言之凿凿地说:“禹本汶山郡广柔县人也,生于石纽。”[3]49此说仍不脱西羌范畴,但已将其出生地进一步具体到郡县体制下的某个确切地点。此说何以形成?地名“石纽”当中的那个“石”字,值得关注。
《淮南子·人间训》可见“禹生于石”的说法,与此关联极大的还有启母石的传说。汉武帝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诏曰:“朕用事华山,至于中岳,获驳麃,见夏后启母石。”[7]1190由诏书来看,启母石在嵩山。而汉武帝亲临观石,说明神石生启是民众的普遍信仰。如此一来,西汉时期便存在“禹生于石”和“启生于石”两种说法。然而,上引武帝诏书存在疑问,颜师古指出:“景帝讳启,今此诏云启母,盖史追书之,非当时文。”[7]190此说很有道理,武帝原版诏书绝不会出现“启”字,如果必须指称夏启的话,原文会用“开”字④。但如果真有“开”字的话,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班固作为汉代史家,在抄录诏书时,断无再抄回“启”字的道理。因此,传世《汉书》所见武帝诏书中的“启”字,极有可能是汉代以后妄增的。诏书原本既无“启”亦无“开”,所谓“夏后启母石”,原本只应是“夏后母石”。这样的话,这个传说既可指禹,亦可指启,但指禹的可能性更大。因为《淮南子》言“禹生于石”,这应是当时通行的说法,此其一;其二,夏启有何不世之功,足以令汉武帝为之倾倒?比较而言,如果是大禹的话,那就合理得多。
在明了西汉长期流行“禹生于石”的传说之后,西汉晚期扬雄所谓禹“生于石纽”,很可能源于对“禹生于石”之说的附会。此说后来流传甚广,逐步成为帝国西南隅的蜀地专利。有学者认为,这个专利权的获得对于“汉晋时期居于蜀的华夏知识分子”来说“非常重要”,因为这关系到他们的“乡土认同”[35]231。而这样的乡土认同,其实与吴越地区经由大禹死葬传说而形成的乡土认同异曲同工,潜藏其下的心理诉求在于,积极融入祖述大禹的华夏文化圈。
结 语
胡适曾说,秦代以后,“中国便走上了统一帝国的轨道”。秦汉统一帝国持续四百余年,“在中国民族史上有莫大的重要”,其重要贡献之一便是“养成了一个统一民族的意识。从前只有‘齐人’‘秦人’‘楚人’‘晋人’的意识,到这个时期才有‘中国人’的意识”[36]52。此说显然注意到,衍生于周文化的华夏共同体内部的整合,是“中国人”意识形成的前提条件。而这种内部整合,就战国秦汉历史来看,一方面固然有赖于铁血战争的强力推进,从而造成一种“六王毕,四海一”的政治大一统;但在另一方面,战争有时而止,在长久的和平氛围中,以大禹传说为代表的柔性文化元素,既可以对帝国的区域控制策略有所启发,亦可以使不同区域文化在碰撞中形成更多趋同的内容。这种春风化雨式的文化整合方式,对于巩固“中国人”意识,无疑具有更为持久的积极效果。不仅如此,由于秦汉帝国的统一规模,“并不限于兼并六国”[37],如此一来,对中原文化圈边缘地区的整合,也是秦汉王朝的一个重大历史使命。而禹葬会稽、禹征三苗、禹生西羌诸说的生成及长期传播,则有力地助推了这一恢宏中国的伟业。
注释
①本文所谓“中国认同”,是对应着顾颉刚先生“中国之所以为中国”“中国人之所以为中国人”的表述而使用的,是对顾先生表述的简洁化。②顾颉刚对大禹传说的研究集中于先秦时期,秦汉以来非其关注焦点。参见顾颉刚:《讨论古史答刘胡二先生》,收自《古史辨》(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105-134 页。而王明珂在讨论华夏边缘问题时,对华夏初祖的黄帝关注较多,于吴地则分析吴太伯故事,于朝鲜则关注箕子故事,对大禹故事亦着墨不多。参见王明珂:《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浙江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③文繁不赘引,可参看张觉:《吴越春秋校注》,岳麓书社2006年版,第153-173 页;乐祖谋点校:《越绝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57 页。④《汉书》卷五《景帝纪》颜师古注引荀悦曰:“讳启之字曰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