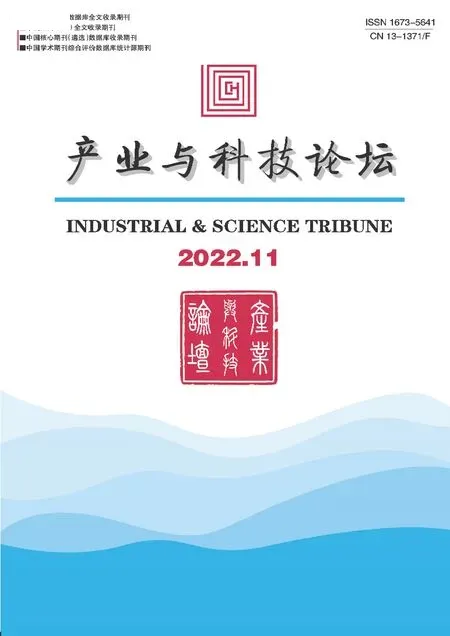认同视域下大学生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培育
2022-02-06□金贵
□金 贵
“认同”一词的英文是identity,又被译作同一性、身份认同。就认同主体来说,认同主要指自我认同与群体认同。在这两种认同中,外在的身份假设与内在人格都很重要。与自我有关的认同,包括了自我身份与人格的确认与表达。与群体有关的认同,包括了群体身份的确认与表达。在上述两种认同中,文化认同与国家认同是主体确认与表达身份的两种基本形式。
显然,在不同的研究视角下,主体身份认同的确认与表达,还是不尽相同的。在心理学领域中,对认同问题的探讨一般会围绕人格问题,探讨人格问题,自然也会探讨到诸如何种认同影响了主体人格的确认与表达这类问题。在社会学及其它领域当中,对认同问题的探讨一般是围绕外在的身份问题,并且突出群体的身份的确认与表达,以及与此相关的文化认同与国家认同。
一、从心理学角度出发探讨大学生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首先,要思考的问题是,在心理学视角下,认同范畴的本质是什么?现在学界认为,认同范畴最早为弗洛伊德所提出,并成为学界广泛瞩目的学术话语。关于弗洛伊德的认同理论,学界的研究也是比较多的。有人认为,弗洛伊德最初谈到认同是病理性的,表现为“癔症”,他在《释梦》中强调的认同是,一种梦的认同。在《哀悼和忧郁》中提出“自恋性认同”,在这里认同是一种普遍的心理过程、被激发的思维方式、一种防御方式,认同与模仿相似,但更接近同化[1]。
在《自我与本我》中[2],弗洛伊德在人格三部论的基础上提到了认同。他认为,“本我”“超我”“自我”三者达到平衡,人才会健康。弗洛伊德的此理论,对理解个人认同也是有帮助的,即个人不仅要认同“本我”,更要体现“超我”的要求,个人认同应具有现实性,既能满足自我的愿望也能达到超我的要求。个人认同的状况取决于,个人对“本我”“超我”及“自我”关系的处理。可见,在费洛伊德看来,认同主要是指自我认同,这种认同,其实也包括了国家认同、文化认同等内涵。
在弗洛伊德之后,对认同理论作出重大贡献的是埃里克森。与弗洛伊德不同的是,埃里克森的认同理论,不仅仅只是一种个体的自我确认与表达,而是更强调自我内部与社会生活之间的关系,于是他提出自我同一性、同一性危机思考方式等。他的《身份认同:青年与危机》是专门探讨身份认同的专著,《童年与社会》《青年路德》《新的身份认同维度》也对认同问题进行阐述。在他那里,认同是一种心理社会的身份认同,是指人格发展的目标,就是追求一种身份认同,这一过程是内在心理和外在实在(社会)相互作用完成的一个连续且进步的过程。身份认同危机则指在青少年期,人格由于各种原因不能得到有效整合,内心自我发生冲突[3]。
总之,在心理学领域中,对于认同的界定一般是从个体人格的角度予以探讨的,个体与人格是理解它的两把钥匙。当然,在心理学当中,社会因素对个体人格的影响,一般会经历内化与外化这两个彼此相连的阶段。
回顾大学生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已有的研究发现,这方面发表的论文与出版的著作也有一些。从已有的心理学方面的研究成果来看,现有的成果,大多体现出埃里克森的研究旨取,即已有的研究并不仅仅只是一个对个体人格的确认与表达,更多的研究强调了自我与社会之间的关系,着力解决如何让大学生养成国民身份,保持同一性。此种国民身份,主要包括了文化与政治两方面的内涵。
这方面代表性的成果有,王娟的《社会思潮与大学生主流意识形态认同》(天津人民出版社,2018);杨建义的《大学生文化认同与价值引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等。
已有研究,揭示出当前一部分大学生存在民族文化认同弱化、理想信念动摇、对主流思想认同不够等认同危机现象。并认为,此种现象对于培育大学生的中华民族认同是有消极作用的。质言之,此种现象对培育大学生的政治认同、文化认同有消极影响,不利于大学生健康人格的形成,不利于大学生中国国民身份的养成。
所以,这方面研究的基本思路就是,强调中华民族历史上就是一个守望相助的共同体,具有丰富的历史文化,并通过加强“五个认同”的教化,使学生增强文化自信,健全文化人格,在政治上、文化上能够培育起国民身份;使学生能够在历史、现实及未来发展规划中坚定自己是一个中国人,必须维护好中华民族是一个共同体的信念与责任。
这方面研究的好处就是能够从学生心理的角度出发探讨问题,能够从个体上升到一般,且具有深邃的历史视野与敏锐的现实政治眼光。但问题是,从个体心理层面来看,不论是国家认同,还是文化认同,还需要解决一些难题。如个体认同了多少?其检验的标准是什么?则是需要心理学科学的数据加以说明与验证的。换言之,现有成果还需要提升的地方,就是需要在心理学方面进行数据积累,并进行专门分析,以研究出当前大学生个体及不同群体间自我人格的特殊性,以及与社会生活之间的关联性。
二、从人类学角度出发探讨大学生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在学术史的梳理过程中还发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即人类学家也很关注认同问题。人类学家们以其参与式观察与深刻的笔触对认同问题,有着独特的见解。
爱德华·泰勒对群体认同问题有独特的见解。他认为,群体之间有着很强的一致性,此种一致性能有力地激励着整个民族团结起来,采用共同的语言、遵守共同的习惯。随着社会的不断向前发展,某些在当时被认为是最重要的观点和行为渐渐地变成一种文化遗留。现代人们,通过文化遗留,可以探求到那些似乎变得不可理解的习俗、观点的文化理解[4]。这些观点对于群体认同,以及自我认同的形成与发展具有启发。
麦克斯·缪勒认为,各个群体的认同具有独特性,其证据在神话、风俗、各民族的语言中。特别是语言,通过对某一词含义及意义的考察可以获得某种认同的流变。尽管每一个群体都有其独特的发展道路,但每一个群体都起源于无限的观念。这样,多样化的群体之间在起源问题上就有了认同的基础[5]。
列维·布留尔考察了原始人的风俗、巫术、语言、算术、语言、疾病及死亡观念,并指出,原始人的思维与现代人有本质的不同,它完全受那些在该社会集体中代代相传的“集体表象”所支配,在个体存在之前“集体表象”就已经存在,并永久存在,它把自己强加于集体中的每一个个体,而支配着“集体表象”的形成及其之间关系的是“互渗律”。布留尔的这种观点,不仅告诉人们原始人的思维特点,其实也启示了他所考察的那些原始人的认同意识特点,即原始人的自我认同及群体认同也是通过“集体表象”与“互渗律”而展开的[6]。
爱弥尔·杜尔凯姆在其图腾研究中认为,图腾不仅仅是一个名,它还是一种刻在身体及物体上的标记。通过杜尔凯姆的图腾其实可以看到,他的认同是通过图腾来表达。图腾有集体图腾、个体图腾及性别图腾。集体图腾其实表达了一种集体认同意识,而个体图腾其实是表达了个体对自然联系的某种认同。对于集体认同问题,他认为认同是一种称为“集体意识”的东西,是一个共同体中不同的个人团结起来的内在凝聚力。某一群体的相似性和共同性特征是建立在与其他群体间存在着差异性的基础之上[7]。
通过上述回顾要看到,人类学家们通过对某人群体长期的观察,运用科学的方法,形成了独特的见解。此种见解对于大学生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研究也是有帮助的。因为,通过对大学生群体长期的观察,运用一系列科学方法,也可以形成独特的看法。要总结的是,现有的运用此种方法,形成比较有代表性的成果,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结合时代精神,研究大学生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1978年以来,中国人民的改革开放实践深刻地改变了中国。改革开放精神、创新精神也就成为中华民族的时代精神,是凝聚中华民族的力量来源之一。在新时代,大学生们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具体表现,又会有所不同。因此,结合时代精神,探讨大学们在不同时代,认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具体形式与做法,成为许多人的选择。
这方面研究成果很多,如李海凤、卢林保的《新时代铸牢大学生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探究》(《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20年01期);王新刚的《新时代大学生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探析》(《中国高等教育》2019年21期);商爱玲的《铸牢大学生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西南政法大学学报》2018年01期);秦世成的《全媒体传播环境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赵汉杰的《当代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创新研究及新媒体路径的实践》(中国书籍出版社,2017)等。
这方面研究的好处是,能够针对现实语境,以人类学参与式观察的立场出发,与时俱进地把凝聚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时代精神融入到大学生的教育当中,这对加强大学生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积极作用。但问题是,大学生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培育,仅仅只依靠单方面的教化是无法实现的。
(二)通过课程改革,加强大学生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高校从事教学与科研的人员,通过自己长期的教学实践与观察,提出课程思政的有效实施,也有利于大学生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培育。因此,通过课程改革,对大学生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进行培育就为学界所关注。
此方面研究成果很多,范春婷、王华敏的《在“纲要”课中铸牢大学生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逻辑理路》(《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20年11期);刘玉的《西藏高校思政课铸牢大学生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探析——以〈马克思主义“五观”教育概论〉为例》(《西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02期)等。
此方面研究的好处就在于充分利用学校理论教育的主战场,对大学生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进行有效培育,使大学生形成“中华民族是一个共同体的意识”。但是,这方面研究没有考虑到社会的复杂性、信息的多元化、全球化的影响,也没有考虑到大学生个体生活的差异性。质言之,大学的课堂教育,是否会对大学生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产生持久影响,需要实践检验。
(三)注重结合少数民族大学生的生活语境,研究少数民族大学生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培育。很多学人,结合少数民族大学生的生活语境,着力研究少数民族大学生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此方面成果很多,如徐柏才的《少数民族大学生的民族认同研究》(人民出版社,2012);郑锦阳、邓淑华的《新时代少数民族大学生“五个认同”的培育》(《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20年22期);冯雪红、张文文的《中华文化认同研究现状及展望》(《贵州民族研究》2020年03期)等。
此类成果的突出特点就是,围绕民族地区、民族地方或散杂居地区少数民族大学生的现状,着力从思想文化、日常生活、政治认同等方面,着力培养少数民族大学生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此类研究突出的价值是,重视对少数民族大学生的思想教化问题,引领少数民族大学生对中华民族的高度认同感,这对培育少数民族大学生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意识极为有利。但问题是,大学生群体具有很强的广泛性,大学生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养成,是一个具有普遍性的问题。
三、从社会学角度出发探讨大学生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在社会学领域,对认同的研究也很重视。吉登斯提出“自我认同”理论,他的“自我认同”理论是对西方个体本位的一种延伸与反思,体现出其对社会因素对个体自我认同作用的塑造作用[8]。在他那里,认同与人的交往活动有关,人存在方式之一是交往,认同发生在交往活动中;认同的核心问题是价值认同问题,是对人的意义感的重新定位和评价的问题。
乔纳森·弗里德曼认为,确立和维持文化认同的条件紧紧地捆系在个人的认同构建方式上。一些类型的认同铭刻或由身体所携带,内在于个人;一些类型的认同是外在于个人,由社会实践形式或人群所采用的象征来标刻。文化认同,指的是给定人群的一组有特征的属性,它不是被实践的,而是内在固有的;不是获得的,而是先赋的。文化认同是特定类型的社会认同的基础[9]。
阿尔弗雷德·格罗塞认为,“集体记忆”在集体——特别是该集体回溯性的身份认同中起到了持久的作用。“集体记忆”的内容多样,它依赖于一个我们称为时代风气的、不太科学的现象。比起消极行动的记忆,积极行动的记忆更容易被提及、接受与保留。“集体记忆”的传递塑造着个体身份的形成,它在每个人所受的影响中占据重要位置[10]。
曼纽尔·卡斯特认为,认同可能有多种,认同都有一个建构的过程,这个过程是否顺利与支配性制度有关,与个体自我的内外与外化是否彻底有关。集体认同大致上决定了自我认同的象征性内容,决定了那些接受或拒绝此认同的人的意义。集体认同捍卫了文化的特殊性,对全球化及世界主义提出挑战[11]。
通过上述社会学的简单讨论,可以发现在西方社会学领域,认同也包括了自我认同与群体认同。群体认同——主要是通过文化认同与集体记忆进行建构的群体认同,对该群体的自我认同的形成具有重大作用。认同的核心问题是价值认同问题。所以,对一个社会学家来说,要塑造一种什么样的文化认同或集体记忆,树立一种什么样的价值观,就显得极为重要,这有利于增加群体一致性。
正如已有研究证明,中华民族是一个共同体,培育大学生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已为社会各界所重视。那么,从社会学的角度考虑,应当如何培养大学生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有三种观点值得注意。
(一)注重从爱国主义养成的角度出发,培育大学生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爱国主义文化是中华民族共有的文化认同,爱国主义信念也是中华民族共有的集体记忆,爱国主义实践是中华民族所有成员共有的行为特征。因此,通过加强大学生们的爱国主义,由此使大学生们自然形成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就成为一种选择。
此方面研究成果也较多。崔健的《国际化视野中大学生爱国主义教育研究》(人民出版社,2020);盛春的《加强青年大学生爱国主义教育》(《红旗文稿》2020年18期);杨静的《加强大学生爱国主义教育》(《中国社会科学报》2020-08-27)等。
这方面研究的好处就是看到,爱国主义能够得到各族各地大学生的普遍认同,是能够唤起大学生中华民族集体意识的一剂良药。但问题是,是从情感层面去加强爱国主义,还是从理性认知、制度规范等层面去加强爱国主义?不同的选择,会有截然不同的结果。如果仅从情感层面出发去探讨,再配合以理性认知,深度唤醒大学生对祖国深深感情,进而去认同中华民族是一个共同体,并不必然在实践行为层面得到实现。这是因为,情感认同、理性认知还没有化为实际行动,爱国主义还需要行为来体现。事实上,爱国主义行为实践,既需要个体的行为自觉,也需要制度规范的保障,但这后一方面的研究,还需要再加强。
(二)从价值观的认同出发,加强大学生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弘扬积极的价值观,特别是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而增加大学生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逐渐地成为许多人的共识。
此方面的成果有:谢玲、孙秀玲的《边疆少数民族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研究》(《北方民族大学学报》2017年01期),郭颖、余梓东的《大学生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研究》(《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20年第22期)等。
这方面的成果好处就是突出了大学生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培育需要在价值层面进行引领。因为,对于大学生来说,形成一种什么样的价值观,不仅对于其个人,而且对于国家及社会都具有重大意义。但问题是,大学生的思想极为活跃,要想让大学生形成一种稳固的符合社会与国家发展要求的价值体系,还需要更加科学的方法,更需要实践加以检验。
(三)注重从文化认同的角度出发,加强大学生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对于大学生群体来说,形成一种什么样的文化认同,对于其形成一种什么类型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也具有积极作用。
此方面的成果,也有很多,如周俊利的《铸牢民族高校大学生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基于文化纽带视角》(《民族学刊》2021年02期);张莉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文化根基与培育机制研究》(《北方民族大学学报》2021年01期);曹庆傲《文化认同视角下铸牢大学生民族共同体意识探究》(《教育评论》2020年03期)等。
现有研究的突出成绩就是突出了文化认同的作用,因为对于一个民族来说,最为持久的内在凝聚力,往往就集中于该民族的文化中。认同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认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认同革命文化,就自然地在文化上建构起共同的集体记忆,这对于培育大学生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极为有利的。但是,这一过程也将是一个持续性的过程,需要人们不断地努力,并努力地推陈出新,如此才会达到预期的目的。
四、结语
总之,从认同理论出发,探讨大学生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培育问题,目前是学界们探讨的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在心理学、人类学及社会学中,认同的概念及表现形式也有所不同。所以,对于大学生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培育来说,就要考虑到各种学科的差别,分别进行研究,以深化人们对大学生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路径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