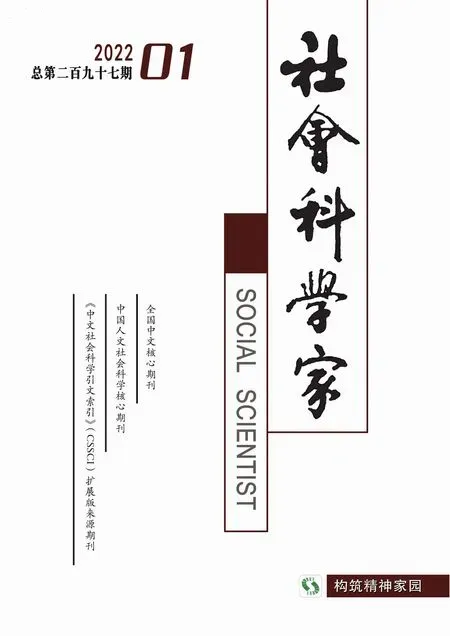城市间性、创意生活与全域美丽的多种可能
——以武夷新区及其旅游业态为个案
2022-02-04林玮
林 玮
(浙江大学 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浙江 杭州 310007)
“推动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是新发展理念的重要内容。党的十八大以来,城镇化进程从只注重物质层面的单维发展,转向了与其他“三化”(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和农业现代化)协同发展的新阶段。从国家层面的表述上看,党的十八大报告还有“加速城镇化进程”的内容,并以之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经济目标”,到党的十九大报告,这一表述就消失了。十九大报告对此前五年的城镇化成绩做出了肯定:“城镇化率年均提高一点二个百分点,八千多万农业转移人口成为城镇居民。”也提出了新的要求,即形成“以城市群为主体构建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镇格局”。
由此,考察党的十九大以来我国城市发展,城市群与中小城市、小城镇的协同关系就变得尤为重要。一方面,城市发展不仅关系到中国经济结构调整方向,关系到户籍改革、土地流转和农民工就业等国计民生的问题,“城市”已经成为人们生活的主要语境;而另一方面,城市发展开始从点状的都市化转向簇群式的发展,“城市群”成为新一轮城镇化的重要内容。也就是说,在物质层面上,原本点状的城市分立开始向带状或片状的区域发展转型,城市与城市之间的物理空间如何开发变得重要起来;在文化层面上,城市与城市之间的相互关系,特别是区(地)域性的文化属性开始受到关注。
这里有一个概念需要略加解释,即“城市间性”(interurbanity)。它至少有两个层面的意义:一是城市研究的关注点要从传统单子化的“一座城市”适度转移至城市与城市之间的物理空间上,即城郊、乡村如何以共同富裕为指向地发展,如“居住在昆山、嘉善,工作在上海市区,用1个小时来市区内上班”。这一层面与已有学者提出的“城市际性”相类似,主要是一种现象描述,且“限于地理空间”[1]。二是城市研究的关注点要从“一座城市”对自身主体性的认知适度转移至一座城市是如何看待另一座城市的,一座城市是如何与另一座城市共享某种文化与经济身份认同的(如江南、岭南、塞北等)。举凡长三角一体化、京津冀一体化、长株潭城市群、广佛全域同城化、汉孝临界协同区、杭州都市圈、南京都市圈,乃至“大下姜”等概念的出现,都显现出一种地缘间性的新特质。
这种趋势的出现,与21世纪头十年广泛出现的新城新区建设有着密切关联。新城新区建设基本是在一座城市的边缘(城郊)与另一座城市之间展开的,它们代表了“城市间性”在新一轮发展中的起步阶段。本文尝试以武夷新区十余年来的发展为例,讨论城市间性在城镇化进程中,尤其是在全域美丽与共同富裕的建设背景中,如何发挥创意式重构和产业迭代优势,促使城镇化走向新阶段。相对福建沿海,闽北山区长期处于欠发达状态,以市区常住人口50万为中、小城市划分标准,其一个设区市(南平)和8县域城市均为小城市①参见中国城市经济学会中小城市经济发展委员会编:《中国中小城市发展报告2011》,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版,第329页。根据2021年5月发布的《南平市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公报(第二号):县(市、区)人口情况》,南平市10个县(市、区)的人口均未超过50万,其中最多的是延平区(约45.5万),参见http://tjj.np.gov.cn/cms/html/tjxxw/2021-05-24/1444066436.html,2021-07-30。——作为东部省份“小城市群”,闽北如何走出一条富有地方特色的新型城镇化路径,对其他地区有着重要的参考意义。2010年,福建省政府批准《武夷新区发展规划》,将武夷新区作为重大战略部署和海西绿色腹地科学发展的重要选择;2011年,国务院批准《海峡西岸经济区发展规划》,提出建设“以南平等城市为中心的闽浙赣互动发展区”;2012年,福建省政府批准《武夷新区城市总体规划(2010-2030)》,要求“把武夷新区建设成为环境优美、绿色生态、经济繁荣、城乡协调的闽浙赣交界区域重要中心城市。”可见武夷新区作为闽浙赣互动发展区,有着重要的城市间性地位。它既要专注于县域发展,又要聚焦区域协调发展,从而走出一条以新区建设为抓手的小城市群簇群式发展道路。
按照规划,武夷新区包括武夷山市全境和南平市建阳区的部分区域,以及武夷山自然保护区。武夷山是中国仅有的四座世界双遗产地之一,旅游资源极为丰富。整个区域处海西腹地,发展以“高、新、绿”为方向已是共识。但如何在城市间性的视野中,发挥城市群的优势,实现保护与开发、人文与经济的协调,实现城市及其群落作为社会生态在当地居民生活与工作的张力中的动态平衡,成为闽北生态、经济与文化建设的空间驱动,却有必要在已有规划之外提出一种新的人地关系,尤其是人与生活空间的价值取向及其可能。
一、城市间性:全域化的现代生活体系
新型城镇化的核心是“以人为本”[2],这一命题确认了人(而非物)及其生活的本体意义。在现代城市中,人的生活具有强烈主体间性特征,表现为人际关系的发生、发展:“城市是一个遭遇他者的场所——不同于自我的他者,无论这一遭遇多么短暂,但却能够改变我们,教导我们认识自我,从而使我们成为‘人类’。”现代城市所具有的这种哲学意味,赋予了城市以及其后的城市间性发展以深刻的价值意义。它既要在物质层面统筹旧城镇化发展所取得的成果,主要是农村土地转让带来的城市地产及其收益对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再投入;又需要在此基础上满足日益增长的新城镇居民的生活需求。前者是城市之所以为城市的物质基础,而后者将日趋成为城市的现代社会本质。换言之,新型城镇化区别于旧城镇化道路的关键,不在于高楼大厦,而在于是否有全域性的现代生活体系。
在这里,重要的是生活体系的现代化。在既往的城镇化进程中,所谓“现代生活”就是客观形态上变得越来越像城市的生活。如旧城镇化道路一般只局限于客观的城市规划层面,它止步于基础设施、交通通信、产业发展、生态旅游、环境保护等外在范畴。这就造成了乡村与城市在物质层面上形成了“无差别城乡”(以浙江省湖州市为代表),如乡村生活中也广泛出现WiFi、奶茶店、咖啡吧、智能机器人等,而现代生活的内里,即主体的“遭遇他者”“成为‘人类’”的意味却无法在客观的规划层面提上日程。这其中最典型的就是“美丽乡村”和“花园城市”(Garden City,或译“田园城市”)。前者在实践过程中已出现了空心化、少游客等问题,而“花园城市”至今还是不少城市的追求,尤其武夷新区的城市规划,极易以“花园城市”为目标①“花园城市”运动的创始人是Ebenzer Howard(1850-1928),1876年他从美国返回英国后提出把城市生活与乡村自然环境相结合的田园城镇建设理论,对现代城市规划与建筑设计传统影响深远。参见马万利:《田园城市理论的初步实践和历史影响》,《浙江学刊》2005年第2期。。事实上,对花园城市理论的批判,恰是20世纪50-60年代美国城市规划运动的转折点。简·雅各布斯就曾说,“把某些文化或公共功能建筑分离出来,消除其与日常城市的联系,这种思想与花园城市的教条完美地契合在一起”,这种功能主义“背后的思想并没有受到质疑”,特别是“花园城市是要被一圈农业带包围的”,它高度凸显城乡差别[1]。可是,以人为本的城市要重视的却不只是物质形态,更要有全域的现代生活以及构成现代生活的人际关系基础——公共信任。
这种在陌生人社会的语境中形成的公共信任及人际交往,是现代生活体系的基石。在城市间性的视野中,它带有城市与乡村的双重意味。它既不是席美尔笔下的陌生人社会,或本雅明眼中的浪荡子社会,也不是费孝通笔下的乡土社会与差序格局。简·雅各布斯对这种理想的现代城市生活体系,曾写过一段相当形象的描述:
它来源于人们在酒吧前停下来喝杯啤酒,从杂货店那里得到一个建议,向报摊主提供一个建议,在面包房与别的顾客交换主意,向门廊边喝可乐的两个男孩点点头,在等着被叫唤去吃晚饭时,向女孩子们瞧上一眼,告诫孩子们注意他们的行为,倾听五金店里的人关于某工作的闲谈,从杂货店主那里借一块钱,赞美新生婴儿,对某人外套的褪色表示同情,等等。
她进一步说:“为什么从杂货店老板或酒吧招待那里获得一个建议,有别于从你的隔壁邻居或一个社会机构的女士那里得到建议——我们必须要了解城市生活的隐私性。”“隔壁邻居”是纯粹的熟人社会,代表着基本没有个人隐私可言的乡村生活经验;“社会机构”则是纯粹的陌生人社会,代表着正式的机构化与工具性的城市生活经验。而带有城市间性的现代生活应该介于二者之间,亦即是雅各布斯所谓的“杂货店老板或酒吧招待”,这些与我们经常交往的陌生人“一方面有一副热心肠,另一方面并不处心积虑地留心我们的私事。”[3]显然,在这里现代生活有着陌生人社会(城市化的大语境)和熟人社会(街区化的小语境)的双重属性。它是城市与乡村的结合,本身就体现出“间性”意味。而正是这些形形色色的人际交往构成的公共生活及其信任基础构成了现代城市和现代生活的本质。在此之上产生的社会安全感和人的幸福感,乃是整个城镇化进程所应抵达的“和谐社会”与“美好生活”的重要标志。可以说,城市间性就是要让这种现代生活变得愈加全域化起来,无论城乡,都可以在享受现代物质条件的前提下,感受生活本位的“美好”。
武夷新区总体“规划”当时所涉总人口约33.29万人,2030年计划中心城区常住人口66万人,而这一人口规模并不足以支撑较大城市的工业经济及其发展。换言之,武夷新区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保持较低人口规模——这一点从“规划”中心城区人均建设用地为135平方米的指标也能得到印证;随着人口集聚和城乡统筹的推进,城市居民、新居民以及外来游客的在地生活理应成为其城市发展的核心。特别是依照城乡一体化的发展要求,武夷新区将原先为乡镇或农村的武夷山市吴屯、星村、兴田、五夫和建阳区童游、将口、崇雒、莒口等地整合进新区发展之中,兴田和将口两个建制乡镇完整纳入中心城区规划,都将赋予这些地区居民原本的“乡村生活”以“城市生活”,亦即实现全域化的现代生活形态。这些乡镇及其所辖的农村本有的“熟人社会”将被城镇化带来的“陌生人社会”所取代。如果处理得当,就会在以往城镇化进程很容易造成的混乱、嘈杂、无序的“城乡接合部生活经验”之外,创造一种新的现代生活体系。“城乡接合部生活经验”是在城镇化高速发展时期,相关组织管理和基础设施建设暂未跟上,导致城乡接合部出现“公权力真空”而形成的一种过渡形态的现代生活。而随着城镇化进程趋于稳定,特别是以新区建设为代表的全域现代,地理空间的现代化与组织管理的现代化遂同步进行。如武夷新区中两个建制乡镇整体进入城市语境中之后,便不可能再产生城乡接合部的生活经验,反而有可能形成既有组织化的公共规范,又有基于乡土乡情而产生的新街区生活样态。这种新的现代生活体系应该是以人为本的,它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以新的文化生态来重塑物质生活,从而使整个城市充满活力、人情与奋发向上的创新精神。已有的“规划”对武夷新区诸多客观面向做出了详尽的计划,但对城市内部生活运作机制及其文化属性和发展方向却无法予以安排。显然,这并非城市规划的工作,它有待于城市自身形成的历史文化引导与当代经济转型和文化创新的实践经验,也需要在具体行进过程中加以总结和凝练。
二、创意生活:当代化的朱子文化复兴
城市间性的实现,需要以基于公共信任的现代生活为表征,而这种表征必须建立在某一文化传统基础之上,才能使“间性”在一定范围(若干城市间)内有彼此认同的可能。而更重要的是,这一基础要以能够融入现代生活形态的方式出现,有着鲜明的当代性特征。在旧城镇化的进程中,文化传统往往被局限在乡村,且总带有负面意味,它很难呈现出复兴的趋势,更不用说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而以城市间性为着眼点的新一轮城镇化既受政策环境影响,需要发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的功能,又因为囊括了大量城郊与乡村的地域,自然可以生发出诸多传统元素,因而也就更容易凸显地域性的文化传统。
仍以武夷新区为例,这里被誉为“闽邦邹鲁”和“道南理窟”,朱熹在此讲学40多年,武夷精舍等学府吸引了天下士人到访,使其一度成为东南中国文化的中心。2021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武夷山,就专程到访朱熹园,了解传统文化传承情况。武夷山与朱子文化的密切关联毋庸赘言,这一关联也是武夷山获得“双世遗”和实现全域旅游升级的重要依凭。只是,这种文化传统的在地延续一方面已出现长期断层,另一方面又受限于区域因素(地处经济欠发达的山区)而难以再生,很难自动出现复兴的文化效果。
这就需要当代元素介入其中,特别是以智能互联网技术为基础,探索历史、文化和创意成为地方经济增长点,进而实现全域现代化的新可能。论者指出,“在创意经济时代,城市的核心竞争力已非以往如此绝对地取决于自然资源是否丰富、土地及劳力成本是否低廉、地理位置是否为交通辐辏等生产与地理要素,而是取决于当地人才与社群的创意与创造能力,是兼顾创意人才与都市生活形态的多重面向考量。”[4]这就是说,“人才”和由人际关系及其公共生活所构成的“社群”乃是创意经济时代城市经济发展的核心。①弗罗里达一直强调创意城市的核心是“人才”(talent)以及围绕人才而产生的社会文化宽容度(Tolerance)及其培养机构,这一点与霍金斯注重从“产业”属性来判断创意经济并不相同。参见Florida,Cities and the Creative Class,New York:Routledge 2005,pp.87-112.武夷山作为旅游城市,一直有热情好客、接纳异己的氛围。这就为地方文化通过对相互间不同生活方式的了解、包容,进而形成该城市的创意阶层(creative class)、营造该城市的创意氛围(creative milieu)提供了相较其他城市来说更多的可能。武夷新区有一所大学(武夷学院),还有包括武夷山、建盏、建本、岩茶等在内具有相当吸引力的文化形态。它们的交互式重构有可能迸发出新的创意形态,使城市充满活力,城市生活体现美学特征。
比如,以朱子文化的当代性表征为路向,重新阐释朱子与武夷山水的关联,使古老传统焕发新意,便可能形成一种新的现代生活形态。长期以来,武夷山总是将其历史文化视为旅游“资源”(而非“生活”方式),以种种商业手段对其加以重建、改造,如闽越王城、武夷宫、止止庵、考亭书院等的复建,都主要是用于吸引游客,发展观光经济,而非真正使其具有现代生活意味。这一行为自有其合理性,但在如是运作下,武夷山和朱子文化便成了“遗址”或“遗产”,与当地居民的城市生活了无关联,对游客也难以发挥“参观”以外的其他作用。这种传统文化所具有的现代性特征与商业价值从属于“服务业”,而非“创意产业”;从属于“服务经济”,而非“体验经济”;造就的“人”及其生活也仅局限于低端的“服务阶层”,而非“创意阶层”。[5]它只能吸引“旅居”的游客,而无法真正形成在地化(定居)的创意生活,更不用说重新汇聚人才,复兴文化传统。
如果把这种以“旅游”为指向的历史文化现代性特征命名为“文化资源论”,那么武夷新区的文化发展还存在着另一种当代性的可能,即“文化生活论”。试想南宋武夷山所具有的创意氛围,仅朱熹在寒泉精舍、晦庵草堂、考亭书院、武夷精舍等教学机构培养出的数百名弟子便足以成为当时闽北城市发展的“创意阶层”,更遑论聚集于环武夷山的霄峰精舍、豸山草堂、少微书院、星溪书院等其他学校培养的大批知识人才;对他们而言,理学不仅是可供参观的物质对象(书院、牌坊、雕塑等),而是日染其中的文化生态。他们的著书立说、教学科研、刊版刻书、文艺创作,甚至日常生活、工作等活动都是一种充满活力与创新意识的文化生活。以朱子为代表的这一地域性“文化”大体等同于这一创意社群(朱子学派)的“生活”本身。而这种“生活论”的朱子文化如果经过现代性重构而兴起,经由高等教育、人才孵化、环境吸引、税收优惠等条件再次笼纳创意人才集聚,那么,武夷新区就有可能应契“创意经济时代”而走向“创意城市”建构的新型城镇化道路。
文化作为生活样态的复兴,要与地方传统相对接,与城市间性的文化认同相吻合,进而形成一种强大的当代化与创意性的力量,以及相配套的系列政策群,最终生成富于文化价值和创新意味的现代生活体系。以南宋独有的祠禄制度为例,它让士人以“佚老优贤”的名义,得主管宫观(专职但不实际执掌)而享受一定的俸禄。这种制度在实行过程中虽逐渐泛滥,引来“增冗员、坏士风、害吏治”,“根蠹国家财经”的议论[6],但整体看,它确实“在制度上促成了一批颇具才学的士人离朝在野,成为里居地方的精英群体,并使得这一群体得到空前地扩大……让他们有较为充裕的时间和基本的经济保障,可以相对从容地专注学问、研习诗文”,进而促成了地方文化、乡贤文化的成型与提升[7]。在当代,这一制度如果可以与企业、基金会等社会捐赠相结合与高校“旋转门”制度相融通而实现创新,便有可能使武夷新区诸多书院遗址发挥出生活意义。可以说,武夷新区的历史文化中蕴含着创意的因子,以创意城市为其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宏观路径,就不是新型产业形态及其文化的简单移植(如招商引资),而是传统文化观念与氛围的成体系复兴,或曰“有机复兴”。“文化复兴是民族复兴的题中之义”[8],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离不开区域文化的有机复兴。武夷新区的朱子文化从“资源论”向“生活论”的转型,不仅是传统服务业向文化创意产业的过渡与升级,也符合晚近以来世界哲学美学的“日常生活转向”,从而将城市间性体现出来。
三、全域美丽:生态性的产业结构迭代
武夷新区地貌以丘陵和河谷盆地为主,长期依靠农业推动地方经济发展。而21世纪之后,其上位城市南平开始进行产业结构调整。这一调整和迭代的过程有很强的代表性,它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而从其历程中可以看出中国地方产业经济发展的基本线索。
第一阶段从2003年开始,当时的市委、市政府提出了“突出工业、突破工业”战略,在竹木加工、饲养、食品等传统产业外,大力发展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造纸及纸制品、有色金属、化工、纺织服装、电力,尤其铝业、碱性电池、化肥、饲料等产业,极大地促进了闽北经济发展。从第一、二次经济普查的数据看,2004年至2008年,武夷新区所涉县域(武夷山市、建阳区、邵武市和光泽县)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生产总值和主营业务收入均翻了一番半以上;2010年前后,南平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发展增速超过41%①参见福建省人民政府第二次全国经济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福建省统计局编:《福建经济普查年鉴2008》(第二产业卷),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10年版,第316-317页;福建省统计局、国家统计局福建调查总队编:《福建统计年鉴2011》,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11年版,第596页。。可以说,闽北工业在21世纪头十年具突飞猛进之势,显示出“突出工业、突破工业”这一闽北山区县域经济发展规划的实际效果,为武夷新区新型城镇化道路提供了坚实基础。
第二阶段可以用南平市2007年开始实施“53358”的园区基础建设战略为起始标志,从那时起,绿色的武夷山区中兴起了工业园区(平台)建设的高潮。南平工业园区、闽北经济开发区、中国笋竹城、政和工业园区等规划面积10平方公里以上的大型工业园区相继出现。2006年,全市工业园区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只有70家,工业总产值为14.05亿元;2019年全市工业园区入驻规模以上企业已达362家,实现工业总产值超1014亿元。
第三阶段是进入2010年,南平市工业发展上了新台阶之后,开始对已有产业进行梳理,去芜存菁,提出了“5+3”重点产业发展模式,即在机械制造、纺织服装、食品加工、林产加工、冶金建材等五大传统产业之外,增加旅游(养生)、生物、创意三大新兴产业作为重点扶持对象。不难看出,这一时期所谓的“5+3”产业类型仍处于以工业(制造业)为主,辅以绿色新兴产业的过渡性发展阶段。而毋庸讳言的是,这一转型背后显现出地方政府对片面重视工业,削弱了武夷新区的绿色腹地优势的某种方向自觉。
第四阶段是2017年之后,南平再次确定现代农业、旅游、健康养生、生物、数字信息、先进制造、文化创意等七大绿色产业作为发展主攻方向,并在当年11月发布《绿色产业发展行动纲要》及其配套政策体系。这一新的产业规划将原本合为一体的“旅游”和“养生”分立,并增加现代农业、数字信息等产业类型,较好地体现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而在这一过程中,最为突出的是依托生态而实现的旅游业高速发展。
21世纪以来,在南平市产业类型化的发展中,旅游业的成效相当显著。从2002年实现旅游总收入14.55亿元到2019年的985.60亿元,增长达66倍;而相比之下,同期全市工业增加值的增幅则要小得多,只从2002年的85.57亿元增长至2019年的611.55亿元②因2020年的产业数据受疫情影响较为严重,本文采用2019年的数据作为比较,以凸显地方产业经济发展的持续效果。数据来源于南平市统计局,http://tjj.np.gov.cn/cms/html/tjxxw/ndsj/index.html,2021-05-10。。这充分说明了武夷新区的产业发展应该充分利用“绿色”资源,将绿色腹地的生态优势转化为良好的投资、宜居环境,以及文化创新和人才孵化效果。特别是要将绿色产业的经济优势与以人为本的创意城市建设和城市间性探索相结合,突出文化创意和自然生态作为全域发展的核心要素,以这两项标准为要求,实现文化经济向美好生活情境的过渡与转化。
以旅游业为例。武夷新区“规划”杜坝、三姑、仙店、兴田和考亭四个旅游区,新建崇阳溪休闲带;突出“养生度假”,塑造“生态绿谷、旅游中心、养生胜地、创意新都”的城市形象。以“养生”为着力点固然避免了“文化资源化”的弊端,突出了“体验经济”,还可延长游客停留时间,从而带动其他行业发展;但以“养生”为主要旅游产品不易突出“创意”效果,也难以与江西梅岭、龙虎山、三清山等邻近的地质同类景区形成差异竞争。更重要的是,以“养生”为特色还可能影响武夷文化中以思想性和学理性著称的理学文化之发挥;不少旅游养生产品进驻保护区,也可能使当地隐逸的人文自然环境受到影响。因此,有必要基于地方文化重塑或凝练武夷山特色的区域养生品牌。如结合朱子文化,突出“隐逸”色彩。在历史上,武夷山一直是中国隐居文化史的重要节点,它对隐士、退仕官员和文人墨客的集聚效果并不亚于终南山,朱子本人也大半生都以奉祠状态,隐居于闽北①宋人罗大经曾以晁以道、陈叔易等隐居嵩山和朱熹隐居武夷山相比,认为隐居“终南、少室之流”与朱熹这般“有道之士,正不可同年语也”,这可视为武夷山隐逸文化的例证,并作为其旅游整合传播的资源。参见罗大经:《鹤林玉露》,王瑞来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43页。。相比终南山以隐居为品牌发展旅游业,已经取得的显著效果,武夷山在这一方面显然尚未布局。隐逸文化是一种生活氛围,它形成的人才聚集不仅可以塑造城市社群生活②关于士大夫乡居对地方社群建设和文化传承的重要意义,可参见许倬云:《我者与他者:中国历史上的内外分际》,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年版,第112-113页。,对武夷新区自然遗产保护也有重要作用,值得加以重视。现代城市建设,尤其旅游业的发展不仅要在开发和保护上做出权衡,必要时还应该持有“拒绝开发”的勇气。
除了隐逸文化,武夷新区的旅游业转型迭代还可结合创意开发。如(1)与会展经济结合,挥发会展对人才、资金的集纳作用,使城市经常处于“节庆”的审美氛围之中,提高其当地居民文化意识和活力[9];(2)与公共艺术结合,充分利用城市公共空间进行艺术创作,使城市社区充满想象力;(3)与茶叶、竹木家居等“准文化产业”结合,通过旅游拉动制造业扩大再生产,使武夷文化具有物质传播效果[10];(4)与学术科研结合,重建雕版印刷中心,以朱子学、建本、建盏、茶学及新区社会经济发展为课题,建立“回乡学者/艺术家短期驻访”和知名高校研究生联合培养等制度,以点带面,实现创意人才集聚。
依托自然禀赋和绿色优势,坚持“退二进三”与“退二返一”相结合,促使产业创新、升级和经济结构调整与发展方式转变融为一体,是武夷新区走出一条城市间性融合发展之路的重要内涵。由创意生态的重塑而形成创意人才(创意阶层)集聚,可以进一步塑造城市风貌与城市精神,其“知识溢出”的外部性还可形成与当地居民、社区的社会互动,最终建构出文化在城市间性中的良性循环。这一方面需要当地高校参与创意人才的培养与孵化,另一方面则需要通过城市文化及其创意开发、政策优惠等实现人才集聚。亦即,产业与文化之间要有很好的协调机制,二者相互配合,共同推动地方文化的重塑。而一旦出现龃龉,就有可能浪费资源,影响发展。如武夷学院曾于2009年设立动漫学院,支持创建“武夷创意动漫产业园”,但没几年就因就业压力而取消编制,动漫专业并入艺术学院中。而事实上,以二次元文化为表现的动漫是极有可能对当地文化共同体的形成产生深远影响的。如共青团中央宣传部试点的南平“大话熹游·卡通朱子”城市文化IP项目,就以“卡通朱子”的形象,以表情包、特色小镇、城市涂鸦、乡村手绘等方式嵌入城市间性广袤的物理空间,在当地逐渐形成了高度的认同,也使全域美丽通过生活场景而直观呈现。
在自然生态资源的基础上,增加结构化的绿色产业布局,并以“生活样态”的形式将自然生态、产业形态和文化业态统合起来,围绕地方特色,形成场景美学,是武夷新区在“美丽中国”与“美好生活”的整体建设框架中,探索城市间性创意表达的根本路径。
四、结语:城市间性的人文面向与多种可能
挖掘和重塑地方文化是破解城乡二元结构的重要推手,也是城市和乡村在生活美学层面实现合一,进而以城市间性展现新的人地关系的重要渠道。闽北山区的经济结构在长期以农业为主、生态环境优越的基础上,按照“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指导,使重污染的工业、制造业逐步退出经济增长主流,为文化创意、物流金融、科教信息等现代服务业发展打开新的空间,尤其以促进旅游休闲产业创新升级,是其调整和转变的主要方向。
就此而言,城镇化的人文面向应该是超越工业化道路的“生活论”取向。列斐伏尔曾指出,尽管工业化与城镇化处于同一历史阶段,但“工业化与城市化并不是同质的,而是矛盾的双重过程。工业化最初是以破坏城市化为前提的,工业化是增长的、经济的过程;而城市化则是发展的、生活化的过程,因此不能用工业化代替城市化”[11]。就此而言,武夷新区无疑在规划上走在了闽北甚至全中国县域经济调整的前列。可是,在实际发展中,城市的人文面向总是受限于工业化的水平和基础,这就需要地方有超越性的认识,通过创意实现弯道超车。党的十九大以来,河南修武以“县域美学”的探索,获得了多方广泛的赞誉,但终究是点状突破,没有在更高的行政建制中实现跨区域的城市间性整合。而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城镇化进程走向“深水区”,城市群与城市间性变得愈加重要起来。这就需要不同地区在地方文化传统的基础上,因地制宜地展开创意实践,实现多种可能。
城市间性的出现,是共同富裕的必然要求。作为物质富裕与精神富裕的统一,共同富裕应该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这就需要从作为生活形态的文化层面出发,鼓励创意,丰富城乡生活,使城市间性、创意生活和全域美丽形成循环互动的共进关系。城市间性的开发,可以让不同类型、不同层次的创意人才都能享有一定集聚空间,通过知识溢出使城乡社群普遍获益。这必然呼唤出创意生活,以及创意空间、文化产业,特别是产业结构的调整,作为其物质基础。而创意生活与城市间性的结合,又为全域美丽提供了新的面向和空间。反过来,全域美丽的生存环境也将成为吸引创意人才集聚的重要因素。
党的十八大提出“美丽中国”的新概念,党的十九大又提出“美好生活”的新目标。“美丽”与“美好”不仅与生态文明相关,又要“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进而提升人民生活幸福感。武夷新区的自然禀赋已极大地赋予了当地生态文明建设的基础,而作为具有浓郁乡村生活氛围的小城市群,武夷新区的居民生活幸福指数也很可能高于大城市。它的“美丽”与“美好”需要在“自然”“生活”和“艺术”之中,找到一种新的平衡。而这完全符合“美丽中国”所具有的美学内涵。这种新的平衡理应以城市间性为基础。长期以来,小城镇(乡村)是作为大都市(城市)的附属和支撑而存在的。日本学者广井良典就曾指出,“东京电力公司把核电站设立在远离首都圈的福岛县、新潟县,这就是最具代表性的体现。高速增长期以后,人们已经逐渐忘记了这种‘城市-农村’的关系,‘3·11’大地震又把它重新摆在了大家面前”。导致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泄漏的“3·11大地震”恰当地说明了城乡分离只是表象,人类生存空间的实质乃是一个共同体。城市间性正是这一“城乡生活共同体”的时代属性。
围绕“人”(市民与村民)重构地方文化,将历史传统与现代创意有机结合,使产业经济发展为人的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服务,不仅是武夷新区,也是闽北乃至全国各城市在新一轮城镇化建设过程中,在探索城市群与城市间性融合发展的过程中的一条理想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