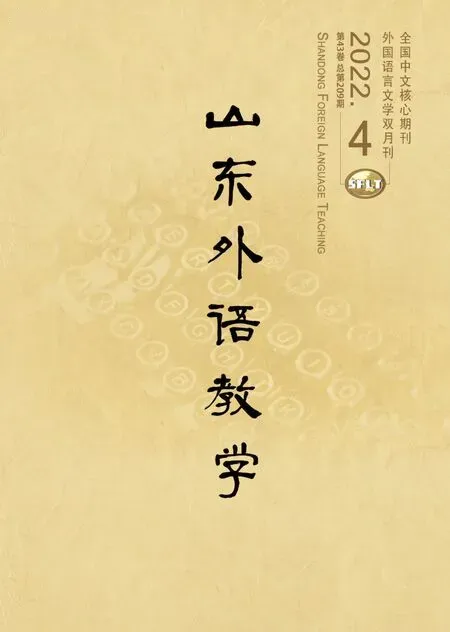国际化视野下外语教师教育研究的转向与发展
——Lawrence Jun Zhang(张军)教授访谈录
2022-02-03马婷LawrenceJunZhang
马婷 Lawrence Jun Zhang
(奥克兰大学 教育与社会工作学院,新西兰 奥克兰 1023)
马婷(以下简称“马”):张教授,您好,非常感谢您能够接受此次访谈。近些年,您的主要研究领域包含外语教师教育研究。众所周知,新时代中国外语教师教育与发展面临诸多新机遇与新挑战。您能否首先谈一下外语教师教育的内涵?您主要关注此领域的哪些方面?从理论和实践层面来讲,哪些将是新的热点和重点?
张军(以下简称“张”):首先,要搞清楚教师所具备的素养或者素质。上个世纪80年代,斯坦福大学教育学教授L. S. Schulman提出 “学科教学知识”(pedagogical content knowledge,简称PCK)的概念,即融合教学内容和教学法,把学科知识以最有效的类比、阐释、例证等方法进行解释和展示,满足学生的不同能力水平和兴趣范围(Shulman,1986;1987)。具体到外语教师教育方面,一是教师的外语知识水平要过关,具备良好的听说读写译等能力;二是教师应该知道如何应用、转化知识;三是如何高效地把知识教授给学生。外语教师教育很多时候关注语言基本技能的培养,往往忽视其在课堂的转化与应用,而PCK的概念强调与教育学相关的知识和技能的重要性,如教育心理学、儿童成长与发展、课堂管理等。当然,随着科技的发展,教师所需要掌握的“学科教学知识”升级为“整合技术的学科教学知识”(technological pedagogical content knowledge,简称TPCK/TPACK),教师除了要掌握基本的学科内容知识、教学法知识,还要学会使用现有的电子教学工具和资源,并且要与时俱进,掌握新的技能和技巧(Mishra & Koehler,2006:1023)。在疫情时代,TPCK显得尤为重要。广大师生封城在家,颠覆了传统的课堂教学模式,这就要求教师具备使用网上教学软件的基本能力,例如Zoom课堂、腾讯课堂、钉钉课堂等,与学生进行网上交流。另外就是录制视频、音频、PPT等,并且能够迅速地学习其它新的教学技术手段用于分享、传播课程资源。教师应该全面地理解学科内容知识、教学法知识、技术知识的内涵以及三者之间的有效整合,并充分将理论付诸课堂实践,包括泛读、精读、听力、口语、翻译等课程的教学。
我认为,以英语作为媒介语的教学(English medium instruction,简称EMI),是近年来外语教师教育领域研究的热点和重点,如教师对EMI的看法、身份认知,学生对EMI的反馈和接受度等。我和同事张东兰(Zhang & Zhang,2014)使用民族志的研究方法,探究了两位汉语为母语的英语教师在新加坡15年教学期间,面临来自母语为新加坡英语的同事和学生对其职业能力的质疑和挑战,以及如何构建和再构建自己的职业身份。姜莉和我于2021年发表在TESOLQuarterly的文章(Jiang & Zhang,2021),探讨了高校英语教师因为教学大纲由通用英语转变为专用英语,不得不重新学习新的知识,继而对自己的身份认知构建产生了变化。
另外,教师的工作动机(motivation)也是常见的热点话题。袁瑞和我(Yuan & Zhang,2017)从元认知的角度,探讨了本科外语专业免费师范生,通过四年的理论学习和教学实践,其职业动机的变化。王迪和我2021年合作的论文(Wang & Zhang,2021)追踪了对外汉语专业硕士生在教育实习前后工作动机和职业身份认知的转变,以及这种转变是否影响其继续留在教学岗位。职前理论学习与教育实习促使学生重新认识自己的身份和动机,这也是社会学的理论,叫做“重新定位”(repositioning)。还有一个热点话题就是教师的自我效度(self-efficacy),例如研究教师是否相信自己有能力培养学生在网络教学平台上的参与度(Bao et al.,2021)。随着国际化进展的加快,“超语”(translanguaging)的概念也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外语教师在课堂上使用汉语和英语两种语言进行授课,也叫做语言共融的教学实践(translingual practice)。前段时间,我就这个概念专门采访了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应用语言学知名学者S. Canagarajah教授(Zhang,2022)。他最早在写作中强调语言使用的平等性,认为英语为非母语的人,在使用英语的时候不要觉得低人一等。外语教师的教学过程中会无形中使用两种甚至多种语言,那么语言共融的优势和劣势也是这个领域的研究热点之一。例如,孙培健和我2022年在具有50余年悠久历史的国际知名期刊RELCJournal上发表的文章(Sun & Zhang,2022),探究了线上同伴互评中的超语现象及其对写作水平的影响。蒋志辉和我及Mohamed (Jiang et al.,2022)专门就这一话题研究了大学英语课堂中学生超语的使用、对超语的态度,以及与教师超语使用的关系。另一个热点就是教师认知(teacher cognition),此方面的研究从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到现在方兴未艾。例如,我和孙强的研究(Zhang & Sun,2022)通过验证有关外语教师语法教学认知问卷的信度和效度,总结出六种主要的语法教学方法。高行珍和我发表在FrontiersinPsychology的文章(Gao & Zhang,2020),正是沿用了TPCK/TPACK的概念,探讨了教师如何认知疫情时代的网络教学,其特点、优缺点、局限以及教师如何通过学习新的信息通讯技术,融合传统的教学方法,满足学生的需求。另外,教师的情绪劳动(emotional labor)和教师积极投入(teacher engagement)也是近期外语教师教育的重要转向,例如用定量、定性方法研究情绪劳动策略(Bao et al.,2022;Li & Liu,2021),教师积极投入对学生成绩的影响等(Wang et al.,2022)。教师可以选择合适的策略调控情绪,规划教学投入程度,教师教育课程内容可以涵盖这方面内容,以满足教师职业发展的需求。
马:从以上您谈及的研究重点和热点发现,目前外语教师教育领域理论和实证研究呈现出多元化,对新时代中国外语教学范式的转变具有较强的启示意义。您的学习和教研足迹曾遍布中国、美国、新加坡、英国、新西兰等不同国家和文化,形成了独特的跨文化视角。您是否了解国外教师培养体系和路径?对中国英语师范生培养有何启示?
张:我在美国的时间不长,前后也就是一个月,主要是在位于加州卡尔弗城的英语语言服务(English Language Services,简称ELS)的总部接受教学管理的实习及培训。当时ELS在中国刚刚开办第一所分校,我受聘兼职担任其教务长,负责任职教师的短期培训以便他们熟悉ELS的九级课程结构及教学理念和方法。1994年,我以教务长的身份受邀,出席在马里兰州巴尔的摩市举办的第28届TESOL国际大会。6000多人出席该届国际大会,我从中学到了不少的新理念、新方法、新技巧,对我自身教学以及我在国内的师范教育教学影响比较大。我对新加坡和新西兰的教师培养体系比较了解,它们是沿袭英国传统的教师培育的方法和路径。新加坡唯一一所教师培训机构是国立教育学院。想要取得教师执业资格,第一种途径是接受五年的本科教育,毕业后颁发文学学士以及教育资格证(Bachelor of Arts with a Diploma in Education)。第二种途径是取得研究生教育文凭(Postgraduate Diploma in Education),可以成为小学或者中学老师。教师执业资格的课程主要围绕教育教学理论和语言技能,例如教育心理学、课堂管理等,具体到英语教学有关的课程,分为写作、阅读、词汇等。学生不仅能够了解理论,也能掌握教学技能,例如如何设计教案、组织活动等。这两种途径的特色就是学生能够有大量的实习时间,大约持续九周。实习学生在中小学有合作教师(cooperation teachers)和指导教师(mentoring teachers),在大学也有导师(supervisors)。中小学指导教师负责跟进学生的日常实习,学生实习结束后回到国立教育学院汇报实习成果,教育学院的导师则会针对学生讲课的优缺点提出建议以便改进,学生在三方合作的模型中得以提升教学专业水平(Zhang,2016)。大学和中小学的合作不仅在职前培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也潜移默化地促进在职教师的职业发展。例如,我和Rahimi等人合作的研究发现,不少有多年工作经验的英语教师认为自己缺乏理论知识和实践技能,迫切需要大学研究者和更有经验的教师的帮助(Rahimi et al., 2016)。
新西兰师资培训与新加坡一致,注重理论学习和教学实践的紧密结合。以新西兰奥克兰大学为例,成为注册教师有两个途径。第一,如果你已经取得学士学位,那么你可以选择继续攻读一年制的教师资格证课程(Graduate Diploma in Teaching),分为幼儿园、小学、中学三个方向。幼儿园、小学教师的培训不区分专业,因为其课程内容涵盖面广,要求教师融会贯通。中学注册老师则要选择两个专业方向,而中国的师范生一般只攻读一个方向。如果报考教师资格证课程,学校会审核本科学位是否符合所选学科的要求,即是否具备一定的学科内容知识(content knowledge)。第二个路径就是攻读教育学士(教学)(Bachelor of Education in Teaching),分为幼教、小学教学、中学教学、毛利语媒介教学四个方向。三年制的教育学士(教学)学位课程包含累计22周的教学实习时间。
新西兰和新加坡的师范教育和师资培训模式对国内的启示如下:一是课程结构的设置充分体现了PCK的概念,不仅包含学科内容,也包含教学法等。二是大量的实习时间和专业教师指导,能让学生有机会将学到的理论付诸于实践。当然,无论是职前教师还是在职教师,都面临如何将课堂上学习到的理论运用到实际的教学实践中的挑战。我和Rahimi等人合作的研究(Rahimi et al.,2016)发现,无论是新入职还是有多年教学经验的英语教师,都认为自己缺乏英语教学相关的理论知识和实践技能。若想解决这个问题,可以考虑职前教师的课堂用语,尤其是知识构建类对话,以此揭示课堂互动模式、实现教学目标的策略,继而帮助教师更好地面对理论与实践难以结合的问题(Zhang & Zhang,2020)。课堂对话不仅让师生有机会共同构建知识体系,也可以让教师站在学生的视角,认可学生对课堂的贡献,建立良好的师生关系(Sybing,2021)。
马:正如您所谈到的教学理论与实践的融通,目前国内师范院校英语师范生的培养也在此方面着力,致力于架构系统的职前教师学科教学能力。您2004年在《课程改革国际期刊》(Zhang,2004), 后来又在《中国应用语言学》(Zhang,2021)都探讨了外语教师教育的课程创新与职业发展的关系,特别是新加坡英语语言教学研究生文凭(Postgraduate Diploma in English Language Teaching, 简称PGDELT)项目。您曾在1995年攻读此文凭,并于1999年博士毕业后成为项目的授课教师,以您对该项目的理解,能否谈谈其对外语教师教育课程设置的启示?
张:始于1985年的PGDELT是针对中国高校在职英语教师职业发展的培训项目,是两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之前的友好之举。项目初期的课程设置与新加坡职前中学教师培训教育研究生文凭(Postgraduate Certificate of Education,简称PGCE)的课程无异,旨在提升教师的英语教学技能,拓宽关于英语语言文学和语言教学的知识面,并且受训老师在新加坡中学有长达三个月的实习。
PGCE的教学安排显然不符合当时参训的中国大学教师的需求:(1)学员本身已经从事教师职业多年,其目标是职业发展而非职前培训;(2)PGCE旨在满足新加坡本土化的语言教学,英语是官方语言、除母语外的第二语言,而英语在中国被视为外语;(3)学员面向中国大学生而非中小学生,在新加坡的中学教育实习就显得没那么重要(Alsagoff & Low,2007)。这个项目突出的特点就是课程大纲会根据受训教师的社会文化与经济背景与需求进行调整。例如,1990年将课程教学重点调整为英语单学科,项目更名为PGDELT,1999年增添了许多学术研究相关课程,2005年包括了语言教学方法论的课程。整体来讲,课程大纲的设置强调理论和实践的契合。另外,项目的成功开展离不开其雄厚的师资,任课教师多为教学和科研领域的佼佼者,具备坚实的理论基础和教学经验。从1985年到2015年,该项目一共实施了31年,为中国培训了1000多名高校英语教师,其中不乏国内外语教学和研究领域的领军人物。
简言之,我认为外语教师教育课程设置的结构和内容要实时更新,适应中国的社会文化的更新,反映外语教学与研究领域新的进展。无论是职前还是在职教师的职业发展和培训,都要不断加深学习PCK和TPCK,这些知识能指导教师在高度情景化的课堂有效地开展教学实践。
马:教师教育的课程结构和内容的设置会受语言政策的影响。在2021年10月上海外国语大学举办的“变化世界中的语言政策:全球规则,本地角色”国际研讨会上,您创新性地提出教师教育中语言政策的显性和隐性教学内涵,您认为语言政策会对教师教育有何影响?
张:宏观语言政策规划不是我的研究长项,我仅就个人体会谈一下。之所以说语言政策是全球规则、本地角色,是因为每位奋斗在教学一线的老师都是语言政策的执行者,任何语言政策都要依托课堂实施和落实。显性的规划是政府官员通过起草文件法律规定来做到的,而教师在课堂上耕耘,是不知不觉地在用自己的行动落实语言规划与政策。教师们不一定亲自阅读政策文献,但是一定会研读教学大纲。熟读语言教学大纲自然也就会了解大纲制定的背景。语言政策往往就体现在大纲的背景里面。
马:您曾多次提及外语教师教育理论的引进与本土化(importing and localising)、理论输出与国际化(exporting and globalising)等问题(Zhang & Ben Said,2014),能否就此再做一下深入阐述?
张:关于教师教育理论的引进与本土化,以及中国的教育理念的输出和国际化,我个人认为是非常的重要。随着国际交流越来越广泛,尤其是过去两年受疫情的影响,大家的线下交流受到了一定的限制,但是网络交流还是很活跃。任何教育教学理念的引进,一定要适合中国的土壤和气候。我们应该经常带着开放的胸怀态度去接触新鲜事物,然后在借鉴的前提下改编,那么就能够为中国的外语教学起到积极的作用。这其中,教师作为教学理论的践行者,如果接受恰当的培训,则有利于新的理论的引进和实践(Zhang,2016)。
反之,中国的新理念也应该要让世人知道。如果所有的科研成果都一味地用中文发表,国外的学者就不会知晓中国的教育教学新理念。所以近些年来,我也在积极地把中国的教育教学理念推向国际。例如2021年,我和河北师范大学张素敏教授合作的文章(Zhang & Zhang,2021),发表在国际一流期刊System上,把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王初明教授的“写长法”(或称“续论”),介绍给国际读者。我最近在审阅FrontiersinPsychology的一篇文章,是有关汉语写作教学理念的。那么我是积极推荐这篇文章,让国际读者了解汉语写作教学,同时会对对外汉语教学有一定的启示。
马:您提及的研究展望对长期从事一线教学的外语老师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您之前曾提到,作为大学教师,那产出新知识、新理论或新方法是责无旁贷的职业要求。但现在的中青年外语教师常常苦于无法提升自身的学术水平和写作能力,您多年担任国际期刊主编和评审专家,在这方面您有什么建议?
张:当然很多老师不一定赞成我的观点,我个人认为,目前在中国高校这个体制背景下,教师是不可能脱离科研的。大学教师区别于中小学老师就在于他们要承担知识创新的责任。中小学教师更多侧重教学方法和成果,就新知识的产出来讲,很少有新的突破。所以,我认为大学教师要责无旁贷地产出新知识、新理论、新方法。课题及方法创新很重要,也没有想象得那么困难,例如探讨某种教学方法,学生的学习动机、自我效度、身份建设,课堂互动类型和话语等。研究分三步走,研究问题、研究设计、研究汇报,通过系统地规划,就能获得这些方面的信息。科研与教学是相互关联与促进的关系,科研能够反哺教学。
具体到论文的撰写与发表,我认为首先要制定写作计划,明确研究目标以及时间节点等。另外,要选择适合的期刊,通过阅读作者指南和往期刊发的文章,明确期刊的办刊方向、话题范围以及受众。关于论文的内容,文献回顾的话题和发表时间要新,紧跟领域的热点。致谢部分说明其他学者提供的意见和帮助,这也是编辑衡量稿件质量的标准之一。投稿后,与编辑部的交流以及如何礼貌而有理有据地回答审稿人的问题也是成功发表的关键。现在学术发表的一个趋势就是开源化,读者可以免费下载文章,而作者的发表周期也比闭源期刊短。选择质量可靠的开源期刊能够扩大文章的影响范围。总之,学术写作能力是学术表达能力的体现,它与语言水平相关,但是同时又是一项专门的能力。
马:新文科建设近年来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这就要求高校外语教师发展跨学科研究能力(陶伟,2022)。您如何看待外语教师的跨学科研究能力?
张:根据跨学科的定义,如果是大类学科,比如说文科跨越理工科,我认为是比较难。那么,如果是文科内部类别下的跨学科交流,我认为这已经成为现实。如今的应用语言学不是单纯的教学研究,它涉及的理论是多方面的,社会学、经济学、文化学,还有传媒方面。例如姜莉和我2021年发表的文章(Jiang & Zhang,2021),虽然话题围绕教师学习,但是使用的理论隶属社会学的身份概念。之前我关注比较多的“元认知”就是心理学的概念(Zhang, 2010)。就教师教育研究而言,袁瑞和我(Yuan & Zhang,2017)曾做过一个从元认知的角度追踪外语师范学生的从业动机变化的案例研究。
马:谢谢您分享有关外语教师教育研究的真知灼见,我对外语教师的关键能力有了更深的理解和认识。我相信外语专业的师生也能从中受益,再次感谢您接受此次访谈。
致谢:特此感谢《山东外语教学》编辑部孙炬老师对本访谈提出的宝贵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