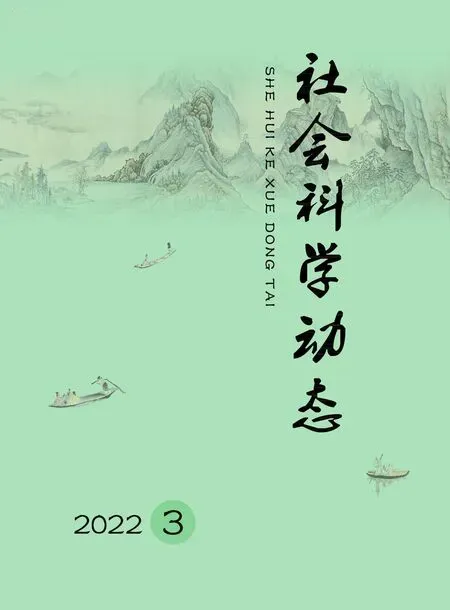差序伦理与差序格局的内生关系考论
2022-02-02徐汉晖
徐汉晖
自古以来,中国就是一个礼制大国, “礼者,天地之序也”①。古人把 “礼”视为天地间的一种基本秩序,而由礼所达到的“序”在于“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②。可以说,中国古代封建宗法社会以 “礼制”为根基,封建之“礼”可从两个层面理解, “广义的礼是国家典章制度(官制、刑法、律历等)、伦理规范(如三纲五常等)与行为仪式(朝聘燕享、婚丧嫁娶等)的总称;狭义的礼则指人类日常生活中所奉行践履的行为仪式与规范,是一个伦理学的概念”③。很明显,古代社会的“礼”所指甚广,意蕴丰富。这个礼“既是国家的规章典制,又是人们进行一切社会活动的准则,更是一系列庄严隆重的典礼仪式”④。古代儒家推崇“道之以德,齐之以礼”,规定了婚礼、寿礼、丧礼、祭礼、节庆礼、座次礼等世俗生活中诸多的繁复礼节,甚至严格推崇男女、上下、亲疏、长幼的秩序之别,这种价值观念推行到人际关系中,就是“方以类聚,物以群分”⑤的差序伦理。
一
王国维认为,封建社会的礼制“其旨则在纳上下与道德,而合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庶民以成一道德之团体”⑥。费孝通认为, “伦理道德是社会对个人行为的制裁力,使人们合于规定下的形式行事,用以维持该社会的生存与延续。因之,在中国传统社会,所有的价值标准不能超越差序的人伦而存在”⑦。而且, “每个人都以自己为中心,以血缘关系为主线,以宗法群体为本位,以及由此而形成的远近亲疏的关系格局”⑧。其实,古人认为“夫礼,必本于天,肴于地,列与鬼神”⑨,最初的 “礼”源于处理人与鬼神的关系,主要内容体现在对天、地、鬼、神的祭祀礼仪上,由此慢慢演化为规定君臣、长幼、男女、亲友之间等级与相互交往的礼仪, “再到反映人生历程的冠、婚、丧葬之礼,不断制度化、神圣化”⑩。封建宗法社会推崇“礼制”,其目的在于使每个人在自己对应的社会角色里遵守相应的人伦规范,从而形成各归其位、和谐有序的社会状态。
然而,中国古代传统的“礼”有等级差序之别, “不同等级的人,行不同等级的礼”⑪。古人云: “夫礼者,所以定亲疏,决嫌疑,别同异”⑫,即为此意。从礼的运行模式看,封建宗法社会之“礼”并不是一种形而上的虚空之礼,它是形而下的,能够融入民间生活,具有很强的实践性和操作性。在乡土社会中,礼往往表现为一种习俗,民间习俗通常吸纳与融进了礼的元素和精髓,共同作用于庶民的起居饮食等生活细节, “礼与俗在循环往复中寻找到社会治理的最佳平衡点”⑬,二者紧密结合在一起,由此形成传统的礼俗文化。因此,礼俗既是一种行为规范,又是一个地区的社会风尚与民众习惯,它涉及到民众衣食住行、婚丧嫁娶等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如婚嫁礼俗、祭祀礼俗、丧葬礼俗、节庆礼俗等,自古以来源远流长。在现实生活中,礼俗往往通过具体的仪式形式,在特定的时空场域中,以象征性的方式,传达出某种祈福思想或文化观念。古人认为,礼俗中的仪式是神圣领域与世俗空间的链接点,人们通过某种仪式可以完成从一种生命状态到另一种生命模式的转变。如“成年礼”的完成,就标志着一个人由懵懂少年正式转变到承担社会责任与自我责任的成年阶段。一般而言,存在于特定地域时空场景中的礼俗,总以某种仪式的形式表现出来,具有一定的表演性。 “仪式的举行是演礼的实践”⑭,而且在具体的礼俗活动中,人们通过礼器、礼容、礼乐等完成一系列的礼法表演,表达与礼俗主题相符合的意义内涵,从而对观礼之人产生潜在的情绪感染与道德教化作用。例如,丧葬礼俗的仪式表演既传达一定的忠孝思想,又表达一种亲疏观念, “丧礼有关的信仰首先体现为儒家推崇的‘孝’的观念。远及祖先崇拜,近尊亲疏差序,由此社会构成一个和谐有序的格局”⑮。
有论者指出: “血缘纽带是差序格局的出发点,也是日常人伦展开的起点。”⑯在传统的乡土社会里,地缘是形成差序格局的物质性根基,人伦关系中的血缘关系则是维持这种根基的核心纽带。可见,差序格局在传统社会固有的体系中存在与运行,这个体系就是封建礼制。封建之“礼”既建构又维持着社会的人伦关系, “并因此使社会呈现出一种‘水波纹’式的差序格局。差序格局里既蕴涵着尊卑和远近,同时也包含着责任和义务”⑰。古人云,爱有差等。由于地缘、血缘、姻缘、学缘、友缘等关系的远近及亲疏不同,人与人之间存在亲疏远近是人伦关系的必然,人不可能毫无差别地同等对待每个人。封建宗法社会差序格局的形成实际上是由地缘、血缘、尊卑观念、等级思想等诸多因素所影响造成的。
在以人伦关系为结构的古代社会里, “伦是有差等的次序”⑱,传统社会的伦理观念讲究“贵贱有等” “内外有别” “长幼有序” “男女有别” “亲疏有差” “男尊女卑” “夫贵妻荣” “母以子贵”等,必然赋予人伦关系的差序性和等级性。在中国古代社会,君臣、父子、夫妇、男女、长幼等以一套严格的伦理界限区分,形成了差序的轻重等级, “差序格局否定人格平等的可能性,不承认权利义务之间的平衡,最终导致差序人格的产生”⑲。因此,在以家庭和家族为结构单位的传统社会里, “中国人的‘家’就像一个圆圈,圈住了自己及与自己有亲密关系的人”⑳,差序格局作为封建伦理的一种结构形式与结构表现,将每个人囿于“熟人”圈际内,实际上束缚了个体的自由发展。因为差序格局的内核是“礼”,而“‘礼’作为一种社会政治制度和伦理规范与‘仁’——最‘完美’的道德观念和品质融为一体,紧紧地束缚着个体、家族和亲族成员的行为规范”㉑。可以说,尊卑观念、孝道思想、长幼关系等几乎所有的伦理规范都浓缩到了古代社会生活相关的礼俗活动中,并对人起着束缚作用。
二
有论者指出, “以嫡长子继承制为核心的宗法制度,和以‘五福寿为先’为特征的‘五福六极’人生模式,同时形成于商、周之际”㉒。可见,自古以来长寿就是人们对生命质量的一种追求,而且在封建宗法社会里,老人长寿也是维系家族秩序的一种需要。因为在父权制的家族社会中,长者能以个人威望约束其子女的行为处事,保证家庭和家族的整体和睦,进而维持地方社会的稳定。在古代法律并不健全的乡土社会里,老人依靠封建礼制治家管家,既能维护大家庭的集体利益,又能调解儿孙小家庭的矛盾纠纷, “长者就是家族、秩序和权威的象征,家长的去世常常会带来家族的分裂或衰落”㉓。正因如此,在中国古代社会,统治者一般不允许老百姓的子女与家中老人“别籍异财”。唐宋时期,官府曾明令“父母在者,子孙不得别财异居” (《宋律》),元、明、清时代的官府也基本延续了前朝旧制。古人云“姜是老的辣”,喻指老人阅世广泛、历练深厚、视野和能力往往超出年轻人。从“老谋深算” “老成持重” “老当益壮” “老骥伏枥”等一系列成语中,不难窥见中国人自古以来就有一种视老人为权威的集体无意识与文化心理。
实际上,给长者祝寿既是巩固长者权威的舆论手段,也成为维护封建礼制“尊尊” “亲亲”局面的一种有效方式。传统家庭通过祝寿活动,邀请地缘、血缘、学缘、亲缘等相关相近的亲朋好友前来捧场道贺,能进一步确认“寿星”在家庭中的地位,同时又凝聚了大家族的血亲关系。封建礼制讲究“上治祖祢,尊尊也。下治子孙,亲亲也。旁治昆弟,合族以食,序以昭缪,别之以礼义,人道竭矣”㉔,其实就是一种有等级区别的差序之礼。这种差序鲜明地体现在“尊尊” “亲亲”的固有观念上,因为“周礼的基本构造,是在 ‘尊尊’与 ‘亲亲’的两个含有矛盾性的基本要求下取得谐和,使上下之间,除了尊尊的权势支配关系外,还有由亲亲而来的互相亲爱的感情,给权势以制约,这便使封建政治内含有一部分合理性”㉕。其实,以家庭长者为尊,以差序的爱为亲,就是封建宗法制按照血缘关系来区分家族嫡庶亲疏关系的一种体现。
孔子曰: “知者乐,仁者寿。”㉖古人认为,君子要有仁爱之心。对于一个国家而言, “君”即“父”;在一个家庭中, “父”即为“君”。在传统的世俗生活中,寿辰仪式以家族长者作为明确的主体,通过亲朋好友的现场叩拜与祝福来树立“父”的仁爱与权威,确立“父权”的尊者形象与地位。当然,家庭长者一般要到50岁“知天命”的年龄以后,才会正式举办寿礼。在传统家庭中,家长拥有绝对的权威与影响力,古代社会把一切尊崇都让位于长者,显现出以“老人”为本位的文化思想。元老重臣在古代政治生活中地位显赫,拥有较大的话语权;在乡土宗法社会中,长老、族老的身份也尤为特殊,他们往往拥有民间“礼治”的法外权限,是封建礼法的执行者与监督人。实际上,这些“元老”均为封建父权制的结构元素。因此,为家族中的“元老”祝寿,是父权制伦理思想在乡土社会的一种实践形式。
在等级社会里,身份决定地位,地位决定座位。封建伦理特别讲究尊卑观念,在寿辰仪式活动中,客人与寿星的亲疏远近关系和身份地位决定了其本人的座次;而且陪客也有讲究,贵重的客人必须由年长的主人陪,一般的客人通常由平辈或晚辈作陪,由此显现出寿辰仪式的“差序礼仪”。同样,在传统的丧葬活动中,也会显现出“差序礼仪”。古语云,亡人为尊。人死后成为了家族 “祖先”当中的一员,要接受家族网络关系中亲朋好友的祭拜,而拜祭者出场的先后顺序、跪拜位置、行礼动作等等礼节,依据与逝者的亲疏关系而存在差别。在丧礼中,主要执事者必须是与逝者血缘关系最亲的人,如儿子、兄弟、堂兄弟、叔伯、堂叔伯等男性;丧礼的生活用度则由逝者家族内的妇女或左邻右舍等来完成。㉗传统丧葬拜祭活动强调亲疏格局的差序之分,实际上既是表达对死者的尊重,也是封建孝道思想和尊卑观念的体现。正如“礼有五经,莫重于祭”㉘(《礼记·祭统》)或如 “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可谓孝也”㉙所言,丧葬礼俗的本义在于表达孝道思想与维持家族秩序。古人提倡厚葬久丧、服孝三年,倘若逝者子女无法做到这点,往往会被舆论视为是伦理秩序的破坏者,是“大逆不孝”。
“礼者,亲疏贵贱相接之体也”㉚,封建人伦关系以“礼”为价值内核,极为注重“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有序等级。我们不妨将这种人伦关系形象化地比喻为“从自己推出去的和自己发生社会关系的那一群人里所发生的一轮轮波纹的差序”㉛,即一种“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叙,朋友有信”㉜的差序格局。在“刑不上大夫”和“贵贱有等”的古代社会,人与人之间既没有法律上的平等关系,也没有人格尊严上的平等关系。正所谓“物之不齐,物之情也”㉝的差等逻辑,在以等级制度建构的差序格局中, “每个人都是君、臣、父、子、士、农、工、商等级序列中的一员,他们的等级身分是相对并且交叉的,是通过社会比较而得到确认的”㉞,因此个体的人格也必定是有差序的。在官场上,一个官员对上级而言是地位悬殊的下属,对下级而言则是他们的顶头上司,对民众而言则贵为“父母官”。即使 “天子”独尊于万民之上,他也必须 “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并不能凌驾于一切。面对“天命”与“圣人”,天子的人格也自然矮化一等,他还会受制于“父皇”与“母后”等长辈的管束。
三
为什么在差序人格的等级社会中,每个人自认贵贱有等、各安其命、各得其宜?因为封建伦理早已规定: “少事长,贱事贵,不肖事贤,是天下之通义也。”㉟在这种伦理规约下,每个人出生之后就必须遵从“少事长”的差序人格,必须遵从“贱事贵”的天下“通则”,要在自己所属的阶层里自甘“认命”。很显然,差序格局否定人格平等,“不承认权利义务之间的平衡,最终导致差序人格的产生;而具有差序人格的个体越多,差序格局的结构也就越稳固并反过来更加有力地塑造差序人格”㊱。
当然,在封建宗法社会里,人们对差序人格习以为常,因为恒常的“礼”早已成为固有的文化信仰。孔子曰: “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㊲即统治者只有以道德引导舆论,以礼仪规制社会,人们就会有廉耻感,且能端正自己。可见, “礼”是维系差序人格和稳固社会等级的最高规范,它是人们必须遵守的“天条”。正所谓“礼者,尊卑之差,上下之制也”, “礼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妻”㊳,礼的功能就在于建构等级观念与维持尊卑秩序。周公制礼作乐,将人划分为“天子、诸候、卿大夫、士、庶人”等三六九等,建立起严格的等级制,让不同等级的人归属不同的阶层,让其社会地位、政治权利和义务也各不相同,后来这种等级制在古代封建社会进一步发展。
封建统治者对民众从上到下极力灌输“贵贱有等,衣服有制,朝廷有位,民有所让”㊴的伦理观念,这种以礼为内核所形成的等级思想对个体而言如同“精神枷锁”,它既起到了遏制思想自由与扼杀人格独立的破坏作用,又是产生社会不平等的文化土壤与制度根源,最终会固化阶层流动,从而限制一个民族的创造力。古往今来,这种“从父” “从夫”和 “从子”的差序人格,更使得封建社会无数女子沦为失去人身自由与精神自由的“苦役”。儒家的“尊尊、亲亲”和“三纲五常”思想,在特殊时代里对维护古代帝王的家族统治起到一定作用,但整体而言,其糟粕远远大于精华。 “亲亲”与长幼有序的家庭关系相关,是家族社会的差序等级; “尊尊”既牵涉家庭和家族生活,也关乎政治领域; “三纲五常”则对君臣关系、父子关系与夫妇关系等至上而下的人格差序作出明确规定。可以说,在这些关系里面,几乎每一点都是桎梏人性自由发展的枷锁与牢笼。尤其是“男尊女卑” “贵贱有等”的等级观, “三从四德” “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贞洁观,极大地戕害了正常的人性,已然成为一种道德之恶。
当一种道德法则违背正常的人性与人道主义精神,以牺牲个体的自由意志和生命健康为前提时,那么这种道德法则并不是善的。亚里士多德曾说: “德性是与快乐和痛苦相关的、产生最好活动的品质,恶是与此相反的品质。”㊵在他看来,恶是美好德性的反面,与道德恶是一致的。中国古代思想家孟子认为,人之性善,所谓恶是放弃或迷失了本性。荀子认为,人之性恶,天下所谓善良是指合乎礼仪法度,遵守社会秩序, “所谓恶者,偏险悖乱也”㊶。中国封建社会的伦理道德有一部分往往贬低个体的生命价值,无视人的生命尊严与世俗愿望,甚至有相当一部分道德律令是男权文化的产物,专门用来禁锢女性身心自由发展的,实际上反映出制定道德法则的人往往以一己利益或集团利益为出发点。因此,我们不难发现,中国封建伦理观念里有一种非常“悖论”的奇怪现象,即普通男子可以拥有三妻四妾,封建帝王更是可以“后宫佳丽三千人”,而偏偏要求女人“夫死从子”从一而终的守贞洁,还要求女人以男人的审美癖好去“裹小脚”,大肆宣扬“女子无才便是德”,甚至还为节烈女树“贞牌坊”,褒扬她们以自我牺牲为前提的守节行为。这分明是男权文化中极为自私的思想糟粕。难怪鲁迅曾在《狂人日记》中假借狂人之口道出了封建道德的历史本相——“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㊷在以长者为本位和男权至上的封建社会里,道德文化的核心往往以牺牲幼者利益、无视女性尊严为基点。学者戴茂堂和江畅先生认为: “传统伦理道德以血缘关系为依据或回返自然性,这就等于取消了道德的超越功能。血缘关系的有限性和自然世界的自私性使传统伦理无法扩展为绝对的神圣法则,起码在逻辑上不能避免某些人被排斥在价值关怀之上。”㊸
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形成了重家庭、重群体、轻个人的伦理文化, “个人只能以孝忠为坐标在家族血缘关系中寻找自己的安身立命之所”㊹。加上以宗法血缘关系为底座的儒家伦理强调“克己” “修身”,注重个性的自我约束,一切以整体主义和群体利益为先,强调个人利益与价值必须让位于以 “家” “国”为代表的集体利益,因此, “家族为了维护表面和平的家风,每个组成份子必须敛抑自己的个性”㊺,家庭成员如果追求个体价值就可能被扣上“忤逆不孝”的高帽子,甚至被视为不守规矩、败坏门风。在传统家庭里,代表封建父权的“祖父” “伯父” “叔父” “父亲”和“长兄”始终处于尊者地位,尤其是家庭中德高望重的“长老”被抬到了家庭等级关系的塔尖上,使他拥有“一言九鼎”的家庭治理权力。在以家族为中心的社会里, “尊尊”的伦理观念一方面不断地强化了身份、性别、地位等各种差异,另一方面“把亲属关系以与父的亲疏远近而依次排序,形成等级差序的家庭人际格局”㊻。在这种格局之下,尊者为大,家庭长老的权力独裁与封建君主的权力独裁大同小异。封建礼法规定,子孙服从长老的教令是义不容辞的义务和责任,倘若家长以子孙“忤逆”或“不孝”的罪名到官府告状,官府无需调查就可以杖责处罚或定罪拘押这些“不肖子孙”,因此对于古代年轻人而言,家庭尊长的话永远是真理,服从其教令和管制乃是天经地义。 “正是夫妇、父子、君臣的儒家伦理思想建构了汉代以后中国传统社会的国家体制和社会秩序”㊼,长老独裁的家庭治理模式一定程度上保障了家族秩序的稳定,从而巩固了封建政权对社会的统治。
然而,在长老独裁的家长制文化语境中,个性活跃的年轻人必须服膺于老人的管制,他们的自主性与独立性容易被漠视,势必造成“代际冲突”。年轻人从小被灌输世代相传的“家风”与“遗训”,作为子女首先要做的是继承家业、延续“香火”,其次是通过个人奋斗进入仕途,光耀祖上“门楣”,却难有自己的意志、自由与人格平等。正如学者梁漱溟所言: “到处弥漫着义务观念之中国,其个体便几乎没有地位。”㊽在传统家庭中,以长者为本位,女性、幼者和年轻人统统服从长者的家庭治理,个人只是“小家”的成员,必须服从家庭和家族的整体利益。
中国封建伦理文化否定个人的主体价值、生命意志和人格尊严,否定个人本位,崇尚家族本位、社会本位和群体意识,注重“大我”,无视“小我”。传统的社会本位思想和家族伦理观念“必然抹杀个体生命的具体性和差异性,使个体无从展露生命的冲动”㊾,最终消解个人本位的主体意识。个人本位以人的价值衡量生命主体,强调个人是价值的主体,只有通过个人的努力奋斗,才能实现自我价值,创造个人幸福。到了“五四”时期,随着西方现代主义思潮涌进国门, “对自我意识较缺乏的中国人产生了强烈的刺激,大大促进了中国人的自我意识的觉醒”㊿,最先觉醒的一代知识分子认识到“立人”的重要性,他们认为封建伦理文化蒙蔽了中国人几千年,是时候揭露其扼杀个性自由的本质,呼吁与争取“人之觉醒”了。五四新文学呼应了“人之觉醒”的时代吁求,中国现代启蒙作家把对个人本位的价值弘扬置于家族小说的文学书写中,通过书写家族长老僵化与独裁的家庭治理模式,批判陈腐的家族本位思想;或借小说主人公“我是我自己的,谁也没有权力干涉”的心声表达,提出“寻找自我”的时代命题,并肯定年轻人为实现自我价值而表现出的叛逆精神。巴金的《家》、路翎的《财主底儿女们》、张恨水的《金粉世家》等家族小说,作者无一例外地集中笔墨揭示家庭长老的独裁治理与个人本位的价值冲突。
几千年来, “中国式”的封建伦理文化与伦理精神已形成一种强大的聚合力、约束力与破坏力,在巩固家族社会、为政治治理服务的同时,又强烈地否定主体尊严与自由, “制造出驯服的、训练有素的肉体, ‘驯服的’肉体”〔51〕,使人的精神高度奴化,从而制造出一代代 “顺民”。正如鲁迅所言: “中国人向来就没有争取过做人的价格,至多不过是奴隶。”〔52〕漫长的封建社会所形成的“国权不下县,县下惟宗族,宗族皆自治,自治靠伦理,伦理造乡”〔53〕,可以说,伦理的触须已深入到传统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每个人从出生直到死亡,一生都背负着莫名的伦理重负,尤其在男尊女卑的语境里,女性因袭和负载的伦理之压更重, “在家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无才便是德” “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等深入人心的伦理观念,却成为制造一个个家庭悲剧与人生悲剧的“祸水”源头。 “在帝国的历史上,女性的道德标准由早先无性别特征的美德如‘仁’ ‘智’等逐步发展为突出强调女性对婚姻的忠贞和对子女的奉献”〔54〕,中国古代女人根本毫无自我,她们的生命沦为了为丈夫、为孩子、为家庭服义务的奴隶之躯,从未有过独立的主体价值。
总之,一个社会的发展进步如果以牺牲弱者、牺牲女性为代价,那么它就是一种“非正义”的发展,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应该与女性受尊重、弱者受保护的程度密切相关。然而, “历史从来不是在温情脉脉的人道牧歌中进展,相反,它经常无情地践踏着千万具尸体而前进”〔55〕。数千年来,那些举着“伦理正确”旗号的“恶理”,对处于封建等级之下的弱者,形成了隐性的伦理镇压,也制造了数不清的人伦悲剧。由于封建伦理本质上并不是一种追求“人人生而平等”的公平伦理,而是强调“爱有差等、人有贵贱、男女有别”的差序伦理,因此必然掩藏着许多反人性、反人道的伦理思想糟粕,也必然在冠名堂皇的“仁义道德”之名义下,建构出个体精神层面的差序人格和社会的差序格局。
注释:
①⑨⑫㉘郑玄: 《礼记正义》,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667、413、58、258页。
②左丘明: 《左传》,岳麓书社2001年版,第33页。
③谢谦: 《中国古代宗教与礼乐文化》,四川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页。
④杨巧: 《道之以德,齐之以礼:传统社会的教化之道》,《西北民族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第4期。
⑤㉔孔颖达: 《十三经注疏》,王弼、韩康伯注,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76、1506页。
⑥王国维: 《王国维论学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页。
⑦⑱㉛费孝通: 《乡土中国》,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40—57、58、35页。
⑧樊凡、刘娟: 《“差序格局”抑或 “关系情理化”:对一个经典概念的反思》, 《华中科技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2018第2期。
⑩吴怡垚、徐元勇: 《先秦儒家礼乐文化的内涵及现代价值》, 《南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2期。
⑪彭林: 《中国古代礼仪文明》,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50页。
⑬龙柏林、刘伟兵: 《传统乐的文化整合功能》, 《重庆社会科学》2017年第2期。
⑭王秀臣: 《礼仪与兴象: 〈礼记〉元文学理论形态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81页。
⑮龙晓添: 《当代民间礼俗秩序与日常生活——以湖南湘乡丧礼为例》, 《文化遗产》2018年第4期。
⑯⑰贾永梅、胡其柱: 《“乡土社会”:以费孝通先生〈乡土中国〉为参照的解读》,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10年第6期。
⑲㊱阎云翔: 《差序格局与中国文化的等级观》, 《社会科学研究》2006年第4期。
⑳张积家: 《容器隐喻、差序格局与民族心理》,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5期。
㉑赵德利: 《血亲伦理悲剧的世纪建构》, 《青海社会科学》2000年第5期。
㉒㉓苏克明: 《中国民间祈寿习俗》,四川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3、13页。
㉕徐复观: 《徐复观论经学史二种》,上海书店出版社2005年版,第15页。
㉖㊲刘兆伟译注: 《论语》,人民教育出版社2015年版,第106、20页。
㉗陈淑君、陈文华: 《民间丧葬习俗》,中国社会出版社2008年版,第54页。
㉙㉜㉝万丽华,蓝旭译注: 《孟子》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101、111、111页。
㉚朱熹: 《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36页。
㉞梁劲泰: 《传统哲学中的等级思想分析》, 《新视野》2018第1期。
㉟孙安邦、马银华译注: 《荀子》,山西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81页。
㊳张岱年等: 《文化的冲突与融合》,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62页。
㊴朱日耀: 《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吉林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39页。
㊵亚里士多德: 《尼各马可伦理学》,廖申白译,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40页。
㊶李英健、李克译注: 《荀子》,万卷出版公司2009年版,第359页。
㊷〔52〕鲁迅: 《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25、212页。
㊸㊹㊾㊿戴茂堂、江畅:《传统价值观念与当代中国》,湖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36、303、210、308页。
㊺韦政通: 《儒家与现代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73页。
㊻汪怀君: 《传统家庭伦理的特征分析》, 《天府新论》2005年第4期。
㊼崔大华: 《儒学引论》,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839页。
㊽梁漱溟: 《中国文化要义》,学林出版社1987年版,第259页。
〔51〕[法]米歇尔·福柯: 《规训与惩罚》,北京三联书店2007年版,第156页。
〔53〕秦晖: 《传统十论——本土社会的制度文化与其变革》,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页。
〔54〕[美]罗莎莉: 《儒学与女性》,丁佳伟、曹秀娟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11页。
〔55〕李泽厚: 《美的历程》,安徽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第4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