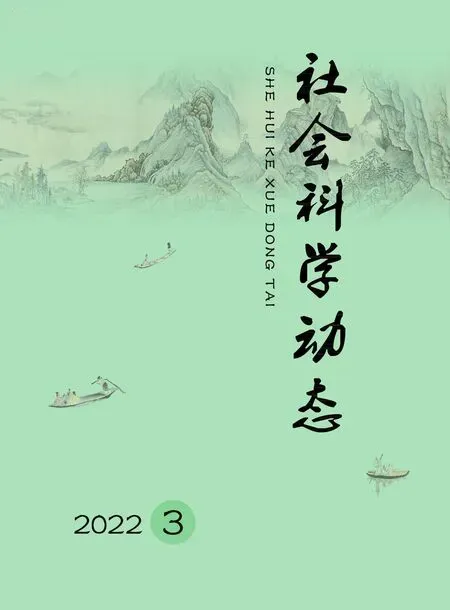人类初始性关系形式是杂交状态吗?
——恩格斯与韦斯特马克的争论
2022-02-02田静辉
唐 鸣 田静辉
时间可以追溯到距今130至100年前。1891年,韦斯特马克的《人类婚姻史》刚一问世,就得到了恩格斯的高度关注。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恩格斯多次提及《人类婚姻史》,不过不是赞扬,而是批评。其时,韦斯特马克年方29岁、初出茅庐,是一个尚不知名的青年学者;恩格斯已是71岁高龄、年逾古稀,乃世界知名的思想家。1921年, 《人类婚姻史》出第5版,按作者的说法是认真考虑了第1版出版后所有的批评意见;既然是所有的批评意见,当然应当包括恩格斯的批评意见;尽管在其中未提到恩格斯的名字,但却涉及恩格斯的观点。可以这样说,恩格斯与韦斯特马克的争论,恩格斯是指名道姓的直接批评,韦斯特马克是针对问题的隔空回应,争论围绕着人类初始性关系形式究竟是否是杂交状态这一问题而展开。
一、恩格斯的观点
恩格斯认为,在人类的早期历史中,存在着一个同从动物状态向人类状态的过渡相适应的杂乱的性关系时期。后来由习俗所规定的限制那时还不存在,或者说不存在后来习俗规定的对性关系的限制,现在或较早时期通行的禁规在那时是没有效力的。那时部落内部盛行毫无限制的性关系,每个女子属于每个男子,同样,每个男子也属于每个女子。不过这种杂乱的性关系状态在日常生活中并不是一片混乱,短时期的成对配偶是经常存在的,与杂交状态并不矛盾。
这样一种人类起初生活于杂乱性交状态的观点,并不是恩格斯提出来的。恩格斯承认这种原始状态早在18世纪就有人谈过,不过只是一般谈谈而已。在家庭史上,巴霍芬是认真对待这个问题的第一人,在其所著于1861年出版的《母权论》中,他把这个问题提了出来作为考察的中心,到历史和宗教的传说中寻找这种原始状态的痕迹。除巴霍芬外,麦克伦南、摩尔根等许多学者都持同样的观点。①恩格斯的主张直接源于摩尔根或受摩尔根的影响最大,这从《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副标题为“就路易斯·亨·摩尔根的研究成果而作”以及该书对此问题的论述都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
恩格斯支持人类初始性关系形式是杂交状态的根据主要有三:
第一,有证据证明这样一种状态确实存在。尽管恩格斯承认,人类性关系的杂交状态早已成为过往,属于非常遥远的时代,以致在历史所记载的最粗野的民族中间或者在社会的化石即落后的蒙昧人中间,都未必可以找到或者找不到过去存在的直接证据或者一个可以证实的例子②,但他仍然认为,在现实和历史中间,可以发现其在遥远过去存在的蛛丝马迹、片段或部分的证据。此外就是民族学的证据,恩格斯说: “不仅兄弟和姊妹起初曾经是夫妇,而且父母和子女之间的性关系今日在许多民族中也还是允许的。班克罗夫特(《北美太平洋沿岸各州的土著民族》1875年版第1卷)证明,白令海峡沿岸的加惟基人、阿拉斯加附近科迪亚克岛上的人、英属北美内地的提纳人都有这种关系;勒土尔诺也提出了关于印第安赤北韦人、智利的库库人、加勒比人、印度支那半岛的克伦人的同样事实的报告”。此外,历史学的证据,恩格斯接着讲: “至于古希腊人和古罗马人关于帕提亚人、波斯人、西徐亚人、匈奴人等的故事,在这里就不必说了”。③
第二,有迹象表明这样一种状态确实存在。恩格斯很有信心地说: “正像居维叶可以根据巴黎附近所发现的有袋动物骨骼的骨片,来确实地断定这种骨骼属于有袋动物,并断定那里曾经生存过这种已经绝迹的有袋动物一样,我们也可以根据历史上所流传下来的亲属制度,同样确实地断定,曾经存在过一种与这个制度相适应的业已绝迹的家庭形式。”④根据摩尔根的发现,美洲易洛魁人奉行着一种同他们实际的对偶制家庭关系相矛盾的亲属制度,这种亲属制度与19世纪上半叶夏威夷群岛上仍然存在的普那路亚家庭关系正好相一致;而夏威夷群岛上流行的亲属制度,又是同当地事实上存在的家庭形式不相符合的;夏威夷的亲属制度向我们指出了一种更加原始的血缘家庭的家庭形式,虽然这一家庭形式的存在已经找不到实际的例证,但它一定是存在过的,否则,就不会产生相应的亲属制度。从血缘家庭再往前推,就可以追溯到杂乱的性关系的社会阶段。因为,血亲婚配的观念是较后发展起来的。 “在血亲婚配尚未发明之前(这的确是一种发明,而且是一种极其宝贵的发明),父母和子女之间的性关系所引起的憎恶,并不大于其他不同辈的人们之间的性关系;而后者即使今天在最市侩气的国家里也还在发生,而且并不引起多大的惊骇;甚至年愈60的老‘姑娘’,如果她们十分富有的话,有时也可以嫁给一个30来岁的青年男子。不过,如果我们从我们所知道的最原始的家庭形式上抛弃那种与它们连在一起的血亲婚配的观念——这种观念跟我们的观念完全不同,而且往往是跟它们直接冲突的,那么我们就得出一种只能叫做杂乱的性关系形式了。”⑤恩格斯在此用的是从摩尔根那里拿来的倒推法:从现代社会老妇少男的结合,可见人们对不同辈性关系的容忍;从人们对不同辈性关系的容忍,可推见原始社会曾经有过这样一个初始状态,人们对父母与子女之间的性关系并不憎恶而是接受。人类的家庭形式既然在专偶制家庭之前有对偶制家庭,在对偶制家庭之前有排除姊妹和兄弟之间相互性关系的普那路亚家庭,在普那路亚家庭之前有排除父母和子女之间相互性关系、但不排除姊妹和兄弟之间相互性关系的血缘家庭,那么在血缘家庭之前就一定有不排除父母和子女之间相互性关系的杂乱的原始状态。
第三,有理由说明这样一种状态确实存在。对勒土尔诺、韦斯特马克等人否认人类曾经历过完全杂乱的性生活这个初期阶段所引用的人类以外其他动物界的例子,恩格斯判定: “它们对于人类及其原始生活条件绝对证明不了任何东西”。⑥尽管脊椎动物的鸟类中存在着忠实的专偶制的例子,但对于人类却丝毫不能有所证明,因为人类并非起源于鸟类。在哺乳动物中可以找出性生活的一切形式,从杂交、类似群婚的形式、多妻制,到个体婚制。至于类人猿的性关系状态,现有的材料相互矛盾,不能提供确定的知识,凡根据这样不可靠的报告而作出的结论必须加以摈弃。进而,恩格斯断言,动物社会对于推断人类社会确有某种价值——但只是反面价值而已。在较高等的脊椎动物中,只有两种家庭形式:多妻制和成对配偶制;在这两种家庭形式中,都只许有一个成年的雄者,只许有一个丈夫。雄者的忌妒,既联结又限制着动物的家庭,使动物的家庭与群对立起来。因此,不能用类人猿的家庭形式类推原始人类的家庭形式,因为动物的家庭和人类的原始社会是两不相容的东西,正在努力脱离动物状态的原始人类,为了在发展过程中脱离动物状态,实现自然界中最伟大的进步,需要以群的力量和集体行动来弥补个体自卫能力的不足。而成年雄者的相互宽容,没有忌妒,是形成较大的持久的集团的首要条件,只有在这种集团中才能实现由动物向人的转变。杂乱的性关系是同动物状态向人类状态的过渡相适应的,只有承认这个时期的存在,才能对原始人类由动物状态向人类状态的过渡做出合理的解释。
在论证人类初始性关系形式是杂交状态以及之后是群婚状态的过程中,恩格斯多次提及韦斯特马克,除个别是对所举例证的引述外,主要是对其观点的批评。对于韦斯特马克关于类人猿是专偶制的断语,恩格斯坚称根本不能作为证据。对于韦斯特马克把两性在生孩子以前一切成对同居状态都叫做婚姻的说法、杂交状态包含着对个人爱恋的压抑以及卖淫是这种状态的最真实形式的观点,恩格斯批评是戴着妓院的眼镜去观察原始状态,永远不可能对它有任何理解。对于韦斯特马克关于在印度的霍人、桑塔尔人、潘札人和科塔尔人部落以及某些非洲民族中于特定节日期间盛行的性关系自由,不是群婚残余,而是原始人和其他动物所共有的交配期残余的认定,恩格斯认为这一结论非常奇怪。
二、韦斯特马克的看法
韦斯特马克否定人类早期历史上曾经有过杂乱的性关系阶段的存在,在《人类婚姻史》中,他用长达七章的篇幅,从各个方面批判“乱交说”。⑦就直接对应恩格斯所作的论证来说,韦斯特马克否定人类初始性关系形式是杂交状态的辩驳主要有三:
第一,韦斯特马克对“实例”进行考察,否定人类性关系的杂交状态曾经是原始时代的普遍现象。韦斯特马克对古代的传说、古希腊人和古罗马人的记载、中世纪的各种说法,到19世纪和20世纪初一些作者(如艾夫白里、伯恩赫夫特、巴斯蒂安、菲茨罗伊、维尔肯、普莱特、施米特、范德利特、维卢茨基等)所举之例,进行了全面详细的考察, “得到的结论是,很难找到比那些记载更不可靠的资料了。其中,有的仅仅是理论家们的曲解,如性欲放纵、频繁分居、一妻多夫、群婚或其类似形式,或者没有婚礼礼仪,或者没有‘结婚’这个词,或者没有与我们相类似的婚姻关系等等,统统都与乱交混淆在一起了;而有的则是基于那些已被证明完全不可靠的资料”。 “在目前或不久以前,没有哪一个未开化的民族生活在乱交状态,这是显而易见的。这一事实,已足以使那些古典作者或中世纪作者在其简单而又含糊的报告中所提到的关于乱交一度盛行于任何民族的推测,全部发生动摇”。“即使真的有或曾经有某个民族生活于乱交状态,那也不能拿来作为证据,而断言乱交状态乃是原始时代的普遍现象。”⑧
第二,韦斯特马克对“制度”进行分析,通过否定摩尔根从类别式亲属制度中的夏威夷亲属制度推导出的“血缘家庭说”,进而否定其从“血缘家庭说”引申出的 “乱交说”。摩尔根的 “乱交说”是从他的“血缘家庭说”导引出来的,虽然他承认人类性关系的杂乱状态已湮没于实证的知识所不能达到的人类迷茫的远古之中了,但他仍坚信可以从理论上推断出这一状态的必然存在。具体来说,只要认定血缘家庭是社会的第一个有组织的形式,是家庭的第一个阶段,就可以推断出此前人类的性关系处于杂乱的原始状态之中。血缘家庭的存在,是摩尔根通过对类别式亲属制度中的夏威夷亲属制度的分析得出的结论。摩尔根把他公布的139个不同民族或部落所使用的亲属称谓分为两类,一类是说明式亲属制度,反映的是个体与个体之间的亲属关系;另一类是类别式亲属制度,反映的是群体与群体之间的亲属关系。他进一步把类别式亲属制度分为两种,一种是图兰—加诺万尼亚式亲属制度,其对应的是普那路亚婚姻和普那路亚家庭;另一种是马来式亲属制度即夏威夷亲属制度,其对应的是血缘婚姻和血缘家庭。在夏威夷亲属制度中, “所有的血缘亲属,不分远近亲疏,全都可以归入到五类之中。我自己,我的兄弟姐妹,我的从表、再从表、三从表以及更远的从表兄弟姐妹,属于第一类。对于这一类的所有亲属,全都使用同一称谓。我的父母和他们的兄弟姐妹,他们的从表、再从表以及更远的从表兄弟姐妹,属于第二类。对于这一类的所有亲属,同样不再加以区分。我对自己祖父母和外祖父母的兄弟姐妹以及种种从表兄弟姐妹所使用的称呼,等同于对自己祖父母和外祖父母的称呼,所有这些亲属属于第三类。我对自己儿女的从表兄弟姐妹所使用的称呼,等同于对自己亲生儿女的称呼,所有这些亲属属于第四类。我对自己兄弟姐妹及从表兄弟姐妹的孙儿女所使用的称呼,等同于对自己亲孙儿女的称呼,所有这些亲属属于第五类。同一类别中的所有个人,均以兄弟姐妹相称。”⑨摩尔根认为,上述亲属称谓实际上是对血缘亲属关系的亲疏和辈分的观点表达,不从群婚习俗的角度出发,无法讲清这种亲属制度的由来。从夏威夷亲属制度可以看出,很早以前一定盛行过婚姻集团按辈分来划分的群婚习俗,同一辈分者,既互为兄弟姐妹,也互为夫妻;不同辈分者,或者共祖父母、共父母,或者共子女、孙子女。这种仅仅排除了不同辈分之间性关系、同辈兄弟姐妹之间存在毫无限制性关系的家庭,就是血缘家庭。夏威夷亲属制度起源于血缘家庭,现行的夏威夷亲属制度表明早前的血缘家庭一定存在。但在韦斯特马克看来,摩尔根的“血缘家庭说”既没有根据,也违背常理。明显的事实是,所谓的兄弟姐妹之间毫无限制的性关系状态,在现存的任何未开化民族中都找不到;一个蒙昧部落的人可以因为不清楚自己的生父是谁而称好几个男人为父亲,但决不会因为不清楚自己的生母是谁而称好几个女人为母亲;一个女人如果称其他女人的儿女为自己的儿女,那也决不会是因为不清楚自己究竟是谁的生母;所以因不知其母而称上一辈的所有女性皆为母亲的说法是不能成立的。问题的关键在于,从夏威夷亲属制度推出血缘家庭必定存在的理论,是把某一社会现象解释为某种并未得到确证的历史状态的遗存。 “现实的社会状况可以为我们理解亲属称谓提供某种启迪。但是如果反过来,以某些亲属称谓来推断历史上曾存在过某种社会状况,那么这种推断大抵上只是一种猜测而已。”⑩韦斯特马克通过对历史与现实不同民族亲属制度特别是夏威夷亲属制度及其研究的比较和分析,得出自己的结论: “以亲属称谓制度为手段探索古代婚俗秘密的努力,尽管投入了大量的精力和才智,但迄今所得到的只是讹误,而不是正确的知识。”⑪从夏威夷亲属制度不能证明血缘家庭,更不能证明杂乱的性关系状态在人类的社会发展中曾经是一种普遍现象。
第三,韦斯特马克对“心理”进行研究,论证性关系的杂交状态构成人类社会历史上一个普遍阶段的不可能。在达尔文之前便有人指出,如果人类实行乱交的话,世界早就陷入男人之间永无休止的争斗之中了。达尔文则曾说过,所有雄性的四脚兽都有一种嫉妒心,这使得两性之间的乱交极不可能在自然状态中实行。⑫韦斯特马克认为,雄性动物总是以一种嫉妒之心将其所占有的雌性动物据为己有,如果在这种占有关系中有第三者介入,它就会发怒。尽管人类男子与一般的雄性动物很不相同,其嫉妒心带有爱的性质,并与屈辱感相伴生,因为嫉妒心的产生,总是因为失去或未能获得对某人的占有,而这种失势又会使一个人对自己的评价降低,但无论是人类或是动物,性嫉妒都是由于失去或担心失去对于自己性欲对象的独占权而产生的一种愤恨之情。性嫉妒的这一显著特点,既可以见诸动物,也可以见诸人类;既可以见诸蒙昧部落,更可以见诸文明民族。各民族的情况不尽相同,世界上的确有一些嫉妒心较弱的民族,但不能否认人类普遍具有嫉妒心。对有人根据一些蒙昧部落有借妻、换妻等习俗,得出这些部落没有什么嫉妒心的判断,韦斯特马克问到:当一个蒙昧部落的人仅仅是由于遵循自己部落的习俗,而把自己的妻子租让给某个来客的时候,又有谁能够确切地知道他内心的感受呢?韦斯特马克进而指出,人们可以有这样那样的感受,甚至是很强烈的感受,只是在某些特殊场合没有以言论或行动的方式明显地表现出来罢了。据此就说没有嫉妒之心,那就大错特错了。对有人关于嫉妒是一种较后发展起来的感情,人类在早期的群居生活中没有嫉妒之心,因而男女处于杂乱性交关系状态的说法,韦斯特马克辩称,没有任何例证能够证明早期人类的嫉妒心比其他哺乳动物弱。 “男性的嫉妒心不仅是乱交的强大障碍,而且由于其特有的暴烈力量还可能防止乱交的发生。”“那种认为乱交已构成人类社会历史上一个普遍阶段的假说,……是迄今为止在社会学探索的整个领域里显得最不科学的假说之一。”⑬
除上述考察、分析和研究外,韦斯特马克还通过对婚前不贞和“初夜权”、宗教性卖淫、借妻换妻以及节日纵欲、母权等问题的抽丝剥茧、条分缕析,否定人类初始性关系形式是杂交状态,虽然没有提到恩格斯的名字,但处处与恩格斯的观点截然相反、针锋相对。例如,对于一些未开化民族中存在的婚前不贞或婚前性自由,恩格斯认为是群婚制的残余,韦斯特马克认为是一种正常的求偶方式或在建立长久关系之前所进行的试婚。再如,对于“初夜权”现象,恩格斯认为起源于群婚制,是妇女为赎买贞操权利而作的献身牺牲或为个体婚而赎身,韦斯特马克认为或是源于普通百姓对初婚之血的恐惧,或是源于人们希望通过与圣者或权贵交媾而获得好处的想法。基于上述论说,韦斯特马克认为, “不能证明在某个民族的历史上,乱交状态曾是两性关系中盛行一时的形式,更不能证明乱交状态曾是人类社会发展中的一个普遍阶段,尤其不能证明这样一个阶段就是全部人类历史的起点。”⑭
三、我们的讨论和评论
恩格斯与韦斯特马克的争论过去已经100年了,时间的流逝并未使问题得到解决,至少在我国学术界对此问题仍然存在着不同意见的分歧。今天我们重拾此话题并进行讨论,无论是从认识人类两性关系变迁的历史来说,还是从探讨人类社会制度最初的起源来看,都有一定的意义。
(一)什么是人类性关系的杂交状态?
恩格斯与韦斯特马克各自眼中的人类性关系的杂交状态其实是有区别的。在韦斯特马克看来,人类社会自始便实行的是一夫一妻制;一些学者所谓的人类性关系的杂交状态,是指一个原始群或一个部落中所有的男人,可以不分彼此地同所有的女人发生关系,由此所生的子女,属于整个群体的状态;是指当时尚无个体婚姻存在的群婚状态。在韦斯特马克那里,乱交与群婚是同一个概念。在恩格斯看来,人类性关系形式有一个发展过程,一开始是杂交,继而是群婚,接着是对偶婚,再后来是专偶婚,杂交是人类初始的与群婚不同的性关系形态。虽然群婚与杂交都是一群男子与一群女子之间的性关系状态,但群婚中的血缘群婚排除了父母和子女、不同辈分亲属男女之间相互的性关系,群婚中的普那路亚群婚不但排除了父母和子女、不同辈分亲属男女之间相互的性关系,而且排除了姊妹和兄弟之间相互的性关系,而杂交则既不排除姊妹和兄弟之间相互的性关系,也不排除父母和子女、不同辈分亲属男女之间相互的性关系。是否排除父母和子女、不同辈分亲属男女之间相互的性关系,是区分群婚和杂交的关键。只要存在父母和子女、不同辈分亲属男女之间相互的性关系,那么就是杂交;反过来说,只要排除了父母和子女、不同辈分亲属男女之间相互的性关系,无论性关系的状况如何,都不是杂交。而且,杂交之所以被称为状态,是因为它不是个别的例外,而是普遍的情况;杂交不是某个部落或原始群的特殊现象,而是全体人类在从动物状态向人类状态过渡时普遍都有的一个历史阶段。
按照恩格斯关于人类性关系杂交状态的界定,如果要认定人类初始性关系形式是杂交状态,就必须找到能够证明人类初始阶段父母和子女、不同辈分亲属男女之间相互性关系普遍存在的证据,或者对人类初始阶段父母和子女、不同辈分亲属男女之间相互性关系曾经普遍存在做出有说服力的推论。
(二)证明人类初始阶段性关系杂交状态曾经普遍确实存在的证据情况如何?
力主人类在最早的家庭形式——血缘家庭之前有一个性关系的杂交状态阶段的摩尔根,明言该阶段的存在只是理论上的一种推论,实际上没有办法通过实证调查获得证据。 “这种男女杂交的状况,表示在野蛮阶段中可能想象的最低状态——它代表人类进步阶梯的最下阶段。……杂交可以从理论上推论出来作为血缘家族的一种必要的先行存在的社会状态;但是,这种事实已隐蔽于人类远古迷雾之中,而为实证的知识所能达到的范围以外了。”⑮
韦斯特马克把一些学者提出的用以支持“乱交说”的各种例证概括为两个方面,一是某些民族在某些古代和现代著作中被认为曾经或仍在过着乱交生活,二是某些习俗被人们想象为系从尚无婚姻存在的文明早期阶段流传下来的遗风。韦斯特马克通过自己的分析认为,这两个方面的例证或者观察记载有误,或者解释说明有错,都不足为证。
恩格斯在此问题上的看法似有前后相互矛盾的地方。如前所述,他一方面承认,在社会的化石——落后的蒙昧人中未必可以找到杂交状态在过去存在的直接证据;另一方面又认为,父母和子女性关系被允许的实例在今日许多民族中可以找到。不过,综观恩格斯的整个论述,从批评巴霍芬到历史的和宗教的传说中寻找原始状态的痕迹,并没有追溯到杂乱的性关系的社会阶段,只是追溯到群婚制。即便是血缘家庭,在历史所记载的最粗野的民族中也找不出一个可以证实的例子来,血缘家庭这一家庭形式的存在,现在我们在任何地方都不能加以证明,所以恩格斯的观点应当是:在历史和现实的人类社会中都不可能找到性关系杂交状态曾经存在的直接证据。大量和普遍的人类学调查表明,在全世界所有的人们共同体即便是最为落后的部落或原始群中,父母和子女发生性关系的情况要么根本不存在,要么只是触犯乱伦禁忌的个例。⑯个例的存在并非被允许,更不能说明一般。
没有直接证据,可否从动物界特别是类人猿那里寻找人类性关系的杂交状态曾经存在的间接证据呢?因为人类来自动物界,类人猿是人类的近亲。韦斯特马克赞同从动物界特别是类人猿那里寻找证据,不过他是从否定的角度去寻找证据,以证明人类性关系杂交状态从来不曾存在。他认为, “婚姻植根于本能,只能用生物学事实才能予以阐明”。“家庭可能就是从作为类人猿和原始人之共同祖先的高级灵长类原种那里继承下来的遗产。”⑰
对从动物界寻找否定的证据,恩格斯特举一例进行讽刺: “如果严格的专偶制是各种美德的最高峰,那么优胜的棕叶就应当属于绦虫了,因为绦虫在其50—200个关节或体节的每一节中都有完备的雌雄性器官,终身都在每个体节中自行交合。”⑱对从类人猿那里寻找否定的证据,恩格斯坚决地予以否定之否定。诚如前述恩格斯所说,19世纪关于类人猿性关系状态的观察和研究还很初步,几乎未能得出丝毫确定的知识,且获取的材料彼此都是直接相互矛盾的,不足为据。
恩格斯所著《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是1884年出版的,时间已经过去100多年了。应当承认今非昔比,100多年来,灵长类动物学得到了长足的进展,今天科学家们对类人猿的观察和研究已经较为深入和全面,现在我们对于类人猿的家庭集团已经有了一些确定的知识。我国学者张鹏称:“在对野生黑猩猩的长达30年的长期调查中,从未见过母亲与成年儿子间的交配,偶尔出现兄弟姐妹交配现象,基本上是哥哥要求与妹妹交配的现象。”⑲20世纪70、80年代,科学家们在对坦桑尼亚贡姆河国家公园野生黑猩猩群的观察中发现,黑猩猩群兄弟姐妹之间基本不发生或很少发生性关系,未见母子之间发生性关系的情况。年轻的雌黑猩猩多在自己所在的群体之外寻找她们所不熟悉的雄黑猩猩,并发生性关系,而在接受自己所在的群体内的成员为性伙伴方面,雌黑猩猩表现得很谨慎。1980年,一位名叫安尼·蒲赛的研究者在其观察报告中写到: “当有在同一群体之中、年龄大到足以做她们的父亲的雄黑猩猩试图与雌黑猩猩交欢时,那四只雌黑猩猩常常会尖叫着撤退;而在同一时期,对于较年轻的雄黑猩猩的求爱她们则会以呈示生殖器并与他们性交来欣然作出回应。”荷兰皇家艺术与科学院院士、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和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美国艾默里大学灵长类动物行为学教授弗朗斯·德瓦尔对此评论说: “那些年轻的雌黑猩猩不可能知道谁是她们的父亲,但通过拒绝与既老又熟悉的雄黑猩猩们性交,她们避免了被可能的父亲受精。” “有强烈的迹象表明,黑猩猩们会自愿或主动避免乱伦。有些人类学家将人类的乱伦禁忌看成纯粹是文化的产物,甚至看成是超乎动物行为之上的一个‘最重要的提升’,但生物学家们却倾向于认为它是一种已经渗透到所有文化中去了的自然规律。”⑳弗朗斯·德瓦尔并不否认,他在对荷兰阿纳姆动物园一个岛屿上放养的黑猩猩群观察中发现,黑猩猩群中个别母子发生性关系的情况也还是存在的。不过这种个别特例作为间接证据,与前述直接证据一样,不能说明一般和普遍。可能有人会说,现在不是过去,类人猿不是人类,从今天类人猿的性生活状况不能类推人类远古时期可能有的性生活状况。但不论怎么说,有一点却是确定的,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从类人猿那里都找不到人类性关系杂交状态曾经存在的间接证据。
(三)对人类初始阶段性关系的杂交状态曾经普遍确实存在的推论情况怎样?
恩格斯反对从对类人猿的观察和研究中寻找人类初始性关系形态的间接证据,他说: “用现今类人猿那样的生活条件根本无法解释向人类状态的过渡;这种类人猿给我们的印象,毋宁说是一种正在逐渐灭绝的、至少也是处于衰落状态的脱离正轨的旁系。只此一点,就足以驳倒由它们的家庭形式类推原始人类的家庭形式的任何论调了。”㉑正是从这一点出发,恩格斯提出了人类初始性关系的杂交状态曾经普遍存在的主要推论:人是一种没有武器的动物,只有形成较大的持久的集团,以群的联合力量和集体行动弥补个体自卫能力的不足,才能实现由动物向人的转变;高等动物的群与成年雄者的忌妒相互矛盾,与家庭相互对立;正在努力脱离动物状态的原始人类,成年雄者没有忌妒,人们不以家庭为单位而以群为单位生活在一起,因此其性关系必然处于杂乱的状态。
恩格斯的这一推论是建立在一系列假设的基础之上的:其一,原始人类实现由动物状态向人类状态转变的必要条件是较大、持久的集团群居生活;群居生活的基本前提是成年男子没有忌妒和人们没有家庭;在成年男子没有忌妒和人们没有家庭的情况下,人类的性关系形式一定是杂乱的状态。韦斯特马克把主要或基本建立在假设基础之上的“乱交说”称之为最不科学的假说。我们认为,建立在假设基础之上的理论并非不能成立,或许需要具备一定的条件,但在通过一定的途径得到确凿无疑或者相当程度的证实之前,最好还是将其视为假说而不是定论较为妥当。
其二,就恩格斯理论自身的逻辑而言,也并非全无值得斟酌与推敲的地方。恩格斯认为,在人类初始性关系杂交状态之后的第一个家庭形式是血缘家庭,血缘家庭是排除了父母和子女、不同辈分亲属男女之间相互性关系的家庭,但恩格斯并没有说明为什么在这种家庭形式中生活的原始群不能形成较大、持久的集团,这种家庭会与原始人类的群居生活相互对立;为什么排除了母子之间、父女之间乃至不同辈分亲属之间相互性关系,原始群就会分裂,人类就不能实现从动物状态向人类状态的过渡;为什么人类初始的性关系形态不会是排除了母子之间、父女之间乃至不同辈分亲属之间相互性关系的形态。别的不说,仅就母子关系而言,我们难以设想,原始群中母子之间的亲密关系会因排除了彼此之间的性关系而受到影响,排除母子之间相互的性关系会引发原始群出现不可调和的矛盾,进而导致群体的分崩离析。
最后,从普那路亚群婚、血缘群婚倒推此前的状况,是恩格斯推论人类初始性关系形式为杂交状态的另一条路径: “我们所知道的群婚形式都伴有特殊复杂的条件,以致必然使我们追溯到各种更早、更简单的性关系的形式,从而归根结底使我们追溯到一个同从动物状态向人类状态的过渡相适应的杂乱的性关系的时期”。㉒然而,前苏联曾有学者根据20世纪人类学的研究认为: “现代科学既没有证明人类从前存在过血缘家庭的资料,也没有证明人类从前存在过普那路亚家庭的资料。不仅如此,而且可以十分肯定地认为,这些家庭形式从来没有存在过。”㉓血缘家庭、普那路亚家庭在人类历史上是否存在过,另当别论。假设血缘家庭、普那路亚家庭确实从来没有存在过,那么从普那路亚群婚、血缘群婚倒推人类初始性关系形式为杂交状态的努力,也就确实不能说是成功的了。
综上所述,回顾当年的那场争论,结合现时的一些思考,我们得到的一个初步结论是:不能肯定地认为人类初始性关系形式是杂交状态,尤其不能简单地认为人类初始性关系形式是未排除父母子女之间、不同辈分亲属之间相互性关系的杂交状态。我们可以对这样一个带有“仰望星空”色彩的、事关人类社会“我从哪里来”的问题,综合地运用人类学、民族学、考古学等多学科的方法和资料,做进一步深入的探索和研究。
注释:
①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只提到麦克伦南关于内婚制、外婚制的研究和观点,未讲麦克伦南也持人类在婚姻制度产生之前曾经历过杂乱性关系状态的看法。关于麦克伦南在此问题上的看法,可参见[芬兰]E·A·韦斯特马克: 《人类婚姻史》,李彬译,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第101—102页。
② “甚至在历史所记载的最粗野的民族中间,也找不出一个可以证实的例子来。” (恩格斯: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38页)这是恩格斯在谈血缘家庭已经绝迹了时说的话。既然血缘家庭都找不到一个可以证实的例子来,那么人类原始的性关系杂交状态就更是如此了。
③④⑤⑥⑱㉑㉒恩格斯: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36、30、36、32、32—33、35、35页。
⑦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的“杂交”与韦斯特马克《人类婚姻史》中的“乱交”,究竟是中文翻译的不同,还是原文即有别,因笔者没有这两本书的英文版而不得而知。还请殚见洽闻者赐教。
⑧⑨⑩⑪⑫⑬⑭⑰[芬兰]E·A·韦斯特马克:《人类婚姻史》,李彬译,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第120—121、221、240、255、278、308—310、277、31、73页。
⑮[美]摩尔根: 《古代社会》,商务印书馆1971年版,第874、877页。
⑯[美]康拉德·菲利普·科塔克: 《人性之窗:简明人类学概论》,范可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311—313页。
⑲张鹏: 《猿猴家书——我们为什么没有进化成人》,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第145页。
⑳[美]弗朗斯·德瓦尔: 《黑猩猩的政治:猿类社会中的权力与性》,赵芊里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4年版,第188—190页。
㉓[苏]Ю·И·谢苗诺夫: 《婚姻和家庭的起源》,蔡俊生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4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