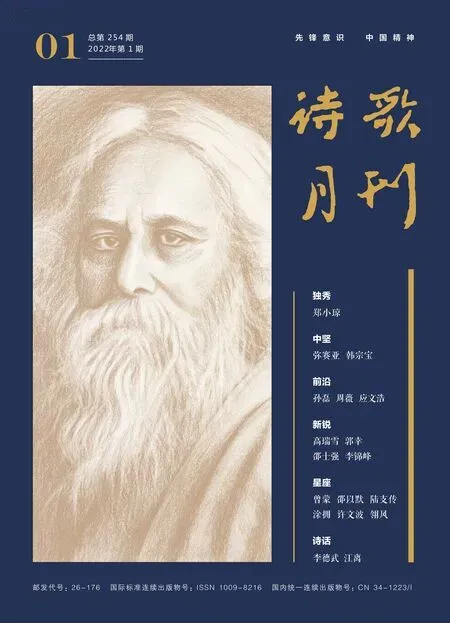从冰凌到滴水
2022-01-28李德武
一个诗人和作家的写作总是不同程度受到其处身之地的影响。这种影响要么是天然的,比如湖畔派诗人所表现出的精神和风格与地理环境的高度契合。华兹华斯每天在山水间漫步,寻找诗歌创作的灵感。自然不仅为他提供了创作素材,也为他提供了精神范本。要么是气质上的,即地理上的气候特征影响到诗人气质,使得同一气候下的诗人气质具有类似的面貌。比如俄罗斯和东欧等寒带地区的诗人都具有一种白银的气质,硬朗、纯洁而忧郁。
我在哈尔滨生活了20多年,尽管哈尔滨的地理气候属于亚温带,但无霜期只有半年时间。寒冷气候对诗人的气质影响表现在诗人们对冰雪情有独钟。若用水的不同形态来形容,我的早期诗歌语言坚硬,具有冰凌一样的锋利;而同为哈尔滨诗人的张曙光的诗则具有一种松散而剔透的雪的特质;诗人桑克的诗则越来越具有春天开江时冰排的特征,硬朗,冲撞,带着由破碎获得的动力奔流而下。冰雪的气质是一种内柔外刚的气质,具有决绝感的纯粹性。我在来苏州之前,对自身气质和地理气候之间的关系是不自觉的。也正是不自觉才让地理和诗人之间的气质关系变得天然可爱。
或许是寒冷的刺激让人的身心本能收缩的缘故吧,北方诗人的对抗性比较强。毫无疑问,这种对抗意识源自内心对某种东西的捍卫。我过去的诗歌就存在这样的问题,且在对抗(批判或揭示)中越是用力,内心收缩的就越紧。我从俄罗斯白银时代的诗人身上也发现了这一点。但这些问题在布罗茨基后期的诗里就很少见到,这也许和他离开俄罗斯寒冷的气候有关。
诗人受地理影响还有一种有趣的现象,就是交往方式。北方由于寒冷,诗人之间的交游唱和不可能像江南诗人那样经常发生在户外,而只能在室内。因此,诗人之间饮酒畅谈是常有的方式。这使得北方诗人都具有某种易于冲动的豪气。冬天的荒凉、单调要靠诗人内在的创造去弥补,而那种铺天盖地的沉寂需要火焰和热血才能将其激活。
还有另一种地理与诗人的关系,这种关系体现为诗人把某种地理环境和景观升华为一种艺术理想加以追求,或作为一种普遍境遇的象征加以审视。比如谢灵运摆脱对老庄思想的依托,把目光投向山水本身,使得之后的山水诗有了山水的本体特征。希腊诗人埃利蒂斯把爱琴海的阳光作为他诗歌情感和语言的理想模式,正如他的著名诗篇《疯狂的石榴树》给人一种热烈、奔放、扑面而来的冲击力。聂鲁达笔下的马楚·比楚高峰可能更代表了他对写作的雄心。艾略特把“荒原”处理成一个象征物,一个地理上的象征物,我们可以把它看作是战后的欧洲,也可以看作是世界的普遍现实。除此之外,地理并不总是以宽容和慈爱的面容与诗人相伴,有时它代表绝望和苦难。比如西伯利亚对于曼德尔斯坦姆,奥斯维辛对于保罗·策兰。每个诗人都会有一个地理留给他的擦不掉的胎记或疤痕。
2002年8月,我举家迁往苏州定居。吸引我作南北长途迁徙的动力是我对江南文化的渴慕。我在大学为学生讲授古典诗歌时,切身感受到语境的陌生。我意识到这种欠缺不是文本上的,而是地理上的。我缺乏的不是对古典诗歌的理解力,而是感受力和体验。第一次我强烈意识到诗意的地理特征是如此重要。当我来到苏州,漫步在山塘街和胥江河岸时,在内心默默嘀咕着:“白居易、刘禹锡,今天我离你们近了,我正走在你们当年走过的街道上。”这种欣悦感不是因为攀缘上唐朝的大师,而是我对唐诗的语境不再停留在想象和猜测阶段,我看到了“春来江水绿如蓝”的感性景观。由绿到蓝,江南的水不只是水,而是水与天的对话,其丰富性和绚烂多姿是北方的水(包括雪与冰)无法比拟的,足以作为江南诗意的代表。一天的不同时间,一年的不同季节,水所表现出的样态都是不同的。为了感受枕河而居的古老苏州韵味,我买的房子就在护城河边上。我越是靠近水就越是认不清它的面目。这时我似乎找到了白居易写出“绿浪东西南北水,红栏三百九十桥”的语感和心境。巧的是,白居易《正月三日闲行》这首诗写的乌鹊桥就坐落在我居住的十全街上。
江南地理对我写作的改变可以从我对水的态度上得到窥探。首先从视觉上我不再像面对雪时那样因强烈的反光而本能地眯起眼睛,而是和水形成一种对视。我从水的变化中也看到了自己的变化,而这一切都在波澜不惊中发生,仿佛有一种无形的力量带动了生命的流动,在那流动的水中具备了天上人间的一切美景。这种美令人沉浸而忘我,它既现实又艺术,既是人间的又是天赐的,让人不禁慨叹天然画本的美妙。一度我迷恋游山玩水,我知道山水的画工远比我的书写完美高级。在诸多的经典中,我太欠缺品读江南山水这一课了。坐在憨山大师当年住持的永慧禅寺里,眺望水天一色的太湖,我看到了烟波浩渺这句成语的出处。在缥缈峰下的水月禅寺里,我也体会到了水月的至高情怀和境界。无数次站在枫桥上看自己的倒影,想到唐朝的张继那颗忧国忧民的惆怅之心。我写了太多关于水的诗,包括夜里听雨。我不由自主地正从一块冰凌变成水滴。是的,我比在北方柔软了许多,也灵活了许多。我那固守自身存在的边界正被某种流动性所打破。在显示尖锐方面,我更喜欢某种滴水穿石的韧劲。而在对话上,我一改對抗的锋利,而变成内省和自修,在有限中感受无限。比如我在《滴水居》一诗中写到:“边界终将消失,一滴水/小到不可分,这样好,我可安居。”
但我并没有抹掉北方留给我的烙印,我也从没有因为南方的丰富性而嫌弃过北方的单调。相反,来到南方才让我对北方的地理和气质产生全新的觉知和感受。我发现有很多北方的美当年并不在意,比如冰凌坠落带给我们的快乐,比如在雪地散步时雪发出的类似骨骼断裂的声音对大地寂静的深刻回应,包括雪在北方具有的生机感等,这些全新的感觉都是我离开哈尔滨之后体会到的。
这些记忆之所以铭记在生命之中,都是因为它是地理写就的,也即天赐的。我也感谢北方生活的经验,让我对江南的美更加敏感,也更加珍惜和自觉。
如今我不再强调北方与南方的区分或对立,它们同时存在于我身上。同时,我提醒自己不要基于风格的成功学和对传统的亲近让自己落入某种地理的模式化图景之中。这种自觉也反映在苏州诗人车前子和小海身上。车前子虽然是苏州人,但他的诗歌地理不是景观的,而是文字的。在我所见的当代诗人中只有车前子把文字看作是自己的诗歌地理。而小海的诗歌地理也不是苏州或海安,而是经验,小海从他的经验中获得元语言。我的诗歌地理属于德勒兹所说的游牧,我不在某一个领域持久驻足,而是不断地告别,通过对语言和形式的创新让自己不断朝向陌生的领域。
坦白地说,我可以在语言和情感上融入江南的细腻和精致,就像一个大刀阔斧的人在江南学会雕刻一方印石。但我不希望自己被定格为江南诗人,不知为什么我总觉得江南太计较了,一种事无巨细的计较。这种计较和岛民的自闭不一样,江南的地理局限在于丰富的人文积累,它太满了。这是一个不容易发现的死穴,即越是完美的越没有变化空间,从而陷入内卷。这种悖论也存在于海岛文化之中。我到了海南才发现四面环海的人眼界和心胸并不一定宽广,反而可能更闭塞。大海比陆地更具有原始的荒凉。任何地理上的特点都可能是某种局限性的东西。为此,我更倾向于艾略特在《但丁于我的意义》一文中谈到的,诗人应该有超越他所属地理空间的“情感范围的宽度”。我没有把园林和江南山水当牙签含在嘴里,而是通过系统地阅读中西哲学,让自己拥有更宽阔的境界。如果我哭泣,我相信我的眼泪不会仅仅属于江南的水滴。
李德武,1963年生于辽宁彰武,现居苏州。著有诗集《窒息的钟》《李德武诗文集》,哲学诗学随笔集《挣脱时间的网——从芝诺的两个悖论说起》《在万米高空遇见庄子》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