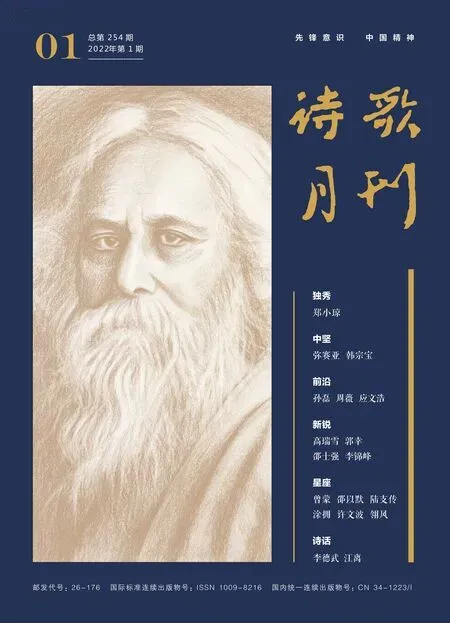积雪(组诗)
2022-01-28韩宗宝

韩宗宝,1973年生于山东诸城,现居青岛胶州。中国作协会员,山东省作协第三批、第五批签约作家。曾参加全国青创会、《诗刊》社第25届青春诗会、《人民文学》“新浪潮”诗会。著有诗集《一个人的苍茫》《韩宗宝的诗》《时光笔记》《潍河滩》《隐忍的抒情》等。
蒙古马
一匹枣红色的蒙古马
从蒙古出发又回到蒙古
蒙古草原上最烈的蒙古马
仿佛早晨刚升起的太阳
当它奔跑 整个草原都在欢腾
风吹着草原 长长的马鬃飘扬如草
当它安静地吃草 整个草原都安静下来
只有马嚼青草或夜草的声音如烈酒
一匹肥壮剽悍的蒙古马
它没有骑手和缰绳 它月光般自由
它是自己的主人 整個苍茫辽阔的蒙古
大草原都是它的疆域 都是它的家园
风吹到哪里它就能跑到哪里
它的血液里有青草的力量
它的四蹄被更多的青草所托举
它不是在奔跑 它是在青草上飞
在蒙古草原上 远远地注视一匹
仰天长啸的枣红色蒙古马 我听到的
不是激烈的嘶鸣 而是马头琴和长调里
突然倾泻而出的春天和花朵
大马群
这奔跑在宣纸上的大马群
简直不像是一群马
像一个横在草原远处的
大写的浑然的苍茫的一字
像不断翻滚涌动着的千里阵云
夹杂着隐隐的雷声和风声
它们仿佛正被某种超自然的
巨大而神秘的力量驱赶着
又仿佛是在黑暗和黎明中
热切地向前追赶着什么
寂静
河谷里现在没有人
只有息下来的风和落日
风吹河水的样子很美
但水没有声音
河边上那块突兀的石头
让这里更加寂静
岸上的草 茂密不堪
有些甚至伸到了河水里
四周的光线渐渐暗下来
但暮色依然是透明的
像那些清凉凉的水
光线里浮动着芦苇的芬芳
一只夜鸟呀地叫了一下
自顾自地远去了
把这里悉数交给了
那些开始鸣叫的虫子们
鸫鸟
这个寂静的下午
在林子的边缘
我听到
一只鸫鸟在叫
一只孤独的鸫鸟
它的叫声欢快 明亮
如果仔细听
似乎夹杂着些悲伤
我不知道
在这个林子的深处
会不会还有
另外一只鸫鸟
我犹豫了一下
没有向林子的深处走去
紫色鸢尾花的下午
后来我看到了那个下午
你插在花瓶里的
紫色鸢尾花的下午
窗外的夕阳已不再燃烧
褪尽了红和热 激情
渐渐地冷却下来
此刻 鸢尾花的紫
是冷静的 非常纯正
那种平静的美 弥漫开来
空气中的夕光散尽之时
鸢尾花的紫 重新还原为紫
它已经超越了一束花
它是整整一个下午
整个下午 再没有别的事物
只有鸢尾花和它的紫
那个下午 鸢尾花的紫
是它自己的颜色
也是一幅油画最明亮的部分
积雪
必须在高原 才能
看到这样冷峻的积雪
它们坚忍 超拔 在炽烈的
阳光下寂静 无言
尤其是山顶上的积雪
洁白 陡峭 苍茫
如何才能洞见积雪内部
坚硬的幽暗和明亮
如何让光芒 俘获
这空荡荡的肉身
积雪在上 苍天在上
谁比山顶还要孤独
雪山顶巅的积雪
众神放牧的羊群和白云
在山顶紧抿着高傲的嘴唇
始终对世界三缄其口
你见过雪崩 就知晓积雪
潜在的沉默和力量
在山顶 有更高的积雪
不是山顶 是山顶的积雪
这更高的积雪 内心
充满拥挤的痛和秘密
一个人身体内部的积雪
无限地接近天空和神
雪豹
在寂静无人的雪线附近
在高山和雪地间
经常会看到
一只昼伏夜出的雪豹
它机敏 警觉
拥有雪崩般的速度
这当之无愧的雪山之王
它主宰着世界和整座雪山
只有在叙述它时
你才能清晰地感觉到
那种潜在的危险——
一只雪豹的注视
雪一样灰白相间的毛发
伺机而动的巨大豹尾
在暮晚 面对一只野山羊
眼神流露出刺骨的寒冷
夕光中的蝙蝠
它们热衷于哲学
它们在人间的黄昏谈论死亡
它们集体在大地上的飞翔
时快时慢 时高时低
它们有比星空还辽阔的听觉
它们穴居 它们在夕光中
引送亡灵 它们是岩石上的倒立者
白天它们是沉默的绝大多数
它们只在傍晚降临 在夕光中抵达
人类的上空 在光明的根部
它们的出现是异样的
它们在捕捉什么 死亡的阴影在扩大
夕光中的蝙蝠 撕开夜色和伤口
为危险命名 它们隐忍的表情
表达了什么 描述一只盲目的蝙蝠
是困难的 真理在夕光中坍塌
剩下的是眼睛和事物的咽喉
比時光和黑暗更深
它们推迟了世界的羞愧
让旷野和村庄不断陷入失眠
这些陌生的生物 向火挑战
仿佛灰烬 终生被人类所反对
它们从不辩驳 它们用飞翔赞美
自由 孤独和舌尖上的盛宴
螽斯
一只翠绿色的螽斯
在夏日的夜晚 在潍河滩上
在故乡空旷的黑暗里
不住地鸣叫 村庄里稀疏的灯光
照着空空荡荡的街道
以及老人和孩子们的恓惶
螽斯 这大地上的乡间
演奏师 在浩瀚又繁密的
灿烂星空之下 在日益凋敝的
乡村小学的操场上
在暮晚 孤独地演奏
已经无人聆听的小夜曲
我曾试图把一只螽斯
这乡村的演奏师 从广阔的潍河滩
带到城里去 城里有听众却没有
它所热爱的白菜和青草
我无法想象和忍受 一只翠绿的
饥饿的螽斯在城市的夹缝里叫
旧唱片
唱片机已经不在了
旧唱片还在
薄薄的一个圆
一圈又一圈的声音
仿佛还在荡漾
旧年连着新年
在新人和旧人之间
隔着一张旧唱片
一个简单的承诺
在过去 在无人知晓的
小镇日渐蒙尘
不会再有电流
通过一根手指般的针
让它旋转起来
童年的木马停着
少年的蝴蝶 青年的
青春 对着中年的白发
一张黑色的旧唱片
它还是唱片
但内容却一片空白
怀表
我记得在梦中
曾经拥有过一只怀表
我穿着民国时的长袍马褂
梳着一条长长的辫子
仿佛是旧式怀表的
另外一条表链
怀表在我的怀里
在左侧贴近心脏的地方
一只旧式的怀表
仿佛是我的另一个心脏
怀表的铜表盖一直在喊疼
除了我没有人能再次打开它
我怕听到那啪的一声
我怕看到
那白色的表盘
黑色的表针
那指针指着的是什么
我在春天的梦里
用一只旧怀表伤春
旧时光中盛开的
那一朵白色的荼
仿佛是另外一只怀表
它已经被人摘走了
飞翔的鲸鱼
我也看到了
那头正在飞翔的鲸鱼
一头传说中的蓝鲸
开始我以为是一个幻觉
它没有遨游在广阔的大海里
而是真实地飞翔在空中
像一把巨大的剃刀
正为人类居住的地球理发
你否认了剃刀的说法
你说它像一架不存在的飞机
它其实不是在飞翔
而是在天空中自如地游泳
它游得很缓慢
它那庞大的奇迹般的身躯
看上去仿佛并不沉重
经过我们的头顶时
它青灰色的脊背
突然喷射出了壮观的水柱
你的眼睛里迅速一片湿润
你坚持认为那不是泪水
而是一场阵雨
阵雨来自一头飞翔的鲸鱼
一头无法呐喊的蓝鲸
一头被人类吃掉了的鲸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