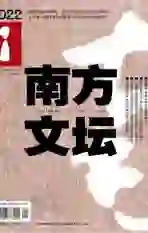多维文化互动与乡土童年塑型
2022-01-26李学斌马艳
李学斌 马艳
在中国“新生代”儿童文学作家群体中,王勇英是独特的存在。20世纪90年代,王勇英以一系列高密度、快节奏的都市校园小说、儿童侦探故事和少年科幻作品步入文坛,引起了儿童文学界的普遍关注。进入新世纪后,王勇英的儿童文学创作由“多点开花”逐渐向“定点透视”转型,并逐渐在乡土儿童文学领域形成鲜明特色。时至今日,王勇英不仅以其对壮族、瑶族、苗族等广西少数民族乡土童年的执着书写铸就了属于自己的文学标识,而且其系列作品所呈现出的钟灵毓秀的山川地貌、素朴端方的乡风民俗、醇厚宽仁的人情人性、斑斓摇曳的童言稚行还构成了风情独具的童年文化景观,成为广西乃至当代原创儿童文学的重要收获。
统揽王勇英新世纪以来的乡土儿童小说创作,其主要作品大体可分两类,一类是以《巴澎的城》《弄泥木瓦》《水边的孩子》等作品为代表的广西客家文化童年书写;另一类是由《里湖山钓蜂》《泥骨布朵》《花石木鸟》《花一样的衣裳》《少年陀螺王》等儿童小说构成的以瑶族、苗族等少数民族民俗文化为背景的地域童年表达。上述作品或呈现广西博白地区客家文化环境下蓬勃、昂扬的童年面貌(《巴澎的城》《弄泥木瓦》);或聚焦特定时期西南边陲少数民族村落中清醇、强健的童年轨迹(《水边的孩子》);或由百岁老人曾祖奶对苗家服饰文化的经年守望达成对下一代的生命启蒙(《花石木鸟》);或通过南丹白裤瑶民间钓蜂民俗的生动摹写呈示地域文化对乡土童年的浸淫和孕育(《里湖山钓蜂》)……
这其中,就民俗文化与童年成长的互动关系而言,王勇英以南丹白褲瑶陀螺文化为依托的长篇儿童小说《少年陀螺王》堪称优秀范例,其所营造的“意象化”社会背景、“典型化”代际关系和“多维性”成长动态在达成对小主人公你落、鼓台、夜角、走鼠等瑶族孩子童年形象塑造同时,也将广西南丹白裤瑶民俗文化之于乡土童年书写的意义体现得淋漓尽致。
一、陀螺:乡土童年的文化意象
人类文明进程中,文化既是人类存在的属性、表征,也是社会发展的动力、根脉。而作为文化之一脉的民俗则是一个民族在特定地域背景与人文环境中形成的具有仪式感和承继性的独特生活方式。就内涵结构来说,民俗因其空间上的确定性与时间上的绵延性在现实层面往往呈现为场景与物象的统一。这就为文学艺术再现民俗文化语境下的生活真实提供了“意象”基础。
说到“意象”,文艺美学中,其指的是融合着主观情意的物象。刘勰在《文心雕龙·神思》中称之为“神与物游”;英国文学批评家瑞恰慈则视其为“一个心理事件与感觉奇特结合的象征”①,无论哪一种说法,其实都在表达同一个意思——意象是物象与心像的统一。具体说,就是寓“意”于“象”,寄“情”于“象”,以“象”显“意”,情意赋形。作为文学形象的胚胎或初级形态,意象既“具有鲜明的可感性,又有隐含的情感性”②。正是基于这样的双重特征,诗歌中,意象常常是诗人移情于物、借物抒怀的凭借;而在小说等叙事文体中,意象则时常充当作品情意表达的“硬核”或“燃点”。换句话说,小说中的意象不仅孕育并聚焦着题旨、形象的多层意涵,而且其“定点爆破”的思维向心力往往还赋予单一物象或场景深厚、绵长的情感意味。
以上述观点为参照,不难发现,王勇英在《里湖山钓蜂》《花石木鸟》《花一样的衣裳》《少年陀螺王》等一系列以瑶族、苗族等广西少数民族民俗文化为背景的乡土童年书写中所依托的,恰恰就是深含民族文化和情感心理积淀的“意象化”表达。
比如,《花一样的衣裳》中,作家借角月奶奶心心念念的“老花衣裳”“老布娃娃”所凸显的是广西隆林地区苗族人民对生活的诚挚眷恋;《花石木鸟》中,苗家曾祖奶在对斑斓美丽的“白羽千花衣”的殷切渴望中寄托的是普通苗族百姓之于美好生活的守护与祈愿;《里湖山钓蜂》里,摇离、蓝泥花、蓝果等孩子对“蜜蜂”由追逐到守护的情感转变,呈现的不仅是心智渐渐成长的瑶族儿童对自然生命的理解、尊重,更有民俗文化浸淫下白裤瑶孩子品格与价值观的社会启蒙……而这样的“意象化”表达到了《少年陀螺王》中,则通过“陀螺”由“竞技实物”而“亲情礼物”而“童年守护神”的意义叠加营构了一种拙朴率真、生机盎然的童年景观。
具体来说,作品中,“陀螺”体示了一种多维度意象存在。它既是白裤瑶陀螺文化的具象、实物,也是小主人公你落、鼓台、夜角等瑶乡孩子现实交往和伙伴关系的纽带。作为文化意象,小小的陀螺陪伴并见证着孩子们的成长。而这一过程在小说中是通过“陀螺”情意赋形的逐层深入体现的。
首先,作品中,作为竞技实物,小小的陀螺传承着白裤瑶民族顽强的生命力和坚强乐观的民族精神。这正如文中布袋爷所说:“陀螺激励我们去竞赛,去展示我们的勇气与精神力量,不是去争个高低,比个输赢。”足见作为竞技工具的陀螺,其初始价值不仅在于获得生命快乐、释放生命能量,同时也是白裤瑶民族源远流长的一种社会交往形式。故事里,无论是祖辈的布袋爷、转脚爷、巴草爷,还是孙辈的你落、鼓台、走鼠,他们之间的情感联络很大程度上拜陀螺所赐,陀螺已然成为他们伙伴关系的重要纽带。此可谓小说中“陀螺”作为文化意象的显在意义。
其次,小说中,陀螺还是泛化了的白裤瑶民族造物神的物象图腾。故事里,从小你落懵懂记事起,老祖父布袋爷就借助两个红青冈木陀螺对他开始了人生启蒙。在布袋爷口中,养育了白裤瑶民族的群山是山脚相连、根脉一体的陀螺山——百里“成千上万,数不清的陀螺在天地间旋转,转出青山,转出绿树,转出飞鸟,转出红桃、白李……”可见,在白裤瑶民族的文化心理结构中,小小的陀螺俨然是拓分天地、开辟鸿蒙、不停旋转着的造物神。基于这样的造物原型和情感心理投射,作为民族竞技文化实物的陀螺,其功能就大大泛化了:变幻莫测的云,是陀螺山群的衣裳;连绵不断的群山,是地面上自由而团结的陀螺;太阳,是更高处旋转的天空中的陀螺;月亮,是能旋转出很多星星的夜空中的陀螺……而当如此原始粗粝、自由率性的造物想象以娓娓动听的方式植入五岁男孩心田时,关乎天地宇宙、四季变更、族群社会、亲情成长等生命认知、情感体验的初始观念就开始与小小的陀螺水乳交融、密不可分了。这一点其实也正是小主人公你落后来迷恋陀螺的情感基础、心理动因。也就是说,民族心理上的“物象崇拜”可视为“陀螺”文化意象的隐含意义。
如果小说对“陀螺”丰富意涵的呈示仅止于此,其文化意象的审美表达还是相对逼仄的。作家显然意识到了这一点,因此,小说在开篇以情节铺陈方式为小主人公你落、鼓台搭建好成长舞台后,随之就以几个孩子围绕着“打陀螺”而形成的错综伙伴关系,以及祖孙之间因陀螺而起的代际冲突将情节脉络和人物情感引向纵深,并由此揭示出隐逸在“陀螺”意象背后的更深层内涵。
譬如,小说开篇就交代:“你落一出生,布袋爷就用上好的红青冈木给你落做了两个陀螺,并作为人生第一份厚礼送给他。”作为一种民族文化习俗,长辈给新出生的孩子送陀螺,其实就是一种生命“洗礼”和成长祝福。当此时,红青冈木不择贫瘠的顽强生命力、经得起千摔万砸的坚强意志,以及做成陀螺以后自由快乐旋转的特定形态,都化为对孩子的殷切期待和美好祝愿。当此际,小小陀螺已然成为你落、鼓台等白裤瑶孩子生命成长的“守护神”。
实际上,在笔者看来,也正是借助于“陀螺”文化意象多层意涵的建构与呈现,《少年陀螺王》才超越了作者其他同类作品略显单一、肤浅的“意象”效应(如《花石木鸟》《花一样的衣裳》),显示出民俗文化语境下童年表达的典型意义。
二、布袋爷:白裤瑶陀螺文化的守望者
“意象化”文学表达之外,《少年陀螺王》中,老陀螺王布袋爷、转脚爷、巴草爷与逐渐成长起来的小陀螺王你落、鼓台之间的代际关系可谓小说乡土童年书写的又一个亮点。
故事里,无论沉敛、低调的布袋爷,还是热忱、爽朗的转脚爷,抑或是睿智、博学的巴草爷,他们与孩子们的良性代际关系都是抽丝剥茧、层层展开的。尤其是布袋爷,其作为老一代“陀螺王”不仅自觉自愿守护、传承着源远流长的白裤瑶陀螺文化,而且还义无反顾弘扬并推动着“踏实、稳重、宽仁、谦和、勇敢、不争”的陀螺精神。
这有情节为证。
小说开头,布袋爷是以打陀螺技艺“传道者”“引路人”身份出现的——“在你落六岁和七岁这两年,布袋爷带着他走了很多村庄……参加赶鸟节、吃新节、年街节等等民族节日。六岁过后……布袋爷带着你落外出,主要目的是他让他看别人打陀螺,看各种技法,还让他跟别人打陀螺,从实打实的过招中学习技艺。”
随着情节推进,布袋爷不仅专门为宣称“再也不打陀螺”的小阿娅鼓台专门做了两个陀螺亲自登门送去,而且还以“砸陀”的方式惩戒并警示孙子头茶,让他明白,打陀螺时输赢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像陀螺一样做人……而当看到因手机普及,村子里的很多孩子开始迷恋手机游戏而逐渐远离陀螺时,布袋爷则忧心如焚,“眉头拧成了节”。他特地去找巴草爷校长表达忧虑,并劝告巴草爷校长“不能让孩子们读书识字之后,忘了传统文化”,敦促巴草爷要管管那些只打电子游戏不打陀螺的孩子。因为在布袋爷看来,打陀螺和读书识字一样重要,而学校“有责任教育我们的后代”继承、发扬白裤瑶陀螺文化。
更有甚者,这位宅心仁厚的老陀螺王在训练小孙子你落备战少年陀螺王大赛同时,竟然将自己多年积累的打陀秘籍毫无保留传授给了你落的竞赛对手……
总之,故事里,无论布瑶村的小男孩,还是蓝水村的小阿娅,他们都从布袋爷宽厚、仁爱的目光中、话语里感受到了热忱鼓励,都从老人强健、有力的打陀螺行动上体味到了小小陀螺对于白裤瑶民族的价值、意义。当此时,布袋爷不仅是白裤瑶陀螺文化恪尽职守的“传道者”,更是身体力行的实践家。
即便如此,可当布袋爷在传授打陀技艺过程中有意无视亲缘关系而对所有孩子一视同仁的时候,这位襟怀宽广的老陀螺王已然超越了白裤瑶孩子打陀技艺“引路人”“传道者”的初始身份,一跃而成为白裤瑶童年文化的建設者、童年成长的“守护神”。
基于这一形象定位,小说中,布袋爷那些教授并见证白裤瑶孩子打陀螺的言行就显得尤为重要——其根本意义就在于不仅指引了这些瑶乡孩子童年成长的方向,而且也昭示着白裤瑶陀螺文化新时代背景下的守望与传承。
三、少年陀螺王:文化互动中的童年塑型
除上述两方面特质,作为民俗文化语境下的儿童小说,《少年陀螺王》在成长主题表达层面也颇具特色。具体说,就是小说里包括家庭亲情文化、童年伙伴文化、地域校园文化、传统民俗文化等在内的社会文化从不同维度形成合力,共同孕育了以“打陀螺”民俗为核心的白裤瑶童年文化,塑造并引领了你落、鼓台等瑶乡孩子的生命成长。
这一点涉及对民俗文化语境下童年社会关系的理解。
西方新童年社会学认为:“童年不仅是一种自然事实,而且更是对这种事实的解释。”③童年不是一成不变的观念现实,而是特定语境下包括政治、经济、宗教、法律、习俗等在内的社会文化的一种建构。世界上不存在一成不变的普遍性的童年。童年都是千差万别、具体而微的,有什么样的社会文化,就会有什么样的童年。
依据上述理论,小说里,你落、鼓台、头茶、夜角等白裤瑶孩子以陀螺文化为生活背景的童年面貌就与他们身在其中的社会文化具有密不可分的关联。具体说,就是这些瑶族孩子实际上浸淫于多维文化构成的成长环境中。而这些文化元素由显而隐、由中心而外围不断拓展,如同一个既封闭又开放的同心圆,共同营造了你落、鼓台们成长的童年文化环境,推动并见证着他们的童年塑型。
这其中,最基础的部分是布袋爷所代表的家庭亲情文化。
我们都知道,家庭是生命发展的原点,是社会的基础细胞,其之于儿童生命成长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少年陀螺王》中,小主人公你落出生在一个三代同堂、和谐美满的大家庭里。“出门跟阿爷打陀螺,回家听阿奶讲故事,能随阿爸走山野,又帮阿妈摘菜花……”幸福的家庭生活孕育了小你落善良、单纯、平和、淡然、与人无争的品性。他甚至有点“不合群”的小小的孤僻。所幸的是,他有一个慈祥、宽厚、仁爱、无私的爷爷。借助陀螺这个小小物件,老陀螺王布袋爷让小孙儿体验了快乐,收获了自信,懂得了做人。毋宁说,以布袋爷为核心宽严相济、爱心满满的家庭亲情文化构筑了小你落沉稳扎实的童年生命底座。
其次是你落与同龄小伙伴鼓台、夜角、走鼠之间由情感交往、游戏活动而培植起来的的童年伙伴文化。
小说中,以陀螺为纽带,小主人公你落和鼓台、夜角、走鼠等小伙伴呈现了一种亦“敌”亦友、相生相克的动态关系。这其中,他和小阿娅鼓台融合而又对峙的友情格外动人。鼓台是个心高气傲的小姑娘。曾经的大城市读书经历让她在瑶乡同龄孩子面前有些小小的傲娇和虚荣。初回蓝水村,她通过有意展示手机游戏,并适时贬抑打陀螺传统而显示自己的优越感。她在用几本课外书为自己赢得“盟友”的同时,也轻而易举将你落“拉下了水”(打手机游戏)……小说中,作家借鼓台这个小阿娅形象所表达的恰恰是童年伙伴文化的复合性及其对身处其中的孩子们的深刻影响。
换个角度,小说里,如果说弥散在从未走出过里湖乡的你落、走鼠、夜角等孩子之间的是一种同质伙伴文化的话,那么接受过大城市文化熏染的鼓台给小伙伴们带来的就是一种异质童年文化。城市见闻、手机游戏、课外读物……当这些突如其来的新生事物不由分说嵌入瑶乡孩子生活的时候,短暂的新奇、迷惑之后,随之而来的就是喜新厌旧式的排斥与接纳。显然,这是童年伙伴文化内部的矛盾、统一、分化、融合。此时,童年伙伴文化的芜杂性、盲目性已显露无余,这需要包括学校、家庭、社区在内的社会文化对其进行规约和统摄。小说里,这个层面的文化守望与童年引领是由布袋爷和巴草爷共同承担的。
诚如前文所述,《少年陀螺王》中,作为白裤瑶陀螺文化的守望者,布袋爷是个颇有几分理想色彩人物,在他身上映现着作家的文化价值观和童年使命感。面对新媒体文化的冲击,为确保打陀螺技艺在白裤瑶年轻一代中的传承,布袋爷可谓操碎了心。也正是得益于他和转脚爷、巴草爷这些老陀螺王不遗余力地守护、倡示、鼓励、引导,白裤瑶民间陀螺文化才得以薪火相传、绵延不绝。
与布袋爷有所不同,作为小学校长的巴草爷是开放包容的瑶乡学校文化的化身,在他身上体现着传统与现代、民族与世界、儿童与成人等多种文化元素的融合。
作品中,面对陀螺文化逐渐式微的境况,巴草爷一方面及时出台措施规约孩子们的游戏行为,引导他们重拾打陀螺技艺;另一方面,又从鼓台所引发的“课外书现象”中敏锐捕捉到了孩子们新的文化需求,并由此开启了对瑶乡童年意义深远的学校图书馆建设。
也正因如此,小说里,我们不仅看到了新时代背景下白裤瑶民间陀螺文化对生机勃勃的新媒体文化的接纳,而且还体味到兼收并蓄的校园文化对于你落、鼓台等瑶乡孩子的情感塑造和精神引领。
小说末尾,当你落和鼓台知晓三位老陀螺王为比赛奖金无法落实而发愁时,两个孩子很快达成了默契。他们以最后一局比赛有意求和的方式帮助三位爷爷避免了窘境。在这里,两个孩子的举动所体现的正是布袋爷、巴草爷寄望于他们的“稳健磊落、正直勇敢”的陀螺精神。这是比“少年陀螺王”名号更为灿亮的精神品格,其所呈示的不仅是陀螺文化在瑶乡童年中的根植与绵延,更有孩子们在多维文化孕育下的情感表达与心灵成长。
至此,作家以家庭亲情文化为基座,以童年伙伴文化、游戏文化、校园文化为主干,以民间陀螺文化为统摄,建构起瑶乡孩子生命成长的完整文化系统,并在此基础上,借助一系列文学手段,在生动呈现儿童生命成长与社会文化动态关系同时,完成了对你落、鼓台、夜角等儿童形象的文化建构和童年塑型。
论述至此,在充分肯定《少年陀螺王》民俗文化语境下童年塑型意义同时,也不能不谈及作品中童年书写方式所存在的偏差或局限。
通观王勇英以壮族、瑶族、苗族等少数民族民俗文化为背景的系列作品后不难发现,其乡土童年儿童小说写作在近十年间实际上经历了从“民俗文化聚焦”(《花一樣的衣裳》《花市木鸟》)和“乡土童年表达”(《里湖山钓蜂》)单向度叙事向“民俗文化融合乡土童年”复合性叙事(《少年陀螺王》)的审美转换。这一审美转型一定程度上标志着王勇英少数民族民俗文化童年书写经历艺术磨砺之后已渐趋成熟。在笔者看来,《少年陀螺王》“文化”与“童年”同步聚焦的复合书写较作家其他同类作品二者分离的单向度叙事,其意义就在于不仅能够增强童年形象的厚重感,而且也一定程度拓展了儿童小说乡土童年表达的艺术边界。
尽管如此,作为一部优秀儿童小说,《少年陀螺王》还是留下了些许遗憾。民俗文化的符号化、人物形象(如布袋爷)的理念化、陀螺文化意涵呈现之峻切、文化传承题旨表达之直白等不足在文中时隐时现,这也让小说中“陀螺”作为文化意象偶现出形象化与理念化杂糅的窘境。而上述问题的出现,说到底,其实还是作家在“民俗文化与童年形象究竟何者为先”的审美选择上首鼠两端、摇摆不定的结果。
窃以为,在这个问题上,王勇英还是应该将乡土童年书写的重心更多聚焦在童年形象的塑造上。道理其实很简单,“小说毕竟是叙事的艺术,儿童小说尤其如此。特殊乡土文化的开掘能够为儿童小说带来清新独特的艺术气象,但当作品对文化的呈现热情湮没了其对于故事艺术的思考,那么文化本身或许就成为儿童小说艺术发展中的一种不无危险的障碍”④。而长久以来,在乡土题材儿童小说领域,我们恰恰陷入了某种错觉,总以为,儿童小说文化层面的艺术价值可以置换故事层面的形象价值。其实,就儿童小说价值构成而言,文化仅仅是必要条件、背景因素,其审美价值或许永远都无法和文学形象等量齐观。
基于此,窃以为,方卫平教授上文的这段评述可谓切中肯綮,值得作家在后续的民俗文化童年书写中深思而慎行。■
【注释】
①[美]艾·阿·瑞恰慈:《文学批评原理》,杨自伍译,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20,第十六章《诗的分析》。
②孙绍振、孙彦君:《文学文本解读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第181页。
③[英]艾莉森·詹姆斯等:《童年论》,何芳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4,第57页。
④方卫平、赵霞:《儿童文学的中国想象——新世纪儿童文学艺术发展论》,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2018,第191页。
(李学斌、马艳,上海师范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