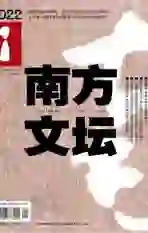古远清:不受待见的研究者
2022-01-26朱寿桐
古远清先生研究水平的高卓,研究个性的鲜明,研究成果的丰硕,都已经,并且正在,而且将会继续成为大家热议的题目,我不想赘言。我想说说古远清先生的“糗事”,即,他还是一个每每“不受待见”的研究者。
所谓不受待见的研究者,就是他所从事的研究不能得到研究对象及其周围文化环境的认可、肯定、支持、鼓励,而是相反,受到忌妒、排斥、讥讽、舍弃,至少是不认同。
研究者不受待见可能是一个普遍的社会现象。你肩不能挑担,手不能提篮,谁愿意待见你?你不事创作,不擅建造,谁乐意待见你?你明明备受束缚却扯谈思想自由,你明明皓首穷经却妄言潇洒倜傥,谁刻意待见你?
研究者不受待见可能还是一个常见的文化现象。你死读书,读死书,谁能待见你?你从书本里搬来教条,压制别人,反过来要求别人从教条中解脱出来,走向创造,谁敢待见你?你厕身于文化的边缘,却以文化中心的守护人自居,谁会待见你?
文人学者的不受待见,乃是不受别人、局外人待见的意思。当然,也可能不受自己人待见,不受同类人待见,那是常有的事,那叫文人相轻。
以上这样的社会现象和文化现象,与我们论题的主人公古远清教授没有太多关系。我这里所说的是他作为研究者不受被研究者待见的情况。
有时候,在研究领域,一种不受待见的现象常常体现为被研究者对自己羽毛的特别珍惜,而那羽毛很可能是塑料制品硬插上去的,经不起别人的拨弄,你去研究它,他反过来觉得你是在有意拨弄,于是将研究者视为仇雠一般。特别是有些文化自信和学术自信不太高的作者或研究者,他们凭借着“三脚猫”式的腿脚在文学或评论的边缘地带铤而走险般地卖弄着,所有试图近前的观察和相应的研究都被视为一种特别需要警惕的挑衅行为,于是,相应的研究者便不会为这样的研究对象所“待见”。就在前些日子,一位在文學评论界颇有影响的评论家发表了关于“现代性”与“当代性”相纠结的论文,另一位同单位的文学理论家便凑近“研究”,立即引起被研究者的警觉,让他警觉到自己的“才疏学浅、词不达意、逻辑混乱”引起了别人的注意,于是在微信群中酿起了一番颇见规模的笔战。这是不待见研究者的一种常见现象。网传一位市级音协领导不懂葫芦丝吹奏,却凭借自己的身份参与表演秀,结果将乐器拿倒了还在自我陶醉、装模作样地“吹奏”。近旁的演奏专家近前示意,要她拿正葫芦丝,竟然被当事人警惕地、厌烦地避开了。这样的情形活灵活现地展示了一种不受待见的“观察”和研究的情形。
还有的时候,在研究领域,一种不受待见的现象体现在一些过于寂寞的被研究者对偶尔具有的研究、评论的一种过激反应,这种过激反应可能导致一种社会聚焦,于是以不待见研究者的方式进行自我炒作。前些年,一位研究澳门文学的学者参与我的研究项目来澳门访学,顺便写了一篇介绍、论述澳门某小说家的文章,揭载于《澳门日报》文艺评论版。该文对该小说家的评价相当正面,对他的生平介绍态度也相当积极,甚至在总体评价上带有某种提携的成分,按说应该是值得被研究者当面致谢的。谁知竟然遭到研究对象的质询:是谁同意这位研究者写这篇文章并且发表的?据说这事情还闹到了特区政府相关部门。真是令人哭笑不得,尴尬不已:辛辛苦苦的研究,掏心掏肺的努力,甚至搜肠刮肚的赞扬,本意在于以“理解”、鼓励的方式为澳门文学和澳门创作者发声,可结果却被不待见若此。还是澳门文学界的朋友道出了真谛:学者写了论文,发表了,很可能不会引人注意,更难让政府部门知晓,而他这么一不待见,则周围人就会关注此事,连政府也知道了,宣传效应不就扩大了吗?更有甚者,过了些年,名人逸事中还可能有某某作家拒绝评论家好评的佳话,那他的形象就更其“高亮”了。果若此言,此作者也就有些太过分了,为了宣传自己、成就自己招数使尽,却不管不受待见的研究者所受的冷遇。
更有的时候,一种狭隘的学术资源占有者,也会不待见相关的研究,以及相应的研究者,因为他将其他研究者视为自己的竞争者。这种情况常常发生在具有特殊地位和影响力但幅员相对狭窄的地区,一般来说这样的地方不会待见外来的研究者,类似于古远清这样的学者。有些地区的同行面对外来的研究(这个词组有些奇怪,学术研究是人文公器,研究本来就不应该分内在与外来)总是显得过于紧张,每遇到对这一地区的文学文化现象感兴趣的研究者,便如同遭遇入侵之敌,好像这些研究领域和相关研究课题早已圈进了他自家的领地,不容别人觊觎,其他人一旦有意问津,则视为仇寇,对之予以排斥、打击或者讽刺。这种对学术研究者不仅不待见而且随时准备加以排挤、进击的现象时有发生,发生于古远清这样的学者身上的概率更大。为什么?我不想说古远清的学术水平让一定区域的研究者有所忌恨,但可以从以下三方面进行分析。第一,古远清作为“外向型”的学者,其选题常常涉入陌生的地带和特别的领域,“侵犯”别人领地在他而言几乎是大概率事件。第二,古远清学术思维活跃,经常对研究对象提出新异的界定,这很容易抢读者的眼球,自然会引起某些同行的侧目而视。第三,古远清作为一位文学史家的学术造诣和学术兴趣常常使他不安于做一般的文学批评家,而这“修史”的热忱每每会触动本地域研究者的敏感神经,于是对他不得不多有忌惮。既然所遭受的多是这样的忌惮,怎么可能受到“待见”?
有时候,在研究领域,一种不受待见的研究常常是被研究者自我膨胀的结果,自我膨胀到异常敏感与研究者对自己的判断与评论,这种判断与评论达不到自己所期望的高度,于是愤然作色,于是拂袖而去,于是道路以目。他与某位著名作家的官司其实一开始肇始于他对这位作家的研究,这样的研究不仅使他不受待见,而且与他对簿公堂,这当然是他作为研究者不受待见的特别的例子。
以上这些文学批评中的不受待见的学术现象,与古远清先生都密切相关。古远清先生是我印象中最常常体验不受待见待遇的研究者。
我不知道他是否有冤屈,尽管他从来不屑于表述出来:我们为什么会不受被研究者以及被研究者的环境“待见”。我们辛辛苦苦,兢兢业业,焚膏继晷,碧落黄泉,查找资料,比对理论,寻证细节,斟酌字句,为一定的对象写下研究文字,可是落得个不受人家待见,这岂非比窦娥还冤?
我自己遇到过这种情况。有幸结识一位诗人,他通过一个朋友向我求序。那诗作非常一般,但考虑到作者是个退伍军人,二三十年写作兴趣浓而不减,是一个有生活与创作热忱的写作者,应以鼓励为主,当然也要指出作品中的一些有待改进的地方,特别是一些旧体诗词平仄不合、对仗不整的问题。我辛辛苦苦写出了一篇文章,发给他,他不仅弃之不用,而且置之不理,从此偶尔相见,亦浑如路人。朋友转话说,本想我多有嘉勉,没想到写了那么多有待改进的地方,这哪里是作序,分明是批评。我猜想这“嘉勉”二字也出自朋友之口,那位作者实际上期望的可能是我的一篇歌功颂德的“宏文”。我赧然、怃然,更多的则是悻悻然,有些忿忿然,这么多的然,其实是说五味杂陈,什么体验都有。这稿件是我对特定的研究对象量身定制的,其他地方不能用,当然也不愿意用出来,硬是白白地写了那么两三千字,之前还认真地阅读那些陌生的有些怪异的作品,核对一些诗词的格律规范,特别是有些词可能有不同的变律,不查清楚是不好随便说人家的,这得花费多大的功夫。遗憾的是这篇文章成了无用的“盲肠”,而且自己还顺便成了不受人待见的主。
由自己的体验总结出不受待见的意思之一:不迎合被研究者的趣味、口味,坚持按照自己的学术良知进行学术发言。古远清先生在这方面做得比我们多得多,受到的不待见也一定比我多,因为他从来就不是一个善于巧言令色地对别人作廉价吹嘘的学者。他说过他有过三次与我所说的辛苦“写序”而不受待见的经历。他的研究一向坚持自己的学术见解,恪守自己的美学、诗学、历史学原则,我行我素地进行特立独行的学术研究,在学术研究的道路上踽踽独步,很少呼应甚至回应同行者的言语与观察,更很少揣摩研究对象自己的意趣与倾向。他对于香港、台湾、澳门文学的现象判断,包括对一些重要作家的评价等等,都往往别出心裁,别开蹊径,虽然有些被研究者对此并不满意,但古远清先生一笑置之,处之坦然,我行我素,匠心不改,由此体现出来的是一种可贵的学术品格,学人风度。细细想来,在我们的文学评论界和学术研究界,长期以来,是不是太多人云亦云、尔侬我侬的理論现象了?大家都热衷于说同样的关键词,热衷于呼应但实际上是重复已经成势或正在成势的说法、概念、理论、表述、判断、推论等等,围绕这一种说法,一个人说了,然后几个人说,然后所有人跟着说,被研究被批评的那些作家乐得接受:原来我们的创作在评论家们的理论账簿上是有说道的,于是皆大欢喜,中间也间或会有一些人出来反思,好像我说得比你早,对方就说,我说得比你全。不少理论家和批评家就是这样过来的,他们用此种方法拿了教授,拿了各种各样的名头,也同时拿到了被研究者的待见,但自己到底说了哪些真正属于自己的话,只有他自己知道以及天知道。但古远清先生从来就不属于这样的研究者,他从不跟着别的人胡诌令人欣喜的概念,或者谈令人耳熟能详的话题,所有的判断都来自自己的领悟与思考,甚至非常固执地拒绝一切已经成势的观念和观察的启发。他的香港文学研究、台湾文学研究,无论对作家定位的判断,还是对文学历史时段划分的认定,都体现出与众不同的思维和方式。
他的《台湾当代文学事典》是一部足资借鉴、足资参考的学术著作,其中收录了台湾文学史料与作家作品的全方位信息,应该是大陆学术界迄今为止关于台湾文学最为翔实的且具检索性和工具性功能的资料集成,不过古远清非常注意学术解读和学术判断的独步性,对“双陈”大战、“三陈会战”等文学现象,概括地表述都显出有些夸张的异端,再如“余光中向历史自首”“陈映真两次被捕”“唐文标事件”“封杀於梨华”“周令飞飞台引发的鲁迅热”“邱妙津等作家自杀”等,既有浓烈的时代气息和历史记忆意味,又有复杂生动的情节性,即对于一般读者而言也会葆有相当的阅读魅力,更重要的是,敢于冒当事人(至少部分当事人)之不待见,甚至是大不韪,敢于做出自己的判断与解读,这样的研究,需要学术定力,也需要学术自信,需要克服来自学术创新方面的各种孤独的恐慌情绪。
古远清在学术上从不缺少幽默、调侃的风格,可同时又保持着犀利甚至尖锐的批评风格,体现的常常是年轻人的血气方刚的做派。他的学术批评常常指名道姓,不留情面,当然同时也显出一种学术正直和义正词严。我记得他2016年对于日本学者藤井省三所著的《华语圈文学史》的批评可谓字字千钧,痛快淋漓,除了学理的坚持而外还体现出学术意气和文化意气的力量,看得人确实过瘾。其实,“华语圈文学”同“华语系文学”从概念内涵上异曲同工,都带有浓厚的非学术性考量,对于这种非学术性因素的撕剥,体现的是一种畅快果敢的气性。古远清给这样的批评风格作过概括,叫作“不戴面具”的批评,那是他在一篇悼念文章中对袁良骏先生的形容,其实也应该是这位保持着年轻人血性和作风的古远清的夫子自道。这些学术批评体现出研究者的胆识和魄力,当然也会引起被批评者的不快、不适和不待见。
这样的研究让许多同行学者耳目一新,也不免惹得别人侧目而视。我就曾经听到一位作者这样“怼”古远清先生:你怎么说的就是跟别人不一样?他的意思是,别人都说我怎样怎样,你怎么就那么“低八度”地说我?
这话说开了,其实是非常简单的道理,学术研究,文学研究,就是应该由研究者自己说话,这话说得别人觉得中听不中听,或者当事人是不是可以接受,其实并不重要。但长期以来的学术研究偏偏就在这样一个简单的常识性的问题上屡屡犯难,我们自己是不是也有这样的体验,一旦发现自己的说法、自己的判断、自己的表述与许多人不一样,与重要的人物不一样,与会议的主调不一样,这时候就会觉得恐慌?这恐慌就像独立高处的那种惶惶然的恐惧,这不叫恐高症,这叫“恐孤症”。只有古远清老师没有这样的“恐孤症”,因为他能够面带笑容对待所有不待见的指控或指责,并且依然我行我素,甚至变本加厉。
既然我们叫这种现象为“恐孤症”,看来就是一种病症,那应该郑重对待,像古远清先生这样。文学研究者有许多人罹患这样的“恐孤症”,养成了跟从别人的习惯,而且一旦不跟从都觉得心里发毛,精神恐慌,原来是学术自信受到了极大的摧残,甚至变得荡然无存。最可悲的还不是这样“恐孤症”的罹患者,而是根本没有机会觉察这种病与自己有关的现象:如果一个研究者从来就没想到过选择自己的学术路径,说自己的话,运用自己的思维,跑出自己的见解,那么,连“恐孤症”的滋味都体尝不到。
于是,文学研究或者学术研究有几种境界:一是无缘、无资格、无准备去体验思想、观念、评论、判断“恐孤症”的学者;二是罹患这样的“恐孤症”并且迅速“克服”这样的病症然后抵达无病无症状态;三是罹患并体验到这样的“恐孤症”,又常常不能自拔地深陷其中,继续净场地体验这样的恐惧;四是感受到“恐孤症”症候,但好不引以为意,更不引以为异,而是乐此不疲,绝不改弦更张,从不引以为惧,以为学术必有的常态,这样的境界便是古远清的境界。■
(朱寿桐,澳门大学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