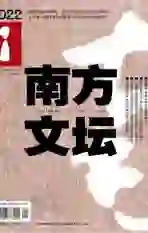当代中国科幻小说中的科技美学问题
2022-01-26詹玲
科技美学作为现代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当代文学叙事中始终处于未完成的状态。以科技为故事基础和精神内核的科幻小说,在科技美学的审美表达方面有着天然的优势。然而,在过去的20世纪,中国科幻小说的科技美学亦没有呈现出应有的特色和价值。进入新世纪后,尽管以《三体》为代表的少量科幻小说,成功突破了科技想象的美学瓶颈,不仅将中国科幻小说,也将中国当代文学的科技美学书写推向了新的高度,但从整体来看,科技美学的建构依然差强人意。是什么导致当代中国科幻小说如此难以张扬科技之美和想象的神采?那些将科技美学探索向前推进的科幻小说,是如何融科技之美入文学想象,激发出更具有创造活力和想象空间的美学新质的?当下的中国科幻创作,在总结既有经验与教训的基础上,需要作出怎样的方向性调整,或者说观念的调整,才能真正弥补中国文学一直缺失的科技美学维度?接下来,本文试图从梳理中国当代科幻小说叙事美學发展历程中出现的两个关键问题:“科普”和“科幻现实主义”入手,辅以《三体》及其他典型文本的科技美学解读,对上述问题展开探讨。
科学知识阐释与认知疏离美学的建构
科幻小说从晚清传入中国之时起,就承担了向民众普及科学知识的历史重任。当时的小说家们努力尝试使用简单、生动文学语言讲解科学知识,做到“析理谭玄,亦能浸淫脑筋,不生厌倦”①。如包天笑、徐卓呆等人就曾用“枯鱼作书”的比拟手法,在《病菌大会议》《元素大会》等小说中对病菌、元素进行拟人化处理,拉近了读者与现代科学的距离,调动了阅读兴趣。新中国成立初期,科幻小说家们沿袭了这种手法进行少儿科普,用生活中常见的事物来比拟太空景观,通过调动读者已有的认知经验,对文本中描述的陌生事物进行同化处理。如把人造月亮形容成一个挂在布满星星的天空里的大轮子(《到人造月亮去》,1956),把太空中的太阳和月亮比喻成嵌在黑幕上的珍珠(《空中旅行记》,1956)等。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科幻创作不再把讲科学知识作为一个重要且必要的目标。很多小说或偏向社会政治,或选用一些不需要过多阐释就能进行故事演绎的技术知识作为文本建构的科学骨架,如平行宇宙、克隆技术等,也就自然而然地不再使用这一功能。
从文本阅读接受的角度来看,用艰深科技理论或距离普通读者日常生活较远的科学知识作为技术内核进行故事搭建的科幻小说,依然需要用好的文学手段来处理知识壁垒的问题。任何具有高科技含量的科幻作品创作,除非作家将阅读对象仅仅设定为同人圈子,以圈内阅读,甚至是自娱自乐为目的,否则必须考虑到读者的接受度问题。当科幻小说中的科技原理和科学知识对读者造成了阅读接受壁垒时,作家需要进行处理,不是因为科普,而是因为阅读接受。加拿大科幻学者达科·苏恩文借鉴俄国学者什克洛夫斯基、托马舍夫斯基提出的形式主义理论,从本质上的认知性和艺术陌生化的角度,将科幻小说定义为一种以疏离(estrangement)和认知(cognition)为宰制的文本②,但如若科学内核与读者日常生活经验过于遥远,读者无法了解作者讲述的科学内容,陌生带来的惊奇和震撼是无法发生的。因此,对于这类小说,往往是硬科幻小说,科普手段的使用并非仅仅为了向读者普及科学知识,而是要在文本内容和读者经验认知之间搭建起一座桥梁,使阅读接受反应得以发生。要在硬科幻的文本中,让读者体味到恰到好处的认知疏离,作家首先要做的,是把“认知”和“疏离”拆分开来。认知疏离的发生,并不是在读者读不懂文本内容,在知识理解方面产生疏离感,而是读者在阅读了小说之后,能够理解故事描绘的科技想象并生成视觉上的画面感,这种画面感与读者己身既有的经验认知产生强烈的反差,带来惊奇、震撼的心理体验。
所以,科学内核坚硬的科幻小说,其认知疏离的美学效果构建往往需要分两步走:一是用形象化、经验性的语言,化解小说中使用的科学原理、知识给读者造成的可能性阅读障碍;二是制造故事中的画面、情节与人类日常现实经验的反差,形成阅读期待与阅读事实之间的感觉错位。没有走第一步,即用科普手段来解决知识壁垒,第二步是很难进行下去的。新世纪以来的不少科幻小说,都有这样的问题。如ShakeSpace的《星语者》(2004)中描写飞船进行空间跃迁的段落中,作家用了引力场偏移环、介子束、度规、等效质量等大量艰涩难懂的科学术语,又没有在事先经过科普处理,而是直接放到跃迁场景的描绘中。即使作者花费不少笔墨,十分细致地讲述了飞船从启动到空间嵌入再到弹射的过程,但对于没有任何专业背景的普通读者来说,很难根据这一大段文字在脑海中形成相应的画面。江波的《银河之心》三部曲中也有这样的弊病。以《天垂日暮》中的一段情节描写为例,李约素驾驶“天狼星”号发现失踪已久的环状飞船“上佳”号时,飞船主脑布丁向李约素讲述了“风暴号”飞船在蜘蛛星附近的经历,其中涉及的一些空间理论概念,如亚空间、宇宙膜、空间曲率、淼空间灾变等,也都没有进行任何解释③,给读者的阅读增加了较大压力。一些作家虽然注意到了文本科学内核的艰涩难懂,也明白要通过阐释来解决,但采取的方式仍是老套的问答式或讲解式,比如汤思一的《鹊桥》(2018)在向读者讲述虫洞的制作原理时,就是把一段长达三百余字的教科书式文字,呈现在读者面前。查杉的《这里是火星》(2018)则用主人公沈冰和林海宁之间的大段问答,来试图讲清量子纠缠。
这些小说虽然在故事情节构造和情感表达方面较之“十七年”的儿童科幻,均有了较大幅度提升,但由于没有很好地解决知识壁垒问题,读者依然会被“读不懂”的艰涩科学原理挡在文本之外,甚而放弃阅读。
类比、故事与隐喻:科普的叙事策略及
美学功能体现
那么,一部优秀的科幻小说,应该如何有效地解决科普问题,使之在消融科学知识壁垒的同时,提升而不是降低文本的文学性?用得最多,也是最常见的科普手法是类比。如萧星寒的《天地大冲撞》中,用人类历史上的氢弹武器爆炸当量和最大的火山爆发当量,类比故事中小行星撞击地球的能量,让读者从历史的疼痛中体会到破坏性力量的可怖;长铗的《昔日玫瑰》用智者芝诺的羽箭类比数轴,讲述“万物皆数,而数并非万物”的科学道理;王晋康的《类人》则用蜜蜂的智慧比喻数字化世界的电脑智慧,直观化电脑智慧发展的层级模式。相比儿童科幻简笔画般形象直白的类比,上述类比的意象和语言更复杂,但拿来与科学知识类比的事物,仍然控制在普通人的知识和生活经验体系内,这也反映了科普叙事从低幼型向普通大众型读者的转变。
个别小说用的类比手段更加高级,比如《三体》。小说第一部刚开头,作者就抛出了一个极其深奥的物理学问题:物质本原的无规律问题。在故事的起始就设置这样高难度的科学问题,从文本设计来讲,是相当冒险的。如若处理不当,读者很可能就会丧失兴趣。刘慈欣的高妙之处在于编织了“射手假说”和“农场主假说”两个故事,用故事中的二维智能生物和火鸡中的科学家,隐喻人类科学家,这样的寓言式隐喻让问题迎刃而解。
维度问题是整部《三体》最为核心的物理学问题,为了阐释清楚维度的升降,以及维度间的关系问题,作家采用了故事套故事的方式,层层架设,重重铺垫。先是《黑暗森林》用蓝色空间号通过翘曲点误入四维空间的故事打底,让读者初步感知三维与四维的差别,触摸四维空间的质感,之后在《死神永生》中,又先后用拜占庭战役中,妓女狄奥伦娜能够穿越三维空间取走物品的故事,针眼画师将看到的人画进画里的故事,渊龙翼膜做的伞以及不符合透视原理的深水王子無法被画入画里等故事,不断强化读者的维度概念,形象可感地让读者明白维度之间的升降问题,从而能够继续跟着作家的想象前行。
用讲故事的方式阐释科学原理,故事情节产生的意义和魅力可以有效地吸引读者全身心地投入阅读,形成与作家/文本之间平等、亲近的交流关系,在不知不觉中理解、接受科学知识和科学原理。在科幻小说的阅读对象从青少年扩大到全民之后,学会用好的故事让读者明晰文本的科学内核更加重要,因为只有这样,才可能获得更多的大众读者,提升科幻小说的影响力。
此外,独特的隐喻技巧,也是《三体》中阐释科学原理的高超技法之一。文学中常见的隐喻手法,是用一个或多个喻体对应本体的单层隐喻。但这样的隐喻,由于文学语言本身的意义不确定性,容易导致信息的不确定性。一方面能够丰富文本的内涵,使故事拥有不同面相的解读而变得“言有尽而意无穷”;另一方面也可能让文本信息不能精准传递到读者那里,或者被误读。《三体》里,为了避免产生歧义,作家独创了一种新的隐喻模式:二维隐喻,即用双层隐喻加单层隐喻的方式来固定双层隐喻的含义。小说里,云天明既要将三体文明的技术信息有效传递给地球,又要确保程心安全,不让三体文明发现他的意图,于是,云天明先是用雪浪纸的卷曲和熨斗熨平两个喻体对应曲率驱动的空间形态这一本体,用双喻体更加模糊、隐晦的特性,骗过三体文明,然后,又用喻体肥皂船对应曲率驱动的飞船本体,用这一隐喻固定住之前的空间形态隐喻指向意义。通过纵横两个坐标来确定单层隐喻,这是典型的科学思维,即用定立界说的方式,排除可能的其他隐喻含义,将情报的意义指向固定下来,使其不再滑动。这样的新型隐喻模式丰富了文学的隐喻层次,使文学隐喻变得更加丰富多样;此外,当这种严谨、指向明确的科学思维与含混、多轨的文学思维发生碰撞时,会形成感性与理性相互交融的艺术审美感受,不但丰厚了审美的层次,也给读者带来了新鲜的认知愉悦,同时也有利于青少年读者科学理性思维能力的建构和培养。
“科幻现实主义”与当代中国科幻的视野
内缩、想象力受限
除了科普的退隐外,1980年代兴起的“科幻现实主义”是导致中国科幻小说科技美学不张的另一原因。希冀科幻小说被主流文学接纳、认同,1981年11月,郑文光提出“科幻现实主义”这一理论主张,认为“科幻小说也是小说,也是反映现实生活的小说,只不过它不是平面镜似的反映,而是一面折光镜”④。随后,这种用科幻的方式来探讨社会问题,“并把它视为现实主义文学的一部分”⑤的主张,得到了当时不少“姓文派”作家的认同。一时间,科幻文坛出现了多篇“科幻现实主义”风格的作品。除了郑文光自己创作的《“白蚂蚁”和永动机》《命运夜总会》《空中的追逐》等外,还有王晓达的《波》、金涛的《月光岛》、叶永烈的《腐蚀》等。
虽然后来的“姓科”“姓文”之争以“姓文”派败北结束,但“科幻现实主义”的种子已经种下,张扬启蒙主义的人性、人情,关注社会现实问题成为之后很多科幻小说家坚持的创作理念。即便在科幻创作处于低迷期的20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依然有慨叹人文精神失落,批判商品经济导致物欲横流的《CM闹剧》《星夜广告》《推销爱情》《二十分钟等于……》等不少反映现实生活的作品发表。进入新世纪后,科幻小说迎来的又一波繁荣热潮中,“科幻现实主义”更受到了不少作家推崇。韩松指出“科幻小说已经成为今天的‘现实主义’文学”,“可以给现实提供新的表现方式”⑥。陈楸帆也认为“在科技日新月异且高度复杂化的今天,科幻小说比起其他的文学形式,能够更有力量,更高密度且更为全息地再现现实图景,它才是最大的现实主义”⑦。关注城乡冲突、阶层固化及生态污染等前沿现实问题的《山民纪事》《北京折叠》《霾之二重奏》《古曼人棉城遗址调查手记》《南岛的星空》《荒潮》等,都呈现出清晰的启蒙立场和现实关怀。
首先,我们必须承认和肯定,“科幻现实主义”这一创作理念的提出有一定的价值和意义。第一,现实关怀为科幻小说在当下这个科幻经验逐渐日常化的科技社会谋求文类的正当性和影响力提供了新的可能。就像英国作家多丽丝·莱辛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被科幻研究者们称为科幻小说之于主流文学的胜利⑧,中国科幻小说凭借对现实的变形式关注,顺利地摆脱了曾经的“少儿”和“科普”标签,越来越被主流文学承认和接受。第二,以科技与人的关系为中心出发的思考,也让科幻小说在现实层面补足了其他文学类型科技维度思考的缺失,大大加强了文学整体关注现实、干预现实的力度和深度。
但是,站在今天的科幻创作角度,“科幻现实主义”也带来了负面问题,便是导致科技美学的不张。当科幻小说以启蒙现实主义文学的文学性为标准,进行美学建构的时候,必然会造成自身特性的缺失。如吴岩所言,“科幻文学是科学和未来双重入侵现实的叙事性文学作品”⑨,科学与未来构成了科幻把握现实的两翼,由此而生发的艺术审美特性,超出了传统意义上的文学审美,是一种“极具科技前瞻性、充满浪漫幻想、富有生命活力的文学形式”⑩。它将传统文学中的时间与空间延展至极致,在“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自我”等传统的人人、人物关系层面之外,拓出“人与宇宙、人与外星文明、人与未来”等新的关系层面,从而大大丰富了“文学是人学”的思考。然而,遗憾的是,对于这些新的关系,整个20世纪的中国科幻小说都做得并不好。虽然将眼光放在了地球之外,或者遥远的明天,但在艺术审美的表达方面,依然停留在较为肤浅的层面。新时期“重返启蒙”的号角吹响后,科幻小说的参与是全方位的,“德先生”和“赛先生”两面旗帜并举,但具体到作家作品层面,便会发现,大多数小说往往“跛足”,即要么专注于“科学祛魅”,要么汲汲于人性张扬,能够两者兼顾的作品较少,其中又能以科学为艺术审美对象,进行美学建构的,几乎没有。
此外,将幻想的脚步黏着在现实的地面,某种程度上则造成了想象力束缚等负面影响。超越日常、超越现实的未来前景构筑是科幻小说的致力所在,这也是科幻小说与其他小说尤其是非幻想小说的本质区别。如果说1980年代初期科幻小说的想象力是因政治意识形态而丧失,那么到了1990年代乃至新世纪,精英文学强大的现实主义传统则成了导致科幻小说想象力丧失的新力量。的确,科学幻想的进入让科幻小说的批判现实叙事增添了些许陌生化的美学魅力,对科技与人关系的关注也让科幻小说更准确、清晰地把握住了我们当下这样一个高速发展的高科技时代的脉搏,但当映射社会现实的着力过猛,反映社会现实而不是将未来照进现实成为这些科幻小说的创作旨归,科幻小说应有的飞扬想象力被大大遏制了。可以说,无法与未来结合的人性思考和民族化想象也许成为一部优秀的现实主义文学,但不可能是一部杰出的科幻之作。
追索真理之真:科幻小说科技美学建构的
理性认知价值体系
在梳理了“科幻现实主义”带来的影响和问题之后,本文想要进一步探讨的是,中国的科幻小说应该怎样做,才能摆脱启蒙现实主义文学的惯有思维模式,成功地建立科幻小说的科技美学范式?在讨论这个问题之前,或者我们需要先解决的问题是,科幻小说中的科技美学范式应该是什么样子的?科技美学包括科学美和技术美两个方面。李泽厚认为“科学美是一种反映美,是人在探索、发现自然规律过程中所创作的成果和形式”,“技术美是人类在实践中创造的客观的工艺美”11。徐恒醇则从当代科学发展的层面,更细致地指出“科学美是以真即合规律性为其内容的,善即社会功能在其中成为一种中介”,“技术美则分别以其合目的性的善为内容(功能美)或以其合规律性的真为内容(技术美)”12。可见,反映自然的本真与技术物形式的和谐、理性以及功能性,是科技美学的主要内涵,科幻小说家们要在文本中搭建科技美学的小屋,其美学内涵的建构不是直接以现实自然和技术物为对象,而是将自然和技术物的现实形态,通过文学幻想加以变形处理,使之成为未来、过去、赛博空间或平行宇宙等某一异空间的非现实形态,从而在本真、和谐、理性等之外,增添了陌生化的另一重美学效果。
基于此,笔者认为,科幻小说的科技美学建构需要做到以下两点:第一,超越以大写的人为中心的传统人文立场,不拘囿于个体的情感与命运沉浮,只有这样,才能将视野真正拓及种族文明、地球文明乃至整个宇宙文明的层面,反映人在自然中存在的本真位置,呈现合乎科学理性的自然秩序和宇宙本质,以及基于这种认知之真的形式之美。这可以说是科幻小说建构科技美学的基础原则。
以太空科幻小说和赛博格科幻小说为例,不少小说在想象外星文明与地球文明的第一次接触,不是侵占地球资源就是友好地将先进文明传输给地球人,赛博格题材中则以想象人工智能拥有意识后,反叛人类,企图取代人类霸占地球的居多,并由此延伸出了星际战争、人工智能战争等战争幻想故事。事实上,这些想象都体现的是人类以自我为中心,从己身出发的价值预设,其结果是将想象束缚在人的利益和生存需求空间里,难以上升至更广阔的视野去看待整个生物界,乃至整个宇宙。阿瑟·克拉克的《与拉玛相会》给人的阅读震撼,就在于跳出了这样的思维模式。故事中的外星造物拉玛在太阳附近停泊,引发了人类的无限种想象,甚至派出飞船到拉玛上进行各种探测,而拉玛从来到太阳系,到获取足够的太阳能源后离开,始终无视地球及人类的存在。作者借拉玛的态度,让我们看到了人类在宇宙中如微尘般的存在事实,从而呈现出宇宙的辽阔深渺,浩瀚无边。中国科幻小说中,这样的作品也开始有所增加。深受克拉克影响的刘慈欣,更是直接在《三体》里提出了“毁灭你,与你何干?”这樣的质问,通过与更高维度文明的对比,将人类的渺小与无力展现得淋漓尽致,从而抹去人的骄傲、无知和盲目,取而代之的是对广袤深邃的宇宙的极致敬畏。陈楸帆《巴麟》中,主人公“我”和周围的所有人一样,在异生物巴麟面前充满人类的骄傲和自豪,而巴麟对人类动作行为的学习和模仿,更让大家觉得它的低人一等。直到“我”主动放弃自己的视角,将意识切换到巴麟的身体里,才发现巴麟眼中的世界原比人类更加丰富多彩,广博深远,反衬出人类在自然界实则无奇的生态地位。夏笳的英文小说《Let’s Have a Talk》则一反传统的人工智能或臣服或反叛人类的思维定式,故事中的人工智能白海狮宝宝们,在衍生出了自己的意识之后,进而发展出了自己的语言,甚至自成一个小社会,他们并不关心人类在想什么,在做什么,而是沉浸在自己的族群世界里。在这些故事里,人不再是大写的、唯一的中心,也不是世界的主宰,在地球上,人是与他的造物、其他生物平等的存在,而在时空无尽辽远的宇宙中,人则是如轻尘般微不足道。传统的人本主义价值体系被颠覆,重新建构起的,是遵从科技理性认知的新价值体系。
在这样的认知体系里,人不再位于中心,看待事物的眼光和态度随之发生改变。例如,王十月的《子世界》中,面对如俄罗斯套娃般重重叠叠的虚拟与现实世界,人已经分不清楚究竟哪一重世界才是现实,自己所处的现实是真实的存在,还是上一层世界里的人布下的虚拟幻象。陈楸帆的《坟》《犹在镜中》《人生算法》等小说,也都在努力探寻虚拟与现实的双重空间里,人的哪一种状态才是真实的。这些小说里诘问的真实,不只是启蒙现实主义文学中的人性真实、情感真实,也是某一事件真相的推理真实、逻辑真实,说到底,是从科学理性出发的真理本真。而它的美学观念向上追溯的思想之绳,可以直接系至柏拉图时代的“美即真理”思想。如本雅明所言,在柏拉图那里,真理是作为美的事物的内涵来展开的13,海德格尔也称“美是作为无蔽的真理的一种现身方式”14。希腊哲学中的美,并非仅仅依据某物外表带来的快感而存在,而是存在于某物存在的真理被揭示之时。人被真理的闪光激发思考,感到震惊,这就是美的感受。
科幻小说将现代时期被割断的美与真相的联系重新关联起来,使读者从求真的指向中获得美的体验。以人物形象的塑造为例,一是科学理性的真实取代人的真实,成为小说美学建构的主要目标,因此,科幻小说中的人物形象并不需要执行丰满、真实这一现实主义文学人物形象塑造原则,他们更多的是代表人类种族,或其中的某一类群体,来为科学理性的真实服务,这或是为什么我们在科幻小说中读到的人物形象,大多平面化、单薄化,缺乏现实主义文学要求的独特个性和福斯特所说的“圆形”人物特征。比如王晋康小说中为追求科学真理或完成科技事业,甘愿付出一切代价的科学家,如《逃出母宇宙》里的楚天乐,《终极爆炸》中的司马完,《太空清道夫》中的太炎,《科学狂人之死》里的胡狼等,他们的所作所为或许并不符合人本主义,甚至有违人类社会的伦理道德,但对真理的执着求索,依然让他们的形象闪耀着令人动容的光芒,尤其当其行为在科学真理和人类生存面前无从抉择时,表现出的矛盾、痛苦和分裂,形成巨大的美学张力,独特且引人深思。二是还原到完全自然人性,复苏动物本能的两性书写。王晋康小说中的两性身体,往往丰满、健美,充满性的欲望,是动物本能状态下的人,或者说体现了人的自然本真状态。如《一生的故事》中我和戈亮的结合,《癌人》里海拉将性欲望作为自己是否具有人性的检验标准,《逃出母宇宙》里为了保障人类太空繁衍、生存的一夫三妻制度等。在这些散发着性魅力的人物身上,体现出的是以科学认知为价值标准的存在之真,以及由这种真显现出的自然之美。
技术物的细节想象:科幻小说科技美学的
独特魅力呈现
当然,对于科幻小说来说,最能够体现“合目的之善”“合规律之真”两个维度的科技之美的,还是对科学事物、技术器物的书写和想象。这就涉及本文要讲的科幻小说科技美学建构要做到的第二点,超越工具性、功利性的科技理性思维,把科学技术物作为与人、自然同等重要,甚至重要性超过前两者的艺术审美对象,通过细节的编织、打磨,景观的架设、描绘,从“合目的之善”“合规律之真”两个维度,建构富有创新性和新奇美学魅力的物意象,激发读者对科技事物的美学感知和审美愉悦。儒勒·凡尔纳的小说之所以令人着迷,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对海洋、地底、太空等普通人少有涉足的自然地域进行了基于大量实证研究基础上的细致描写和由此延伸开去的创造性想象,而这些描写和想象中的美,闪烁着知性和智的光芒,让读者在追随美的同时,踏上求真的道路。
在科技物意象的建构中,技术细节想象最能体现科幻的独特美学魅力。不同的艺术材质,体现出不同的技术美学价值。电子、金属、各种化学物质等现代科技材质,体现出的是科学技术之美。优秀的技术细节想象,能够通过遣词造句,使现实生活中不存在的事物生动可感地呈现在读者的脑海里,调动起读者对技术美学的感知,对科学精神的向往以及对未来科技想象的憧憬。但是,技术细节想象的难度又处于文学想象的顶级,不仅需要作家有十分专业的技术知识背景,还要以现有技术为起点,进行超越客观生活的细致想象,赋予不存在的科技意象鲜活、饱满的质感。此外,如果是距离读者日常生活较为遥远的技术细节想象,还需要一定的科普叙事技巧,帮助读者解决阅读屏障,这样才能在读者的脑海里形成真实可感、清晰具体的画面。扎实的科学专业技能、敏锐的审美眼光、良好的艺术潜能和天马行空的想象力等多方面能力兼备的作家,少之又少。放眼世界科幻文坛,能够在文本中展开精妙的技术细节想象的作家,亦是屈指可数。
郑文光是较早迈出这一步的中国作家。写于1950年代的《火星建设者》中,作家就开始尝试在文本中进行技术细节想象。小说在描绘火星生产基地时,用“锗片”“无线电望远镜”“钢架”“人工合成土壤”和“超声波”等极富金属质感和现代科技气息的事物,颠覆了读者经验世界里的农田耕地画面,带给了读者超凡奇特的美学感受。1980年代的《战神的后裔》进一步强化了技术细节描绘,以建设者们测验、分析火星烟雾一节为例,作家极其细致地向读者讲述钻井的搭建和操作过程,甚至连烟雾中的各种化学元素也一一罗列,产生的阅读效果有二:一是大大增强了文本的真实性,二是这些科学术语放在文学文本中,产生了陌生化的效果,尤其是对于非专业读者,而且容易转化为认知间离的审美效应,刺激和提升阅读的兴趣。但如果科学专有名词和相关专业理论造成的阅读障碍过多,不但无法对读者形成阅读挑战的欲望和探究未知的吸引力,反而会起到相反的效果。比如小说第十二章,一开头作者就抛出三篇高深的天文学科学报告,读起来艰涩难懂,枯燥乏味,大大降低了阅读兴趣。
除了鄭文光,新世纪之前还有少数作家作品中也有些许技术细节想象,如刘咏《两根奇特的手杖》、童恩正的《在时间的铅幕后面》等。《两根奇特的手杖》中详细地记录了遗传学家鲁大全搜集细胞资料,进行实验分析的步骤,但由于文本语言过于平实,只有操作过程的堆砌,缺乏必要的故事情节支撑,原本新奇的想象也变得索然无味了。《在时间的铅幕后面》的技术细节多集中在考古方面,无论仪器探坑还是人工挖掘,作家都准确捕捉到了细节的关键点和敏感部位,将神秘的考古工作传神地展现在读者面前,应该说非常成功。可惜的是,童恩正的考古技术细节基本属于写实范畴,缺乏丰富的从现实延伸开去的技术想象。
总体而言,新世纪之前,中国当代科幻小说中的技术细节想象质量并不高,很多作家也并不重视。除去本身难度大,要求高之外,还有两个原因:第一,少儿科普型科幻的科普需求,基本集中在科学原理的阐释,技术细节专业程度高,对于少儿读者并不适用,也没有太大必要;第二,不以科普为需求的科幻小说,在彼时并没有意识到技术细节的文学审美功用。他们所关注的,更多是现实主义文学观念下的文学性。虽然我们在郑文光等人的小说创作中,看到了初步的技术细节想象,但与其说这些书写是一种自觉的叙事美学探索行为,不如说是对文本科学知识严谨性、准确性的需求,以及相关推测性想象可能实现的合理性的展示。
新世纪以来,技术细节想象成就最高的作品,非《三体》莫属。刘慈欣曾回忆自己小时候第一次看到大型火力发电机组和在头顶呼啸而过的高速歼击机时,心灵感受到的震颤。他称,“这震颤只能来自对一种巨大的强有力的美感的深切感受”15。这种“巨大的强有力的美感”就是现代工业科技的技术美。《三体》中,作家用大量的技术细节将这种宏伟、理性、充满着速度感和力量感的技术美,清晰具象地呈现在读者面前。在此,本文仅以《黑暗森林》中关于“水滴”的章节部分为细读对象,从物象质感构建、认知错位与转向、科学语言与文学语言的交融三方面展开探讨。
第一,物象的质感构建。几乎所有读过《三体》的读者,都会被文本中瞬间横切巨型舰船的纳米丝、直接将世界从三维降至二维的二向箔等武器描写深深震撼。小说里由强相互作用力材料制成的宇宙探测器水滴,“外形完美,这颗晶莹流畅的固态液滴,用精致的唯美消弭了一切功能和技术的内涵,表现出哲学和艺术的轻逸和超脱”16。这个外星武器以细腻的光影变化、严谨的比例结构和超凡理性的形式秩序征服了地球人类,被比喻为“一滴圣母的眼泪”。从外观上看,水滴十分符合工业革命时期的机械美学标准,即简单流畅的几何形态。刘慈欣十分推崇阿瑟·克拉克《与拉玛相会》中的物象描写,盛赞这部作品“体现了科幻小说创造想象世界的能力,整部作品就像一套宏伟的造物主设计图,展现了一个想象中的外星世界,其中的每一块砖都砌得很精致,很理性”17。《三体》尽管没有像《与拉玛相会》那样,呈现出“一套宏伟的造物主设计图”,但实现了将技术想象世界的每一块砖都砌得很精致、很理性的追求。
传统文艺理论在谈到艺术构成要素时,往往只注重精神层面,如主题、内容和形式等,忽略或弱化物质层面,如质材、工具和技法等。技术美学强调的就是物质基础这个层面,物质如何创造美,是技术美学的核心。以前文谈到的“水滴”为例,“水滴”最令人惊叹和震撼的是制造它的材质。作者花费了大量笔墨,细致描绘了“水滴”的质感。“水滴”镜面的光滑程度超出了人类的想象能力,即使放大一千万倍,“其光洁度与周围没有被放大的表面没什么区别”,用地质锤用力砸,同样在一千万的放大倍数下,“仍是绝对光滑的镜面”18。小说借物理学家丁仪之口,告诉读者只有在分子像被钉子钉死一般相互固结的情况下,自身振动消失,才会达到这样的光洁程度。不同的材质给人以不同的美感,如果说泥土给人以古朴之美,石头给人以坚实之美,金属给人以冷峻之美,那么制造水滴的这种材质由于并不存在于现实世界,读者无法直接展开想象,因此,作家采用将人类的小型无人飞船“螳螂号”的机械臂和“水滴”进行对比,使读者借助现实世界中的物质基础,向上延伸想象,想象的参与让读者对这种物质美学品质的感受和把握更具有积极性和自主性,产生的文本印象也就更深。与此同时,这种对比之下产生的张力美学如此强劲,强劲到让人类消弭了对那个遥远世界的陌生感,“代之以强烈的认同愿望”19。艺术的美是无国界的,而在这里,水滴的美让读者感受到的是,艺术的美是无种族、无文明的,自然美、人工美和机械美的内在联系有了重新的思考路径。
第二,认知错位与转向。前文已述,科学内核坚硬的科幻小说,其认知疏离的美学效果构建往往需要分两步走,即先将超验性的太空幻想景观,通过类似的日常事物比拟,使其同化为读者已有的认知结构。这一步完成之后,作者要继续进行的是用同化失败的方式,让读者形成认知错位并感受巨大的新奇感和震撼感,并随之调整、改变既有的认知结构,完成认知重建。作家在关于“水滴”的描写中,用技术细节搭建出的认知错位堪称典范。
“水滴”是一个完全虚构的物体。读者根据作者的描绘,如“头部浑圆,尾部很尖”,像“一滴水银”的“水滴”形狀,以及“纯洁”“唯美”“飘逸”等词语,结合日常经验中对水的认知,即把水看作是生命之源,和平的象征,以及“水滴”无法在高频波段进行任何探测的特性,很自然地在脑海中形成美与善的价值判断,并认同文本中的人类对“水滴”的印象,认为“水滴”是“三体世界发往人类世界的一个信物,用其去功能化的设计和唯美的形态来表达一种善意,一种真诚的和平愿望”20。这一判断,与后文中“水滴”在一分二十八秒内摧毁近两千艘恒星级战舰的暴烈摧毁行为,形成了鲜明对比,反差强烈的剧情反转,极端的认知错位,给读者造成巨大的心灵震撼。落差如此大的认知错位,如果处理不好,有可能形成文本前后的不一致,甚至断裂,影响阅读的接受。刘慈欣的聪明之处,在于用物理学家丁仪这一角色进行了恰到好处的铺垫处理。丁仪承担的叙事功能,是在读者形成“水滴”美与善的认知的同时,又一点点撕裂这一认知,让之后认知转向的发生变得平滑。
小说里,当大家都被“水滴”的美折服,并把这种无瑕的美与善结合,将“水滴”视为和平信物时,丁仪的沉默和阴沉的脸色如万里晴空远端的一小朵乌云,为后文的认知反转埋下了伏笔。他对“量子号”指挥官们的喜爱和赞美,犹如预先为他们被“水滴”毁灭奏响的挽歌。悲剧还未发生,凭吊的咏叹调已激荡于读者心间。之前飘荡在晴空远端的乌云逐渐前移,阴影也不断扩大。及至丁仪带着三位军官对“水滴”进行进一步检测,发现“水滴”的真实力量和攻击性目的,并发出“傻孩子们,快跑啊”的呼唤时,乌云已凝结成骤雨,伴随着狂风呼啸而下。而这种大开大合的叙事效果,在丁仪这一角色的层层铺垫、预设下,没有显得过于突兀,在给读者造成强烈冲击的同时,又让读者有足够的心理准备迎接这种撞击,从而有效地提升了阅读的愉悦感和期待度。
第三,科学语言与文学语言的交融。不同于经验性的、形象的文学语言,科学语言的目的在于阐述科学原理,因此追求的是准确无误的表达。科学语言进入文学文本起到的叙事效果,是清晰化、直观化读者对事物意象的感受,强化文本的逻辑性和真实性。《三体》中“螳螂号”探查“水滴”的这一段,用“五十米”的距离,“半个小时”的飞行,“四光年外”和“近两个世纪”等数字表述,将宇宙空间的辽阔直接拉到读者面前。作家用了四百多字的篇幅描绘“螳螂号”接触“水滴”的过程,“悬停”“近距离扫描”“绝对零度”“超长机械臂”“六指夹具”这些科学词汇既有着科学的理性和严谨色彩,又不过于生僻,营造出影视剧慢镜头般逼真、生动的视觉效果,再加上“舰队百万人的心脏”、三小时后“地球上的三十亿颗心脏”的悸动,凸显出人类全体对整个捕获过程的极端关注,强调这是一件改变人类整体命运的关键事件。
需要注意的是,科学语言特有的冷静、客观和理性,再加上极为准确的技术细节描写,往往会使呈现出来的画面看不到作家的个人印记和主观色彩。并且如前所述,过多科学语言的使用,容易导致文本变得枯燥、干硬。因此,优秀的科幻小说,其语言的使用往往都是科文交融,科学语言的精确和理性强化读者对事物意象的物质性感受,文学语言的形象和感性则配合科学语言,一起调动读者经验世界的认知储备,唤起读者的主体情感想象,从而加深这种物质性感受的主观精神体验,两者有机结合,能够很好地调动读者的阅读积极性。
《三体》的影响,加上国外科幻优秀之作的大量译介,以及中国科幻创作群体新生力量迅速成长等多方面原因,近年来有少量年轻的科幻小说家已经具备了较为高超的技术细节想象营构技巧,例如陈楸帆的《荒潮》,用层叠繁复却不显累赘的精妙语言,描绘出各类赛博人形象,生动传神,鲜活而饱满。尤其是小米人机合一时,用意识操控钢铁身躯,电击自己的人类躯壳时的情景,精到又简洁的语句,编织出极为细腻、确切的细节画面,真实可触,给人以身临其境的现场感。此外,王诺诺的《故乡明》、张冉的《太阳坠落之时》等作品也颇值一提。《故乡明》里给月球抛光的技术细节想象,宏阔壮丽,富有诗意,《太阳坠落之时》中的太空战争场景辉煌壮烈,极具大开大合之美,与刘慈欣的作品有着异曲同工的现代工业技术美感。
遵从科学理性认知的真理之真,技术细节想象的营构以及前文所谈到的将科普作为叙事美学手段,都只是科幻小说科技美学建构的某几个侧面,不能代表科幻小说科技美学建构的全部。并且科幻小说作为小说类型的一种,首先要努力做到的是小说的基本美学需求,在达成了小说基本美学需求的基础上,才有进一步建构科技美学这一更高层级美学需求的可能。莫言在诺贝尔文学奖颁奖典礼时的主题发言《讲故事的人》,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告诉了我们好作家的基本能力,就是要能讲一个好故事。而好故事的最低标准,就是要让听的人能听懂。这便是本文为何要从梳理20世纪中期中国科幻小说的科普叙事问题入手,因为这是对中国科幻小说科技美学建构问题进行反思的第一步。而在完成了第一步的基础上,着手展开对科幻现实主义问题的重新探察,目的是将科幻小说从其他的小说类型中抓取出来,放大、凸显科幻的美学特质,让科幻小说成为科幻小说,而不是其他小说的模式变形,只有这样,科幻小说才能产生其独特的美学意义,为小说乃至整个文学打开更多的美学生长空间。
此外,还需一提的是,在探讨科技美学建构问题的文本案例选择上,本文将较多的篇幅放在了《三体》上。的确,无论从科普叙事、科学理性之真还是技术细节想象方面,《三体》的科技美学书写迄今为止依然没有哪位中国作家作品能够超越。当然,这也与刘慈欣的成长经历和专业背景等有关。在“一种神话般的宏大历史叙事中开始自己的生活的”成长经历,使他的作品中往往呈现出大开大合的宏阔气势,人类整体主义的价值情怀,且自然而然地流露出理性乌托邦主义的诗性气质。博大、开阔的视野,以及理工科的专业背景,让作家在阅读译介作品的时候,倾向于儒勒·凡尔纳、阿瑟·克拉克等人的作品,并形成了他后来冷静客观的写作态度,以及执着于工笔描摹技术细节的叙事技巧。同时,作家亦自接受20世纪80年代初期作品影响较深,而那个时期,正好處于中国科幻小说“科、文”之争,新旧交替的驳杂阶段,既有依然坚持“十七年”少儿科普型科幻的创作,也有向主流文学学习,开拓文学新空间的尝试,因此,对刘慈欣的影响也是多元复杂的。所有这些,构成了《三体》及其他创作科技美学的建构基础。对于刘慈欣之后的作家,尤其是80后作家而言,大机器工业时代已经远去,但并不代表大机器意象及其相关的技术细节想象已经结束,毕竟人类的太空之旅仍然处于造梦阶段,跃入苍穹的理想依然需要靠尖端的科学技术物来实现。除此之外,新生代作家还有更大的技术美学空间有待开拓,比如后工业信息化社会中的赛博科技美学。虽然已有少数作家,如陈楸帆、江波等,在赛博书写方面进行了不少美学实践,也取得了一些成果,但对比美国赛博小说如《黑客帝国》《网路杀神》《副本》等,便会发现需要改进和提高的地方还是非常多的,比如上述作品中繁复绵密的细节意象编织出的巴洛克式虚拟空间,以及现实与虚拟交错跳跃和穿梭的场景切换描写等。此外,综合新生代作家更为阔大、国际化的创作视野,以及更为自由的创作空间,如果能摆脱20世纪中国科幻小说创作中出现的问题,相信经过一定时间的积累和沉淀,会有更为优秀的,至少在科技美学方面不输于甚至超过《三体》的作品出现。■
【注释】
①鲁迅:《月界旅行·辨言》,《鲁迅全集》第10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第152页。
②[加]达科·苏恩文:《科幻小说变形记:科幻小说的诗学和文学类型史》,丁素萍等译,安徽文艺出版社,2011,第8页。
③江波:《银河之心·天垂日暮》,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2012,第60页。
④郑文光:《答香港〈开卷〉月刊记者吕辰先生问》,载黄伊编《论科学幻想小说》,科学普及出版社,1981,第141页。
⑤彦桦 :《中国科幻小说的现况及发展》,《明报》1981年7月8日。
⑥韩松:《在今天,科幻小说其实是“现实主义”文学》,《中华读书报》2019年1月30日。
⑦陈楸帆:《“超真实”时代的科幻文学创作》,《中国比较文学》2020年第2期。
⑧M.G.Lord,“Doris Lessing’s Nobel:A Victory for Science Fiction”,Los Angeles Times,Oct.15,2007.
⑨吴岩:《科学与文学结缘的奇葩——百年西方科幻》,《世界文化》2015年第2期。
⑩王卫英、姚义贤:《科幻小说界说及其审美意蕴》,《科普创作通讯》2012年第1期。
11李泽厚:《谈技术美学》,载《走我自己的路:杂著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第188页。
12徐恒醇:《科技美学的历史渊源和方法辨析》,《山东医科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2期。
13[德]瓦尔特·本雅明:《德国悲剧的起源》,陈永国译,文化艺术出版社,2001。
14[德]马丁·海德格尔:《艺术作品的本源》,载《林中路》,孙周兴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第46页。
15刘慈欣:《混沌中的科幻》,载《刘慈欣谈科幻》,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2014,第80页。
16181920刘慈欣:《三体·黑暗森林》,重庆出版社,2008,第371-372、380、378、367页。
17刘慈欣:《使我走上科幻之路的外国文学作品》,《花城》2018年第12期。
(詹玲,杭州师范大学文艺批评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