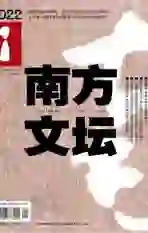李章斌的新诗研究
2022-01-26王彬彬
李章斌在同一代际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者中,应该有些特别。本科,李章斌上的是南京大学历史系。硕士阶段进入南京大学中文系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学习,硕士毕业接着攻读博士学位,师从丁帆教授。但攻读博士学位期间,赴美国加州大学拜著名的中国新诗研究专家奚密教授为师,时间一年。所以,李章斌算是南京大学与美国加州大学联合培养的博士。博士毕业留校,只用两年时间便顺利获得副教授职称,这当然是十分罕见的。说“顺利”,是因为在现在激烈的职称竞争中,李章斌的职称晋升在各个层面都没有任何异议,因为他的成果实在是很突出。当上副教授后,李章斌又以访问学者的身份赴美国加州大学进修过一年。在副教授的职位上,李章斌也没有停留多久,便又以各个层面都没有异议的顺利晋升为教授,并且很快成为博士研究生导师。
但我说的“特别”,并不指职称晋升上的顺利这类事。本科毕业于历史系,这是李章斌的比较特别之处。四年的历史学专业性学习,当然使得李章斌的知识结构和精神视野有着更丰富的历史内涵和历史维度。目前,李章斌虽然还没有有意识地进行跨学科研究,但在对穆旦等诗人的研究中,却明显表现出一种历史感。李章斌的另一个比较特别之处,是英文特别好。这一茬的学者,英文普遍不错,但李章斌的英文水平应该超乎侪辈。李章斌完全能够阅读英文文献、理论著作,也能够以英文进行学术论文的写作。李章斌的文章,频繁征引英文论著。有些原著便是英文,有些则原著并非英文,而是德文、法文等西方原著的英文译本。有些西方论著,目前没有汉译本,而能够以英文阅读,当然就比不能如此者多了一种学术资源。李章斌研读、参考的西方论著,有的原著并非英文著作,而是德文、法文等著作的英译本。这样的论著,即便有汉译本可读,但汉译本的可信度也远远不如英译本。这是一定的。不久前,有翻译界和出版界的权威人士公开表示,目前汉译学术著作,百分之六十以上不可信。对于这一点,我是深信不疑的。我们的很多翻译界人士,是只懂某种外语却不太有文化的。翻译文学性书籍者,没有起码的文学鉴赏力,甚至也没有必要的文学常识,所以完全可能把一本诗意盎然的书译得面目可憎。翻译学术性著作者,没有起码的学术修养,所以会把孟子译成门德修斯,会把蒋介石译成常凯申,会把胡适的家乡徽州译成惠州。翻译界人士还有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就是汉语表达能力不够好,所以他们的译文,常常夹缠不清、语无伦次,让人无从捉摸。可是如果不能从非汉译本吸取资源,而又需要异域营养,就只能依赖百分之六十以上不可信的汉译本了。英文好,同时李章斌也似乎特别善于搜寻英文资料,这就使得他在学术研究中具有了又一种优势。
李章斌对中国新文学中的诗歌情有独钟,从读博士开始,一直致力于新诗研究。他的研究大体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对一些重要诗人的个案研究,另一方面是对新诗创作中一些基本的理论问题的探讨。李章斌多次表达过这样的意思:新诗诞生百多年了,但新诗创作中的一些基本的理论问题,例如节奏、格律、韵律等,却一直未得到深入的探究。我是同意这种看法的。新诗是否也应该有必须遵守的规则,新诗创作是否也应该在约束中表现自身的美,新诗创作中的自由是否有限度以及如果有又在哪里,诸如此类的问题,并非没有被关注过。新诗诞生的那天起,这些问题就被提出,就被谈论,此后甚至一次又一次在某种机缘下被重新提及。但每次讨论都浅尝辄止。新诗创作者和研究者,好几代人了,一直没有在一些基本的问题上达成起码的共识。在某些时期,看似人们都认同、拥护甚至赞美某种同一的新诗美学原则,但那其实是源于外在的强制。当强制消除,新诗创作和研究界,立即在美学趣味和美学观念上四分五裂。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诗创作和研究界表现出一种十分奇妙的状态:在创作上,最陈古的方式和最新潮的方式共存;在研究中,最老旧的话语和最时髦的话语并在。诗歌创作和研究界之外的人,往往有“看不懂”的慨叹。就是置身新诗创作和研究界的人,恐怕也未必看得很懂。最近数十年的新诗创作和研究界,给人的最突出印象,便是乱。或许正是有感于此种现状之不合理,李章斌多年致力于新诗创作和研究中一些基本理论问题的梳理、辨析和研究。澄清、阐明一些基本的理论问题,让新诗创作者和研究者在这些基本的理论问题上达成最低限度的共识,可能是李章斌的一种学术理想,一种文化追求。所以,李章斌的两类文章,对具体诗人的研究和纯理论性的探讨,最终都有共同的指向,即都归结到对那些基本理论问题的思考。
李章斌对一系列新诗创作上的重要诗人,例如穆旦、卞之琳、痖弦、多多、张枣、朱朱等,进行了个案性的研究。这些诗人,都被人反复谈论过,尤其像穆旦、卞之琳、痖弦这样的诗人,海内外研究得很多。但李章斌的研究,仍然有充沛的新意。李章斌的問题意识是不同于他人的,所以,李章斌的视角也是独特的,而最后的学术观点也必然是创发性的。
同许多人一样,李章斌也十分推崇穆旦。但李章斌对穆旦又有着颇不同于他人的感受、理解。李章斌的博士学位论文就是以穆旦为研究对象。论文扎实、厚重,当然是很优秀的博士论文。后来,李章斌又写了多篇研究穆旦的论文。《重审穆旦诗中“我”的现代性与永恒性》,对穆旦诗作中的“我”作出了新的解读。此前的研究者,都从穆旦与现代主义的关系角度理解穆旦诗作中的“我”,即认为穆旦诗作中对自我残缺性的表现和对完整性的追求,都是现代主义的典型特征。李章斌却指出,仅仅从现代主义的角度理解穆旦诗作中的这一精神现象,是不能对这种精神表现做出充分的解释的。李章斌指出,穆旦诗作中的此一精神表现,与柏拉图思想和基督教精神影响有关,同时,还与中国现代历史的血腥相关联。这就使得穆旦诗作的“我”以更为丰富、深邃和复杂的品格出现在我们面前。“我”是诗歌创作中频频出现的抒情主人公。古今中外都如此。中国的新诗,也从一切开始便如此。但李章斌最后强调,穆旦诗作中的“我”,与其他诗人,例如郭沫若诗作中的“我”,有着极为不同的内涵。穆旦诗作的“我”,既不同于浪漫派诗作中傲视一切、顾盼自雄的“我”,也有别于一心要参与历史、改造世界的理性主义的“我”。这就让穆旦诗作的独特价值进一步显现。李章斌是通过细致的文本解读逻辑地、也是自然而然得出这种结论的。
细致的文本分析是李章斌新诗研究的基本方式。而文本分析得以展开和成立的前提,是敏锐的艺术感觉,是良好的文学领悟。李章斌具备很好的理论修养,同时又具备对文本细致而妥帖地进行分析的能力。其实,文本分析,还有一个耐心问题。细致的文本分析,意味着对一字一句进行品鉴、解说,是很烦琐的。但对于李章斌的学术目的来说,却又是绝对必要的。李章斌要梳理、阐发新诗的节奏、格律、韵律等问题,就必须进行这种烦琐的字句分析。而李章斌显然具备这份耐心。这份耐心保证了李章斌在每篇文章里都能将文本分析进行到底。良好的理论修养又保证了李章斌的文本分析没有停留在纯然感性的层面,而总是能将感觉、领悟升华为某种普遍性的理论认识。
李章斌的论文《“在言语所能照明的世界里”:穆旦诗歌的修辞与历史意识》,论述的是穆旦诗歌创作中修辞意识与历史意识的关联。穆旦诗歌有着个性鲜明的修辞表现。意象的营造、隐喻的运用等遣词造句方式,用李章斌的话说,往往激烈、繁复得令人眼花缭乱,也让很多读者如坠五里雾中,无从把握其意旨。有人认为穆旦的复杂仅仅表现为修辞的复杂。如果这说法成立,那就意味着穆旦的诗歌创作只是在玩弄修辞游戏。李章斌不同意这种看法。以细致的文本分析为手段,李章斌在穆旦的修辞方式与穆旦对现实的感受之间建立了密切的联系。李章斌强调:穆旦的特有的修辞方式,是植根于对现实的深切感受;是现实的阴暗、血腥,迫使穆旦的诗作以激昂与沉郁相交织的方式出现;穆旦诗作甚至在修辞的细微方面都体现了作者对现实的独特感知。所以,穆旦绝不是在进行修辞表演。李章斌进一步强调,穆旦实际上为新诗写作如何介入历史树立了典范。把一个作家的修辞手法与其历史意识结合起来分析,是我十分心仪的文学研究方式。毕竟脱离历史意识而谈论修辞手法和脱离修辞手法而谈论历史意识,都有着明显的缺憾。
说李章斌总是把对个案的研究上升为对某种理论问题的思考,这是从他那些论文的题目就能看出的。例如,《重审卞之琳诗歌与诗论中的节奏问题》;例如,《痖弦与现代诗歌的“音乐性”问题》;例如,《走出语言自造的神话——从张枣的“元诗”说到当代新诗的“语言神话”》;例如,《成为他人——朱朱与当代诗歌的写作伦理和语言意识问题》。在这些题目中,每一个具体的诗人都与某种具有普遍意义的理论问题相关联。《重审卞之琳诗歌与诗论中的节奏问题》一文,是在以卞之琳诗歌中的节奏表现和其诗论中对节奏的认识为例,表达自己对新诗创作中节奏问题的思考。同许多基本的理论问题一样,新诗创作中的节奏问题,是一直没有被真正深入地研究过的问题,也是新诗创作和研究界长期没有达成最低限度的共识的问题。李章斌的文章开头就明确表示,自己写作此文的目的之一,就是要解决这一悬而未决的“课题”。以对卞之琳诗作和讨论的分析为切入口,李章斌提出了对节奏问题的比较系统的认识。李章斌发现,卞之琳诗作中的节奏运用,与他对节奏的理论认识,其实是有着矛盾的。卞之琳诗作中,其实大量存在着“非格律韵律”;也正是这种“非格律韵律”的巧妙运用,使得其诗作具有特别的魅力。在论文里,李章斌对节奏、韵律、格律三者的关系做了理论性的区分。李章斌认为,韵律是一个比格律更宽泛的概念;格律当然是韵律,但只是韵律的一种表现形式,而不等同于韵律;因为非格律韵律也是一种韵律。在借鉴中外理论的基础上,李章斌对节奏、韵律、格律的内涵分别做了精细的论说。这样的论文,有着明显的理论上的创意。
长期以来,中国文学研究怎样利用异域理论资源的问题,是一个十分成问题的问题。对异域理论的生搬硬套,对异域理论的活剥生吞,数十年来是普遍存在的现象。中国文学研究,在许多人手里,变成了以中国文学作品和文学现象印证某种异域理论的劳作。劳作者如果能够遵守一些基本的学术规范,例如,一篇论文只借助一种异域理论,或者说,一篇论文里只用中国文学印证一种异域理论,而那印证过程似乎也还合乎逻辑,就算是很好的情形了。但即便如此,除了又一次证明了那种理论的合理性,什么也没有说明。但这样的情形其实是很少见的。更多的时候,我们读到的这类研究,是一篇文章里套用了多种异域理论,或者说,是用中国文学的作品、现象印证了多种异域观点。其原因,就是如果只搬套、吞剥一种异域理论,无法完成一篇论文。开头部分说到的问题,在他看来只能借助甲种理论,于是就搬套一番从汉语译本上学来的甲种理论;中间部分说到的事儿,在他看来只能借助乙种理论,于是就吞剥一番从汉语译本上学来的乙种理论;后半部分谈及的现象,在他看来只能借助丙种理论,于是便挦撦一番从汉语译本上学来的丙种理论。这不但是生搬硬套、生吞活剥,而且在搬套、吞剥过程中表现出强烈的机会主义色彩。这样的搬套、吞剥过程,当然没有逻辑的条理可言,当然谈不上言之有理。那些中国文学的作品、现象与那些异域理论,始终互不相干,始终你是你而我是我。利用异域理论更好地阐释了中国文学的作品和现象,这当然谈不上。就是以中国文学作品和现象印证异域理論,也远远没有做到。人们把这样的情形形象地称作“两张皮”。数十年来此种现象之所以普遍存在,我想,原因可能有两种。一种是,有许许多多的中国文学研究者,对文学的历史进程没有自己的见解,对文学作品也没有起码的感受能力,却又要写文章、出成果,那怎么办呢?对异域理论的搬套吞剥、稗贩挦撦,便是一种很好的办法。另一种原因,是文学研究中持续甚久的对异域理论的崇拜。写一篇研究中国文学的文章,如果里面没有一点西方时髦理论在那里装点,就完全没有理论性,就完全没有学术性,就不应该称作论文。如果西方现代理论出现得不够多,也意味着理论性不够、学术性不够、作为论文的资格不够。既然搬套、吞剥西方现代理论是高大上的事业,而除了搬套、吞剥花大气力从汉译本中学来的西方理论,又没有别的从事学术生产的办法,那当然就会一头扎进搬套、吞剥西方理论的大业中去。说了这么多此种现象,意在强调,李章斌虽然有着良好的西方理论的知识、修养,但却从不干生搬硬套、生吞活剥西方理论的事情。李章斌对西方理论的征引,总是自然而然的,是有所节制的,尽量避免超出必要的限度。不独西方理论,中外古今的理论,都成为李章斌感受、观察、判断问题的趣味、眼光和能力。李章斌总是在对文本细致分析之后,上升为对某种具有普遍意义的理论问题的思考;总是把某个具体问题与某种具有普遍意义的理论问题相勾连。李章斌的文学研究,是有着充分的理论“内涵”的。我之所以把“内涵”打引号,意在强调,李章斌文章的理论性,是自下而上、自内而外地生成的。文学研究的理论价值,本应该这样生成;文学研究的理论品格,本应该如此确立。
在对具体诗人的研究之外,李章斌还写了些纯粹探讨诗歌理论问题的文章。《“韵”之离散:关于当代中国诗歌韵律的一种观察》就是一篇有分量的纯理论论文。诗歌的韵律问题,当然是诗歌创作和鉴赏中的一个基本问题。千百年来,中外都有不少对此问题的谈论、言说。忽视中外种种旧说而自言自语地研究韵律,显然是荒谬的。李章斌在充分注意和合理借鉴已有理论的基础上,对当代中国诗歌的韵律问题进行了很深入的探讨。李章斌的问题意识,是“中国当代诗歌韵律的变化与社会文化条件之间的内在关联”,亦即探讨的是政治、经济、文化氛围对诗歌韵律的影响,这就别开生面了。就韵律论韵律,或许永远解释不清一些基本问题。而站在政治、经济、文化的角度观察诗歌创作的韵律问题,则可能让我们把问题看得更清楚。李章斌指出,传统诗歌之所以能够建立起为社会认可的平衡对称的韵律原则,是因为传统社会有着“从万物中寻找同一性的世界意识”,而这种共同的世界意识造就同质性个人文化群体。有了这种同质性的文化群体,那种普遍性的诗歌韵律原则才能够形成。在中国当代诗歌史上,特别注重诗歌韵律的时期,是20世纪50—70年代,而这一时期也正是文化观念、文学趣味和社会生活高度同质化的时期。这时期有两类诗歌很流行,一是民歌体诗歌,一是政治抒情诗。这两类诗都有极强的韵律感,所以也极其吻合那种在各方面极其同质化的社会环境。当这种文化观念、文学趣味和社会生活的同质状态发生变化甚至裂溃,那种普遍性的韵律原则也就失去坚实的现实基础。先锋诗人们,像躲避瘟疫一樣躲避那种“整齐对称的韵律结构”,像抵制病毒一般地抵制“声音的公共性、整一性”,其实是在躲避和抵制人类精神的同质化。普遍性的韵律原则崩溃了,整齐对称的韵律结构散架了,并不意味着新诗就彻底失去了对韵律的追求。李章斌以多多等人的诗歌创作为例,说明80年代以后的自由诗,追求的是一种个人化的韵律。这种个人化的韵律,虽然不像公共性的韵律那样平衡、稳固甚至僵硬,而是有着更多的流动性,但仍然让诗歌具有一定的韵律感。所以,躲避和抵制了“整齐对称的韵律结构”的自由诗,内在的韵律仍在,也仍然有着一定的同一性,只不过表现为“流动的同一性”而已。李章斌把这种现象称作韵律之离散。这样的见解,确实有很大的启发性。
李章斌还很年轻,但在新诗研究上已颇有气象。我所希望于李章斌的,是长久保持学术热情。对于一个在学术研究上天资甚好的青年人来说,只要不丧失学术热情,其他问题都不成问题。■
2021年6月7日
(王彬彬,南京大学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