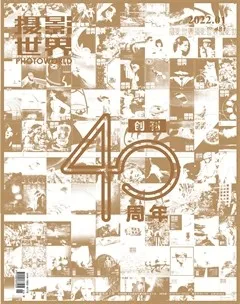投向长城的目光
2022-01-21陈晓琦
陈晓琦

维克多·雨果曾经这样形容巴黎圣母院:“这个可敬的建筑的每一个面,每一块石头,都不仅是我们国家历史的一页,并且也是科学史和艺术史的一页。”对于中国人而言,长城也是如此。
按照史学界多数人的看法,筑长城抵御外敌侵入,早在2000多年前的春秋战国时期就开始了。从那以后又经过了众多诸侯国和多个朝代的修筑,长城的长度越来越长,规模也越来越大。秦、汉、明,作为修筑长城最多的三个王朝,每个朝代的修筑长度都超过了5000公里。按2012年国家文物局公布的数据,中国历代长城遗迹总长度是21196.18公里,其中明长城东起辽宁虎山,西至甘肃嘉峪关,总长度近9000公里,今天我们所说的万里长城主要指的是明长城。

长城是中国历史上费时最久、工程最大、体系结构最为完善的国防工程。它的功能重在御敌,建筑和使用都服务于战争。《孙子》有云:兵者,国之大事也,死生之地也,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对于一个国家来说,战争是生死存亡的大事。中国两干多年的金戈铁马历史,让长城不仅承载了历朝历代与民族生死存亡息息相关的命运关注,也铸造了长城的國家地位和精神意义。

“长城”一词在春秋时期就已经出现并被广泛使用。管仲与齐桓公的对话说:“长城之阳,鲁也。长城之阴,齐也。”可见当时齐鲁两国是以长城为边界的,并且长城也是两国重要的地标。南北朝时,刘宋大将军檀道济功高震主,遭宋文帝猜忌加害,临刑时愤然脱帻投地说:“乃复坏汝万里长城耶。”可见,在南北朝时期,长城已经超越了具体的军事设施,具有了国家层面的象征意义。陆游诗《书愤》中写道:塞上长城空自许,镜中衰鬓已先斑。”这里,长城是御敌卫国的精神意象。1644年,吴三桂打开山海关放清兵入关,长城失守,朝代更替,长城对于国家重要意义的例证再添一笔。清代,康熙不修物质的长城,却着力修筑精神的长城:“守国之道,惟在修德安民。民心悦,则邦本得,而边境自固,所谓‘众志成城’者是也。”“众志成城”是对长城象征意义的精辟概括。纵观中国历史,不论是城在国在、城失国亡的史实,还是历史人物论述长城的观点,都汇合在长城的内涵之中,成为长城历史的一部分。

从历史上来看,长城的作用和意义在国家、民族生死存亡的严重危机下会有更加充分的彰显,但长城作为一个深入人心的国家与民族的象征符号及其精神内涵的真正确立,应该是在近代才得以完成或者说达到一个新的高度。晚清以来,国家积贫积弱,面对强敌屡战屡败。一系列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的签订,极大地激起国人对一个能够抵御外侮、坚不可摧的力量的向往,于是长城作为承载这种力量的象征意义得到了新的升华,并在抗日战争中达到了顶峰。“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军队在华北进行的第一次大规模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战役,就是在长城一线展开的。1933年1月到6月,中国军民重创日寇,史称“长城抗战”。“用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成为时代的最强音,长城成为一种“国家叙事”。
在当代的知识体系中,“叙事”对国家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在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看来,现代民族国家本身是一种“想象的共同体”,必须借由共同的文化记忆和历史叙事来维系。有代表性的典型景观作为国家的视觉叙事,在今天的文化传播中已非常普遍。在我们的记忆中,长城作为国家叙事的视觉形象,是以经过整修的北京等地的长城为模板的:长城如巨龙蜿蜒于崇山峻岭,阳光普照、蓝天映衬、云雾卷舒之际更加气势恢宏、无比壮丽。美好的形象表现出强大的力量和坚定的意志,饱含着胜利的自豪感,飞扬着英雄主义姿态。摄影家无数关于长城的精美图像,对于长城形象的塑造和传播无疑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长城作为国家的视觉叙事是以国家和民族为价值主体的,体现国家民族共享的价值观念体系,是对社会共享的价值观念进行强有力的整合,是一个历史性和现实性的存在。它不容置疑,并作为一种强大的精神力量以集体主义的图像方式进入个体经验,融入日常生活。当杨越峦把长城作为一个长期关注的摄影题材时,已经深入人心的长城叙事已然成为他的拍摄的基本认知和历史背景。
杨越峦出生、工作在河北,与长城相关的阅历和长城意义的熏陶已经融入他的生活,这些都会影响他的观看,介入他的长城影像。从他的作品中,我们能清晰地感到家国情怀与家乡情结。对他来说,拍摄长城不仅是艺术创作,也是应尽的责任,因此他极为投入且充满激情。
不少人拍摄长城,只是面对长城雄伟壮观的形象和在时间侵蚀中显示出的残缺沧桑的美感,表现出一种唯美主义的出场方式和观光者的创作姿态,而杨越峦的拍摄则是出于一种历史的追寻与叙事的建构。
这是一个精心制定的拍摄计划,杨越峦一年又一年奔波于河北的崇山峻岭之间,循着长城的身影,感受着历史的沧桑,思索着长城的意义,回顾着发生在这里的故事。从不同的角度、用不同的景别拍摄这些断壁残垣。从大环境中蜿蜒起伏的走势、墙体的功能结构、建筑方式、使用材料以及当年使用留下的痕迹,等等,他一段一段地走过河北境内未经修复的长城遗存,宏微并至地展示长城的历史面貌,并用数万字的“拍摄散记”,记下了拍摄的经历和思想的收获,用坚韧执着和扎实的影像,为我们慢慢揭开长城的面纱。2012年,杨越峦完成第一个阶段的创作,出版了《中国·野长城》摄影作品集。“野长城”是民间对那些未经修葺、以自然状态呈现于荒野的长城遗存的叫法。不生活在长城一带的人,甚至即使是生活在长城一带的人,都很少去这样地观看长城。杨越峦用影像给出另外一种长城样貌:一条巨龙的残骸,饱经岁月的蚀刻,雄风不再,远去了烽火硝烟,坍塌残颓中透出几多悲凉,它随着时间的流逝渐渐地湮灭于山野,走向最后的归宿,充盈着一种凝固的、沉浑的诗意。那些美轮美奂的长城影像是让人仰望、欣赏的,但由此也形成了一种遮蔽,让我们的目光停留在表面浮层,很难再深入下去,“野长城”则打开了这种遮蔽,让长城向我们敞开,每个人都可以去凝视、思考、发现,长城成为一个社会的言说对象,一个可以以各种方式自由出入的公共领域,我们由此进入一个历史现场,对长城的思考和发现都将构成长城历史的一部分。

《中國·野长城》在长城摄影中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可以看作长城摄影从“浪漫主义”到“现实主义”的一次历史性转身。1980年代唯美主义的兴起到1990年代纪实摄影的热潮,中国摄影在改革开放社会背景下的发展波澜壮阔,其艺术观念和影像文化的积淀影响深远,也影响了摄影家投向长城的目光,促成了长城摄影的转变。因此,杨越峦长城摄影中的历史文化视角、对于真实性的维护以及纯影像意味的语言等,既是属于他个人的,也是属于摄影史的。
2009 年5 月27 日,迁西县潘家口:……曾经的关城与相邻的喜峰口,一起被淹于水下,形成独特的水下长城奇观。干旱水浅时,长城的敌楼与城墙露出面,让人倍感世事沧桑之变。1933 年春天的长城抗战,喜峰口、罗文峪一带的战事尤为惨烈,堪称中华民族的伟大史诗。著名的《大刀进行曲》,就取材于这次抗战……
2012 年2 月24 日,抚宁县花场峪—卢龙县桃林口:……离开花场峪又赴卢龙县的桃林口。这里是交通要冲,军事地位异常重要,山险、城坚、墙固,长城曾经非常壮观。由于拦河筑坝修水库,关城被毁,老百姓修房盖屋,甚至垒猪圈、沿地边,也都拆用长城砖,于是曾经的辉煌杳然不再。人们说这是世界上最昂贵的村庄:用长城砖盖房子。后来老百姓觉悟了,深深忏悔,在村口立了一块“知耻碑”,并捐出长城砖建立了“醒悟楼”……
《中国·野长城》仍然处于那种“宏大叙事”的框架之中,视线主要集中在长城本身,即一种建筑的存在,叙述仍然基于长城的毋庸置疑的象征意义。确实,长期以来长城所代表的文化内涵已经深刻地铭写在我们的思想和语言的深处,以至于我们不会再用一种不同的方式从一个不同的角度看待长城和叙述我们的经历了。
在“野长城”之后,杨越峦走出了河北,向着全国各地的长城延伸:辽宁、天津、北京、内蒙古、山西、陕西、宁夏、甘肃、青海、新疆、河南、山东甚至西藏,全国拥有长城的省份,除了黑龙江、吉林,他都走到了,包括新疆罗布泊的烽燧。随着空间的展开,长城由一种建筑的视觉形象转换为一种广阔的生活现实。杨越峦看到:长城周边私开乱采和对长城的保护,一片片光伏和风力发电的覆盖,重大建设工程穿过长城村庄……“风雨的侵蚀,时光的阻隔,确实让我们对失却了实用价值的长城颇多无知和误读,长城的密码也越来越难以破解。”身体力行的跋涉使杨越峦终于从宏大叙事中的长城想象转向了对社会现实的反思,这种转变对于长城摄影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同时,杨越峦并没有否定或抛弃长城本有的象征意义,他对长城的历史认知和崇敬之情早已深入内心。只不过对他来说,长城的象征意义已经由主题转化为背景,这为他展开了一个从国家符号转变到生活现实,充满丰富性和复杂性的新时空。
杨越峦开始跳脱出“野长城”的叙述框架,寻找并建立一个新的叙事方式。荒野戈壁上,长城是一道浅浅的划痕,呈现出一种时光中的湮灭。而大漠中孤寂的烽燧又仿佛让时间静止,残颓废弃的村舍有春联飘红,风化成土堤的城墙上方乍现耸立的现代工厂,村民的生活并不富裕但不乏现代化的工具和时尚用品,“他们的生产生活方式好像一方面在穿越,一方面在定格”。杨越峦用影像蒙太奇制造出他们之间的一种陌生化和紧张感,这些长城的景象成为发散着多重语义与丰富边界的景观,他通过影像重构表达了对历史记忆和现实场景的一种辩证性思考,改写着我们关于长城的想象与记忆,同时也是对这种想象和记忆的一种存在意义上的探寻。杨越峦努力争取自由而有效的表达,寻求新的超越和突破。在这些作品的视觉表征的背后,可以看到一种构建自我的图像体系的努力,并且基本形成了一套表达自己思想的影像语汇,这是在长城历史的上下文和艺术家个人创作思路中产生的。这其间,作者本人从来没有放弃一个摄影家对历史的良知和社会的责任。
杨越峦始终重视自己内心的观感,顽强地保持着自己的个人趣味。而他跳脱出凌空蹈虚的符号化的宏大叙事,从纪实性视觉表达到个性化观看语境建立的实践,与中国摄影的当代发展进程有着高度的契合。任何一个摄影家都是在历史和文化中的,这恰恰揭示了人在历史中的真正状态。
杨越峦说:“长城改变了以往的历史,也正在改变着我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