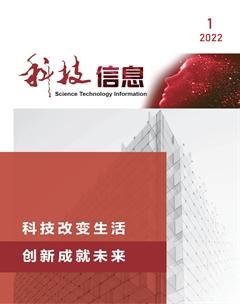南朝宋孝武帝刘骏龙山族葬墓及史事试探
2022-01-10郭良
摘要:本文细致考察了南朝宋孝武帝刘骏及其王皇后、殷贵妃、废帝刘子业及刘子鸾等生前史事,考察了其死后的葬地。对于学界认定的刘骏与王皇后的合葬墓景宁陵提出了新的意见,本文认为南京江宁西善桥宫山“竹林七贤”墓可能不是刘骏的景宁陵,景宁陵当在龙山上。按照南朝族葬习俗,刘骏一家除废帝外其余四人都葬在了龙山之上。本文提出元嘉时期宋武帝刘裕将鸡笼山改为了龙山,此龙山不是本文要探讨的岩山改名的龙山;宋孝武帝刘骏改岩山为龙山,此龙山也就是本文探讨的刘骏家族墓葬地龙山。《舆地纪胜》《元丰九域志》中都提到“宋武帝”改岩山为龙山,此处“宋武帝”当为“宋孝武帝”。南宋时编的《舆地纪胜》或是承袭了《元丰九域志》的错误。《太平寰宇记》指出宋孝武帝改岩山为龙山。《方舆胜览》真实记载了元嘉时期宋武帝刘裕改鸡笼山为龙山的史实,纠正了宋武帝改岩山为龙山的错误认识,《方舆胜览》与《太平寰宇记》保持了一致认识,本文认为《方舆胜览》和《太平寰宇记》的记载是正确的。在南朝宋时期南京同时存在两座以龙山命名的山脉。
关键词:资治通鉴;元丰九域志;刘裕;刘骏;南京;西善桥;宫山;竹林七贤;景宁陵;岩山;龙山;鸡笼山
《通鉴》卷第一百二十九,宋纪十一,世祖大明六年(壬寅、四六二)页四〇六二(册九)[1],引《元丰九域志》文本:冬,十月,壬申,葬宣贵妃于龙山。〔九域志:江宁府有龙山,山形似龙。江宁府即建康。〕凿冈通道数十里,民不堪役,死亡甚众;〔亡,逃亡也。〕自?江南葬埋之盛,未之有也。又为之别立庙。〔古者,宗庙之制,妾祔于妾祖姑。汉氏以来,薄太后生文帝,钩弋夫人生昭帝,皆就园置寝庙,未尝别立庙也。史言帝溺于女宠,纵情败礼。为,于伪翻。〕
1.《九域志》王校本卷第六,江南路之江南东路,次府,江宁府,建康军节度。唐升州。伪唐改江宁府。皇朝开宝八年为升州,天禧二年,为江宁府,建康军节度。治上元、江宁二县。[2]通过检索,江宁府条下没有关于龙山的任何记载。王校本附录《新定九域志(古迹)》卷六,江宁府,龙山,旧名巌山,宋武帝改曰龙山,形似龙见。[二][3]
此处注释[二]校勘记:旧名巌山至形似龙见,底本无此十五字。《舆地纪胜》卷一七建康府龙山:「九域志云,在江宁县南四十里,旧名岩山,宋武帝改曰龙山,形似龙见。」此脱,今据补。由上可见,《元丰九域志》正文没有龙山的任何记载,但是,在附录《新定九域志》中却详细叙述了龙山的情况,使人一目了然。此处令人困惑的是,《舆地纪胜》一书中提及《九域志》中记载了在江宁县南四十里有一座巌山,南朝宋武帝刘裕因其外形酷似龙出现的样子,从而改名为龙山的历史典故,今天读来,让人觉得饶有趣味,并且形象地把握了这座山的外观特征。
2. 本校结果:
据以上记载检《舆地纪胜》记载:全。龙山,九域志,在江宁县南四十里,旧名岩山,宋武帝改曰龙山,形似龙见。[4]王校本在引用时,加了“曰”字不妥。此处小字注释“共四十六页,全”意在表明,《舆地纪胜》建康府这一部分内容,在该文献中得以完整保留,确保了文献记录者这一部分内容是完整无缺的,增强了关于龙山资料记载的完整准确性,完整是准确的前提基础。那么,《舆地纪胜》指出《九域志》记载了龙山的情况,而今本《元丰九域志》正文中却没有任何巌山或龙山的记载,只是在《新定九域志(古迹)》中进行了记述,这使我们质疑《元丰九域志》的版本,至少在《舆地纪胜》作者的年代,可能存在《元丰九域志》不同的版本流传,或者说就是流行着《新定九域志(古迹)》不同于《元丰九域志》这样单独的版本,否则,关于龙山的记载在王校本正文中没有任何踪影,令人困惑。这里指出南朝宋孝武帝刘骏十分宠溺宣贵妃,贵妃去世后,耗费巨大人财物力,单独建造了宣贵妃的陪葬陵,以至于役使修建陵墓工程之人数量多,催促施工紧迫,兼之工程施工难度大,十分艰巨而导致大量死亡。陵寝建设完成之后,冬十月节,将其葬于龙山陪葬陵中。
《宋书》记载,大明八年夏闰五月庚申,帝崩于玉烛殿,时年三十五。秋七月丙午,葬丹阳秣陵县岩山景宁陵。[5]宋孝武帝刘骏死后,被安葬于丹阳郡秣陵县岩山。由上文可知,岩山就是龙山。南朝宋时之丹阳郡即后来之江宁府。若信从《资治通鉴》、《新定九域志(古迹)》以及《宋书》本纪的记载,可知,刘骏与殷淑妃死后都葬在了龙山。
《宋书》又载,孝武文穆王皇后讳宪嫄,琅琊临沂人。废帝即位,尊为皇太后,宫曰永训。其年,崩于含章殿,时年三十八。祔葬景宁陵。[6]可见,刘骏的正宫孝武文穆王皇后死后与孝武帝合葬于龙山景宁陵。《资治通鉴》记载:大明六年,夏,四月,淑仪殷氏卒。考异曰:《南史》曰:殷淑仪,南郡王义宣女也;义宣败后,帝密取之,假姓殷氏;左右泄之者多死。或云,贵妃是殷琰家人,入义宣家,义宣败,入宫。今从《宋书》。追拜贵妃,谥曰宣。上痛悼不已,精神为之罔罔。颇废正事。[7]宣贵妃死后葬在龙山,单独设立祭祀庙,见于《南朝寺考》一文。
《建康实录》载孝武皇帝骏事:(大明六年)冬十月壬申,葬宣淑妃殷氏于龙山。[8]本文所引《资治通鉴》条文记载的宋孝武帝的宠妃宣贵妃与《建康实录》所记载的“宣淑妃殷氏”,即殷淑妃是同年同月日下葬,二者为一人。《宋书》载:晋武帝采汉、魏之制,置贵嫔、夫人、贵人,是为三夫人,位视三公。淑妃、淑媛、淑仪等是为九嫔,位视九卿。高祖(刘裕)受命,省二才人,其余仍用晋制。世祖孝建三年,省夫人、修华、修容,置贵妃,位比相国,进贵嫔,位比丞相,贵人位比三司,以为三美人。[9]可见,到了宋孝武帝时,延续本朝后妃制度,但提高贵妃地位,仅次于正宫皇后。《南史》载殷淑妃身世:殷淑妃,南郡王义宣女也。丽色巧笑。义宣败后,帝密取之,宠冠后宫。假姓殷氏,左右宣泄者多死,故当时莫知所出。及薨...追贈贵妃,谥曰宣。...上痛爱不已,精神罔罔,颇废政事......或云,贵妃是殷琰家人入义宣家,义宣败入宫云。[10]《南齐书》载谢超宗为新安王刘子鸾的常侍:谢超宗,陈郡阳夏人也。祖灵运,宋临川内史。父凤,元嘉中坐灵运事,同徙岭南,早卒。超宗元嘉末得还。与慧休道人来往,好学,有文辞,盛得名誉。新安王子鸾,孝武帝宠子,超宗以选补王国常侍。王母殷淑仪卒,超宗作诔奏之,帝大嗟赏。转新安王抚军行参军。[11]《大正新修大藏经》记载孝武帝为死去的殷淑妃延请高僧做法事超度:释昙宗,姓虢,秣陵人,出家止灵味寺。少而好学博通众典,唱说之功独步当世,辩口适时应变无尽,尝为孝武唱导行菩萨五法礼竟。......后殷淑仪薨,三七设会悉请宗......着《京师塔寺记》二卷。[12]殷淑妃去世后,陪葬龙山。
《宋书》载孝武与殷淑妃所生子刘子鸾:大明四年(460),年五岁。....母殷淑仪,宠倾后宫,子鸾爱冠诸子。凡为上所盼遇者,莫布入子鸾之府、国。六年(462)丁母忧。追进淑仪为贵妃,班亚皇后,谥曰宣。葬毕,诏子鸾摄职,以本官兼司徒,进号抚军、司徒,又加都督南徐州诸军事,八年,加中书令,领司徒。前废帝即位,解中书令,领司徒。......帝素疾子鸾有宠,既诛群公,乃遣使赐死,时年十岁。....太宗即位,诏曰:“.....可以建平王景素息延年为嗣”追改子鸾封为始平王,食邑千户,改葬秣陵县龙山。[13]刘子鸾因殷淑仪有宠于孝武而贵,复因废帝即位被杀,褫夺王爵,再因明帝即位平反,复王爵,续国祚。子鸾在明帝时也被葬在了龙山,此处秣陵县龙山即南京江宁县龙山。
琅琊王室早在东晋南渡后就是江南门阀大族,政治势力庞大。田余庆先生说:门阀政治是一种特定条件下出现的皇权政治的变态。它的存在是短暂的;它来自皇权政治,又逐步回归于皇权政治。他认为,严格意义上的门阀政治只存在于江左的东晋时期,前此的孙吴不是,后此的南朝不是;至于北方,并没有出现过门阀政治。[14]孝武帝采取措施加强皇权。殷贵妃的去世使孝武帝性情大变,遂整日沉迷酒色,不理朝政。孝武一度想废太子立始平王,导致帝后矛盾。殷淑妃去世后皇位继承人没有定下来,带来了深重的政治危机,以致政变的祸乱,致使废帝和王皇后死于政变。
《宋书》载王皇后及家族事:元嘉十二年,拜武陵王妃,生废帝、豫章王子尚...。世祖在蕃,后甚有宠。上入伐凶逆,后留寻阳,与太后同还京都,立为皇后。后父偃,字子游,晋丞相导玄孙,尚书嘏之子也。母晋孝武女潘阳公主,宋受禅,封永成君。偃尚高祖第二女吴兴长公主讳荣男,少历显官...。....世祖继位,以后父,授金紫光禄大夫,领义阳王师...,常侍、王师如故。偃谦虚恭谨,不以世事关怀。孝建二年卒,时年五十四。追赐开府仪同三司,本官如故,谥曰恭公。[15]王皇后的出身显贵,后父及诸子仕宦皆贵;刘劭弒父僭位后世祖刘骏帅军讨伐成功,王皇后得立正宫。孝建二年刘义宣在荆州反叛,六月,刘骏平定刘义宣之乱后不再信任和重用宗室亲王。王皇后之父王偃也恰巧就在孝建二年死去,虽未交待去世前后情形,想必也是不被信任,兵权被夺。由于刘骏改革,启用寒门为中枢要职,削夺贵族权利,触动了亲王、大贵族、大地主阶层的政治经济利益。这里没有交代王皇后家人去世后葬在哪里,是否也在龙山?
《资治通鉴》载孝武帝刘骏事:上为人,机警勇决,学问博洽,文章华敏;省读书奏,能七行俱下。又擅骑射,而奢欲无度。自晋室渡江以来,宫室草创,朝宴所临,东、西二堂而已。晋孝武末,始作清暑殿。宋兴,无所增改。上始大修宫室,土木被锦绣,嬖妾幸臣,赏赐倾府藏。坏高祖所居阴室,于其处起玉烛殿。...上末年尤贪财利,刺史、二千石罢还,必限使献奉,又以蒲戏取之,要令磬尽乃止。终日酣饮,少有醒时。常慿几昏睡,或外有奏事,即肃然整容,无复酒态。由是内外畏之,莫敢驰惰。[16]《资治通鉴》又载:(大明八年)夏五月壬寅:是日,太子即皇帝位,年十六,大赦。秋七月丙午,葬孝武皇帝于景宁陵景宁陵在丹杨秣陵县巌山。庙号世祖。庚戌,尊皇太后曰太皇太后,皇后曰皇太后。乙卯,罢南北二驰道,及孝建以来所改制度,还依元嘉。尚书蔡兴宗于都座慨然谓颜师伯曰:“先帝虽非盛德之主,要以道始终。三年无改,古典所贵。今殡宫始撤,山陵未远,而凡诸制度兴造,不论是非,一皆刊削,虽非禅代,亦不至尔。天下有识,当以此窥人。”师伯不从。[17]太宰义恭素畏戴法兴、蔡尚之等,虽受遗辅政,而引身避事,由是政归近习。法兴等专制朝权,威行远近,诏敕皆出其手;尚书事无大小,咸取决焉,义恭与颜师伯但守空名而已。[18]关于孝武昏睡等按照常理推则真伪参半。这段讲了废帝登基后废除孝武帝改革,孝武改革归于失败。王太后疾笃,使呼废帝。帝曰:“病人间多鬼,那可往!”太后怒,谓侍者,“取刀来,剖我腹,哪得生宁馨儿!”己丑,太后殂。乙卯,葬孝穆皇后于景宁陵。王后从孝武帝谥,当做武穆。[19]史书未明言王皇后因何疾笃?但是废帝对王太后的不孝之辞推断是政敌的政治抹黑,将大逆不道罪名强加到废帝头上,借此掩盖王皇后为明帝刘彧集团谋害的事实。《资治通鉴》中记载废帝继位后为巩固皇权,开杀戒,辱戮皇族王公大臣,最后死于权臣王公的政变。《南史》载:帝少好读书,颇识古事,粗有文才,自造孝武帝诔及杂篇章,往往有词采。刘子业虽年轻,但文学造诣非浅。[20]《南史》载:(景和)元年九月戊戌,还宫。帝自以为昔在东宫,不为孝武所爱,及即位,将掘景宁陵,太史言于帝不利而止。乃纵粪于陵,肆骂孝武帝为“齄奴”,又遣发殷贵妃墓,忿其未孝武所宠。初,贵嫔薨,武帝为造新安寺,乃遣坏之。辛丑,免南徐州刺史新安王子鸾为庶人,赐死。....时帝凶悖日甚....是夜,湘东王彧与左右阮佃夫、王道隆、李道儿密结帝左右寿寂之、姜产之等十一人,谋共废帝。....寿寂之怀刀直入,姜产之为副...追及之...乃崩于华光殿。于是葬帝于丹阳秣陵县南郊坛西。[21]这一段讲帝后立储矛盾,废帝政事混乱,引起臣下反叛被杀,内中另有隐情。废帝也葬在了南京江宁的南郊西坛,但不在龙山上。
事实上,宋武帝之子少帝义符,在文帝义隆当政时,在朝廷内外同样有属于自己的嫡系政治力量,其政治势力也在潜孳暗长。皇位传至孝武帝刘骏时,朝廷内外这种政治力量上的角力和力量对比始终存在,有人主张文帝刘彧这一支主政是意料中事,废帝刘子业在世祖去世时皇位不稳固,刘彧这一派政治力量在上下其手,明争暗斗。刘子业内心恐惧,其悖乱行为的政治背景根于此。对废帝,文献中多史家故意抹黑,恶意丑化的言辞,借此反衬出新君的英明,掩盖新君诸多罪恶事实。客观上,废帝对群下的控制十分不利,在巩固皇权的政治斗争中陷于被动,又不能更严厉的杀伐果断,遂被刘彧集团内外勾结,设计加以谋害。
《宋书》载,扬州,丹阳尹,秦鄣郡,武帝元封二年,为丹阳郡。晋武帝太康二年,分丹阳为宣城郡,而丹阳移治建邺。元帝太兴元年,改为尹。建康令,本秣陵县。汉献帝建安十六年置县,孙权改秣陵为建业。晋武帝平吴,还为秣陵。太康三年,分秣陵之水北为建业。慜帝即位,避帝讳,改为建康。秣陵令,其地本名金陵,秦始皇改。江寧令,晋武帝太康元年,分秣陵立临江县。二年,更名。[22]可见,汉武帝时的丹阳郡到了西晋初,治所已经移治建邺。汉代的秣陵县到了孙吴时改为建业。西晋灭吴,一度改回汉代的秣陵县旧称。到了西晋太康三年,则将秣陵县分割,其水北部分仍旧称为建业县,建业县之名遂得以保留。慜帝时避讳改建业县为建康县。这是历史上秣陵县最终定名为建康县之始。晋代太康时期,丹阳郡将治所移到了建业县,即建康县。《宋书》所谓的“丹阳郡秣陵县”实是汉代称谓,到了西晋时期,已经更名丹阳郡建康县。《宋书》提到太康元年分割秣陵县设立临江县,第二年更名为江宁县,到了第三年又分秣陵县水北部分为建业县,而秣陵县仍然保存。事实上,即将秣陵县最终划分为江宁令、建业县和秣陵县三部分。所谓江宁令就是江宁县。《舆地纪胜》卷一七建康府龙山:「九域志云,在江宁县南四十里.....」,江宁县就是此处的江宁令。
唐修《晋书》载,扬州,丹阳郡汉置,本秣陵,孙氏改为建业。武帝平吴,以为秣陵。太康三年,分秣陵北为建邺,改“邺”为“业”。江宁太康二年,分建邺置。.......秣陵。[23]《晋书》地理下指出漢代的丹阳郡晋代属扬州管辖,其中包括的建业县和江宁县都是从秣陵县中分化而来,秣陵县是“一县三分”而各有其一。《晋书》提到了西晋时期秣陵政区的变化,与《宋书》州郡志的说法一致。建业县或建业令及江宁县的设立时间,梁与唐代的说法一致。
前文提及《新定九域志(古迹)》与南宋学者《舆地纪胜》关于龙山的记载吻合的情况,这种说法基本上可以推断是南宋时期学者沿袭了北宋时期《九域志》的说法,困惑之处只在于这一记载不见于今天王校本《九域志》的正文,而是记录在《新定九域志》古迹门中,引发我们对于该书版本的质疑。我们需要考察隋唐直至五代宋初,江宁县和建业县的行政分化组合情况,才能更清晰的看到,到了《元丰九域志》文献记载之前,尤其是江宁县更名江宁府的情况,否则,到了南宋末年元初的胡三省注解《通鉴》时,胡注“九域志:江宁府有龙山”的提法便不易解。毕竟宋亡元兴,政权屡经更迭,政区也在时刻变化,想必去宋不远,胡三省修《通鉴》时还能看到《新定九域志》古迹等文献,故而能加以引用。
南齐承东晋,疆域地理一贯,变化不大。《南齐书》载:扬州京畿神阜。汉、魏刺史治寿春,吴置持节都州牧八人,不见扬州都督治所。太康元年,吴平,刺史周浚始镇江南。元帝为都督,渡江左,遂成帝畿,望实隆重。领郡如左,丹阳郡:建康、秣陵、丹阳、湖熟、江宁......[24]可见,南朝齐沿袭东晋、宋疆域,扬州所辖丹阳郡所管县中就有江宁县,建康县为丹阳郡的治所。前引《晋书》、《宋书》对于建康、江宁县等的设置情况比此处介绍更细致。
《梁书》、《陈书》等正史无地理志部分。《二十五史补编》载:扬州自汉以来皆为刺史治,梁领郡八。州治。《通鉴》元帝承圣元年九月,以王僧辩为扬州刺史。二年正月,僧辨发建康。陈霸先代镇扬州,九月,诏辨还镇建康。丹阳尹,《宋书·州郡志》:汉置,郡治宛陵。晋太康二年,移治建业。梁领县四。建康,本汉秣陵县地。《沈志》,孙权改秣陵为建业。晋武帝平吴,还为秣陵。太康三年,分秣陵之水北为建业。慜帝即位,避讳改名建康。梁武帝时,建都于此。《太平寰宇记》引《金陵记》云:梁都之时,城中二十八万户,西至石头城,东至倪塘,南至石子冈,北过蒋山。东西南北各四十里。自侯景反,元帝都江陵,冠盖人物多南徙。有台城....。洪氏结合史料,考查了建康城内的各处标志性建筑及山脉。我们考察《梁书》记载的江宁境内各山岗及其与龙山的联系:钟山亦名蒋山。《梁书·敬帝纪》太平元年六月甲辰,齐遣军至蒋山龙尾。……《梁书》疆域志没有关于龙山的记载。[25]
《二十五史补编》载:扬州自汉魏以来皆为刺史治。陈领郡三。州治,《陈书·程文季传》(见《陈书》卷十,程灵洗附程文季传,第173页),世祖嗣位,除宣惠始兴王府限内中直参军。是时王为扬州刺史,镇冶城,府中军事,悉以委之。丹阳尹,《宋志》,汉置郡治宛陵。晋太康二年,移治建业。《寰宇记》,晋元帝渡江,都建康,改丹阳郡为丹阳尹。陈郡领县七。建康,本汉秣陵县地。《三国·吴志》,建安十六年,孙权移都秣陵。明年改秣陵曰建业。《晋志》,武帝平吴,以为秣陵。太康三年分秣陵北为建业,又改业为邺。慜帝立,避讳改建邺为建康。《金陵记》云,梁都之时,城中二十八万户,自侯景反,元帝都江陵,冠盖人物多南徙。陈时,中外人物不过宋齐之半。梁武帝、简文帝及陈氏诸帝皆都焉。有宫城。江宁,本汉秣陵县地。《宋志》,晋太康元年,分秣陵立临江县。二年,更名江宁。有梅岭。考察建康下记载的山岗与龙山的联系:大壮观山,在上元县北十八里,与《舆地纪胜》龙山在江宁县南四十里的记载不符,与龙山无关。……白土冈,《金陵记》冈在城东三十里,南至淮即钟山南麓。石子冈,《寰宇记》,石子冈周围二十里,今城南高座寺后即石子冈之地。[26]白土冈在江宁城东三十里。《陈书》疆域志对各山岗的介绍相对《梁书》有关内容简略,都与龙山无关。由上引《二十五史补编》梁、陈时期可见,建康在梁陈时期都是首都首善之地。关于建康城的设置始末交代的很详细,与前述各文献内容基本一致,但没有关于龙山的记载。
《隋书》,丹阳郡,自东晋以后置郡曰扬州。平陈,诏并平荡耕垦,更于石头城置蒋州。统县三。江宁梁置丹阳郡及南丹阳郡,陈省南丹阳郡。平陈,又废丹阳郡,并以秣陵、建康、同夏三县入焉。大业初置丹阳郡。有蒋山。当涂、溧水。[27]《隋书·地理志》记载了隋灭南朝陈国后,扬州江宁县政区新的变化,新的江宁县下辖秣陵县、建康县和同夏县,到了隋炀帝大业初年,把新的江宁县再次升格设立丹阳郡。可见,隋代的江宁县包含了建康县等三县之地,后又升丹阳郡。《旧唐书·地理志》,润州上,隋江都郡之延陵县.....干元元年,于江宁置升州,上元二年,复为上元县,还润州。[28]《新唐书·地理志》,升州江宁郡,至德二年以润州之江宁县置,上元二年废。光启三年复以上元...四县置,......八年,复为扬州,又以延陵、勾容隶之,省安业入归化,更归化曰金陵。九年,州废,更名金陵曰白下。贞观九年,更白下曰江宁。肃宗上元二年又更名。[29]这是《新唐书》关于江宁县从唐初到安史之乱和肃宗时政区的变化情况。由隋志新旧两唐书地志记载可以看到上元、金陵、秣陵、建业、建康、归化在不同历史时期名称虽异,所指相同。隋唐时,金陵与江宁之间相互替代称呼较为频繁。隋志新旧两唐书地志都未提及龙山。
《元和郡县志》载:上元县,本金陵地,.....。晋之渡江,乃五百二十六年,遂定都焉。隋开皇九年平陈,于石头城置蒋州,以江宁县属焉。武德三年,杜伏威归化,改江宁为归化县。九年,改为白下县,属润州。至德二年,于县置江宁郡,干元元年改为升州,兼置浙西节度使。上元二年废升州,仍改江宁为上元县。[30]《元和志》所记与前述隋唐地志相仿。同上江宁县载:孝武帝骏景宁陵,在县西南四十里岩山。[31]《元和志》指明了宋孝武帝的景宁陵位于江宁县西南岩山这一地理方位和远近距离。
《通典》载:大唐初,润州或曰丹阳郡,辖六县:丹阳江宁...。江宁本名金陵,秦始皇改为秣陵。汉丹阳县在此。建安十六年,吴改为建业。晋武平吴,还为秣陵,又分秣陵立临江县。二年,改临江为江宁。三年,分秣陵水北立建業,避慜帝讳,改为建康。后又分置同夏县。隋平陈,并三县,置江宁县,又置蒋州,后废。大唐初,复为蒋州,寻废为江宁县。有钟山、蒋山、石头城、玄武湖...。[32]《通典》的记载也与前述文献雷同。《通典》未提到龙山或岩山。《旧五代史》、《新五代史》没有关于金陵江宁乃至龙山的记载。
《太平寰宇记》载金陵江宁一地历史上的政区沿革变迁:升州今理江宁、上元二县。古扬州之域。战国时.....楚灭越,初置金陵邑。秦改金陵为秣陵。以下记载与前述正史地理郡县记载基本相同,但更详细。[33]《寰宇记》记载了岩山的情况:岩山,在县南四十五里,其山岩险,名为岩山。宋孝武改曰龙山。葬宣贵妃殷氏于龙山,孝武亦葬此。[34]北宋乐史《寰宇记》记载了江宁县岩山的地理位置以及孝武帝改山名、孝武帝和殷贵妃葬在龙山的史实。《方舆胜览》载:鸡笼山,《寰宇记》“在城西北九里。宋雷次宗居此。元嘉中改曰龙山,以黑龙尝现于真武湖,此山临湖上。[35]其次,我们比较南宋学者《舆地纪胜》与北宋《太平寰宇记》、《元丰九域志(古迹)》的记载发现,三者在龙山改名这件事的记载上有出入。乐史认为是“宋孝武帝刘骏”改的名称,《舆地纪胜》和《九域志(古迹)》却认为是“宋武帝刘裕”。宋武帝是南朝宋的开国君主刘裕,孝武帝刘骏是刘裕之孙,完全不是一回事。那么,究竟是宋武帝还是宋孝武帝改岩山为龙山呢?本文认为宋武帝刘裕所改的山是鸡笼山,将鸡笼山改为龙山。《舆地纪胜》记载的“宋武帝”改岩山为龙山,此处“宋武帝”应该是“宋孝武帝”,遗漏了“孝”字。岩山是宋孝武帝刘骏所改。再次,就是龙山到江宁县的距离问题。《寰宇记》认为是“县南四十五里”,《舆地纪胜》认为是“县南四十里”,究竟哪一种文献的记载更精准呢?正史和地理总志都找不到判断以上问题的历史依据,需要结合地方志作进一步考证。
《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南京条记载有方志24种,其中府志12部,县志12部:府志:〔景定〕建康志50卷,[宋]马光祖修,周应合纂(1261抄本,1801年刻本)等。县志:〔万历〕上元县志12卷,(明)程三省(1593年)修,李登等纂(1597年刻本)等。〔正德〕江宁县志10卷,(明)王诰修,刘雨纂(1519年刻本,1938、1948年铅印本)等。[36]
本文考察编纂年代较早的《景定建康志》和《正德江宁县志》。据《宋元方志丛刊》记载,宋马光祖纂修的《景定建康志》版本情况:《景定建康志》五十卷,[宋]马光祖修,周应合纂,宋景定二年(1261)修,清嘉庆六年(1801)金陵孙忠慜祠刻本。[37]据《景定建康志》龙山的记载:龙山,在城西南九十五里,周回二十四里,高一百一十二丈,入太平州当涂县,北有水。以其山似龙形,因以为名。[38]金陵府志对龙山的介绍指明了龙山与江宁县城的相对空间方位、距离、山体的周长和高度,以及称为龙山的缘由。这里我们注意到方位上与《舆地纪胜》《寰宇记》的记载有很大出入。我们按照宋代的尺距进行换算,南宋时期一尺是31.2厘米,一里是1800尺,即561.6米,九十五里是53352米,即53.352公里。山体周长是24里,即13478.4米,即13.4784公里。山的高度是112丈,即349.44米。这个距离远超出我们计算的上引宋代地理志书的“南四十里,南四十五里”的距离。地理方位显然是府志的记载正确。同样是宋代的地理志书,记载出入如此之大,令人不解。在建康府志江宁县地图上看不到龙山的标志。《景定建康志》载:江宁县,附廓,东西八十五里,南北九十八里。西南到太平州当涂县界一百六里,以章公塘为界,自界首至当涂县一十七里。[39]《景定建康志》皇朝建康府境之图,可以看到江宁县界与太平州界的地理方位关系。[40]因为龙山山体已经进入当涂县界,因此,龙山实际是江宁县与当涂县两县的界山。如果从江宁县城中心算起,则需扣除南北方向的一半即五十里左右,可以由城中抵达县的西南边界,这样从江宁县城西南角算起,到龙山基本就是四十五里。因此,我们可以初步确定,龙山在江宁县城西南四十或四十五里的数据都比较接近实际情况。《太平寰宇记》与《舆地纪胜》等的记载都不误,基本属实。
《正德江宁县志》叙县境云:按金陵志,古建康附城惟设一县,名称数易,为江宁,为白下,为归化,最后为上元。....则府城即县城,县不复置城。《金陵志》云,今县则南唐分上元十九乡所置者。比时上元东西九十五里,南北八十五里。江宁东西少十里,南北又多上元十三里。然则二县之境无伯仲。宋元皆因唐旧。这一段记载了江宁县名称的历史变迁,县境的情况与《景定建康志》所述江宁县的县境完全一致。同上,疆域载:“如四望山、古靖安道、石头庐、龙山西麓皆属焉。...南至太平界,皆因宋元故境。宋元县界东西八十五里,南北九十八里。东至上元县界。”同上,山阜载:龙山,在县西南九十五里,高一百十二丈,周二十四里。以其山似龙形,故名。[41]这里就记载了龙山的情况,其与江宁县的相对地理方位,空间距离,得名原由,山的海拔高度,山围的大小都做了介绍,与府志《景定建康志》的记载尤其是山的体量数据几乎完全一致,地理方位与空间距离也一致。
《中国文物地图集》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的文物图上没有标注西善桥宫山北麓“竹林七贤”墓。龙山附近标注了三座墓葬:娘娘山晋墓、官家山六朝墓(东吴末东晋初墓葬,南京博物馆朱兰霞先生撰《江苏江宁官家山六朝早期墓》,《文物》1986年12月。)、陶村土墩墓(47-B27陶吴镇龙山陶村北约100米,地处低丘岗沿,周代墓葬遗址,地面采集到原始瓷等)。[42]这三处龙山附近遗址都与本文讨论主题无关。
今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上庄园(红星大道西)有一处名为龙山的山峰。唐代的大尺一尺是30厘米,一里为1800尺。梳理以上宋代历史文献我们得知龙山在江宁县南四十里或四十五里。那么按照唐尺计算就是21600米到24300米,即21.6到24.3公里。从今天的卫星地图进行大致的测量,南京市江宁区政府驻地到龙山的直线距离是20公里多一些,与历史文献记载基本相符。此一龙山当即南朝宋孝武帝所改岩山为龙山的龙山,也即刘骏族葬之地。
罗宗真指出,南京市博物院和文管会于1960年5月16日至6月3日在南京西善桥宫山北麓发掘一座南朝古墓,南620米即为太(泰)岗寺新石器时代遗址。此墓在宫山北麓下,这一带均为丘陵,宫山只是其中一座小土山,海拔27.2米,由粘性黄土构成。该墓系依山坡自然倾斜挖成土坑,在生土坑壁内砌墓室,上面填土而成。墓门、墓道经过破坏,墓室完整,可看出墓的全部建筑结构。墓为长方形砖室券顶墓,方向70度,总厂8.95米,宽3.1米,高3.3米。从墓室的结构看是单室砖砌券顶墓是南朝早、中期的形式。[43]该墓墓室壁画上出现了“叉手”,也叫人字栱,作者援引刘致平《中国建筑类型与结构》指出,“汉阙及崖墓、明器、画像石有许多斗栱的实例。...在汉末的墓内壁画上常可见到用许多人字栱的做法,位置是在檐下而又很多、很密。图315人字叉手及昂械等斜枋。人字栱的使用是汉末至唐这一段时期的事情,以后便销声匿迹了。”[44]作者通过出土文物形制的比较,判定该墓的历史上限为东晋。文章认为“本墓出土文物中最有价值的,当为墓室两侧的两幅砖刻壁画,这在南京六朝墓中尚属初次发现。”[45]该壁画拓本见于罗宗真先生着《六朝考古》图版8“竹林七贤”砖印壁画”。[46]壁画所绘为阮籍、山涛等“竹林七贤”和先秦高士荣启期,通过考察“竹林七贤”的生卒年,根据学界已知的嵇康等四人生年最早是山涛(205-283,卒年最晚是王戎(234-305)的情况进行推断,认为“向秀、刘伶、阮咸三人,看来(与阮籍等四人的生卒年)也不会相去太远,其卒年最迟当在东晋初。七贤的生卒年代,为我们提供了壁画和这座墓的上限年代,即最早不过东晋中期。再者,从壁画中的字体看来,是由八分书进到楷书,也正当东晋到刘宋的时期。”作者认为“竹林七贤”为墓主人所崇拜,则墓主人当也是士大夫阶层人物;该墓壁画画风与东晋中期以后的画家顾恺之(343-405)画风相似,且据张彦远《历代名画记》记载顾恺之曾经画过阮咸与荣启期像,推测此画可能出自顾恺之之手,或是与顾恺之同时代或年代接近的画家所为。最后,推定墓室壁画的年代是晋--宋之间的作品。文章认为:“无论就墓葬结构、遗物形制、壁画作风来看,都说明这座墓葬应该是南朝晋宋时期的。”[47]该文的撰写得到大师胡小石先生的指点。
罗宗真《六朝考古》一书对于六朝尤其是南京考古遗迹发现的总量和分布范围、特点、青瓷窑址的分布和工艺技术发展水平、陵墓与石刻、墓砖文字纹饰和砖印壁画以及墓葬遗物等各方面进行考察考证,其中涉及六骏墓的有多处。本书指出“江苏境内重要六朝考古发现和纪念表”中列有刘骏墓,“重要纪年遗物和传世文物”一栏注明:砖印“竹林七贤”壁画,把出土文物作为墓葬断代的重要历史依据。[48]六朝陵墓主要分布在南京附近,陵墓一章第一节表4-1六朝帝后表,书中列举了孝武帝刘骏景宁陵和孝武殷淑妃墓,把“竹林七贤”壁画和人形栱作为墓葬断代依据,这里也可以看出南朝陵墓采取族葬这种方式的历史特点。[49]书中表4-2列出建国以后,经考古调查,地面有遗迹可考的遗迹33处,其中与文献相符或基本相符的有24处,其中南京11处,江宁9处,第69页序号9记载:西善桥宫山1处,可能为南朝宋孝武帝刘骏景宁陵,与文献记载地理位置符合,无地面遗迹,由南京市博物院、南京市文管会发掘。这是从陵墓出土时所在的地理位置与历史文献记载基本符合角度对墓主人和墓葬年代作出的判断。[50]该书墓葬结构一节中指出,“六朝墓葬据目前已知考古资料,均为砖室结构,砌造墓室之前必先开凿墓坑,这种劈山营造规模宏大的墓坑反应当时陵墓的规模。”[51]该书指出六朝陵墓与一般六朝墓葬不同,陵墓均为大型的单室墓,没有前后室或侧室。顶虽亦为券顶或穹窿顶,但其规模较一般墓为大。表4-3举南京附近发掘的豪门世族墓与之相比较,西善桥七贤壁画墓赫然在列,被定性为皇帝陵墓而非豪门大族墓。南朝陵墓多为横穴墓,而不是竖穴,这是由南方的气候和土壤偏湿等地理环境因素导致的。[52]该书指出,六朝陵墓较汉唐帝王陵墓的规模仍有逊色,是由于当时封建割据偏安一隅,经济能力有限所造成的。这就告诉我们我们不能用汉唐那样大一统强盛王朝的陵墓去跟偏霸一方的割据王国墓葬规模去比较,二者没有可比性,我们要实事求客观认识,对南朝皇陵墓规模等的考察要避免先入为主的主观错误认识,排除汉唐大墓的干扰和影响。[53]该书指出,由于六朝陵墓大多遭到破坏,所以遗物不完整,无法找出遗物、葬具,随葬的全部内容和它们的规律,对墓葬断代带来了不利影响。[54]
除了罗宗真先生的考古报告以外,有关学者也根据自己的研究提出了各自的学术观点,此处一并考察,以便对墓主人的身份有更深入的认识。
韦正先生的文章提供或补充完善了几种关于墓葬断代的新的依据。作者根据多处同一时期墓葬形制的比较以及直线和斜形人字形叉手出現时代的早晚(参考了宿白先生《日本奈良法隆寺参观记》提出的南北朝晚期叉手递嬗演变规律)推断西善桥墓类型梁时最多,齐已出现,所以该墓时代上限可断到刘宋后期;根据出土青瓷盘口壶形制特征类型,推断西善桥墓盘口壶流行于南朝,上限至少可以到刘宋;西善桥墓耳杯形制流行于南朝,上限可到刘宋;西善桥带流带把罐形制流行于南朝,上限可到刘宋,甚至更早一些;陶俑时限遵从女俑为刘宋中期至齐。该文结论认为该墓葬的年代为刘宋中后期,墓主为王侯。[55]
我疑惑,就是文献记载刘骏及王皇后、殷淑妃、刘子鸾一家是族葬在龙山,刘子业虽葬江宁,但不在龙山上。目前有关机构考证“竹林七贤”墓是在宫山北麓,估计是刘骏与王皇后合葬的景宁陵,但没有下最后的结论。但是宫山的实际规模等情况与地方志中明确记载的龙山的规模不可同日而语,龙山的体量远大于宫山。虽考证此墓的建造规模是六朝时期的王侯之墓,但是却很难就说是景宁陵。按照正史及地方志的相关记载,龙山与宫山的位置似乎不在一处。由今南京市清代两江总督府旧址向南三公里为中华门,中华门外是西善桥,“竹林七贤”墓即位于西善桥地区,西善桥位于今南京市雨花台区,太(泰)岗寺遗址位于该墓南面620米处,都位于秦淮河以北地区,西善桥是横跨秦淮河,沟通南北交通的桥梁。中华门的位置据《中国历史文化名城词典》南京市古迹园林一节“中华门”词条的记载,中华门位于南京城南,因正对聚宝山(即今雨花台),故而明清两代叫聚宝门,1931年改为中华门。[56]龙山山峰则位于江宁区上庄园红星大道旁,远在秦淮河以南地区,龙山西南接壤的就是安徽省马鞍山市当涂县。由上文可知,龙山就是当涂县与江宁县两县界山的一部分。通过前面正史以及宋代《景定建康志》和明代《正德江宁县志》的记载,可以清楚看到,龙山就在江宁县的西南,距离县城95里,海拔112丈,周回24里,山体比较雄伟,很有气势,因此南朝宋孝武帝族葬墓依龙山建陵是合情合理的。因此,按照各类文献的记载以及今日遥感地图进行综合判断,此处的龙山才应该是南朝宋孝武帝刘骏及其家人族葬之所。所以,对于宫山北麓“竹林七贤”墓葬的男女合葬墓的墓主人是否为南朝宋孝武帝刘骏的推测似要谨慎对待。本文不揣谫陋冒昧,提出愚者薄见,以就教于方家,请方家不吝指正。
参考文献:
[1][7][16][17][18][19]﹝宋﹞司马光.《资治通鉴》[M].卷129,第4062页,北京:中华书局.1956.6。[7]同1,卷129,宋纪十一,第4060页。[16]同1,卷129,宋纪十一,孝武帝大明八年,第4065-4067页。[17]同1,卷129,宋纪十一,孝武帝大明八年,第4067-4068页。[181同1,卷129,宋纪11,大明八年,第4069页。[19]同1,卷129,宋纪11,大明八年,第4069-4070页。
[2][3]﹝宋﹞王存撰,王文楚、魏嵩山点校.《元丰九域志》[M].北京:中华书局.1984.12,第239-240页。[3]同2,同卷,第633--634页至634页。
[4]﹝宋﹞王象之.《舆地纪胜》[M].卷一七,建康府,北京:中华书局,第748页。
[5][6][9][13][15][22]﹝梁﹞沈约《宋书》,本纪第六,卷六孝武帝,第135页。[6]同5,卷四十一,后妃,第1289页。[9]同5,卷四十一,后妃,第1269页。[13]同5,卷八十,列传四十,孝武十四王,第2063-2066页。[15]同5,卷四十一,第1289页,后妃,孝武文穆王皇后。[22]同5,卷三十五·州郡一,第1027-1030页。
[8]﹝宋﹞马光祖修,周应合纂,《建康实录》[M],卷十三,宋世祖孝武皇帝骏,机械工业出版社,2009,第484页。
[10][20][21]唐李延寿:《南史》[M],卷十一,列传第一,第323-324页。
北京:中华书局.1976.6。20同10,卷二,宋本纪中,第二,第72页。21同10,卷二,宋本纪中第二,第69页。
[11][24]﹝梁﹞萧子显撰,《南齐书》[M],卷36,列传第17,北京:中华书局.1972.1,第635页。24同11,卷14,第245页,州郡上,扬州。
[12]《大正新修大藏经》第五十册,史传部二,子,释家,二○五九,高僧传卷十三,唱导第十,释昙宗四(第416页-1)。
[14]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8,自序。
[23]﹝唐﹞房玄龄:《晋书》[M],卷十五,北京:中华书局.1974.11,第458-460页。
[25]二十五史补编委员会,《二十五史补编》[M],第四册,洪齮孙撰《补梁疆域志》[M],上海:上海开明书店,卷一,第4361-4431页。
[26]二十五史补编委员会,《二十五史补编》[M],第四册,藏励龢撰《补陈疆域志》,卷第一,第4443-4475页。
[27]﹝唐﹞魏征:《隋书》[M],卷31,北京:中华书局.1973.8,第876页。
[28]﹝后晋﹞刘煦等:《旧唐书》[M],卷40,地理三江南东道,北京:中华书局.1975.5,第1583-1584页。
[29]﹝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M],卷41,北京:中华书局.1975.2,第1056-1057页。
[30][31]﹝唐﹞唐李吉甫着,贺次君点校:《元和郡县图志》[M],卷第二十五,江南道一,润州所管上元县,北京:中华书局.1983.6,第594页。31同30,第597页。北京:中华书局.1983.6,
[32]﹝唐﹞杜佑:《通典》[M],卷182,州郡十二,北京:中华书局.1988,第4824-4825页。
[33][34]﹝宋﹞乐史撰,《太平寰宇记》,王文楚等点校[M],卷之九十,江南东道二,升州江宁县,北京:中华书局.2007.11,第1775页。34同33,升州江宁县,第1777页。
[35]〔宋〕祝穆撰,祝洙增订,施和金点校,《方舆胜览》,北京:中华书局,2003,卷十四,江东路,建康府,江宁县,第237页。
[36]中国科学院北京天文台主编.《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M].江苏省南京市有关方志情况,北京:中华书局.1985,该书第310-313頁。
[37][38][39][40]中华书局编辑部,《景定建康志》[M],见于宋元方志丛刊(第1311-2180页),北京:中华书局,1989,影印说明,江苏省,第二页。《景定建康志》,卷之十七,山川志序一,山阜,第412页。39同37,江宁县,第356页。40同37,江宁县,第68页。
[41]﹝明﹞王诰修,刘雨纂,《正德江宁县志》,《金陵全书》丛书之一种,南京:南京出版社,2012.04,该书第6页,22页,25页。
[42]国家文物局,《中国文物地图集》,江苏分册[M],南京文物分布情况,北京:中国地图出版社,第156-157页。
[43]罗宗真,《南京西善桥南朝墓及其砖刻壁画》[J],《文物》1960年第8、9期合刊,第37-42页。
[44][45]刘致平,《中国建筑类型及结构》(第三版)[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0,45同43,见原文。
[46][47][48][49][50][51][52][53][54]罗宗真,《六朝考古》[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12月版,46,47见原文。48同46,第265页。49同46,第58页。50同46,第64页。51同46,第85页。52同46,第87页。53同46,第88页。54同46,第90、91页。
[55]韦正,《南京西善桥宫山“竹林七贤”壁画墓的时代》,[J].《文物》,2005,(04),第99-111+25页。
[56]中国历史文化名城编委会,《中国历史文化名城词典》南京二古迹园林[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5.12,第179页。
作者简介:郭良(1973.6~),男,祖籍潍坊,现供职于喀什大学图文研究中心,研究生毕业,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化、地方文献及图书情报学研究。参编著作一部,公开发表专业学术论文二十多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