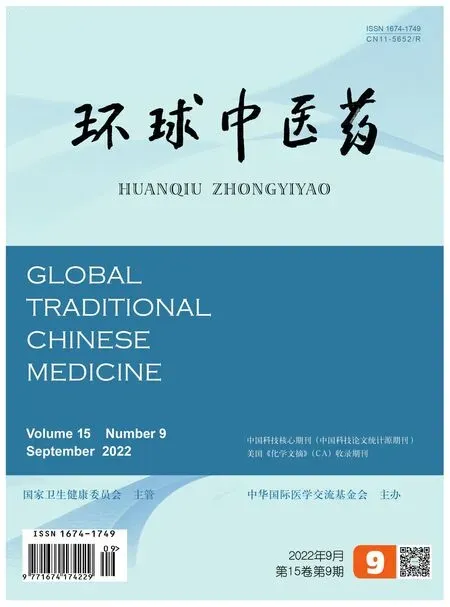基于Toll样受体4/核因子-κB信号通路中医药干预溃疡性结肠炎作用机制的研究进展
2022-01-01贾福运高望
贾福运 高望
随着近年来在溃疡性结肠炎(ulcerative colitis,UC)领域的研究不断深入,诱发UC的分子信号通路已被熟知,其中以Toll样受体4(Toll-like receptor 4,TLR4)及核因子-κB(nuclear factor-kappa B,NF-κB)密切相关[1],TLR4可通过与脂多糖等融合从而诱发炎症反应来调节机体自身免疫[2],由TLR4介导的髓样分化因子88(myeloid differentiation factor88,MyD88)依赖性途径能诱导NF-κB抑制蛋白激酶IKK的磷酸化,最终激活NF-κB信号通路[3]。NF-κB作为一种核转录因子具有高度保守性,其广泛存在于人体各类组织中,它能特异性结合κB在多种细胞基因启动子和增强子中的转录序列位,且参与机体内免疫、炎症反应、细胞增长、病毒感染等[4]。当机体处于非激活状态下,NF-κB以非活性形式存在于胞浆中,即NF-κB与其抑制蛋白(inhibitor of NF-κB,I-κB)家族形成复合物,NF-κB只有在离开I-κB进入细胞核调控转录时才被激活,因此活化后的TLR4/NF-κB信号通路能调节肠粘膜损伤治疗UC。本文基于TLR4/NF-κB信号通路,寻求中医药在调节炎症因子、调控巨噬细胞移动抑制因子(macrophage migration inhibitory factor,MIF)、抗氧化、下调环氧化酶-2(cyclooxygenase-2,COX-2)及修复肠黏膜屏障治疗UC作用机制方面进行综述,旨在为临床提供理论参考。
1 中医药通过干预TLR4/NF-κB信号通路调节炎症因子
1.1 调节炎症因子的平衡
炎症反应在UC病理机制中处于核心位置,其中细胞因子能在炎症介质中调节结肠黏膜的病理性损伤[5]。调节炎症因子之间的平衡[6]及T细胞活化[7]在UC的发生进展中有重要作用。当促炎因子过度表达时能加速介导UC的进展。肿瘤坏死因子α(tumor necrosis factor α,TNF-α)是由活化的对巨噬细胞所产生,能促使肠道黏膜在局部的炎性改变,而且能促进白细胞介素(interleukin,IL)-1及IL-6的分泌,共同作用于细胞因子的炎症反应[8]。IL-8是被细胞因子TNF-α和IL-6所促进生成,主要是通过对嗜碱性粒细胞和对T细胞的趋化作用以及加速中性粒细胞的粘附与活化[9],并且与UC的疾病活动指数水平呈正相关性[10]。IL-17是由辅助性T细胞17分泌,既能诱导内皮和上皮细胞促使IL-6和IL-8等炎症因子的产生,同时还能修复肠道黏膜的通透性[11]。
抑炎症因子IL-2是由Th1所分泌出的一种抑炎因子,能调节NK细胞活化且增加巨噬细胞的杀伤作用,有研究显示与健康人相比,UC患者体重的血清IL-2水平与疾病的进展呈负相关[12]。主要由Th2及单核巨噬细胞所产生的IL-10能够调控细胞的增殖与分化,参与免疫反应过程[13],且研究发现,肠上皮细胞应激反应能在体内缺少IL-10的小鼠中所产生,从而进展为炎症性肠病[14]。而IL-13作为一种双重调节的细胞因子,既能损伤上皮细胞屏障功能[15],又可增加肠黏膜固有层细胞分泌[16]。
研究发现[17],在五味子甲素诱导下的大鼠尿液中乳果糖、L/M比值明显降低,尿液中甘露醇水平提升,说明其可减少大鼠结肠黏膜的通透性,且上调血清转化生长因子(transforming growth factor,TGF)-β1和IL-10表达,下调血清IL-6和TNF-α水平,表明五味子甲素可通过干预TLR4/NF-κB信号通路干预UC大鼠模型,调节促炎和抑炎因子之间的平衡。马克龙等[18]研究发现,肉桂醛能明显改善白念珠菌诱导下UC小鼠结肠黏膜中的状态,减少血清及结肠组织中细胞因子TNF-α、IL-1β、IL-6和IL-8的含量,促进抗炎因子IL-10的表达,同时下调结肠组织树突状细胞相关性C型植物血凝素1、TLR2、TLR4和NF-κB的蛋白表达水平,表明肉桂醛可能是通过抑制白念珠菌的增殖,调节TLR4/NF-κB信号传导途径以调节UC中的炎症因子。田先翔等[19]研究发现,板党多糖能下调4,6-三硝基苯磺酸(trinitro-benzene-sulfonic acid,TNBS)诱导下UC大鼠结肠粘膜中TLR4、IL-6、NF-κB、TNF-α mRNA的表达,上调IL-10的mRNA的表达,表明板党治疗UC可能是通过抑制TLR4/NF-κB信号传导途径,调节抗促炎症因子表达水平从而改善UC的进展。蒋晓梅等[20]发现通过黄连总生物碱干预后的肠粘膜组织中IL-6、TNF-α水平明显下调,IL-10水平升高,磷酸化丝裂原活化蛋白激酶p38抗体和NF-κB蛋白表达水平及NF-κB蛋白表达阳性率显著降低,表明黄连总生物碱能缓解肠粘膜炎症损伤,抑制NF-κB通路,从而调节UC中的炎症因子。崔娜娟等[21]研究发现,柴芍六君汤能通过抑制TLR4/MyD88/NF-κB信号通路过度激活,下调促炎因子IL-17水平,上调抗炎因子IL-4和IL-10蛋白表达,从而治疗UC,减轻肠道炎症反应。研究采用TNBS法制备UC大鼠模型,发现黄芩苷能明显改善结肠大体形态,且与抑制炎症反应的分泌呈剂量相关性,高剂量的黄芩苷可下调结肠组织中TNF-α、IL-8和IL-1的表达水平,降低NF-κB的蛋白水平,上调I-κBα表达水平[22]。Feng等人[23]采用不同的造模及检测方法发现,与美沙拉嗪对照组相比,用黄芩苷灌胃后UC小鼠结肠黏膜中NF-κB p65和TLR4的表达降低,且黄芩苷能够明显调节结肠组织中促炎(TNF-α、IL-6和IL-13)和抗炎(IL-10)细胞因子的mRNA表达,而美沙拉嗪只能调节促炎(TNF-α、IL-6和IL-13)的mRNA表达。以上研究可表明黄芩苷能有效干预NF-κB活化以达到调节炎症因子的作用。
1.2 干预促炎症因子
徐敏等[24]选用50只雌雄各半的Wistar大鼠,以病证相结合的理论,用辛辣高脂的食物进行喂养后复制湿热内蕴型UC大鼠模型后发现,与柳氮磺吡啶组相比,经高剂量的芍药汤干预后,可显著下调大鼠肠黏膜中的TLR4、NF-κB p65的表达水平,降低促炎因子IL-6的基因表达,从而干预TLR4/NF-κB信号通路过度激活以修复结肠黏膜,达到治疗UC的目的。同样祖健等人[25]选用湿热内蕴型大鼠造模后发现,芍药汤能明显降低促炎因子IL-8的含量,加速肠粘膜的修复。本文认为这可能与实验的检测方法不同及培养大鼠模型的周期不同有关。闫曙光等[26]研究发现,黄连素与6-姜烯酚联合应用后,二者能显著地干预肠道上皮组织TLR4/NF-κB信号通路的异常活化,通过抑制TLR4受体表达从而抑制NF-κB蛋白磷酸化,降低下游炎症因子TNF-α、IL-1β的含量,最终达到抑制炎症反应的效果。陈天杰等[27]研究选取临床中慢性复发型UC患者106例发现,参苓白术散对慢性复发型溃疡性结肠炎效果显著,其作用机制可能通过抑制NF-κB活化,促进肠黏膜损伤修复,降低相关炎症因子IL-1β、IL-6、IL-8、TNF-α及低氧诱导因子(hypoxia inducible factor,HIF)-α从而降低复发率治疗UC。李姿慧等[28]研究选用参苓白术散对脾虚湿困型UC小鼠进行研究发现,参苓白术散通过抑制NF-κB信号通路上游磷酸化,进而阻止NF-κB核移位,下调大鼠血清中TNF-α、IL-6及IL-1β水平,从而抑制炎症因子,治疗UC。以上三种实验采用不同的药物只对促炎因子TNF-α、IL-6、IL-8及IL-1β进行干预,或许可以考虑当前治疗UC应着重以调节这类促炎症因子为主。
细胞因子的免疫调节在溃疡性结肠炎的治疗中占据重要地位,本文指出调节特定炎症因子来调节蛋白表达水平治疗UC。而最近研究证实,IL-17[29]、IL-23[30]亦与UC关系密切,那么今后是否可从TLR4/NF-κB信号通络为切入点,干预IL-17及IL-23从而治疗UC。
2 中医药通过干预TLR4/NF-κB信号通路干预MIF
MIF是由巨噬细胞及T细胞所分泌的细胞因子,且是含有不同生物特性的前炎症因子。作为一类促炎性细胞因子,MIF在应激状态下能将炎症性疾病中的中性粒细胞及巨噬细胞向炎症灶聚集[31],抑制巨噬细胞游走。易文等[32]研究发现,采用TNBS复制UC小鼠模型后,通过四逆散可减轻炎症因子对小鼠结肠内膜的损伤,抑制NF-κB活化,下调IL-1β、IL-6和TNF-α的表达水平,上调抗炎因子IL-4、IL-10的表达,从而干预巨噬细胞移动抑制因子MIF及对应的受体CD74基因表达。孙娟[33]研究发现,一定浓度的参苓白术散能显著改善UC小鼠的结肠组织学病变,抑制促炎因子TNF-α和巨噬细胞移动抑制因子MIF的释放,上调抗炎因子IL-10与表皮生长因子的表达,下调TLR4及NF-κB表达,表明参苓白术散可通过调节TLR4/NF-κB信号通路及纠正细胞因子平衡治疗UC。钟宇等[34]将56只大鼠随机分成正常组、模型组、美沙拉嗪组及不同剂量的芍药汤组后,采用紫外光光度法、酶联免疫吸附法、免疫组化及蛋白免疫印迹法检测结肠组织中相关蛋白的含量发现,芍药汤组能呈剂量依赖性地调节TLR4/NF-κB信号通路,降低血清和结肠组织中髓过氧化物酶(myeloperoxidase,MPO)、P-选择素、MIF及血小板血栓烷B2的含量,下调TLR4和NF-κB蛋白表达,进而抑制炎症反应,加快结肠黏膜修复治疗UC。并且大量研究显示,在UC疾病的发生进展中,MIF作为主要细胞因子发挥了重要作用,其多种炎症因子能被免疫细胞及巨噬细胞所活化,进而发挥在免疫与炎症类疾病中的作用[35]。
当前研究领域多在研究单一CD74受体作用于TLR4/NF-κB信号通路,缺乏对抑制MIF中CD44[36]、趋化因子受体4[37]和趋化因子受体7[38]受体的相关研究。并且联合多受体分子共同发挥协同作用应是未来研究领域的重点,例如MIF与CD44/CD74复合体共同结合后,能促使丝氨酸磷酸化,从而触发相关信号通路[39]。
3 中医药通过干预TLR4/NF-κB信号通路调节氧化
机体在氧化过程中能产生多类高化学活性氧,如丙二醛(malondialdehyde,MDA)、超氧化物歧化酶(superoxide dismutase, SOD)、MPO等,而调节氧化—抗氧化失衡则是治疗肠道黏膜损伤的关键之一[40]。LI等[41]研究发现,葛根芩连汤能降低TLR4的表达和NF-κB的活化,减轻UC小鼠结肠氧化应激,降低由中性粒细胞所分泌出活性酶MPO[42]及由自由基所引起的脂质过氧化反应的结晶MDA[43]表达水平,提高谷胱甘肽含量,同时下调结肠TNF-α、IL-6、IL-1β和IL-4等炎症因子的表达,从而治疗UC。刘雪枫等[44]选取50只雄性大鼠随机分成五组,采用生化法和酶联免疫吸附法检测结肠组织中的蛋白水平,研究发现党参多糖能明显调节结肠黏膜形态,抑制NF-κB蛋白表达水平,下调结肠黏膜组织中MDA、IL-6、TNF-α水平,上调IL-10 mRNA表达,表明党参多糖能够调节抗脂质氧化,干预NF-κB信号通路从而治疗UC。宋艳等[45]研究发现,黄芪多糖能显著干预小鼠体内炎症因子的表达,通过抑制NF-κB蛋白水平,下调血清TNF-α、IL-6水平,且抑制结肠黏膜组织中MPO活性、MDA、P-选择素及血小板血栓烷B2水平,激活血清TGF-β1水平及结肠组织SOD活性,从而改善小鼠体内炎症因子的释放及组织氧化应激损伤。
抗氧化在治疗UC中具有不可替代性作用,而当前研究多集中在MDA及MPO方面,而SOD是当前领域研究新发现的抗氧化因子,其作用机制能清除自由基,通过抑制脂质过氧化反应表达,维持细胞膜的稳定性进而治疗UC[46]。但当前对中医药影响SOD的研究颇少,今后应增加中医药对多种抗氧化因子的共同协调研究,以提高治疗UC的多面性。
4 中医药通过干预TLR4/NF-κB信号通路下调COX-2
COX-2作为花生四烯酸代谢体系中的关键酶,能增强肠黏膜在机体中的保护性作用,促进肠上皮细胞的修复[47]。当机体被炎症介质、内毒素等干预后,其表达量随之增加,进而破坏结肠黏膜,导致UC的进展。CUI等[48]研究采用TNBS法制备UC大鼠模型后发现,COX-2在体内及体外的蛋白表达显著增加,经黄芩苷干预后能阻断脂多糖和TNBS诱导的炎症反应,在阻断脂多糖刺激的NF-κB、p65核转位中起直接作用,且降低了p-NF-κB、p65、p-IκB的蛋白表达,而增加了IκB蛋白的表达,通过抑制TLR4及NF-κB的激活,下调COX-2、TNF-α、IL-1β及IL-6的表达,从而减少炎症反应,治疗UC。李多等[49]采用免疫复合法制备UC大鼠模型后发现,经复方黄柏液干预后的大鼠能明显抑制抑制NF-κB的激活,进而下调炎性介质TNF-α及IL-6的表达及COX-2蛋白表达,促进结肠黏膜的修复。
考虑到COX-2能被多种炎症递质和细胞因子如IL-1、TNF、表皮生长因子等所诱导,进而催化花生四烯酸合成炎性介质前列腺素E2,导致炎细胞因子浸润。考虑到当前研究领域尚未对此进行相应抑制,笔者认为这应是未来研究侧重点,且清热燥湿类药物是中医药介入TLR4/NF-κB信号通路治疗UC的主要方法之一,那么是否考虑临床上具有同样药性的中药有效成分及复方在下调COX-2方面均有显著的效果?
5 中医药通过干预TLR4/NF-κB信号通路修复肠黏膜屏障
肠黏膜屏障包括机械、化学、免疫及生物屏障四部分,而紧密连接蛋白(tight junction protein,TJP)作为机械屏障的基础结构,在防止有害物质和病原体通过肠腔进入粘膜下层方面起着关键作用[50]。肌球蛋白轻链激酶(myosin light-chain kinase,MLCK)也是屏障功能障碍的关键效应器和潜在的治疗靶点,MLCK在肠道炎症期间参与TJ调节[51],两者在作用靶点方面都能显著的抑制炎症反应进而治疗UC。Kang等[52]研究构建了TNBS诱导的UC大鼠模型,选用补中益气汤作用于大鼠,并使用柳氮磺吡啶栓药物进行比对发现,二者对TNBS诱导的UC大鼠具有相似的治疗效果,通过降低TLR4、NF-κB表达,增加UC大鼠中TJP蛋白表达,且补中益气汤能显著恢复肠黏膜结构,减少炎症浸润,通过减少促炎细胞因子TNF-α和IL-1β的结肠产生从而减轻大鼠结肠炎症,治疗UC。此研究还发现补中益气汤同样可以抑制MLCK,减弱TNF-α诱导的p65核移位和IκB磷酸化,从而改善屏障完整性。
当前中医药干预肠黏膜屏障只停留在修复肠黏膜机械屏障方面,缺乏对其他领域的研究,且中医药应从肠黏膜多靶点、多层面角度修复肠黏膜结构、降低肠黏膜通透性、调节肠道免疫功能及肠道菌群等多方面联合治疗,发挥其独特治疗UC的优势。
6 展望
随着中医药对UC研究领域的不断深入,已经探寻到TLR4/NF-κB信号通路与UC发生进展密切相关,中药单体及有效成分、复方均可证实通过TLR4/NF-κB信号通路在调节炎症因子的平衡、修复肠黏膜屏障、下调COX-2的表达、抗氧化、调控巨噬细胞移动抑制因子方面疗效显著。
本文认为当前在对TLR4/NF-κB信号通路干预UC作用机制方面存在以下不足:(1)在构建UC大小鼠模型方面缺少统一的标准,对不同类型的造模方式提取出的研究重点不尽相同;(2)单味中药及有效成份干预TLR4/NF-κB信号通路,是不是脱离了中医之道?在今后的研究中,是不是可以把中医辨证分型与靶向中药及有效成份相互结合,这在一定程度上为研究提供了思路;(3)另外,中药复方在干预TLR4/NF-κB信号通路中,多以标本兼顾、扶正祛邪为主,由多味药物配伍后组成的复方在作用机制上尚未明确,且缺乏循证医学证据及专家指南共识,在临床疗效评估方面也存在标准不统一,从而缺乏疗效的可靠性。因此,今后可运用新兴研究方法,如网络药理学、基因组学等进行整体信息的融合,充分挖掘出更有效的中药复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