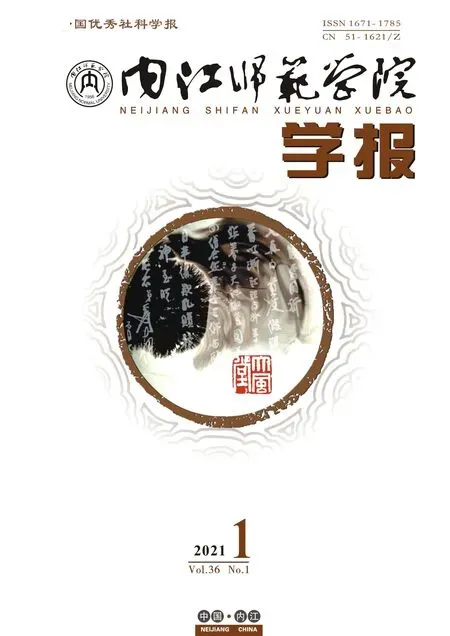论张大千职业画家生涯的起点与动因
2022-01-01李厚琼于军民
李厚琼, 于军民
(内江师范学院 文学院,四川 内江 641100)
张大千(1899-1983),四川内江人,中国近现代绘画史上最具有世界性影响的国画大师之一。辞世虽已三十余年,但依然受到海内外艺术圈、收藏界和学术界的高度关注,其书画作品持续受到热烈追捧。笔者通过CNKI(中国知网)发现,近40年来,标题冠以“张大千”的研究文章多达八百余条,是关注度最高的两位国画大师之一(另一位为齐白石)。台湾学者巴东说:“在我看来,真正的艺术大师,至少要有创作的历史纵深和深厚的文化底蕴,更重要的是,他要有继往开来,承前启后的艺术气度和成就。而张大千,无论外界对他的评价有多极端或两极分化,他也是当之无愧的大师。”[1]张大千不仅是中国近现代绘画史上有着世界性影响的国画大师,也是中国近现代史上最为成功的职业画家。据2015年胡润研究院发布的《2015胡润最畅销中国艺术家》,张大千以17.8亿元人民币的成交额位列第二,仅略低于齐白石18.7亿元。两位艺术家的成交额远远超出第三名的傅抱石9.2亿元。张氏一生以画谋生、以画交友,身前身后都享有崇高的声誉,这在中国历代绘画史上并不多见。
张大千自26岁在上海举办首次个人画展开始,历次画展均相当成功。张大千首次在上海宁波同乡会办画展,每张画20元银洋。经历30余年的积淀,到了1963年,张氏在美国举办画展,其《巨荷图》被《读者文摘》创始人华莱士以14万美金高价收购,创下当时中国画售价新高。张大千晚年在台湾创制巨幅泼墨泼彩《庐山图》,画尚未完成,就已经传出其润笔高达1000万台币,相当于他构筑台北新居摩耶精舍费用的两倍,令人咂舌。到了2010年,张氏晚年一幅泼彩作品《爱痕湖》拍出1.008亿元人民币高价,刷新全球中国画的拍卖纪录。随后香港苏富比又将张大千《嘉耦图》拍出1.599亿元人民币的新高。2016年香港苏富比更是将其去世之年所作泼墨泼彩《桃源图》拍出2.7亿港元的高价,震动全球。除齐白石以外,还没有哪位中国画家的拍卖价过亿元。可以说,中国绘画史上还没有哪位职业书画家身前身后都持续地受到艺林和市场的热捧。张大千堪称中国绘画史上最成功的职业画家。
一、张大千职业画家生涯的起点
谢家孝在其《张大千的世界》中写到,1924年张大千扬名秋英会(据林玉、刘振宇及王中秀等的考证,秋英会实为1928年事,似张大千晚年的回忆有误[2])的前后,张大千还并未走上职业画家之路。“大千先生早年由于家境富裕,从不为稻粮生计愁,加上性格洒脱,一直过着惬意的名士生活,他成名之初,也不鬻画,纯为愉情遣性。”谢家孝认为张大千职业画家的起点是随后于1925年在上海宁波同乡会举办的首次个人画展。该年由于家族经营破产,经济陷入困境,不得已“只有学时髦开画展卖钱”[3]42-45。笔者认为事实恐非如此。张大千职业画家的起点可能早在1920年前后就开始了。其大风堂弟子刘侃生回忆:“我认识张大千先生是在1921年,当时我在南京工作,每次路过杨公井笺扇庄都能见到先生的作品。”[4]1921年张大千回到内江老家,为当地资圣寺书赵贞吉诗碑。该诗碑至今尚立于内江翔龙山资圣寺旧址。可推测张大千此际作为职业画家已小有画名。张大千老友陈巨来回忆二人的最初交往,也明确指出,张善子、张大千兄弟二人于1920年前后寓居上海,目的就是开辟鬻画市场。“甲子(一九二四)之前,二人即来上海,居西门路西成里,家在弄内,画室在沿马路楼下,楼上为黄宾虹所居者。当时以外路人来申鬻画,无人注意。时沪上书家清道人、曾农髯正大名震全沪,门生极众。二人遂亦执贽侍函丈。”[5]29按照陈巨来的观察,张氏兄弟二人拜师曾李二人,一个重要目的就是借此扩大影响、积累人脉、拓展交际圈,为鬻画事业铺平道路。拜师后,善子、大千积极组建曾李同门会,利用同乡好友所开餐馆“蜀腴楼”悬挂画作扩大影响,也托老师向交好同行赠送画作扩大知名度(如陈巨来就是通过其师赵叔孺家中悬挂的善子画作而知晓善子的)。1924年春,曾熙为张大千作《季爰书画例言》并代订润格。在《季爰书画例言》中曾熙云:“一日纨贽就髯席请曰:愿学书。髯曰:海上以道人为三代、两汉、六朝书,皆各守家法,髯好下己意不足学。因携季见道人。道人好奇,见季年二十余,其长髯且过髯,与语更异之,繇是季为髯书,复为道人书,人多不能辨,近则刻苦求于髯与道人书之外,卓然自立矣。季初为画,喜工笔人物,及见髯与道人论画山水,则喜方方壶、唐子华、吴仲圭、王叔明、大涤子,花卉则喜白阳、青藤、八大及扬州诸老。季昆季中,多善为计学,近又蜀中富人矣。季因不汲汲自见,然终日为人奴隶,亦何所取,因为之定其书画例。”[6]可见张大千决定走鬻书卖画的职业画家之路,并非如他对谢家孝所说,是家庭经济破产后不得已的行为,而是不愿“为人奴隶”,渴望自立门户的主动之举。
二、张大千走上职业画家之路的动因
按照大千老友陈巨来的说法,“当时以外路人来申鬻画,无人注意”。书画市场的竞争很大甚至很残酷。比如画家姚钟葆(叔平)“寓沪,从老画家何煜学作花卉,殊采可观。画不遇时,居恒郁郁,还苏愤而自沈,先其兄殁仅数月也。”[7]337由于始终打不开市场,尽管质量上乘却无人问津,最后竟郁郁而死。为了保持在书画市场中的竞争力,沪上一流画家如吴昌硕、吴湖帆、冯超然等也都各有秘不示人的绘画绝技不外传,甚至对自己的门生弟子也保密,“知识产权”的意识比之当代艺林尤过之。为了争夺市场,采取针尖对麦芒的敌对做法也是常有的事,完全不顾文人体面。如陈巨来所举自己的例子:“及叔师故世,余治印生涯日盛,曾订润例,速件加十倍。他亦订润例,速件草草者,减十倍。见余即若不相识矣。”[5]190吴昌硕之孙吴志源甚至被艺林竞争对手雇凶绑架,不得不请出黑道大佬黄金荣出面摆平[7]139-140。既然职业画家之路如此艰难,张大千为何还是走上了职业画家这条充满崎岖的人生之路呢?笔者认为至少应该通过其家族的特点和海派文化的影响两个方面去探究根源。
(一)来自家族兴衰变迁的影响
张大千出生于四川内江一个富裕的商人家庭。其父兄等人开有百货公司、钱庄、轮船公司等多种实业,财力雄厚,在当地很有势力,并不是一些文章中所说的出身“贫穷人家”。大千师曾熙讲:“季昆季中,多善为计学,近又蜀中富人矣。”大千自己亦说:“我家在内江是望族。”[3]1也正因为家境殷实,张家才能够顺应当时有钱人家的潮流,先后送出善子和大千留学日本。善子在日本加入同盟会,逐渐参与政治,成为名流士绅。1911年7月,四川保路同志会内江分会就是在张善子的主持下成立的。端方入川镇压保路运动,因与善子交好,故特别留宿内江,张家负责全程接待。端方后在资州被杀,善子提供了极为重要的情报。张大千在日本留学期间,是一个阔绰的留学生,花高价雇了一名日本人做他的专职翻译。“别的留学生一年才花几百元,我一个月就开销了。”[3]29张大千从日本留学归国后,在上海拜师曾农髯、李瑞清两位前清遗老学习书画,没有相应的财力支撑也是不可能的。为了讨好老师家的门官,以便有更多机会观摩老师写字作画,张大千曾在父亲授意下向门官奉上数百元重金。张大千早年收藏名人字画,也常常是家里汇出巨款支持。一次因为家中汇款尚未到位,老师曾农髯还帮助解了燃眉之急,垫支了八百大洋[3]30。这种出手阔绰的生活方式,一旦遭遇变故而必须过一种节省的生活,是很难适应的。张家后来因为经营不善而致使家族实业破产倒闭。为了能够继续过上阔绰的生活,别无他技的张大千只能坚定走职业画家之路。张大千晚年在台北接受记者谢家孝采访时,谈到了自己的这段心路历程。他说:
“我们家的生意,原本做得很大,事业也经营得很多,开了一家福星轮船公司,那一年出了麻烦,有一艘叫‘大胜’号的轮船,在长江撞翻了隶属贵州军人袁祖铭号鼎卿的一只运盐木船,更糟糕的是船上还有一连兵,几乎全军覆没;当时贵州军的势力,时常侵入四川,这个祸可闯大了,盐船易赔,人命无价,袁祖铭索偿,派人到四川来查封了我家好多产业,于是元气大伤。”
“当初四川另外两家姓张的,以我家财力雄厚,一再要求要与我们合作,在蜀中号称三张事业,除了轮船公司而外,又有百货公司、钱庄等等,我家三家兄就以轮船公司总经理名义驻宜昌,我四家兄亦以百货公司总经理名义经常在上海负责进货,谁知另外二张玩的空头花样,拿我们的钱抵他们的帐,亏空不少。我记得就在我二十六岁那年的端午节前后,多面夹攻,周转不灵,我家的生意就倒闭了。”
“家里没有钱供给我了,第一次感到:要用钱自己找的困难了,我还有什么本事来赚钱呢?只有学时髦,开画展卖钱了。”[3]44
张大千接受谢家孝采访的这段夫子自道,正如前文所言,虽不能由此认定为其职业画家生涯的起点,但家族经营的破产,必然极大地刺激张大千下决心在职业画家之路上弄出名堂来,以支持张氏家族继续过上富足的生活,接续家族庞大的开支。事实上,张大千的传奇一生也正是以此为标的的。张大千极为看重亲情、友情,始终抱持为亲人工作、为友朋奉献的中华民族传统美德,这是他刻苦自励、以画谋生的强大动力。女儿张心庆回忆:“爸爸那些年真是挣不完的钱,还不完的账,经济负担特别重。有时,我的心里也很闷,替爸爸担忧发愁。我们家本来姊妹就多,负担沉重,二伯父过世后,留下二伯母、两个姐姐和一个哥哥,他们读书、嫁娶,父亲也都一手管了下来。三伯父、三伯母也已年迈,父亲时常牵挂;还有一些爸爸的学生也住在我们家,甚至连他们的家属爸爸都照顾到了。这的确不是一般人所能做到的。我们家就像个无底洞,每年究竟要花多少钱,谁也说不清。我扳着指头算,父亲至少要供养三十多口人。”[8]146直至大千晚年萍踪海外,也一刻未忘接济大陆一众亲友。跟亲友们的通信,常常有一个很直接的主题,就是为亲友购物、寄画或汇款。如其给三哥张丽诚的家书写到:“哥与三嫂身体近日如何?弟谨仍月兑港币一百元以为生活补助。”[9]66“老年弟兄天各一方,不得相见,惨痛万分!月初经过香港,曾托一门生兑上美元五十元。度此信到时,此款亦收到,外寄砂糖二公斤、花生油五公斤、花生米二公斤、红枣一公斤、肉松二公斤、云腿四罐。……弟于万里之外,每年卖画可得美金万余,只是人口稍多,足够家用。”[10]23给九侄张心义的信中写到:“故乡大水,日夜不安。……叔亦衰退不如二三年前远矣。写字作画,亦复腕指战擎。即友好书札往返,大都乞人代复。只有绘画与楹联挂幅,虽不佳,必须亲笔。兹恳徐伯郊老伯汇上,与三叔三妳添助日常零用。”[10]289
张大千曾经对女儿张心瑞讲:“你爸爸是条老牛,这么大一家人,都要靠我这条老牛在外挣钱。”[3]122这是张大千对自己的爱女说过的掏心窝子的话,也是张大千在新中国成立后没回大陆的重要原因,与政治立场无关,也与是否爱国无关。他思考问题的方式是基于谋生所需的市场的商业思维。毫无疑问,张大千有着一般职业画家所不具备的非凡的商业思维和市场意识。20世纪50年代初期齐白石曾辗转致信张大千,希望其在海外代为出售画作,以纾生活之困,故画价只需100美金即可。张氏对此感慨万分:“哎,这话可令我心酸啰,齐先生的画岂只值一百美金?我的画单只在日本的裱工,小小的一幅,往往就要一百多美金的工钱!”[3]93张大千作为龙门阵摆出来的这些故事,虽不见得特别准确,但联系当时的时代背景,应该有一定合理性。齐、张二人虽同为那个时代著名的职业画家,共同创造了文人绘画市场的辉煌,但在商业思维和商业运作上,张大千的确很难超越。拜师曾熙、李瑞清,积极与沪上书画界名流互动,积极参加各种书画展览活动,积极展开宣传造势,努力构建专业的运作团队,准确捕捉市场风向,投市场所好,这些都直接或间接地体现了他高明的运作手段。作为有名的石涛专家、作伪高手,其少年狡狯甚至一度扰乱京沪两地书画市场。寄居海外期间设法与毕加索的会见,更是被全世界所关注,画坛从此有了“东张西毕”之谓。跟家族善于经商一样,张大千似乎从小就表现出了独特的商业思维。张大千少年时代就有用书画作品来换取钱财的成功经历,让他印象深刻。张大千自己曾向子女提到,十岁那年,与小伙伴一起,卖春联赚钱[8]57。大千十二岁那年,发生了两件让他记了一辈子的大事。一是开始吃肉,二是为抽签算命的“河南女”画签画,“开始卖画赚钱”。“八十枚小钱画廿四张,我好高兴,八十个小钱在我是笔大钱,当时我只记得四个小钱就可以买到一两烧腊!”[8]6笔者认为,少年时代的这些鬻书卖画的独特经历对张大千后来走上职业画家之路提供了心理上的强烈暗示。
(二)海派商业文化对张大千走上职业画家之路的影响
据记载,上海设置县级行政区划的历史是从元代开始的,距今不过数百年。直到晚清,才逐渐发展成为一个人口近20万的商业城市。1843年,上海开埠,随后出现租界。到19世纪末,仅上海租界人口就激增至40多万,外侨约占1.6%,其余为上海和其他省的居民。长期的华、洋共处、五方杂居,使得中西文化不断碰撞,英美等国先进的城市管理和经营理念不断引入,城市经济遂迅猛发展。在20世纪初成为与伦敦、纽约、巴黎齐名的“东方大都会”,充满着多元、创新、时尚的特质和浓厚的商业氛围。海派文化也就在这样的氛围下诞生和发展了起来。20世纪30年代,文艺界围绕京派和海派文化的特质进行了一场深刻的论争,不少文化名流和社会精英(如苏汶、沈从文、曹聚仁、鲁迅等人)加入这场讨论。这场讨论的结果不管对海派文化是持贬损还是褒扬的态度,一个共同的认识是海派文化是植根于商业大都会的产物,商业性是海派文化最重要的基因。鲁迅对当时京派文化和海派文化的本质一针见血:“要而言之,不过‘京派’是官的帮闲,‘海派’则是商的帮忙而已。”[11]756-758海派文化对商业性的倚重无疑也一定程度上影响到文艺的独立品性,使一部分文艺作品沦入庸俗媚世的境地,但透过历史的烟云,我们还是发现,那些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杰出成就并影响了中国文艺现代化进程的艺术家及其创作的文艺作品,很多都出自十里洋场的上海。“文化从为官走向为民,从官场走向民间,从农业文化走向商业文化,这是中国大地上文化的一次最深刻的转型。只有姓‘商’的海派文化,才能做到中西融合海纳百川。”[12]
海派书画同其他海派文艺一样,也是随着上海这座新兴的商业大都市经济的繁荣而发展起来的,同样具有浓郁的商业特质。“自海禁一开,贸易之盛,无过上海一隅。而以砚田为生者,亦皆于于而来,侨居卖画。”按照王琪森的划分,第一代海派职业书画家以任伯年为代表,时间在19世纪末;第二代以吴昌硕等为代表,时间在民国初;第三代以“三吴一冯”(吴湖帆、吴待秋、吴子深、冯超然)为代表,时间在20世纪20、30年代。此际迎来了海派书画的鼎盛期,一大批书画家攒聚上海,鬻书卖画为业[13]。张大千自1917年日本留学归国后,即长期置身上海,接受海派文化的洗礼。耳濡目染无疑对他走上职业书画家之路具有极大的刺激。他的两位恩师曾农髯、李瑞清都是以前清遗老的身份寄身上海靠鬻书为业,本就是职业书画家。对于自己的职业书画家身份,李瑞清有一段夫子自道:“自欧美互市,航轨东合,顷岁以来,商战益烈。运筹用策,不出市廛;灭国争城,无烦弓矢。是以大贾贵于王侯,卿相践同厕役。尊富卑贫,五洲通例。若夫贫困不厌糟糠而高语仁义者,诚足羞也……不得已,仍鬻书作业,然不能追时好以取世资,又不欲贱贾以趋利,世有真爱瑞清书者,将不爱其金,请入其值以偿[14]53。如此明确的“入其值以偿”的职业画家意识,不可能不影响到青年张大千的价值观的形成。
那么,职业书画家的卖画收入在当时处于一个什么水平呢?是否能够支撑一个画家及其家庭的基本开支呢?尤其是张大千这样一位以出手阔绰著称的富家子弟,卖画收入是否能够满足其个人及其家庭的庞大开支呢?这里我们需要先将彼时书画市场的基本情况作一了解。据张大千自述,其第一次办画展是在1925年秋天,在上海宁波同乡会馆。“早年我开画展,每次都是一百张,这一百幅画总是以一个月的时间画成,山水人物花鸟无所不有,我的第一次画展,是在上海宁波同乡会开的。当时也很妙,我不分画别,每张画一律定价二十元银洋。”[3]45二十元在当时处于一个怎样的物价水平呢?在五四前后,北京大学一级教授胡适、辜鸿铭、马叙伦、蒋梦麟、沈尹默、马寅初等人月薪为280元。“20年代初,北京生活便宜,一个小家庭的用费,每月大洋几十元即可维持。”[15]101当时上海情况类似。如果一个五口之家月入六十六元,就可以过上“小康水平”的生活,且这样的家庭占比仅仅4%,以知识阶层和公司职员为主[15]123-124。由此看来,张大千自二十多岁刚步入职业画家行列,就能通过画展收入跻身精英阶层的生活。而且每张画二十元的标价,在当时还只能反映青年画家的润例水平,并不是一流书画家的标准。如1925年吴昌硕为自己年仅21岁的弟子徐穆如订“虚云阁润例”时,标价为堂幅四尺六元、六尺十二元、八尺二十元。刻印,每字一元。大千自己于1926年刊登在《中国现代金石书画家小传》上的润例为:“山水人物点景倍值。堂幅丈二尺三十元。一丈二十元。八尺十二元。七尺十元。六尺八元。五尺六元。三四尺四元。” 而当时一流名家的润例则高出很多。如刊登在同一杂志上的大千师曾熙的润例为:“花卉堂幅六尺四十元,四五尺三十元,二三尺十八元。山水不论粗细笔照花卉加倍。”又如1925年5月沪上名家吴待秋润例:“山水:堂幅三尺五十元、四尺七十元、五尺九十元、六尺一百二十元、八尺二百二十元。佛像:视山水增二成。花卉:视山水减四成。”另一名家吴子深同一年的润例标准:“折扇银十两。纨扇八两。立轴每尺十两,四尺而止。条幅每尺八两,六尺而止。” 当时一流名家的润例水平显然比青年画家高出很多。“当时海派书画家,特别是像‘三吴一冯’这样的名家,月收入都在千元以上。作为自由从艺者,其经济条件远远要比大学教授、报馆主编,乃至高级职员等优越得多。”[16]2-16书画市场呈现出的巨大活力以及所带来的可观收入,使张大千看到了靠鬻书卖画保持阔绰的生活方式的可能,这正是促使张大千走上职业画家之路的巨大动力所在。
综上,笔者认为,张大千无疑是中国绘画史上少有的能将追求绘事与追逐财富完美结合的天才型大师。优渥的家境、聪颖的天资帮助张大千一开始就结交了艺林泰斗曾熙、李瑞清等人,打下了坚实的艺术根基。维持衣食无忧的富足的生活是他在家族生意突然受挫时不甘沉沦的动力源泉。来自家族的良好的商业思维使他能够彻底摆脱一般文人书画家“羞于言利”的心理,从而穷尽各种商业手段使自己在上海滩迅速立足并扬名。同时,海派商业文化宣扬的“大贾贵于王侯,卿相贱同厕疫”的新时代精神,也为张大千精心培育自己的艺术市场提供了肥沃的土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