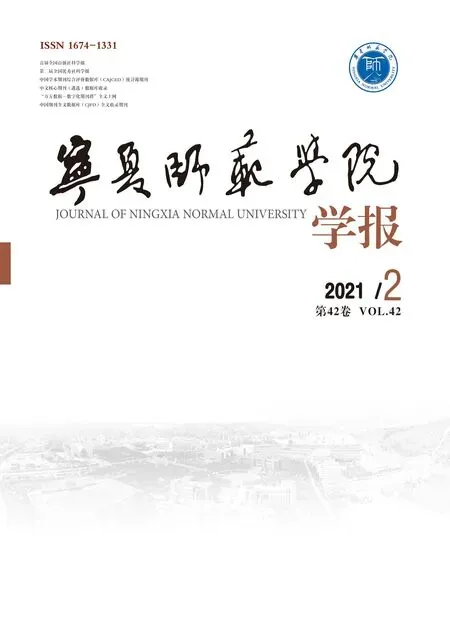当代宁夏小说创作的审美观探析
——以“新三棵树”与郭文斌小说为例
2021-12-31张一博
张一博
(北方民族大学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宁夏 银川 750021)
新时期以来宁夏小说创作活跃,助推了宁夏文学的快速发展,也引起了研究者的关注。从近年来宁夏小说研究看,大部分研究侧重对宁夏小说创作的个案研究。有些论著虽厘清了宁夏小说创作的发展脉络,系统梳理了宁夏文学史,从审美的维度切入文本内部肌理,但代表性著作只有李生滨所著《审美批评与个案研究——当代宁夏文学论稿》。其他论著虽也涉及以审美的眼光来观照宁夏小说,但只作为论著的一个章节来谈及,所占比重相对较少,没有全面系统地梳理,对于宁夏小说蓬勃发展态势与其较丰富的阐释空间来说,似乎是不太相匹配的,这是宁夏文学研究的遗憾。基于此,本文在前人研究基础上,剖析新时期以来宁夏小说创作的审美意蕴,力图从多个维度研究宁夏小说,通过对其深入系统地整理和研究,尝试发掘宁夏小说的丰厚审美内涵,希望能为宁夏小说的审美研究提供参考。鉴于宁夏作家群体较大,本文只选取部分作家为研究对象,即以张学东、漠月、季栋梁、郭文斌四位作家的小说为重心。因为张学东、漠月、季栋梁三位作家作为宁夏文学“新三棵树”的代表,其小说创作具有一定的典型性,能较真实与全面地揭示出宁夏小说的整体审美格调与作家的内在审美追求;郭文斌则作为“安详诗学”的传播者,通过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溯源,让久居都市的人们重获心灵上的安详,在当下有重要的社会现实意义,其小说作品的创作主题、审美意象与诗意语言也体现了极强的审美意义。因此,本文最终选取这四位作家的小说为重点观照对象。
一、审美主题的多样性与含混性
宁夏地处西北,面积较小,但宁夏文学有“小省区、大文学,小短篇、大成绩,小草根、大能量,小作品、大情怀”的美誉。新时期宁夏作家积极创作,他们立足于独特的地理环境,既秉承着中国悠久历史文化的美学传统,坚守传统的审美道德,又结合西方艺术文化资源,创作出根植于多种异质文化的作品,多样性与含混性便构成了宁夏小说的审美主题。
郭文斌的长篇小说《农历》取材于中国传统文化,它以农历节气为章节,以两个孩童为叙事主体,通过讲述他们在日常生活中对传统民俗由陌生到逐渐熟悉的全过程,展示出中国传统乡村文明的静穆与安详,并暗含作者对其在商业文明侵蚀下日渐消弭的忧虑。小说集《吉祥如意》也把创作主题追溯到传统文化对心灵浸润的维度上,借五月和六月姐弟俩的视角,体会平凡日常中随处可见的民俗文化,流露出丰厚的民俗美学意蕴,进而让读者领略中国民俗的魅力,因此,文本中体现出丰厚的审美文化内涵,彰显出其小说创作的诗性审美主题。
张学东则把创作笔触指涉到更为广泛的社会现实空间,透露出其小说创作主题的杂糅性。其《超低空滑翔》取材于亲身经历,是中国首部以民航生活为叙事题材的长篇讥讽小说,作品彰显出以讽刺为特色的另类审美价值。《西北往事》则为读者呈现出一个遭受政治与经济双重磨难的家庭,在苦难中仍持有坚韧的事迹,含有一些苦难美学的韵味。作品在一定程度上还原了历史上掩藏的真相,揭示出少年成长进程中的心理隐秘,流露出特异审美情调。《妙音鸟》则又将读者带回到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西北的偏远村庄羊角村,体验特殊年代下权力的相互倾轧、人物内心欲望的挣扎与苦难绵延的人生,以及在这种反常的环境下孕育出来的高贵灵魂,小说始终高扬着苦难美学的旗帜。
新时期以来,宁夏作家不断创作,部分作家选择回归中国传统文化,在烛照现代人的精神世界时,弘扬传统优秀文化对人心逐步异化的疗救功效,通过对中华多民族文化的倾情书写,作家小说始终充盈着天人合一的中华民族精神与乡愁美学的独特气质,充实了文本的象征意义与文化底蕴。除了郭文斌这个代表性作家外,漠月也常从大漠深处找寻人们之间的温情与良善,其小说创作多取材于故乡阿拉善地区小人物的日常生活,从中探寻出中华民族精神品格。
还有部分作家创作主题呈多样性,得益于其对外面世界的悉心体悟,在人文精神失落与信仰危机弥漫的后现代社会语境中,既可以选择关注特殊年代背景下小人物的生存境遇,体悟他们的命运沉浮,如张学东的《西北往事》《家犬往事》《妙音鸟》等;也可以关注当下的生活现实,其创作便呈现出后现代语境下的社会图景,不仅丰富了文本的审美内涵,增加了审美张力,也使审美主题愈加多元与含混。
宁夏其他作家小说创作的主题也很有审美特点,如查舜倾心建构出梨花湾这个美好的审美意象空间,景美人更美的乡土文明给人以愉悦的情感享受;火仲舫则坚持把中华传统民俗元素纳入小说创作中,在人物日常生活的自然流动中散发传统文化的魅力;阿舍灵动的叙事思维与开阔的视野胸襟决定了她在创作历史小说时游刃有余,既能入乎其内,又能超乎其外;平原与曹海英凭借女性心理独特体验对都市知识女性的内心隐秘世界展开烛照,由以往单纯地描写女性自身存在的问题向外界不断拓展,从生理、心理与社会维度对女性意识进行挖掘。
二、审美意象的多重呈现
意象是我国美学学科建设核心范畴之一,意象符号作为一种审美客体,在作家主观情感投射下带给读者审美阅读体验,进而完成诗意景观的审美建构。朱志荣认为:“意象创构是主体通过体悟外物呈现为空灵之象,获得精神愉悦的过程,也是主体通过直观体悟诱发情感与想象,力求自我实现的过程,其中体现体悟、判断与创造的统一。”[1]
郭文斌的《农历》《吉祥如意》《寻找安详》等小说涉及节日、母亲、孩童、荞麦、煤油灯等审美意象,作家结合生活经验,选取多个意象来纳入文本创作中,并灌注丰富的情感认知与审美经验,构建出有着审美余韵的意象序列,当其通过文本进入大众视野时,已非简单冰冷的文字符号,而是作者已进行了艺术的审美化处理,再经过读者多维度解读,使心灵得以浸润。作者通过对多种意象的精心择取与打磨,使其焕发出特有的审美魅力,暗合了读者的审美期待,审美意象在文本中的多重呈现,使文本的审美价值尽得彰显。
漠月的《湖道》《放羊的女人》《锁阳》《父亲与驼》等小说涉及父亲、女人、骆驼、羊群、狐狸、锁阳等意象,这些意象是作者在家乡阿拉善较为熟稔的,那里不仅是以骆驼为代表的动物生存的特殊区域,也是以锁阳为代表的植物可以存活的地带,同时,这样独特的地域文化孕育出来了坚韧挺拔的男性与隐忍博爱的女性。漠月正是熟知这个养育他的家园,故他在创作时任意选取家园的一草一木作为审美对象,这些独特和丰富的审美客体便凝聚了作者极厚的情感浓度,有着丰富的审美张力,呼唤起“都市之子”久违的家园意识,极易唤起大众情感共鸣。
宁夏作家通过对审美意象在文本中的多重呈现,赋予其全新审美内涵。马金莲的扇子湾、李进祥的清水河、漠月的阿拉善,它们成了作家小说中独特的文学地理标志与空间意义符号,也成了历史记忆性的地标。作家始终关注着那些承载了其生命经验与情感记忆的家园,对生于斯长于斯的故土持温情回望,对生长于其间的万物都有一种悲悯的情怀,付诸文本,变成一个个极具情感张力的审美意象。对故乡的回忆与书写、虚构与想象已成为宁夏作家创作中的重要价值取向与叙事立场。在某种意义上,“他们不仅很好地承续了宁夏文学的历史传统,更是在此基础上不断拓展进取,形成了各自迥异的个性特色,从单薄、生涩而渐渐丰满、成熟,展现出多元化的面相。”[2]从宁夏作家身上,我们可以看到地域化写作是有美好前景的,而且宁夏也是一个多民族文化多元共生的地方,地域化与民族化自然成为宁夏小说的真正底色。郎伟曾说:“这样的地域文化底色,反映在宁夏短篇小说的创作当中,便是作家们会不自觉地在作品当中细致描绘民族民间的风土人情,将地域的民族的精神生活内涵审美性加以呈现,从而形成氤氲于宁夏短篇小说之中的特殊的地域文化和民族文化情调。”[3]
三、多样的审美表达
近年来,宁夏作家既立足于传统,继承了中国古典的诗性审美表达方式,又勇于创新,积极借鉴西方艺术表达技巧,融合了克制冷静的现实主义与奇异惊艳的魔幻主义笔法,体现小说多样的审美表达,从而建构出西北边地独特的乡土社会人文景观,文本极富艺术张力与审美冲击力。
张学东的《妙音鸟》体现出作者具备超强的虚构能力与蓬勃的艺术想象力。首先,“妙音鸟”是个人面鸟身的神鸟,小说中这个意象意味深长,它具有双重含义,一方面是指妙音鸟来自遥远的喜马拉雅大雪山,有着曼妙的声音,一旦被人听到,则会让人潜心向善,另一方面则指的是生活在羊角庄的人们,如寡妇牛香与乡村教师秀明等底层人物,他们良善的品性像妙音鸟一样能指引他人走向正途,因此,这个意象具有丰富的审美内涵。其次,大量的神话、传说与荒诞不经的情节贯穿整个文本中,不仅很大程度上复活了那段时期的历史,还重构出一个驳杂的审美空间,在这个充满离奇的意象空间中,有活人与灵魂的对话、村头游离的冤魂、复活的狼皮、狼群对寺庙的敬畏等不可思议的事件,这种另类的审美表达方式给读者极强的审美冲击力。在羊角村发生的一切,既是一种传说,是作者的一种虚构式写作,也是曾真切发生在这个村子里的,这些匪夷所思的情节与那个年代真实发生的一切形成同构关系,展示出了民间文学形式与作家小说之间的互文性特征,具有一定的魔幻现实主义色彩。“由于这种‘陌生化’的艺术趣味的存在,‘现实’在他的小说中常常会突然遁入遥远之地,而某种穿越人生与人性的‘寓言’质地却清晰地显现了出来。”[4](P369)
季栋梁的长篇小说《锦绣记》则采用了双线交叉进行的叙事策略,即文本用两条线索呈现两代人进城的故事,打破了以往宁夏小说创作中单线叙事的局限,极大扩充了文本含量,使情节更加紧凑圆润,具有丰富的审美价值。除去在写作手法上的审美化表达,季栋梁在语言上也精雕细琢,力求小说语言的审美化呈现,迥异于郭文斌与漠月诗意语言的叙述风格,季栋梁秉承了宁夏作家以方言俗语进入文本的传统,使小说通俗易懂,流露出鲜明的地域与民族特色,粗粝质朴的言语搭建起独特的审美空间;在句子结构上,也产生大量名词、形容词活用成动词的现象,打破了句子本身旧有的格律规范,达到了陌生化的效果,重塑起全新的审美研究范式,文本也真正实现了审美表达的多样化。
宁夏小说成就突出,得益于作家掌握多样的审美创作与表达技巧。从语言的审美化呈现层面考量,有郭文斌、漠月的诗化语言叙述模式,郭文斌善于借用孩童的视角提炼出世间情感最“纯”的部分,在中华传统文化的深厚积淀中找寻安详,在诗性的语言中体悟孩童内心世界的纯真无瑕;而漠月对生养他的阿拉善始终持温情回望,对当地的风土人情予以深情书写,流露出浓厚的家园皈依情结,诗化语言在小说中的穿插运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当地人们在生存与精神上的苦难,让读者对陌生的大漠风情有了全新认识。张学东、季栋梁小说语言采用口语化叙述策略。张学东擅长取材于历史长河,通过回溯历史,建构出离奇的审美空间,借用他人的口吻彰显人性力量,平实化的语言风格贯穿小说的始末,让人读来不觉生涩;季栋梁坚持书写乡土大地上艰难生存的众生,既不回避苦难,也不渲染苦难,而让乡土文明自身的劣根性得以自然呈现,其小说语言多为当地口语俗语,也不讲究对语言的精雕细琢,而还以语言的本来面目。
从写作手法的审美化表达来观照,郭文斌、漠月惯用单线性叙事,他们沿袭了中国传统的写作模式,较少使用西方写作技巧。张学东、季栋梁尝试用双线性叙事,他们接触到了较多的西方文化,诸如魔幻现实主义、女性主义、生态主义等理论思潮,并积极学习与借鉴西方文学叙事上的表达技巧,文本的写作手法得以多样化表达。宁夏小说中多样的审美表达方式,将引领宁夏文学迈向新的台阶,成为中国文学中熠熠生辉的一部分。
四、结语
本文从审美主题的多样性与含混性、审美意象的多重呈现、多样的审美表达三个维度研究新时期以来宁夏小说的审美观,窥探宁夏小说内部蕴含的深层美学肌理,进而重新发现宁夏文学创作的生命力与生长点。新时期以来,宁夏作家的小说创作呈井喷式态势,从20世纪80年代的“两张一戈”“三棵树”“新三棵树”,再到如今的“宁夏文学林”,宁夏作家高频率地活跃在当代文坛上,他们凭借各自小说文本中建构出的独特话语体系为宁夏多样化文学打了一针“强心剂”,助推了宁夏文学的发展繁荣,使宁夏文坛在现今众生喧哗的社会潮流中脱颖而出,成为中国文学发展链中必不可缺的一环。如张富宝所说:“可以这样说,‘宁夏文学’或(‘文学宁夏’)的出现,不仅使宁夏这一曾经遥远而陌生的地理名词变成了一个丰富生动、充满内蕴的文学形象和文化意象,散发出神秘而亮丽的光芒;与此同时,它也为当代中国文学注入了一股新鲜的血液,增添了一种新的元素,贡献了一种新的可能性,进而为中国当代文学的兴衰变迁提供了一种特殊的参照。”[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