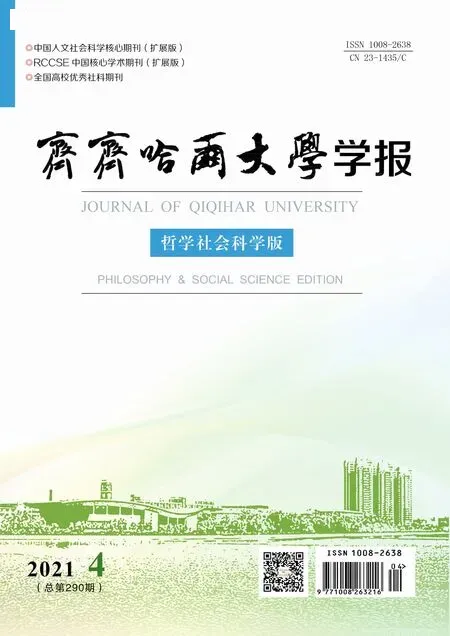北宋诗僧题植物画诗的创作渊源及其与“文字禅”之关系
2021-12-31刘泽华
刘泽华
(福建师范大学 文学院,福建 福州 350007)
北宋题植物画(传统画科花鸟画又可细化为动物画、植物画以及动植物画)诗①创作主要分为四类,即题林木画诗、题竹子画诗、题梅花画诗、其它题花卉画诗。由于北宋大批能文善诗的禅僧涌现,从咏物诗到题画诗创作,以及佛化植物深度契合作者的创作心态,于是使得题植物画诗成为表现“诗、画、禅”的重要载体。文章重点围绕题林木画诗、题梅花画诗与“文字禅”的契合会通进行剖析,通过具体可见的绘画以及画中的自然植物,衬以禅意、禅境、禅机、禅趣,再借助古代诗歌意象的二重想象与建构,让植物、绘画、诗歌、禅学四者完美地熔融于一体。诗僧群体的题植物画诗创作相较于普通文士,其联结诗与画间的媒介是不一样的。文士是通过“能诗知画”或“擅画知诗”等实现诗与画之间的贯通,而诗僧群体是以“文字禅”作为沟通诗画的一种重要媒介,形成“诗与禅合”、“禅与画会”的紧密衔接方式,而最终是要达到一种“诗情画意融禅味”的艺术表现效果。
一、诗僧题植物画诗之创作渊源
宋代诗歌的一个重要分支就是宋代题画诗,而宋代题画诗的内容按照传统画科或创作题材进行分类,可以分为题山水画诗(钟巧灵博士学位论文《宋代题山水画诗研究》)、题动物画诗(李源清硕士学位论文《宋代题动物画诗研究》)、题植物画诗(刘泽华硕士学位论文《宋代题植物画诗研究》)以及题人物画诗(陆艳阳硕士学位论文《宋代题人物画诗研究》)。其中,北宋诗僧(禅师)群体创作的题植物画诗又是宋代题植物画诗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与佛教思想的联系是非常紧密的。究其原因,主要有三点:
其一是古代佛教与自然植物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如“佛化植物”或“禅化植物”的出现就是一个很好的印证,“不少佛化植物,在本土传统中就有丰富的历史文化积淀,有的形成并称,广为人知,影响深远,如‘岁寒三友’松竹梅,梅兰竹菊‘四君子’之类”,[1]此外与佛陀相关的植物,如无忧树、阎浮树、吉祥草、菩提树、竹子、檀耳、娑罗树、七叶树等;佛教的花类植物,如莲花(钵头摩、优钵罗、泥卢钵罗、拘物头、芬陀利)、优昙花、曼陀罗花、曼殊沙花、茉莉、阿卢那花、金婆罗花、婆师迦花、苏摩那花、俱苏摩花、阿提目多迦花等;佛教的香料植物,如沉香、旃檀、优尸罗草、多摩罗跋香树、瞻卜树、熏陆香树(乳头香)、多揭罗香树、安息香、龙脑香等;佛教的修法植物,如木穗子、阿梨树、芥子、波罗奢花、多罗树、频婆树等;佛教的药用植物,如甘露、毗醯勒、阿波末利迦草(牛膝草)、郁金、蕃红花、轲地罗、奢弥草(枸杞子)、珊陀那、安禅那、迦罗毗椤树(羊踯躅)、尸利沙树(合欢)、诃梨勒、呵梨陀(黄姜)、迦罗迦树、迦毗陀树(梨树)、频螺树、红婆树等;佛典的奇异植物,如如意树、波利质多罗树、乐音树、好坚树、衣领树、尸陀林等;经论譬喻的常见植物,如庵摩罗果、庵摩罗树、空花、恶叉聚、须弥南树、伊兰树、拘毗陀罗、铁树、稗梯、芦苇、波罗翅树等。这里“佛化植物”(禅化植物)引用狭义观,是指诗僧(禅师)群体笔下创作的具有禅理、禅意、禅趣的自然植物意象。
其二是众多诗僧积极参与创作,北宋诗僧基本都有“学士大夫为之助”的传统,并且诗僧群体士夫化已经成为普遍现象,诗文兼擅,悠扬风雅,如僧惠洪(觉范)、僧祖可(正平)、僧善权(巽中)、僧道潜(参寥)等,惠洪笔下的枯木,《法云同王敦素看东坡枯木》:“君看壁间耐冻枝,烟雨楂芽出谈笑”;[2]244墨梅,《华光仁老作墨梅甚妙为赋此》:“惭愧高人笔下春,解使孤芳长不老”,[2]54《妙高老人卧病遣侍者以墨梅相迓》:“多谢高情饯春色,十分浑在一枝梅”,[2]734《妙高梅花》:“戏折寒梅画里传,便知香爨揽佳眠”,[2]1023《谢妙高惠墨梅》:“雾雨黄昏眼力衰,隔烟初见犯寒枝”,[2]1022《书华光墨梅》:“一枝已清妍,交枝更媚妩”,[2]565《琛上人所蓄妙高墨戏三首·并序》其一:“那料高人笔端妙,一枝留得雾中看”;[2]1023桃花,《次韵张敏叔画桃梅二首》其一:“好在一枝长不死,谩烦诗笔扫烟云”,[2]1032《次韵张敏叔画桃梅二首》其二:“玉骨冰姿过眼空,却烦摹刻倩诗工”[2]1032等。祖可笔下的乔松,《书秦处度所作松石》:“长怀祝融天柱峰,万年不死之乔松”;[3]14611枯松,《咏秦处士作枯松》:“林壑卷帘相照映,坐令公子发幽思”;[3]14611树木,《书性之所藏伯时木石屏》其二:“淡巃嵷烟雨色,老槎牙霜霰痕”;[3]14611墨梅,《墨梅》:“一枝无语淡相对,疑在竹桥烟雨边”[3]14611等。善权笔下的墨梅,《送墨梅与王性之》其一:“道人笔下有春色,写出江南雪压枝”,[4]2212《仁老湖上墨梅》:“幻出陇首春,疏枝缀冰纨”[4]2212等。道潜笔下的枯木,《同赵伯充防御观东坡所画枯木二首》其二:“萧然素壁倚枯枝,行路惊嗟况所思”[5]241等。北宋诗僧创作的题画诗(包括题植物画诗)与同时期文人士大夫的创作,如梅尧臣、欧阳修、司马光、苏轼、苏辙、黄庭坚、晁补之等,在创作风格以及审美倾向方面是有一定区别的,一般情况下文士比较注重描绘画家的构图和画境,对绘画技艺表示服膺于心。但是当诗僧们面对画作时,会非常自然地增添一些禅语、禅趣、禅意,笔下会经常出现如“道人”、“万象”、“禅斋”、“幻出”、“不死”、“尘寰”、“无尘”、“僧坊”、“拥衲”、“道眼”、“三昧”、“心净”等一系列佛教语词,由此可见佛教思想的介入,让北宋诗僧的题植物画诗创作已经不单是一种感官的享受,而往往具备了参禅悟道的欣悦。
其三是诗僧群体与画师的往来唱和,葛兆光先生《禅宗与中国文化》指出:“到宋代,禅僧已经完全士大夫化了,与大字不识的六祖惠能不同,他们不仅历游名山大川,还与士大夫们结友唱和,填词写诗,鼓琴作画,生活安逸恬静、高雅淡泊又风流倜傥”,[6]43-44如惠洪与花光仲仁的往来,惠洪,字觉范,又自号冷斋、寂音、甘露灭等,真净克文禅师之法嗣,精于诗词。花光仲仁擅画墨梅,北宋宣和年间,惠洪与花光仲仁的诗画往来、酬唱极为紧密,“惠洪《石门文字禅》、《冷斋夜话》中与仲仁有关的作品有诗十一首、词二首、赋赞杂文十七篇”,[7]如惠洪描绘的仲仁笔下墨梅,《华光仁老作墨梅甚妙为赋此》:“惭愧高人笔下春,解使孤芳长不老”,[2]54《妙高老人卧病遣侍者以墨梅相迓》:“多谢高情饯春色,十分浑在一枝梅”,[2]734《妙高梅花》:“戏折寒梅画里传,便知香爨揽佳眠”,[2]1023《谢妙高惠墨梅》:“径烦南岳道人手,画出西湖处士诗”,[2]1022《书华光墨梅》:“一枝已清妍,交枝更媚妩”,[2]565《仁老以墨梅远景见寄作此谢之二首》其一:“道人三昧力,幻出随意现”;[2]55僧祖可与秦湛的唱和,祖可,名苏序,出身京口苏氏,与善权同学诗,气骨高迈,“工诗之外,其长短句尤佳,世徒称其诗也”。[8]492秦湛,字处度,号济川,秦观之子,曾通判常州,仕至宣教郎。幼承家学,善画山水。而《书秦处度所作松石》、《咏秦处士作枯松》应是僧祖可和秦湛往来后作,祖可描绘的秦湛笔下松木,《书秦处度所作松石》:“高堂奋袖风雨来,霜干云根动秋色”,[3]14611《咏秦处士作枯松》:“秦郎真是旧摩诘,写出崔巍霜雪姿”;[3]14611僧善权与花光仲仁的唱和,善权是江西诗派“三僧”之一,临济宗黄龙慧南之法嗣,“丛林梁栋权与洪”,惠洪最推崇善权,“以文学之美致高名于世”,[2]1681而《仁老湖上墨梅》当是僧善权和花光仲仁往来后作,善权描绘的仲仁笔下墨梅,《仁老湖上墨梅》:“幻出陇首春,疏枝缀冰纨”[4]2212等。
二、“文字禅”对题植物画诗创作之影响
在北宋以及由北入南阶段“禅宗在文化和文学的复苏发展中,仍发挥了重要的催化剂的作用,尤其对于诗歌创作的意义不可低估”,[9]13儒士研治经藏,留意禅悦;禅师博究书史,兼及外典。北宋禅师把“以文字为禅”的言意观从佛禅经籍、师祖语录引置到其它语言文学作品之中,如北宋契嵩《三高僧诗·并叙》其一《霅之昼能清秀》:“禅伯修文岂徒尔,诱引人心通佛理”[3]3560以及惠洪《赠涌上人乃仁老子也》:“应传画里风烟句,更学诗中文字禅”,[2]730这两句话也就成为两宋众多诗僧“舞词弄札”兼涉文学创作的重要依据之一。正是由于北宋中后期“文字禅”及“以文字为诗”现象的兴盛,这直接影响到传统文士以及诗僧群体的题画诗创作,从而全面推动了两宋乃至宋后佛禅题画诗的长期繁荣。“文字禅”最早见黄庭坚作于元祐三年(1088年)的题画诗《题伯时画松下渊明》:“远公香火社,遗民文字禅”,[10]325北宋任渊注曰:“《高僧传》曰:‘彭城刘遗民、豫章雷次宗等,依远游山,远乃于精舍无量寿像前,建斋立社,共期西方,乃令遗民著其文。’又陈舜俞《庐山记》曰:‘遗民与什肇二师,好扬榷经论文义之华,一时所挹。’乐天诗:‘本结菩提香火社。’《维摩经》曰:‘有以音声、语言、文字而作佛事。’《传灯录·达摩传》:道副曰:‘如我所见,不执文字,不离文字,而为道用。’东坡《寄辩才》诗有‘台阁山林况无异,故应文字不离禅’之句”,[10]325-326“文字禅”原意是指刘遗民为慧远等的西方斋社而作的净土誓文,之后引申为一种诗僧“文士化”以及文士“禅林化”的文化融合现象,周裕锴先生总结“文字禅”:“一是指研读佛经,领会禅理;二是指借诗文示悟说禅;三是指参究语录公案”,[9]30禅僧之诗可称为“文字禅”,也就是“一切禅僧所作忘情的或未忘情的诗歌以及士大夫所作含带佛理禅机的诗歌”。[9]30
谈到“不离文字”,惠洪《题百丈常禅师所编大智广录》:“佛语心宗,法门旨趣,至江西为大备。大智精妙颖悟之力,能到其所安。此中虽无地可以栖言语,然要不可以终去语言也”,[2]1471-1472又道潜《赠权上人兼简其兄高致虚秀才》:“穷愁肯学郊与岛,高瞻已能追晋魏。文章妙处均制馔,不放咸酸伤至味”,[3]10809此外“直到北宋中叶后,文字化才发展为大规模的席卷禅宗各派(云门宗、临济宗、曹洞宗)和诗歌各派(荆公体、元祐体、江西体)的普遍现象”,[9]4从“不立文字”到“不离文字”的渐进过程,以上两处也为北宋诗僧借助文字进行题画诗创作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与实践指引,如惠洪、祖可、善权、道潜等,借助“文字禅”的推广与普及创作了大量的题画诗,实际也是“以诗说禅”的重要表现形式,这里“文字禅又可称为文字般若,是悟空的方便法门,即通过文字翰墨获得精神解脱”,[11]159其中“文字禅”是宋代禅宗的基本形态之一,使语言文字获得了合法地位,真正实现了“不离文字”。元好问《答俊书记学诗》:“诗为禅客添花锦,禅是诗家切玉刀”,[12]394禅僧向诗者借得诗境,以诗歌的形式、语言来阐发禅义、禅理以及禅之体验,而在“文字禅”的推动之下,北宋诗僧的题植物画诗创作呈现出多种题材、多域指向、多重意蕴的诗歌、绘画、禅理以及自然植物之间的横向融通的发展趋向。明代释达观《石门文字禅序》:“盖禅如春也,文字则花也。春在于花,全花是春;花在于春,全春是花。而曰禅与文字有二乎哉”,[2]1以“禅”喻“春”,以“字”喻“花”,两两结合,双向互通,说明禅理、禅意与文字存在着同一性,同时又把“禅”与“字”、“春”与“花”(评论佛事,则花是文字,春是禅[13])二元对立的传统宗教观念进行沟通、调和,南宋严羽《沧浪诗话·诗辩》评曰:“学汉魏晋与盛唐诗者,临济下也。学大历以还之诗者,曹洞下也。大抵禅道惟在妙悟,诗道亦在妙悟”,[14]12同时“禅悟与艺术思维有共通性”,[15]329这就造成了诗歌、绘画、禅理以及植物意象在不同维度下、不同领域下的一种相对平衡状态,而将四者有机结合起来的诗学典范,便是诗僧笔下创作的题植物画诗。如惠洪《琛上人所蓄妙高墨戏三首·并序》:
淮上琛上人,袖妙高老墨戏三本来,阅此,不自知身在逆旅也。妙高得意懒笔,而琛公能蓄之,琛之好尚盖度越吾辈数十等也。为作三首,结林间无尘之缘。
年年长恨春归速,脱手背人收拾难。那料高人笔端妙,一枝留得雾中看。
修叶闹花增秀色,为谁幽径撒秋香。还如此老行藏处,不为无人亦自芳。
一幅湘山千里色,碧天如水盖秋宽。磨钱作镜时一照,乞与禅斋坐卧看。[2]1023
序言:“淮上琛上人,袖妙高老墨戏三本来,阅此,不自知身在逆旅也。妙高得意懒笔,而琛公能蓄之,琛之好尚盖度越吾辈数十等也。为作三首,结林间无尘之缘”,[2]1023说明诗僧惠洪借用淮上琛公所珍藏花光仲仁之墨梅来抒发自己敬佩琛公的喜好,歆慕花光画艺,为此希望能够结识有缘之人。这三首题画诗“那料高人笔端妙,一枝留得雾中看”、“修叶闹花增秀色,为谁幽径撒秋香”、“一幅湘山千里色,碧天如水盖秋宽”,通过“笔端妙”与“雾中看”说明画技之高超,“增秀色”与“撒秋香”说明画意之丰满,“千里色”与“盖秋宽”说明画境之辽阔。因为“妙高得意懒笔”,让画中的梅花因为细致雕刻而栩栩如生,笔下的梅花因为“文字禅”的延展而惟妙惟肖,“文字禅”将语言文字的功能发挥得淋漓尽致,把禅宗的澄心观照融入诗歌与绘画中的梅花意象,从而突破了常形、常理的限制。又如“不为无人亦自芳”、“乞与禅斋坐卧看”里的“坐卧看”就是以禅观画的例证,以禅意、禅趣来助诗兴,又通过创作题植物画诗衬映出禅味,这里“诗画与禅学的沟通,实际上是由宗教的觉悟走向艺术表达的过程,禅宗的‘游戏三昧’为文人‘墨戏’提供了充分的理由”,[11]159使墨梅意象通过“文字禅”的助推得到进一步的文字铺展与文学演绎。
李泽厚先生《中国古代思想史论》指出:“禅宗非常喜欢讲大自然,喜欢与大自然打交道。它所追求的那种淡远心境和瞬刻永恒,经常假借大自然来使人感受或领悟。”[16]193诗僧创作的题植物画诗会比其他文士增添一些禅意、禅境、禅机、禅趣,而通过文字化、书面化的禅语以及禅意的直接诠释,从而在客观创作实践的层面,开拓出一条勾连“诗”、“禅”的重要途径。譬如诗僧的笔端下,经常会出现“道人”:“道人三昧力”、“径烦南岳道人手”、“道人笔下有春色”,“道人”是指得道之人,或指修道之人。“出家人”即专门求道、修道者,故称“道人”,如《梵志頞波罗延问种尊经》:“佛言:‘我是时亦作道人字阿洫,众人共呼我道为天道。’”[17]878上《大智度论·卷三十六》:“如得道者,名为道人;馀出家未得道、因得道者,亦名为道人。”[18]245中“万象”:“万象回笔端”、“万象难逃笔端妙”,“万象”是指宇宙内外一切事物或现象,如《成唯识论·卷十》:“言含万象,字苞千训。妙旨天逸,邃彩星华。幽绪未宣,冥神绝境。孤明敛暎,秘思潜津。”[19]110下《华严策林》:“非我离于情想,无缘绝于贪求。收万象于目前,全十方于眼际。”[20]597上《古尊宿语录·卷二十四》:“寂寂无一事,醒醒亦复然;森罗及万象,法法尽皆禅。”[21]291下“禅斋”:“禅斋长伴炉烟袅”、“乞与禅斋坐卧看”,“禅斋”是指禅室、禅房,佛徒习静之所,如《释氏要览·卷上》:“中阿含经云:‘佛入禅室燕坐。又有呼为禅斋,斋者,肃静义也……’”[22]78《五灯会元·卷三》:“贞元十一年憩锡于池阳,自建禅斋,不下南泉三十余载。”[23]137“幻出”:“幻出随意现”、“幻出陇首春”,“幻出”即呈现之意,带有一定虚无缥缈、空幻不实的色彩,又寄寓着禅师“空花幻出”之观念,如《妙法莲华经玄义·卷四上》:“此则从心幻出业,幻出见思,幻出无知,幻出无明。”[24]723中《宗镜录·卷九十七》:“身从无相中受生,由如幻出诸形像。”[25]937下“不死”:“万年不死之乔松”、“好在一枝长不死”,“不死”指永生不死的境界,译作甘露,又涅槃称不死,从本不生,今亦不灭,故曰“不死”,如《胜天王般若波罗蜜经·卷六》:“总持如妙药,能疗众惑病。犹彼天甘露,得者永不死。”[26]720下《大萨遮尼干子所说经·卷五》:“布施法者,后得不死甘露法药。”[27]339中《大方广佛华严经·卷五十九》:“菩提心者,则为甘露,能令安住不死法故。”[28]776中《大般涅槃经·卷二十六》:“甘露之性令人不死,若合异物亦能不死。”[29]521上此外,还涉及“尘寰”、“无尘”、“僧坊”、“拥衲”、“道眼”、“三昧”、“心净”、“造物”、“天机”、“无期”等语词,以禅心观画,以禅语题诗,让诗画明显蕴含禅意,这些词汇表现出作者的禅宗意旨、禅修见解乃至禅悟意境等重要内容,使得北宋诗僧的题植物画诗显示出浓厚的“诗禅互通”创作倾向。
北宋诗僧的题植物画诗会经常出现“作诗”、“诗成”、“诗笔”、“新诗”、“笔端”、“援笔”、“谁写”、“写出”等词汇,凭借“文字禅”的媒介作用,也让题画诗创作既体现出“诗禅相通”,又体现出“诗画相通”。如祖可《书秦处度所作松石》:“怜君作诗自无敌,游戏诗余画成癖”[3]14611,祖可认为绘画不仅是“诗余”,而且是“游戏”,通过后续题写,虽未见到真画,但是让秦湛的松石跃然纸上。惠洪《法云同王敦素看东坡枯木》:“为君援笔赋新诗,诗成一笑尘寰小”,[2]244惠洪与王敦素共同欣赏苏轼《枯木怪石图》,在据画题诗后,作者觉得尘世万物包含在这题画诗之中,透过文字即可窥见画境、诗境已经融为一体,画之空灵与充实,诗之灵动与传神,让作者能够“放神八极,逸想寄尘寰外”。[30]32《次韵张敏叔画桃梅二首》其一:“好在一枝长不死,谩烦诗笔扫烟云”、[2]1032《次韵张敏叔画桃梅二首》其二:“暗香错莫知谁写,多谢黄昏一阵风”,[2]1032惠洪为张敏叔(宋人,工画花木,存世《名花十二客》)画桃、画梅题写,“诗笔”说明庆幸还有梅花没有凋零,可以让自己用笔墨表现乐于归隐山林的生活意趣。“谁写”说出正是傍晚的一阵及时风,让我们知道即使白雪皑皑,也无法阻隔清淡梅香,寂寞冷落更消蚀不了梅花的高洁品质。“‘文字’是诗与禅最终融合的唯一中介”,[9]159通过题画诗的语言文字载体,禅师以诗明禅,了悟个中机缘,“诗禅的双向渗透更成为有理论指导的自觉实践”,[9]159“正是诗家和禅家对文字形式中抽象精神(句中之眼)的共同追求以及诗家语和宗门语在表达形式上的相似性,才使得诗与禅融合的可能性最终转化为现实性”,[9]159如祖可《墨梅》:“一枝无语淡相对,疑在竹桥烟雨边”,[3]14611“无语”意谓梅花的寂静无声,但是通过画笔的初次描绘以及墨笔的再次描刻,不仅让梅花凸显“春妍”,更是透过淡淡暗香而寻觅到梅花在“烟雨边”的踪迹。又如祖可《咏秦处士作枯松》:“秦郎真是旧摩诘,写出崔巍霜雪姿”、[3]14611《书性之所藏伯时木石屏》其三:“胸中定自有此,笔端乃一见之”[3]14611等,诗句里“写出”、“笔端”等,应不是题写的意思,而是用画笔绘出,只是借用“写出”、“笔端”等词汇,让画之“写”和诗之“写”二者达到进一步的混融,力求实现一种笔意层面的诗画融通。
又如惠洪《法云同王敦素看东坡枯木》:
此翁胸次足江山,万象难逃笔端妙。君看壁间耐冻枝,烟雨楂芽出谈笑。想当却立盘礴时,醉魂但觉千岩晓。恨翁树间不画我,拥衲扶筇送飞鸟。并作玄沙息影图,禅斋长伴炉烟袅。王郎自是玉堂人,风流合受莺花绕。何为爱此枯瘦蘖,嗜好果超凡子料。为君援笔赋新诗,诗成一笑尘寰小。[2]244
“万象难逃笔端妙”,如苏轼《次韵僧潜见赠》:“道人胸中水镜清,万象起灭无逃形”,[21]880《次韵吴传正枯木歌》:“东南山水相招呼,万象入我摩尼珠”。[31]1962“并作玄沙息影图”,据任渊《黄山谷年谱》注《题伯时画观鱼僧》曰:“子瞻画枯木,伯时作清江游鱼,有老僧映树身观鱼而禅,笔法甚妙。予为名曰《玄沙畏影图》,并题数语云”,[32]212“禅斋长伴炉烟袅”,如宋祁《善惠大师禅斋》:“丈室传心地,安闲岁腊赊”,[3]2372张方平《禅斋》:“顿悟红炉一点雪,忽惊闇室百千灯”,[3]3853惠洪题植物画诗多次出现“万象”、“禅斋”、“拥衲”等佛教语词,又借助苏东坡《枯木怪石图》(《木石图》)的申补与临济宗黄龙派之“文字禅”的延展,看似仅仅是佛教术语的直接引入,其实也代表着一种佛教话语形式以及语境系统在北宋诗僧题画诗创作活动中的有意建构,其创作题材不仅涉及山水、花鸟(动物、植物、动植物)、人物等传统画科,还出现大量的以寺庙、寺僧、佛像为描绘对象的题画诗。画幅蕴含禅意,诗歌展现禅理,画入禅境,诗化禅机,让惠洪进一步意识到以诗续画,以画助诗,再结合禅理、禅典以及禅语的催化,就是实现诗、画、禅融通的重要方式之一。而“画与禅的会合,出现绘画的禅化与禅的绘画化,以禅入画,以画说禅,画与禅相互影响,相互渗透,呈现双向交流的特征”,[33]161诗歌“既是抒情的(心、志),又是审美的(精、美);既是听觉的、音乐的(言、声)艺术,又是视觉的、造型的(书、画)艺术”,[15]13于是“据画题诗”就成为惠洪实现“明心见性”的重要途径之一。画境与禅境、画意与禅意,诗境与禅境、诗意与禅意的双向交流,“以诗颂说禅的‘文字禅’倾向,是连接宋代禅与诗关系的重要桥梁”,[15]13其本质是通过题诗点明禅意,申补画外禅语,借此参悟禅机,万缘随心运转,清净自性本心,非常自然贴切地把诗情、画意、禅味融贯起来……
综上,吴企明先生《诗画融通论》具体指出禅学思想在“诗画融通的交汇点上所发挥的审美观照和妙悟的作用”[33]153是非常重要的,并直接导致了“诗画艺术融合禅意后出现的审美新境界”,[33]153而这种以“文字禅”为媒介的整体空间结构,第一是基础层:诗僧身份(抑或是具有佛教背景的文士);第二是理论层:禅理、禅语;第三是兴味层:禅悦、禅趣,多维立体的组织结构,进一步促成诗、画、禅三者共通起来,形成一种全新的宗教审美范式与审美境界,也成为北宋题画诗写作传统与北宋文艺思想史的重要环节。
注释:
(1)文中所引宋代诗歌如无特殊注明,均选自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编《全宋诗》(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